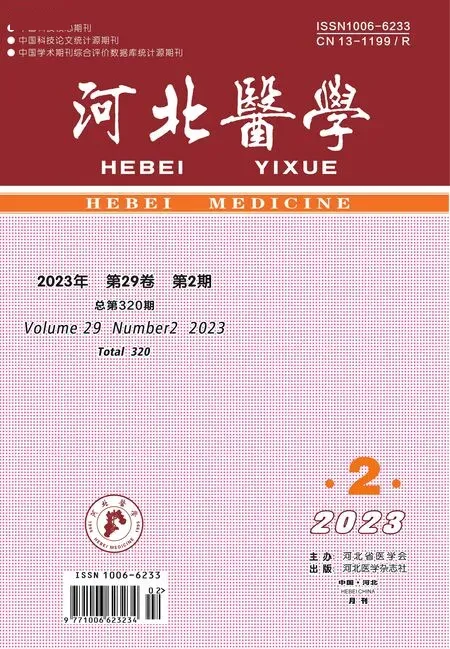sLOX-1 HIF-1α IGF-1對動脈瘤性蛛網膜下腔出血后遲發性腦缺血的預測價值研究
姜海洋, 陳 虎, 張登文
(1.空軍軍醫大學唐都醫院神經外科, 陜西 西安 710038 2.中國人民解放軍聯勤保障部隊第970醫院神經外科, 山東 煙臺 264000)
動脈瘤性蛛網膜下腔出血(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aSAH)是指顱內腦動脈瘤破裂,血液流入蛛網膜下腔引發的征兆,為蛛網膜下腔出血的主要病因,發病急驟,致死、致殘率高[1]。遲發性腦缺血(delayd cerebral ischemia,DCI)為aSAH常見并發癥,也是導致aSAH患者死亡或嚴重殘疾的主要原因之一。aSAH后DCI發生率可達30%,雖然顯微外科的發展使預后得意改善,但仍有約半數患者因此死亡,且存活者多伴隨嚴重后遺癥,生活質量較差[2]。因此,早期預測aSAH后DCI風險,并予以早期干預,對于改善預后具有重要意義。DCI的發生機制尚不明確,目前認為,腦血管痙攣、炎癥反應等因素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3]。可溶性凝集素樣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受體-1(soluble lectin-like oxidized low-density lipoprotein receptor-1,sLOX-1)參與蛋白降解、脂質吞噬等過程,在機體缺氧缺血、炎癥狀態下大量合成,既往研究發現其與缺血性腦卒中有關。缺氧誘導因子-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為機體缺氧狀態下的核轉錄因子,與神經細胞凋亡等諸多病理過程有關[4]。近年來的研究發現,aSAH患者的預后受到神經內分泌功能的影響,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IGF-1)可影響神經細胞的生長、凋亡,且有研究發現其對腦卒中不良預后具有一定預測價值[5,6]。本研究旨在探討血清sLOX-1、HIF-1α、IGF-1水平對aSAH后DCI的預測價值,詳述如下。
1 材料與方法
1.1研究對象:選取我院2019年3月至2022年3月期間104例aSAH患者作為研究對象。aSAH的診斷參照《動脈瘤性蛛網膜下腔出血診治指南》[7]中相關標準:顱腦CT可見蛛網膜下腔出血,并經數字減影血管造影確診。納入標準:符合aSAH診斷標準;發病至入院不超過24h;臨床資料完整;對本研究知情同意且自愿配合。排除標準:入院后2d內死亡者;伴有嚴重的肝腎功能不全者。
1.2DCI診斷[8]:發病4d內出現神經功能缺損體征;癥狀持續1h以上;CT排除顱內再出血、腦積水、腦水腫,同時可見新的梗死灶,符合上述標準即可診斷為DCI。
1.3一般資料收集:收集患者性別、年齡、動脈瘤位置等一般資料。
1.4Hunt-Hess分級[9]:1級:僅有輕微頸強直或頭痛癥狀,或無癥狀;2級:有顱神經麻痹,中重度頸強直、頭痛,無其他神經功能缺失癥狀;3級:輕度灶性神經功能缺失,或處于倦睡、意識模糊狀態;4級:中重度偏側不全麻痹、木僵狀態,或有早期植物神經系統功能障礙;5級:去大腦強直、深度昏迷狀態,瀕死。
1.5臨床指標檢測:均于患者入院時采集外周靜脈血,采用全自動生化分析儀測定三酰甘油(triglyceride,TG)水平,并監測顱內壓(intracranial pressure,ICP)。
1.6血清sLOX-1、HIF-1α、IGF-1水平測定:均于患者入院時采集外周靜脈血,3000 r/min離心15min,分離血清,-80度凍存待檢。采用酶聯免疫吸附法測定血清sLOX-1、HIF-1α、IGF-1水平,試劑盒分別由北京百奧萊博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江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美國R&D生物藥品有限公司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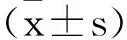
2 結 果
2.1一般資料:104例患者中,男43例,女61例;年齡29~84歲,平均(51.22±10.69)歲;責任動脈瘤位置為前循環90例,后循環14例。根據術后是否發生DCI,將患者分為DCI組和非DCI組。DCI組Hunt-Hess分級、TG、ICP均高于非DCI組(P<0.05),兩組性別、年齡、責任動脈瘤位置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一般資料比較
2.2兩組血清sLOX-1、HIF-1α、IGF-1水平比較:DCI組血清sLOX-1、HIF-1α水平均高于非DCI組(P<0.05),IGF-1水平低于非DIC組(P<0.05),見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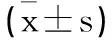
表2 兩組血清sLOX-1 HIF-1α IGF-1水平比較
2.3血清sLOX-1、HIF-1α、IGF-1水平與臨床指標相關性分析:Pearson相關性分析顯示,血清sLOX-1、HIF-1α水平與TG、ICP、Hunt-Hess分級均呈正相關(P<0.05),血清IGF-1水平與TG、ICP、Hunt-Hess分級均呈負相關(P<0.05),見表3。

表3 血清sLOX-1 HIF-1α IGF-1水平與臨床指標相關性分析
2.4血清sLOX-1、HIF-1α、IGF-1水平對aSAH后DCI的預測效能:ROC曲線顯示,血清sLOX-1、HIF-1α、IGF-1聯合檢測對aSAH后DCI具有較高的預測價值,見圖1、表4。

表4 血清sLOX-1 HIF-1α IGF-1水平對aSAH后DCI的預測效能

圖1 血清sLOX-1、HIF-1α、IGF-1水平預測aSAH后DCI的ROC曲線
3 討 論
aSAH發生率和致死率較高,且整體預后不佳,DCI為aSAH常見并發癥,同時也是大致aSAH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通過簡便快捷的實驗室檢查,預測aSAH患者DCI風險,并盡早干預、優化護理、合理配置醫療資源,對于改善aSAH患者預后,降低病死率具有重要意義。
DCI的發生機制目前尚不明確,有觀點認為,動脈瘤破裂后,血液大量涌入蛛網膜下腔,紅細胞裂解產沉積,誘發炎癥反應,對血管內皮細胞造成持續性損傷,引起DCI[10]。sLOX-1為血管內皮細胞攝取過氧化低密度脂蛋白的受體,而過氧化低密度脂蛋白可加重炎癥反應及內皮損傷,參與動脈粥樣硬化發生與發展的病理過程。既往報道發現,aSAH患者后基底動脈壁sLOX-1表達增加,故sLOX-1可能與aSAH腦血管功能障礙有關[11]。本研究結果顯示,DCI組血清sLOX-1高于非DCI組,分析原因是DCI患者炎癥反應刺激sLOX-1大量分泌。進一步的Pearson相關性分析顯示,血清sLOX-1水平與TG、ICP、Hunt-Hess分級均呈正相關,表明血清sLOX-1水平與aSAH病情程度及aSAH后DCI的發生密切相關。HIF-1α是一種具有轉錄活性的核蛋白,其靶基因與炎癥發展、缺氧適應等病理生理過程有關,其通常在缺血缺氧狀態下表達。研究發現,在缺血缺氧性疾病、顱腦損傷中存在HIF-1α異常表達[12]。另有報道顯示,HIF-1α可作為重度顱腦損傷患者近期預后的預測指標[13]。本研究發現,DCI組血清HIF-1α水平高于非DCI組,且HIF-1α水平與TG、ICP、Hunt-Hess分級呈正相關,提示aSAH后DCI患者伴隨HIF-1α表達上調。
除了腦血管痙攣、炎癥反應之外,近年來的研究發現aSAH患者的預后還與其心血管、神經內分泌功能狀態有關。腦出血會對下丘腦、垂體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故aSAH患者可能會伴隨神經內分泌功能障礙。目前已有諸多aSAH患者神經內分泌功能變化與其預后關系的相關報道,多數觀點認為生長激素缺乏是aSAH后最為常見的一種垂體激素分泌異常,而生長激素主要通過IGF-1發揮作用[14]。IGF-1是與胰島素結構同源的多肽,在機體中的作用也與胰島素類似,具有促進細胞生長增殖、調節糖代謝、創傷修復等多重作用,是對神經元生長至關重要的活性物質。IGF-1參與缺血缺氧性腦損傷的病理過程,具有保護中樞神經細胞的作用,腦出血、腦梗死等疾病急性期伴隨IGF-1表達下降。本研究結果顯示,DCI組患者血清IGF-1水平低于非DCI組,提示aSAH后DCI患者IGF-1表達上調。Pearson相關性分析顯示,血清IGF-1水平與TG、ICP、Hunt-Hess分級均呈負相關,證實IGF-1與aSAH病情及aSAH后DCI相關。ROC曲線顯示,血清sLOX-1、HIF-1α、IGF-1單獨及聯合預測aSAH后DCI的敏感度/特異度分別為87.10%/79.50%、90.30%/83.60%、83.90%/79.50%、96.80%/78.10%,對應的AUC分別為0.894、0.920、0.886、0.975,證實血清sLOX-1、HIF-1α、IGF-1聯合檢測對于aSAH后DCI具有較高的預測價值。
綜上所述,sLOX-1、HIF-1α、IGF-1與aSAH后DCI的發生有關,aSAH后DCI患者伴隨血清sLOX-1、HIF-1α表達上調及IGF-1表達下調,三項指標聯合檢測對于aSAH后DCI具有較高的預測價值,臨床中對于aSAH患者可監測上述三項指標變化,以評估aSAH患者病情,預測DCI發生風險,并予以早期干預和優化護理。本研究納入樣本量有限,未來尚需進一步擴大研究范圍,以得到更客觀準確的結論,并對sLOX-1、HIF-1α、IGF-1在DCI中的作用機制進行深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