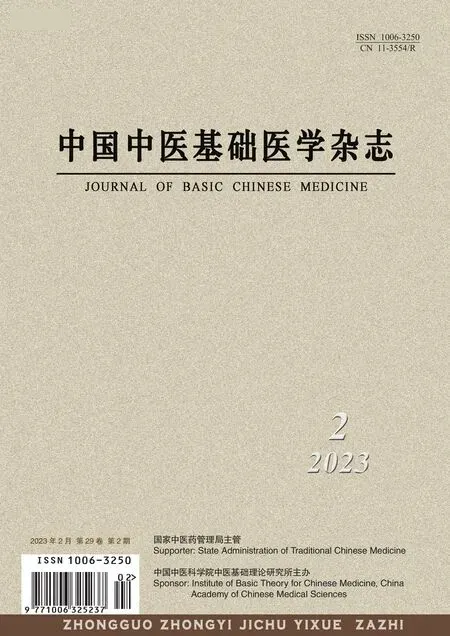副文本視角下《洗冤集錄》翟理斯譯本譯者行為研究?
葉柳倩,曹雨薇,趙 霞
(北京中醫藥大學人文學院,北京 100029)
《洗冤集錄》是人類文明史上第一部系統的法醫學論著,后世所有關于此學科的著作,都以其為藍本[1]。至20世紀初,《洗冤集錄》的國外譯本已有7個國家19種版本,為中國文化外傳做出巨大貢獻[2]。《洗冤集錄》第一個英譯本TheHisYuanLu,orInstructionstoCoroners是英國漢學家翟理斯(Herbert A.Giles)于1873年發表。該譯本在當時得到了西方醫學界人士的認可,被譽為“最有影響,最具權威”的英譯本[3]。譯本中副文本的使用調節譯文語境,使譯文概念清晰、明確,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法醫學乃至中醫學在西方文化中的文化空缺現象,增強了譯文可讀性;對中醫特有意象的闡釋處理,弱化了中醫語言模糊的異質性,提升了文化交流效果。文章通過對譯本副文本深度化語境作用的研究,探討譯者行為以揭示清末中國法醫學典籍翻譯與意識形態的互為關系,譯者的翻譯原則、策略與方法,以及譯本在西方的譯介情況。翟理斯作為前英國駐華外交官、著名漢學家,一生編撰中華譯著繁多,對清末時期的中學西傳以及英國漢學研究產生過重大影響[4],其翻譯策略具有首創性,因此研究翟理斯在翻譯《洗冤集錄》過程中產生的譯者行為也對當下包括中國中醫、法醫典籍等在內的科技典籍外譯傳播有借鑒意義。
目前《洗冤集錄》英譯本研究主要集中于譯本的概覽性評價,如邱玏[3]之譯本的簡評;王惠萍[5]從東方學視角探究翟理斯譯本的翻譯策略;王珊珊、趙霞[6]對譯本中的中醫文化翻譯進行探討。但研究較少從副文本角度關注譯者在翻譯中的積極作用,如譯者翻譯行為對譯本傳播效果的影響,彼時社會歷史文化環境對譯者的影響等。本文旨在從副文本視閾下對《洗冤集錄》翟理斯譯本(以下簡稱翟氏譯本)進行詳實梳理,并從譯者在翻譯活動中體現的主觀能動性和譯者所處的社會歷史文化環境對譯者行為的影響等角度揭示譯者的翻譯行為,為當下中國科技典籍外譯提供借鑒。
1 “副文本”理論概述
早期副文本概念。副文本(paratext)概念最早由法國敘事學理論家熱奈特(Gérard Genette)提出,指那些存在于文本內外“閾限”(liminal)的相關文本,它們包圍并延長正文本[7]。巴切勒(Kathryn Batchelor)分析界定熱奈特副文本概念認為,“副文本包含任何為文本提供評論、將文本呈現給讀者以及影響文本接受的元素。副文本元素既可以以物質形式呈現,也可以以非物質形式呈現。呈現方式既可以附加在文本上(內副文本),如書名、前言,也可以與文本分開(外副文本),如作者訪談、日記等”[8]。
巴切勒進一步發展了副文本概念。巴切勒在綜合分析研究熱奈特副文本的基礎上,發展形成了個人的副文本理念。巴切勒認為考察副文本就是考察譯者行為[8],但以往相關研究多以熱奈特的傳統定義為導向,依據位置來判定副文本元素,用以分析譯者行為。巴切勒認為該定義無法適應翻譯研究的發展,她從功能性視角對翻譯中的副文本重新作了界定,即副文本是為文本“有意識設計”的一個門檻,這一門檻能潛在影響文本的接受方式[8]。
根據巴切勒關于副文本的新定義,副文本元素不再局限于其在文本中的位置,而是依據譯者是否“有意識”設計,因而本研究除了涵蓋常規可見“顯性”副文本,如前言、標題、注釋等,也包含需與原作比較才能發現的“隱性”副文本,如譯者對原作內容選擇性的省譯、不譯等。
2 翟理斯《洗冤集錄》譯本簡介
2.1 翟理斯《洗冤集錄》譯本的中文底本
譯本具有雙重身份——可被視為原作的副文本,也可被視為自身帶有副文本的原文本[9],可見譯本中副文本的產生與原作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性,因此,中文原作在譯本副文本研究中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在本研究中“原作”指在中國典籍文獻整理時的專用術語“底本”,即校勘、翻譯、刊印書籍時作為依據的本子。
《洗冤集錄》自南宋(1247年)成書以來,衍生了多個版本,各有優劣。譯本原文底本的確定,是譯本研究的基礎,否則不僅會對翻譯內容產生偏差,亦不利于對譯本中的譯者行為進行深入研究。隨著時代的發展及各種因素的變化,譯者的翻譯策略注定有時效性以及局限性,但底本是不變的,這就為典籍譯作研究提供了不可動搖的定量依據,因此對譯本的底本考證十分重要。
翟氏譯本的中文底本為清代童濂所刊的《補注洗冤錄集證》(1843)[10],與《洗冤集錄》原作一脈相承,下面對童濂刊《補注洗冤錄集證》的成書過程簡要梳理。
2.1.1 童濂刊《補注洗冤錄集證》與《洗冤集錄》原作一脈相承 康熙三十三年(1964年),由清代律例館校正,朝廷正式頒發《律例館校正洗冤錄》,又稱《校正本洗冤錄》或《洗冤錄》,該本以《洗冤集錄》為主,以王明德《洗冤錄補》為輔,在許多方面繼承了宋慈以后的法醫學成就[10]。
嘉慶元年(1796),王又槐、李觀瀾增補《洗冤錄集證》,其中卷一至卷四是王又槐在《校正洗冤錄》四卷基礎上進行增輯,卷四之后是李觀瀾的補輯[11]。
道光十二年(1832年),阮其新在王又槐、李觀瀾《洗冤錄集證》基礎上增補加注《補注洗冤錄集證》[10]。道光十七年(1837),張錫蕃重刊《補注洗冤錄集證》[11]。
道光二十三年(1843),童濂在張錫蕃版《補注洗冤錄集證》的基礎上進行刪削,重刊《補注洗冤錄集證》[10]。
從以上童濂所刊《補注洗冤錄集證》的成書經過可見,該版本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沿襲《校正本洗冤錄》的內容和體例,但其核心內容包括體例等與《洗冤集錄》一脈相承,是在《洗冤集錄》基礎上,拓展記錄了宋慈以后的法醫學成果,對于揭示中國古代乃至近現代法醫學發展進程具有重要價值。
2.2 譯本特點
翟理斯在其譯本前言指出,因為看到當地中國驗尸官員在案發現場隨身攜帶他現在所翻譯的這本書,才知道《洗冤集錄》的存在,進而對這一階段的中國文明產生興趣,開始研究和翻譯《洗冤集錄》,由此對中國古代法醫學體系有了認識[12]。可見,翟理斯的翻譯目的側重向西方讀者介紹當時的中國文化,并非專業的中國法醫學術研究,其翻譯原則與策略以及副文本的使用體現了譯本翻譯過程中的譯者行為以及典籍的人文特色。
此外,翟氏譯本較少保留原作非正文內容,如原作注釋,王又槐、阮其新等的附記,附考,補注,頂批等,第四卷后增補的四節及附刊《作吏要言》均被略去[10]。并且,翟理斯處理中西方文化差異的翻譯策略獨具特色,例如將原作中不雅內容譯成拉丁文或是刪除,省略原作中介紹人骨、致命部位等含有中國古代解剖學知識的部分等。上述譯者行為與副文本理論相契合,也是本文采用副文本理論研究翟氏譯本的原因。
3 《洗冤集錄》翟氏譯本的“副文本”
在翟氏譯本中,“顯性”副文本包括書名、目錄標題、腳注以及括號,這些副文本共同組成譯本的體例框架,是讀者能直觀可見的存在,影響讀者對譯本的第一印象和閱讀方式;“隱性”副文本包括翟理斯對原作不雅內容的刪除、中醫特有意象的隱藏以及中國古代解剖知識的略化等,這些副文本是讀者需與原作相比較才能發現,這一策略潛在過濾讀者的閱讀內容,影響讀者對譯本的接受方式。
3.1 “顯性”副文本
3.1.1 書名 書的命名,具有總括全篇,點明主旨的作用。翟氏譯本的書名為“TheHisYuanLu,orInstructionstoCoroners”(洗冤錄或驗尸官指南),其中前半部分“His Yuan Lu(洗冤錄)”為原作書名的本體,采用的是音譯(零翻譯)策略,無附加信息含義;而后半部分“Instructions to Coroners(驗尸官指南)”便是對書名本體乃至譯本內容的補充說明,與底本的實用功能相契合。
據翟氏譯本前言所示,因當地官員驗尸時隨身攜帶的童濂刊《補注洗冤錄集證》給翟理斯的深刻印象,才引發其翻譯研究《洗冤集錄》的興趣,由此可推測翟理斯選用該書作為譯本的中文底本是具有偶然性的。且作為清末時期來華外交官,翟理斯更傾向于通過譯本向西方讀者介紹當時中國的法醫文化,因此譯本書名采用了音譯策略,通過譯音代義的方法,保存源語的語言特色,傳遞源語文化,但同時也阻礙了原文符指和符釋的傳遞。為了彌補音譯策略在傳遞信息上的弱勢,且受譯本底本對當地官員驗尸的實踐指導作用以及當時英國流行的“實用主義”影響,翟理斯沒有進一步闡釋“洗冤”的實際含義,而是增加“Instructions to Coroners”,作為譯本功能性的補充說明,使譯名與底本實用功能更加貼合。
翟氏譯本的譯名與1981年出版的美國教授馬伯良(Brian E.McKnight)《洗冤集錄》譯本(以下簡稱馬氏譯本)有較大差異。馬氏譯本書名為“TheWashingawayofWrongs:ForensicMedicineinThirteenth-centuryChina”,意為“洗除錯誤:十三世紀的中國法醫學”,書名前半部分“The Washing away of Wrongs”對原作書名本體“洗冤”采用直譯,保留了原作書名的文化內涵,后半部分“Forensic Medicine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十三世紀的中國法醫學)”則表明了譯本內容的主旨。
馬伯良作為中國史教授,具有較強的學術翻譯動機,即為了研究中國十三世紀即宋代法醫學的發展狀況,因此譯名后半部分體現的譯文主旨與他本人的翻譯初衷相合。并且為保證學術的嚴謹性,在《洗冤集錄》宋刻本已失的情況下[10],馬伯良選用的中文底本是現存與《洗冤集錄》原版最為接近的元刊版[13],同時為保證學術的客觀性,清楚地傳達原作內容,該譯本書名采用意譯策略。
通過比較以上兩個版本的譯本書名可知譯者個人背景和翻譯動機對譯本書名有重大影響,雖然兩者都是前半部分書名本體,加后半部分內容補充說明的組合模式,但因為采取的翻譯策略不同以及譯文內容主旨差別,導致最終呈現的結果截然不同。
3.1.2 目錄標題 翟氏譯本共有四大章,每章下各有幾個小章節。在翟氏譯本中,翟理斯把本應譯為“chapters”的大章譯作“books”,把本應譯為“sections”的小章節譯作“chapters”[14],并在前兩個大章前都設置了相應的小目錄,非常特別。究其原因是翟理斯在譯本翻譯過程中受到底本框架體例的影響。童濂所刊的《補注洗冤錄集證》共由四冊書組成,每冊書前都有目錄,因而“book”指代每冊書,“chapter”指代書中各個章節。
此外,通過觀察對比譯本中兩個小目錄的標題與正文部分相對應的標題,發現兩者的譯文并不完全統一,例如同是對“辨四時尸變”這一標題內容的翻譯,小目錄標題為“decomposition of body at different seasons”,正文部分標題為“decomposition different at different seasons”;類似的還包括“examination of decomposed corpses(已爛尸)”與“examination of a decomposed body(已爛尸)”等,反映出翟理斯翻譯的隨意性。相較于目錄對正文內容的導向性功能,翟氏譯本中小目錄的出現更傾向于譯者把底本目錄當成一個正式文本來翻譯,目錄和正文沒有從屬關系。
另一方面,盡管在譯本后兩大章節中并無小目錄的設置,但仔細對比譯本和底本內容可發現,翟理斯把底本后兩大章節的目錄標題轉到相對應的譯本正文內容中,同時增加了底本正文內容中沒有出現的小標題,如在“Miscellaneous Remarks on Wounds(尸傷雜說)”篇中,有Hunger(餓死)、Catching Cold(傷寒)等點明死者死因的小標題,同時依據底本書眉上的頂批,正確劃分了相應的驗尸小節,使讀者查找閱覽起來更加直觀便利。
綜上可得,翟氏譯本的目錄標題設置,體現出底本的框架體例對譯本的內容設計有較大影響。同時,翟理斯通過將底本的副文本元素轉移至譯本正文中的形式轉換的方式,達到保留原文內容且使譯本格式符合譯語讀者閱讀習慣的目的,亦為當下典籍外譯時,由文言文格式的中文文本轉化為現代文格式的中文文本的方式提供了借鑒。
3.1.3 腳注 翟氏譯本僅使用六處腳注對譯文進行補充說明,原作中前人遺留的批注全部省去,最大程度地弱化譯本中“他者”的存在感。相似的翻譯行為也可在翟理斯翻譯的《聊齋志異》譯本中見到,除極少數例外,翟理斯在絕大多數篇目中都對“異史氏曰”棄之不譯[15],而這些翻譯行為的發生是由于翟理斯受到當時英國社會文化意識的影響。19世紀中后期的英國小說,總體上已擯棄了18世紀歐洲小說形成時期“敘述者”在文本前面、中間或結尾處的插入式點評[16]。由此翟理斯遵循英國小說主流敘事模式,刪改譯本使之符合譯語讀者的閱讀習慣。
3.1.4 括號 受上述社會文化意識因素影響,括號在翟氏譯本中出現了58次,主要有三種作用:補充說明,省略概括以及標明原文小字注疏。
補充說明主要用于補充原文中被省略的有意義的詞匯或短語,或是用于說明中國特有文化負載詞,目的是使譯文更準確地傳遞原文思想,方便譯語讀者理解,如在例1[12,17]中,翟理斯根據自己對于中國武器“抓子”和“流星”的認識,在括號中將其分別具體描述為“holding a sharp iron rod pointed like a pencil”,和“a piece of iron at the end of a string ”,便于譯語讀者對其進行具象化理解,亦使譯文更加完整通順。
例1.原文:……有鐵尺、金剛鐲、抓子、流星等類。
譯文:…as life-preservers, knuckledusters, iron hands [holding a sharp iron rod pointed like a pencil], shooting stars[i.e.,a piece of iron at the end of a string ]…
省略概括主要用于概括原文中譯者持有懷疑態度的篇章內容,目的是在保留原作整體框架的前提下,避免譯語讀者接收錯誤信息,如例2[12,17]中,翟理斯選擇省略原文列出的具體致命部位,將其籠統地概括為含義模糊的總數,規避了中西方文化對于人體解剖概念的差異。
例2.原文:一仰面致命(共十六處),頂心……腎囊(婦人產門,女子陰戶);一仰面不致命,兩眉……十指;一合面致命(共六處),腦后……腰眼(左右);一合面不致命,發際……
譯文:[Sixteen vital spots are enumerated on the front of the body,and six on the back; thirty-six non-vital spots on the front,and twenty on the back.]
括號標明原文小字注疏,特指括號中的內容為原文正文中的小字部分。例3[12,17]原文中的括號內容便為原作正文中的小字注疏,對前文起著補充說明作用,加強文章的可讀性和易讀性,保留此內容對譯文有相同作用。
例3.原文:……其傷痕處有紫赤暈(磕傷無暈,毆傷有暈)。
譯文:…will have a purple and red hole.[Wounds from knocking against things have no halo;those from blows have.]
以上括號的諸多用途體現出翟理斯以功能為導向的翻譯策略,但有些作用,如省略概括等,由于譯者過濾掉其認為不適合的信息,人為導致部分信息在傳播中被丟失,而讀者只能無意識地被動接受。例2被省略概括的中醫“致命之處”有許多已經被現代醫學所證實,如頭骨的囟門,枕骨及頸部區域,胸骨的上下部位,會陰部及陰囊等[1],而這些信息被統一概括成數字,造成有效信息損失。
總而言之,上述翟氏譯本“顯性”副文本透露出影響譯者行為的各種因素,例如直觀的書名設置,體現譯者個人翻譯動機對譯本命名的影響;譯文小目錄以及標題的設置,展現待譯底本版本體例對譯者設計譯本框架的影響;刪除原作中前人的批注,表現譯者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對其譯本風格模式的影響;括號的設置,顯示出功能導向的翻譯策略對譯者行為的影響。這些因素促成譯本體例框架的形成,間接影響讀者對譯本的第一印象以及閱讀方式。
3.2 “隱性”副文本
3.2.1 不雅內容的刪除 在翟氏譯本中,翟理斯將其認為不雅的內容(例如檢驗婦女尸的部分)翻譯成拉丁文或直接全部刪除[13],又或是以一言蔽之,例4[12,17]中,翟理斯將“玉莖、產門”這兩個生殖器官名詞替換成“any part of the body”,類似的處理還有將“糞門”以字符“&”代替。該翻譯行為體現出翟理斯深受當時重視社會道德教化的英國維多利亞時代背景影響。
例4.原文:不可令仵作人等遮蔽玉莖、產門之類,大有所誤。
譯文:[Do not let the assistants intercept your view of any part of the body,as this would be a very serious hindrance.]
虔誠信教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一個重要標志。19世紀主導英國宗教界的是對道德生活、秩序、紀律等過分苛求的福音主義[18]。從譯文上看翟理斯是其教義的踐行者,并且這種翻譯行為也在他的其他譯作中多有出現,如翟理斯《聊齋志異》譯本中,刪改原作內容,規避或剔除了原文中涉及血腥、生殖、性事等在他看來“不潔”的內容[15]。出于對當時大部分英國受眾接受品位和審美取向的考慮,采取該種翻譯策略也是順勢而為之。
3.2.2 中醫特有意象的遮蔽 《洗冤集錄》作為一部古代法醫學著作,蘊含豐富的中醫學知識,翟理斯基本上采用歸化翻譯,意圖使西方讀者理解陌生的中醫學術語[5],但也因此遮蔽了部分中醫特有意象,如“氣”“血”等。
例5.原文:生前受打,氣絕血聚成傷害,人之血附氣而行氣,既壅而血亦壅故堅硬。
譯文:But where the blows were given before death,the blood congeals into a wound there where vitality ceases-[i.e.,at the spot struck]. Now the blood is dependent for its motion on vitality;if vitality stops,the blood stops also-hence the hardness.
例6.原文:……其人已死血氣不行,其痕無血廕。
譯文:…because the man is already dead and circulation has stopped,there will be no subcutaneous appearance of blood.
例5[12,17]原文實際反映了中醫氣、血之間的重要關系,即氣能生血、行血、攝血,血能生氣、載氣,這是中醫最基礎的理論之一。翟理斯在譯文中將“氣”直接闡述為一種“vitality(生命力)”,盡管這與氣在中醫學中的基本概念,即氣是構成人體和維持人體生命活動最基本物質較為相符,但“氣”的含義復雜多元,翟理斯為了使句意更加清晰易懂,往往根據語境對“氣”做不同處理,沒有將“氣”的本質闡述明白,導致“氣”本身意象的隱藏,在例6[12,17]中,翟理斯直接用“circulation(血液循環)”代替“血氣”的含義,致使中醫“氣為血之帥,血為氣之母”的整體概念在譯文中沒有顯現。
事實上,由于19世紀正處于西方對中國態度由仰視、平視轉變為俯視的時期,西方中心主義盛行,翟理斯想要把處于弱勢文化的中國作品向西方強勢文化順利輸出,就不可避免受到當時社會歷史語境的影響,對原文取舍,譯本傳播策略等方面更側重西方讀者受眾,使譯本更容易被譯語讀者接受。
3.2.3 中國古代解剖知識的略化 《洗冤集錄》的主要內容不僅包括各種尸傷檢驗和區分方法,還有解剖知識,其中“論沿身骨脈”篇采用大段文字專門介紹了中國古代人體骨骼。由于當時西方解剖學發展水平高于中國,翟理斯僅用一句話“A mere list of bones”將這段內容省略概括,表現出對當時中國解剖學知識懷疑的態度。
西方解剖學發展至十九世紀,人體解剖的全部細節幾乎已經弄清楚了[19]。反觀中國解剖學史,雖然解剖行為的發生最早可追溯至商紂王時期,至宋代也出現過如《歐希范五臟圖》和《存真圖》這樣的解剖佳本,但之后便無任何太大發展,即便中醫的骨骼知識較全,也存在多處錯誤[20]。翟理斯對中醫解剖學持有懷疑態度,在盡量保證譯本框架完整的前提下,選擇將存疑內容略化,以避免譯文誤導讀者。
以上這些“隱性”副文本表現出譯者順應當時社會文化歷史環境的翻譯行為特征,例如在當時英國嚴格禁欲的清教氛圍下,刪除回避原文的不雅內容;在西強中弱的文化形勢下,犧牲原文特有意象,使用歸化翻譯的策略;順應當時西方解剖學水平高于中國的事實,略化原文存疑內容。這些“隱性”副文本以不易察覺的方式,影響了讀者對譯本的接受。
4 啟示
在一個多世紀里,翟氏譯本是《洗冤集錄》權威性的譯本,盡管到1981年被馬伯良基于現存最早的元代版本為底本的譯本所取代[1],但依然不能否定翟氏譯本的價值。翟理斯作為中國法醫學典籍英譯領域的開拓者,所采取的翻譯策略具有首創性,為后來的譯本提供了參考模板。雖然其著作因缺乏“技術性的細節”被后世學者詬病,但其清晰易懂的特點為所有階層的人提供了入門讀物[4]。除去翟譯本中某些醫學的誤譯,譯本副文本體現的以功能為導向的翻譯思路,為今天的中華典籍外譯提供了實質性經驗。對翟氏譯本的研究需從歷史角度認識譯本在當時的成功及其價值,抓住定量,借鑒其優點,發現變量,結合所處時代社會文化環境特點闡釋譯者行為、譯者與語言及社會歷史環境之間的多重變量關系。
4.1 社會時代環境影響譯本內容
在翟氏譯本中,有諸多“隱性”副文本,包括不潔、存疑內容等,這是囿于當時社會歷史文化環境影響,由特定時代因素所導致。隨著時代發展,相關因素早已發生改變。很多因時代技術限制而存疑的部分已經被現代科學技術所證明。因此對于目前的典籍外譯來說,某些尚難界定內容也應在標注明白的前提下翻譯,保留,尊重讀者接收對等信息的權利。世界逐漸融合成一個包容多元的大社會,求同存異便是當今社會的共通主題,中華典籍外譯要順應這一趨勢,自信展現中華文化魅力。
4.2 譯者動機決定原文底本選擇
原文底本體現譯者翻譯目的與翻譯策略。從副文本角度看,除了譯介中國文化外,翟氏譯本“顯性”框架設置顯示出底本的模板作用,包括影響譯本的目錄標題設計等。《洗冤集錄》的衍生版本眾多,歷史上曾經發生過把《律例館校正洗冤錄》當成《洗冤集錄》原本研究的情況[21],因此確定待譯底本非常重要。翟理斯曾因為其選用的中文底本非《洗冤集錄》原本,而被認為其譯本根本靠不住等的評論。但從譯者個人翻譯動機看,翟理斯的翻譯目的是向西方讀者介紹實用的法醫學著作以及清末中國法醫學體系。清末時期法醫學的發展水平明顯高于宋代,童濂刊版也為當時《洗冤集錄》的最新版本[1],因此是合理的。不足之處是未能在譯本前言或是他處標明童濂刊版與原底本的區別。
4.3 譯者文化屬性影響翻譯策略
在翟氏譯本中,翟理斯站在來華外交官的立場,以西方讀者為第一翻譯導向,為達到使讀者理解句意的目的,在犧牲部分原文特有意象的前提下使用歸化翻譯策略。而在當今時代,與西方文化的輸入相比,中國文化的輸出仍顯弱勢,與當年“中學西傳”的境況有相似之處,只是譯者主體從西方傳教士轉變為中國學者。中國譯者在傳播中華典籍時應做好譯介主體的角色轉變,追求翻譯的文化對等,既要以平等的身份傳達中華文化,保證典籍中中國特有意象的完整性,也要考慮西方受眾的接受程度。
4.4 副文本賦予譯文更多交流能量
在翟氏譯本中,“顯性”副文本不僅解決了由于語言轉化而產生的意義遮蔽問題,保留了原作的體例信息特點,而且使中華文化專有項能在譯語文化中得到體現;“隱性”副文本則淡化了文化禁忌,弱化了文化差異,減少了文化沖突,加強了譯文可讀性。兩種副文本雖一個在做加法,一個在做減法,但都賦予了譯文更多的交流能量。
5 結語
翟理斯《洗冤集錄》譯本采用多種“顯性”和“隱性”副文本策略,是法醫學典籍英譯的首創之作。盡管因缺乏“技術性的細節”而受到后世學者們的詬病和批評,但不可否認其在當時為“中學西傳”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為后來的馬氏譯本及其他中醫、法醫學典籍外譯提供了應用實例,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研究譯者的翻譯行為及其影響因素對當下中華典籍外譯具有重要借鑒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