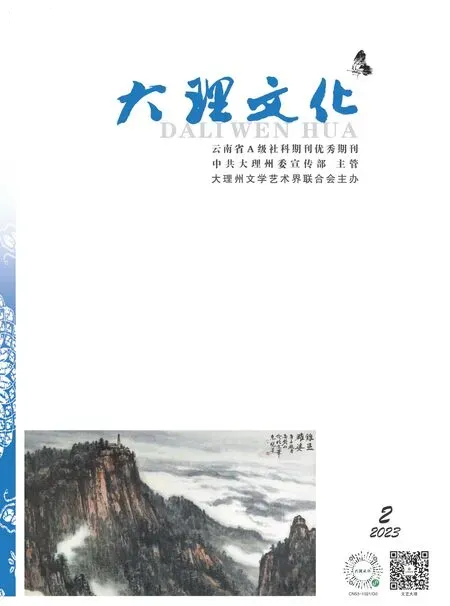情系空谷蘭(外一篇)
●原因
2021年在京期間,曾攜內子到昌平一家養老機構看望張長老師。從網絡查有關資料得知,這是一家較為高檔的養老機構。吃的是小湯山供給的有機蔬菜,看病有定點的掛鉤醫院,并且可以由專車接送,各方面條件都還不錯。但從平日與張老師的電話或微信聯系中,知道他雖然有家人經常探望和體貼關心,卻因深陷于對昆明生活和云南朋友的懷念而常常感到孤寂落寞。
由于是疫情期間,養老院不讓我們進入,只是電話通知張老師到大門口與我們相見。不一會,張老師就出現在我們等待的視線里:在一個陪護人員的陪同下,他一步一步慢慢地走著,步履蹣跚,及至來到我們面前,只見他頭發蓬亂,臉色蒼白,神情委頓,明顯比往日瘦了很多。這就是往日動作利索精干、面容清朗、目光明澈的張老師嗎?這就是前兩年還雄心勃勃地對我說,想在有生之年再完成一部長篇小說創作的張老師嗎?老和病對于一個人的改寫,真是既不可思議又無可奈何,讓人凝噎。
保安找來了一條板凳讓我們坐下。張老師說:“老是頭暈,是頸椎的毛病。”我說:“張老師多保重。”然后就彼此相望,默然不語。幾十年的亦師亦友,分別四年,藏了一肚子的話,卻于見面時兩人都不知從何說起。
那天張老師給我的感覺是,這個才華橫溢、筆下著作也曾名震四方的人,老了!老得像一本發黃的線裝書,老得像一株深秋的梧桐樹!心中不禁暗暗祈禱:愿他長命百歲!
然而,既在規律之中又在我的愿望之外,一年后張老師終因患病多年于北京辭世,消息在一個陰晴不定的早晨傳到云南,聽聞后不勝悲慟。記得柳宗元在《吊屈原文》中說過這樣一句話:“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仿佛其文章。托遺編而嘆喟兮,渙馀涕之盈眶。”是的,今后是再也看不到張老師的容貌了,但閃現著他身影的他的文章仍在。近日捧讀他贈我的《張長文集》,不禁淚水盈眶,一些往事也于悲痛之余慢慢浮上腦際。
與張老師結緣,是從投稿開始。事情大約發生在1983年年初,當時我大學畢業才幾個月。那時候,為了不讓新工作單位對我產生不務正業的印象,我化名“毛毛”用妻子的工作地址向《邊疆文學》投寄了一組散文詩。稿件很快就獲得刊登。責任編輯就是當時擔任這份刊物詩歌散文編輯組組長的張長老師。素昧平生的他,還給我發來了一封參加《邊疆文學》創作班的邀請函。由于無人頂替自己承擔的教學任務,我沒能參加筆會,也沒有機會在較短時間內向張老師告知情由。后來,有機會與張老師見面了,他問我認不認識大理州有一位叫毛毛的作者。我說那就是我,張老師先是有點驚愕,繼而撫掌大笑后說:“你的作品風格柔美,我還以為是個女作者呢。”就這樣,在親切自然的氣氛中和張老師認識了。張老師那次編發的雖然不是我的處女作,但是分量比較重,對我堅定走文學創作道路起到舉足輕重的鼓舞作用。那是完全無私的幫助,我至今銘記在心。
以后和張長老師的接觸逐漸多了起來。
第一次較長時間的相處,是1986年和張老師一起去哈爾濱參加中國散文詩學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途經北京并作短暫停留期間,他帶我去看望馮牧,拜訪劉心武(劉先生出差在外,只見到了他夫人)。在哈爾濱開會和到松花江邊、大興安嶺采風時,他攜我致敬艾青,并介紹我認識劉湛秋、柯藍、郭風等文壇大家。張老師的熱心和真誠,使我這個第一次出遠門、初出茅廬的文學青年得以大開眼界。如今憶起,心中猶熱。
那段時間,張老師似乎鐘情于散文詩的寫作。參會之前,我剛剛拜讀了他發表于《人民文學》的《大理印象》:“山,透明,有冰晶的雪。水,透明,能看清水蝦的須。石,透明,浮現出山林,云影。”在這組散文詩里,大理的美被他逮個正著,并用玲瓏剔透的文字,將其展現得入木三分。散文詩是一種以小見大的文體。張長的散文詩,沒有波德萊爾《巴黎的憂郁》里的“惡之花”,也沒有魯迅《野草》里對靈魂的無情解剖;不像泰戈爾的《吉檀迦利》美得玄秘,也不像何其芳的《畫夢錄》美得凄迷。但他和這些大家一樣,都是以“美”作為俘虜讀者的魔杖。張長的散文詩,美在清澈。
那次東北之行后,張老師發表了《松花江》《火山口森林》《死去的紅松》等一批散文詩。
在文學創作上,張長老師是個多面手。他常常這樣回顧自己的文學之路:由寫詩到寫散文詩再到寫散文然后寫小說最后寫隨筆小品。他甚至認為,這個模式,可以為那些剛踏上文學創作之路的人借鑒甚或踐行。對于自己的作品,他同意一些人的看法:詩不如小說,小說不如散文。從他的著作年表上看,他發表第一首詩(也是第一篇作品)是在1957年8月,最后一次發表詩(不包括散文詩)是在1988年。現在讀他的這些詩,覺得由于受那個時代的文風影響,一些詩確實有主題先行,圖解政治的印痕。但其中有些表現邊地人情風物之美的詩,還是可圈可點的。如《椰林短笛(六首)》等,就寫得含蓄、深情,富有民歌韻味,能讓人獲得美的享受。
張老師的前期散文和他的詩歌、散文詩一脈相承,善汲取西雙版納少數民族風情的美韻,富有詩情畫意。可以看出,他的佳作《空谷蘭》在這些散文中已經閃現著朦朧的影子。
張老師的音樂系列散文(曾結集出版,書名《另一種陽光》),脫胎于他對西方古典音樂的熱愛。素養的深厚,品鑒力的高超,感受的獨特,使得這批文章別有風韻。前些年,有一本獲得省獎的散文集,竟然部分抄襲了張老師這批散文中的字句和段落。這樣的侵權雖然令人不愉快,但是否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張老師的這批散文的確讓人愛羨有加而使得有人不恥進行抄襲?
平民系列散文,也是張老師散文作品中的上乘之作。以平民的視角來寫平民的吃穿住用、喜怒哀樂,把自己真實定位為一個平民,這正是張老師的高貴之處。張老師還將一些底層人物納入自己的筆下,《擺腌蘿卜攤的姑娘》《掃街老人》《護工小袁》等,都灌注了他對普通人的關切、關愛和尊重,彰顯了作家的良心。
張老師后期的散文,多為隨筆小品。在文集中,他將其收入《雜感雜記》一輯。我曾在他的一次作品研討會上說,張長老師近年多寫隨筆小品類文章,是他的文學之路走到了爐火純青階段后的自然選擇,甚至是必然選擇。“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他的這些文章綿里藏針、時顯鋒芒,簡約如三秋之樹,蒼勁似寒山之石,充滿力量和魅力。用王蒙在為他的文集寫的序里的話來說:“(這些文章)增加了一點尖銳。”當然這種尖銳,仍然發自一顆善良的柔軟的富有溫情的心。行霹靂手段,懷菩薩心腸。他的這些富有思想深度和人生況味的散文,體現出他文學風格的另一面。
和他們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作家一樣,張長老師也曾深受蘇俄文藝的影響。這在他的有些作品中時有體現。他曾經很向往那片長滿白樺林的土地,并與我相約,適當時去旅游。他心中的俄羅斯,在柴可夫斯基和肖斯塔科維奇的音樂中,在列維坦和希施金的油畫里,在屠格涅夫、巴烏托夫斯基的文字中,在俄羅斯姑娘碧藍色的眼睛里。但由于他患了前列腺方面的疾病,我們終于未能成行。當然,即使他還健康地活著,如今的俄羅斯也不能去了,由于疫情,更由于戰火。
張老師文思敏捷,凡外出開筆會或采風,都會有相關作品問世。當年他和另一位作家結伴而行到德宏、大理采風后寫出了一篇小說的事,給我留下較深的印象。
那時我在大理州文聯供職,接待外地作家來訪,是我的份內工作。白天,我陪張老師他們采訪。有閑暇時,邀他們到家聊天、喝茶。也就是那一次的接觸,張老師認識了內人、小女,并逐漸成了我們的家庭好友。有意思的是,兩位老師到德宏六七天后,原路返回時竟只剩張長老師一人。張老師笑說,在德宏游覽一寺廟時,一時興起,大家抽了一次簽。誰知同伴抽到的是一支下下簽。本來只是抽著玩玩,這位同伴卻因此憂思忡忡、心神不寧,竟至提前乘飛機回昆明去了。事情有點好笑,我們聽聽也就過去了。
不久后,我們就讀到了張老師的短篇小說《求簽》。作品構思精妙,細節生動,把一個被負面信息攪擾得坐臥不安的人寫得活靈活現。這篇小說,先后被《小說選刊》《新華文摘》轉載,張老師也曾以“求簽”兩字作為自己一本小說集的書名,可見他對這篇作品比較滿意。
如今重新捧讀收編進《張長文集》里數量頗豐的小說作品(其中長篇小說《太陽樹》獲駿馬獎,數十篇中短篇小說中也有數篇獲獎),對比之下,覺得還是他早期創作的、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此獎項后納入魯迅文學獎)的《空谷蘭》,是一座他自己的高峰。這篇小說雖然篇幅不長,卻是他在西雙版納17年生活積淀的結晶、升華,也是他美學觀念的完美呈現。《空谷蘭》里那些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美麗的風物,以及承載著這一切的散發著青春芬芳的美好時光,那么的詩意盎然、雋永,讓人至今陶然神往。
張老師為人低調、謙和,但從不向權貴摧眉折腰,骨子里總透出一種清高孤傲之氣。“人不可有傲氣,但不能沒有傲骨。”他常常這樣說。
張老師生活節儉,穿著樸素。他在散文《平民的衣》里,說到過這樣一件事:曾在機關大院門口候一位來訪的朋友,一個也到這里來找人的姑娘看了他一眼后問:“你是門衛嗎?”朋友來后,張老師講給他聽,朋友看看張老師的穿著后大笑。因為那天張老師穿的是“老三色”,再加一雙臃腫的大棉鞋。
由于兒女在外地工作,張長老師長時間獨自生活,獨自不問收獲地筆耕,心境就難免會寂寞。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古樸的穿著,就是他寂寞心境的外化。穿著寂寞的衣,走著寂寞的路,他也許是一個不合時宜的人。
每逢要外出參加文學活動,張老師就會有些緊張。這種時候,我往往會接到他的電話,問我是否也去參加,如果同去,就事先約定要和我共住一個房間。這是因為他睡眠不好,需要有一個安靜的宿伴。當然,他的這種邀約,也透露出他內心深處潛藏著一縷孤寂,體現出他的一種對溫暖友情的渴求。
在整理編輯《張長文集》期間,張老師曾邀請著名的書法家范曾先生為之題寫書名。可能因為范先生太忙,他將題寫的書法作品寄給張老師時,《張長文集》已經付印。張老師就只好將范先生的字印為書簽,夾于文集內。我曾陪張老師尋找和選擇文印公司,參與審看書簽的設計、談價等事項。對于一個作家,出文集、印大書法家題寫的書簽,也應該算一件志得意滿之事。但我在有事先離開文印公司時,回頭一望,才發現還在與文印人員磋商的他,言談舉止依然那么不顯山露水,穿著依然素凈得不能再素凈。他確實屬于那些“自己得不到撫慰,卻總愿撫慰別人的人(傅雷評價莫扎特的話語)”。當然,是用他作品里的溫暖和亮色。
真的,有時看到瘦削的張老師穿著一身過時的服裝走過來,我會覺得他是從另一個時代走出來的人,50年代?或者更早?恍惚中,我甚至會覺得,他是從一條古舊的雨巷里走來的,就像那個著名的丁香詩人一樣,默默彳亍著,等待著什么事,什么人。
記得張老師曾經說過,作為人,誰都免不了一死,好在搞寫作的,在這個世界上多少會留下一些痕跡。是的,這個人曾經真誠地活過,曾經蘸著自己的心血堅持不懈地寫過,直至耗盡生命。
張長老師是云南省較早在全國產生影響、獲得聲譽的一位作家,筆下著作多次獲國家級文學大獎。他用溫情和美來照亮人心,給我們留下了一筆永恒的財富。
張老師在《空谷蘭》里寫到了一種愛伲人把它叫做伊散玉瑟花的蘭花。這種花顏色淡藍,有著特殊的香氣,一般生長在人跡罕至的深山老林,靜靜地開,靜靜地落,悄悄把色彩和芬芳傳遞到人間。

能不能這樣說,張長老師自己就是一株這樣的空谷蘭?
我所認識的林非先生
我與先生結緣,和很多文人一樣,是由文字開始的。
“我并不認識這本散文集的作者原因先生,是他經由江蘇作家王志清先生的介紹,囑咐我撰寫一篇讀后的感受,這樣才很高興地聯系上了。”這是林非先生為我的散文集《在生活的郊野》所寫的序里開頭的一段話。
那是1999年的事。
當年7月下旬,我給先生寄去了新編散文集的樣稿,煩請先生為之寫一篇序言。當時,先生正準備赴承德北邊的塞罕壩國家森林公園采風。臨行前夜,他冒著難耐的酷熱翻讀了300多頁校樣,并記下了一些想法。后來他徜徉在河北與內蒙古交界處的那片森林和草原時,還在為序文的撰寫進行著思考。回到北京后,他又將樣稿仔細地覽閱了一遍,然后寫下了3000余字的感受。
林非先生是著寫過《現代散文六十家札記》《中國現代散文史稿》的現代散文研究家,同時他自己也是一名優秀的作家。他極力提倡新時期散文創作必須沖破過去幾十年散文的思維模式,奮起開拓一條振興與繁榮散文的新途徑。他寫過《離別》那樣可與朱自清的《背影》媲美而又具有自己獨特風格的文章,還有《話說知音》那樣進入全國高考語文試卷的一大批名篇佳作,同時還寫過《魯迅和中國文化》等具有巨大影響力的著作。為我這樣一個素昧平生,當時還相對年輕的作者寫序,他完全可以像某些名家一樣,凌空蹈虛地寫一些大而化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文字。但他沒有絲毫敷衍。他驅遣自己特有的明澈雋永的文筆,對我的那些文章進行條分縷析,給出懇切準確、深邃精湛、情理交融的評點,讓我受益匪淺并得到很大鼓舞。
先生在《序》中說:
也許由于曾經致力于散文詩寫作的緣故,原因先生筆下的許多篇章,都洋溢著一種濃郁的詩意,有時顯得飄忽和溫柔,有時又顯得奔騰而雄壯……這當然得歸結他感受的能力和表達的才氣,很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作者在書寫許多靈動的形象時,也同時追求著表達出其中哲理的涵義。原因先生確實是在不斷深入地抒寫整個人寰中種種命運的軌跡……描摹這樣的故事時,顯出了一種充滿憂慮和思索的音調……也正好透露出作者對于一種非常珍貴的審美理想的追求。
先生還在《序》的最后說:“我在誠摯地祝賀他這本散文集出版的同時,也多么盼望著能夠不斷讀到他更多更好的散文作品。”
能夠在素不相識的情況下,僅憑對我的一些文章的閱讀,就寫下這樣一些知情知性甚至可以說是知心的語重心長的激勵文字的,是一位什么樣的人呢?我不由暗中猜想著先生的容貌。
令人高興的是,收到先生撰寫的序文后不久,與先生見面的機會就來了。
大約是同年深秋,中國魯迅研究學會到昆明開年會。作為學會的會長,林非先生到臨參會。
得知此消息,我立即去看望先生。
先生身形較高,兩眸有神,言談舉止盡顯彬彬學者氣質,是“江天一色無纖塵”那樣的人物,讓人一經接觸,就心生敬愛之情。
有一件事,讓我一直難忘。
先生在昆明停留期間遇到了一件事:某省一位高官,來電話表示愿對中國魯迅研究學會進行經濟資助,條件是希望能成為研究會副會長。
像魯研會這樣的民間學術團體能獲一筆資助,對于今后學術活動的開展,自然大有裨益。但擔任研究會的副會長,必須得有一定的學術水準、學術成果和學界影響,而此公充其量只能算魯學研究的熱心人。因此,接受資助還是對之婉拒,成為一個問題。
“該怎么處理呢?”先生沉吟著。
也許先生覺得我是局外人,且相對年紀較輕,就想聽聽我的看法。我已記不清當時自己是怎樣表明心中的想法了。但據我所知,后來學會采取的態度是完全“魯迅風”的:摒棄了實用主義而選擇了對原則的堅守。
第二次面見先生是2001年12月我赴京參加中國作家協會第六次代表大會期間。
擇一個休會的上午,我乘坐公交車輾轉到了先生的住地。打電話問先生家所住的單元樓層,得知先生的書房和居室在同一單元的上下樓層,內部連通。有趣的是,我到了書房層,敲門,無人應答。打電話,先生說在居室層等我。我立即下樓,敲門,也無人應答。打電話,知道先生已急匆匆趕往書房層迎我了。我又立即上樓,去叩啟書房層的門,先生竟又已急趕往居室層了……這樣的擦肩錯位,竟然重演了兩三次,實在好笑。現在想來,出現這種情況,是兩人見面的心情都太急迫的緣故。
待在書房坐定,我有點窘愧,低頭直搓兩手,先生卻滿臉微笑地看著我。
先生談魯迅研究、談散文創作,娓娓道來,每每有獨到見地,讓我如沐甘霖,如坐春風。
一個上午很快過去,先生熱情地留我共進午餐。先生自己吃得很少,卻不停地給我拈菜,然后微笑著看我剝蝦、手托荷葉餅卷裹片皮鴨。多少年過去了,我仍覺得那家小餐廳的清蒸基圍蝦、北京烤鴨,是不管多么高級的酒店都不能吃到的美味。
我向先生告別時,先生從書架抽出了一本厚重的書送我。書名:《中國魯迅學通史》。
回到作代會代表的住地——離盧溝橋不遠的一家部隊賓館。當晚,我開始閱讀先生的贈書。這部由張夢陽著寫的宏著,很多論點和資訊,都是我這個熱愛魯迅作品的非專門研究者所未聞的。而林非先生寫的序言,更是思想理論深度和斐然文采兼具。
為什么要進行魯迅研究,其終極目的何在?林非先生在這篇序文中借鑒巴人在1938年10月發表的《超越魯迅——為魯迅逝世二周年紀念而作》一文中的觀點,表明學習與研究魯迅的目的是要超越魯迅。在序文里林非先生說:
魯迅作為一個思想如此深刻而又時刻關愛著整個民族的作家,確實是很難超越的。然而……(我們)千萬不要只滿足于去吹捧一些玩弄和炫耀知識的碎片,卻對自己民族的命運漠不關心的輇才小慧之徒,千萬不要興高采烈地去詆毀和謾罵像魯迅這樣巨大的精神文化現象,千萬不要重復像屈原在《卜居》中所說的“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那樣的狀況。我們應該不斷地向著深刻的思想挺進,向著關懷整個民族的道德境界升華,這也正是進行魯迅研究的終極的目的。
在一盞臺燈的光影里讀著這些振聾發聵的文字,先生對這個世界充滿期許的微笑又浮現在我眼前。落了一夜的雪。抬起頭,只見雪后的朦朧曙色中,滿窗松竹的影子輕輕晃動。
第三次見先生,是2003年7月。那年,在云南省文山州舉辦普者黑文學創作筆會,邀請了先生、余秋雨、舒婷等幾位作家參加。回程時他們途經昆明,我去看望了先生。先生精神依然健旺。先生說:“普者黑那旖旎的水,奇異的山,真是讓人相見恨晚。”這次普者黑之行,激發先生寫下了著名的游記散文《普者黑泛舟記》。正如魏建軍在《林非游記散文漫談》中所說,“當林非先生的游蹤進入普者黑時,藝術家的氣質和心性完全呈現出來了。”
林非先生在文中寫道:
我出神地俯視著這被陽光照耀得多么清亮的水波,只見那一朵朵縹緲的白云,在透明的湖水里緩緩地游弋。我輕輕地彈撥著水波,想扣問這淼淼的白云,想邀請它浮出靜謐的水面,訴說那九霄云外的往事。
由清亮的水波到縹緲的白云在湖水中游動,再到邀請云朵浮出水面講說九霄云外的往事;從對逼真景物的描畫到擬人想象的運用再到心緒的激揚飛蕩,都被先生細膩而又富有節奏感地呈現出來。在這里,所有的景語皆情語。先生的這篇文章,以它唯美的色彩,讓我一讀再讀。

小船穿過一莖莖的荷葉,讓盛開的蓮花在我們頭頂微微搖晃。這云南高原上多么涼爽的風兒,把我吹拂得萬分的舒暢,真想在花叢中永遠地棲息下去。
浪漫的情思往往妊娠并臨盆于美麗的景致中。意猶未盡的先生,忘記了疲乏,又參加了夜晚的蕩舟。憂傷的傳說,潑水的嬉戲,姑娘們的美麗舞姿,在迷蒙夜色的籠罩下,如夢如幻,更充滿了濃郁的詩意。但先生在良辰美景中,生發的卻是深沉的慨嘆:
瞧著岸上歡歌狂舞的人們,才真正懂得,只有當水草茂密,魚蝦成群,大家都豐衣足食的時候,才可能萌生出濃郁的詩意來。而如果在專制暴政的胡亂折騰底下,不準許種植莊稼,不準許養育魚蝦,這樣肯定就會饑寒交迫,餓殍遍野,卻還不準許自由地抒發憤懣的意見,像這樣的話,哪里會有詩,哪里會有出自內心的歌唱和舞蹈?
胸中丘壑,在萬頃波濤中突兀而起。泄涌和流淌得那么自然,正如足球巨星的臨門一腳。在美景中寄寓了高曠境界、現代精神、平民視角和學者情愫。
前兩年,云南文史研究館欲編一套《云南文化名篇》的叢書,作為一個館員,向叢書的現代當代部分,我極力推薦了先生的這篇作品。當然,讀到先生的這篇文章,是先生回到北京一段時間后的事。
那天,聽先生講述了普者黑之行的一些感受后,想到先生坐了大半天的車,可能比較疲累,我就未在先生下榻的房間多作逗留,轉而去看望舒婷。忽然接到先生電話,說尚有幾句話要對我說。快言快語的舒婷急忙催我快去。
到了先生房間,先生拿出了他在文山購得的一包土特產遞給我,說:“人在旅途,身無長物,留個念想。”原來在我向先生告辭后,先生總覺得應贈我一點什么以表惜別之情。想來想去,才想到了這包在文山所購之物。
我的眼睛一下子濕潤了。雖然中國有一句古話:“長者賜,不可辭。”但我還是力勸先生把這包土特產帶回北京。我嘴里說,畢竟,它能讓您想起普者黑的山山水水。心里卻說,先生,您贈予我的已經夠多了。您潤物細無聲的教誨,夠我用一生去領受、咀嚼和消化吸收。
那以后我和先生再也沒有見過面。
2010年,我到江西省新余市參加中國報紙副刊研究會的一次年會。期間,游覽了新余這座“鋼鐵之城,工業之邦”的另一側面——柔媚的仙女湖。那是一片散發著迷宮般誘惑的水域。湖湖相扣,島外有島,港灣交錯,山峰對望。登上湖中的名人島,我注意到路旁有幾排剛種下不久的樹木,那排新林前面豎著一塊標牌,上面刻寫著種樹的名人,順著一看,竟然有“林非”這樣的字樣。原來,我算是踏著先生的足跡來到了這里,只可惜擦肩未遇,錯過了一次見面的機會。后來,我在刊物《黃河》上讀到了先生寫的散文《仙女湖記游》,這也是一篇游記佳作。
可以說,先生的游記散文在中國文壇上是獨樹一幟的。他奉行“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古訓,身體和靈魂一次次邁開腿腳,一次次放下行囊。每到一處,厚重歷史的現場讀取,美麗風物的現場體驗,既對心靈進行著強勁地撞擊,又對情感進行著熾烈地點燃,無限的情意和深邃的哲思就從他的筆下汩汩流出。他的游記散文不僅表現自然人文之美,還常常蘊含著對現代觀念的探尋和向往,對人性之惡、現實之丑的審視和批判,引導著人們去追求一種理想的人生。《比薩斜塔下的沉思》《小喬墓下的思索》等等都是這樣的代表性作品。先生曾經說過:
游記是一種充分表達獨創個性和抒發豐盈心靈的文體,在被迷人的景致感染、撞擊與震撼之后,就會激發出澎湃的情思,描摹著自己別具只眼的印象。而當這種灼熱的感情與深沉的哲理,融會于諸多鮮明的形象之際,思考著人類在大地上和歷史中所面臨的勞作、追求、命運與前途,詠嘆著激蕩自己內心的歡樂或悲愴的時候,就一定會趨向于十分美好和高曠的境界,引起廣大讀者濃厚的興趣,并且從中獲得應有的啟迪。我愿意在溫馨與熱忱的人世中,爭取寫出像這樣更讓自己感到欣慰的游記來。
《仙女湖記游》就是先生這種游記散文理念的成功實踐和鮮活例證。
今年8月的一天,忽然接到先生的夫人、中國傳媒大學教授、著名傳記作家肖鳳老師的電話。她告訴我,先生主編的《中國現當代散文300篇》(2003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一書精縮為122篇了,近日要以《中國現當代散文選》為書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其中仍收有我的散文《圓通山花潮》,因要尊重作者的著作權益,出版社委托先生詢問我是否同意文章收入這本書中。這自然是求之不得之事。感謝先生!
先生選編的《中國現當代散文選》,收入了蔡元培的《洪水與猛獸》、陳獨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辯書》,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周作人的《喝茶》,李大釗的《五峰游記》等等自新文化運動以來到當今文壇上先生認可的名篇佳作,堪稱權威選本。拙文能夠忝列其中,深感榮幸。附帶說一句,也許由于受先生此前曾把我的《圓通山花潮》編入《中國現當代散文300篇》的影響,此文也曾收入季羨林先生主編的《百年美文》中。
肖老師告訴我,林非先生已91歲高齡,身體尚可。我表達了對先生的思念,并說有機會一定要登門探望。
別時容易見時難。先生,我們還有再見的機緣嗎?
先生,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