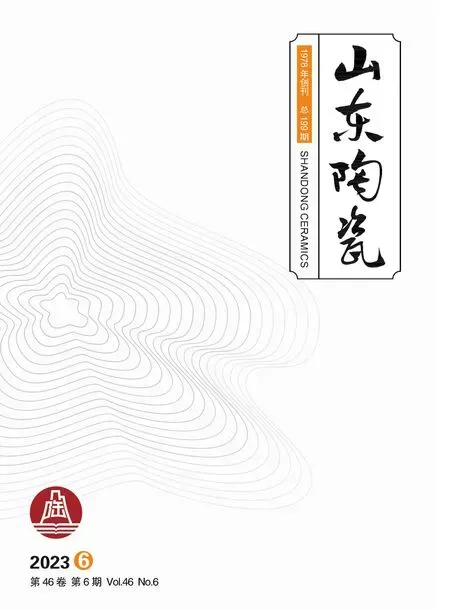氣氛美學視野下陶瓷器物在視覺藝術中的意義生產研究
路子琰,穆宏非
(1.韓國京畿大學一般研究生院,luziyan940922@163.com;2.韓國京畿大學一般研究生院,2214381449@qq.com)
在20世紀后半期,以德國為代表的歐洲學術界在哲學、美學領域將“氣氛”作為重要的研究范疇,思考人面對某物時的在場性感受以及人在空間中的身體性體驗。這種區別于傳統美學研究范式的新美學研究被稱為氣氛美學。氣氛美學作為新美學的核心概念,是由德國學者格諾特·波默教授在《氣氛美學》[1]一書中提出。當把“氣氛”作為審美范疇去分析具體藝術作品時,尤為強調作品的總體性。也就是說,欣賞者在欣賞一件藝術作品時,作品總體性的氛圍決定了欣賞者的審美體驗。即使欣賞者對作品中的某個局部或者某個元素印象更為深刻,也是因為總體性氛圍的烘托而產生的。從這個角度而言,僅對陶瓷器物本身進行美學研究而忽略了陶瓷器物在諸多視覺藝術中的意義生產,就有了局限性。本文以氣氛美學為視野,以繪畫和建筑這兩類視覺藝術為分析對象,分析陶瓷器物在視覺藝術中的意義生產,從而為陶瓷美學研究提供具體參照。
1 氣氛美學的內涵
在人與人、人與物、人與空間、人與自然等的互動關系中,因人的感知而產生在場性認知與體驗,構成了氣氛的意涵。當遇到某人感覺到他有些反常,反常即是人與人互動關系的氣氛。同理,當看到某款新能源汽車感覺很有“未來感”、經過某個郊外小屋感覺“陰森恐怖”、走在雨后的秋季街道上略顯“傷感”等等,都是由氣氛傳導至主體的在場性感知。
氣氛是間性的,而不是二元對立的。當我們說人與人、人與物等等的在場性感知時,“與”指的就是二者之間的互動關系以及由此產生的主體性感受。主體對于氣氛的感受是感性的,同時也往往是不確定的、發散的。因此,主體對于氣氛的描述,往往是用比擬詞語或形容詞,如”油膩”“輕快”“蕭瑟”等等。一幅打動人的藝術作品,其動人之處往往無法用語言精確且全部地表述出來。換句話說,表述出來的詞語往往指的是對這幅作品的評價,而非感受。那些無法用語言表述的部分才是審美活動中最為重要也最有價值的。因此,當我們用“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或“回味無窮”形容某一時刻的感受時,意味著這是一次令人珍惜的高峰體驗。例如,當孔子聞韶之后的“三月不知肉味”,恰恰是審美活動中的高峰體驗,用“不知肉味”形容聞韶之后的滿足感,而不是用其他理性詞語描述聞韶后的狀態,也正說明了審美活動中情感體驗不可言說的特性。
氣氛美學強調主體在主客關系中獲得的感性認知,而不強調具體的評價。“氣氛是感知主體和感知對象的共同現實。它是感知對象的現實,作為其在場的場域;也是感知主體的現實,只要他在察覺到氣氛之時,以一種特定的方式,身體性地在場。”[2]氣氛的產生與獲知,離不開感知主體和感知對象的共同在場。藝術作品是觀眾的感知對象,當觀眾感知到某種氣氛并因此而獲得情感滿足的時候,意味著藝術作品的魅力與人的體驗達成了互動性關聯。
因此,在藝術創作中,藝術家通過富有創造性的構思,將無形的構思予以物化,進而形成藝術作品,在這其中,藝術家需要考慮如何制造氣氛,甚至可以說,氣氛營造得恰當與否關系著藝術作品的質量;在藝術欣賞中,藝術作品能否打動觀眾,往往取決于觀眾是否切身感受到了藝術作品的氣氛。延續著這一學理脈絡,就為分析視覺藝術中的陶瓷器物奠定了基礎。
2 陶瓷器物在繪畫作品中的意義生產
繪畫作品是一種人造物,畫框所界定出來的內部空間屬于繪畫的整體,而畫框之內的畫面又有不同的視覺元素,如人物畫有人物形象和背景、山水畫有山石樹木等。如此一來,面對一幅藝術作品則有了兩個基本的維度:一是這件作品的整體,即眼前由畫框所框定的作品;二是這件作品中的畫面元素,即作品內部空間的內容與形式。當觀眾欣賞某件藝術作品的時候,既是對這件作品整體的欣賞,也是對這件作品中的具體元素的欣賞,觀眾欣賞的眼光穿梭于這兩個維度,大多數情況下觀眾無法也無須理會這種維度的變化。但是,反過來說,如果觀眾對一幅作品進行欣賞時獲得了充分的體驗,那么,這種體驗必然是在“人與藝術作品”的欣賞過程中獲得的,是由人的目光到藝術作品再返回人的情感的過程。
1980年,羅中立的作品《父親》(圖1)一經展出就打動了無數的觀眾。這幅作品從創作完成到現在歷經40余年的洗禮,已經成為美術經典。無論是觀眾在作品面前受到的震撼與感動,還是這幅作品引起美術界的討論并被中國美術館收藏,都證明著這幅作品具有豐富的氣氛。
這幅作品中引人注目的是作為父親的農民手捧一個粗瓷茶碗,碗的外層涂著青花釉,碗身繪有“魚紋”。粗瓷茶碗與農民形象一起構成了什么樣的關聯?粗瓷茶碗在作品中的出現又為觀眾的審美感知帶來了哪些意義?
從氣氛美學的視野來看,《父親》中的農民形象,黝黑的皮膚,滄桑的臉龐,以一種特寫的方式呈現在觀眾面前,觀眾面對眼前的農民形象,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父親。堅毅又愁苦的眼神,粗大又褶皺的雙手,寬厚又佝僂的肩膀,無一不讓觀眾感受到深沉和崇高。也正如作者在創作時所言:“那是1975年的除夕之夜,雨夾著雪粒不斷向人們撲來,在我家附近的廁所旁邊,守候著一位中年的農民,他用農民特有的姿勢,將扁擔豎在糞池坑邊的墻上,雙手放在袖里,麻木、呆滯,默默無聲地叼著一支旱煙……這時,我心里一陣猛烈的震動,同情,憐憫,感慨……一起狂亂地向我襲來。我要為他們喊叫!這就是我構思這幅畫的最初沖動。”[3]從羅中立的創作自述來看,作者是因在除夕夜看到一位農民而產生了情感的共情,并產生了為他們喊叫的沖動。這是飽含人道主義情懷的藝術家的品質。當藝術家將這種沖動進行創作并予以視覺化呈現的時候,他畫的不是除夕夜看到的那個場景,而是以巨幅的尺寸、運用超級寫實主義的手法描繪了一位農民的特寫形象,并且加上了手捧粗瓷茶碗的動作。“茶碗”“青花釉”“魚紋”,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視覺表意符號,積淀著民族文化的心理結構和審美意識[4]。這無疑是畫家以其才華和個性,為這幅作品營造了氣氛。
藝術家制造的氣氛,是將承載中華文明輝煌成就的農民與承載中國文明精神符號的魚紋粗瓷茶碗并置在一起,讓普通的農民承載了中華民族的意涵,讓普通的粗瓷茶碗成為了華夏文明的視覺符號。作者的這種創造性表達,無疑讓《父親》這幅作品具有了深刻且豐富的氣氛。當觀眾面對這幅作品時,首先看到的就是農民臉龐的特寫,臉上的皺紋、黝黑的面龐等具有典型性的樣貌與觀眾的審美感知發生作用。父親手捧的粗瓷茶碗,又強化和鞏固了觀眾對這幅作品的感受厚度,讓觀眾對這幅作品的情感連接更加深厚和堅固。“《父親》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中國農民的代表,而中國農民,難道我們不能說他們是中華民族的代名詞?從這種意義上說,羅中立的《父親》并不僅只是一個大寫的‘人’或農民的‘父親’,而且在更深的層面上也是中華民族的象征。”[5]也許觀眾并沒有自覺意識到畫面中的粗瓷茶碗發揮了怎樣的作用,但粗瓷茶碗的符號指向與深沉的農民形象一起,在無聲無息地為觀眾帶來了情感的震撼。這種震撼,觀眾也許無法言說,更無須言說。
藝術家制造的氛圍與觀眾感受到的氛圍均以作品為中間介質,又返回到觀眾的感知之中,讓觀眾感動、滿足、回味。《父親》這幅作品,正是將“農村”“農民”“茶碗”“青花釉”“魚紋”等具有關聯性的語匯及其所表征的意義結合了起來,才使這幅作品散發出強大的心理震撼。粗瓷茶碗作為普通百姓的生活符號,以及粗瓷茶碗上的魚紋作為華夏文明的標識符號,在觀眾的審美感知中完成了對作品意義的賦予,也完成了觀眾在場性體驗的意義生產。
3 陶瓷器物在建筑中的意義生產
一幅繪畫或者一座建筑,其本身并沒有中性客觀的特點,之所以說一幅畫“唯美”或一座建筑“雄偉”,是基于人對“物”的感受而產生的主觀性評價。在藝術欣賞過程中,當人面對某件藝術作品時,作品中的內容或形式構成了人的感知對象,且不同元素之間相互支撐、共同營造某種氣氛。
建筑作為視覺藝術的一大類型,人們對建筑的感受也因建筑的實體以及建筑的空間所營造的氣氛而給人們在場性體驗。四川美術學院的羅中立美術館(圖2)是體現陶瓷器物融入建筑設計制造氛圍的代表性案例。羅中立美術館2012年開始建設,2015年建設完畢并開館。這一美術館既是展示藝術作品的公共空間,其建筑本身也是視覺藝術作品。美術館的外墻鑲嵌了回收的數十萬陶瓷碎片作為裝飾。無論是建筑的頂部還是四周立面,都被陶瓷碎片覆蓋,形成了以陶瓷碎片為外衣的建筑特色,與玻璃幕墻材質的博物館、磚墻材質的美術館等形成鮮明的差異,也因此形成了極為明顯的建筑風格。
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提出了“光韻”的概念,認為藝術家的創作以及展示的場所,使得藝術原作具有獨一無二的“靈韻”。當電子圖像對藝術原作進行復制和傳播的時候,雖然能夠更大范圍地讓受眾認識和熟悉藝術品,但隨之而來的后果是藝術作品“靈韻”的消失。藝術家的簽名、藝術家的風格、藝術家作品的不可復制,均構成了對藝術“靈韻”的維護。藝術品本身與藝術品的圖片,其中最為明顯的區別,是前者有其獨一無二的“靈韻”,而后者,只是前者的可視化替身。[6]本雅明的這種論述,非常精彩地觸及到了藝術原作的價值內涵。但是,這種藝術“靈韻”的論述在中國陶瓷藝術欣賞之中是一個偽命題。在中國陶瓷器物制作過程中,無論是制作者還是欣賞者,并不追求陶瓷器物的獨一無二的屬性,尤其是民窯生產的瓷器,其本身就是為了供百姓日常使用而生產,批量化制作和燒制是其生產狀態。當瓷器進入百姓家服務百姓生活的時候,陶瓷在日常生活情境中是作為一種實用器物而被使用,同時也因陶瓷器物與中國人日常生活的緊密關聯而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視覺符號。
羅中立美術館之所以沒有按照常規的美術館建設范式建設,而是使用大量的陶瓷碎片作為視覺元素,與建筑師的用意及對空間氣氛的考量緊密相關。羅中立美術館位于重慶市沙坪壩區大學城,處于四川美術學院虎溪校區東大門右側。沙坪壩區是著名的磁器口古鎮,從康熙年間到乾隆晚期廣泛設有窯廠并生產大量瓷器。因此,瓷器的生產歷史以及至今留存的磁器口古鎮,構成了沙坪壩區的歷史遺跡,也成為地域性的符號。設計師基于這種地域文脈的優勢,充分發揮地域文化特色,將回收的廢舊陶瓷打碎,按照顏色進行分類,根據圖案的整體設計,將不同顏色的陶瓷碎片拼貼成豐富而有秩序的圖案。當陶瓷碎片覆蓋建筑墻體之后,整體的視覺效果不僅傳承了地域文化,而且也因圖案造型的明快和五彩繽紛,更加契合了作為專業美術學院的美術館建筑所呈現出來的文化的內涵,以及與年輕人群體相匹配的青春、活潑的整體氣氛。
王智穎在《氣氛美學視角下的陶瓷藝術審美與批評研究》一文中,認為藝術已不再只是審美形象的“物化”,而是趨于“場景化”。她把氣氛分為“原氣氛”與“環境氣氛”,對于陶瓷作品批評而言,原氣氛指陶瓷材料和表現手法所體現出來的審美意蘊,環境氣氛則是陶瓷產品在特定環境中進行使用或呈現時所給人的審美感受。原氣氛與環境氣氛構成了對陶瓷藝術進行欣賞的路徑,也是陶瓷藝術批評的方法。[7]從氣氛美學的視野來看,無論是身處四川美術學院的師生,還是經過此地的居民,在場者并不會像關注美術館內部的藝術作品一樣關注美術館建筑上的陶瓷碎片。也正因如此,陶瓷碎片作為一種非完整狀態的陶瓷器物的存在方式,當被作為建筑的皮膚裝飾于建筑外立面時,陶瓷碎片就成為了建筑的表達語言而得以展示在人們面前。這座既傳承地域文脈又承載美術學院公共展示空間的美術館,以陶瓷碎片裝飾的方式營造了氛圍,在場者也因其不拘一格的設計風格和靈動而又有創意的氣質,獲得了關乎于地域文化、藝術創造力等諸多維度的審美體驗。如此,陶瓷碎片的創意化呈現,賦予這座美術館鮮明的個性,也成為感知主體“身體性地在場”的表征。
4 結語
在大多數情況下,陶瓷器物往往既是欣賞對象,也是氣氛制造的元素。例如,當人們進入陶瓷器物展覽的空間時,人們的欣賞體驗既來自于陶瓷器物,也來自于身處的空間。當欣賞者邊走邊欣賞眼前的陶瓷器物時,到底是陶瓷器物本身決定了欣賞者的感受,還是身處的空間決定了欣賞者的感受,此時已經無法確定,這正是氣氛美學強調的物我關系的核心指向。通過上述分析來看,陶瓷器物在不同視覺藝術中的出場,與其他元素一起營造了視覺藝術的氛圍,而這種氛圍也塑造了感知主體的在場性體驗和身體性感受。從氣氛美學的視角研究陶瓷器物與人的關系,以及陶瓷器物在不同媒介、不同空間中的意義生產,能夠為陶瓷器物的美學研究提供新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