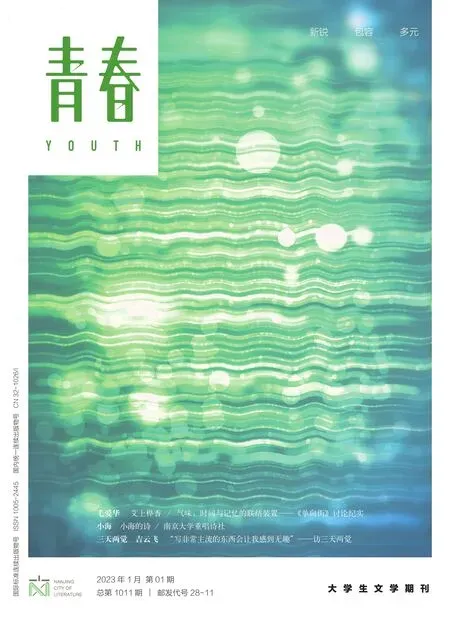小青鳥
鹽城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黃靚
一個深夜,我從夢中醒來,床前泊著月光,如銀色的海,而惘然的心是一葉小舟,在曠闊之上漫無邊際地漂游。過去的十九年,我渾渾噩噩生長,吃不夠,睡不夠,從未有過這樣的靜夜思。
這是入學的第二周,軍訓接近尾聲,正課即將開始,新人新事奔涌疊加,時間的每一處罅隙都躍動著欣喜,而與此同時,一份說不清、道不明的情緒也在暗自生長。起初沒人肯承認自己想家。怎么可能想家呢?自由、鮮活、未知,正是擺脫高考重壓的我們所渴望的生活。怎么可能想家呢?
每晚的睡前神聊,從八卦教官、比較社團、討論不同專業、贊美或吐槽食堂飯菜,逐漸轉移到講解各自的家鄉及過往,并在此話題流連不去。宿舍六個人,小潘是蘇北本地人,悅悅和我分屬蘇南、蘇中,其他三人則分別來自云南、山東和西藏,因此宿舍微信群名為“祖國大好河山”。女生們的想法千奇百怪,難得一致,只在一點獲得共鳴,就是離家之后,漸漸對“家”有了清晰的概念。
“我的家鄉是個縣城,老,舊,但不邋遢。一年四季鮮花盛開,游客不多也不少,日子很安逸。”段亦塵是哈尼族,人長得黑而瘦,聲音卻很沉靜,像縈繞在明月周圍的彩云,又像雨林中不斷冒出的菌菇。我們躺在黑暗里,聽她描繪遠在滇南的建水。小火車緩緩穿行,山上長滿綠油油的茶樹,清風送來古塔的鈴聲,精巧的洋房映襯著厚重的合院。老街經過修舊如舊的維護,古樸與時尚并存,銀匠埋頭打造花樣繁復的飾品,鑿著,錘著,拉絲,繞圈,掐花,仿佛在細細地雕琢時光。
有舍友和我一樣,跟隨旅行團去過云南的“昆大麗香”,在走馬觀花的游覽中,建水是個可有可無的景點。段亦塵從小到大未出過小城,卻認定那是世上最好的地方。我們笑她是井底之蛙,她不為所動,在她看來,沒有比天空的顏色、風的溫度、水的聲音,還有花開草長更重要的事了。
思鄉的魔盒就此打開。徐嬌講煙臺的晚上,是鏗鏘爽利的快板專場。她家是種植大戶,課余時間她基本都在農場干活,騎三輪車,開拖拉機,摘蘋果,種白菜,捆大蔥,施肥,打掃雞兔窩棚,什么都干,除此之外還常跟村里的武師練拳腳。
與好說好動的山東小嫚不同,悅悅是典型的江南美人,蒼白柔弱,窗簾上的蜘蛛都有可能引發一場暈厥。她們那里教育內卷嚴重,她從幼兒園開始即在各類輔導班中奔走,考試成績從未低于年級前十,鋼琴、舞蹈拿到最高級位,圍棋、外語也多次獲獎,代價是小小年紀便患上神經衰弱。
小潘未滿十八歲,在我們中年齡最小,在家卻是老大,下面還有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這在蘇北不算稀奇。她極聰明,只是不肯用功,初中時請人幫忙申請了游戲賬號,就此沉迷手游。軍訓寶貴的休息時間,大家癱倒在地,只有她掏出隱藏的手機分秒必爭地打游戲,并因隊友太菜而開視頻與其對罵。“我才不想那個家呢。”她對父母重男輕女的思想充滿憤恨,輪到她講述的夜晚,說了許多與外婆、外公共同生活的童年趣事。
卓婭的家最遠,西藏阿里,離天最近的地方。開學當天,一身朋克裝的她頂著“奶奶灰”短發,涂著“爛番茄色”口紅,左右耳朵各戴三個耳釘出現,顛覆了我們頭腦中約定俗成的西藏女孩形象。相處后才發現,她熱情善良,單純得近乎“呆”。她向我們展示藏區生活,與游客眼中的詩情畫意不同,一代代藏人輾轉于冬夏牧場,日常充斥著繁重的體力勞動和與惡劣氣候無休止的對抗,求學、求醫格外艱辛。她向往繁華舒適的都市生活,但知道自己的心永遠屬于高原。
一向后知后覺的我,挨到最后才講,是因為感到家鄉普普通通,沒山沒海,有限的經歷更是平淡無奇,除了上學還是上學,沒什么好說的。然而在那晚的靜夜思中,一些本以為模糊的往事貝殼般呈現于記憶的沙灘,星星點點,微小而特別。
我初中就讀的學校,學風嚴謹刻板,只要有點滴空余,諸如因下雨取消體育課,或者副科老師請假,主科老師便競相占課,絕不給人松懈的機會,就連晚自習,也常出現幾科老師各據一方答疑解惑的場景。他們對時間如此錙銖必較,卻肯花一整天帶我們去鄉下挖山芋。秋日的田野廣闊明朗,藍天白云下,水鳥蹁躚,湖塘泛著金光,那是師生們唯一一次無拘無束的游玩,也是我首次領略到蘇中平原的美。
高中時光緩慢又迅疾。緩慢是由于昏天黑地,似乎只有深夜凌晨而沒有白天,迅疾則是我沒來得及多想便結束了。高考完最后一次去學校,僅僅相隔幾天,卻恍如隔世。通往宿舍樓的水杉樹依舊靜默挺拔,報告廳旁幾樹石榴花開得明艷如火,大操場中有幾個班在上體育課,教學樓里不時傳出瑯瑯的讀書聲,唯獨畢業班所在的那排教室冷冷清清。我在其中一間找到語文老師,她正指揮幾個學弟、學妹打掃衛生,地上到處是畢業生拋撒的試卷和書本,黑板成了心情墻,畫滿龍飛鳳舞的線條。我把輔導材料還給她,向她道謝,也道別。她站在圍欄邊目送我,從五樓到一樓,每走到樓層轉角,都能看到那個不斷揮手的嬌小又堅定的身影。高中三年,她每學期都會給每位同學寫信,不談大道理,只講小事情,還常在考試周給大家發棒棒糖。印象最深的是高二分班前夜,她給大家放電影《肖申克的救贖》,當甜美的高音二重唱《今宵微風吹拂》在教室響起,陽光、雨露、月色、花香同時來到每個人的心中,化解著無處安放的躁動和憂郁。
時間帶著人飛跑,身后風景成了明信片,我們交換閱讀,驚嘆連連。六個不同星球的生物,落到同一個暗黑營地,必須斬妖除魔,才能重生——這是小潘的說法。開學前大家遞交了生活習慣和興趣愛好的調查問卷,以為住在一起的將是性情相似的人,然而實際卻如此千差萬別。離奇“算法”使人費解,或許這正是世界的玄機。
宿舍朝向西北,對著校園的湖,遠處有大片空地,稀稀拉拉長著一些植物,相鄰學院的擴建工程似乎總在休眠狀態,塔吊高懸,靜物般隱藏著張力。再遠處橫著高速公路的立交橋,傍晚時從窗口望去,渾圓的落日懸在天際,橋上車來車往,落日一點一點被夜色吞噬,流溢出無可名狀的沉寂之美。
從秋到冬,再從春到夏,卓婭坐在窗前看落日的次數越來越多,像極了圣-埃克蘇佩里筆下悲傷的小王子。她在大一下學期談戀愛,大二下學期分手,度過跌宕起伏的一年。我們忍耐著,看她高調秀恩愛,留長發,穿長裙,為那個男生省吃儉用買禮物,爭吵猜疑,淋雨哭泣。她本以為一切如高原景物般具備清晰的輪廓,不含糊不茍且,沒想到在感情中迷失了方向。從前那個充滿熱力的小太陽,變成一株濕答答的滴水觀音,一度卑微得讓全宿舍的人都抬不起頭。她的分手夜是全宿舍的狂歡節,徐嬌專門下樓買可樂和薯片,砰砰砰,嘭嘭嘭,漫天爆米花飛舞,梁靜茹的《分手快樂》太軟弱,被小潘換成霉霉的Last Christmas(《去年圣誕》),我們以圍巾結成長裙,在夜燈旁跳鍋莊,直到把卓婭逗笑。
除去這段不成功的經歷——成不成功已不重要,作為卓婭戀愛的見證者,我們真切感受到她歷劫后的成長。全宿舍只有段亦塵處于持續的戀愛進行時。雖然徐嬌動輒“我也是有老公的人”,她最初微信名為“彭于晏老婆”,被輔導員在班會上不點名批評:“個別同學,認知停留在初中水平,盲目追星,網名粗俗……”于是她改為“晏晏家那口子”,仍然被批,最后改成“彭&徐”,可能覺得已無可救藥,輔導員不再管她。在大家眼里,小潘是個滿嘴跑火車的孩子,我雖沒有戀愛經驗,卻是理論家,解答婚戀問題時頭頭是道,而悅悅從入學開始就不改“學霸”秉性,學習外的時間還要跟水土不服作斗爭,從胃腸失調到皮膚過敏,根本無暇顧及其他。段亦塵男友是她的高中同學,他上了北大,她考到這所幼師學院,從隱蔽的早戀,到落差極大的異地戀,充斥著種種不確定,但她并沒有很焦慮,最起碼在我們面前沒有過多表現。“順其自然吧,記住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就行了。”她有一顆與實際年齡不相稱的佛心。
有關焦慮,悅悅最有發言權。第一年高考,她考完第一場就崩潰了,心悸,發抖,出汗,控制不住地哭泣,甚至不愿睜開眼睛。復讀一年,她擔心噩夢重演。再次高考前,從前的競爭對手特地請假回來帶她去爬山,那個微胖的女孩當年以全校第一的成績被一所985 錄取,學了生物。在清風吹拂的山頂,她告訴她高考并不可怖,大學也絕非萬事無憂,進大學后自己拼盡全力只勉強達到及格線,有兩門課程還差點掛科,無奈之下拋開矜持,常跟同學交流,在思想的碰撞中不斷調整自我,尋找出路。
她們的人生尚淺,還談不上“相逢一笑泯恩仇”,卻因坦誠而多了前所未有的心氣相通,那一刻,悅悅感到某種釋懷。極目遠眺,飛鳥在天際輕盈掠過。她認定那是傳遞信息的青鳥,很難說清它來自何方,去往何處,卻是她晦暗青春里最為鮮明的記憶。
“你們相信青鳥的存在嗎?”一次夜聊,悅悅問大家。睡前的昏沉中,我仿佛看到她窮究不舍的眼睛。鹽城的風吹粗了她的皮膚,跟家人視頻時,她媽媽對她用了“壯實”一詞。她喜歡所學專業,還額外完成自考項目,摒棄外來的壓力后,她從學習上獲得了真正的快樂。
裝睡是不可能的。我含糊地表示許多詩詞里都有青鳥的蹤跡。卓婭尤其愿意相信,因為高原人一向珍惜各種生命體之間的聯絡。而徐嬌認為是迷信,她不喜歡帶有縹緲色彩的東西。段亦塵則把它定義為一種意念,并從哲學和醫學兩方面進行解釋。
“我玩過一個游戲,龍族憑借青鳥的智慧化解危機,并尋找到最適合族群生存的星球。且不說游戲投映現實,平行宇宙里存在一切可能。”小潘說了一番老氣橫秋的話。
春學期一開始,我們就在宿舍上網課,看老師在空蕩蕩的教室對著桌椅講話。每次打飯宿舍只能派出一個人,拎著飯菜艱苦地上下樓。浴室不開,洗澡在宿舍解決。快遞、外賣一概停止。每天核酸,各類填報瑣碎而繁雜。書桌緊鄰窗臺,因此我常對著那個湖發呆。它的大名叫“學子湖”,呈彎月狀,周圍綠蔭環繞,像通透的翡翠,更像通往無垠宇宙的神秘海。
草木不管疫情,自顧自生長。封校多日,西校區的樹上掛滿青藤,水泥路也長出雜草,于是出現了蛇。保衛科掛起警示牌,起先集中力量對草木進行大規模修剪,接著四處投藥,結果湖里漂起死魚,中毒的老鼠步履蹣跚地出現在陽光下,抽搐著死去。
我一度認為它不會好了,曾經的“相看兩不厭”變成如今的“相顧空淚垂”,疫情起伏,想來實在使人喪氣。可是有一天,湖邊響起機器的轟鳴聲,一群人在那兒忙忙碌碌,兩天后,水被抽干,露出幽深的湖底,填山造海的人們繼續忙碌,清污,建造,修補,打掃,持續兩周,最后往里面注水,一場奇跡般的工程這才宣告結束。
接連幾天雨,氣溫驟降。中午輪到我打飯,特意提前下樓,先到湖邊游蕩。我有點愧對湖,因為曾對它失去過信心,而脫胎換骨后的它仿佛并不介意。湖水在寒風中顯得格外潔凈,新砌的護坡也展示著樸實的造型,波光粼粼中,依稀有魚游動。我走近幾步,想看得清楚些,忽然聽見有人喊我。
“同學,同學!”幾步遠的柳樹下,站著一個年輕的女老師,黑發齊肩,系著紅圍巾,抱著書,應該是剛下課。她取下口罩,沖我熱誠地笑著。
我也向她致意。她走過來,簡單地聊了幾句,臨走時,把圍巾系在我脖子上,關照我早春氣候變化無常,注意頭頸保暖。
懵懂著去打飯,回宿舍后大家猛夸新圍巾,于是我講起湖邊際遇,并勸大家別頹廢,那個老師說很快就要恢復線下上課了,琴房、舞蹈室、圖書館、體育場也將正常開放,我可以去琴房找她還圍巾,她每周六都在那里給鋼琴調音。在舍友們的哄笑和提醒中,我這才明白老師的良苦用心,原來她以為我心理出了問題,于是不動聲色地進行勸慰。再次望向窗外,湖在那里,不遠也不近,靜默地流淌著溫情。
大二一個很普通的晚上,連著幾天,氣溫都很高,出現了蚊子。卓婭癡迷于新入手的花露水,噴得太多,導致整個宿舍彌漫在濃烈的香味中。徐嬌在上鋪連打幾個噴嚏,表示忍無可忍,段亦塵說聞到了夏天的味道。我沒吭聲,但下一秒,耳機里就響起了《夏天的風》。手機播放的是未知電臺的歌,播到哪首都是隨意的,歌聲傳出的瞬間我呆住了,一下子就明白了電影里經常因美麗的巧合就對某個人心動的感覺。正是這些看似偶然的點滴,使我們感知外界,并與萬物產生關聯。
轉眼來到大三,專業理論進入最后階段,過后便是各種實踐與考試。同學中,有人即將結束學業踏上社會,有人繼續在本專業考本讀研,也有人打算改變專業開啟新的人生方向。學校請來一位早已退休的特級教師給我們講課,四個學前教育班的同學,把偌大的階梯教室坐得滿滿當當。
老教師從教五十余年,從普通教育開始,到后來解決特殊兒童的教育難題,在漫長的教、學、研過程中潛心摸索,使一個又一個幾乎被放棄的孩子獲得正常的人生。課程快結束時,有同學問,如果試過多種方法,仍不見成效怎么辦。
“投入全部的真誠,重復和堅持。”老教師回答。
她一頭花白的短發,背也略顯佝僂,眼睛卻讓我想到清澈的湖水。身后黑板上,掛著她逐一講過的圖片,蒙特梭利,三維立體,全息音樂環境,圖畫法……有幾張還在輕輕搖晃,仿佛提醒大家注意它們的精彩。她和它們一樣,散發著從容的氣息;她在我們身邊,帶有真切的關懷,因而更加堅定和純粹。
窗外是學校的植物園,正值豐沛濃烈的深秋,松樹結著松塔,碩果累累,槭樹科植物絢爛多彩,如激情飛揚的大幅油畫。陽光灑滿教室,照著一排排桌椅,一級級臺階,一個個身影。流金歲月,我們感悟著,質疑著,探尋著,發現著,如同世間青鳥,從未停止飛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