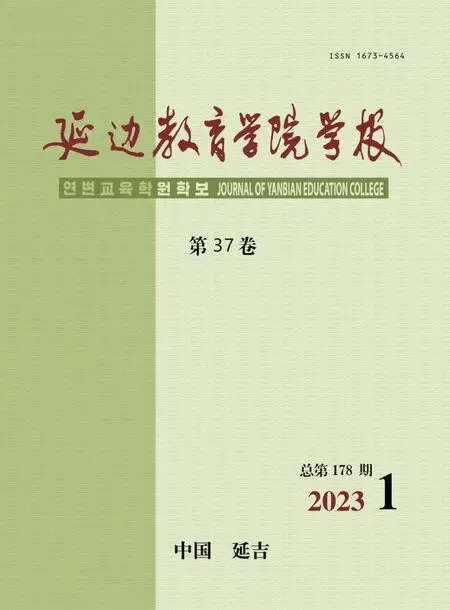試論儒家美學在人格塑造中的建設性意義①
吳慧珍
(漳州科技職業學院,福建 漳浦 363202)
泱泱華夏最初的美感記憶,大約可以追溯到那個“羊大則美”的上古時代。東漢經學家許慎對于“美”在字源上的追溯為:“美,甘也,從羊從大。美與善同意”。由此,可以衍生出兩種不同的內涵:一則,“羊大則美”,是由于感官上的直覺體驗,它很好地滿足人自身的身體欲求;二則,“美與善同意”,則很可能在于它隱含了一定的倫理需求或說社會意義。從許慎對“美”的解釋中,我們或可追溯華夏美學中尤其是儒家美學之中非常重要的一些特質,而這些特質構成了我們的審美傳統中舉足輕重的共同記憶。
春秋戰國時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際,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先哲自覺繼承夏商周三代文化遺產,涵泳六經,遠宗堯舜道統,近守文武禮制,孔子以“仁”釋“禮”,為莊嚴肅穆、規整有序的“禮”注入了溫情脈脈的“仁”的心理情感,把“禮”從外在的社會性的規范約束引向個體人心,變而為人性的自覺,把理性的社會秩序建構在感性柔軟的人性沃土之上,從而使孔門仁學具有了超越時代局限的原始人道主義色彩。
在儒家學派對“禮樂”文化的繼承與重塑過程中,儒家的美學也自覺承繼“羊大則美”“美與善同意”的上古遺風。若要探討儒家美學之于人格教育的建設性意義,則需要回歸對儒家美學的特質的探討,而這種探討毋庸置疑,不能脫離孔門仁學的語境。
1 實踐理性的生命情調
先秦儒學尤其是孔門仁學的一大特點在于貫穿著強烈的實踐理性。李澤厚先生具言:“這種‘實踐理性’,首先指的是一種理性精神或理性態度。……用冷靜的、現實的、合理的態度來解說和對待事物和傳統;……用理智來引導、滿足、節制情欲;……在人道和人格的追求中取得某種均衡;……一切都放在實用的理性天平上加以衡量和處理。”②
在審美問題上,儒家美學顯然也滲透著這種“實踐理性”。《論語·述而》載:“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在人格修養中,“道”是志向,“德”是根據,“仁”是歸依,“藝”則側重陶冶,傾向于指代“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在這四者之中,如果說,前三者是一種內在的自我建構,那么“藝”就是對這種建構的一種補充。換言之,前三者是不易外顯的內涵,“藝”則是這種內涵的外在流露與表達。而“游于藝”這種掌握了技藝規律的自由,建立在“道”“德”“仁”的基礎上,卻又是人格修養的高階境界。孔子不止一次強調審美對于人格建構的意義,《論語·泰伯》載:“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在人格修養的實踐中,“詩”帶來的是心志的啟發、智慧的開蒙,“禮”則規范了人的社會意識、外在理性,而內在心性的塑造則需要通過“樂”的熏陶來完成。
由此觀之,孔子為人格涵養指出了一個路徑——“文質彬彬,然后君子”——既是由內而外的發揚延伸,亦是由外而內的反哺滋養,而人格的最終完成,訴諸審美。孔子不僅在理論上為世人指引了修養的道路,更重要的是,他也用一生在踐行、貫徹他的審美主張,為世人指出的是一條具體可感、切實可行的踐行之道。《論語》多處記載了孔子的審美實踐和審美體驗,諸如“侍坐篇”之“吾與點也”的志趣,“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的陶醉,凡此等等。誠如余秋雨先生所言:“孔子對我們最大的吸引力,是一種迷人的‘生命情調’——至善、寬厚、優雅、快樂,而且健康。他以自己的苦旅,讓君子充滿魅力。”③
2 溫柔敦厚的詩樂教化
孔子從內在的涵養出發,將人格修養的完成指向審美。那么,儒家的人格建構是如何在審美之中得以完成的呢?從《論語》到《樂論》,乃至《禮記·樂記》,儒學諸子就此問題圍繞“藝”“樂”形成了相對系統的論述。《論語》中的“藝”“樂”基本上是一種對于藝術的隱約寬泛的指稱。“樂”見諸《禮記·樂記·樂象》:“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樂器從之。”“藝”則指代“禮樂射御書數”等“君子六藝”。用我們現在的理解,“藝”“樂”基本可以解釋為陶冶性情的藝術形式,而在儒家尤其指稱“詩樂”。
2.1 “思無邪”與“興觀群怨”
孔子非常重視詩歌的思想情感對人心的教化作用,他曾不止一次勸勉后學“不學《詩》,無以立”。《論語》中多次提及他與弟子們討論《詩經》的審美意義。《為政》篇載:“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八佾》篇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直言《詩經》思想情感的表達合乎分寸而不過度,可使人歸于中正平和。
不止于“思無邪”,孔子還認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陽貨》)。“興”,乃“感發志意”(朱熹);“觀”,是“觀風俗之盛衰”(鄭玄);“群”,是“群居相切磋”(孔安國);“怨”,是“怨刺上政”(孔安國),即反映民情。
在此,孔子確立了詩歌中正平和的審美傾向,又非常全面地論述了其言志、觀風俗、相切磋、美刺等作用。在詩歌的美感未獲得全面認知的時代,孔子首先給予了它非常重要的社會教化功能,從而賦予了華夏詩歌美學以第一重含義——善!亦即,詩歌的美,首先在于它傳達了一種中正平和、和柔巽順的善。這樣一種“美與善同意”的美學主張,開啟了兩千年“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從而使得我國的文藝傳統烙上了鮮明的人格色彩。
2.2 先王立樂以化人
孔子對于音樂的重視,一點都不亞于詩歌,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才會有“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這樣始于“詩”成于“樂”的論述。如果說,詩歌的教化功能在于興發感動,啟發智慧,那么音樂則以更直接的方式深入內心情感的熏陶與塑造。
儒家先賢對音樂陶冶人心的力量有著普遍敏銳的直覺。他們認為,音樂源自人心,《禮記·樂記·樂象》有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謂之樂。”這種發源于內心感動的合于音律的音樂形象,以它獨特的形式傳達著人的精神意趣、情感節奏。荀子《樂論》開篇即言:“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于聲音,形于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即是說,音樂的產生本是順應人們情感上的需要,而先王作樂便是意在因勢利導,節制和感化人心。《禮記·樂記·樂本》則進一步論及“審樂以知政”:“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正因為敏銳地察覺到詩樂對于移易情感、陶冶性情、塑造人格的巨大助益,孔子才付出了巨大的心力在詩樂的審美教化之上,據司馬遷《史記》記載,孔子曾經對《詩經》進行大規模的音樂校正工作,使之合于雅頌之音,以合于禮樂涵養。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孟子),“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荀子),音樂以其發于肺腑、不可作偽的“真”,通過特定的節奏、韻律表之于“美”的形式,最終又為人心所感,直抵人心柔軟,達到陶冶性情、塑造人格的目的,即“善”。從而,在儒家先哲這里,審美與人格涵養再度相輔相成,“詩樂”教化貫穿人格塑造之始終。
3 中庸至德的哲學尺度
儒家對于詩樂的美學寄托,包含著非常鮮明的倫理色彩,也包含著深厚的情感色彩。而為了使這種用力不至于過度,先哲依然把這種美學主張納入“中庸”的界限之內。《論語·雍也》載:“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朱熹引注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亦即“允執厥中”,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之意;“庸”即用,亦即尋常實用、恒常不易的穩定狀態。儒家把“中庸”奉為“至德”,強調在一種不極端的權衡變通之中達到精準的恒久的平衡、穩定,亦即恒常。這種不極端的分寸感,體現在它的美學思想中,便是情理兼勝,便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便是“樂由中生,禮自外作”。
3.1 情理兼勝
儒家的美學處處可感的是豐盈的人情味,它繼承了上古“羊大則美”的遺風,并不排斥現實人生中的感官快樂,而是對之采取了一種積極的接納態度。荀子《樂論》言:“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然而,儒家對這種感官快樂的肯定、包容卻并不是無度的,而是非常自覺地納入理性之中的。誠如孔子對《韶》樂的欣賞與陶醉,是因為“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論語·八佾》)。美是從藝術形式、感性層面說的,善則指藝術作品理性層面的、社會性的內容,亦即造就美的本質意義。感性的抒發總是在符合社會的理性規定中進行,才能實現感性與理性、自然性與社會性的融合統一,這依然可以歸結到“文質彬彬,然后君子”的教誨,也是從“羊大則美”的感官快樂,指向“美與善同意”的人格涵養。
3.2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儒家美學非常重視藝術對人心的建構作用,但也非常重視對其尺度的把握,倡導的是“發乎情止乎禮義”的“中和”之美。《論語》就曾多次強調《詩經》“思無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中正平和之美。《中庸》有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人的各種情感應當接受一定的規范、節制,使之不過度。梁漱溟先生《儒佛異同論》指出:“情感動于衷而形著于外,斯則禮樂儀文之所以出,而為其內容本質者。儒家極重禮樂儀文,蓋謂其能從外而內,以誘發涵養乎情感也。必情感敦厚深醇,有發抒,有節蓄,喜怒哀樂不失中和,而后人生意味綿永,乃自然穩定。”深厚的情感,發之以節制、溫和,是豐盈的性情的抒發,亦可成為對接受者的心靈的一種雋永綿長的熏陶、滋養。
3.3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
儒家將“禮樂”并舉,《禮記·樂記》認為“樂由中出,禮自外作”,又認為“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秩序也。和,故萬物諧化;序,故群物皆別。”在這里,音樂超越了一般的藝術形式,而獲得了非凡的倫理意義。“禮”是從外在的規范、約束來塑造人的社會性從而建立秩序的,而“樂”則直接訴諸人的內在情感意志。“禮”的作用在于區分等級差異,而“樂”則能彌合差異與等級,二者一表一里,相輔相成,完成對人的塑造乃至實現社會的穩定。
儒家先哲很早便意識到,“樂”是人內在性情、修養的一種具象的抒發,是人之品德、涵養的藝術化呈現。《禮記·樂記·樂象》又言:“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以為偽。”在音樂之中,蘊涵著深厚的情感,恢弘的氣象,柔順的情志,外化為美妙的形式,傳達出高遠、超越的境界。音樂以它的真、善、美使我們感蕩心靈、澡雪精神,從而凈化、提升思想境界。
由此觀之,儒家先賢“禮樂”并舉,由禮而樂,由理性而感性,于感性中包蘊理性,從邏輯語言走向音樂語言,從表現倫理的語言導向審美的語境,把“真”“善”的追求融匯于“美”的境界之中,從而完成對人格的陶冶塑造,而從始至終貫穿著“中庸”的哲學尺度。
4 結語
信息時代瞬息萬變,人生充滿未知,人于現實世界中浮浮沉沉,知識是應變之術,卻非安頓人心之道。眾生于這無常世間,尋找精神的安頓,或走向宗教,或走向哲學,或走向藝術。而早在兩千多年前的理性覺醒之時代,我們的儒家先哲,便已為世人鋪就了一條“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修養之路,孔子說“修己以安人”(《論語·憲問》)。而這“修己”,便是人格塑造,便是精神安頓。如何安頓呢?夫子說“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人格的涵養,“道”是志向,“德”是根據,“仁”是歸依,這是內在的自我建構,是內在理性秩序的自我完成,而“藝”則是這種內涵的流露與表達,卻同時也滋養著這個理性的內在世界,正所謂“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誠如宗白華所言:“藝術的境界,既使心靈和宇宙凈化,又使之深化,使人在超脫的胸襟里體味到宇宙的深境。”④儒家的美學理念,出之以“真”“美”,而最終達于“善”之境,于人格修養一路,確乎指引了一條切實可行又高瞻遠矚的路徑,乃至千年以降,無數后學引以為精妙法門。
近年來,我國復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成大勢所趨,意在返本開新。如今,高職教育提出課程思政化的指導方針,也意在立德樹人。而于此,儒家先哲無疑為我們今日的審美教育與人格教育都提供了許多具有跨時代意義的指引,吾輩懷鉛吮墨,亦當“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暉以自燭”(鐘嶸《詩品》),自覺傳承先哲的教導,或可在三尺講臺立為一方師表,照應后來者。
注釋:
②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孔子再評價[M].北京:三聯書店,2010:25.
③余秋雨.中國文化課·孔子的路[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20:62.
④宗白華.美學散步·中國藝術境界之誕生[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