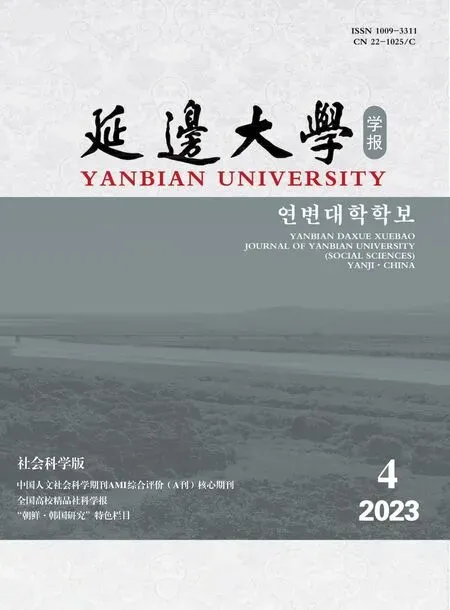丁若鏞“自主之權”與“善惡”的內在邏輯探析
高明文 崔美玲
“自主之權”是丁若鏞(1762-1836,字美庸,號茶山)自己創造出來的新概念,是支撐他倫理學體系的三個核心要素之一。因此可以說,對自主之權的理解會直接影響對丁若鏞倫理學的整體把握。如果丁若鏞的倫理學是一個完整的體系,那么我們必須假設其“自主之權”有一個“原意”。那么,這個原意到底是什么?這是本研究主要解決的問題,進而揭示“自主之權”與“善惡”的內在邏輯關系。
當前學術界對丁若鏞的“自主之權”觀念主要有兩種路向的研究:一種是從《天主實義》的觀點出發探究其含義,認為丁若鏞的“自主之權”觀念源于對利瑪竇(M.Ricci)“意愿”(通常被解釋為自由意志,即free will)觀念的繼承。(1)[韓]白敏禎:《茶山心性論的道德情感與自由意志》,《韓國實學研究》2007年第14輯,第405頁;Don Baker,“Thomas Aquinas and Chong Yagyong:Rebels Within Tradition”,Journal of TASAN Studies,No.3(2002),p.61;[韓]金榮一:《丁若鏞上帝思想》(韓文版),首爾:景仁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96-204頁。另一種是從康德(I.Kant)哲學的視角分析,認為丁若鏞的“自主之權”應當被理解為道德性自律(moral autonomy)。(2)[韓]張勝熙:《茶山丁若鏞倫理思想中的自主之權研究》,《民族文化》1998年第21輯,第280頁;Mark Setton,Chong Yagyong:Korea’s Challenge to Orthodox Neo-Confucianism,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7,p.85.以上兩種路徑的研究有不同之處,也有共同之處。不同之處在于前者強調“自主之權”是人可以自由地在善與惡中選擇其一的能力,后者強調“自主之權”是人可以戰勝惡的自我約束能力;共同之處在于二者都預設了絕對的“善”和“惡”,同時也預設了人具有客觀判斷“善”和“惡”的超驗能力。
這種在絕對的善與惡中選擇其中之一的思維方式是傳統西方倫理學中常見的形態,但是在東方倫理學中卻并不多見。丁若鏞作為朝鮮朝后期最著名的儒家學者,創建“自主之權”概念難道只是為了引進西方哲學中的自由意志觀念或是道德性自律?如果真是如此,丁若鏞又該如何解決自由意志觀念與儒家仁學體系之間的張力?在這些問題意識的推動下,通過研究發現,丁若鏞的“自主之權”與西方傳統哲學中的自由意志或道德性自律大相徑庭。
為盡可能接近“自主之權”的原意,探究“自主之權”與善的內在邏輯關系,本研究選擇詮釋學(hermeneutics)“以經解經”的方法論,即通過文本(text)詮釋文本。在文本的選擇上,本研究將采用茶山學術文化財團于2012-2015年整理并出版的《定本與猶堂全書》。(3)丁若鏞的著作起初以《與猶堂集》《洌水全書》等不同書名流傳下來,后來為紀念丁若鏞逝世100周年,其外玄孫金誠鎮歷經5年時間重新加以整理,由鄭寅普和安在鴻校對,于1938年完成了總154卷、76冊的鉛活字體版《與猶堂全集》,文本質量不高。為此,茶山學術文化財團于2012-2015年對丁若鏞著作重新進行整理并出版《定本與猶堂全書》(以下簡稱《全書》,本文所引相關參考文獻均出自此書),《全書》共37冊。
一、權:認知主體的能動性
丁若鏞在東方倫理學的發展史上做出了三個重要的貢獻。其中之一就是首次提出了“自主之權”概念,以強調每個人都具有“欲善則善”的自主性和能動性。那么人的自主性是如何可能的呢?在這樣的本質性反思下,丁若鏞給出的根據是因為人的心具有自主之權。他說:
天之于人,予之以自主之權,使其欲善則為善,欲惡則為惡,游移不定,其權在己,不似禽獸之有定心。(4)丁若鏞:《全書》第7卷《孟子要義》,首爾:茶山學術文化財團,2012年,第94頁(下同,不再標注)。
天之賦靈知也,有才焉……。才者,其能、其權也。麒麟定于善,故善不為功,豺狼定于惡,故惡不為罪。人則其才可善可惡,能在乎自力,權在乎自主。故善則贊之,惡則訾之。(5)《全書》第13卷《梅氏書平》,第362頁。
根據丁若鏞的觀點,人有“心”,動物也有“心”,但動物的心是受動的定心。例如,麒麟的定心只會使其行善,豺狼的定心只會使其行惡。既然動物的行為已被定心鎖住,那么它們的善行就不能算為有功、惡行不能算為有罪。如果一種行為不能論功論罪,那么行為的主體自然就不會為自己的善行感到自豪,也不會為自己的惡行感到羞恥,更不必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
然而,丁若鏞認為,人與動物不同,人的心有動物所沒有的“自主之權”,并進一步主張:就是這個“自主之權”使人的心具有了開放性和能動性。那么他所謂的“自主之權”到底是什么?“自主之權”為什么能夠使人的心具有開放性和能動性?若要理解此概念的內涵,首先要澄清“權”字在丁若鏞倫理學體系中的含義。“權”字在他的著作中主要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權力、權勢或職權。在《經世遺表》《牧民心書》《欽欽心書》中他說:
宋初趙普為樞密使,與中書省,并立分權,互稱二府,其職之要且重如是也。(6)《全書》第24卷《經世遺表》,第100頁。
嘉慶辛酉秋,睦萬中、洪羲運、李基慶等,操生殺之權,日除善類,如草薙禽狝。(7)《全書》第3卷《牧民心書》,第376頁。
縣監崔倫怯于權勢,只囚驛吏,余悉不問。(8)《全書》第30卷《欽欽心書》,第104頁。
從以上例文中可以看出,丁若鏞的“權”概念確實有權力、權勢或職權等含義。但是丁若鏞并沒有將“權”概念僅僅局限在這一層面上使用。在他看來,“權”概念在儒家思想中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核心概念之一。但如果只把“權”字理解為權力、權勢或職權,不僅會使人誤認為自己真的具有可以為所欲為的權力而做出反中庸的行為,還會給社會帶來“爭權”的不良風氣。為此丁若鏞試圖運用乾嘉考據學的方法還原“權”概念在先秦儒學中的含義,并將其安排到自己倫理學的核心位置以穩固體系的對稱性。他在解釋孔子的“未可與權”時說:
權者,圣人之切喻也。有衡于此,其星五兩也。置銀子一兩則其權縣于一兩之星,乃得中也。銀子三兩則其權不得膠守一兩之星,必移之于三兩之星,然后乃得中也。以至四兩五兩,莫不皆然。禹稷胼胝,顏回閉門,皆移之而得中者也。尾生抱柱,伯姬坐堂,皆膠之而失中者也。權之所期,在乎中庸。圣人所謂擇乎中庸,正是衡人之擇星以安錘也。后世論道者,率以中庸為經,以反中庸為權。于是,喪不守制曰權,葬不備文曰權,貪縱不法曰權,篡逆無倫曰權。凡天下悖亂不正之行,一以權為依,斯蓋世道之大禍,程子所論嚴矣。唐陸贄《論替換李楚琳狀》云:“權之為義,取類權衡。衡者,秤也。權者,錘也。故權在于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于事,則義之輕重不差。若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奸邪,由此誤也。”案,此論明確真切。(9)《全書》第8卷《論語古今注》,第340-341頁。
丁若鏞認為“權”字的原意應該是“秤砣”,用來測量物體的重量。測量物體的重量時一邊掛著要測量的物體,另一邊用秤砣左右移動尋找平衡(中)。他還認為,孔子將具有“秤錘”意義的權字延伸為“衡量事物輕重”的“權衡”使用。但是到了孔子之后,那些熱衷于論道的人卻將“權”字理解為權力、權勢、職權等,犯下各種敗亂和錯誤,成為世道之禍根。為此丁若鏞特別提起程子對“權”的解釋,還引用唐朝政治家陸贄文章中的一段話強調人有判斷情境并規劃符合情境行為的心之權衡。(10)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116頁。程子曰:“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同時,丁若鏞還舉了兩組例子。一組是“禹稷胼胝”和“顏回閉門”。禹、稷和顏回的行為雖然表面上看似完全不同,但是在丁若鏞看來都做到了符合各自情境的行為,因此可以視為“中”。第二組是“尾生抱柱”和“伯姬坐堂”的故事。尾生抱柱的行為雖然看似“信”,伯姬坐堂的行為雖然看似“貞”,但在他看來都不能算符合情境的行為,因此不能視為“中”。
由此不難看出,丁若鏞概念體系中的“權”實際上就是指包括情境判斷能力在內的邏輯性推理能力。關于這一結論還可以從他的其他論述中得以證實:“心之為物,活動神妙,窮推物理,即日月星辰之運、天地水火之變,遠而萬里之外,遂而千古之上,可以放遣此心任其窮。”(11)《全書》第6卷《中庸自箴》,第216頁。“人之大體,即生即知,復有靈明神妙之用,故含萬物而不漏,推萬理而盡悟。”(12)《全書》第9卷《論語古今注》,第278頁。丁若鏞認為人的心是活動的心。它活動神妙,可以使人掌握事物的運行規律、變化規律,并用之以推知千萬里之外的事、遠古的往事,甚至還可以推知尚未發生的事。
如此這般的人心之權在面對道德情境時也會發揮其神妙的作用。例如,當某人處于特定情境時,首先會判斷自己所處的情境并加以分類,然后再探索和規劃符合當前情境的道德行為。在探索和規劃符合特定情境的行為時,會在多種可能性中預設出幾種可行的最佳行為。例如,“如果我在這種情況下做A的行動,就很有可能會出現A′的結果;A′的結果是否符合目前的情境?如果同樣情境下做出B的行為,出現B′結果的概率就會很高,那么B′的結果是否符合當前的情境?如果在這種情境下做出C的行為……。”這樣的心理活動與杜威的“倫理預演”(ethical rehearsal),或者與約翰遜(Mark Johnson)的“道德想象力”(moral imagination)有相似之處,即都需要花費一定的時間。如果情境簡單則需要的時間就會少;如果情況復雜,則需要的時間可能會更多,因為所有的變數都要在人的心中一一被權衡。當然,圣人也不例外。丁若鏞對圣人的推理過程做了如下描述:
擇乎中庸者,非就中庸之內,擇執其一善也,每遇一事,商度義理,陳列眾善,擇取其合于中庸者以自守也。(13)《全書》第6卷《中庸自箴》,第244頁。
圣人于未發之時,戒慎恐懼,慮事窮理,甚至有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為思慮……中也者,不偏不倚之名。必其人商度事物,裁量義理,其權衡尺度,森列在心,無偏倚矯激之病,然后方可曰中,方可曰大本。又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之事,一一點檢,驗諸天命,然后方可以得中。(14)《全書》第6卷《中庸自箴》,第293頁。
根據丁若鏞的理解,不管是圣人還是凡人,不管是小到個人行為還是大到集體行為,想要做出符合情境的行為都要經過商度義理、陳列眾善、一一點檢、驗諸天命的過程。行為規劃完成以后,如果能夠將其轉化為現實中的具體行為,且達到了預期目標,那么就可以在此行為之上貼之以“仁”“義”“禮”“智”“信”等具有道德性質的概念符號。但如果在判斷情境時發生誤差或者在商度義理、陳列眾善、一一點檢、驗諸天命時出現失誤就會直接造成行為的偏移。因此,丁若鏞在探討善惡的關系時曾說:
夫善與惡對,未盡善則歸于惡而已。善之與惡,如陰陽黑白。非陽則陰,非白則黑,陰陽之間無非陰非陽之物,黑白之間無非白非黑之色。即未盡善,明有一分惡根,未及盡去者也。(15)《全書》第8卷《論語古今注》,第137頁。
在丁若鏞看來不存在西學所謂的“絕對的善”和“絕對的惡”,如果存在,那么人的行為中不屬于二者的一般行為就如同動物的行為沒有著落,沒有責任。所以他強調只有“符合情境的行為”和“不符合情境的行為”。試想秤砣在秤桿的情形,秤砣只要稍微脫離適當的位置,它的平衡就會崩塌。尋找平衡點的位置是一項高難度的技術活動,而非簡簡單單地在善和惡中選擇其一的自由意志問題或是制約惡的道德性自律。學者高承煥也曾提出過與此相似的主張。他在解釋丁若鏞的“擇善”概念時認為,所謂的擇善是指在眾善中選擇一等的善,而非在善與惡中做出決斷。(16)[韓]高承煥:《茶山丁若鏞權衡論探析》,《茶山學》2016年第9期,第199-200頁。因此可以很確切地說,丁若鏞所謂“可善可惡”應該被理解為“所有人都能做出符合情境的行為,也能做出不符合情境的行為”。這是一種非形而上學式的善惡觀。
總之,丁若鏞的“自主之權”不是人可以為所欲為的權利,也不是決定生殺的權力,而是以善為目的的行為規劃能力。若如丁若鏞所言,每個人都具有“自主之權”,就意味著每個人都能夠行善。如果每個人都能夠行善,就意味著每個人都能夠決定自己要不要行善。如果每個人都能夠決定自己要不要行善,就意味著每個人要對自己的行為承擔相應的責任。(17)William K.Frankena,Ethics,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3,p.170.因此,可以得出結論:丁若鏞的“自主之權”中包含人的決定、能力和責任。
二、惡:思維的停滯
上文著重分析了“自主之權”的內涵。經過分析發現,丁若鏞的“自主之權”是以善為目的的行為規劃能力,屬于人的思維活動。如果這一結論符合丁若鏞的原意,那么就可以推知“惡”的產生很有可能會與“自主之權”有密切的關系。關于這一假設,可以從《全書》中充分地得到證實。丁若鏞在《西巖講學記》評價鯀與禹的治水方法時曾說:
凡天下之水,莫不有沖決之性,故決開蟻孔,俄成尋丈之深,唯河水不然,濁流淤淀,挨次增積,河身日高,而致有旁潰泛濫之患。鯀則不明潤下之性,故不思所以,而輒去泛濫處盡力以障之。……禹之治水,雖不知如何用力,而即曰“導水”,則非開導疏鑿之謂耶?后世治河,專用鐵龍爪鑿去淤泥,后出愈巧,可謂得其要者哉!(18)《全書》第4卷《文集》,第294-295頁。
丁若鏞認為,鯀之所以治水失敗是因為他不知道水的潤下之性,因此“不思”如何導水,而一心只想著如何障水,最終釀成千古罪案。相反,禹清楚地知道水的特性,能夠判斷當前水勢不能用堵的方法,而應該采用疏通的方法。至于怎樣疏通水流,丁若鏞雖然沒有在文中詳述,但是我們可以通過以上案例確認兩個倫理學上的重要信息。第一,想要在某件事情上做到不偏不倚,最首要的環節就是正確地判斷情境。如果在判斷情境的時候出現失誤就會直接限制人的思考范圍,從而無法規劃正確的行為。第二,盡管行為者的初心是為百姓造福,但如果行為者的所作所為不符合預期要求仍要承擔相應的責任。除以上案例之外,還可以從《全書》中找到更多類似的倫理案例:
牧之陋者每云:“毋發我笱。遑恤我后。”竭澤以漁,以供一飽,遂使鯤鮞絕種,而蓮子、蓮根、管、蒲之屬,取之無節,亦不厲禁。故國中陂池,皆空澤而已,豈非民牧之羞哉?宜于澤旁置舍為守。凡有所用,皆給本價。設為約條,俾后人遵,斯亦不藏、惡棄之義也。……鮒魚固美矣,何至竭澤以為病乎?夫惟不思之過也。(19)《全書》第29卷《牧民心書》,第158頁。
“牧之陋者”為求一飽,抽干池塘里的水捉魚。這種行為形成風氣,最終導致國中的池塘全部枯干。丁若鏞認為,牧之陋者之所以會犯下這樣的惡行是因為“不思”。那么何為不思?他說:“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20)《全書》第8卷《論語古今注》,第342-343頁。在丁若鏞的概念體系中不思就是不對事情的反面進行考慮,就是指不去發揮人的“自主之權”探索行事之“中”,也可以認為不進行思維試驗。這是一種停止思考的狀態。那么是什么樣的因素阻礙人思考呢?丁若鏞給出了三個因素。
第一,被眼前的利益所誘惑或者是被酒色所誘惑。他說:“蓋云人性本善,其或所行不善者,必由陷溺。陷溺之法,或以財利,或以酒色,而大抵多由于培養。”(21)《全書》第7卷《孟子要義》,第200頁。在丁若鏞看來,人的本性樂善而恥惡。在大部分人的心中進出酒樓逍遙快活的行為和使用暴力欺壓百姓的行為不是善的行為。但沉迷于酒色的人進出酒樓時心中只有一時的快活,不會思考自己的行為會不會給他人帶來多大的傷害,也不會思考這樣的行為會造成怎樣的后果。被財貨誘惑的官吏欺壓百姓時心中只有眼前的利益,不會思考自己的行為會不會給百姓帶來痛苦,也不會考慮自己的行為會使百姓對自己失去信任。
第二,被社會習俗所玷污。他說:“陷溺之術,或以形氣之私欲,或以習俗之薰染。”(22)《全書》第7卷《孟子要義》,第200頁。丁若鏞認為使人拒絕思考的因素中更惡劣的當屬習俗之薰染。他在批判朱熹把“中庸”的“庸”字解釋為“平常之理”時說:“世之人,方且以流俗習紐之事,謂之平常之理。一聞性道之說,方且愕然以為反常違俗。圣人于此,又以平常之理立之為標榜,率天下而納乎平常之軌,其孰不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以習其鄉愿之行哉。”(23)《全書》第6卷《中庸自箴》,第296頁。被眼前的利益或者酒色所誘惑的人增多,社會上就會形成不良的習俗。習俗一旦形成,平常之理也就會隨之而建立,這就會給人的思維帶來很大的限制。朝鮮后期社會上下盜竊成風,偷盜者被抓后常用社會風氣為自己辯護,主張自己的行為沒有錯。但是總有一些出淤泥而不染的人,這些人往往都是知人之性且善于思考的人。
第三,使人不思的最惡劣的因素是陷入異端怪論或占卜。關于這一論斷可以從以下兩段陳述中得以證實。他說:“后世禮樂既壞,情欲自縱,或逸樂而招災,或愁苦而傷和,夭札相續,氣像凄慘,則于是乎噓陽吸氣之術,熊經鳥申之方,馳騖于其間,淫邪幽怪之說,陷溺其良心,金石煩燥之劑,戕賊其天和,無補于壽命之原,而徒使人迷惑而不知反。哀哉!”(24)《全書》第4卷《文集》,第318頁。“今人平居既不事神,若唯臨事卜筮,以探其成敗,則慢天瀆神,甚矣。余疏釋《易》象,為明經也。若有人謂‘《易》例即明,可以行筮’,則不惟占驗不合,而其陷溺不少。此余之所大懼也。今人守正者,宜廢卜筮。”(25)《全書》第17卷《易學緒言》,第280頁。陷入異端怪說或是占卜都意味著放棄思考。二者的共同之處都以某種極端的信仰為前提,都把某種教義或命令作為行為的絕對準則。不同之處在于,陷入異端怪說的人從不考慮自己所處的情境如何,只會把所信仰的教義和命令作為行為的絕對綱領。但沉迷于占卜的人與陷入異端怪說的人不同。他們雖然重視自己所處的情境,但只會按照卜辭的指示去行事,不會自主推測將來會發生什么事情,更不會提前準備應對可能會發生的事情。雖然二者應對情境的方式不同,但都拒絕思考。所以丁若鏞再三強調:不要沉迷于異端邪說和占卜,遇事應多傾聽圣人的告誡,發揮“自主之權”知慮巧思。
若如丁若鏞所言,人人都具有判斷道德情境的能力和推萬里而盡知的能力,那么人的情境判斷和倫理性推理是不是絕對精準且不會出現失誤呢?關于這一問題,丁若鏞認為,即使是圣人也有不能做到的事,且在推理時也會失誤。他說:
道體至大,造端乎夫婦。而及其至也,雖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彼耝耰鍛斫之賤,販糶漁獵之徒,將何以盡知其精微乎?況資稟不齊,愚魯不慧者,貴族亦時有之,況賤族乎?(26)《全書》第8卷《論語古今注》,第300頁。
天之于禽獸也,予之爪,予之角,予之硬蹄利齒,予之毒,使各得以獲其所欲而御其所患。于人也,則倮然柔脆,若不可以濟其生者,豈天厚于所賤之而薄于所貴之哉?以其有知慮巧思,使之習為技藝以自給也。而智慮之所推運有限,巧思之所穿鑿有漸,故雖圣人不能當千萬人之所共議,雖圣人不能一朝而盡其美。(27)《全書》第2卷《文集》,第281-282頁。
丁若鏞清楚地認識到即使是圣人也會在判斷情境和規劃行為過程中出現失誤。他在談論顏回的失誤時說:“《中庸》曰‘民鮮能久矣。’能久則圣人也。顏子不能無過,故曰‘不貳過。’不能無過則不能無間斷,但其間斷甚疏,故曰三月不違。”(28)《全書》第8卷《論語古今注》,第216頁。這也就是說任何人都不可能會做到絕對客觀地判斷和毫無差錯的規劃。即便圣人有超乎常人的能力也不及千萬人共同商議。圣人與常人的區別只在于能做到“三月不違仁”,能做到“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并不是說三個月以來在善和惡中選擇了善,而是能夠長期做到符合情境的行為。
總而言之,丁若鏞認為惡的產生原因是不思。他說:“茍不思之,必至陷溺其心,而失其從違之正。”(29)《全書》第7卷《孟子要義》,第210頁。他進一步主張限制人思考的因素有三種:首先是眼前的利益或酒色,其次是社會習俗,最后是異端怪論或占卜。眼前的利益或酒色屬于個人因素,社會習俗屬于環境因素,異端怪論或占卜屬于迷信因素。然而,丁若鏞并不認為人擺脫了以上因素就能在任何情境中做出不偏不倚的行為,因為情境可分為簡單和復雜。在復雜的情境下,例如社會倫理場合、經濟倫理場合、行政倫理場合、外交倫理場合,一個人不可能做到精確無誤的判斷和規劃,即使做到了也很難在多種可能性中準確地找到最合適的行為。因此可以說,圣人是一點一點磨煉出來的,而不是從天而降的。常人也能通過不斷的努力成為圣人。
三、善:行為的不偏不倚
丁若鏞認為每個人都有“自主之權”,因此人在自己所處的情境中能夠做出符合情境的行為。但是他還認為即使是圣人也不可能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做到不偏不倚。那么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把握情境的適宜,最大限度地規劃行為之善?這是他又一個必須思考的問題。丁若鏞認為,一個人如果想要最大限度地實踐善,首先要做到“誠”,然后要做到“學、問、思、辨”。他在回答李汝弘和金承旨的信中說:
竊以學、問、思、辨之功,非誠不立,一有詐偽,不可曰誠。故鏞于經傳之業,惟是是求,惟是是從,惟是是執。方其擇執之時,未嘗不博考廣證,研精殫智,持其心如鑒空衡平,核其義如斷訟治獄,然后乃敢立說,豈敢以疑似之見,同聲吠影,以違大同之論哉?(30)《全書》第4卷《文集》,第143頁。
茍有志于義理者,宜博求當時事跡,詳知當時文字,又參之以往古之事,以達宇宙之情,然后擇其正而執之,有違于正者,斯攻之斯曉之焉,可也。(31)《全書》第4卷《文集》,第66頁。
以上雖然是關于丁若鏞做學問的方法,但是同樣適用于倫理實踐之中。一個人想要行事為善,最重要的就是誠。誠在他的倫理學體系中具有多重含義。從上到下的順序來說,首先,可以理解為“天道”;其次,可以理解為“人道”;最后,還可以將其理解為人道與天道合一的慎獨功夫。(32)[韓]張勝熙:《茶山丁若鏞的誠修養功夫與道德教育》,《道德倫理教育》2012年第35號,第85頁。但如果從丁若鏞行事倫理的角度來講就可以理解為一個人渴望行事為善的真誠無妄的態度。丁若鏞之所以強調誠,是因為人在行事前和行事中的“慎重”“認真”“持之以恒”等態度都源于此。因此可以說,誠是一切善行的第一級階梯。所以他在寫給李汝弘的信中強調不能有“詐偽”,在寫給金承旨的信中強調要“志于義理”。
其次,就是“學、問、思、辨”。眾所周知,學、問、思、辨出自《中庸》第二十章:“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丁若鏞以此作為行事為善的方法論。他說:“學、問、思、辨,乃誠之者之所為也。”(33)《全書》第6卷《中庸自箴》,第263頁。他在《答洪聲伯簽示》中探討“古之學者”與“今之學者”的區別時還說:“古之為學者五,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今之為學者一,曰‘博學之’而已。自矜也,故不欲審問。虛驕也,故不欲慎思。怯懦也,故不欲明辨。本無真切為善之志也,故不肯篤行。以無篤行之志,故自審問以下,自不能用力耳。然明辨即畢,亦有竟不肯篤行者,斯則尤無良矣。”(34)《全書》第6卷《中庸自箴》,第236-237頁。那么該如何理解篤行前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所謂博學就是通達地學習、廣泛地學習,這是吸收知識的過程。丁若鏞說:“學者,學所以知。”(35)《全書》第8卷《論語古今注》,第32頁。即有關求知的一切行為。(36)[韓]林憲奎:《茶山丁若鏞〈論語〉“學而”“不知命”章注釋研究》,《東洋古典研究》2017年第69輯,第546頁。學的內容包括有關事物本性的知識,有關衣食住的知識,有關灑掃、應對、進退之類的儀節,有關圣人言行的知識,有關自我修養的知識等。任何情境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學的內容都是前人通過畢生的經驗和不斷地學習總結出來的,適用于大部分人和大部分情境的一般知識和事情發展的一般規律,有利于誠之者準確地認識自己的處境,正確地規劃符合情境的行為。因此,學習前人對事物的洞察力、判斷力、理解力和推理能力會為那些從心底想要行事為善的人提供指南。
審問是審慎地探問、深入地追問,是對所學的知識進行鞏固的過程。丁若鏞說:“若志于義理,必須博求當時事跡。”因為即使是圣人也無法超越千萬人共同討論。丁若鏞之所以強調博求當時事跡,其原因是在判斷某一情境時,沒有什么方法比詢問當事人更準確;在策劃接下來的行為時,沒有什么方法比詢問經歷過類似事件的人更為準確。所以,他在《牧民心書》中也說“牧以時巡行村野,問其疾苦,詢其愿欲,曲遂其情,以培其根,勿撓勿侵,如恐或傷,此調大病之法也。”(37)《全書》第29卷《牧民心書》,第315頁。
慎思是謹慎地思考、周密地思索,是對所學、所問的知識進行消化、升華、運用的過程。丁若鏞在解釋《論語》中“季文子三思而后行”時說:“三思,謂熟思也。人惟不思,故恒犯罪惡。使季文子誠能一思再思,豈至黨惡而修怨乎?”(38)《全書》第8卷《論語古今注》,第188頁。在他的倫理學中“思”與“自主之權”具有不可分割的關系。可以說思是“自主之權”的充分條件。其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善。這就引發了又一個東方倫理學中的重要討論,那就是善行能不能必然給行為者帶來喜,帶來福;惡行能不能必然給行為者帶來悲,帶來禍的問題。為此,丁若鏞特別強調“明辨”。
所謂明辨就是明晰地分辨、明確地判別,是擇定行為的過程,即判斷應該走什么樣的路。在丁若鏞看來惡行并不一定會給人帶來禍,但是如果持續行惡,人的身體和精神就會變得憔悴。善行也并不一定會給人帶來福,但是如果持續行善,人的身體和精神就會變得至剛至大。也就是說,短期內惡行可能比善行更能給行為者帶來物質上的滿足和肉體上的舒適,但從長遠來看并非如此。他說:“禍福之理,古人疑之久矣。忠孝者未必免禍,淫逸者未必薄福,然為善是受福之道,君子強為善而已。”(39)《全書》第4卷《文集》,第31頁。“人今日行一善事,明日行一義舉,集義積善,積之至久,則心廣體胖,睟面盎背,而浩然之氣,與之滋長,至剛至大,塞乎天地之間。于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譬諸草木,是乃茁茂蕃鮮者耳,今日行一負心事,明日行一負心事,仰而愧天,俯而炸人,厭然外掩,怛焉內疚,頭為之低垂,眸為之眊,正氣沮蹙,噫欠自發,積之即久,神遁志亂,反覆降屈,不成人形,譬諸草木,是乃荒穢憔悴者耳。”(40)《全書》第4卷《文集》第31頁。丁若鏞要求人明辨是非禍福的道理是因為大部分人只知道惡行并不一定會給人帶來禍,善行也并不一定會給人帶來福,但是不知道惡行最終會給人的精神成長帶來消極影響。這是人生的普遍規律,所以他將其表述為“宇宙之情”,即超越時間和空間的人生大道理。因此,在丁若鏞的倫理學中,行為者是自己所產行為的主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所有責任。所以他從未強迫人行善,而是反復告誡人行善為什么好,行惡為什么不好,并將通過這一過程后的善行稱為“人善”。(41)[韓]張福童:《丁若鏞道德哲學的惡問題研究》,《東洋哲學研究》2004年第39輯,第170頁。
綜上,丁若鏞認為,一個人如果想要最大限度地實踐善,首先要做到“誠”,他之所以強調誠,是因為人在行事前和行事中的慎重、認真、持之以恒的態度皆源于此。因此可以說,誠是一切善行的第一級階梯。其次,行為者要做到學、問、思、辨。所謂學是有關求知的一切行為;所謂問就是審慎地探問、深入地追問情境的事宜;所謂慎思,指謹慎地、周密地規劃符合情境的行為;所謂明辨就是明晰地辨別禍福之理,使自己完全成為行為的主人,責任的擔負者。
四、結語
本論文的目標是探究丁若鏞“自主之權”概念的“原意”,進而揭示“自主之權”與善惡的內在邏輯。為此選擇了哲學詮釋學的以經解經法作為方法論,著重分析了以下三點問題:第一,何為自主之權?第二,人行事不善的原因是什么?第三,如何規劃符合情境的行為?經過對文本的分析得出了以下結論:1)自主之權是以善為目的行為規劃能力;2)人之所以行惡是因為放棄思考;3)規劃符合情境的行為,首先要做到“誠”,其次是“學問思辨”。
如果以上的結論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本研究可能會為學界做出以下兩個貢獻:第一,可以說明學界普遍認可的兩種觀點,即認為“自主之權”是自由意志的觀點和“自主之權”是道德性自律的觀點存在誤解或不全面的可能性;第二,可以說明丁若鏞在創新性發展傳統儒學的過程中并沒有采取簡單引進西學觀念,而是在揚棄糟粕中積極地發揚儒學的精髓。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遺憾,那就是未能回答丁若鏞哲學中具有主宰作用的“天”與“自主之權”之間存在著的看似矛盾的關系,也就是天的主宰與人的自主如何兩立的問題。關于這一問題,我們將在后續研究中進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