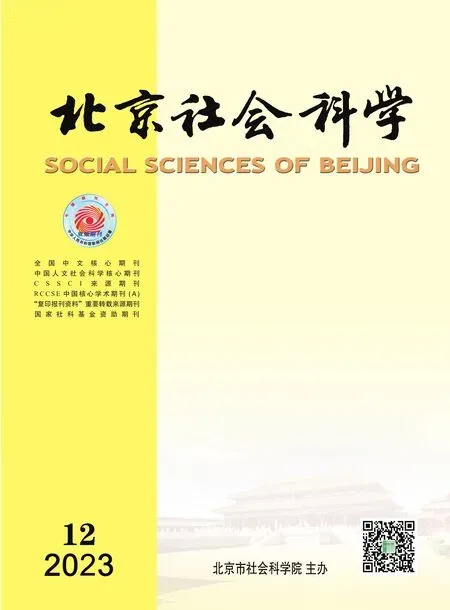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政治教育敘事
鐘啟東
一、引言
描述方法不等于運用方法,這對歷史唯物主義來說更是如此,熟練背出基本原理并不代表真正研究了問題。真理之所以是具體的,既是因為真理被把握為觀念上的具體,也是因為真理被運用于具體實際,前者是對真理的揭示,后者是對真理的檢驗。真理既不迷戀也不封閉于純粹的思維領(lǐng)域,而是面向塵世生活敞開自身,并“帶著詩意的感性光輝對整個人發(fā)出微笑”[1],力求在人的實踐中及對這種實踐的理解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xiàn)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2]。作為“此岸世界的真理”,歷史唯物主義既是研究方法,也是敘述方法,致力于改變世界,能將真理用于具體實際,解決問題、形成經(jīng)驗、揭示規(guī)律并恰當(dāng)?shù)財⑹鍪虑楸旧怼km然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理論研究和實踐工作的指導(dǎo)思想共識已久,人們也在這個“關(guān)于現(xiàn)實的人及其歷史發(fā)展的科學(xué)”[3]指導(dǎo)下不斷拓深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追問和原理建構(gòu),并將其學(xué)科體系、學(xué)術(shù)體系、話語體系及實踐體系牢牢安置于歷史唯物主義地基之上,但是有一個學(xué)科基礎(chǔ)問題始終沒有得到直接提出和前提回答,即作為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客觀現(xiàn)象,思想政治教育在自身形成發(fā)展歷程中蘊涵著怎樣的歷史唯物主義邏輯?換言之,如何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方法來揭示和表述思想政治教育的緣起變化、本質(zhì)規(guī)定?在此意義上,所謂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政治教育敘事,不過是力求回到原理本身來研究和表述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成發(fā)展歷史,揭示其現(xiàn)實開端、階級本質(zhì)和意識形態(tài)規(guī)律,助力新時代思想政治教育深化發(fā)展,從世界歷史的原則高度上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fù)興,為世界謀大同。
二、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現(xiàn)實開端
思想政治教育從哪里開端?這是具有本質(zhì)意義的前提性問題。這個問題一方面是在詢問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實踐活動從哪里開端,另一方面是在詢問思想政治教育學(xué)研究、理論建構(gòu)從哪里開端,前者“似乎”是活動開端、行動起點,后者則指向理論開端、邏輯起點。之所以要特別強調(diào)是“似乎”,不只是因為這里暗含著對這種認(rèn)識的否定,更是因為是否把活動開端和理論開端根本區(qū)別開來,是資產(chǎn)階級思想政治教育同無產(chǎn)階級思想政治教育在開端和前提問題上的本質(zhì)差異,而這種異質(zhì)性又是由唯心史觀和唯物史觀的截然對立所規(guī)定的。因此,為了說明這個開端問題上的理論分歧,并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現(xiàn)實個人活動本質(zhì),有必要先從唯心史觀和唯物史觀的對立說起。具體到馬克思恩格斯的經(jīng)典文本之中,就是歷史唯物主義這個科學(xué)的歷史觀同“意識形態(tài)家們”形形色色的錯誤歷史觀之間的觀念對立、開端差異。
馬克思發(fā)動哲學(xué)革命的精神要旨,是為無產(chǎn)階級革命和人類解放“制定新的世界觀”,這是通過醞釀、提出和完善“新唯物主義”來實現(xiàn)的。正如馬克思在《〈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批判〉序言》中回憶他和恩格斯撰寫《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理論初衷時所澄明的那樣,歷史唯物主義的提出和闡發(fā)具有雙重目的,除了要清算“從前的哲學(xué)信仰”,更重要地是闡發(fā)“我們的見解與德國哲學(xué)的意識形態(tài)的見解的對立”[4]。歷史唯物主義是這樣一種“新唯物主義”:跟唯心主義相比,它強調(diào)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從人們的物質(zhì)生活過程來說明構(gòu)筑其上的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與精神生活,而不是相反;跟舊唯物主義相比,它把“對象、現(xiàn)實、感性”“當(dāng)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dāng)作實踐去理解”“從主體方面去理解”,而不是僅僅“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5],避免把人的本質(zhì)臆想為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在現(xiàn)實性上將其理解和把握為社會關(guān)系的總和。
構(gòu)成新唯物主義批判對象的錯誤觀點,前者以鮑威爾、施蒂納的思辨唯心主義為代表,后者以費爾巴哈的人道唯物主義為代表。二者的共同點既在于他們都沒有真正離開過“黑格爾體系的基地”,還在于他們在歷史領(lǐng)域都是徹頭徹尾地信奉“唯靈論”或者“思辨的創(chuàng)世原則”,都是“各自在神學(xué)的領(lǐng)域內(nèi)徹底地貫徹黑格爾體系”[6],區(qū)別僅僅在于前者力求拋棄神學(xué)、后者則希望拯救神學(xué)。而這又是因為作為其哲學(xué)源頭和精神原則的黑格爾體系本身就是形而上學(xué)改裝過的“神正論”,正如黑格爾在《精神現(xiàn)象學(xué)》序言中所坦誠的那樣——“上帝的生活和上帝的知識因而很可以說是一種自己愛自己的游戲”[7]。在馬克思看來,這些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和其他一切民族意識形態(tài)沒有任何特殊的區(qū)別,由于它們都持有唯心史觀,因而一方面,它們和神學(xué)具有完全相同的理論開端和邏輯起點——“上帝實體”“自我意識”“類”“唯一者”等,二者之間的區(qū)別僅在于把抽象的開端想象成什么、設(shè)置在哪里及它是如何創(chuàng)造歷史的。另一方面,二者都認(rèn)為思想、概念和精神才是決定性的本原,“觀念、想法、概念迄今一直支配和決定著現(xiàn)實的人,現(xiàn)實世界是觀念世界的產(chǎn)物”[8]。“批判的思想活動一定會使現(xiàn)存的東西滅亡,而要做到這一點,他們或者認(rèn)為有他們的孤立的思想活動就已足夠,或者希望爭得共同的意識。”[8]如此一來,假如世界和歷史不是由上帝創(chuàng)造的,那就是由思想和觀念締造的。這兩種認(rèn)識具有相同的實質(zhì),只不過前者是由上帝親手締造,后者則是由上帝化身的無數(shù)邏格斯來貢獻(xiàn)智慧和力量,所以全部歷史不過是證明自我意識、絕對理念的生成外化史。正如按照思辨的洞見,“人的本質(zhì)的全部異化不過是自我意識的異化”[9],因為“當(dāng)思辨在其他一切場合談到人的時候,它指的都不是具體的東西,而是抽象的東西,即觀念、精神等等”[10],所以它們直截了當(dāng)?shù)亍鞍熏F(xiàn)實的人變成了抽象的觀點”[11],并聲稱只要群眾聽從它們“寓言的教導(dǎo)”,在觀念秩序中超出了舊世界的思想范圍,就能超出舊世界的秩序范圍,也就能獲得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
但是,不僅馬克思恩格斯對這種達(dá)到了頂點的“整個德國思辨的胡說”表示明確反對,而且人民群眾也對這種“無內(nèi)容的空洞”和“思辨的自我循環(huán)”絲毫不感興趣并充滿厭煩。這是因為,其一,以這些胡說和臆想為哲學(xué)英雄的資產(chǎn)階級意識形態(tài),把政治解放同人的解放混淆起來。其二,思辨造成這種混淆的意識形態(tài)顛倒,一方面是由于它們虔信其中的唯心主義教條,另一方面則是由于這種顛倒連同其唯心主義信仰,是“意識形態(tài)家們”所不自知的,正如他們不知道“政治解放并沒有消除人的實際的宗教篤誠,也不力求消除這種宗教篤誠”[12]那樣,當(dāng)然他們也就不可能看到,完成了宗教解放的“政治國家”竟然同“基督教國家”有著驚人的一致性,那就是“國家根本沒有廢除這些實際差別,相反,只有以這些差別為前提,它才存在,只有同自己的這些要素處于對立的狀態(tài),它才感到自己是政治國家,才會實現(xiàn)自己的普遍性”[13]。其三,這種對立是由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之間的現(xiàn)實分裂造成的,思辨作為“顛倒的世界”既會必然生成又要竭力掩蓋構(gòu)筑其上的“顛倒的世界意識”“天賦人權(quán)”“生而自由”“私人財產(chǎn)神圣不可侵犯”等資產(chǎn)階級意識形態(tài),以理性和公義之名先后出場,導(dǎo)致現(xiàn)實的個人“不僅在思想中,在意識中,而且在現(xiàn)實中,在生活中,都過著雙重的生活——天國的生活和塵世的生活”[13]。其四,這“雙重的生活”日益表現(xiàn)為“雙重的壓迫”,即日益異化成一種不堪忍受的力量,人們“僅僅在思想中站起來,而讓用思想所無法擺脫的那種現(xiàn)實的、感性的枷鎖依然套在現(xiàn)實的、感性的頭上,那是不夠的”[14],要想徹底解決“塵世的顛倒”以及構(gòu)筑其上的“理論的對立”,就必須在現(xiàn)實個人的社會行動中借助“使用實踐力量的人”來推進(jìn)和完成,從而將之上升為“有原則高度的實踐”,追求和實現(xiàn)“普遍的人的解放”。
綜上所述,“思辨的胡說”之所以是“意識形態(tài)的顛倒”,正是因為它把“抽象的人”作為自己的理論開端和邏輯起點,盡管它認(rèn)為自己確實看到了市民社會中現(xiàn)實的人,但是它不知道也不真想知道,這個現(xiàn)實的人其實已經(jīng)是被市民社會的顛倒邏輯所顯示出來的假象了。于是,頗為吊詭的資產(chǎn)階級思想政治教育悖論就這樣產(chǎn)生了:從理論構(gòu)建來看,它的整個意識形態(tài)體系和思想政治教育學(xué)說,都是從“抽象的人”“想象的人性”這個虛構(gòu)開端出發(fā)的,倒金字塔式的意識形態(tài)結(jié)構(gòu)似乎不堪一擊、一推就倒;但在實際生活中,這個意識形態(tài)結(jié)構(gòu)卻又是如此的穩(wěn)定深入,以致于在現(xiàn)代性的日常生活中無孔不入、無時不有。這是因為,一旦到了市民社會深處,資產(chǎn)階級意識形態(tài)不是相信“自由、平等、博愛”這些格言教化,而是借助分工、車間、工資、商品乃至“步兵、炮兵、騎兵”這些現(xiàn)實性力量來建構(gòu)強加于人們身上的利益分化和本質(zhì)物化,從而更加全面深入地影響著現(xiàn)實個人的精神生活和觀念圖景,普遍導(dǎo)致“個人現(xiàn)在受抽象統(tǒng)治”[15]。
因此,資產(chǎn)階級思想政治教育只是“似乎”在從“抽象的人”這個邏輯開端出發(fā),實際上它的真正秘密和行動開端同樣是“現(xiàn)實的個人”及其物質(zhì)利益需要。否則,資產(chǎn)階級何以能夠做到既相信自己編制的意識形態(tài)神話,又原諒自己道貌岸然地在世界各處理直氣壯地踐踏和破滅這些意識形態(tài)神話呢?歸根到底,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那樣: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會使自己出丑,因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16],這些個人“不是他們自己或別人想象中的那種個人,而是現(xiàn)實中的個人”[17],這些個人區(qū)別于動物的地方不在于他們有思想,而在于他們把生產(chǎn)生活資料作為第一個歷史行動,并隨著這種行動的變化深入改變著自己的思想觀念,所以“歷史的活動和思想就是‘群眾’的思想和活動”[18]。
可見,既然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zhì)上是實踐的,那么思想政治教育也要遵從這個規(guī)律,無論它被歪曲到何種地步、被美化為何種理想,它在現(xiàn)實性上總是誠實地把具體個人的物質(zhì)生產(chǎn)行動作為真正開端。思想政治教育從來都是現(xiàn)實的個人活動,是構(gòu)筑于現(xiàn)實個人的物質(zhì)生產(chǎn)及其利益關(guān)系之上的教育實踐活動。只不過由于理論開端的差異導(dǎo)致了關(guān)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學(xué)說假設(shè)和體系構(gòu)建,資產(chǎn)階級及其辯護(hù)者們從“抽象的人”出發(fā)走向虛假、偽善和反動。與之相反,馬克思恩格斯則始終立足“現(xiàn)實的個人”及其物質(zhì)行動,來清算哲學(xué)信仰、破解歷史之謎、塑造新的世界觀,終止了“思辨的胡說”,為無產(chǎn)階級革命和人類解放,確立了“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fā)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xué)”[19],亦即“此岸世界的真理”。
三、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階級本質(zhì)
從“現(xiàn)實的個人”出發(fā),思想政治教育是如何形成發(fā)展起來的?既然實質(zhì)上都把“現(xiàn)實的個人”作為行動起點和實際開端,為何資產(chǎn)階級思想政治教育要采取顛倒的意識形式,把現(xiàn)實的人抽象為“原子”“帽子”“觀念”或者“類”,并在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體系中徹底顛倒市民社會的真相本質(zhì),從而將自己與現(xiàn)實基礎(chǔ)的真實聯(lián)系模糊起來?在思想政治教育形成發(fā)展過程中,那個具有決定性作用的理論內(nèi)容和實踐動因,既然不是神的意志,也非思維的強制,那它究竟是什么?
黑格爾說過,開端并不會停留于自身,而是要向前展開并實現(xiàn)潛在于自身的豐富內(nèi)容。既然“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20],那我們索性就從資本主義思想政治教育這個成熟形態(tài),是如何從這個現(xiàn)實開端生長出來、又是如何歪曲這個開端的整個過程說起。關(guān)于黑格爾說的“開端”,馬克思曾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探討商品規(guī)律時,借用一句神學(xué)術(shù)語直截了當(dāng)?shù)赜枰曰貞?yīng)和揭示:“起初是行動。因此他們還沒有想就已經(jīng)做起來了。”[21]當(dāng)然,馬克思在這里是調(diào)侃商品占有者陷入了類似浮士德那樣的困難處境——如果不使自己的商品在社會行動中同其他商品發(fā)生交換關(guān)系,不使自己的商品同一般等價物相對立,那么就不能把商品變現(xiàn)為貨幣,完成“商品的驚險的跳躍”,就會摔壞“商品占有者”[22]。于是,商品占有者來不及多想,就總是已經(jīng)在圍繞W-G-W這個買賣邏輯和G-W-G這個增殖邏輯奔走忙碌于全世界了。
在這里,馬克思進(jìn)一步揭示到:“商品本性的規(guī)律通過商品占有者的天然本能表現(xiàn)出來。”[23]作為物質(zhì)關(guān)系、物質(zhì)動因的“商品本性的規(guī)律”,能夠支配“商品占有者的天然本能”,人的創(chuàng)造物竟然反過來支配人本身,而且這種支配還在“商品占有者”那里表現(xiàn)得自然而然和天經(jīng)地義。這就說明,人的本質(zhì)力量在“商品拜物教”中徹底異化了,并且這種異化深刻塑造了市民社會的運行規(guī)律和支配人格。資本邏輯力求把所有人都變成金錢的奴隸,就像它把自己想象成“普照的光”那樣,它總是渴望按照自己的樣子創(chuàng)造出一個世界。那些被資本邏輯牢牢支配的人們或許沒有意識到,但是他們已經(jīng)這樣做了[24]。置身資本主義社會,“每個人都力圖創(chuàng)造出一種支配他人的、異己的本質(zhì)力量,以便從這里面獲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滿足。”[25],從而每個人都不得不“精打細(xì)算地屈從于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來的欲望”[26]。
既然異化如此嚴(yán)重,那么人們?yōu)楹螞]有清醒認(rèn)識到資本邏輯及其拜物教對現(xiàn)實個人的支配呢?人不是“有意識的生命活動”嗎,不是能夠“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識的對象”[27]嗎?這是因為人和人之間的關(guān)系異化成了“被物的外殼掩蓋著的關(guān)系”[28],流通領(lǐng)域的平等表象掩蓋了生產(chǎn)領(lǐng)域的剝削本質(zhì)。馬克思在這里借鑒了黑格爾的洞察方法,把資產(chǎn)階級社會分成表象世界(現(xiàn)象)和本質(zhì)世界(現(xiàn)實)兩個維度,前者表現(xiàn)為商品交換的流通領(lǐng)域,后者則是商品制造的生產(chǎn)領(lǐng)域。流通領(lǐng)域遵從平等交換的正當(dāng)法則,人的勞動作為商品被投入市場,看起來也是得到了這個平等法則的充分尊重——賣出勞動、拿回工資,從而掩蓋了生產(chǎn)領(lǐng)域中每天都在真實發(fā)生的,制造并榨取剩余價值的剝削秘密。這就導(dǎo)致“生產(chǎn)層面所發(fā)生的事實,在流通層面被否認(rèn)了”[29]。在這里,“否認(rèn)”意味著流通層面對生產(chǎn)層面的“顛倒”,亦即“顛倒的表象世界”對“顛倒的本質(zhì)世界”的顛倒,它巧妙地采取了“正是商品世界的這個完成的形式——貨幣形式,用物的形式掩蓋了私人勞動的社會性質(zhì)以及私人勞動者的社會關(guān)系,而不是把它們揭示出來”[30],結(jié)果是“貨幣關(guān)系掩蓋了雇傭工人的無代價勞動”[31]。這個“顛倒的表象世界”不僅“掩蓋了現(xiàn)實關(guān)系”,而且“顯示出它的反面”,使得“資本主義生產(chǎn)所固有的并成為其特征的這種顛倒,死勞動和活勞動、價值和創(chuàng)造價值的力之間的關(guān)系的倒置”,不僅“反映在資本家頭腦的意識中”[32],而且成為“工人和資本家的一切法的觀念”和“庸俗經(jīng)濟(jì)學(xué)的一切辯護(hù)詞”[31]表現(xiàn)自身形式的現(xiàn)實依據(jù)。
如果僅僅從作為表象世界的商品流通領(lǐng)域來看,“這個領(lǐng)域確實是天賦人權(quán)的真正伊甸園。那里占統(tǒng)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quán)和邊沁。”[33]然而,一旦離開這種表象和抽象,“我們的劇中人的面貌已經(jīng)起了某些變化。原來的貨幣占有者作為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占有者作為他的工人,尾隨于后。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zhàn)戰(zhàn)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34]。可見,資本主義生產(chǎn)領(lǐng)域的異化力量和壓迫結(jié)構(gòu),被流通領(lǐng)域顛倒了,后者作為冒充本質(zhì)的表象,被抽象地把握為“自由、平等、所有權(quán)和邊沁”等意識形態(tài)。不僅把現(xiàn)實的人抽象為“原子”“帽子”“觀念”或者“類”,而且用這些抽象觀念及其意識形態(tài)體系,掩蓋了生產(chǎn)領(lǐng)域的普遍奴役及其剝削秘密,使人們沒有意識到資本邏輯的支配,卻已經(jīng)在這種支配下行動,使人們即使體驗到全面異化的生理痛苦和心理痛楚,卻找不到真正的苦難之源和仇恨對象,只能對機器、對生產(chǎn)線、對自己和同類生悶氣、發(fā)脾氣。
這就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生產(chǎn)及其思想政治教育支配的秘密,這個秘密不過是說明占統(tǒng)治地位的物質(zhì)力量(即便它是“顛倒的世界”)同時也成為占統(tǒng)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顛倒的世界意識”),前者對于后者的生成變化具有最終決定性,后者沒有獨立性,但是對前者具有特殊重要的反作用。這個反作用,既可以是辯護(hù)、支撐和推動力量,也可能是反駁、消解和革命力量,甚至?xí)鹨欢ㄉ鐣r代的覆滅。思想政治教育體現(xiàn)為何種性質(zhì)和強度的觀念意義、現(xiàn)實性力量,在根本上取決于它處于哪個歷史階段、取決于它為哪個階級服務(wù)。說到底,思想政治教育是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的集中體現(xiàn),反映著一定群體、集團(tuán)、階級的物質(zhì)力量和根本利益,因而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導(dǎo)性思想政治教育,都是服務(wù)于剝削階級、壓迫人民的統(tǒng)治工具。但在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到不可調(diào)和、必須訴諸決戰(zhàn)的革命時代,在一定普遍性上代表了被壓迫階級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和物質(zhì)利益的革命等級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會揭穿和批判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及其支配體系,動員組織人民大眾團(tuán)結(jié)起來反抗壓迫、爭得解放,摧毀舊世界、建立新世界。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是階級斗爭的歷史產(chǎn)物,既是剝削階級用來全面奴役廣大勞動人民的統(tǒng)治工具,也是革命階級用來全面反抗奴役的革命武器,前者是為了鞏固和延續(xù)統(tǒng)治,后者是為了推翻并實現(xiàn)統(tǒng)治,前者是為了確立并教化統(tǒng)治階級的思想,后者是為了揭穿和取消這個思想統(tǒng)治,從而將自己階級集團(tuán)的理論原則和觀念體系提升為在社會意識領(lǐng)域中“占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二者總是存在于階級斗爭之中,只不過是大多數(shù)時候看起來比較平靜緩和,后者一般來說也多是潛伏在社會意識領(lǐng)域、社會思潮之中,盡可能地采取隱蔽的形式和滲透的策略來建構(gòu)并傳播自身利益原則。直到革命的風(fēng)暴口徹底到來之前,它才浮出水面“跟他舊日的生活與觀念世界決裂”,“使舊日的一切葬入于過去而著手進(jìn)行他的自我改造”[35],并隨著革命階級推翻了現(xiàn)有統(tǒng)治、贏得政權(quán),而成為主導(dǎo)性的意識形態(tài)力量和支配性的精神力量,“就如閃電般一下子建立起了新世界的形象”[36]。
資產(chǎn)階級領(lǐng)導(dǎo)文藝復(fù)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開展民主革命使西方社會從中世紀(jì)的黑暗統(tǒng)治下掙脫出來正是如此;只不過它一旦確立起自己的統(tǒng)治階級地位,就把無產(chǎn)階級和人民大眾拋棄了,“普遍的人權(quán)”變成“普遍的謊言”,所謂“人人平等”不過是“有錢人之間的平等”,所謂“個人自由”不過是“工人自由得一無所有”,因為真正自由的從來就不是“現(xiàn)實的個人”而是“貪婪的資本”。正是由于資產(chǎn)階級背叛革命,“啟蒙的驕傲”變成了“致命的自負(fù)”,“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變成了“公開的、無恥的、露骨的剝削”[37],它曾經(jīng)“用來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現(xiàn)在卻對準(zhǔn)資產(chǎn)階級自己了”[38],這才有了與資產(chǎn)階級意識形態(tài)截然對立的無產(chǎn)階級意識形態(tài)。
無產(chǎn)階級意識形態(tài)真實代表了全體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思想原則,它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引領(lǐng),以共產(chǎn)黨人為領(lǐng)導(dǎo)主體,真正致力于實現(xiàn)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和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開創(chuàng)了“為人類求解放”的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態(tài)。在此意義上,歷史唯物主義本身就是無產(chǎn)階級同資產(chǎn)階級展開理論斗爭和意識形態(tài)較量的時代產(chǎn)物,并且正是由于它的歷史性出場,社會主義才從空想變成科學(xué),共產(chǎn)主義運動才找到了“真理的青天”和“理想的彼岸”。
四、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識形態(tài)規(guī)律
既然思想政治教育是階級斗爭的歷史產(chǎn)物,而階級斗爭又始終圍繞著國家政權(quán)展開,那么思想政治教育自然也貫徹著深刻的國家本質(zhì),不是在保衛(wèi)國家政權(quán),就是在爭奪國家政權(quán),總是力求在權(quán)力形式上成為國家支配人的意識形態(tài)力量。
不同于黑格爾從“倫理理念的現(xiàn)實”和“絕對自在自為的理性東西”[39]來理解國家的本質(zhì),把普魯士國家看成“神自身在地上的行進(jìn)”[40],馬克思顛倒了這種唯心主義的國家觀,提出“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fā)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zhì)的生活關(guān)系”[41]。不僅國家的本質(zhì)和屬性,而且國家采取何種形式、履行哪些職能,都是由“市民社會”決定的。進(jìn)入階級社會以來的人類歷史,在市民社會領(lǐng)域總是存在著階級對立和階級沖突,這就使得構(gòu)筑其上的國家獲得了雙重的階級屬性——國家既是階級斗爭的結(jié)果,也是階級斗爭的原因。
作為“結(jié)果”,國家不僅表明它自身是階級斗爭不可調(diào)和的,卻又不得不把沖突保持在一定“秩序”范圍內(nèi)的社會行動,而且表明它自身“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的這種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國家這種與實際的單個利益和全體利益相脫離的獨立形式,同時采取虛幻的共同體的形式”[42]。但這“虛幻的共同體的形式”卻真實擁有著強大的物質(zhì)力量和精神力量,從而保證一個階級統(tǒng)治著其他一切階級。作為“原因”,國家掌握著“公共權(quán)力”,使統(tǒng)治階級獲得了鎮(zhèn)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因而每次階級斗爭都必然要圍繞著國家政權(quán)及其公共權(quán)力的爭奪來進(jìn)行,不管是正在統(tǒng)治的階級,還是反抗統(tǒng)治的革命階級,掌握“國家機器”都是他們的階級理想和斗爭原則。所以,馬克思恩格斯明確指出:“從這里還可以看出,每一個力圖取得統(tǒng)治的階級,即使它的統(tǒng)治要求消滅整個舊的社會形式和一切統(tǒng)治,就像無產(chǎn)階級那樣,都必須首先奪取政權(quán),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說成是普遍的利益,而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43]這就是說,即便是實現(xiàn)了人民大眾對一切剝削階級的專政統(tǒng)治,具有前所未有的世界歷史意義,開創(chuàng)了人類文明發(fā)展的新紀(jì)元,無產(chǎn)階級革命也必須在國家的本來意義上開展革命行動和思想建構(gòu),這就需要覺悟民眾、團(tuán)結(jié)人民、振奮精神,因此必須及時地建構(gòu)能夠集中體現(xiàn)自己階級與全體勞動人民根本利益的思想原則、理論體系,亦即堅決反抗并致力于取消資產(chǎn)階級意識形態(tài)支配地位的無產(chǎn)階級意識形態(tài)。可見,無論是國家的階級本質(zhì)需要,還是表現(xiàn)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階級斗爭的國家形式需要,都被歸結(jié)為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需要和意識形態(tài)的國家需要之間的內(nèi)在一致性,使得“國家”與“意識形態(tài)”在市民社會中和人類歷史上被同時創(chuàng)造出來。
于是,“國家作為第一個支配人的意識形態(tài)力量出現(xiàn)在我們面前”[44]。這具有歷史發(fā)展的必然性:首先,作為階級統(tǒng)治的工具和形式,國家一經(jīng)產(chǎn)生就形成了思想領(lǐng)域的支配關(guān)系,就是說“國家一旦成了對社會來說是獨立的力量,馬上就產(chǎn)生了另外的意識形態(tài)”[45],而這“另外的意識形態(tài)”是由“社會上占統(tǒng)治地位的物質(zhì)力量”所決定的,也就是要由“支配著物質(zhì)生產(chǎn)資料的階級”來提供,這個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chǎn)資料”,所以“統(tǒng)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占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46]。其次,國家要把“統(tǒng)治階級的思想”描述并確立為“普遍性的思想”或者說“國家的思想”,使之進(jìn)一步成為“一個時代的占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這就要由“這一階級的積極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識形態(tài)家”[47]來編造幻想或者揭示真相。最后,無論出于哪種情況,正如國家表明它本身就是階級對立那樣,它同時也表明自己就是意識形態(tài)力量本身,因為掌握著國家政權(quán)的階級“還作為思維著的人,作為思想的生產(chǎn)者進(jìn)行統(tǒng)治,他們調(diào)節(jié)著自己時代的思想的生產(chǎn)和分配”[47],也就塑造了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的支配關(guān)系、統(tǒng)治秩序——不僅被統(tǒng)治階級要服從統(tǒng)治階級的思想秩序和觀念支配,而且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那些“在實際中他們是這個階級的積極成員”但又“很少有時間來編造關(guān)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的國家成員,也要準(zhǔn)備接受這些思想和幻想,服從這個意識形態(tài)力量的引導(dǎo)和教化,以便“這一階級本身受到威脅的時候”[47],能團(tuán)結(jié)起來保衛(wèi)自身和國家。
可見,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需要和意識形態(tài)的國家需要是同一個事情,那就是統(tǒng)治階級會在一切領(lǐng)域中塑造“并且決定著某一歷史時代的整個面貌”[47],也就是全面貫徹自己的統(tǒng)治意志。只不過前者表現(xiàn)為這個事情,對于確立“觀念的上層建筑”的辯護(hù)渴望,后者則是體現(xiàn)了這個事情對于加強“政治的上層建筑”的權(quán)力渴望。國家要實行階級鎮(zhèn)壓、開展公共管理,當(dāng)然需要法的意識、政治的原則、倫理的觀念、哲學(xué)的理念乃至宗教的信念等意識形態(tài),為之辯護(hù)和論證,因而它就會支持意識形態(tài)力量的理論活動和教育行動;反過來說,這些“意識形態(tài)的諸形式”,不管它們自身多么完善精致、深刻透徹,都不能直接去影響和塑造人的思想生活,不僅要借助“國家的形式”來對自己進(jìn)行確認(rèn)和賦能,而且要借助“國家的力量”來貫徹和實現(xiàn)自己。
在此情形下,思想政治教育就在階級斗爭歷史上被迫切地發(fā)明了出來。這個發(fā)明意味著,思想政治教育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作為國家權(quán)力的意識形態(tài)行動被積極地構(gòu)建和確立起來。之所以要對思想政治教育的歷史出場做嚴(yán)格的限定,是因為在國家產(chǎn)生之前,原始社會中就逐漸形成了一些類似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和功能的宗教活動和部落教育,它或許有著很高的社會威望和教化成效,卻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完整形態(tài)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它還不是階級斗爭的歷史產(chǎn)物,還不是國家統(tǒng)治的權(quán)力與工具。只有當(dāng)階級斗爭激化到一定程度后,思想政治教育才隨著國家的產(chǎn)生而被構(gòu)建和確認(rèn)起來,并始終圍繞國家政權(quán)和發(fā)揮意識形態(tài)力量來展開自身行動;統(tǒng)治階級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如此,革命階級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如此。總之,思想政治教育在國家層面一經(jīng)出場,就迅速成為貫穿國家經(jīng)濟(jì)生活、政治生活及精神生活等各個領(lǐng)域并在其中發(fā)揮重要作用的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這既是因為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質(zhì)上是現(xiàn)實個人的社會實踐活動,又是階級斗爭的歷史產(chǎn)物,而這與國家和意識形態(tài)恰好有著相同的性質(zhì)和前提;更是因為思想政治教育能有效地總結(jié)經(jīng)驗、加工觀念、訴諸批判、揭示思想、制造體系,從而可以很好地滿足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需要;還是因為思想政治教育能有目的、有組織、有計劃地進(jìn)行國家宣傳、社會動員和個體教化,從而可以很好地滿足意識形態(tài)的國家需要,也就成了國家著手建設(shè)并不斷強化意識形態(tài)支配體系的必然選擇。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國家支配個人意識形態(tài)力量的集中體現(xiàn),遵循著意識形態(tài)支配個人的基本邏輯。關(guān)于這個意識形態(tài)力量及其支配邏輯,阿爾都塞曾經(jīng)力求從“意識形態(tài)物質(zhì)化”的理論維度做出說明:一方面,阿爾都塞認(rèn)為“國家”和“意識形態(tài)”是同時存在著的兩個“現(xiàn)實”[48],前者是包括政府、行政部門、軍隊、警察、法院和監(jiān)獄等“鎮(zhèn)壓性國家機器”,后者則是“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AIE)”,是“由各種確定的機構(gòu)、組織和相應(yīng)的實踐所組成的系統(tǒng)”[49],包括教育機器、家庭機器、宗教機器、政治機器、工會機器、傳播機器、文化機器等等。“鎮(zhèn)壓性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的區(qū)別在于,前者直接使用肉體暴力,后者則是“不以占統(tǒng)治地位的和顯性可見的方式訴諸肉體暴力”[50]發(fā)揮支配功能,但這并不表明意識形態(tài)沒有國家的強制屬性。另一方面,在意識形態(tài)如何具體發(fā)揮功能這個問題上,阿爾都塞認(rèn)為答案在于喚問主體的鏡像結(jié)構(gòu),“所有意識形態(tài)都通過主體這個范疇發(fā)揮的功能,把每個具體的個人喚問為具體的主體”[51],使個人在承認(rèn)、臣服于意識形態(tài)這個“大主體”的前提下作為“主體的個人(你和我)‘運轉(zhuǎn)起來’”[52]。阿爾都塞特別指出,資產(chǎn)階級就是通過宗教意識形態(tài)、道德意識形態(tài)、法律意識形態(tài)、政治意識形態(tài)甚至審美意識形態(tài)等“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把無數(shù)主體(生產(chǎn)的當(dāng)事人)喚詢出來“使它自動運轉(zhuǎn)起來”,保障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再生產(chǎn)及其對工人的剝削關(guān)系能永世長存[53]。
我們當(dāng)然不能同意阿爾都塞在把“意識形態(tài)物質(zhì)化”的過程中,過分看重、片面發(fā)展意識形態(tài)的實體屬性和功能結(jié)構(gòu),因為這不僅模糊了“政治的上層建筑”與“觀念的上層建筑”之間的本質(zhì)區(qū)別,更是在討論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參與構(gòu)成的“上層建筑”與“下層建筑”基本關(guān)系時陷入結(jié)構(gòu)主義錯誤,強調(diào)生產(chǎn)關(guān)系對生產(chǎn)力的優(yōu)先性。但是,我們可以從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tài)理論中進(jìn)一步探討歷史唯物主義視域下,國家作為第一個支配人的意識形態(tài)力量,是如何運用思想政治教育進(jìn)行個體支配的。在此意義上,阿爾都塞關(guān)于意識形態(tài)鏡像喚問機制的理論假設(shè),構(gòu)成了關(guān)于意識形態(tài)支配邏輯、思想政治教育運行規(guī)律的思想探求。這種思想探求的正確之處在于:其一,阿爾都塞不僅指出了意識形態(tài)斗爭中的階級性質(zhì),而且指出了每個國家都會運用意識形態(tài)來鞏固政權(quán)、保障生產(chǎn);其二,阿爾都塞注意到了意識形態(tài)與主體的關(guān)系,并運用“大主體”與“小主體”的解釋結(jié)構(gòu)來表述了前者召喚后者的鏡像原理;其三,阿爾都塞沒有停留于純粹精神領(lǐng)域探討這個鏡像召喚機制,而是進(jìn)入實踐領(lǐng)域、生產(chǎn)領(lǐng)域,指出這個召喚機制存在于以國家為中心的全部社會生活領(lǐng)域,不僅存在于政治、教育、文化、傳播等“上層建筑”領(lǐng)域,而且存在于生產(chǎn)領(lǐng)域,因為“生產(chǎn)的場所”也是“階級斗爭的場所”[54]。生產(chǎn)領(lǐng)域生產(chǎn)著意識形態(tài)。
既然國家政權(quán)是階級斗爭的最高問題,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對個體的支配,需要國家形式和國家力量作為背書與支撐,也就不言而喻了。問題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究竟是如何促成意識形態(tài)對個人的喚問和感召的,并使后者作為主體自動運轉(zhuǎn)起來的?秘密同樣藏在國家身上,具體來說,就是在國家(階級斗爭)創(chuàng)造出思想政治教育進(jìn)行意識形態(tài)支配這個事情本身之上。因為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成發(fā)展表明了,在存在著階級斗爭的社會生活里,也就是在國家的全部社會生活里,意識形態(tài)支配個人的統(tǒng)治需要和個體委身于意識形態(tài)的信念渴望是同時存在的,只不過在剝削階級統(tǒng)治的國家里是顛倒著的存在,只有在無產(chǎn)階級專政和實現(xiàn)了人民民主的國家生活里,這種“同時存在”才不僅正立著,而且是統(tǒng)一的。
就前者來說,馬克思在批判資產(chǎn)階級領(lǐng)導(dǎo)的政治解放時說過,政治解放既不力求也確實沒有消除各種實際的宗教篤誠,政治國家僅僅是把宗教從公法領(lǐng)域驅(qū)逐到私法領(lǐng)域中去,導(dǎo)致人們在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立對抗中過著“雙重的生活”,而這又是因為“政治國家對市民社會的關(guān)系,正像天國對塵世的關(guān)系一樣,也是唯靈論的”[13]。所以,資產(chǎn)階級的政治國家可以使人同時擁有“宗教徒和公民”雙重身份,就像它所構(gòu)筑的意識形態(tài)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同樣具有雙重特征那樣:既有新教倫理,也有資本主義精神,一邊是信仰的渴望,一邊是財富的欲望,半是圣歌的回音,半是槍炮的恫嚇,結(jié)局是抽象的痛苦伴隨著抽象的活動。
就后者來說,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chǎn)黨宣言》中指出:“共產(chǎn)黨人并沒有發(fā)明社會對教育的作用;他們僅僅是要改變這種作用的性質(zhì),要使教育擺脫統(tǒng)治階級的影響。”[55]共產(chǎn)黨人并沒有發(fā)明意識形態(tài)力量和思想政治教育,但是他們要改變這種力量和教育的性質(zhì):一方面,如果從終極意義上看,那就是要改變其階級屬性,使其在未來社會(共產(chǎn)主義社會)不為任何統(tǒng)治階級服務(wù),而要實現(xiàn)這個改造的前提就在于,世界歷史已經(jīng)消除了階級壓迫、廢除了階級國家;另一方面,在這個終極理想實現(xiàn)之前,必然存在著一個向共產(chǎn)主義社會過渡的歷史階段、社會形態(tài),這就意味著,在社會主義國家條件下改變意識形態(tài)力量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質(zhì),只能在這個國家的人民內(nèi)部來探討,對于階級敵人則必須“保留原案”。
具體來說,在已經(jīng)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由于共產(chǎn)黨人和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國家通過建設(sh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來強基固本、凝心聚力和人民通過信仰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來安身立命、全面發(fā)展具有內(nèi)在一致性,所以意識形態(tài)在這里就不再表現(xiàn)為“顛倒”而是“實證的科學(xué)”,正如思想政治教育在這里不再表現(xiàn)為“統(tǒng)治”而是“發(fā)展”那樣。如果說這里還存在發(fā)生“顛倒”和進(jìn)行“統(tǒng)治”的現(xiàn)實必要,那就是針對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和人民范疇以外的剝削階級、敵對勢力來說的。客觀的情況也是如此,在無產(chǎn)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過渡階段,不可避免地同時存在著人民和敵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對立,畢竟無產(chǎn)階級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存在,不局限于某一民族國家,正如共產(chǎn)主義理想的最終實現(xiàn)也將是世界歷史事件那樣。
在這之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還要對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本身的“顛倒”進(jìn)行“顛倒”,揭穿它的本原真相及構(gòu)筑其上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還要對剝削階級實行專政統(tǒng)治,并將這種“顛倒”和“統(tǒng)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告訴人民。因為在這個發(fā)生過渡的歷史階段,即便是最理想的狀態(tài)——社會主義已經(jīng)從資本主義社會中完全掙脫了出來,也還是或多或少地帶有后者的影響和痕跡,但最現(xiàn)實的狀態(tài)則是當(dāng)今世界依然處于兩種意識形態(tài)、兩種社會制度的基本對立之中。所以,無論哪種情況都不能動搖和取消意識形態(tài)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階級屬性,畢竟歷史已經(jīng)留下了資產(chǎn)階級一度卷土重來的復(fù)辟悲劇和意識形態(tài)驚悸,何況“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背景下資本主義世界,越是內(nèi)亂和衰退,它們就越能體會到“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56]的不安和恐懼,它們對社會主義的政治仇視和意識形態(tài)進(jìn)攻,就會愈加頻繁和惡劣。
五、結(jié)語
綜上所述,不管那些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學(xué)說和思想政治教育體系將人抽象成什么、將現(xiàn)實歪曲到何種程度,“現(xiàn)實的個人”始終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實際開端。構(gòu)成思想政治教育邏輯起點的這個實際開端的第一個歷史活動,是生產(chǎn)自己的物質(zhì)生活本身。在由此展開的社會生活所結(jié)成的各種關(guān)系中,對國家和意識形態(tài)的產(chǎn)生具有最終決定作用的,是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和物質(zhì)利益,正是圍繞著后者進(jìn)行的在現(xiàn)實性上存在普遍不公的生產(chǎn)和分配活動,引起了階級分化、孕育了階級思想、導(dǎo)致并激化了階級斗爭,在使國家作為第一個支配人的意識形態(tài)力量出現(xiàn)在我們面前的同時,也使思想政治教育作為國家權(quán)力的意識形態(tài)行動在歷史中正式登場。
對于當(dāng)代中國來說,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指導(dǎo)地位的根本制度,持續(xù)推動世界范圍內(nèi)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意識形態(tài)、兩種社會制度的歷史演進(jìn)及其較量向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發(fā)生重大轉(zhuǎn)變,并在這種重大轉(zhuǎn)變中更好地構(gòu)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培育人民信仰、增強民族希望、促進(jìn)世界團(tuán)結(jié),不斷引領(lǐng)和實現(xiàn)人民美好生活,深入推進(jìn)中國式現(xiàn)代化和開創(chuàng)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就是在堅持和展開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政治教育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