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村之殤
沈惠勤
游覽過江浙一帶許多古村落,都少不得敞開幾座頗有歷史根基的大門大戶,也免不了擺出幾件古董舊物,一沾上名人雅士之氣,一貼上某朝某代標簽,便似乎得了尚方寶劍,可以轟轟烈烈地以此為憑大搞旅游建設,吸睛無數,村子猶如注射了一劑長生藥,好羨慕這樣的村落,以此為家鄉,人生之根就可以深深地扎下去。
蘇州虎丘山北麓平平展展地臥著一個大村落——北莊,原名北莊基,除了兩塊石碑是清朝的,其它而言:外部平淡無奇,內部局促擁擠,于是在城市化進程的發展建設中注定要經歷一場變遷。歷史是一張網,只張羅大魚巨蟹;歷史也是一只沙漏,無情地篩漏那些細沙碎屑。村落,也像人,如果不足以偉岸、巨大,終將隕滅在歷史長河。一個無名之輩面對一個無譽之村的殤情,能做的事情微乎其微,碼些文字,也注定隨風而去,一如煙云。盡管如此,還是忍不住地要在它拆遷之際傾盡歌詠之心,這個村落終究是我們一群漁民后代的家鄉啊!
北莊內塘養魚的歷史,從春秋時期開始已有兩千多年,《蘇州府志》《姑蘇志》和《吳縣志》中均有記載。
越國大臣范蠡協助越王勾踐滅吳后棄官為民攜美女西施駕著輕舟來到蠡口、黃橋一帶隱居漁獵,留下了西施浣紗西堰柵的美麗傳說。漢武帝年代,約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間,無錫的葛、金、沈三姓人士駕著三只扁舟為奔波生計尋覓而至,在黃橋北莊地段捕魚為生,搭建棚戶,落戶定居,繁衍后代。
一個地方從某一歷史時期走出,如若輝煌過,必定會留些遺存。北莊村歷經一個又一個時代,卻鮮有像樣的遺存,世世代代漁民在這片土地上自給自足,隨著時節行走,興而后枯,枯而后興,一茬又一茬,小草一樣生生息息、平平凡凡。即便許多當下老者曾經見證過解放前村內的大戶人家,有一座在20世紀70年代前后還做過北校校址,終究也抵擋不住歷史潮流,湮滅了。
世世代代的漁村居民,一代又一代在此繁衍生息,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的數十年間,漁村在人口爆炸后,以老莊基為核心,向東南北三個方向輻射發展,一躍變成了一個超級漁村。
浩浩北莊村,709戶民宅,基本是興建于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蘇式小樓,或兩間開,或三間開,粉墻黛瓦,也不乏摻雜一些戴綠色或紅色琉璃瓦帽的小洋樓,它們從南木圩、小河南、老莊基、河南巷、灣堂、長村、里浜、擺渡口、短浜上、獨水墩、三家村,一路覆蓋,綿延整個北莊大村落。東塘河、門前浜、前浜、后浜、蘇州河等自然的河流或截、或穿、或圍、或隔,錯綜其間,民居鱗次櫛比,錯落有致,形成了自由貿易的小集市,頗為熱鬧。俯瞰村落,猶如一只莊雞正在虎丘山麓的三角咀東邊振翮撲食。
時代的洪流流經村落,村落陷入不堪重負的困境,場面高低,村巷窄小,加之地形復雜,汽車難以入內,村落無法適應膨脹的發展之需。姑且在各處開膛挖肚,螺螄殼里做道場,零星地建立了幾個停車坪。然而,仍然逼仄。
當拆遷放上具體的議事日程,村民便掰著手指歷數家珍。這個漁村中能當得起家珍的便是兩塊石碑,它們一如這座漁村被封存的兩枚歷史印章,又像遺世的老人。一塊為《奉旨勒石永禁》碑,行文繁復地詳細記述了一件清朝時期的漁事。內容為北莊漁民受生活勞作之逼,聯合起來與黃天蕩湖霸蕩棍開展斗爭,獲得了官府支持。另一塊為《奉旨遵憲蠲免漁課永禁泥草私稅》碑,所刻碑文有長洲縣漁民陸江、葛華等43人呈告當地豪強地主和漁霸向漁民橫征暴斂私稅的情況、蘇州府海防廳查詢的情況、清地方政府對吳中豪強私征漁稅的禁令梗概。
石碑為憑,北莊漁民養魚從此走上了一段太平昌盛之路。
清朝的石碑靜靜地矗立在21世紀村民的小樓前,當年的“永禁”早已不復再起作用。然而,石碑終究鐫刻著這個村落中漁民曾經流淌的血淚,在漁村和石碑決絕斷離的拆遷節點,令人感嘆的是主人行將離去,但石碑卻像一對被卸下的翡翠鐲子,執著地留住了主人的血脈,帶著這份漁村的氣息,石碑何去何從?也許會靜立某博物館的一個角落,沒有風餐露宿的困苦,卻再無漁民激浪的豪情回響。
關于北莊村養魚,民國版《吳縣志》載曰:“介于閶齊二門之南北莊基,均以畜魚為業。其畜之,也有池,養之也有道,食之也有時,魚有巨細,以池之大小位置之,時有寒暖,視水清濁調和之,大要春夏宜清,秋冬不妨濁也。食有精粗,審魚之種類飼養之,鯖魚食螺、鯇魚食草。防其飛去,置神以守之。”寥寥記述,從中隱見養魚之繁復和漁人之艱辛。
北莊內塘養魚確非順風順水,在歷史長河里,漁民靠著一條船風里來雨里走,成就了淡水養殖業,培養出了聞名遐邇的北莊粉青魚。漁民勞苦功高,漁船功不可沒:漁船是漁民的腳,行走四方,奔波勞碌;漁船是漁民的心,顛簸水流,隨波忐忑,操勞辛苦。
而一只漁船之于一條魚兒的意義又何在?
漁船是魚兒流動的家。一條小青魚苗,原非土生土長,來自遙遠的長江灘涂,一只漁船千里迢迢逆流而上取得魚苗,小心翼翼,呵護備至,魚苗方能得以抵達北莊村西三角咀水域大大小小、規格不一的花子潭安家落戶。一條漁船猶如一個流動的家,它長途跋涉改變了一條幼小生命在長江水流里野生的命運。到得池內,喂以雞蛋、輔以豆漿,漁民對于一條魚苗的呵護也許勝過愛家里的子女。
漁船是魚兒備食的艙。一條漁船也許曾經奔赴過陽澄湖、金雞湖、獨墅湖、黃天蕩,漁民歷經一場辛苦的撈草勞作后,漁船馱滿沉甸甸的水草,老牛一樣,涉水而歸,草魚卻有了飽享的福;一條漁船也許還曾奔赴過太湖,漁民借此流動的水上平臺吸回滿艙的螺螄,又涉水而回,青魚卻有了飽食的樂;一條漁船還曾奔赴過蘇州市河,歷經與各種船兒的博弈,終于在激流里不辱使命運回一船艙糖糟,夠魚寶們飽食終日,享樂無窮。
漁船也是魚兒行走的腳。北莊村的漁民好個勤勞智慧,先前從長江里淘來魚苗,后來科學養魚,自己培育金貴的魚苗,開啟了傳經送寶之路。春日里,漁船肩負新的使命,承載魚秧,外出送達四方八鄰。冬日里,漁船裝滿肥碩的粉青魚,奔赴上海,為上海人歲末年終的團員宴增添美食。船兒奔走四方,風雨飄搖,運載魚兒,抵達目的,無怨無悔,矢志不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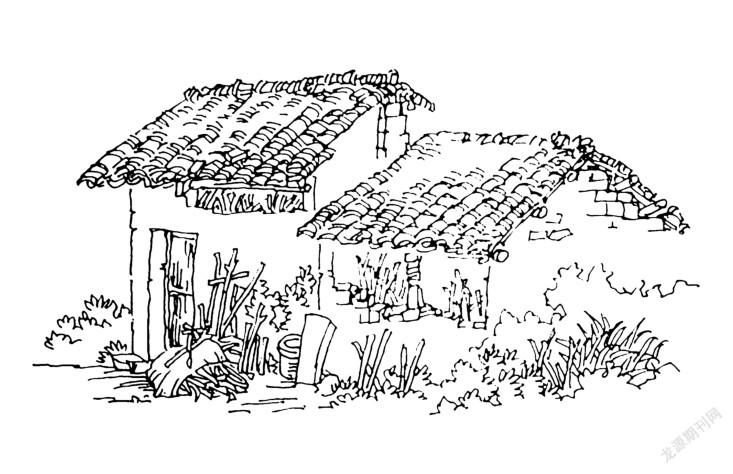
漁船從晨曦里出,從暮靄里歸;漁船從靜波里去,從風浪里回。一條漁船在歷史里行走了兩千多個年頭,終于蒼老了船舷,斑駁了船艄,船櫓累了,擱下無力的臂膀,停歇在21世紀的漁村,像一位疲憊滄桑的老人,她睜著渾濁的雙眼,看一眼村外馬路上汽車的絕塵,靜靜地睡倒在通關橋邊塘河灘頭。風雨里落下的塵土淤積在船艙,滋生一叢青草,祭奠曾經勞碌在漁村的生命之船——一個仿若呵護了眾多魚兒的老媽媽。
一條漁船,能奔波,能運輸,能儲藏,它用兩千多年的堅守,讓一條北莊的粉青魚名揚四方,曾經有村民無比自豪地抱著魚兒參加了全國群英會,北莊內塘養魚大村的名聲讓村民攢足了底氣。
然而,一條童話一樣崛起的青魚在歷史的舞臺上迅速地隱退了,時代的車輪在漁村邊轟鳴,漁民上岸奔波新的營生。豐富的物資里,魚兒找不到自我;曾經污染過的水源里,魚兒無法寧靜。魚兒嗚咽,決絕于21世紀的河流。石碑見證了漁民曾經為一條魚兒所做的努力,卻沒有記下一條漁船的功勛。
2018年的春天,北莊漁村拉開了拆遷的大幕。21世紀20年代前后數年之間,漁村斷斷續續拆遷了,一本書寫了兩千多年的吳地漁文化,沉重地合上最后一頁,留下的既有失落的傷痛,也有重新崛起的歡愉。
拆遷之際,村西口的三角咀濕地涌動著一股股春潮,似乎在說:歷史不會忘記。是的,歷史不會忘記:
那條船兒雖然沒能久留,但也許變作了村頭上空的弦月。
那條魚兒雖然沒能久留,但也許化作了漁村居民的血脈。
拆遷后的村子不再,然而,漁村居民的血脈尚存,漁文化的基因密碼仍然可以鮮活,鮮活在每一個鄉人心中,永遠永遠!
——選自西部散文學會微信公眾平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