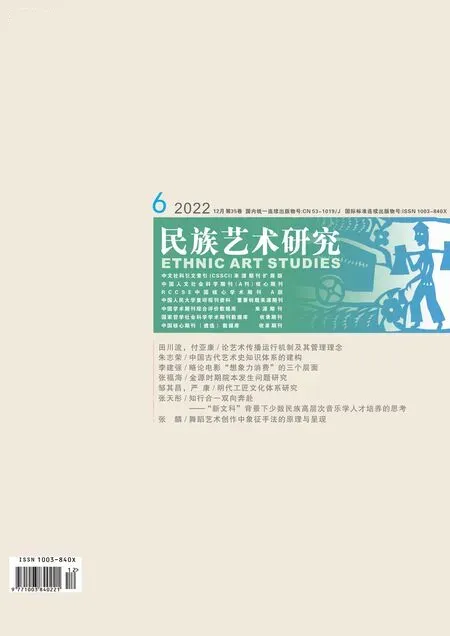論藝術鄉建的本質與要義
張 犇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推進,“藝術鄉建”也成為近年的熱點話題,各界寄希望于通過藝術手段的介入,實現喚醒鄉村文化潛力、激活鄉村魅力尊嚴、賦能鄉村振興的目標。
藝術與鄉村的相遇,早在30多年前即已出現。其時,諸多高校美術專業將寫生課程引入景色優美的村落,在完成教學任務的同時,也為所在村落帶來一定的經濟效益,并引發了一股村落興辦寫生基地的風潮,這成為20世紀八九十年代雖然另類卻極為有效的 “鄉村開發模式”。有相當一部分保護完好、文化底蘊優渥的村落,如西遞、宏村、周莊、同里、麗江、大理等因此而聲名鵲起,引來政府的重視和打造。宏村、西遞、周莊、麗江等甚至成為世界級的文化遺產和我國文旅產業中的排頭兵。這種現象雖不能完全等同于當下的 “藝術鄉建”,但與藝術的關聯性卻顯而易見,一定程度上亦可視其為是藝術鄉建的發軔。
不過這些藝術介入鄉村建設的行為,還只是一種無意識的自發行為,而且,這個時期圍繞寫生所進行的相關村落改造行為,也基本不能歸為藝術鄉建,此時的鄉村完全處于被動和弱勢的地位。
黨的十九大提出的關于鄉村振興戰略的20字方針 “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目的就是推進城鄉融合、共同發展,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2020年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之后,這20個字已成為鄉村振興國家戰略的總體要求。“藝術鄉建”也因此應運而生,目的是通過藝術手段和方式,在完成美化鄉村風貌基本任務的基礎上,激發鄉民的內生動力,將扶貧與扶智相結合,助推實現美好生活的愿望,營造具有當代鄉村特色的新型文化生態系統。基于此,參透 “藝術鄉建”的本質與要義,是藝術介入鄉村的必要前提。
一、介入·融入:“藝術鄉建”的本質與旨趣
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要繼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其中建設鄉村文化生態成為重要一環,這為藝術鄉建提供了機遇,但難度也顯而易見。如:怎樣找到鄉村文化生態協作性、互動性的有效途徑,如何凸顯鄉村文化的地域性、創新性等。凡此種種,均成為藝術鄉建必須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一)“藝術鄉建”的實踐維度
自改革開放以來,大量鄉村人口進城務工,在促使城市風貌日新月異的同時,鄉村人口的流失和鄉村文化空心化現象也愈發嚴重,特別是隨著近年來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處于轉型期的鄉村與城鎮文化之間尚未形成成熟的結構性關聯,使已瀕臨困境的鄉村文化的存續脈絡已有斷裂之虞,鄉村的文化生態系統亟須修復。
在中國,關注鄉土文化早有先例,20世紀二三十年代即已出現對鄉土文化的革新探索,如梁漱溟發起 “儒學下鄉運動”,晏陽初與陶行知希望通過教育與文化進行鄉村改造等,均體現出近代有識之士對鄉土文化革新的思考。
當前的藝術鄉建,則是在新時期對于鄉村文化革新與修復的新探索,協同鄉村振興,從鄉村文化精神、情感需求、民俗復構、文旅協同等多方面進行系統性設計治理,正是“藝術鄉建”的實踐維度。
因此,必須明確的是,藝術鄉建不僅僅只是吸引畫家入駐、學生寫生、展覽表演、民宿設計等淺表化活動,更不應成為某些藝術家假 “藝術鄉建”之名將其作為獲取利益的名利場。這是因為,以藝術的手段介入鄉村振興,其目的所在并不是彰顯藝術本身的特色,而是希望通過藝術審美等有效的途徑,參與到恢復鄉村傳統禮俗秩序和倫理精神的工作之中,進而激發鄉民的內生動力,產生主體性意識,積極參與其中。因此,藝術介入鄉村振興的工作,要在充分認識藝術屬性的基礎上,考察和衡量藝術對于鄉村振興和文化建設是否真正具有現實意義。“藝術對于鄉村的建設,不是單維度從藝術到藝術,從設計到設計,而是以藝術為抓手,服務于鄉村振興五大任務。”①陳炯、趙乾:《“藝術鄉建”的幾個價值》,《藝術工作》2021年第3期,第21頁。必須明確的是,參與鄉村振興工作之中的 “藝術”,絕非是學院派、藝術圈中慣常的 “藝術”概念,而是將其進行了外延,必須要根據鄉村振興實際工作的需要,根植于鄉村的服務體系中,從而使“藝術”真正介入和融入鄉村振興的宏偉戰略之中。
無論是作為藝術鄉建的謀劃者,還是藝術鄉建的實施者,只有在明確了藝術鄉建對于鄉村文化生態復構重要性的基礎上,藝術鄉建的既定目標才有可能實現。因此,對于目前藝術鄉建中所出現的一些不足,我們雖然可理解為是轉型期的陣痛,但必須加以重視和矯正,以保證藝術鄉建能真正介入和融入新時期鄉村文化生態系統的復構工作之中。
(二)藝術鄉建的文旨所歸
因數千年傳統文化的浸潤,幾乎每一位中國人的心底都深守著一份無處安放的 “鄉愁”。從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到“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從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到 “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無不表達出個體性或群體性的深沉鄉愁。這種深入中國人骨髓的鄉愁情結,雖然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理想,但依然是對于構筑詩意家園的執念。
鄉愁的本質是指因思鄉心切而生發出的情感上、心理上的愁思和對于家鄉的眷念,也因此成為人們對于尋根情感的深沉表述。哲學意義上的鄉愁 (Homesick)是指對于無法還鄉的 “此在”的哀悼與對 “詩意存在”的尋找。②參見向麗 《懷舊·鄉愁·烏托邦——中國藝術鄉建的三重面向》,《民族藝術》2021年第3期。德國浪漫主義詩人諾瓦利斯 (Novalis)則將哲學看作 “鄉愁”,錢鐘書在 《說“回家”》一文中,將諾瓦利斯的 “鄉愁”視為 “其實是思家病,一種要歸居本宅的沖動”,并說 “回是歷程,家是對象。歷程是回復以求安息,對象是在一個不陌生的、識舊的、原有的地方從容安息。”各時期各國別的學者均從多學科、多角度詮釋和描繪出人類對于鄉愁情感的依賴和覓尋。
但鄉愁終歸是理想化的情結和烏托邦式的幻象,如今鄉村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已大量疏離了傳統鄉村的固有本質,鄉情鄉俗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愈發淡化,甚至動搖了中國人幾千年來的情感根本。
基于此, 《鄉村振興戰略規劃 (2018—2022年)》中規定:傳承鄉村文化,留住鄉愁記憶,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在這種大勢之下,藝術鄉建必須將 “記得住鄉愁”作為自身工作的文旨所歸,多方協同,構建出適應當代社會語境的鄉村文化生態系統,助力鄉村振興戰略的不斷推進。
鄉土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底色,中國歷來重視鄉土文化的革新。費孝通先生在1948年出版的 《鄉土中國》第一篇 《鄉土本色》的第一句就明確提出:“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①費孝通:《鄉土中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年版,第1頁。梁漱溟在 《鄉村建設大意》中也指出:“至于創造新文化,那更是鄉村建設的真意義所在。鄉村建設除了消極地救濟鄉村之外,更要緊的還在積極地創造新文化。所謂鄉村建設,就是要從中國舊文化里轉變出一個新文化來。”②梁漱溟:《鄉村建設大意》,鄉村書店,1936年版,第16—17頁。
鄉土文化是孕育鄉愁的土壤,鄉愁也成為鄉土文化之根,但近四十余年的快速發展,時代卻疏遠了鄉土文化,以至于鄉愁在今日竟無處落腳。
鄉村振興的全面推進,為鄉愁情結的落腳和鄉村文化生態系統的復構提供了可能,藝術介入鄉村振興,正是喚醒鄉土記憶、使鄉愁效用最大化的最合理方式,這應成為藝術鄉建的文旨所歸。
二、復構·賦能:藝術鄉建的要義與途徑
所謂 “藝術鄉建”,指寄望采用藝術的方式、手段介入新時期鄉村文化的生態建設,通過 “文化賦能”“美育賦能”,推進農村社區營造,強化鄉民文化認同,激活鄉村內生動力,復歸鄉村傳統禮俗倫理,復構鄉村文化生態,從而構建出新型鄉村文化景觀和藝術理想,促發其依循人文秩序文化行為的產生。
需要再次強調的是,藝術鄉建絕非少數藝術家認為的簡單化的駐村寫生畫畫,而是一種系統性的文化建設行為,也非將城市文化、高校資源等與鄉村文化強行嫁接,是基于目標村落的客觀需求,多方協同,進行有針對性的文化賦能和藝術賦能,以進行目標村落文化生態的激活與恢復。藝術鄉建自始至終都必須 “服務”和 “賦能”意識,既關注物的 “創造”,又重視人的 “塑造”,重塑鄉民的主體性意識,這是 “‘主體間性’的問題,更是 ‘多重主體性’的問題。”③劉姝曼:《鄉村振興戰略下藝術鄉建的 “多重主體性”——以 “青田范式”為例》,《民族藝術》2020年第6期,第137頁。
質言之,藝術鄉建并非對鄉村進行 “藝術化” “藝術性”的根本性重構,而是要因循鄉村傳統的文化邏輯、使 “記得住鄉愁”的記憶效用最大化,進而實現修復鄉村文化生態的目標。概而言之,藝術鄉建的初級目標是在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基礎之上,提升和確立鄉民的主觀能動性,其旨歸則是協同各方,建構新時期的鄉村文化生態模式。因此,在藝術鄉建中,需要充分考慮鄉民主體以及藝術鄉建與村落的關系,關于“主體性”和 “主體間性”關系問題的討論必然要提上日程,這也促使藝術鄉建成為了一種深層次的社會行為。
“相對于 ‘主體性’而言,‘主體間性’是對前者的揚棄,把片面的 ‘主體性’升華為自由的 ‘交互主體性’,不僅肯定自我或人的主體性,也肯定世界或他物的主體性,并承認主體間的平等對話”,④劉姝曼:《鄉村振興戰略下藝術鄉建的 “多重主體性”——以 “青田范式”為例》,《民族藝術》2020年第6期,第136頁。也就是說,藝術鄉建必須 “在尊重差異性的基礎上建構 ‘主體間性’的權力架構,推進生成鄉建共同體。”⑤王孟圖:《從 “主體性”到 “主體間性”:藝術介入鄉村建設的再思考——基于福建屏南古村落發展實踐的啟示》,《民族藝術研究》2019年第6期,第151頁。可見,藝術鄉建絕非少數藝術家所想象的是其隨心所欲的實驗場。
據此,我們可以做一個總結:藝術鄉建應針對鄉村內具的精神性、區域性和成長活性,以 “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為前提,通過對話與溝通,以改良、修復乃至重構新時期的鄉村文化生態,重啟鄉村文化活力,促成文化賦能、藝術賦能的多維度、系統性文化建設行為。所有的藝術鄉建行為必須要在尊重鄉民 “主體性”的基礎上,進行 “主體間性”的思考與實踐。
(一)固本與造意
藝術鄉建的目的并非彰顯藝術的強勢,而是藝術所應承擔的社會義務和反哺社會的自覺意識,是協同多方力量對鄉村社會秩序、鄉俗文化生態的修復,是藝術面對新時期鄉村文化生態復構中的迫切需求所進行的跨學科探索。
當下鄉村文化的衰落凋敝已成事實,長期流傳和具有廣泛參與度的民俗 “非遺”活動的生存空間也日趨逼仄,而城市文化的誘惑,愈發加速了鄉村的空心化。再者,傳統村落空間、組織結構、村民關系結構以及勞作模式、生活方式等的變化,使當今鄉村文化系統表現為一種被動性與主動性兼具的“文化適應”和 “文化應激”。①參見張犇、樊天波 《“氣氛”與 “在場”——非遺保護背景下少數民族民俗文化模式的構建要素》,《藝術評論》2021年 第10期。
鄉村振興戰略不僅是單純的推動物質形態的發展,還肩負推進鄉村文化建設的重任,因此,“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只有鄉民主體有效存續,鄉村才能真正和持續地振興。但現實卻并不樂觀,鄉村中青壯年勞動力的不斷外流,造成鄉村人口結構問題凸顯,又由于鄉村規劃的錯位,衍生出 “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鄉村”等新問題的出現。
如何增強鄉民的固守信心,吸引外出鄉民返鄉,乃至吸引城市人群入駐、旅游、觀光、投資,將經過精準扶貧之后生活水平獲得極大提升的鄉村進一步升華,復歸鄉村文化生態,已成當下亟須。藝術鄉建正是希望通過藝術的啟蒙與召喚,激活鄉民的文化情感。因此,打造其 “在地性”“原真性”“氣氛性”等特色應成為藝術家、設計師們的共識,從而實現藝術介入鄉村行動從淺表化向鄉村本體建構的轉換。簡而言之,就是通過藝術與多方資源的協同,實現 “文化賦能”“藝術賦能”“美育賦能”的目標。
但 “賦能”絕不僅限于對有資源的鄉村的賦能,而應是普惠性的賦能,就理論角度而言,是設計倫理使然,這就要求是總體性鄉村社會文化生態的賦能,而非以賦能為幌子的有選擇的賦能。因此, “固本”與 “造意”應成為賦能的主要內容,即通過修復或重構鄉村文化生態系統實現 “固本”,通過最大化發揮鄉愁記憶效用,營造和構建適應新文化語境和鄉民精神需求的民俗文化秩序以“造意”。
目前對鄉村文化生態的修復,“基本策略是先給整個村莊的房子 ‘穿衣戴帽’,然后舉行各種各樣的策展活動,包括舉辦藝術節,只是不以藝術節作為主要抓手。這種模式往往比較重視當地的傳統手工藝。因為要想修復當地的社會與文化生態,經濟方面是最為重要的。致力于社會與文化生態修復的這班藝術家,大多很關注當地的手工藝,為了策展,甚至把其他地方的一些鄉土藝術也挪用過來。其實,強調從整體上修復鄉村社會與文化生態的藝術家,心中想的也往往是鄉村旅游,不管是 ‘穿衣戴帽’,還是策展,并非給本地村民看,而是為了吸引來自城市的游客。”②季中楊:《“藝術鄉建”的審美理念及其文化邏輯》,《粵海風》2021年第5期,第51頁。
這種模式在一些有資源的鄉村確實取得了一定成效,如 “‘青田范式’是以地方性知識為主線的……這其中包括青田依稀可見和有跡可循的村落歷史、宗族家庭、道德禮俗、民俗節慶、信仰系統以及生產生活等關系維度,而其中的每項還得依賴當地人具體的生命實踐及開放性的探索來拓展。”③渠巖:《藝術鄉建:中國鄉村建設的第三條路徑》,《民族藝術》2020年第3期,第18頁。“青田范式”并沒有重點彰顯藝術與審美的首位度,而是將藝術家作為推動該模式的主導角色,多層次參與文化賦能的實踐行動,成為近年來 “藝術鄉建”中一個比較成功的案例。
但其局限性依然存在,對于缺乏自然景觀和人文資源的鄉村,如何實現文化賦能?“近年來的藝術鄉建問題很多……外來藝術介入的問題在于忽略了本地民眾的藝術傳統,無視它們的自我生長、自我表述和自我傳承。其介入后的鄉建只是無靈魂的外觀,不再是有根的繼承,成為外來的藝術打造和視覺包裝。”①方李莉:《中國藝術人類學的理論和實踐》,《貴州大學學報 (藝術版)》2021年第3期,第13頁。這類現象的出現,說明目標村落還具有一定的打造價值。而那些既無自然資源,又無人文資源的鄉村,卻很難獲得外來藝術的關注。
對此,筆者認為,若要實現藝術鄉建的普惠性目標,助力構建鄉村自我認同的文化內循環系統,應成為文化資源匱乏鄉村藝術鄉建工作的主要方向,所謂的 “固本”與“造意”兩大要素,正是基于這種思考。
強調 “固本”與 “造意”,目的是在鄉村振興背景之下,恢復、修復乃至重構親和、真實、有生活意味的鄉村文化生態氛圍,培根固本,激活文化空間效力,形成鄉愁的召喚魅力,勾連過去、現在與未來,修復與重構鄉村的禮俗秩序和文化審美,實現鄉村文化生態從 “遮蔽”到 “看見”的轉換。
綜上所述,藝術鄉建應摒棄將鄉村作為藝術家試驗場或者工作室的狹隘思路,積極深挖和復構鄉村傳統文化脈絡,促進包括審美與功能、傳統與現代、城市與鄉村、人文與自然等在內的物質與非物質融合,恢復、修復和重構鄉村文化生態,最大化地發揮出藝術鄉建的社會功能。
(二)場所的精神
方李莉教授認為,未來最重要的藝術家也許不僅是要創作藝術作品,而是想辦法成為新的生活樣態與形式的創造者。②《藝術鄉建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搜狐網,https://www.sohu.com/a/299415573_149159,發表時間2019年3月6日。
藝術鄉建的目的是通過藝術手段對于鄉村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進行系統性治理和優化,“初衷意味著人們認同鄉村生活方式,承認鄉村與城市一樣,是一種文明形態,并與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在價值上是對等的。但是,在 ‘城鄉中國’階段,由于鄉村主體性缺失,人們并沒有把鄉村生活視為一種可選擇的生活方式,而是將其視為一種文化消費對象,毫無疑問,這使得 ‘藝術鄉建’往往與初衷背道而馳”,③季中楊:《“藝術鄉建”的審美理念及其文化邏輯》,《粵海風》2021年第5期,第53頁。成為一種 “審美幻象”。
因此,以 “固本”與 “造意”為基準,加強 “場所精神”的營造,有可能成為藝術鄉建打破 “審美幻象”的有效手段。
“場所精神”由挪威建筑理論家諾伯舒茲(Christian Norberg-Schulz)在其 《場所精神:邁向建筑現象學》一書中提出,諾氏借助海德格爾、皮亞杰 (Piaget)、凱文·林奇(Kevin Lynch)等的觀點,嘗試為建筑走出現代主義的局限找到一條新路。在諾氏看來,“場所”的本質不只是具體物質,而是由環境中人所熟悉事物的點點滴滴,經過長時間“人化”,集聚了各種有意義的特性,形成了復雜的空間結構,也因此形成了 “場所精神”,是一種 “人化”與自然共情的 “環境的氣氛”。因此,無論是單體建筑、群體建筑——村落、公共空間等具有明確特性的空間,都會成為 “人”的立足點和物理活動、人文活動的區域,進而轉變成為有意義的場所。當 “人”體驗到場所的意義時,就找到了“存在的立足點”,產生 “方向感”與 “認同感”,“場所精神”也由此產生。
鄉村聚落是基于歷代鄉民的生活需要和文化行為而逐步形成的,其類型各異的人文特質也使鄉村具備了形成 “場所精神”的基礎。在當前城鄉轉型的歷史背景之下,鄉村文化生態的衰退,直接掣肘了人們對鄉村固有的 “場所精神”的認同,而這也正是藝術鄉建所應面對和解決的任務。
在藝術鄉建工作中,強調場所精神的打造和注入,不僅有助于目標鄉村形成令人熟悉和穩定的文化空間秩序,而且還能有效慰藉返鄉鄉民的精神和滿足外來入駐者的心理需求,并可使藝術鄉建更加 “普惠”,更加充滿正義性和公平性。
有鑒于此,把握目標村落的人本性,尊重在地鄉民的價值觀念、審美情趣、村規鄉約、宗法秩序等,將 “場所精神”理論有機地融入目標村落的文化場域建設之中,多維度協調和依循鄉村的功能定位、空間形態、文化秩序等內在邏輯,最大限度地杜絕迎合外界觀看、賞玩的單向度功利行為需求,以“固本—造意—場所精神”為線性建設目標,由 “介入—融入”,完成藝術家與民眾的“和解”,并友善地共同“在場”。
結 語
“藝術鄉建”無疑需要藝術家的參與,但以過于藝術的角度和觀念介入當前的鄉村建設之中,實質上是對于目標鄉村的輕視,是對鄉村應有形態的狹隘想象和藝術家的孤芳自賞,如 “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們對于老物件、老建筑的欣賞與贊美,純粹是一種后現代的審美觀念。這種觀念并非人人都擁有,必須經歷過較高層次的文化教育,且具有對現代城市文明的反思后,才能夠產生這種美學觀念,繼而對鄉間生活產生向往。……藝術家們雖然宣稱尊重鄉村肌理與鄉愁,不以現代的、都市的審美理念去改造鄉村,而是讓固有的鄉村之美呈現出來,但事實上,所謂固有的鄉村之美,顯然不是來自鄉民的審美視角,恰恰是現代的、都市的審美理念,是迎合城里人 ‘鄉愁’情感結構的一種審美幻象。”①季中楊:《“藝術鄉建”的審美理念及其文化邏輯》,《粵海風》2021年第5期,第54頁。
這種現象的頻繁出現,表現出一些藝術家過多地以 “我”的身份考慮 “他”的位置,宣泄 “我”的藝術觀念,缺乏對 “他”應有的在地文化特性的思考,這導致 “很多人在過著假想的理想生活,過著別人眼中的理想生活。”
海德格爾 (Martin Heidegger)認為,天、地、人、神是相互交融的,只有超越主客對立的狀態,才能達到 “詩意地棲居”之境界。藝術參與鄉村振興的意義并非只是對于已有鄉村文化的根本性重建,而是在恢復和修復鄉村禮俗秩序和倫理精神的基礎上,喚醒和激發鄉民的主體意識后進行的建設。“藝術鄉建”不僅要完成由藝術啟蒙向鄉村本體—鄉村文化—生態系統建構的轉換,還應著力激活鄉村隱逸卻鮮活的審美基因,使其參與到當代審美經驗的生成與重構之中,最終實現整合在地性優勢資源,復構鄉村文化生態發展模式,加快實現鄉村社會新時期可持續發展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