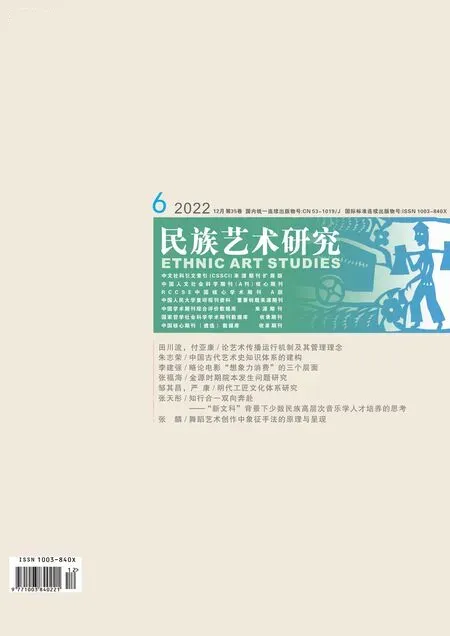對 “當代戲劇之命運”討論的反思與批判
穆海亮
“當代戲劇之命運”討論,源于2002年歲末劇作家魏明倫在鳳凰衛視 “世紀大講堂”所做的談話。這次談話激發了 《中國戲劇》編輯的職業敏感性,于是便以此為題,在該雜志開設專欄進行探討,持續一年之久。此后又趁熱打鐵,于2003年底在廣東佛山召開專題研討會,為此次討論畫上句號。
從2002年至今,已經過去20個年頭。我們之所以重返 “當代戲劇之命運”討論的“現場”,至少有兩個理由。其一,這是21世紀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戲劇理論討論。不能不承認,理論批評滯后于創作實踐是中國戲劇的固有態勢,現代中國的戲劇理論批評曾被視為“殘缺的戲劇翅膀”①參見宋寶珍 《殘缺的戲劇翅膀:中國現代戲劇理論批評史稿》,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可無論如何,20世紀終究還是出現了諸如五四時期新舊戲劇論爭、戲劇大眾化、話劇民族化、戲曲現代化以及80年代 “戲劇觀”論爭等影響深遠的理論探討,并取得一定的理論成果。進入21世紀以來,真正從整體上關注戲劇自身建設、集中探究戲劇藝術發展規律的理論批評幾乎難覓其蹤,而“當代戲劇之命運”討論恰是較為難得的甚至也是迄今為止絕無僅有的一次有意識的理論探討,其參與人員之眾、涉及范圍之廣、觀點交鋒之激烈都引人矚目。其二,20年的時間盡管并不算長,但對學術探討而言,就時間來說,已經具備了 “歷史化”的基本條件。當時過境遷之后,我們可以以更加客觀更加理性的眼光來重新審視這其中的理論得失:當年的討論中所做出的種種 “預判”,在今天得以證實還是證偽?當年探討的諸多理論問題,對戲劇藝術產生了哪些影響,對今天有何啟示價值,或呈現出何種思想局限?當年討論所涉及的藝術實踐問題,今天是圓滿解決了還是沉疴依舊?因此,20年后重返 “當代戲劇之命運”討論,就不單單是在進行理論的反思,同時也具備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討論的三個向度
“當代戲劇之命運”討論主要圍繞一個論題的三個向度而展開。一個論題,即當代中國戲劇的命運 (現實處境與未來出路);三個向度,即戲劇命運怎么樣?為何出現這樣的命運?我們應該如何應對?換而言之,也就是當代中國戲劇的命運 “是什么”“為什么”與 “怎么辦”的問題。
關于第一個向度,參與討論者幾乎眾口一詞地承認,當下中國戲劇確實面臨重重危機。至于危機的表現及程度,則有不同看法。魏明倫認為,當代中國戲劇之危機并不在于創作的困境,而在于觀眾的稀少。“當代戲劇的一度創作、二度創作都可以與歷代戲劇媲美”,“從劇本到演出,從內容到形式,從發揚傳統到緊跟新潮,從京津滬渝到南北省會,人才輩出,好戲連臺”①魏明倫:《當代戲劇之命運——在岳麓書院演講的要點》,《中國戲劇》2002年第12期,第5頁。;但問題是,即便戲再好,觀眾也不上門。魏明倫將這一現象歸納為 “臺上振興,臺下冷清”②魏明倫:《當代戲劇之命運——在岳麓書院演講的要點》,《中國戲劇》2002年第12期,第5頁。。一石激起千層浪,魏明倫此言在戲劇界引起強烈反響:觀眾流失、“臺下冷清”的說法引起絕大多數劇人的共鳴;至于說 “好戲連臺” “臺上振興”,則引來眾多戲劇人的反駁。
林克歡認為,魏明倫的觀點過于武斷和簡單化。他直言不諱地指出:“當代中國的戲劇現狀,遠談不上人才輩出,好戲連臺。臺上未必振興,臺下也未必冷清。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劇種,不同的劇目,不同的體制與運作方式,盛衰盈虧,差異極大。”③林克歡:《文化生態與戲劇生存空間》,《中國戲劇》2003年第2期,第18頁。劉平認為,所謂 “臺上振興,臺下冷清”的觀點在邏輯上是站不住腳的:從戲劇史的經驗來看,如果臺上真的 “振興”、佳作頻傳,臺下的觀眾一定是非常踴躍的;如果所謂的 “振興”僅僅是某種外力推動所帶來的舞臺上一時的“熱鬧”,那 “臺下冷清”也就沒有什么可遺憾的。劉平進而指出,“當代戲劇的一度創作可以與歷代戲劇媲美”之說不符合創作實際,“今天的觀眾不愿去劇場看戲,就是因為好戲太少,而好戲少的根本原因是好的劇本太少,再好的導演也做不成 ‘無米之炊’的事”。④劉平:《要 “莎士比亞化”,還是 “席勒化”——關于中國當代戲劇之命運的思考》,載姜志濤、曉耕主編 《叩問戲劇命 運—— “當代戲劇之命運”論文集萃》,中國戲劇出版社,2005年版,第361—362頁。基層戲劇工作者黃森林結合自己多年擔任縣劇團團長的切身經歷,指出魏明倫的這種觀點 “欠妥”,他自己在工作實踐中最深切的感受恰恰是 “好戲太少”:老戲過于陳舊,新戲則大多短命夭折。⑤參見黃森林 《戲曲必須與時俱進》,《中國戲劇》2003年第5期。就連曾做過文化部藝術局局長的曲潤海也并不諱言,所謂 “臺上振興”存在虛假的一面,即使獲過大獎的戲也不見得好,有些貌似 “陽春白雪”的作品獲獎之后就 “壽終正寢”,“雅俗共賞的戲卻沒有真正受到提倡和支持,廣大基層群眾能看到的新戲并不多”。⑥曲潤海:《從臺上臺后看中國當代戲劇之艱難》,《中國戲劇》2003年第3期,第24頁。譚霈生也認為,戲劇危機產生的主要原因并不在觀眾不愿進劇場,而在于戲劇界沒有提供足以吸引觀眾走進劇場的優秀作品。⑦參見譚霈生 《生機與自救》,《中國戲劇》2003年第12期。傅謹有所保留地贊同魏明倫所說的戲劇危機之根源不完全在戲劇創作的觀點,又做了一分為二的辨析。一方面,我們有那么多優秀的傳統戲劇作品 (“好戲”)和戲劇藝人,卻缺乏在這樣多變的社會背景下將優秀劇目和名角傳達給大眾的途徑和手段;另一方面,我們當下對所謂 “好戲”的評判標準存在偏差,不是尊重觀眾的趣味,而是遵從文化主管部門和 “專家評委”的趣味,尤其是當戲劇的 “賽場”壓倒 “市場”之后,“戲劇表演團體與一般觀眾的審美趣味之間越來越顯疏離狀態”。⑧傅謹:《工業時代的戲劇命運——對魏明倫的四點質疑》,《中國戲劇》2003年第1期,第14頁。在傅謹看來,這才是戲劇危機最主要的表現。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關于當下戲劇的危機,大家的爭論是建立在某種共識基礎上的觀點分歧。這一共識就是,當下戲劇確實處境艱難,觀眾流失嚴重,但并非只有死路一條,只要找準病因、對癥下藥,戲劇仍能維持其正常的、哪怕是 “一席之地”⑨魏明倫語。參見高揚 《關于 〈當代戲劇之命運〉的幾點補充》,《中國戲劇》2002年第12期。的生命延續。既然如此,其中的關鍵問題就是要給戲劇望聞問切、尋找病因了。
這就涉及到論爭的第二個向度——戲劇為什么會遭遇危機。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真可謂針鋒相對、不可開交。魏明倫將戲劇危機歸咎于當代人生活方式、文娛方式的巨大變化,尤其是以電視、電腦為代表的 “斗室文娛”和以體育比賽為代表的 “廣場文娛”,將戲劇藝術擠壓到 “時尚”之外。在這種情勢下,戲劇界向來引以為自豪的戲劇注重觀演之間當面交流的優勢,完全轉化為致命弱點,進入劇場交流恰恰成為戲劇欣賞的極大不便;再加上戲劇自身缺乏 “一本萬利”的商品屬性,與商品社會、市場經濟很難融合,因而 “熒屏時代、網絡世界、商品社會、斗室文娛、廣場游戲,以及轉型階段人心浮躁等多種因素,導致當代戲劇觀眾稀少”。①魏明倫:《當代戲劇之命運——在岳麓書院演講的要點》,《中國戲劇》2002年第12期,第5頁。林克歡則從文化生態的角度來探討戲劇的生存問題。他認為,在今天這樣一個社會分工日益精細,休閑娛樂、藝術欣賞方式日漸多樣化的商業時代,觀眾的分層與流失是極其自然的事情,演藝市場的重新洗牌也并不令人擔憂;但是,今天極其復雜的文化生態確實給戲劇發展帶來諸多挑戰:“處在這樣的現實場景與整體氛圍之下,受著多重壓力與多種困惑的戲劇藝術家們,一方面要拆解國家神話的宏大敘說,一方面又要抵制戲說、滑稽模仿、無厘頭逗笑的泛濫;既要抗拒日漸物質化、商品化、平面化的生存環境,應對消費文化的大肆擴張,又要克服名譽與經濟利益的種種誘惑,努力創造出某種有利于當地戲劇發展的新局面,真是談何容易。”②林克歡:《文化生態與戲劇生產空間》,《中國戲劇》2003年第2期,第19頁。馬也從整體上接受了魏明倫的觀點,又從全球化和大眾文化的學理角度做了更深刻的剖析。他認為,全球化導致的美國化、快餐化、同一化,以及大眾文化、消費文化、后現代主義文化對傳統和經典的消解,都使得文化格局乾坤顛倒,戲劇能夠偏居一隅、茍延殘喘就已經不錯了。于是,馬也得出了比魏明倫還要悲觀的結論:“‘戲劇的命運’從根本上說,是掌握在 ‘時代需求’這只看不見的手中。如果是時代不需求、不怎么需求、很少需求、少部分需求、大部分人不需求,戲劇自身再努力,也難以走出困境。”③馬也:《當代戲劇命運之斷想》,《中國戲劇》2003年第6期,第8頁。
傅謹則明確反對魏明倫的 “斗室文娛”說。他認為,將電視的興起乃至于多元娛樂形式的出現看成戲劇陷入困局的原因,“這樣的論斷實在是膚淺、皮相之至”。其理由是,電視只是一種傳播手段,它固然可能使得一部分人改變去劇場看戲的習慣,但也可能成為非常有效的傳播工具,使更多的人有機會欣賞戲劇表演,進而因喜歡上戲劇而走進劇場;更何況,如果文化娛樂更為繁榮的歐美發達國家并未出現今日中國戲劇這樣的危機局面,如果當下中國同樣受到電視等多元娛樂形式沖擊的出版等行業也沒有陷入戲劇這樣的危機中,我們還有什么理由說今天中國戲劇的危機是由多元娛樂形式的興起造成的呢?因此,在傅謹看來,戲劇危機另有原因。他論述較多的,一是非市場化的體制弊端,二是傳統的斷裂:“中國戲劇確實存在危機,一方面是悠久濃厚的戲劇傳統只有很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得到了較好的傳承,另一方面是經過 ‘文革’前后十多年的斷層,演藝人員的表演藝術水準出現了大幅度的下降。這些歷史造成的原因,加上戲劇長期處于非市場化的體制之中,很難吸引一流人才 (優秀編導人才的流失也是出于同樣的原因),這些都決定了目前中國戲劇的藝術水平很難達到一個比較理想的高度。”④傅謹:《工業時代的戲劇命運——對魏明倫的四點質疑》,《中國戲劇》2003年第1期,第14頁。曲潤海也不認同魏明倫的說法。作為一名長期從事戲劇管理的文化工作者,他很坦誠地指出,管理體制和指導思想的陳舊與死板,是造成戲劇危機的重要原因。⑤參見曲潤海 《從臺上臺后看中國當代戲劇之艱難》,《中國戲劇》2003年第3期。
當很多戲劇家把戲劇危機的根源歸咎于多元娛樂、大眾文化、商品社會、管理體制等外部環境時,也有少數戲劇人將對戲劇危機的思索指向了戲劇自身的藝術生態。彭奇志首先承認,戲劇危機當然有其外部原因——民族認同危機和戲劇消費主體社會邊緣化;同時,中國戲劇存在著嚴重的結構性矛盾:“一是藝術產品結構性矛盾突出,基礎設施建設多年虧欠,藝術產品有效供應不足;二是藝術生產單位體制性矛盾突出,使文化沒有形成利益驅動下的多元化投資體系;三是戲劇的功能在當代起了潛性的變異,民間的、自娛的、自發的功能被無形地隱藏,微妙地取而代之的是宏大的教化的功能。”①彭奇志:《在重構中重生》,《中國戲劇》2003年第10期,第6頁。
既然關于戲劇危機的 “病因”眾說紛紜,因而針對 “病因”而討論的第三個向度——戲劇人應該怎么辦的問題,大家提出的 “救治”方案自然也就各不相同。大體而言,可分為三類。其一,強調國家政策對戲劇的支持與保護。比如魏明倫指出,既然戲劇的危機主要不是由其自身造成的,而源于外部環境的擠壓,那么戲劇在這一特殊困難時期,更需要有人來 “養”,國家必須給予一定的特殊政策扶持。這一說法得到了多數討論者的贊同,尤其從那些基層戲劇從業者的發言中,更能體會到其渴望得到政策扶持、資金支持的強烈愿望。至于具體的扶持策略,則在大同之中又存小異。其二,呼吁大力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尤其重要的是把戲劇推向市場,激發市場活力,提升戲劇適應市場的能力。這一觀點以傅謹為代表,同樣引起很多人的共鳴,戲劇不能完全脫離市場也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當然,討論者同時指出,在市場本身尚不成熟、機制尚不夠健全的情況下,戲劇暫時仍然離不開國家政策的扶持,但扶持不是最終目的,暫時的 “供奶”是為了以后更好地 “斷奶”。其三,倡導從整體上優化戲劇生態,營造有利于戲劇發展的空間,這就需要內外兼修。其中較具代表性的觀點,如彭奇志指出的——既要優化戲劇的外部環境,使其能夠面向市場;同時戲劇自身也要通過內在調整,完成戲劇本身的現代性重構。王蘊明則強調:“要處理好全球化與民族化、現代化與多元化、大眾化與小眾化、面臨市場與堅守文化品性、創作自由與導向性的關系。”②王蘊明:《近視與遠矚——也談當代戲劇之命運》,載姜志濤、曉耕主編 《叩問戲劇命運—— “當代戲劇之命運”論文集萃》,中國戲劇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336頁。
二、戲劇 “向外轉”的理論傾向
“當代戲劇之命運”討論早已落下帷幕。當喧嘩過后,站在今天的立場上重新回顧這次討論,坦誠地講,我們的感受不免有些復雜。一方面,從參與討論的諸多文章看,不管是面對戲劇危機的焦慮、無奈甚至哀嘆,還是為振興戲劇而搖旗吶喊、出謀劃策,都體現著藝術家和理論家們維護戲劇藝術的拳拳之心,這著實令人感動;而且,其中的某些論述確實扣住了戲劇發展的脈搏,甚至閃耀著思想的火花,時至今日仍能引人思索,并引發一定的回響。比如,戲劇人在討論中發出呼吁,希望以國家政策扶持戲曲發展,這在今天已有現實的響應,尤其是包括國務院 《關于支持戲曲傳承發展的若干政策》等一系列文件的出臺,還有國家藝術基金等各個層面對戲曲藝術的持續資助,戲曲藝術的保護、傳承與發展問題,甚至已經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在此背景下,理論家當年倡導的對戲曲之 “傳統”的高度重視,在今天也已成為劇界的共識,乃至全社會已形成了尊重和弘揚戲曲傳統的良好氛圍,并正在自上而下地促進戲曲傳統的 “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再如,傅謹等理論家大聲疾呼戲劇體制改革、推動戲劇藝術的市場化,這些聲音今天仍然值得重視,盡管戲劇市場化的過程十分艱難,改革的效果也尚未充分彰顯,但無論如何,這一觀念已逐漸深入人心,相關工作實際上也在逐漸推進中。
但另一方面,我們不無遺憾地看到,“當代戲劇之命運”討論這場21世紀以來絕無僅有的大規模戲劇理論探討,在理論建設方面并未結出真正的碩果。更有甚者,其中不少參與討論的文章,由于與戲劇藝術本體、創作實踐有著較多隔膜,幾乎僅僅成為一紙空文的話語狂歡,因而也就難以對當時乃至此后的戲劇發展 (尤其是戲劇創作),產生真正強有力的理論指引。究其原因,固然與戲劇生態本身的復雜性有關,但同樣不容忽視的因素還在于,本次討論呈現出顯而易見的甚至頗有些極端化的 “向外轉”的傾向。這就是說,其討論的焦點主要集中于戲劇危機的外在表現、造成危機的外部原因、解決危機的外部策略,而真正圍繞戲劇藝術本體所展開的學理性探討則遠遠不夠深入,因而使得其理論建構存在明顯局限性或錯位。
首先,這次討論 “向外轉”的傾向,很大程度上是由論題本身決定的。“當代戲劇之命運”這一帶有 “悲壯感”和 “預言性”的論題,幾乎注定了其討論的焦點被置于戲劇的外部環境。這從肇其端的魏明倫宏論中就顯示出來了。既然在魏明倫看來,中國戲劇的危機并不是沒有好戲,而是戲再好觀眾也不來看,那么,這就不是戲劇本身的原因了,其 “罪魁禍首”必然在于惡劣的外部環境。因此,此后的討論主要就圍繞戲劇危機的外圍因素而展開,將戲劇危機的表現歸結為觀眾流失,戲劇危機的原因歸咎于斗室文娛、商品社會、大眾文化的影響和體制的束縛,將解決危機的策略寄托于政策扶持、市場化改革,等等,顯然這些都是外部闡釋的必然結果。
其次,退一步說,即使是對戲劇外部生態環境的討論,原本也可以觸及諸多方面的問題,但這次討論卻把重心放在了諸如時代更替、社會變遷之類客觀環境造成的 “外部問題”上,而很少論及人為原因導致的戲劇藝術本體自身的 “內部問題”。其實,正如署名 “朝問”者所指出的那樣, “三分人禍”即戲劇創作出現問題是 “導致戲曲從 ‘危機’走向更大的 ‘危機’,直至滅亡的一個重要因素”。①朝問:《生于民間 死于殿堂》,《中國戲劇》2003年第10期,第15頁。然而,在具體的討論中,更多討論者都傾向于將其歸咎于 “外部問題”,而有意無意地規避人為原因導致的 “內部問題”。關于 “外部問題”,可以暢所欲言;而一涉及 “內部問題”,大家就心照不宣地顧左右而言他。
其三,即使只論 “外部問題”,原本也可以富有學理性,正如傅謹、馬也那樣真正呈示深層探討的文章,即使我們不能認同其觀點,但其思考的深刻性也能給人以啟示。可遺憾的是,在這次看似十分激烈的討論中,真正在深刻的學理層面展開論述的只是少數,更多的討論并無學術及實踐價值。有的是一些淺表化的泛泛之論;有的是為了辯論而辯論,看似針鋒相對,其實是斷章取義;有的是自說自話——如:編劇強調自身的創作成績,基層院團領導呼吁資金支持;有的看似深奧,實則故弄玄虛——如:對 “場”之問題的糾纏不清,看起來頗有些嚇人,但實際上距離戲劇藝術的本體相當遙遠。等等。
對戲劇而言,外部環境固然不能說不重要,尤其跟其他藝術門類比較起來,戲劇所受的外部影響恐怕是最為明顯的。但是,對于任何一個有著獨立審美價值和完整藝術自律性的藝術門類來說,如果僅在外部環境里打轉,而對其藝術本體的關注和思考不夠深入,其討論就難免遭遇理論的錯位,戲劇自然也是如此。過多地關注外因 (外部環境)而忽視內因 (戲劇本體),可以說是本末倒置;在討論 “外部問題”時,過多意氣之爭而較少理論建樹,可以說是隔靴搔癢。指望本末倒置、避重就輕、隔靴搔癢的討論產生深刻價值和深遠影響,幾乎是不太可能的。關于 “當代戲劇之命運”討論這一 “向外轉”的傾向,譚霈生在當時就意識到了:“如果我們把 ‘外部問題’視為高于一切的關鍵,而忽視對 ‘內部問題’的正視,并不利于討論的深入。”②譚霈生:《生機與自救》,載姜志濤、曉耕主編 《叩問戲劇命運—— “當代戲劇之命運”論文集萃》,中國戲劇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頁。劉平也在討論中明確指出,戲劇的危機不在觀眾,而在自身,并不是因為有了 “斗室文娛”觀眾才不進劇場,而恰恰是戲劇創作者把觀眾從劇場里 “趕跑了”,“不是觀眾 ‘很難安心坐下來陪同臺上演員對面交流’,而是有些舞臺創作 ‘割斷’了觀眾與演員交流的渠道和機會,使得觀眾無法與臺上的演出交流。所以,觀眾才沒有了看戲時的審美愉悅,從而產生了失望情緒,而遠離了劇場。”①劉平:《要 “莎士比亞化”,還是 “席勒化”——關于中國當代戲劇之命運的思考》,載姜志濤、曉耕主編 《叩問戲劇命 運—— “當代戲劇之命運”論文集萃》,中國戲劇出版社,2005年版,第363頁。
那么,戲劇的內部問題究竟是什么?其實這又回到了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戲劇創作的困頓。劉平認為:“理論偏頗和創作思想的狹隘造成了作品內容的淺薄,創作上的‘一窩蜂’造成了藝術上的公式化與概念化,創作觀念的陳舊導致作品中缺乏思想。”②劉平:《要 “莎士比亞化”,還是 “席勒化”——關于中國當代戲劇之命運的思考》,載姜志濤、曉耕主編 《叩問戲劇命 運—— “當代戲劇之命運”論文集萃》,中國戲劇出版社,2005年版,第363—368頁。這些觀點并不新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影響中國當代戲劇發展的痼疾,進入21世紀之后也沒有明顯改善的跡象。如果戲劇創作停滯不前,那么戲劇危機也就不太可能得到緩解,當戲劇家無法提供優秀作品時,想把觀眾吸引進劇場就只能是一種癡心妄想。所以,觀眾的流失是戲劇創作出現問題的結果,而不是戲劇危機的原因。但遺憾的是,“當代戲劇之命運”討論一窩蜂地指向外部環境,一味地對戲劇的惡劣環境倒苦水,真正屬于戲劇本體的問題反而被擱置了。
三、戲劇危機與 “理論疲勞”
如果將20世紀80年代的 “戲劇觀”論爭和21世紀的 “當代戲劇之命運”討論貫通起來考察,我們更能清晰地看到當代戲劇理論 “向外轉”的清晰軌跡。早在 “戲劇觀”論爭開始時,戲劇人已經意識到戲劇危機的原因在于戲劇本身,陳恭敏將其歸結為 “自然主義的寫實手法”和 “公式主義的形象圖解”③參見陳恭敏 《戲劇觀念問題》,《劇本》1981年第5期。,前者指向戲劇審美形式的僵化,后者指向戲劇思想內容的庸俗社會學。既然如此,如果要真正解決戲劇危機,也就自然需要內容與形式雙管齊下。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戲劇觀”的論爭主要集中寫實與寫意、舞臺假定性等戲劇形式方面的問題,而戲劇題材內容的維度則被有意無意地懸置了。從反思內容轉向討論形式,可以說是戲劇理論的一次 “向外轉”;不過,由于形式畢竟也屬于戲劇本體的范疇,所以在突破機械的寫實主義、探索劇作風格及舞臺樣式多樣化方面,“戲劇觀”論爭終究還是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然而,到了21世紀的 “當代戲劇之命運”討論,其則不僅很少關注戲劇內容,而且就連20世紀80年代熱衷討論的戲劇形式問題,也不再引起人們的興趣,大家都集中“火力”去討論戲劇的外部環境問題了。這顯然是戲劇理論建設又一次的 “向外轉”。頗有意味的是,馬也在1986年對 “戲劇觀”論爭的形式化轉向所作的機智風趣的描述,也十分具有前瞻性地 “預言”了21世紀 “當代戲劇之命運”討論的走向。馬也這樣說: “從‘假、干、淺’轉到 ‘形式呆板’ ‘手法老化’,從公式主義的觀念圖解轉到 ‘公式主義地套用形式’,從 ‘不真’轉到樣式的 ‘不新’,從內容轉到形式,從內科轉到五官科,從內里的不美轉到容顏的不美,從容顏的不美轉成鏡子的不作美。”④馬也:《理論的迷途與戲劇的危機》,《戲劇》1986年第1期,第5頁。如果說 “戲劇觀”論爭是 “從內科轉到五官科,從內里的不美轉到容顏的不美”,那么, “當代戲劇之命運”討論就確實是 “從容顏的不美轉成鏡子的不作美”了。
“當代戲劇之命運”討論呈現出這樣的局面,并不令人意外。一方面,關于戲劇題材內容的討論早在20世紀80年代前期就被“疏導”了,這在21世紀同樣不大可能深入展開,即使要談,也只能是談諸如概念化、公式化、工具主義等那些老生常談的問題;另一方面,關于戲劇形式的開拓在20世紀80年代是困擾戲劇家的焦點和難點問題之一,但在21世紀劇壇,隨著戲劇敘事與結構方式的靈活拓展、戲劇風格的新奇絢麗呈現、技術手段的突飛猛進,舞臺形式早已變得極其豐富,戲劇形式早已不再成為問題,自然也就不大能夠引起人們討論的興趣了。既然形式問題不必討論,而內容問題仍然不便討論,所以面對越發嚴重的戲劇危機,戲劇家也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 “理論疲勞”。更何況,當20世紀80年代 “戲劇觀”論爭時,人們意識到危機,也能看到解決的途徑,大家就對理論抱有很高的熱情;而20年過去,當戲劇危機已深入骨髓 (已經到了要探討 “命運”的階段),甚至如果真的像某些戲劇家所預言的那樣,戲劇已經不被 “時代”所 “需要”了,那么,戲劇人對于理論研究不僅會感到“疲勞”,更有甚者,任何理論討論都可能是“徒勞”的。
在新時期戲劇40年之際,著名導演王曉鷹以親歷者的身份重新思考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戲劇的創新問題,說了下面一段話:
今天的戲劇藝術所面臨的創新課題肯定要比當年多得多也廣泛得多,譬如院團管理機制的創新、優質資源整合的創新、社會合作乃至國際合作模式的創新、以現代理念進行宣傳推廣和市場開拓的創新、持之以恒的觀眾教育培養計劃等方方面面的創新。但是戲劇的根本問題還是創作問題,如果只從創作層面上講,我們認為,有必要再次面對30年前的 “新時期戲劇”遺留下來的那個問題,即突破在創作中妨礙我們更好地表現人的深刻性、復雜性、獨特性的思維模式,突破公式化、概念化的藩籬,現在還要加上突破政績化、功利化、淺薄化、庸俗化的羈絆,以爭取真正意義上的藝術表達的自由。①王曉鷹:《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戲劇 “創新”問題再思考》,《文藝報》2018年7月23日。
在王曉鷹看來,今天戲劇所面臨的方方面面的問題,其中固然有很多不得不依賴于戲劇外部環境的優化來解決,諸如劇團管理、資源整合、市場開發、宣傳推廣、觀眾教育等等;但其中最為重要的問題,終究還是戲劇創作,尤其是在舊有的公式化、概念化痼疾尚未根除的情況下,又疊加了政績化、庸俗化的羈絆。在這樣的語境中,王曉鷹所期盼的 “真正意義上的藝術表達的自由”,仍然是一種美好而遙遠的愿景,而 “當代戲劇之命運”討論的 “向外轉”與 “理論疲勞”,就更是難以避免出現的必然結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