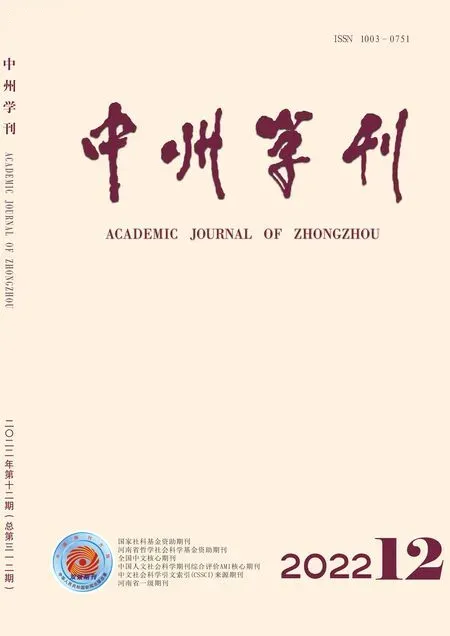西方中國形象演變的歷史圖景
——13—20世紀前半期西方人眼中的中國
趙 鳳 玲
自20世紀50年代“形象學”興起之后,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引起了學者的廣泛關注,如忻建飛的《世界的中國觀——近兩千年世界對中國的認識史綱》、周寧的《中國形象:西方的學術與傳說》等。西方的中國形象演變,從歷史進程來看,可分為歷史形象研究和當代形象研究,兩者之間有著必然的聯系。當下西方塑造的中國形象都可以從歷史上西方的中國形象演變中找出根源,甚至有一脈相承的關聯。研究西方中國形象演變歷史,把握不同時代西方塑造中國形象的特點,有助于我們重塑中國形象,扭轉西方對中國形象塑造邏輯的錯誤認識。
一、夢幻的形象
在13世紀之前,中國和西方對彼此的了解幾乎為零,中國和歐洲的文獻記載很少提及對方。13世紀之后,歐洲和中國的關系有了歷史性的突破,尤其是蒙古西征,更是為中歐經濟和文化的交流創造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歷史契機,“蒙古人的征服,使歐洲與中國的相互了解和交通在一切接觸中斷了至少四個世紀后又得以恢復,而且不僅僅是恢復而已。公元十三和十四世紀之后歐洲對中國的知識,甚至古代貿易最繁榮的時期都未曾有過的”[1]107-108。從歐洲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是傳教士、商人和一些冒險家,在短短的兩個多世紀,西方出現了許多關于中國的文本,既有傳教士和商人寫的史志、游記、書信,也有一些文人寫的小說、詩歌等文學作品。正是這些文本,“中國才第一次為歐洲所了解”[2]。
在這一時期,到達中國的傳教士留下的文本主要是柏朗嘉賓的《蒙古行紀》,書中對中國北部的自然地理、環境變化以及人民的生活習俗、宗教信仰的介紹,其“可靠性和明確程度方面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一直是首屈一指和無可媲美的”[3]13。其他傳教士的文本還有魯布魯克的《東行紀》、孟德高維諾的書信和馬黎諾里的《游記》。
旅行者留下的文本主要有兩個:一是《馬可·波羅行紀》,它一直被人們認為是第一部向歐洲全面介紹中國的“奇書”。在這部書里,馬可·波羅記載了當時元朝40多個城市和地區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狀況,他以幾乎狂熱的筆墨,構建了一個比當時歐洲更為文明、更為繁榮和富庶的中國形象。可以說,這部書是歐洲新航路開辟之前歐洲人了解神秘東方的重要途徑。二是《鄂多立克東行紀1687-1692》,這本書全方位描述了當時中國各地的風土人情,尤其是對杭州的記述,稱杭州是“天堂之城”“全世界最大的城市”[3]73。
文學家筆下的中國形象,主要體現在《曼德維爾游記》中,書中記載,中國金銀遍地,宮殿富麗堂皇,社會歌舞升平,欣欣向榮。它再一次激發了歐洲人對中國濃厚的興趣。
以馬可·波羅、鄂多立克和曼德維爾為代表的傳教士、商人和文學作家,通過自己的筆觸,將一個地大物博、城市繁華、政治文明、商貿發達、交通便利、人民富庶的中國形象帶入黑暗的中世紀歐洲,誠如赫德遜在《歐洲與中國》一書中所言:“馬可·波羅一家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前就已經為中世紀的歐洲發現了一個新大陸,這一發現對歐洲人的思想習慣有著深遠的影響。”[1]137這種影響主要是開啟了歐洲人對中國神話般的夢想,對中國理想社會的追逐,不僅僅是財富方面,還有對中國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羨慕和學習。
中世紀的歐洲,貧窮、混亂、王權衰弱,和東方的中國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中世紀末期的歐洲人渴求一種物質化的異域形象,以幫助其超越當時基督教文化所面臨的困境”[4]。恰好此時期的傳教士、商人和文學家的文本,給了歐洲人對中國理想化的形象描述,不管這種形象是神話,還是海市蜃樓似的充滿不可抗拒的誘惑力,都誘使歐洲的冒險家們對前往遙遠的東方尋找財富的王國充滿向往,也激勵人文學者大膽挑戰基督教的禁欲主義,積極追求現實的幸福和世俗的快樂。
二、理想的形象
15世紀新航路的開辟,滿足了歐洲人到達世界各地的愿望,對于歐洲人來說,最遙遠、最富庶的中國無疑成為他們的集體想象,一批批使節、商人和冒險家踏著海浪,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尋求他們想象中的天堂般的生活和令人垂涎的財富。
這一時期從歐洲來華最多的還是傳教士,他們成了西方中國形象構建的主力軍,在傳教士的筆下,留下了相當多的關于中國的記載,較有影響的有葡萄牙多明我會修士加斯帕·達·克路士的《中國志》、西班牙傳教士馬丁·德·拉達的《出使福建記》《記大明的中國事情》、西班牙圣奧斯丁會修士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以及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的《利瑪竇中國札記》。傳教士關于中國的報道,除了他們的傳教內容,還對中國作了較為全面的描述,涉及自然環境、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宗教、民族性格等,尤其是《中華大帝國史》和《利瑪竇中國札記》,對當時歐洲掀起的“中國熱”無疑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傳教士和商人筆下的封建制度,確實是當時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皇帝高高在上,閣老德高望重,以議會制形式決策,司法公正、制度健全,教育制度完善”[5]。中國是“當今全世界已知管理最佳的國家”[6]。
關于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在18世紀前的西方著作里都是模糊的,甚至是神秘的,到了利瑪竇筆下,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才首次彰顯在西方人面前。在利瑪竇筆下,中國人溫文爾雅,“以講究溫文有禮而知名于世,這是他們最為重視的五大美德之一”,“對他們來說,辦事體諒、尊重和恭敬別人,這構成溫文有禮的基礎”[7]63。“中國的道德書籍充滿了有關子女應尊敬父母和長輩的教誨”,“世界上沒有別的民族可以和中國人相比”[7]27。
誠如異域文化交流一樣,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認識,首先是從能感知到的物質文明開始的,仰慕先進的、鄙視落后的。西方對中國的形象認識也是如此,中世紀的歐洲遠遠落后于中國,西方人對中國感觸最明顯的還是物質,之后才能進入精神層面。可以說從17世紀開始,在西方進入啟蒙運動之后,西方對中國的形象的認知也進入另一個層面,即精神層面,中國精神層面的光輝形象開始引起西方人文領域的仰慕,西方的中國形象進入理想形象構建的頂峰,“中國熱”在西方社會悄然興起。這是17世紀末到18世紀中期一段最耀眼的時光。
17世紀的歐洲正是啟蒙運動不斷發展的時期,歐洲中世紀的封建主義和宗教神學的藩籬不斷地被突破,理性和科學逐步確立。對于歐洲的一些人來說,遙遠東方的中國不僅有他們羨慕的財富和土地,更有可以利用的文化價值,因此,此一時期來華傳教士的筆下,理想化的中國成為啟蒙主義者可資精神寄托的思想源泉,同時,傳教士尋求中國經典和基督教教義相通的精神旨趣,帶動了中國儒家經典被譯介到西方,為歐洲的啟蒙運動提供了理想的參照。傳教士在這一時期對中國的介紹主要文本有柏應理的《中國哲學家孔子》、白晉的《康熙皇帝》、李明的《中國近事報道》、基歇爾的《中國圖說》和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
柏應理的《中國哲學家孔子》第一次刊印了孔子的畫像,全面系統介紹了儒家學說。李明在《中國近世報道》中更是詳細描述了中國的物質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特別對中國的尊孔、祭祖和儒家學說大加推崇,認為“中國人連續兩千年都保持了對上帝的膜拜和景仰,簡直可以作為基督徒的表率”[8]。基歇爾在《中國圖說》中更是以專題的形式介紹了中國的物質、制度和思想文化層面的內容,特點是圖文并茂,通俗易懂,使中國形象逐漸傳播到歐洲,引起了普通大眾的興趣。當然最重要的圖書還是《中華帝國全志》,這本書是有關中國問題的百科全書。在作者的筆下,“中國人令人驚奇的溫和”,“中國人的價值觀念更加文明和禮貌”[9]。
當然在17—18世紀,歐洲社會對中國文化的介紹,主要還是得力于哲學家的努力。長期從事西方中國形象史研究的學者似乎在這方面達成了共識,認為歐洲啟蒙運動時期西方的哲學界之所以從游歷中國的文本所塑造的中國形象中挖掘歐洲社會所需要的理想范本,主要是啟蒙主義者想用理性的旗幟來代替宗教神學的權威,為資本主義文化代替宗教神學文化創造條件。縱觀世界各國,遙遠東方的中國哲學思想就成為他們心目中“最偉大的思想,他們的形而上學之最高理想”[10]。
在傳教士、游歷者對中國的各種文本描述中,哲學家們從各種資料中構建理想的中國想象,如萊布尼茨的《中國近事》《論中國哲學》、伏爾泰的《風俗論》、魁奈的《中國帝國的專制制度》等。在萊布尼茨看來,中國的道德哲學要遠超歐洲,“中國人完美謀求社會和平以及人與人相處的秩序”,不同于歐洲的“人與人相互為狼”,中國的倫理和德政是解救邪惡的正確道路,“中國人恪守一定禮制,是通過經常實踐而形成的天性,樂于遵守”[11]。為了贊美中國的德政,他還塑造了康熙皇帝這個“德統天下、內圣外王”的理想中國君主的形象。伏爾泰,也是中國文化的崇拜者,他贊揚中國的文化傳統,汲取中國文化的養分來豐富自己的思想體系。他敢于突破中世紀以來歐洲的基督教歷史觀,認為世界歷史是從中國開始的;他更是贊揚中國的重史傳統,贊揚中國是開明君主治理的典范,中國的政治體制是理想的政治模式,“中國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東西是道德和法律”[12]249。他相信,“人類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國政治還要優良的政治組織”[13]。魁奈也認為中國的君主專制制度是最接近于理想的社會治理模式,“歐洲應該以中國為榜樣,把研究和宣傳構成社會框架的自然法則,當作統治工作的主要目的”[14]。
18世紀的歐洲,崇拜中國的熱潮達到了頂峰,從器物到文化和哲學思潮,再到文學藝術,“中國熱”影響了歐洲社會的方方面面,中國成了歐洲人談論的話題。歐洲人對于中國的認識,從“上一個世紀我們并不太了解中國”[12]252,到“對中國,甚至比對歐洲的若干地域還要熟悉”[15]。法國作家格雷姆曾說:“在我們這個時代,中華帝國獲得人們的特殊的注意與研究。首先是傳教士從那個遙遠的國度寫回豐富多彩的報道,令人心神向往,這樣就形成了一種大眾觀念。”“然后是哲學家運用這些報道,從中提取各種有用的資料,批判自身社會的弊端。因此,中國一時成為智慧之鄉,美德與健康的信仰之鄉,中國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政府,歷史最為悠久,品德最為清廉,中國的法律、藝術、技藝都可以成為全世界的榜樣。”[16]尤其是1700年1月7日為慶祝新世紀的到來,法國國王路易十四身穿中國服裝,坐著一頂中國的八抬大轎現身在凡爾賽宮舉行的盛大舞會上,將歐洲追逐中國風推到了高潮,之后“中國情調”成為引領歐洲時尚的主流,歐洲人偏好中國器物,熱衷于模仿中國人的生活習俗和藝術風格,中國風尚在歐洲無處不在。
三、落后的形象
18世紀中期之后,一股批判中國的聲音悄然響起,伴隨著“禮儀之爭”和馬戛爾尼訪華,這股貶損中國的聲音愈演愈烈。尤其中英鴉片戰爭失敗后,愚昧、落后成為西方話語中的中國形象,這種國家形象在歐洲占據話語權的時代一直延續。
漢學家艾田普在《中國之歐洲》一書中說:“過分仰慕中國,就有排斥中國的危險。就像在一切人類活動中,人們總要走向極端。”[17]250原本對中國無比艷羨的西方人在18世紀中期卻罕見地出現了批評的聲音,“從那個世紀的中葉起,盡管在重農主義者中曾一度又掀起中國熱,但是中國癖已處在江河日下的狀態”[17]252。可以說從18世紀中后期開始,西方眼中的中國形象開始出現逆轉。
為何會出現如此轉變?這是因為,18世紀中后期,歐洲尤其是英國完成工業革命后,急需大量的工業產品原料和更廣闊的市場,幅員遼闊、物產豐富的中國成為英國乃至歐洲的首要目標。1792年馬戛爾尼使團的訪華以失敗告終。自認的頭號工業文明的資本主義強國,在中國栽了跟頭,導致馬戛爾尼在回國后整理的報告和發表的日記里,把大清朝描繪成落后和愚昧的形象。鴉片戰爭后,為了維護西方文明的話語權,“劣等他者”就成為西方描述中國形象的主要內容。在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下,中國形象在西方逐漸失去了昔日的光輝。
從19世紀一直到20世紀中期,西方的外交使節、商人、游歷者們不再關注中國文化的優秀成分和對世界的貢獻,而是從中國的社會、道德、宗教以及中國人的樣貌等方面,建構頹敗的社會、腐朽的政體以及沒落的道德等中國形象,在他們的一再努力下,一個腐朽落后的中國形象呈現在西方人面前,西方國家對中國和中國人充滿傲慢的鄙視和偏見。
在西方的中國形象構建中,中國人的身體樣貌是首先被嘲諷的,服飾和外貌成為他們構建中國形象的主要標志物。如清朝人留的長辮子,是西方人重點關注的對象,他們把長辮子稱為“豬尾巴”,極盡鄙視。西方人還對中國女性的纏足表現出譏諷和批判,為了達到目的,他們不惜筆墨大肆渲染。
在描述中國人的精神時,“虛偽”“自私”等詞語經常出現在他們的文本中,勤勞智慧等美德則很少被關注。經過無數西方人帶有偏見的描述,“東亞病夫”的形象在19世紀成為西方的中國形象。對于中國社會形象的描述,在19世紀乃至20世紀前半期,破敗的城市、貧困的農村成為西方人描述中國社會的主要內容,如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在《中國覺醒》一書中描述的,“無論誰來到這個城市(北京),遠看過去光耀萬里,宛若天堂,但走到近處一瞧,便覺敗興,眾多不堪入目的景象就會直入眼瞼。不論是宮殿還是茅舍,都一樣骯臟”[18]。甚至十里洋場的上海,在西方人的筆下也是污穢不堪,“所有的街道十分狹窄和擁擠,大量的人古古怪怪,商店空空如也”[19]。這顯然是有所選擇和帶有偏見的描述。
在19世紀之前,中國對西方來說是美德和信仰之鄉的化身,但進入19世紀之后,隨著國門洞開,越來越多的西方傳教士和游歷者深入中國腹地,他們選擇性地用略帶夸張的筆墨把中國落后的一面帶給西方公眾。不論是傳教士、游歷者,還是商務人員,在他們描述的文本中,中國人是“虛偽”“自私”的,社會是丑陋的,在這些西方人的不懈努力下,“劣等他者”的中國形象呈現在西方世界。
四、被“妖魔化”的形象
吉爾特·霍夫斯塔德說:“人人都從某個文化居室的窗后觀看世界,人人都傾向于視異國人為特殊,而以本國人的特征為圭臬。”[20]19世紀以來,西方國家“劣等他者”的中國形象正是西方在優越感支配下對中國的“妖魔化”描述。西方國家以西方為中心,用西方的政治制度、道德信仰、價值觀念、生活禮儀為標準,衡量其他民族和國家,其高高在上的文化心態一旦得到滿足,就會更加鄙視和凌駕于其他國家和民族之上。而這種心理如果得不到滿足,或者當其他國家在某些方面超越并有可能對其霸權造成影響時,他們對其他國家的看法就會發生扭曲,妖魔化、丑化甚至仇視其他國家就成為主流。
文化沖突和融合,只有近距離接觸才能對各自形象的形成產生作用。從19世紀開始,隨著一批批中國人出國謀生,不可避免地帶去了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和道德觀念,這對當地人產生了某種心理壓力,尤其是美國從19世紀中期開始的多次排華運動,就是這種恐懼心理的具體表現。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移民海外的華人讓西方親身感受到了心理壓力。首先,具有悠久文化傳統的中國人,即便移民海外,依然恪守母國文化傳統和信仰習俗,不愿意皈依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也就很難融入西方社會,對當地人來說他們是游離于主流社會的他者;其次,移民海外的華人勤勞肯干,任勞任怨,這些和西方完全不同的品德讓西方人感受到了一種競爭壓力。從19世紀末開始,在西方尤其是美國,一方面他們大造輿論,把中國和中國人描述為野蠻、落后的“劣等他者”;另一方面又把西方國家的社會矛盾,如經濟收入差距、失業壓力歸咎于華人和他們搶飯碗,進而激起種族仇恨。這其實就是“來自西方種族主義思潮中對龐大的外族人口的某種‘心理上的’排斥、仇視與恐慌”[21],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美國的一些文學作品更是推波助瀾,如美國作家杰克·倫敦在《空前的入侵》中,把中國描述為邪惡的入侵者。“妖魔化中國”是西方近代以來中國“劣等他者”形象的延續,也是一種有關中國形象的極端的意識形態化的心理表現。
結 語
西方的中國形象演變的歷史,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形象特征,大體經歷了夢幻的形象、理想的形象、落后的形象和被“妖魔化”的形象四個階段。每一個階段西方的中國形象既與中國在當時世界的地位有關,也與西方國家在世界的地位有關。針對不同時期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英國漢學家雷蒙·道森在其《中國變色龍》一書中用“變色龍”來概括幾個世紀以來西方的中國形象演變的歷史。“變色龍”不是指中國的形象在不同時期呈現的不同特點,而是指西方在不同時期對中國的不同認知。西方在創造中國形象的同時,也在塑造著自身形象。通過幾個世紀西方對中國形象的塑造,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西方對中國形象的塑造,并不是認識和再現中國的現實,而是要構筑一種西方需要的中國形象,一種以西方文化為主導的“他者”形象。基于這樣的認識,對西方國家針對中國的各種丑化、敵視也就一目了然了,對中國、中國文化任意的詆毀和“妖魔化”,不過是近代以來西方中國形象的內在延續,是有選擇性的塑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