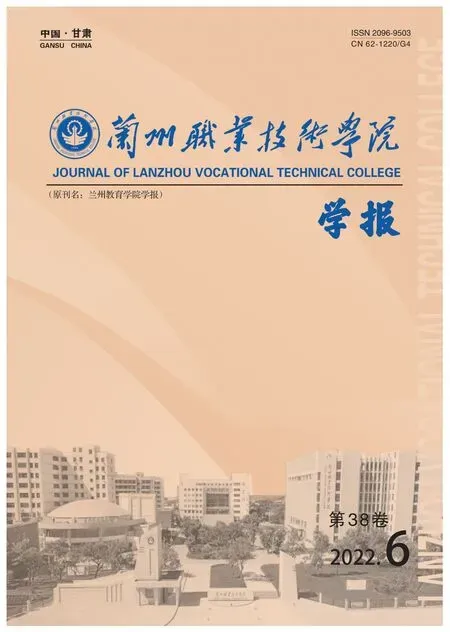“中國農(nóng)村派”農(nóng)村調(diào)查觀的特點、意義及啟示
朱鴻翔
(泰州職業(yè)技術(shù)學院 經(jīng)濟與管理學院, 江蘇 泰州 225300)
一、引言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各界掀起了一股農(nóng)村調(diào)查熱潮,其調(diào)查主體之多、范圍之廣、內(nèi)容之豐富、觀點之多樣均前所未見,調(diào)查的總次數(shù)不下于九千次[1]。在這些調(diào)查活動中,由于調(diào)查人的調(diào)查目的、學術(shù)理念、知識背景、身份立場等存在顯著差異,導致調(diào)查方法和結(jié)論各不相同。其中,以陳翰笙、薛暮橋等“中國農(nóng)村派”為代表的一批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者以科學理論為指導,以“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會”和《中國農(nóng)村》為陣地,以生產(chǎn)關(guān)系為研究對象,采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對江蘇無錫、河北保定、廣東番禺、云南景洪等地的農(nóng)村進行了調(diào)查。包括王寅生、張錫昌、瞿明宙、石凱福、張稼夫、錢俊瑞、劉端生、姜君辰、孫冶方、秦柳方等在內(nèi),該群體學者主持或參與了若干項調(diào)查項目的調(diào)查設(shè)計、調(diào)查訪問和資料整理,并利用調(diào)查資料寫出了一批頗有見地的調(diào)查報告。鑒于其調(diào)查活動的科學性質(zhì)和歷史影響,以及該群體學人在新中國經(jīng)濟學界的地位和作用,建國后學術(shù)界對其農(nóng)村調(diào)查活動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得出了一系列科學、客觀的結(jié)論。但梳理后發(fā)現(xiàn),這些成果大多以“活動”本身作為研究對象,尤其聚焦于無錫和保定的兩次調(diào)查經(jīng)歷,內(nèi)容上也更側(cè)重于史實陳述和成果點評,而立足思想史視角,對他們農(nóng)村調(diào)查觀展開系統(tǒng)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見。對該群體農(nóng)村調(diào)查觀特點及意義的考察,不僅有助于從獨特視角加深對陳翰笙等人農(nóng)村調(diào)查活動的認識,還能開啟觀察早期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中國化的一扇窗口。同時,透過這一學術(shù)活動與中國共產(chǎn)黨革命斗爭運動的緊密聯(lián)系,也有利于在一個更宏大的歷史背景下深入理解觀念的形成和變遷趨勢。
二、調(diào)查觀的主要特點
(一)科學性
在“中國農(nóng)村派”學者的農(nóng)村調(diào)查觀中,閃爍著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證法的光芒。他們以科學理論為指引,在試圖“研究中國農(nóng)村社會的復雜的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以及直接間接支配著中國農(nóng)民的整個經(jīng)濟體系”這個大目標下,秉持事物之間相互聯(lián)系和不斷發(fā)展的辯證法觀點,將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與工業(yè)、勞工、城市發(fā)展、國際貿(mào)易、社會變革等諸多問題通盤考慮,并以此為前提設(shè)計規(guī)劃調(diào)查活動。他們通過對收入、支出、消費等核心要素的細分,探討不同情境中這些概念絕然不同甚至相反的意義,從而擺脫了其他調(diào)查活動僅僅只詢問“你有多少財產(chǎn)”“每年多少收入多少支出”這樣膚淺問題的弊端,使其農(nóng)村調(diào)查觀呈現(xiàn)出鮮明的科學特征。
作為應(yīng)用科學理論的示例之一,薛暮橋特別強調(diào)調(diào)查方法的選用要視調(diào)查目標和內(nèi)容而定。他舉例說,如果希望獲得土地分配、耕畜農(nóng)具、農(nóng)業(yè)勞動以及各階層分類等方面的數(shù)據(jù),必須采用挨戶調(diào)查。而對租佃制度、雇傭制度、借貸制度、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農(nóng)產(chǎn)運銷、農(nóng)村副業(yè)等問題僅作一般研究的話,就可以采用概況調(diào)查。此外,在典型調(diào)查方法下,如果僅需了解該地的一般情形,要選擇有代表性的中等情況的調(diào)查對象;如果要研究某些特殊問題,就要選擇該項問題表現(xiàn)最明顯的對象[2]。這種思路充分體現(xiàn)了一切從實際出發(fā)和實事求是的特點,并在陳翰笙領(lǐng)導的無錫農(nóng)村調(diào)查中同樣得以體現(xiàn)。由于無錫農(nóng)民基本以種稻為主,各鄉(xiāng)的地勢、水利、作物、土壤、交通、市場等要素大抵相同,而農(nóng)村中村戶田權(quán)分化頗深,調(diào)查團因此遵從實際,按各村自耕農(nóng)、雇農(nóng)、佃農(nóng)、工人和商人的數(shù)量,將無錫農(nóng)村分為普通村和特殊村兩種。繼而又從各鄉(xiāng)選出9個普通村和13個特殊村,對此22村進行挨戶調(diào)查,共計調(diào)查1207家。另外,又于附近選擇33村,以及作為各村經(jīng)濟中心的8座市鎮(zhèn),作了概況調(diào)查[3]5。這種普通村和特殊村點面結(jié)合的調(diào)查方式,既兼顧了調(diào)查能力,省卻重復勞動,又保證了調(diào)查數(shù)據(jù)能夠有效支撐相關(guān)結(jié)論。
(二)批判性
“中國農(nóng)村派”學者身體力行,在全國范圍內(nèi)開展廣泛的農(nóng)村調(diào)查,還源于對其他派別或機構(gòu)調(diào)查情況的不滿。對于形形色色“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影響下的中國學者”所開展的農(nóng)村調(diào)查,他們著力揭示其缺陷,批判其目的。例如,陳翰笙指出,民國北京政府農(nóng)商部的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與統(tǒng)計,“其簡陋虛妄之點不勝枚舉”,由該部所出具的種種數(shù)據(jù)根本無法使用。而由金陵大學美國教授主持的農(nóng)村調(diào)查,“所用表格大都不適于當?shù)厍樾巍薄嶋H上,陳瀚笙非常反對卜凱等只關(guān)注生產(chǎn)力而忽視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傾向,認為后者不但對于復雜田權(quán)及租佃制度未能詳加剖析,甚至對于研究農(nóng)村經(jīng)濟所絕不容忽視的“雇傭制度、農(nóng)產(chǎn)價格、副業(yè)收入、借貸制度等等”,也是視而不見。至于哈爾濱東省鐵路經(jīng)濟調(diào)查局于1922—1923年開展的北滿農(nóng)業(yè)調(diào)查,陳翰笙認為其一是絕少涉及貧農(nóng),二是忽視了自耕農(nóng)與其他農(nóng)民在投資和收獲上的各種差異,三是沒有調(diào)查與農(nóng)村經(jīng)濟有著重要關(guān)系的借貸事項[3]4。從陳翰笙的指摘來看,所謂缺陷既包括了統(tǒng)計對象和內(nèi)容的走偏,也表現(xiàn)為調(diào)查數(shù)據(jù)的不實和遺漏。又如,張錫昌認為,非馬克思主義者所開展的調(diào)查僅僅顧及各種作物的播種面積、產(chǎn)量、價格、農(nóng)家收支,以及農(nóng)民生活等社會表象,其主要目的,“無非是要告訴他們怎樣可以用搶劫似的低廉價格來收買農(nóng)產(chǎn);怎樣可以把他們的商品推銷到中國農(nóng)村中來”。他因此斷言這類調(diào)查都不能夠說明中國農(nóng)村破產(chǎn)的真實原因[4]。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者對于技術(shù)派那種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式方案的不以為然和竭力反對。正是基于對已有調(diào)查各種不足的認識,他們才得以有意識地采取改進措施,建立起一套科學、完整的調(diào)查觀。
(三)發(fā)展性
“中國農(nóng)村派”學者秉持發(fā)展理念,根據(jù)實踐經(jīng)驗,能夠不斷修正和充實自己的調(diào)查觀。一方面,調(diào)查技術(shù)隨實踐經(jīng)驗而不斷進步。例如,調(diào)查者在保定進行的調(diào)查工作即吸取了很多無錫經(jīng)驗。針對無錫調(diào)查時農(nóng)戶們對很多問題不能詳答,含糊答案反而妨礙統(tǒng)計的狀況,調(diào)查者們將保定調(diào)查修正為抽樣調(diào)查。此外,在技術(shù)手段上,保定的挨戶調(diào)查表格,紙張做到大小劃一,免去了折疊和展開的繁瑣。在表格布置上也更加整齊,節(jié)省了三分之一的總面積,表格內(nèi)容則更加完備和進步。另一方面,調(diào)查內(nèi)容會隨著時間變化而持續(xù)調(diào)整。1937年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中華民族形成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黨的階段性重點任務(wù)隨之發(fā)生變化,“中國農(nóng)村派”學者隨即調(diào)整了調(diào)查方向和內(nèi)容。例如,作為對讀者“用什么方法來察知戰(zhàn)時農(nóng)村經(jīng)濟現(xiàn)況”問題的回應(yīng),劉懷溥撰寫了《戰(zhàn)時農(nóng)村經(jīng)濟訪問綱要》一文。他認為,在戰(zhàn)爭狀態(tài)下很難開展大規(guī)模的精密調(diào)查工作,但通過訪問法扼要地察知戰(zhàn)時農(nóng)村經(jīng)濟實況,不但容易著手,而且十分必要,這也是他擬定大綱的初衷。和以前相比,這份大綱中加入了一些極富時代特征的調(diào)查內(nèi)容,政治方面如農(nóng)村各階層對于抗戰(zhàn)的態(tài)度、當?shù)乇!⒓组L是何種分子等,經(jīng)濟方面如抗戰(zhàn)發(fā)動后農(nóng)村生產(chǎn)有無增加減少情況、當?shù)赜袩o藉故戰(zhàn)事逼債及廉價兼并土地的情形等[5]。
(四)指導性
“中國農(nóng)村派”學者為了最大程度地獲取第一手資料,曾經(jīng)長期指導全國各地農(nóng)村進步青年知識分子如何開展調(diào)查。《農(nóng)村通訊》是《中國農(nóng)村》的一個重要欄目,農(nóng)村通訊員們撰寫的調(diào)查報告經(jīng)常在該欄目得以刊載。由于這些報告直接來源于農(nóng)村,且由生活其間的人根據(jù)實際體驗撰寫,因此堪稱“研究中國農(nóng)村問題的最寶貴的參考資料”[6]。 考慮到在農(nóng)村承擔調(diào)查工作的相關(guān)人士文化程度較低,且未接受過系統(tǒng)訓練,故而怎樣在雜志上通過幾篇文章就能使他們迅速地掌握調(diào)查方法就成為編輯部面對的問題。在《農(nóng)村通訊怎樣寫法》一文中,編者就農(nóng)村調(diào)查與通訊寫作的幾個要點進行了說明。其中在講解撰寫農(nóng)村通訊的目的時,點明了是要“說明某一農(nóng)村社會問題”,所以需要的材料“不是自然現(xiàn)象”,而是“人與人的社會關(guān)系”,這就為學習者圈定了未來調(diào)查的內(nèi)容和范圍,并使其注意到此種調(diào)查的特點和意義所在。同時提醒學習者注意,“一切事實最好不要從它們的靜態(tài)上來觀察”,而是要從“動態(tài)”上去把握,這不僅體現(xiàn)了唯物辯證法的觀點,而且使學習者很容易迅速理解和掌握這一要領(lǐng),并能自覺將之運用到調(diào)查工作中。他們通過對不同年度的情形對比,將更有利于揭示農(nóng)村的興衰變遷過程。除了綱領(lǐng)性要求之外,指導者對于報告中如遣詞、造句等寫作細節(jié)也都有所涉及,他們建議農(nóng)村通訊的寫作者應(yīng)避免使用空洞、模糊的語言,而要列明具體事實和正確數(shù)字,以便讀者理解。
學者們的指導不僅局限于一般性內(nèi)容,還會就某一具體調(diào)查事項親自擬定調(diào)查大綱,以為廣大農(nóng)村調(diào)查者提供更為清晰和具體的方向及路徑指引。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會研究部曾于1935年7月擬定一份《暑期調(diào)查研究工作大綱》,作者在這份大綱中依次說明了調(diào)查的中心問題、研究項目和調(diào)查對象等內(nèi)容。由于預期參與對象是全國范圍內(nèi)的廣大讀者,該文特地對不同區(qū)域可以開展何種主題調(diào)查進行了舉例說明,諸如日本帝國主義的推廣華北棉產(chǎn)計劃、英美煙公司在魯豫等省的收買煙草方式、皖贛兩省的茶葉運銷統(tǒng)制等[7]。這種按地區(qū)確立不同調(diào)查主題的做法正是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者的典型觀點,恰如陳翰笙所指出的那樣:“中國各地農(nóng)村社會進化之程度,甚不一致。農(nóng)村經(jīng)濟之調(diào)查勢必分區(qū)進行,方為合理。”[3]5
(五)學術(shù)性
除了以問答性短文為載體所表現(xiàn)出來的指導性功能之外,學者們撰寫的主題論著還因其系統(tǒng)完整的闡釋而具備了一定的學術(shù)性,其中最為出色的是張錫昌所著的《農(nóng)村社會調(diào)查》一書。該書是上海黎明書局所出版的鄉(xiāng)村教育叢書的一種,此套叢書的出版是鑒于當時鄉(xiāng)村教育運動方興未艾,但研究鄉(xiāng)村教育的書籍卻十分稀缺,以致從事鄉(xiāng)村教育的人,“每感參考工具缺乏之苦”[8]。故叢書在內(nèi)容方面力求適應(yīng)鄉(xiāng)村環(huán)境,立足于鄉(xiāng)村實際問題,確立了“俾切實用”的編寫旨趣。叢書在形式編排方面,每章都在開始先列出中心問題,然后才進入正文部分,并以之呼應(yīng)章首,將其作為解決問題的工具,最后是“設(shè)計研究”,即通過實際案例進一步驗證理論內(nèi)容。作為叢書之一,張著充分體現(xiàn)了這一編寫思路,每章章首的問題極具啟發(fā)性,如“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一章中,作者的提示性問題就有:關(guān)于土地問題,應(yīng)該調(diào)查什么;關(guān)于農(nóng)民勞動,應(yīng)該調(diào)查什么;農(nóng)村中高利貸資本和商業(yè)資本的作用,應(yīng)從哪幾方面入手觀察,等等。這些問題除了引出相關(guān)的關(guān)鍵概念之外,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內(nèi)在邏輯性,并將農(nóng)村調(diào)查行為與系統(tǒng)的學術(shù)研究有機銜接起來,為讀者勾勒出開展農(nóng)村經(jīng)濟社會研究的具體取徑。此外,該書對于農(nóng)村社會調(diào)查在歐美及中國的演進、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的特性、中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的特質(zhì)以及中國農(nóng)村市場的性質(zhì)等理論性問題也有專題論述,體現(xiàn)出較高的學術(shù)水準。《中國農(nóng)村》編輯部在答讀者“如何利用寒假舉行農(nóng)村調(diào)查”問中,重點推介了此書,并提醒說,“該書最精彩的部分是第五章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和第四章調(diào)查材料的整理”。[9]
除了著作之外,學者們還撰寫出若干篇質(zhì)量上乘、學術(shù)性較強、可為范本的調(diào)查報告。韋健雄曾向讀者推薦了《中國農(nóng)村》一卷所刊載的《廣西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河南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浙江的土地分配》《江蘇的土地分配和租佃制度》《無錫三個農(nóng)村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調(diào)查》等篇目,他建議讀者對這幾篇調(diào)查報告“細細玩味”,并相信這樣可以有助他們對中心問題的把握[10]。總體而言,和卜凱等學院派相比,“中國農(nóng)村派”學者們的學術(shù)性毫不遜色。他們不僅具有扎實的知識基礎(chǔ)、強烈的問題意識、豐厚的學術(shù)素養(yǎng)、清晰的研究思維,而且始終強調(diào)和堅持嚴謹、踏實的調(diào)查作風,從而使該群體調(diào)查觀附著上了濃厚的學術(shù)底色。
三、調(diào)查觀的歷史意義
(一)調(diào)查觀的形成和發(fā)展體現(xiàn)了中國共產(chǎn)黨人對于先進理論的學習和應(yīng)用能力
無錫和保定兩次調(diào)查活動中的骨干成員陳翰笙、張稼夫、秦柳方、薛暮橋等人都是中共黨員,這些活動從始至終都有中共地下黨組織和地下黨員的積極參與[11]。他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圍繞黨在土地革命時期的指導思想、革命路線和奮斗目標,選取農(nóng)村調(diào)查研究作為著力點,在獲取原始資料的同時也論證、宣傳和闡釋了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說。此外,以揭示中國農(nóng)村社會性質(zhì)和貧弱根源為目的的調(diào)查活動,不僅能為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的革命斗爭提供先行資料和理論支撐,而且有助于爭取全國民眾對黨的政策的理解和認同。
(二)調(diào)查觀所秉持的以生產(chǎn)關(guān)系為中心的思路顯示出一種全新的經(jīng)濟社會研究模式
和形形色色的技術(shù)派主張截然不同,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者所運用的階級分析方法獨樹一幟。盡管該群體學者有時過于注重生產(chǎn)關(guān)系而將生產(chǎn)力置于從屬地位[12],但筆者認為,評價一種思想或行為,不能脫離其歷史背景。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者的農(nóng)村調(diào)查服從和服務(wù)于中國革命的大局,尤其很多文章是為應(yīng)戰(zhàn)而著,在反駁非議之論時,為取得最佳效果,難免會出現(xiàn)“厚此薄彼”的情況,這只能說是存在于特殊歷史階段的一種方略,不宜過分求全責備。
(三)“中國農(nóng)村派”學者農(nóng)村調(diào)查觀的形成和發(fā)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的一次成功嘗試
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和農(nóng)民問題研究為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的中國化提供了一個應(yīng)用場景,該群體的農(nóng)村調(diào)查觀是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在具體領(lǐng)域的折射和運用,其身份背景則決定了中國共產(chǎn)黨人在此種觀念的形成中發(fā)揮了主導作用。從撰寫的論著亦可看出,學者們已經(jīng)具備了將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jié)合的理論自覺和研究能力。雖然細究起來其中的某些觀點并非純粹經(jīng)濟學范疇,但“從廣泛論及經(jīng)濟涵義之外的階級斗爭、社會革命等政治及其他涵義,到聚焦經(jīng)濟理論和政策分析,正是其時中國經(jīng)濟思想發(fā)展與演變的特征之一”。[13]
(四)“中國農(nóng)村派”學者的農(nóng)村調(diào)查觀憑借其獨特的理論內(nèi)涵,為研究中國共產(chǎn)黨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思想發(fā)展史和中國近代經(jīng)濟思想史提供了一條基本線索
時至今日,對中國共產(chǎn)黨百年來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思想研究仍不充分,針對建國前的研究成果尤其缺乏。究其原因,在于搜集、梳理相關(guān)主題的原始資料,以及對其作貫通性的解讀和分析均存在一定困難。研究者既要對中國近代農(nóng)業(yè)和農(nóng)村經(jīng)濟有透徹把握,又要有足夠的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理論儲備,換言之,需兼具良好的史學和經(jīng)濟學雙重素養(yǎng)。鑒于此,不若先選擇若干合適恰當?shù)那腥肟冢詾楹罄m(xù)的綜合研究奠定基礎(chǔ)。再有,陳翰笙等人的經(jīng)濟思想后來還發(fā)展成為黨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基石之一,對新中國的經(jīng)濟理論與實踐都有著深遠影響。綜上,研究該群體學者包括農(nóng)村調(diào)查觀在內(nèi)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思想,在橫向上有利于開發(fā)利用黨的有關(guān)“三農(nóng)”思想資源,在縱向上有助于展現(xiàn)中國共產(chǎn)黨百年來的經(jīng)濟思想發(fā)展歷程。同時,他們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思想本身也是中國近代經(jīng)濟思想史不可或缺的有機構(gòu)成,且因其具有的引領(lǐng)作用而極富歷史意義和研究價值。
四、調(diào)查觀的當代啟示
(一)要注重提升對先進理論的研究和應(yīng)用能力
早期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理論學習和應(yīng)用經(jīng)歷充分昭示出我們黨在百年奮斗歷程中始終具有高度的理論自覺。黨的十八大以來,這一優(yōu)秀傳統(tǒng)更是得到進一步的傳承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是不斷發(fā)展的開放的理論,作為這一理論的最新成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需要我們?nèi)妗⑸钊搿⑾到y(tǒng)地學習,并以之指導我們的實踐。
(二)要準確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創(chuàng)新的過程
“中國農(nóng)村派”通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在中國的實踐,得出大量的科學結(jié)論,提煉出一系列理論觀點,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程中的重要篇章。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當代馬克思主義和二十一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正是在深入研究和精準把握世情、國情的基礎(chǔ)上,不斷創(chuàng)新、發(fā)展、豐富和完善,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推至一個新的高度。
(三)要充分認識黨在不同時期所形成的豐富經(jīng)濟思想均可成為構(gòu)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理論體系的養(yǎng)料
“中國農(nóng)村派”等先輩學者對如何開展中國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和農(nóng)民考察的闡釋充分表明,從典型人物、重要專題、關(guān)鍵產(chǎn)業(yè)等維度出發(fā),總結(jié)中國共產(chǎn)黨經(jīng)濟思想的演進歷程,掌握其理論、歷史和邏輯脈絡(luò),不僅能夠提供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早期中國化的寶貴經(jīng)驗,更可以采其精粹,以為充實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理論體系之用,從而“推進充分體現(xiàn)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jīng)濟學科建設(shè)”。[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