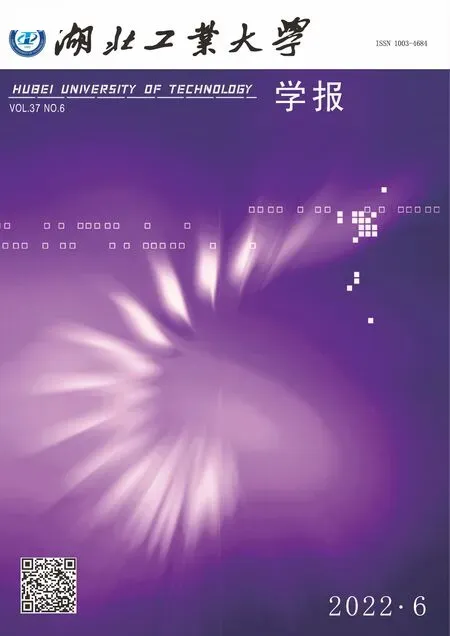前景化視角下平行語言結構及其翻譯研究
陳 彧,李 巖,陳順子
(1 湖北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湖北 武漢 430068;2 湖北省大冶市城東高中,湖北 大冶 435100)
莫言是中國當代文學代表作家之一,中國首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注重錘煉語言,其語言特色鮮明,極具個性化。被中美媒體稱為“莫言唯一首席接生婆”的美國翻譯家葛浩文認為,莫言寫作特點之一就是將語言陌生化,產生前景化效果。前景化作為文體學重要概念,在文學文本分析中占有重要地位,平行語言結構作為常見的前景化手段廣泛運用于文學作品。翻譯過程中如何在形式和功能兩個方面再現源文本中的前景化表達,為譯文讀者提供與源語讀者類似的閱讀體驗是翻譯工作者面臨的挑戰。莫言擅長利用平行語言結構塑造小說人物并突顯作品主題,葛浩文采用多種翻譯策略處理這些前景化語言的翻譯。本研究以葛浩文譯版莫言小說中刻畫主人公形象的平行語言結構及其英譯文本為案例,探究其翻譯策略及效果,以期為文學翻譯中的前景化處理提供參考范式,為更好地翻譯平行語言結構實現前景化提供思考。
1 前景化與平行語言結構
前景化(foregrounding)是文體學中與背景(background)、自動化(automation)、常規(convention)相對應的概念,它起源于俄國形式主義思潮,由維克多·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提出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概念演變而來[1]。陌生化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時期,雖然亞里士多德沒有明確使用“前景化”“陌生化”等字眼,但他的“驚奇”“不平常”“奇異”等說法表述的就是陌生化現象。亞里士多德認為使用奇字能使文章風格高雅并脫穎于平凡。由于人們慣于對常規事物視而不見,使用違反常規的語言文字則能喚起讀者的好奇,制造陌生感和新奇趣味。陌生化是詩歌、小說等文學作品慣用的手法。文學之所以區別于非文學,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語音、語法、語義特征的凸顯程度[2],這種不同于其他文體的特殊結構使文學獨具特性,產生獨特的藝術效果。
前景化概念最早出現在《標準語言和詩歌語言》中,布拉格學派代表人物穆卡羅夫斯基(Mukarovsky)基于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理論,將前景化定義為“對標準常規的系統化違反,是引人注目的、新穎的”語言結構[3]。日常用語和常規語言使語言自動化、慣例化,導致人們忽視語言表達的魅力。要打破這種狀態,就必須反常規化、反自動化,運用非自動化的奇特語言構成前景化,引起人們的注意,使人們從麻木的狀態中驚醒過來,感受語言的藝術效果[4]。
不同于布拉格學派聚焦于“前景化”之“偏離”現象,雅各布森更加關注“前景化”的另一重要形式——平行語言結構。受索緒爾的組合關系(syntagmatic relation)與聚合關系(paradigmatic relation)影響,雅各布森提出“投射說”,把語言符號的關系分為組合(combination)和選擇(selection)兩種,認為詩歌是將聚合軸上的語言根據等價原則投射到組合軸上[5]。根據雅各布森的等價原則,同一聚合體內各個成分是等價的,如詩歌中的頭韻、尾韻、排比、反復等現象均為等價的表現。這些修辭手法所產生的前景化表達,為文學文本提供更多選擇,產生更多藝術美感,使得文章或者詩歌在音韻、句式上具有豐富層次。平行語言結構作為前景化的重要表現形式,為語言前景化研究打開了新途徑,為修辭化語言生成動因及意義提供解釋。利奇認為,平行和偏離都是詩歌的語言特征,在前景化研究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6]。
國內主流學者提出,文體學研究中的前景化包括兩個方面:對于常規語義、語法的違反以及語言的重復使用和排比[7]。文獻表明,從“偏離”角度分析中國小說語言的學者較多,從平行語言結構視角分析小說前景化現象的研究并不多。江南[8]從詞匯和語音兩個層面分析新時期先鋒小說中平行原則的體現,其研究立足于反復、排比、照應等修辭手法,但未討論該類文本的翻譯策略。孫會軍[9]有關文學作品中“反復”現象及翻譯策略的研究表明,反復格作為一種修辭手法是作者精心設計的陌生化文學性表達,使其“前景化”地實現作品的文學性,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需要盡可能地保留其風格才能傳達源文前景化形式所要表達的效果。
平行語言結構作為實現前景化的重要手段,在新時期先鋒小說中有大量的運用和體現。魔幻主義作家莫言小說中更是運用了大量平行語言結構使其文字極富韻律、朗朗上口。由于平行語言結構在語義、句式上的重復,翻譯過程中譯者要意識到平行語言結構多數是作者有意為之,服務于突顯人物性格與事態發展以及作品主題意義,翻譯過程中要盡可能保留其文體風格,努力達到與源文本同等的前景化效果,幫助譯文讀者準確理解小說人物,領悟作品主題意義。
文學翻譯重內容輕形式的做法屢見不鮮,文學翻譯傾向求穩求舊,習慣采用歸化表達方式,多采用單一表達代替平行語言結構中語義重復的部分,導致譯文形式和意義的缺失。本文對莫言小說中平行語言結構及葛浩文英譯版開展案例分析,探究譯文采取何種翻譯策略來實現譯文與源文同等的文學性,并最大限度地傳遞前景化效果。
2 平行語言結構及其翻譯策略
平行語言結構的形成與人類語言生成的基本過程有關,語言的生成是一個選擇的過程,一個句子中出現的每一個詞、詞組都是在眾多相似或相關的語言單位中選擇的結果。這些被選擇的詞(或詞組)之間有相似、相近或相反的關系遵循著一種對等的原則。文體學者認為,詩歌語言以及所有的小說語言,都遵循著一種對等原則,即語言中的成分在語義和結構上擁有更多的相似、相近或相反的關系,包括語義上的對應與呼應、結構和韻律上的對等、重復等[10]。
文學作品的形式和內容常常“不可分”,文學的目的不僅是信息傳遞,更是通過詩學語言將常規語言陌生化,激發人們對于語言形式的關注,欣賞語言的藝術效果。譯者要想成功地翻譯一部文學作品,一定要將形式與內容放在同等重要地位,識別前景化語言,最好采用異化的策略,最大限度地在譯文中體現源文的前景化及其效果[11]。莫言作品從主題形式到語言表達都充滿靈動的想象,兼具跳躍性與獵奇性,并且他在語音、詞匯、句式層面大量地運用平行語言結構。平行語言結構在小說中運用最主要的作用之一是突顯人物描寫,刻畫主人公形象。考慮到篇幅問題,本文將聚焦語音、詞匯、句式三個層面,從源于四本小說中收集到的127語料中,選用5個比較典型的案例來探討葛浩文在翻譯用來突出小說人物性格的平行語言結構所采用的翻譯策略及功能實現。
2.1 語音層面
莫言小說中平行語言結構在語音層面有大量體現。莫言喜歡在韻律和節奏層面斟酌用詞,在描述事件時,采用擬聲詞、疊詞來營造氛圍,給讀者提供審美享受的同時,賦予文字形象生動又朗朗上口的特質。押韻、對偶也是莫言善用的修辭手法,鋪排詞句,創造平行語言結構,給讀者帶來藝術體驗。
例1:三天中的每一個畫面、每一個音響、每一種味道都在她的腦子里重現……喇叭嗩吶……曲兒小腔兒大……嘀嘀嗒嗒……哞哞哈哈……嗎哩哇啦……咿咿呀呀……嘰哩欻啦……直吹得綠高粱變成了紅高粱……(《紅高粱家族》)
Every scene from those three days, every sound, every smell entered her mind...the horns and woodwinds...little tunes, big sounds...all that music turned the green sorghum red.(Howard Goldblatt,1993)
例1描述的是少女戴鳳蓮回憶自己從坐上花轎離開家到騎著毛驢回家三天的經歷,此時她正陷入嫁給麻風病人前途未卜的境地。文中先以“每一”鋪陳三天的經歷(“畫面”“音響”“味道”),接著用系列擬聲疊詞來描繪耳之所聽,從而映射心中所想,暗示戴鳳蓮內心的焦急與無奈。通過頻繁使用疊詞,將聲音描繪推至前景的位置,促使讀者去感受主人公內心的萬千思緒。
譯文中葛浩文將“horns”“woodwinds”“tunes”“sounds”排列鋪陳,借助尾韻“s”,構成了平行語言結構,讀起來朗朗上口、韻律十足,與源文中對于喇叭聲音描述中的尾韻“na”“da”“ha”“la”“ya”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巧妙地還原了前景化效果。另一方面,葛浩文采用歸化翻譯策略,省譯擬聲疊詞,雖然順應了英文行文規則,卻降低了譯文讀者閱讀審美享受,無法體會到作者新奇的描寫手法,也不能感同身受小說人物內心的掙扎。譯文未能很好地體現源文語言的前景化效果,如能采用直譯加音譯的方法,將聲音描繪添加進譯文,能幫助譯文讀者同樣關注到作者表達的情感,獲得與源文讀者等效的審美效果。筆者試譯如下:
Every scene from those three days, every sound, every smell entered her mind...the horns and woodwinds...little tunes, big sounds...di di da da...mou mou ha ha...ma li wa la...yi yi ya ya...ji li gua la...all that music turned the green sorghum red.
2.2 詞匯層面
反復(即重復)、語義對立是平行語言結構在詞匯層面的主要表現形式。就莫言小說而言,詞匯層面的平行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某種意象的重復使用與呈現,構成反復格;二是運用對等原則并置鋪陳二元對立的詞語,構成平行語言結構,實現前景化。莫言通過構建平行語言結構,延長讀者對語言的感知過程和品味時間,增強其作品的美學功能。
例2:那條斜街是條肉食街,露天里擺著十幾個燒肉的大鍋,鍋里煮著豬、羊、牛、驢、狗的頭,豬、羊、牛、驢、駱駝的蹄,豬、羊、牛、驢、狗的肝,豬、羊、牛、驢、狗的心,豬、羊、牛、驢、狗的肚,豬、羊、牛、驢、狗的腸,豬、羊、牛、驢、狗的肺,豬、牛、驢、駱駝的尾巴棍兒。
Stewed meat was sold from a dozen open-air cooking pots—the heads of pigs, sheep, cows, mules and dogs; the feet of pigs, sheep, cows, mules and camels; the livers of pigs, sheep, cows, mules and dogs; the hearts of pigs, sheep, cows, mules and dogs; the stomachs of pigs, sheep, cows, mules and dogs; the entrails of pigs, sheep, cows, mules and dogs; the lungs of pigs, sheep, cows, mules and dogs; and the tails of pigs, sheep, cows, mules and camels.
例2選自《四十一炮》,小說以20世紀90年代初農村改革為背景,主人公羅小通是位身體發育成熟、心理卻停留在少年時代的巨嬰。小說通過羅小通的狂歡化式訴說,描寫了農村改革初期兩種勢力、兩種觀念的激烈沖突,揭示人性的裂變的同時,寫出了人們在是非標準、倫理道德上的混沌和迷茫。“愛吃肉”是少年羅小通最大的特點,在物質匱乏的年代,肉是農村家庭的奢侈品,加上小通母親的“吝嗇”,吃上肉成為羅小通“此生最大的夢想”。小說對肉食街的描述出奇的詳細,常規寫作中可以省去的“豬、羊、牛、驢、狗”卻在這里重復了8次,讓讀者腦海里構建出一條滿是肉鋪的街道,掛滿了各式各樣的肉,四處彌漫著肉味。對比羅小通夢而不得的“吃肉”渴望,這情景給他帶來的折磨會引起讀者的思考并探究其中原因。帶著尋找羅小通將如何滿足內心對于“肉”的渴望,讀者會饒有興趣地參與到小說敘事當中。
譯文表明,葛浩文采用異化翻譯策略處理例(2)中的重復性語言,通過直譯保留了源文的前景化效果。不斷重復的“pigs, sheep, cows, mules and camels(dogs)”這5個意象還原了莫言所構造的平行語言結構,延長了讀者閱讀時間,以同樣醒目的方式抓住讀者眼球,激發讀者去思考作者重復同樣意象描寫的原因和意圖,聯想羅小通對“肉”的渴望,就能更深刻地理解羅小通的內心活動,羅小通這個人物形象更立體地展現在讀者面前。譯者還原源文本中平行語言結構,保留了源文的前景化效果,實現了源文作者的意圖,是非常成功的翻譯案例。
例3:他看到了一幅奇特美麗的圖畫:光滑的鐵砧子,泛著青幽幽藍幽幽的光。泛著青藍幽幽光的鐵砧子上,有一個金色的紅蘿卜。紅蘿卜的形狀和大小都象一個大個陽梨,還拖著一條長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須須象金色的羊毛。(《透明的紅蘿卜》)
His eyes, big and bright to begin with, now shone like searchlights as he witnessed a strange and beautiful sight: a soft blue-green light suffused the sleek surface of the anvil, on which rested a golden radish.In shape and size it was like a pear, though it had a long tail, every fibre of which was a strand of golden wool.
例3選自《透明的紅蘿卜》,小說講述的是一個頂著大腦袋的黑孩,從小受繼母虐待,沉默寡言,經常對著事物發呆,并對大自然有著超強的觸覺、聽覺等奇異功能的故事。例句中重復著“泛著青藍幽幽光的鐵砧子”的意象,突顯了黑孩對大自然的奇特感知力,通過反復的修辭手法,使畫面感更加立體,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譯文中,葛浩文采用了歸化翻譯策略,按照英文的表達習慣,用“which”代替“泛著青藍幽幽光的鐵砧子”的意象描寫,雖然更符合英文的表達方式,但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前景化效果。源文中的表達雖然構成語義的重復,但是通過反復強調,能夠將場景描繪得更加生動立體,使“泛著青藍幽幽光的鐵砧子”這一意象在讀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達到與主人公黑孩感同身受的效果,體會到黑孩對于自然事物的奇異感知。省略重復性描寫的譯文弱化了讀者對場景的感知,無法達到源文中同樣的效果。筆者認為,為了更好的還原源文的平行語言結構,實現作者的強調人物描寫,應將作者著重重復表達的意象翻譯出來,試譯如下:
His eyes, big and bright to begin with, now shone like searchlights as he witnessed a strange and beautiful sight: a soft blue-green light suffused the sleek surface of the anvil.There existed a golden radish on the anvil with a soft blue-green light.The golden radish was like a pear in shape and size, though it had a long tail, every fibre of the long tail was a strand of golden wool.
在文學家看來,形式是文學作品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文學的基礎和文學性的體現,與內容處于同等重要地位。作者此處的重復并非毫無意義,而是通過對細節的刻畫,讓讀者理解黑孩感官系統的特殊性,對于小說塑造的黑孩形象有更加深刻的認知。因此,譯文中對于源文平行語言結構的省略處理,雖然將文本內容傳達給讀者,但是文本形式的缺失弱化了人物形象描寫,譯文讀者無法深入了解主人公黑孩的奇異感知系統,這是譯文的一大缺憾。
例4:他有一個情婦。她有時非常可愛有時非常可怕。有時像太陽,有時像月亮。有時像嫵媚的貓,有時像瘋狂的狗。有時像美酒,有時像毒藥。他想和妻子離婚又不想離婚。他想和情婦好下去又不想好下去。他每次犯病都幻想癌癥又懼怕癌癥。他對生活既熱愛又厭煩。(《酒國》)
He had a mistress, who was sometimes adorable and sometimes downright spooky.Sometimes she was like the sun, at other times the moon.Sometimes she was a seductive feline, at other times a mad dog.The idea of divorcing his wife appealed to him, but not enough to actually go through with it.Staying with his mistress was tempting, but not enough to actually do it.Anytime he took sick, he fantasized the onset of cancer, yet was terrified by the thought of the disease; he loved life dearly, and was tired to death of it.
例4選自《酒國》,莫言運用褒貶色彩對立兩組詞語“有時可愛有時可怕”,“有時像嫵媚的貓,有時像瘋狂的狗”來形容同一對象——主人公丁鉤兒的情人。接著用四組情感矛盾的短句來描述丁鉤兒充滿矛盾的內心:想離婚又沒有勇氣,對情婦感情搖擺不定,想生病又怕生病,對生活的時愛時厭,展現了一個人最真實最赤裸的內心感受和復雜情緒。
葛浩文在譯文中以異化策略為指導,采用直譯的方法,將這些充滿矛盾的意象“adorable”“spooky”、“the sun”“the moon”“a seductive feline”“a mad dog”一一再現,后又將主人公丁鉤兒內心充滿矛盾的情感進行鋪陳:明明想要離婚,但又說“but not enough to actually go through with it”;明明想和情婦在一起,卻說“but not enough to actually do it”。這一處句式的排列,再現了主人公的矛盾心理,并形成了相同語義的對稱排列。譯文中同樣構成平行語言結構,巧妙地再現源文的前景化風格,引起讀者對于這一語言排列的思考,進而體會小說人物內心復雜而真實的感受,同時也使得前景化的文學效果得到很好的傳達。
2.3 句法層面
平行語言結構在句法層面多體現為句式的整齊排列,即排比修辭手法,由于中英語言結構差異,實現語言前景化對譯者來說是一個挑戰。
例5:最先一批兇狠的雨點打得高粱顫抖,打得野草觳觫,打得道上的細土凝聚成團后又立即迸裂,打得轎頂啪啪響。雨點打在奶奶的繡花鞋上,打在余占鰲的頭上,斜射到奶奶的臉上。(《紅高粱家族》)
The first truculent raindrops made the plants shudder.The rain beat a loud tattoo on the sedan chair and fell on Grandma’s embroidered slippers; it fell on Yu Zhan’ao’s head, then slanted in on Grandma’s face.
例5通過將雨點掉落的動作“打”進行排列描寫,出現了七次“打”字,通過不斷地重復、鋪排,突出了此刻雨勢之大,也映射出主人公戴鳳蓮(奶奶)在經歷劫匪之后內心的忐忑以及對“余占鰲”情感的萌芽。通過排比的修辭手法,對于“打”這個動作的重復刻畫,構建音律統一的平行語言結構,使這段文字不僅傳遞信息,同時產生審美效果,并由此引發讀者對于人物內心的審視和探索。
在英譯的過程中,葛浩文采用歸化翻譯策略,通過省譯源文中排比修辭和擬聲詞“啪啪響”來適應英文表達習慣,卻使譯文語言失去韻律感。葛浩文將源文不斷重復的“打”字省譯后,原文的強調意味被削弱,由于雨滴不停地“打”在奶奶的周遭、“打”在奶奶身上,如同打在奶奶心上,這個重復的“打”字映射出主人公內心的忐忑與悸動,這一層含義在譯文中并未體現出來。譯文對于源文形式的省略,使得平行語言結構的前景化效果大打折扣,對于譯文讀者來說,很難獲得與源文讀者同樣的閱讀體驗。筆者采用異化原則,對譯文進行調整,試譯如下:
The first batch of fierce rain hit the sorghum trembling, hit the weeds frightened, hit the road on the fine soil cohesion into a ball and then immediately burst, hit the palanquin roof snapped.The raindrops hit the grandmother's embroidered shoes, hit Yu Zhanao's head, and slanted to the grandmother's face.slippers; it fell on Yu Zhan’ao’s head, then slanted in on Grandma’s face.
3 總結
前景化理論是文學文本分析的重要內容,它強調形式與內容的同等重要,前景化語言的翻譯是文學翻譯當中具有重要研究意義的話題。平行語言結構在小說主人公刻畫中起著重要作用,本文通過對莫言小說中此類語言的研究,從語音、詞匯、句法三個層面結合案例展開分析。研究表明,平行語言結構在實現主題意義、塑造人物形象、增加語篇美感等方面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翻譯過程中,譯者通常以異化為原則,多采用直譯、直譯加音譯的翻譯方法,盡可能地再現源文的前景化效果,使譯文讀者能夠更好體會翻譯文學帶來的新奇體驗,更好地感知和理解小說的主題意義,樹立小說主人公人物形象。葛浩文翻譯的莫言作品多采用異化的翻譯策略,盡力還原莫言文本中詞匯、句式、語音的平行。但是由于中英文化差異,也有部分譯文采用了英文讀者熟悉的表達方式。當然,先鋒小說中的前景化研究是一個復雜龐大的工程,遠非幾個例子就能窮盡。有關平行語言結構翻譯的研究,有待更多學者去實踐和探索,為前景化語言現象提供更多的有效翻譯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