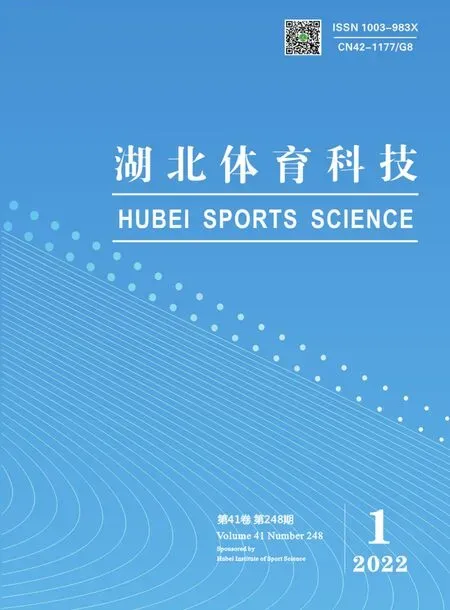競技體育“金牌”代價下運動員職業發展的現狀研究
周光輝
(青島市平度市實驗中學 體育教研室,山東 青島 266700)
從“東亞病夫”的紙被捅破,到“東方不亮西方亮”的戰術提出,面對競技體育金牌期待,中國隊不斷提交讓百姓滿意的答卷。 盡管“舉國體制”的金牌成本投入太高,但當觀眾親臨賽事現場或坐在電視機前, 他們的心理也會隨著競技場面跌宕起伏,在此情況中,甚至還出現了競技體育倫理問題,或稱競技體育異化,競技體育也為之付出了正常與非正常代價。 隨著競技體育投入與產出的不相適應, 人們開始回溯競技體育的政治化戰略選擇,審視“金牌邊際效益”,金牌的最大化并不代表競技體育的最優化, 體育強國的判斷標準也不是獎牌榜上的金牌數量。 我國競技體育發展的生命線可以是任何形狀,可以指向任何方向, 但要有根準繩衡量游戲人的活動及行為范圍。 然而對競技體育的代價分析又陷入糾纏不清的理論和現實問題。 本文首先對競技體育“金牌”代價進行梳理與發現,其次對競技體育運動員發展面臨困境進行闡釋與分析, 最后提出競技體育“金牌”代價下運動員發展救贖良方,以期待從代價根源入手,推動競技體育蓬勃發展。
1 競技體育“金牌”代價梳理
1.1 投入與產出不一的社會代價
不可否認, 在奧運會上獲得金牌是很榮耀、 很興奮的事情,對于振奮民族精神、增加我國作為體育大國乃至世界強國的自豪感,可謂意義重大。 不過,金牌是有成本的。 “投入與產出不一”是指競技體育人才培養投入與產出效益的不一,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資金投入與金牌價值產出的不一。 傳統計劃經濟框架下“舉國體制”競技體育金牌投入主要依賴國家資源以及納稅人的資金, 據悉現在中國各地少年體校的在校生約有20 萬人,從“少年體校”到運動員培養成的七、八年里,如果每人每年花費的培訓費用為2 萬元的話,那么20 萬人一年就要花費40 億元。對于奧運金牌的產出,2007 年《中國奧運金牌價值報告》計算出了10 枚奧運金牌的價值,第一位是男子110 m 欄冠軍劉翔商業價值為4.61 億元, 其他9 塊奧運金牌的價值總計8.94 億元,比起巨額投入,這點產出微不足道,技巧型的大量項目基本沒有商業價值,除去運動員應有分成,其余多成體育官員和教練集團的集體利益, 政府財政可以說是回報為零[1]。二是運動員期望投入與退役后現實生活產出的不一。 在尚未實行專業體校訓練體制形勢下,運動員從小進入當地業余體校邊學習邊訓練或全天候訓練,“只要刻苦訓練,將來拿世界冠軍,一生就會有個依靠”的想法成了訓練的出路,不計后果以及超負荷訓練, 使他們在享受鮮花和掌聲之后面臨年齡大、沒文化、就業難、傷病纏身以及缺少社會關愛等的現實困境。
1.2 壟斷與競爭不一的制度代價
“舉國體制”有著嚴重的政治化傾向,以國有方式盤踞了競技體育的主要資源,堵塞了商業體育的發達之路,體育產業的成長受到嚴重抑制。 排球、籃球、網球這些本來表演性很強的體育項目,其商業價值都未能充分開發;在“舉國體制”身側半官半商踽踽獨行的足球, 也只能在制度畸變中可悲地淪為談資笑料[2]。 在現行以行政性壟斷為主要壟斷形式的背景下,行政壟斷與市場競爭并存,“壟斷與競爭不一” 體現在兩個方面,1)資源配置不均下行政權威降低。 競技體育資源包括人力資源、物力資源、財力資源、信息資源以及法規政策資源,隨著體育產業化、職業化、市場化以及社會化發展,競技體育資源的稀缺性及競技體育資源與人們需求之間的差距逐漸拉大,競技體育是“原本該由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領域”,然而“國有”形式下,競技體育成績演變為官員升遷等的評判標準,出現競技體育公信度下降、“年齡門”“腐敗案”等不和諧現象;2)競技體育公平觀下的行政手段矛盾解決。 競技體育中的公平觀是指人們對于競技體育運動中公平問題的看法或認識,可以用“政府辦”來形容我國競技體育管理體制的行政特色。 當游戲化的競技體育被高度政治化, 使得政府在這一制度中占據絕對的主導地位, 在多元發展主體與多元利益并存的局面下,為達到博弈均衡,政府就需要消解阻力,如大量行政審批權被掌控。 由于政府的強勢操控,行政手段下有了“最終解釋權”。
1.3 預期與結果不一的價值代價
競技體育中,金牌是最好的褒獎,然而在金牌期待社會環境中,“情感經濟”“眼球經濟” 等的博弈使得競技體育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由于過度競爭、商業操縱、政治追求的膨脹,最終形成體育自身的異己力量。 這可以歸結為3 個方面:1)競技體育核心價值觀的異化。 現代競技體育的舉辦逐漸成為一個國家展示綜合實力的有力舞臺, 奧運會也漸成為展現民族精神的窗口,尤其是當奧運會各國獎牌排行榜數據被大肆播報,對比賽勝利的渴望及民族自豪感的滿足使得競技體育的結果和目的逐漸喪失其文化教育的本質, 淪為國家政治和商業的附庸, 組織和承辦競技體育比賽成為組織者攫取政治砝碼和經濟利益的共同模式;2)競技體育參與者的異化。 主要指參與者職業道德缺失, 即體育界中標榜職業道德卻一再做出一些有損體育精神的行為,如運動員資格作弊、裁判員執法不公、興奮劑和濫用藥物等;3)競技體育利益相關者關系的異化。 即指競技體育的經濟利益和社會知名度等使得人與體育間關系的失調,表現在3 個方面:1)競技體育的技戰術、組織管理和行為方式不斷被客體化,成為支配人的一種強制力,進而反過來支配人;2) 競技體育的參加者在高額懸賞的誘惑下, 在求職、 改變社會經濟地位, 或其他各種社會目的的驅使下進行的;3)競技體育不能直接與參與者的終身幸福相關聯,造成他們的精神上、軀體上、社會性上的不幸。
1.4 需求與滿足不一的人文代價
我國現行的競技體育發展以政府為主導地位, 將奧運會設置為競技體育的最高層次, 秉持著以專業體工隊長期集訓為主體的訓練體制以及以全運會為核心的競賽體制, 急功近利戰略化、 揠苗助長經常化等的弊端使得競技體育不得不為之付出相應的人文代價。 首先,運動員傷病問題。 長期的甚至過早的專業化訓練使得運動員傷病問題不容諱言。 目前,我國各級體工隊多采用“時間戰”和“消耗戰”的訓練形式,大負荷、高強度、長時間造成運動員多方面的損傷,尤其是青少年運動員,“更快、更高、更強”,一百多年前顧拜旦先生將這句話定為奧林匹克格言的時候, 恐怕不會想到若干年后的今天會有很多運動員希望再加上一條,更健康,也許不久前他們還是媒體爭相報道的體育明星,是深受對手尊敬和恐懼的場上霸主,但當傷痛來襲,有些運動員不得不在最后時刻退出比賽;其次,運動員退役后就業問題。 對于退役后運動員再就業問題可以說存在著三大因素的阻礙,一是政策因素,表現在就業保障不到位和保障力度相對薄弱兩個方面。 二是運動員自身因素,表現在文化素質低以及生存技能單一兩個方面。 對于運動員退役后生活問題,早有關于鄒春蘭、安琦等人的報道。 2019 年的退役運動員數據顯示, 正在就業的退役運動員只有16.56%,三分之一的人在待業中[3]。最后,運動員后備人才培養問題。一是現行運動員培養形式導致選拔困難。 二是學訓矛盾引發職業生涯憂慮。 三是選材機制不符合競技體育實際。
2 競技體育“金牌”代價下運動員發展困境分析
2.1 體育職業化矛盾與均衡的環境沖擊
2017 年國乒以非競技方式再次走紅, 自體育職業化改革開始,在受到推崇的同時也飽受爭論。 職業體育的賽事門票、廣告、轉播等運營手段后的商業利益追求與“專業體育”“舉國體制” 的金牌和成績以及體制內秩序感的競技追求之間的矛盾,昭示著劉國梁不是敗給了政治斗爭,而是體育的職業化[4]。作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中國足球職業化道路逐漸走向越職業越墮落的深淵,至今無法自拔。 中國籃球的職業化僅僅比足球職業化晚了一年,然其“職業”素養的建設卻并沒有擺脫所謂的“中國特色”,甚至媒體間出現“中國足球的今天就是中國籃球的明天”的斷言[5]。職業體育,歸根溯源就是把作為娛樂的體育比賽作為商品提供給觀眾, 球隊所有者和比賽主辦方從中獲取利益,職業運動員從中獲得報酬的經濟行為。 這個定義也清晰地闡明了職業體育的宗旨是利益至上, 而并非奧林匹克精神中推崇的更高、更快、更強,這也是奧運會曾經長期禁止職業體育進入的原因。 所以將職業體育和成績、錦標劃等號的認識原本就存在誤區,職業體育并不是為成績和錦標服務,成績和錦標只是職業體育發展到一定高度之后所帶來的附加效應[6]。 究竟是應該全面推行職業化體育,還是部分保留舉國體制,這是我國體育多年以來一直在爭論的話題。 不過,在這種無休止的爭論中,中國的競技體育卻在這兩種模式中“各得其所”——李娜式的成功和關天朗的橫空出世讓人不得不為職業體育歡呼,但跳水、體操和舉重的長盛不衰則依然是依靠舉國體制來保駕護航。
2.2 職業階段決策選擇的有限理性限制
競技體育具有“工具性”,通過某種手段達到最優利益或者成為他人的目標或工具,這主要表現在:1)競技體育作為人類實踐的對象,與其它體育主體相互聯結,使體育參與主體具備工具價值,并為此積極能動表現;2)競技體育權力空間、經濟空間、政治空間被拓展,開始出現商業化、市場化、職業化,致使最優利益被掌控或存在沖突,體育主體出現分離;3)競技體育最優利益被上升或放大至國家、民族層面,各類體育主體瓜分原本存在弊病的利益空間,為擁有各自“利益空間”,競技體育以及體育主體出現“異化”。 作為與其對立統一的價值理性,其關注點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終極意義和行動方向,代表的是對某一具體行為合理性的判斷和理性思考, 是對人性的思考[7]。 隨著科技與創新飛速發展,在把競技體育推向高潮的同時也把競技體育帶入與競技體育精神相悖的困境, 競技體育運動員既受到理性的驅使,也受到情感、價值偏向等非理性因素的影響,使得個人不具有完全理性而具有選擇理性,如對興奮劑的使用,完全理性的競技體育運動員不會使用興奮劑。 競技體育是不帶刀槍的戰爭, 通過某種大家共同認可的方式來決出勝負,盡管在輿論猛烈的批評聲中,運動員上綜藝是“不務正業”的說法尤為顯眼。 粉絲經濟時代,體育明星們也著手打造體育IP 的商業價值延續和其作為明星運動員的粉絲經濟效應, 當應對由于運動員非理性而帶來的惡果,“君要臣拿金牌,臣拿不到,只能請罪”成為了他們的選擇理性體現。
2.3 金牌邊際效益與成績交換帶來的不良結果
這里主要指出在運動員軍營化管理滋長惰性、 對運動員投資引發邊際效率以及成績交換代價之后顧之憂難以解決境況下運動員的努力熵及競技體育職業精神。 1)現行體制下一個優秀運動員需要經歷從少年業余體校到省隊甚至國家隊再到最后專業大約15~20 年的時間, 即人生1/4 的時間與外界隔絕,漫長、枯燥的軍營化生活使得運動員得不到外界反饋信息,滋長無謂惰性;2)《奧運爭光計劃》在2008 年奧運會達到頂峰,猶如達到增長極限,高年薪與高獎勵下,作為政治、民族意義砝碼的金牌“含金量”遞減;3)“看似是職業球員,但卻是把項目看成名譽、 金錢和生存方式”(郎平,2011), 這種情況下,運動員以成績換職后保障,現實卻“生活凄慘”。 在種種迎合而又抵抗情況下的效率,是一種低效率。2012 年奧運會中韓羽毛球“消極比賽”事件,最能發現運動員低效率的主要根源:其一,表面上奧運精神重在參與,可實際上,作為中國隊員,拿金牌已經被賦予了諸多意義。 首先是政治高度,拿了金牌,說明你為祖國、為人民、為黨爭得了榮譽;其次是政績工程,有多少領導、教練和相關人員也與金牌聯系在一起,輸不起;再次,是運動員個人的命運和前途,金牌意味著一切,第二或第三僅是證明參與比賽,而后會是另一翻待遇;最后,才是運動精神本身。 其二,運動員是理性的,總是按照制度規則或教練意圖作出行為,使自身的收益最大化,哪怕面臨交易,所以運動員的表現無可厚非,因為他們的終級目標是金牌。
3 競技體育“金牌”代價下運動員發展救贖良方
3.1 增殖剩余價值,磨滅“可賣品”標簽
在我國運動員體制下,每個運動員都是由國家出錢培養,當一名運動員在競技體育場上體現他的價值,發揮他的能量,才具備了商業價值,這樣一來,運動員也不再僅僅是顧拜旦意義上的奧運選手,他們開始被權利、商業所綁架。 從李娜的案例中能夠看到出路:由政府直接投資、經營運動員,并榨取運動員剩余價值的模式早該成為過去式[8]。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中指出了剩余價值的另一種含義,即“物品經利用后所剩的價值”。 運動員在被“利用”期間,“非賣”的標簽不可信,既然是物品,就有保質期,就連姚明從“非賣品”變為“可賣品”也在情理之中[9]。 要磨滅“可賣品”的標簽,有力的方式便是增殖運動員剩余價值,可通過以下3 種途徑:1)價值形成過程:運動員形成基于勝任力的競技體育人力資本過程, 包括: ①社會動機——為國爭光、為民謀福,內驅力——明確運動員意義遠超一個稱號。②特質——運動員個體特色,如責任感、親和力等。③自我形象——社會角色和自我認知, 還包括內隱成分如熱情。 ④技能——與專業相關的理論、 技術與實踐能力。 ⑤知識——如何使用、發現,而不是注重知識容量;2)價值創造過程:競技體育主體創造基于四象限的體育決策過程,包括高成本且高效益(競技體育體制改革)、低成本且高效益(“三顧茅廬”式賢能任用)、低成本且低效益(興奮劑“作惡”)、高成本且低效益(監管真空陷阱);3)價值增殖過程:運動員產出基于二次創作的無形資產過程,包括自我成長如“洪荒少女”、自我表達如玩轉“粉絲經濟”、自我延伸如運動員無形資產歸屬問題研究、自我超越如“姚明時代”。
3.2 構筑精神體系,消逝“行貨感”流弊
NBA 最喜歡說的一句話就是“Business is business”(在商言商),所以黑紙白字談錢并不低俗,恰恰反倒是種職業的表現。 而我國的職業聯賽由于不夠“職業”,所以人們天天嘴上喊著渴望職業精神,但恰恰遇到事情又最缺乏職業精神[10]。 與在商言商非“人情”主宰的制度體系相比,在中國要做點事情似乎很難,處處要照顧所謂的“中國式情誼”,上至政府下至運動員,“人情化”主宰和“在商言商”體制都能使運動員陷入兩難境地,尤其在“自用價值”不足的情況下不得不經歷“行貨體驗”。 2016 年金球獎揭曉,人民日報指出“年輕球員要學習C羅的職業精神”,競技體育要職業化,運動員職業精神的培養是繞不開的話題[11]。 認為培養運動員職業精神,首先要構筑起競技體育“金字塔”型職業精神體系,即目標層:奧林匹克精神;核心層:競技精神;基礎層:職業精神、民族精神、團隊精神。 1)明確運動員職業定位。 要明確賽場運動員對于“創造優異成績和奪取比賽優勝”的“牛鼻子”作用,且具有自身當前角色對于公眾人物形象塑造影響力的自覺意識;2)實施“新養狼計劃”之“強獅計劃”。 “走出去,請進來”的“養狼計劃”關鍵點在培養對手成“狼”。 而同樣秉持“走出去,請進來”的“新養狼計劃”即鼓勵國內運動員參與國際賽事,引入國際職業賽事,關鍵點在于培養自己成“狼”,成為“文明的獅子”;3)規避“消極應戰”。 對勝利及賽后豐厚獎勵的渴望而默許運動員服用違禁藥品是最好的闡釋,要避免運動員“君要臣拿金牌”式的被動行為,另外,建立《運動隊官員監督管理條例》,防止政府保護下的“尋租行為”。
3.3 關注角色倫理,避免“乞討門”事件
在體育史上,競技體育運動員似乎都要經歷“從朝圣者到觀光客”的身份轉變,然而在對奧林匹克競技與奧林匹克精神追求的進程里, 競技體育場上存在著道德主義與功利主義的均衡博弈。 “中國女排11 連勝”熱背后引發出關于薪資待遇的“冷”思考:郎平年薪200 萬人民幣,張常寧年薪約50 萬左右;男足艾克森稅后年薪折合人民幣約8 000 萬,國內球員任航年薪達1 580 萬;男籃易建聯年薪為2 500 萬,郭艾倫350萬[12]……可以說奧林匹克陷入了現代性倫理困境:奧運目標和商業目標究竟誰給誰讓位? 運動員究竟該追求自我超越還是關注經濟利益? 現實情況里有關“奧運冠軍近況悲慘”的實例仍可列舉,大牌選手的退役有時是策略性行為,更多普通選手的退役則是不得不為之的職業選擇。 “如果你未曾走上過金字塔的頂端,那么你連退不退役,都不會有多少人關注,更別說退役后何去何從了。 ”面對退役后的角色轉換,運動員更需要的是一種身份,在角色與人的真我相背離的矛盾下,有必要關注“運動員薪水應該用在哪里”的有關問題:1)供給端:重組退役運動員補償尺度。 需要對運動員該得的保障和政府應盡的義務間做出界定,明確退役運動員的保障責任和邊界;2)需求端:做好需求管控,根據需求的生命周期,繪制時間軸式“路線圖”,將需求與優勢相結合,實施戰略性管控模式,構建“雙邊生態”;3)科研端:打造體育經紀人的人才供應鏈條。 首先,創新體育經紀人人才供應思維,如粉絲人力資本思維、人才社會化與社區化思維。其次,關注人的潛能,識別高潛質人才。優秀人才需要引和挖,而不是坐等其上門求職。 再次,做好體育經紀人的二次開發與能力升級。 即不是在任用后就急于讓他搞業務,而是要對其進行二次人力開發,要他真正去理解產業和項目,提高認知。 最后,重視體育經紀人的退出管理。
4 結語
競技體育“金牌”追求下,運動員逐步陷入“專業的陷阱”,且在體育環境大好形勢下, 運動員尚未形成與體育大國向體育強國邁進進程中相匹配的職業精神。 要明確金牌是手段,而不是目標。 沒有代價就沒有進步,抑制非體育觀念,弘揚奧林匹克體育精神是當務之急。 要把握運動員“迎合”與“抵抗”不一的效率代價根源,消除張尚武式“為國爭光”隱憂,填補運動員職業化漏洞,抖擻運動員職業精神,把榮耀寫在共和國的國旗上。
——評《休閑體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