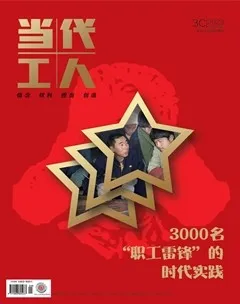何處少年水流東
我第一次真正接觸炸藥,或者說接觸真正的炸藥,不到15歲。
在老家峽河鄉(xiāng),第一條通村公路修于1963年,如今擺在眼前的,卻是一條蜿蜒九曲的泥巴路。由峽河鄉(xiāng)到最頂頭的雙峰村,有25里。這25里路,說通也通,說不通也不通,峽河山狹水猛,年年夏秋發(fā)大水,水對公路有仇,沖了修,修了毀,你死我活。鄉(xiāng)里的主要業(yè)余生活就變成了修地、修路。
鄉(xiāng)書記說,這一回,一定要把路修好了。
炸藥在那時還沒成為管控物資,可以隨便買賣和使用。夏天時,大人提了裝炸藥的尿壺下到黑龍灣炸魚,轟地一炮下來,能炸百十斤鱸魚。
隨便是隨便,但并不是免費的。除了到供銷社購買,鄉(xiāng)里大部分人會自制炸藥。修房基、開山取石、移除礙事的路障、平整地坎,甚至劈開某棵大樹,都要用。炸藥制造起來也容易,像做一鍋玉米粥似的,鐵鍋下架起熊熊柴火,鍋里倒入硝銨、松樹鋸末、洗衣粉……成分不一而足。翻炒、融化、冷卻,就成了。如果爆破力不夠,再加入棉花燃過的純灰,但這東西太金貴,峽河不產(chǎn)棉花,誰也舍不得把棉褲扒了燒成灰,就用一種茍木的炭粉代替,茍樹也比其他樹種金貴得多。
就連幾歲的孩子都會造土炸藥包:火塘里取一塊通紅的炭,放在一塊平面石頭上,上面蒙一小片舊棉花,蓋一層細土,一錘砸下去,啪的一聲,火花四濺,開襠褲再添一窩小窟窿,挨爹娘一頓好揍。
修路需要大量炸藥,鄉(xiāng)里窮,沒辦法,只能購買一半、自制一半。土方用自炒的炸藥,石方用從供銷社購買的炸藥,有些軟硬不吃的沙石方就用二合一的摻和品。路修到后來,財力實在無力支撐,就全靠自制。一片破舊牛圈里架起三口大鐵鍋,整天鐵鏟叮當,煙氣騰騰,嗆得牛們站在半坡上,不敢回家。
我跟著生產(chǎn)隊的大人一起修路。我們生產(chǎn)隊運氣不好,分到的路段全是石方。那地段叫大石幢,剛開始,誰也沒把這塊石頭當回事,10斤炸藥傾堆在石頭上,引雷管導火索,轟的一聲響,大家興奮地趕過來,一看,石頭完好,像什么也沒有發(fā)生過。
可能是炸藥太少了。再領來足足50斤,又轟的一聲,炮聲傳到10里外,近處人家的檐瓦落下一溜,山雀們?nèi)紗×寺暋J^還照樣,絲毫無損。
大伙兒無計,晚上開會商量破解辦法。最后,我一位表叔說,倒有個辦法,只怕花錢。生產(chǎn)隊隊長說不怕花錢。表叔又說,他打了半輩子獵,會秘制炸藥,他造出的炸藥包在肉里,指丁大一點兒就威力驚人。
第二天,表叔的炸藥制出來了,看著像一袋捂了的黃米面。轟的一聲,石頭裂成了八瓣。
路打通的第二年,表叔死了,查不出來得的是什么病,滿身青一塊紫一塊,大概是過敏造成的。表叔秘而不宣的炸藥秘方,到底使用了什么特殊成分,再沒人知道了。
1999年,我在礦山打工。
在礦山,人和錢都不算什么,炸藥才是老大。那一米一米巷道,一斗一斗礦石,一坨一坨黃金,一卡車一卡車鋁、鉬、鐵、銅錠……都是炸藥轟出來的。現(xiàn)代礦業(yè)生產(chǎn),炸藥才是真正的第一生產(chǎn)力。
我打工的第一站,是河南三門峽靈寶秦嶺金礦老鴰岔。
老家距小秦嶺并不遠,所以有去秦嶺礦山打工的傳統(tǒng)。20世紀80年代起,那里就成為家鄉(xiāng)人民的“臨時銀行”,日子過不下去了,去取就是。取多取少,看本事和運氣。有人用力氣取,有人用技術取,有人用命取,這里面有說不盡的故事。
開始時,我啥也不會,混在一幫人里拉車。兩輪的加重架子車,鋼圈部分加焊了鋼筋,能承重一兩噸,一趟一趟把爆破工爆下來的礦石或毛石拉出洞。我們叫作渣工,最苦,錢也最少。沒啥技術要求,這行當最不缺工人。
負責爆破掘進的師傅基本不和我們打交道,他們下班,我們上班。他們有獨立的工棚、獨立的灶,廚房倒出的垃圾里總有魚頭雞骨。
巷道爆破掘進使用的炸藥,叫銨梯2號巖石粉狀炸藥。我當時想,為啥用2號,難道1號3號不行?后來自己做了爆破工,在培訓班學習過才知道,1號3號還真不行。對付這種中硬度的巖石,只有2號最合適。
真正領教到銨梯炸藥的厲害,是在兩個月后。
那一天,工作面渣出到一半,出現(xiàn)了一塊大石頭,不下500斤。這種情況常常出現(xiàn),是掘進的巖層中出現(xiàn)了突然的斷層,沒有被炸碎。錘砸、釬撬,用盡了力氣,都沒辦法讓它碎開或裝上車廂。工作面不騰開,接下來的風鉆作業(yè)就沒辦法開展。巷道已經(jīng)掘進到了5000米,空氣越來越少,地熱越來越重。大家流著汗,已精疲力竭,商量怎么辦。
小四川說,用炮炸。干出渣這行已七八年,小四川最有經(jīng)驗。他是我們的班長,每月多300元領班工資,也就最有話語權。我說最好還是請示一下,小四川說他沒這個閑力氣。閑力氣我也沒有,出去來回近萬米。
從岔道里拿過來一包炸藥,共20節(jié),像20支火腿腸。把3節(jié)炸藥管撕碎了,傾倒在石塊上。微黃、干凈、新鮮,有一股淡香。這是我從沒見過的高威力炸藥。我來點火,他們4人撒開腿往遠處跑。洞道筆直逼仄,伸向不見盡頭的地方,像極了電影里的墓道。我們?nèi)缫蝗罕I墓賊,緊張慌忙。等他們跑得頭燈只剩下4顆小星星,我開始點火。這里缺氧,我把氣門調(diào)到最大,打火機哧的一聲躥出一股火苗,導火索又躥出一股火花,一尺多高,把洞壁照得徹亮。
我拔腿就跑,洞壁唰唰往身后退。咚的一聲巨響,一股力量從身后推過來,那力量實在太快,我的礦帽被推掉在地,礦燈摔滅了。那力量越過了我,一直向前推,把洞壁上的風筒扯得嘩嘩響。我耳朵里只有一股聲音,細細綿長又急迫,像秋后垂死的蟬叫。
銨梯巖石炸藥適用于中硬度巖石的爆破作業(yè),但在潮濕的礦洞環(huán)境中容易結塊失效,在有水條件下的爆破效果不理想,2000年前后被淘汰出局了。因它對外界敏感度不高,在殘炮的處理和裝填操作中,銨梯巖石炸藥減少了無數(shù)事故,它至今令那一代爆破人懷念。
時間到了2005年,我已是一位技術精純的爆破工了,走南闖北,腳踩無數(shù)山頭。經(jīng)手使用的炸藥,大概要用火車皮來計算。
隨時間推移,作業(yè)條件、效果等要求的變化,炸藥的品類性質(zhì)也在發(fā)展、提升。此時礦山爆破廣泛使用的已是乳化炸藥,尤其對付爆破掘進這行,而這行最難的,是打天井。所謂天井,就是從山體深處向上的、通天的井,用作分層巷道連通或向地面排煙通氣。也有從地面向下鑿進的,但那太慢、太耗力。這些井50米、80米、幾百米高度不等。
包頭的春天來得特別慢,特別晚,老家陜南已是鶯飛草長,這里還是一片寒徹,廣野千里,蒼黃枯萎。春天像一位遲到的學生,遲疑著躲在門外邊,探頭探腦不敢往教室進。
那天我和強子一班。他本來在另一組,他的伙伴病了,感冒發(fā)燒好幾天,害得他耽誤了好幾天,少掙不少錢。他女兒上大學,每天都要花錢,不拼命不行。而我的搭檔正好去了包頭。強子算我半個師傅,我在高中打籃球時他就上山了,但技術始終不怎么長進。干這一行也是需要天分的,天分包括對巖石的認識,對炸藥爆破力的把握,炮位的合理布局以及填充炸藥的微妙深淺與多少等。
天井已經(jīng)打到了70米深,這是導爆引線告訴我的。100米整盤的導爆引線,平巷上只余30米了。每爆一茬兒炮,索繩向上拽兩米。天井80度向上,其實和90度垂直沒什么區(qū)別。站在工作面的鐵梯上向里看,有些頭暈。一口痰,能直接落在下面的平巷上。平巷不時有人經(jīng)過,像沒有長大的小人。鉆沒開時,他們喜歡向上看,看見兩個忙碌的人,如樹上摘果的猴子,說一句“媽呀”,我們聽得很清。
我操作風鉆,強子幫襯。石頭異常堅硬,大概快接近地表了。要在碗口大的面積內(nèi)打出7個4厘米大小的掏心孔,得非常用心。釬桿轉動起來,鉆頭在巖石上高速撞擊,火花四濺,漸漸進入。我把風鉆功速開到三擋,釬桿舊了,有些彎曲,它在空中繞出一個個飛轉的圓圈。我想起《七劍下天山》里對楚召南的一句描寫:“連人帶劍舞成一團白光。”我憑著手感,努力讓釬桿與標桿保持平行等距,保證孔位的質(zhì)量。
我們從早上8點一直工作到下午6點,掌子面上打出了28個深孔,掏心部位的炮孔像一朵摳去了蓮子卻依然精美的蓮蓬。強子和我的衣服都被汗?jié)裢噶耍恢睗竦阶顑?nèi)層的褲頭。他時不時沖我一笑,露一口白牙。
裝填了整整一箱炸藥,24公斤。擰了起爆器,我們躲在內(nèi)巷里數(shù)炮聲。這是慣用的程序,炮聲夠了,爆破就成功了。我聽到轟的一聲又一聲,再緊密的一串,我聽見石頭大水一樣不斷落下來,沒完沒了,遠超往期的量。
“透了。”我拉住強子往出沖。但是晚了,巷道被落下來的石塊堵死了。打透的位置一定在山體的某個松軟部位,那里有無盡的石頭垮塌。
炮煙像一床被子一樣裹住了我們的呼吸。我聞到了深烈的硫黃和硝銨的味道,淡淡的松香的味道,后來,什么味道也沒有了。
醒過來的時候,正是正午。天空藍得沒有一絲云彩。北國的春天到底還是來了,吹過來的風,有一股牛羊的味道、戈壁草芽的味道,還有歸化的南風的味道。強子四仰八叉地躺在我身邊的礦渣上,他還沒有醒過來,眼角流著一片濕漬。礦山的慣用方法,被炮煙熏了的人,不能放屋里,要放渣坡上讓冷風吹醒。
我隱隱聽見工頭和一幫人說話:“這倆狗日的,也是命大,虧是乳化炸藥,換成別的梯恩梯或銨梯,可能就沒救了。”
工棚那邊飄過來一支歌,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好聽極了:
青春要是過去
何處你找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