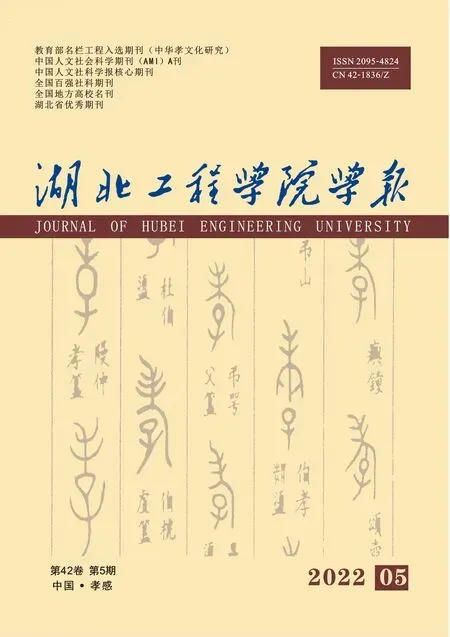朱子孝論探微
余 光
(華僑大學 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福建 廈門 361021)
“孝”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面向。朱子是宋明理學的集大成者,其孝論淵源于孔孟,承接自二程,既體現了先秦儒學重視人倫日用的現實色彩,也彰顯了宋明理學視域下的形上超越性。近年來,關于朱子“孝”主題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使得朱子孝論得以細致呈現。但是學界并沒有完整的去探討朱子孝論的多種維度,涉及到心性之孝的討論也不夠精深。鑒于此,本文嘗試深入挖掘朱子文本,把朱子孝論這個思想案例置于理氣、心性與工夫這三個大框架中逐一分疏,并重點闡明孝的心性意涵,以此呈現朱子孝論之全貌,從而更加準確地把握朱子孝論的精神實質。
一、理氣合一:孝的根原來處
關于“理”,朱子指出:“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1](6冊,512)他認為“理”的主要內涵可以概括為“所以然”與“所當然”,“所以然”即自然哲學范疇,可以理解為“自然之理”以及事物背后的根本原理;“所當然”即倫理哲學范疇,可以理解為“道德之理”也即人類社會的道德規范。在朱子看來,“所以然”與“所當然”是存在與價值的統一,自然界與人倫界相互貫通,兩個世界并非斷然割裂。
就“所當然”的人倫世界而言,倫理法則都是對天理的分殊,朱子說:“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為君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2]487天地之間只有一個“理”,“理”是天地萬物共有之理,“仁敬孝慈”等人倫道德被天理所先驗含攝,都是分殊了天理以后而形成的。所以“孝”的根源在于“理”,由“理”到“孝”是“理一分殊”的運化過程。進一步,朱子指出并不是有了君臣父子之后才有“忠”“孝”之理,他強調:“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無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卻旋將道理入在里面!”[2]2971也就是說,人倫道德根源于天理,是天理在人類社會的體現,而天理則先于倫理關系而存在,這就強調了理實體的絕對性、永恒性與超越性。
另外,“孝”與“氣”之間的關系也不容忽視。
“氣”是構成萬事萬物的物質材料,是“理”“掛搭”的載體,理氣相合而派生出自然事物與倫理道德。朱子說:“蓋氣則能凝結造作,理卻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2]4所以盡管理是“生物之本”,是氣化萬物的所以然者,但它自身只是一個“潔凈空闊”的本體,并不能單獨生成萬物。而氣則是“生物之具”,是理發用流行的動因,具有化生萬物的現實功用。所以只有依靠有作為之“氣”的交感化生的活動,才能使“孝之理”在人類社會發用流行,從而進一步下落到個體心性。可見,朱子實則是以理氣結構來探討孝的根源,“二者相合生成世間萬事萬物并掌控著其運行秩序。人及人倫體系的生成建構自然也是如此。”[3]82
因此,朱子以天理為本源,認為人類社會的倫理道德都是由理氣相合而產生,其本質為“分殊之理”。就“孝”而言,“孝”指“孝之理”(1)“孝之理”除了指此處先天的“分殊之理”外,還可以指后天的侍奉父母的道理準則,如“德是自家有所得處在這里。且如事親孝,則孝之理得;事兄弟,則弟之理得,所謂在這里,但得有淺深。”(《朱子語類》第三冊,第1057頁。),為“天理”之分殊,是“理”在父子關系上的發用流行。朱子一再強調要從大本大根上去尋求孝的終極根源,“如論孝,須窮個孝根原來處”[2]3435,“源頭便是那天之明命”[2]1634。他從理氣二元結構來解釋孝的來源,使孝從經驗性的倫理道德一躍而為先驗性的分殊之理,從而使孝具備了本體宇宙論色彩下的形上性與正當性。
不過,孝作為天理之分殊,雖然具有形上性,但終究不是形上本體,能作為本體的只能是第一性的天理。這就顯然不同于“孝本論”,“孝本論”強調“孝”的本根性,如《孝經》認為:“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4]28這是說,“孝”統攝了天地人三才之道,它既是自然世界的流行法則,也是人倫世界的道德根基。所以《孝經》作者認為“孝”不僅是人倫道德的根本,也是宇宙的大本大源。而朱子則質疑這一觀點,他甚至還刪改文字,作《孝經刊誤》,其根本原因在于朱子哲學屬于理學色彩下的“理本論”,所以盡管他賦予了孝以形上性,但他始終認為形上本體只能是“理”而非“孝”。
二、心統性情:孝的心性結構
朱子的“中和新說”是他成熟時期的心性論,體現為心性情的三分架構,其基本內容是“心統性情”“性體情用”“性發為情”。在心性方面,朱子孝論涉及到孝在心、性、情這三個層面的不同面向,即“孝心”“孝德”以及“孝情”。
就“性”而言,朱子一方面強調:“性中只有仁義禮智。”[2]113一方面又說:“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1](23冊,2778)這是說,若泛而言之,性中包含眾多德性。就大目而言,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德,此四者是性的基本內容和本質規定。另外,由于“仁包四德”,所以“仁義禮智”四德又可被“仁”所統攝,此仁為“專言之仁”,即“心之德”。進一步,性理的集中體現其實也是仁性,“蓋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2]566-567。不過朱子又說:“仁者,本心之全德。”[2]740仁的大目雖然只包括四德,但仁作為德性之全體,其實也包含了其他德目,這些德目并非本身就是仁性,而是被仁性所統攝的分殊之德。所以仁義禮智乃至孝弟忠信等具體德目其實都被仁性所統攝,并且是一種分殊之德。就“孝德”而言,朱子強調:“孝弟即仁之屬。”[2]580孝德首先是包含在仁性中的具體德目,但孝德并非仁性,只是被仁性所統攝。[5]46結合上文,“孝之理”作為“分殊之理”,由天道下貫而來,賦予人便構成了心中的“孝德”,即“德者,得之于心,如得這孝之德在自家心里。”[2](2)此處的“孝德”是指人先天稟賦的德性。另外“孝德”還可以指后天的道德品性,如“如事親時自無不孝,方是有孝之德”。(《朱子語類》第三冊,1056頁。)2084所以孝德在根本上根植于天命之性,并可稱之為“孝之性”。
由于“慈孝是天之所以與我者”[2]677,所以孝德先驗本然的就內在于心,此孝德和良知良能亦有關。孟子概括良知良能的內涵為:“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6]360朱子注為:“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6]360陳壁生由此指出:“親親出自良知”[7]300。“愛親”即“親親”,此處都指“孝德”。這是說,“孝德”是從良知良能那里產生的,良知良能“乃出于天,不系于人”[6]360,具有先驗性。所以“孝德”就是指人先驗本有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孝敬父母的知識與能力,是良知良能在父子關系上的發用流行。人有此孝德,就可以自然而然的行孝,即“孝弟者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也。”[1](6冊,613)“孝德”不僅是良知之發用,其實也是“明德”。朱子明確指出:“孝是明德。”[2]332“明德”即是心也是性(3)就明德為心而言,朱子說:“明德者,人之所得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四書章句集注》,第3頁)就明德為性而言,朱子說:“我之所得以為性者,便是明德。”(《朱子語類》第二冊,第389頁)。就性而言,他說:“人本來皆具此明德,德內便有此仁義禮智四者。”[2]321可見,“明德”有時也被朱子稱為仁性。所以“孝德”屬于“明德”,也即“仁性”。
值得注意的是,牟宗三先生批評朱子“只以仁義禮智等普遍之理為性,其余俱視為形而下之情”[8]322,從而“性中無孝弟”[8]321。牟先生認為朱子走的是性體情用的路子,性中只包括仁義禮智,從而性中無孝弟,這無疑是誤解了朱子。由上可知,朱子認為性作為德之源,雖然只以仁義禮智為本,但是其他德性也都被仁性所統攝。一切德目包括孝德都是天之所賦,人之所受,乃性分之所固有,仁體“為一切德之源而無一之能外”[8]322說的不只是明道,也適用于朱子。對朱子而言,性是萬理之總名,“性分之內,萬理皆備”[6]344。仁義禮智則是性所具萬理的四大綱要,“性是理之總名,仁義禮智皆性中一理之名”[2]114。所以“仁性”統攝“孝德”,“孝德”屬于“仁性”,且“仁性”為“孝德”之本。這也是朱子所謂的“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2]577,即未發之性體的角度。不過,朱子又引程子說:“性中只有個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2]577-578那么這是否意味著牟先生批評朱子“性中無孝弟”的說法是有道理的呢?其實不然。在這里,“曷嘗有孝悌來”指的是“孝情”而非“孝德”。進言之,先驗之“孝德”無疑是屬于“仁性”的,但是經驗之“孝情”卻不屬于“仁性”,而是“仁性”之發用。“仁性”的發用就涉及到了現實的情感層面。
就“情”而言,朱子說:“仁是愛之理,愛是仁之用。”[2]568此處“仁”指“偏言之仁”,為“愛之理”。“仁之體”是情感未發之際的性之本體,“仁之用”是情感已發之際的形下之情。就性情關系而言,“渾然天理”的仁性通過心的知覺作用,發用為外在的愛之情,其中就包括孝情。如他說:“仁是性,發出來是情,便是孝弟。”[2]579此處“孝弟”指“孝弟之情”,孝情作為一種經驗性的情感,其產生不能離開父子關系,“蓋有父子,則便自然有親。”[2]286并且父子關系為體,慈孝之情是用,“君臣、父子、國人是體;仁敬慈孝與信是用。”[2]125在父子關系中,心由物、事而動,仁性便發為孝情。其中仁為性、體;孝為情、用,即“仁是性,孝弟是用。用便是情,情是發出來底”[2]577,并且體與用之間是一種相即不離的關系。就“仁者,愛之理”而言,仁是愛之理,孝是愛之情。愛之理是孝之情發動的內在依據,孝之情是愛之理發用于外的源始體現。
值得注意的是,仁體不僅會發而為孝情,也會發用為其他情感,但是朱子認為相對于其他情感,孝之情最先發用,即“孝弟為仁之本”[2]576。他說:“如愛,便是仁之發,才發出這愛來時,便事事有:第一是愛親,其次愛兄弟,其次愛親戚,愛故舊,推而至于仁民,皆是從這物事發出來。”[2]3502孝情的先發性在朱子那里有著深刻的考量。從理氣發用的角度來看,孝具有源初性。他說:“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后及于仁民;又推其馀,然后及于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6]210祖先與后代都是一氣之流行,所以具有同構性,由此孝便具有了生成論上的優先性與源始性。在儒家看來,人一出生就擁有了一種親親的家族歸屬感,“‘親親’甚至都還不是一種德性,它比德性更基礎。”[9]236-237也正如此,孝就具有了其他情感所不具有的“親切”特征,“但孝弟至親切,所以行仁以此為本。如這水流來下面,做幾個塘子,須先從那第一個塘子過。那上面便是水源頭,上面更無水了。仁便是本。行仁須是從孝弟里面過,方始到那第二個第三個塘子。”[2]3502-3503朱子認為,儒家所謂的情感并非墨家那種均質無差別的兼愛,而是一種具有親疏遠近關系的仁愛。孝作為一種最親切的情感,是儒家愛有差等的一本論的體現。所以情感的發用首先是“孝之情”,表現為對父母的敬愛;其次發用為其他道德情感,表現為對天地萬物的仁愛。這就是“親親—仁民—愛物”的“差序格局”,此“自然之序”,實不容顛倒。
進言之,仁性在父子關系上的發用會產生孝情,在其他關系上的發用便能產生其他情感,這些情感其實都是“惻隱之心”的發用。朱子明確指出:“惻隱之心方是流行處,到得親親、仁民、愛物,方是成就處。”[2]2315“惻隱是仁之發”[2]3499,“惻隱之情”亦是仁性之發用,其發用過程貫穿于“親親—仁民—愛物”的全過程。不過“惻隱之情”作為一種對人與物的愛,范圍就不局限于親親了,而是由親親出發推擴到了萬事萬物。但若只是在親親層面,“惻隱之情”則體現為“孝情”。換言之,孝情屬于“惻隱之情”的具體化,是“惻隱之情”在父子關系上的顯現。朱子還用比喻來形象說明:“仁是根,惻隱是根上發出底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枝葉。”[2]3501由此也可看出,“孝情”的本質為“四端之情”而非“七情”。因為“四端”是道德情感,屬倫理之愛,“七情”是自然情感,屬心理之愛。由四端之惻隱而來的愛和七情之愛并不相同。孝情在本質上是一種最本源的倫理之愛,體現為子女對父母的道德情感而非自然情感,所以“孝情”為“四端之情”。朱子進一步指出:“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2]1577。情自性由心而發出,性本善,人之常情天然的就應該體現為一種好善惡惡的本善傾向。就孝情的發顯而言,其本應純善無惡,即“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6]335然而,普通人的情感容易受到心中氣稟的遮蔽,所以可能會出現不中節的情況。因此,為了克服“氣稟所拘”與“人欲所蔽”,朱子特別強調后天的禮樂教化與修養工夫對情感發而中節的規范。
由上可知,在已發之“情用”的角度,朱子認為孝指“孝情”,“孝情”為“仁性”之發用,并具有相對于其他情感的本源性。另外,由性到情的發用離不開心,就“心”而言,朱子其實也討論過孝與心之間的關系。他說:“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2]395心是“具眾理而應萬事”的存在,是承載性理與情感發用的場所,“心便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2]395。心的知覺作用決定了其可以認知“孝之理”,心的主宰作用決定了其可以完成仁性到孝情的進路。朱子進一步說:“德是有得于心,是未事親從兄時,已渾全是孝弟之心。”[2]1052“孝之理”賦予人便構成了心中的“孝德”,所以盡管人還沒有進行事親的后天實踐,但是心中依然先驗具備了上天所賦予的“孝德”。心稟此“孝德”而為“孝心”,人在“孝心”的主宰下,“孝情”呈現出一種自然而然的真誠狀態,即“‘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皆發于心德之自然。”[2]577在父母面前,子女之心處于一種“心肯意肯”的自覺自愿的狀態,孝情的流行則是仁性的一種不容已的發用體現。這并非由任何外在要求所強力為之,在一定程度上屬于自律道德。進一步,當主體將實踐范圍從父子關系推擴至其他倫理關系上時,“仁心”就不僅僅體現為“孝心”,還會體現為諸如“慈心”“忠心”等其他各種道德之心,這些具體之“心”都是“仁心”在不同倫理關系上的發用流行。
就父子關系而言,朱子說:“仁是理之在心者,孝弟是此心之發見者。”[2]580“仁心”是性理在人心中的運作,“孝”則是“仁心”在父子關系上的顯現。在仁性發為孝情的進程中,心自身亦會從寂然不動的本然狀態發展為感而遂通的發用狀態。朱子認為,此心之動其實也是“良心”之發用,“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于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6]292良心即仁心,但良心卻非孝心,良心之發用才是孝心。若認為良心是孝心,則容易混淆朱子與心學家之間的區別。比如在王陽明看來,良心即本心,心即理,孝心也即良心本心,“孝德”也即良知良能。而在朱子那里,“孝德”非良知良能,而是良知良能之發用,“孝心”也非“良心”,而是良心之發用。也正如此,朱子批評弟子“孝弟仁之本,是良心”[2]563的觀點,認為“不須如此說,只平穩就事上觀。”[2]563其中分歧的緣由在于,對陽明而言,心、性、理是本然合一的狀態,而朱子卻認為心性有別,不可直說合一(4)朱子有時也認為心與性可以合一,指出心與性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系,但那主要是指渾然天理的圣人,以及普通人先天的本然狀態或后天經過修養工夫后而達到的“心與理一”的境界。。他指出:“心與性自有分別。靈底是心,實底是性。靈便是那知覺底。如向父母則有那孝出來,向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2]395對朱子而言,心與性不可混淆。性是在心之理,是超越的形上之理以及先驗的道德本質。心則兼理氣,居于形上形下之間,具有主動性、靈明性,可以兼體用,統性情。就“孝”而言,“孝德”屬于仁性,“孝心”是指心,二者并不相同。另外,由于“孝心”的產生需要與具體的物、事相接,所以“孝心”其實也關聯著“孝情”。
因此,心作為一身之主宰,可以使本然之孝德發為外在之孝情,不過仁性到孝情的發用過程并非暢然無礙,因為孝心會受到氣稟與人欲的影響,從而可能難以產生純善之孝情,但這并不意味著孝心或孝德本身有任何缺損或喪失。朱子強調:“卻是后來人欲肆時,孝敬之心便失了。然而豈真失了?于靜處一思念道,我今日于父兄面上孝敬之心頗虧,則此本來底心便復了也。”[2]1312-1313孝心承載孝德,孝德先天就內在于心,并非一定要見于物、事才能產生。而后天的道德實踐則需要恢復本心中的明德,即復其本心。在這個過程中,人就能逐漸意識到自己先天稟受的孝之明德的存在,孝心也并不會因為物欲遮蔽而消失。若人能進一步主敬涵養,格物窮理,則依舊可以識得自家孝心與孝德,使得孝心達到渾然天理的狀態,從而使孝情發而中節,最終完成仁性到孝情的進路。
值得說明的是,雖然孝可以在心、性、情這三個層面分而言之,但是心性層面的孝,朱子經常是仁孝對舉。他說:“論性,則仁是孝弟之本。惟其有這仁,所以能孝弟。仁是根,孝弟是發出來底;仁是體,孝弟是用;仁是性,孝弟是仁里面事。”[2]3499這是說,仁為性,主靜,指“愛之理”,為體;孝為情,主動,為仁性之發用,為用。仁性與孝情是心性論中最重要的仁孝關系,也是孝在心性論中最重要的面向。盡管如此,心性層面的孝依然具有獨立于仁的內涵。總結來說,就性而言,孝指“孝德”,仁性統攝孝德;就情而言,孝指“孝情”,孝情為仁性之發用;就心而言,“孝”指“孝心”,“孝心”作為“仁心”之體現,不僅能知覺性理,也能完成仁性到孝情的發展過程。
三、仁義禮智:孝的實踐原則
盡管孝在心性層面具有如此精微的理論意涵,但是朱子認為孝最終還是要落實到現實生活中,以此成為具體的孝道行為,此即為工夫層面的孝。他說:“德者,得之于心,如得這孝之德在自家心里。行出來方見,這便是行。”[2]2084工夫層面的“孝”指“親親”,即“孝行”。朱子認為:“善事父母為孝”[6]48;204,他將“孝”定義為子女敬養父母的道德規范(5)在朱子看來,“孝”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孝”與“弟”相對應,即“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四書章句集注,第48頁》)。廣義的“孝”則將二者兼而言之,即“孝親敬長”之義。本文討論的“孝”主要是指廣義的“孝”。,這不僅包括對父母身體上的奉養,也包括對父母精神上的尊敬。
在行孝的過程中,朱子認為“行孝”是“行仁”的根本,“論行仁,則孝弟為仁之本”[2]577,行仁首先需要從行孝開始。不僅如此,他還進一步說:“只孝弟是行仁之本,義禮智之本皆在此:使其事親從兄得宜者,行義之本也;事親從兄有節文者,行禮之本也;知事親從兄之所以然者,智之本也。”[2]563在這里,行孝不僅是行仁之本,同時也是行義、行禮、行智之本,并且在實踐過程中,孝行其實也關聯著仁義禮智四德。如他說:“只是這一個物事,推于愛,則為仁;宜之,則為義;行之以遜,則為禮;知之,則為智。”[2]3503孝行在仁義禮智的道德規范下,會隨著不同情境而相應展現出仁愛、得宜、謙遜、明辨等不同特征,正如張立文先生所言:“仁義禮智信是一個統一的愛親的各個層面的施行和全過程。”[10]498以下主要探討孝行在仁義禮智規范下的不同展現。
就孝行與仁而言,朱子主要強調子女對父母的一種發自內心的愛。他說:“其慈,其孝,這便是仁”[2]3413。這種愛不僅指身體上的奉養,也包括精神上的尊敬,二者都統一于子女真誠的仁愛之心。在身體奉養方面,他說:“如‘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是不孝;到能昏定晨省,冬溫夏凊,可以為孝。”[2]321朱子指出子女要悉心侍奉父母,使父母一年四季保持身體安康。不過身體奉養只是最基本的層面,若只局限于身體奉養而無敬意,則為朱子所不許,“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6]56朱子強調尊敬父母比侍奉父母更為重要,這與孔子的“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6]55的孝道思想一脈相承。在敬重父母方面,朱子強調“三年無改”的重要性。他說:“才說‘三年無改’,便是這事有未是處了。若父之道已是,何用說無改,終身行之可也。”[2]626他認為如果父之道合理,則終身可以堅守,這是子女對父母敬意的體現。而此敬意也離不開內在的心理基礎。就孝行背后的心理基礎而言,朱子不僅強調敬,也強調孝心的真誠。他說:“如欲為孝,雖有七分孝,只中間有三分未盡,固是不實。雖有九分孝,一作弟。只略略有一分未盡,亦是不實。”[2]437他認為人要盡全力去實行孝道,并要達到一種真實無妄的仁心、誠心狀態。反之,“若外面假為孝之事,里面卻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2]1902朱子強調內心仁愛與真誠的目的是為了防患有“孝行”而無“孝心”的“舉孝廉,父別居”的假孝行為。
就孝行與義而言,朱子說:“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義。”[2]3413義是指子女只需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而無須孝敬他人的父母,孝道行為的對象只能是自家父母,而非他人父母。但若子女不孝敬自己的父母,反而去孝敬他人,這就是“悖德”,即“‘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2]563;[2]2608。儒家的愛是有差等的,親親之愛只能體現在自家父母身上,這是義的節制與界限含義的體現。但這并不意味著“仁”與“義”之間相互對立,或“仁者愛人”與“親親為大”之間存在矛盾。朱子一再強調“孝”的源始性,人要以孝為出發點,以父母為中心,將道德情感與道德行為推擴至萬事萬物,這是儒家一本論的體現,其中體現為一種邏輯上的先后序列。其次,朱子還指出:“義者,宜也,宜即義也;萬物各得其所,義之合也。”[2]2056義還可以指得宜、合宜。這是強調子女的孝道行為要合宜,而這就涉及到了孝行背后的一整套禮儀規范。
就孝行與禮而言,朱子說:“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7]51禮是天理在倫理關系上的體現。朱子指出:“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于禮而不茍,其尊親也至矣。”[6]55子女要終生以禮對待父母,可見禮儀規范在孝道行為中的重要性。因此,朱子作《朱子家禮》《儀禮經傳通解》等禮學文獻,將孝道教育和禮儀教化相結合,在理論上規定了很多具體可行的道德準則,從而將孝道思想平民化、通俗化,使得人人皆可行孝。比如在《朱子家禮》中,他規定了子女對父母的生活起居乃至生老病死的一系列禮儀規范。如父母生病時,朱子指出:“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游,舍置余事,專以迎醫、檢方、合藥為務。疾已,復初。”[1](7冊,883)子女在父母生病時應該悉心照料,而非撒手不管。在父母去世時,朱子強調喪禮的重要性,從喪服的選取、入殮的時間與地點以及最后的灰隔土葬法,朱子深刻詮釋了“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6]55;255的傳統儒家孝道的核心精神。此外,朱子還尤其強調祭禮的重要性,祠堂有著“報本返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1](7冊,875)的祭祀功能。子孫后輩在祠堂以“仁孝誠敬”之心祭祀先祖,以達至“祖考精神,便是吾之精神”[2]752的感通境界,從而將父母之孝推擴至祖先之孝,這是朱子代際傳承的家族觀念的體現,有利于塑造良好的家風族風。不過,盡管朱子規定了如此繁多的禮儀,但這些禮儀并非一種外在的強制規范,而是天理至善的體現。子女尊禮循禮,則是自家孝心的自然流露,即“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6]368
就孝行與智而言,朱子說:“若是知得親之當愛,兄之當敬,而不違其事之之道,這便是智。”[2]3503智是指蘊含在孝行中的理性原則,子女要認識到孝道背后的“所以然與所當然之理”,將明辨是非的理性能力納入孝行中,如此才可能做出合理的孝道行為,反之則可能淪為愚孝。如二十四孝中臥冰求鯉的王祥,其孝心雖感天動地,但卻是缺乏理智的愚孝行為,并不值得提倡。事實上,盡管在《朱子家禮》等文獻中,朱子對孝有著嚴密完備的規范,但其實也會體現出一種理性的權變觀念。他說:“經只是一個大綱,權是那精微曲折處。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是經常之道,如何動得!其間有該不盡處,須是用權。權即細密,非見理大段精審,不能識此。”[2]1204-1205他認為孝道中所蘊含的仁義禮智等道德規范不可更改,這是經;但是在具體情況中,子女可以做出合乎現實的孝行,這就是權。朱子強調在特殊時刻可以靈活變通,而非死守教條,這無疑具有非常理性且溫情的色彩。比如說,當父母有過錯的時候,子女就不應該盲目順從,而是要懂得權變,在必要時甚至還可以諫諍父母,“蓋父母有過,己所合諍,諍之亦是愛之所推。不成道我愛父母,姑從其令。”[2]3386智體現為一種權衡的“是非之心”,在大是大非面前,要勸諫父母歸于正途,這才是真正的孝,即“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6]85-86
大體而言,孝行關聯著的仁義禮智四德其實都可以被仁所統攝,即“義只是知事親如此孝,事長如此弟,禮亦是有事親事長之禮,知只是知得孝弟之道如此。然仁為心之德,則全得三者而有之。”[2]569-570由于“仁包四德”,所以其他德性都可被仁所統攝。因此朱子在一定意義上是“以仁論孝”,本質為“仁孝”,體現的是一種溫情的仁學色彩與豐厚的人文理性。總結來說,朱子一方面強調子女要盡孝,要將孝要做到極致,“如事君則推致其忠,事親則推致其孝,與人交則推致其信,皆事事上推致其極。”[2]1912-1913另一方面又指出有時候出現一些無傷大雅的孝行也無妨,“且如人孝,亦只是大綱說孝,謂有些小不孝處亦未妨。”[2]868這些孝行也并非禁錮人的枷鎖,而是人推行孝道、完善仁德的重要方式。子女在父母面前,心有所感,仁性就會發為孝情,若孝情能發而中節,則情感流露即為天理之流行,而無私欲之夾雜。由此,人就可以在自然本真的孝道行為中,識得自家先天本具的完備性理,體悟到生意流行的至善天理,從而進一步完成仁民愛物的道德實踐。
四、余 論
朱子孝論是其哲學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主要涉及理氣、心性與工夫這三個層面。他在理氣層面探討的是孝的來源問題,在心性層面探討的是孝在心性結構中的內涵問題,在工夫層面探討的是孝的實踐問題。關于孝在這幾個層面的不同面向,其實可以用“明德”的概念來加以貫穿,朱子說:“明德,是我得之于天,而方寸中光明底物事。統而言之,仁義禮智。以其發見而言之,如惻隱、羞惡之類;以其見于實用言之,如事親、從兄是也。”[2]331-332他認為,明德是指光明的本然之理,乃天賦人受。明德在心上的總體為仁義禮智之性,明德在心上的發見為四端之情,明德在現實生活中的實踐為具體的倫理行為。可見,“明德”既體現了“得之于天”的形上性,也體現了“發見”“實用”的形下性。就“孝”而言,“孝”作為“理”之分殊,賦予人便構成了心所固有的仁義禮智四德,其中仁性統攝孝德。在父母面前,子女之心因物、事而動,仁性就發而為孝情。當孝情進一步發展到具體的孝道行為,則是儒家形上到形下、超越到現實的最終完成。從理氣層面到工夫層面,主要是理發用為萬事萬物的過程;從工夫層面到理氣層面,主要是人體認天理的過程,人的心性則起到了貫通本體與工夫的作用。如此,朱子孝論體現了一種天命流行與下學上達的天人合一路徑,這是儒家內在而超越精神的深刻體現。
當然,朱子孝論并不是沒有缺陷的,比如父子地位的不平等以及對個體性的重視不足等等。所以有些學者認為朱子孝論具有階級性和愚民性,并進一步批評中國的孝道倫理與家庭倫理的種種弊端,其實這是對朱子以及儒家孝論的一種誤解。就朱子孝論而言,孝乃天之所賦,其根源純善無惡。但是由于在發用過程中受到“氣稟所拘”“人欲所蔽”,所以可能產生愚孝甚至不孝的情感與行為。不過人卻可以通過修養工夫,在孝道實踐中以仁義禮智四德要求自身,以達致“大孝”與“達孝”的境界,從而促進父子關系的和諧以及維護家庭生活的穩定。在朱子那里,他反復強調孝的重要性:“圣人教人,大概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2]159,“孝者,百行之源”[2]942。因此,在下一階段,我們可以繼續推進朱子孝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從而為即將“無家可歸”的現代人提供一種合乎道理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