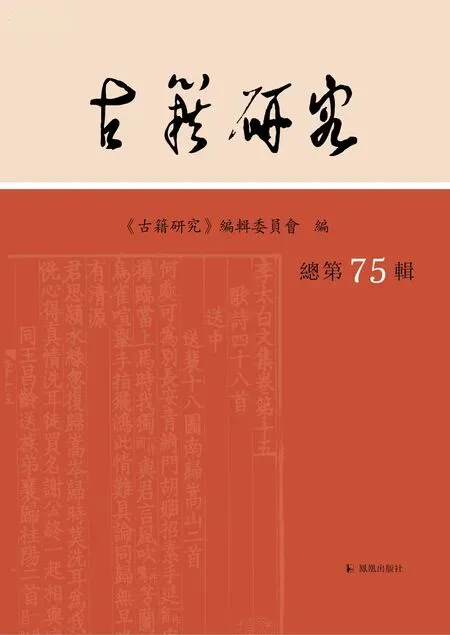跨出閨門:虞山詩派女詩人吳綃的成就與毀譽(yù)*
劉 一
關(guān)鍵詞:吳綃;虞山詩派;馮班;齊梁詩風(fēng);《嘯雪庵集》
明清之際嶄露頭角的女詩人雖多,但能與主流詩壇接觸者尚不像清中葉那樣常見。多數(shù)女性只能獨(dú)自吟詠,或在閨闈內(nèi)尋找知音。被隔離在主流詩壇之外,導(dǎo)致女詩人在創(chuàng)作方法上缺少自覺,多憑女性與生俱來的靈心鋭感來抒情達(dá)意,以天然、真率的風(fēng)格取勝。能通過取法前人來型塑個(gè)人風(fēng)格的女詩人已極稀少,能緊追一時(shí)一地詩學(xué)風(fēng)氣的女詩人更少。在這樣的背景下,虞山女詩人吳綃的藝術(shù)發(fā)展經(jīng)歷和生活經(jīng)驗(yàn)都顯得與衆(zhòng)不同:因生於華閥之家,歸於文學(xué)之苑,吳綃在詩學(xué)教育和社會(huì)交往方面都有較好機(jī)遇,這使她的才華和人格得到儘量的舒展:在藝術(shù)上,吳綃跟從馮班學(xué)詩,以女性身份實(shí)踐自古以香艶綺靡稱的齊梁、晚唐風(fēng)格;在生活中,她跨出閨闈,遊蹤萬里,以詩爲(wèi)媒,廣結(jié)賓朋。在吳綃的作品和當(dāng)時(shí)的詩文評(píng)中,她是一位德才兼?zhèn)涞呐裕谠娫捄鸵笆冯s談的傳聞逸事中,卻留下了她把持官府、言行放蕩的敘述,此間的矛盾引人深思。吳綃通過取法前人、追隨流派風(fēng)格而向更大的詩學(xué)傳統(tǒng)靠攏的做法,其形象在集部和説部中的離與合,都爲(wèi)我們討論明清之際女性詩歌的發(fā)展和傳播問題提供了難得的視角。
一、 進(jìn)入流派的女詩人
明末清初的虞山,文學(xué)風(fēng)氣濃厚。錢謙益主持的虞山詩派致力於清除明詩積弊,並在此基礎(chǔ)上探索詩歌發(fā)展的新方向,其麾下俊采星馳。馮班本是其中一員,但後期其詩學(xué)觀念與錢氏發(fā)生分歧:與錢謙益由中晚唐溝通宋、元的詩學(xué)路徑不同,馮班從晚唐溫、李綺艶一派入手,上溯齊梁詩風(fēng),下襲宋初昆體風(fēng)格,抱定齊梁一脈,非與齊梁詩風(fēng)相關(guān)者不學(xué)。馮氏這一支脈在當(dāng)時(shí)的虞山詩壇也産生了相當(dāng)?shù)挠绊懀冯S者衆(zhòng)多,甚至在女詩人中也得到了熱烈的呼應(yīng),吳綃就是一個(gè)典型。
吳綃字素公,一字冰仙,號(hào)片霞,長(zhǎng)洲人。約生於萬曆三十八年至萬曆四十二年(1610—1614)之間。據(jù)記載,吳綃幼研經(jīng)史,詩文書畫不教而能。天啓三年(1623),以十幾歲的年紀(jì)就能畫相思鳥之形,並配之以同題詠物七律。當(dāng)時(shí)即被稱爲(wèi)“香奩宋玉,金粉江淹”(1)(清)鄒漪:《吳冰仙詩集小引》,《嘯雪庵集》,李雷編:《清代閨閣詩集萃編》,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本文所引吳綃詩及部分序評(píng)皆出自此書,其出處直接標(biāo)注在正文中的引文後,下同。(第一冊(cè)第245頁)。吳綃17歲歸虞山許瑤,婚後夫妻間琴瑟和諧,頗極唱和之樂。在虞山,吳綃幸得馮班指授詩藝,追隨馮氏倡導(dǎo)的齊梁詩風(fēng),創(chuàng)作詠物、艶情之類風(fēng)格麗靡的詩歌,經(jīng)馮班揄揚(yáng)後,聲名鵲起。順治十五年(1658)前後,吳綃離開虞山,隨夫遠(yuǎn)宦河南,後又至蜀中。隨著眼界的開闊,她的詩歌題材也驟然拓寬,像男性詩人一樣記遊、贈(zèng)答、詠史、懷古無所不包,在原本綺靡細(xì)潤(rùn)的風(fēng)格之上增添了清雄氣概。約康熙三年(1664)許瑤身故,吳綃返回江南。因訟事以詩爲(wèi)媒,廣謁文人才子、官宦名流,後於康熙十年(1671)謝世,所刊有《嘯雪庵集》《嘯雪庵題詠》《嘯雪庵新集》《嘯雪庵題詠二集》《嘯雪庵詩餘》,選集《吳冰仙詩》等,是明清之際存世作品較多且風(fēng)格卓異的女詩人之一。
上文已提及,吳綃在詩學(xué)上最初受知於馮班。馮氏常飛翰指點(diǎn)吳綃的詩書藝術(shù),《與高陽夫人論書札》針對(duì)吳綃用筆的缺陷開出處方,提醒她“稍看季海,使筆在畫中、力出字外”(2)(清)馮班撰,(清)何焯評(píng),李鵬點(diǎn)校:《鈍吟雜録·附録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58頁。。《古今樂府論》從源頭講解古詩樂府發(fā)展史,言簡(jiǎn)意賅,並將其最擅長(zhǎng)的辨體意識(shí)金針度人。(3)據(jù)沈德潛《清詩別裁集》卷三一,“馮定遠(yuǎn)文集中有《與高陽夫人論古今樂府源流》,即謂素公也”。對(duì)吳綃的詩歌才能,馮班始終極力揄揚(yáng),在她故去後,馮氏作《高陽夫人挽詩》,其中有“欲定新詩品,應(yīng)同班婕妤”(4)(清)馮班:《鈍吟餘集》,清初毛氏汲古閣清康熙陸貽典等刻《鈍吟全集》本。之句。以首倡五言詩的女詩人班婕妤作比,可見對(duì)吳綃的推重。在馮班的援引下,吳綃逐漸進(jìn)入虞山詩壇主流文人交際圈,參與重要的詩學(xué)活動(dòng)。例如,順治十八年(1661)五月,錢謙益紅豆村莊的紅豆樹二十年復(fù)花,秋季結(jié)一子。爲(wèi)此,錢氏前後作絶句18首,並邀同人和之,邑中詩人馮班、錢曾、陸貽典、錢龍?zhí)琛?yán)熊、王應(yīng)奎等無不響應(yīng),不啻爲(wèi)虞山的一次文學(xué)盛會(huì)。吳綃也參與其中,一氣創(chuàng)作出十首絶句賡和,每首皆次錢氏原韻,展示出充沛的才情。
吳綃出色的藝術(shù)才華首先爲(wèi)她在虞山及周邊贏得聲名。吳中文人震驚於她的才華,贈(zèng)以才子之名,競(jìng)相抄録編選她的作品,加以傳播。早在順治十二年(1655),梁溪鄒漪即抄撮《吳冰仙詩》一卷編入《詩媛八名家集》,贊美吳綃“真可謂才子者也”,並稱“予選名媛詩,首推重冰仙”(第一冊(cè)第245頁)。順治十六年(1659),桐城陳焯不僅爲(wèi)《嘯雪庵詩集》作序,而且“全録其稿。擬取少作,選入明詩”(5)當(dāng)時(shí)陳焯的《宋元詩會(huì)》尚未完稿,但從句意可見,他已開始規(guī)劃將吳綃詩編入《明詩會(huì)》。。還發(fā)出“是寧區(qū)區(qū)才子足以盡夫人乎”(第一冊(cè)第148頁)的感嘆。從此,吳綃聲名日盛一日。順治十八年(1661),虞山詩壇巨擘錢謙益爲(wèi)吳綃作《許夫人詩序》。降及康熙九年(1670),吳偉業(yè)又爲(wèi)其作《小引》。至此,時(shí)稱“江左三大家”中的二位都肯定了吳綃的詩歌成就,有這樣名重一時(shí)的文壇泰斗揄揚(yáng),吳綃的名聲也隨之播向遠(yuǎn)方。
康熙十年(1671),吳綃和馮班相繼謝世。塵埃落定之後,馮班弟子嚴(yán)熊作《馮定遠(yuǎn)先生挽詞二十章》,其中第十二章聚焦的正是吳綃與馮班的這段詩歌因緣,詩云:“記曲旗亭更讓誰,金閨往往誦新詩。試吟明月空枝句,半是天才半是師。”自注:“吳夫人冰仙學(xué)詩於定翁,曾賦《梨花》詩云:‘露下有光翻見影,月明無色但空枝。’真名句也!”(6)(清)《嚴(yán)白雲(yún)詩集》卷七,《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0冊(cè),第65頁。後兩句在贊美吳綃脫俗的詩歌才華之外,更表彰出馮班對(duì)吳綃詩歌的影響和點(diǎn)化之功,其中透露的信息值得重視。近年來,針對(duì)吳綃及其詩詞藝術(shù)的研究不斷涌現(xiàn)(7)如熊曉曉《吳綃與〈贈(zèng)藥編〉研究》,浙江大學(xué),2012年碩士學(xué)位論文;蘇菁媛《一片琉璃照影空——吳綃〈嘯雪庵詞〉研究》,《臺(tái)中教育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8年,22(2)等。,但吳綃受地域詩風(fēng)影響而呈現(xiàn)出的流派風(fēng)格卻未得到條理化的呈現(xiàn)。與此同時(shí),吳綃作爲(wèi)一名女性詩人,如何像“才子”一樣作詩,融入男性主導(dǎo)的詩學(xué)傳統(tǒng),這些問題都未得到深入探究。
二、 吳綃詩歌的晚唐齊梁體風(fēng)格
《嘯雪庵集》初刊時(shí)僅三卷,依次爲(wèi)《嘯雪庵詩集》《嘯雪庵題詠》《嘯雪庵新集》。《新集》內(nèi)可考的創(chuàng)作時(shí)間最晚的作品是《雪窻》,題下注:“庚子小春鄜署作。”(第一冊(cè)第256頁)庚子小春即順治十七年(1660)十月。考慮到許瑤請(qǐng)陳焯、胡文學(xué)、李瀅、黃中瑄(8)黃中瑄小引篇末所題時(shí)間爲(wèi)“乙亥新秋”,誤。考陳焯、胡文學(xué)、李瀅三人爲(wèi)吳綃所作的序,文末均署“已亥”。又據(jù)序言內(nèi)容可知,陳焯等三人作序地點(diǎn)均在許瑤當(dāng)時(shí)外任的武安或周邊。考慮到黃中瑄引文中也有“予客武安,初晤蘭陵”等句,篇末又講明“題於平干古剎”,則可推知此篇引文應(yīng)與陳焯等人序一樣,是己亥年在武安當(dāng)?shù)兀瑧?yīng)許瑤邀約而作。大概因字形相近,誤將“己亥”書爲(wèi)“乙亥”。再者,己亥後三年,許瑤即謝世,黃中瑄不可能於乙亥年與瑤初會(huì)於武安。四人爲(wèi)《嘯雪庵集》作序、引,事均在順治十六年(1659),可知此時(shí)他或已開始爲(wèi)刊行做準(zhǔn)備。兩年之後,復(fù)請(qǐng)錢謙益作《許夫人詩序》,大約此時(shí)準(zhǔn)備工作已大致完畢。又考慮到王士祿康熙三年(1664)完成的《宮闈氏籍藝文考略》中已記載吳綃“所著有《嘯雪庵集》三卷”(9)(清)王士祿:《宮閨氏籍藝文考略》卷八,《藝文》,上海:上海雜志公司,1936年第1卷第6期,第6頁。,可推知,此三卷本最終的刊行年代應(yīng)該就在請(qǐng)錢謙益作序的順治十八年(1661)之後不久。三卷本中,卷三《嘯雪庵新集》收録的多是吳綃隨夫宦游幽冀時(shí)的作品。前兩卷,即《嘯雪庵詩集》《嘯雪庵題詠》收録的則是虞山時(shí)期的作品。在虞山,吳綃跟隨馮班學(xué)詩,自然受到馮氏所倡齊梁詩風(fēng)的熏陶,這種熏陶也切實(shí)地反映在她的早期創(chuàng)作之中。
馮班倡導(dǎo)的詩學(xué)路徑是從晚唐溫、李綺艶一派上溯齊梁,吳綃的創(chuàng)作恰恰呈現(xiàn)出鮮明的晚唐綺艶詩風(fēng),這一點(diǎn)當(dāng)時(shí)就有論者指出。比如,李瀅小序云:“夫人工詩,善屬文。五七言清麗芊綿,匠心獨(dú)造,奴視西昆諸體”(第一冊(cè)第151頁)。王士祿《宮闈氏籍藝文考略》引《神釋堂脞語》曰:“冰仙冶情雋筆,得之玉溪爲(wèi)多,樂府詩亦間師昌谷,仿其譎艶,緯以風(fēng)情。”(10)《宮閨氏籍藝文考略》卷八,第6頁。也點(diǎn)出了吳綃詩風(fēng)與李賀、李商隱的血脈聯(lián)繫。
吳綃對(duì)晚唐、齊梁詩風(fēng)的偏好是顯而易見的,研究者也都注意到了。但她是如何具體把握晚唐溫、李和齊梁詩風(fēng)內(nèi)涵的,這在她的創(chuàng)作中又以什麼樣的邏輯表現(xiàn)出來?這些問題還沒有得到細(xì)緻的考察。馮班擅長(zhǎng)辨體之學(xué),其詩論中最具價(jià)值的是詩體論。在接受齊梁、晚唐詩風(fēng)時(shí),他也采取了先判定典型體制,然後從體制入手學(xué)習(xí)的策略,這有力避免了浮於題材或辭藻的淺層模仿。作爲(wèi)馮班得意弟子,吳綃顯然對(duì)馮班的辨體之學(xué)有所領(lǐng)會(huì),她師法齊梁、晚唐詩風(fēng),主要是從幾種典型體式入手的,以下分述之。
首先是詠物七律。馮班與吳綃以七律題寫的常是晚唐溫李派詩人和齊梁宮體詩人熱衷吟詠的春風(fēng)、春墀、梅花、牡丹、熏籠、燈花、帷帳、歌娘、伎女、纖手、鞋履、綉衫等或纖微或綺艶之物。比如吳綃的《戲和詠手》:“春蔥露洗玉摻摻,一掬清波削月兼。按管參差調(diào)鳳翼,鳴箏出沒弄瓊尖。因憐花好鬟頻整,爲(wèi)寄魚封綉懶拈。閑摘海棠看又拈,巧侵蝶粉若爲(wèi)嫌。”(第一冊(cè)第157頁)被吟詠的手不僅形態(tài)優(yōu)美,而且靈巧好動(dòng),它時(shí)而掬水弄月,時(shí)而按管調(diào)箏,時(shí)而整鬟拈綉,時(shí)而摘花侵蝶,做的都是青年女性熱衷的事。吳綃的女性身份容易使此詩看起來像是對(duì)她閨中生活場(chǎng)景的一次集中展示,事實(shí)卻不一定如此,這首詩更有可能來自對(duì)晚唐的齊梁式綺艶詩歌的刻意仿效。
《詠手》這個(gè)題目,晚唐之前未見專門吟詠,在韓偓、秦韜玉、趙光遠(yuǎn)等人手中卻集中涌現(xiàn)出數(shù)首七律,是晚唐綺艶詩風(fēng)的一種典型。韓偓等人的七律《詠手》寫法相近,即首句寫手的形態(tài),後七句借描寫手的動(dòng)作生發(fā)出一幕幕香艶的女性生活畫面。以秦韜玉《詠手》爲(wèi)例:“一雙十指玉纖纖,不是風(fēng)流物不拈。鸞鏡巧梳勻翠黛,畫樓閑望擘珠簾。金杯有喜輕輕點(diǎn),銀鴨無香旋旋添。因把剪刀嫌道冷,泥人呵了弄人髯。”(11)(清)彭定求編:《全唐詩》卷六百七十,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7662—7663頁。以鑒賞的目光看待女性,描繪種種甜美輕鬆的閨閣生活場(chǎng)景,自己的真情實(shí)感卻付之闕如。兩相對(duì)照之下,可以看出,吳綃的《戲和詠手》在構(gòu)思命意和賦寫技法上都與秦韜玉詩不差毫分,甚至兩詩的韻腳也相同。將她這首《戲和詠手》視爲(wèi)對(duì)秦韜玉《詠手》的一次追和也不爲(wèi)過。這一例“巧合”提醒我們注意,吳綃《戲和詠手》之類的詠物七律,寫的雖是閨闈常景,但創(chuàng)作出發(fā)點(diǎn)可能不是寫實(shí),而是擬古,創(chuàng)作動(dòng)機(jī)不在於抒發(fā)自身女性化的思緒或哀樂,而是決心以體式作爲(wèi)突破口,對(duì)晚唐詠物七律的典型技法作亦步亦趨的模仿,從而鍛煉自己的詩法、詩藝向目標(biāo)風(fēng)格接近。除《戲和詠手》之外,吳綃的詠物七律還有《嘲春風(fēng)》《燈花》《曉帷》《牡丹》《緋桃》《美人臨池》《愛妾換馬》等。大都具有摹寫精細(xì)、窮形盡相、設(shè)色艶麗、筆觸工巧的特色。雖然在詠物時(shí)會(huì)映帶大量有關(guān)女性生活和情愛的意象,但始終不觸及內(nèi)心,感情色彩十分淡薄,體現(xiàn)出典型的晚唐齊梁體風(fēng)格。
其次是艶體歌行。明代擅長(zhǎng)辨體之學(xué)的許學(xué)夷認(rèn)爲(wèi)“語多綺艶”“聲調(diào)全乖”的七言歌行始自蕭綱,可見宮體詩人已開始創(chuàng)作艶體歌行,則它也是齊梁詩風(fēng)的一種典型體式。晚唐,以溫、李爲(wèi)代表的綺艶一派復(fù)追齊梁之體,也創(chuàng)作艶體歌行,如李商隱《又效江南曲》《無愁果有愁北齊歌》《射魚曲》《宮中曲》《燒香曲》以及溫庭筠《金荃集》的前兩卷,均爲(wèi)此體。陸時(shí)雍《詩鏡》評(píng)溫庭筠艶體歌行曰:“深著語,淺著情。”(12)(明)陸時(shí)雍:《唐詩鏡》卷五一,《詩鏡》,保定:河北大學(xué)出版社,2010年,第1170頁。意思是這類詩長(zhǎng)於創(chuàng)造大量鮮麗的形象,而不肯暢盡地抒情達(dá)意。作爲(wèi)在齊梁和晚唐均受到青睞的一種體式,艶體歌行也被馮班所重視。馮氏的艶體歌行數(shù)量頗多,從風(fēng)格上看主要學(xué)溫庭筠、李商隱和李賀,他曾作溫庭筠創(chuàng)題的《夜宴謡》《春曉曲》,李商隱創(chuàng)題的《燒香曲》,還曾兩次寫作李賀創(chuàng)題的《十二月樂辭》。
與馮班一樣,吳綃也作過《十二月樂府辭並閏月》。李賀是元和詩人中對(duì)溫、李影響較大的一位,溫、李艶體歌行中的峭艶、哀麗風(fēng)格,很大程度上來自對(duì)李賀歌行修辭設(shè)色的刻意學(xué)習(xí)。馮班和吳綃之創(chuàng)作《十二月樂府辭》,動(dòng)機(jī)之一應(yīng)該是從李賀處尋找溫、李奇峭之氣的源頭,並通過模仿來把握其修辭、用字特色。以吳綃《十二月樂府辭並閏月·五月》爲(wèi)例:“小口銀瓶瀉輕緑,寒影花生濯纖玉。細(xì)葛如煙湘簟清,香濕紅綃睡新足。綵絲系臂當(dāng)佳節(jié),塘邊古柳新蟬咽。園葵垂葉庀芳根,當(dāng)花朵朵凝猩血。”(第一冊(cè)第181頁)重視原始感覺,拋棄固有名詞,大量運(yùn)用“輕緑”“寒影”“纖玉”“香濕”等感覺性代詞。刻意違反日常性,對(duì)柔美的花朵偏下“猩血”這樣帶有蠻荒意味的修飾語,成就一種艶而峭、麗而哀的詩境。這正是李賀歌行的典型手法和典型特色。
此外,《嘯雪庵集》中的《送春》《春晚曲》等篇也系艶體歌行。如《送春》:“軟風(fēng)吹日琉璃光,纖蛾縈夢(mèng)蘭被香。錦魴掉尾波靨靨,翠鈿細(xì)點(diǎn)鋪池塘。赭汗驕行縱金勒,輕紈夾鐙棠梨色。西陵草暖松刺新,翠蓋飛塵歸路直。紅鉛欲墜春煙動(dòng),有淚無言暗相送。高堂歌徹綺筵收,歡餘坐覺羅衫重。腰帶圍寬珠續(xù)續(xù),年年袛恨芳華促。羲和西轡爲(wèi)誰遲,繞枝空有蝴蝶哭。”(第一冊(cè)第155頁)此詩寫的是齊梁十分流行的思婦遊俠題材,作者對(duì)物象刻畫抱有極大熱情,一面對(duì)春日的軟風(fēng)、閨中感懷的女子、池中的錦魴和翠萍做了細(xì)緻新穎的形容,另一面加意摹寫遊俠的輕紈、金勒、浪遊道路上的暖草新樹以及車馬掀起的飛塵。與令人眼花繚亂的物象描寫形成鮮明對(duì)比的,是對(duì)感情的淡化處理。詩中有一位思婦,作者對(duì)她“紅鉛欲墜”“有淚無言”的嬌弱姿態(tài)加意刻畫,卻很少直白表達(dá)她內(nèi)心的愛恨。“年年只恨芳華促”一句約略透露了她對(duì)愛的惆悵之情,但很快又折返描寫她病瘦的身軀和纖細(xì)的腰肢。很顯然,此詩更注重的是創(chuàng)造華美艶麗的形象,而非暢快地抒發(fā)感情。這與溫庭筠《金荃集》“深著語,淺著情”的艶體歌行如出一轍。要言之,吳綃的艶體歌行以客觀化的態(tài)度描寫景物和女性的情感生活,創(chuàng)造出豐富的意象和華美的詩境,卻絶不抒發(fā)個(gè)人化的情感,近似晚唐溫庭筠。她刻意違反日常性,重視原始感覺的表達(dá),成就峭艶、哀麗的特色,又近於李賀。
再次是吟詠女性形象和男女情事的七言絶句。宮體詩人已經(jīng)開始創(chuàng)作措語艶麗的七言四句體(13)許學(xué)夷在《詩源辯體》卷九中說:“孝威七言四句有《詠曲水中燭影》一篇,較明遠(yuǎn)語更綺艷而聲調(diào)仍乖。下流至梁簡(jiǎn)文七言四句。”,晚唐綺艶派詩人中,韓偓、唐彥謙的艶體七絶在內(nèi)容上和宮體詩有相通之處。馮班集中有不少描寫女性形象和情感生活的七絶,吳綃也是如此。女性詩人寫女性題材的詩歌,乍看起來很自然,但能夠把女性看作完全的客體,客觀地體寫女性色相和情緒,而不作主觀化的情感抒發(fā),這就是宮體一脈的獨(dú)特遺産了,它要求創(chuàng)作主體以男性化的視角品鑒女性的容色。(14)張一南:《我見猶憐——唐代女詩人的齊梁體創(chuàng)作》,《文史知識(shí)》,2014年第3期。這在當(dāng)時(shí)不是一般女詩人能措手的。
《嘯雪庵詩集》中有《吳中有唱和百聲絶句者命題恨於未雅然已煩翰墨不欲棄之聊存其廿首》組詩。從題目看,此詩的創(chuàng)作動(dòng)機(jī)是追逐當(dāng)時(shí)當(dāng)?shù)氐脑妷L(fēng)尚,但讀後發(fā)現(xiàn),吳綃客觀體寫女性色相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時(shí)時(shí)關(guān)涉六朝舊事的寫作手法,都與晚唐韓偓《香奩集》中的七言絶句一脈相承。如吳綃《駡裙》:“八幅湘波見似空,雙鈎開處觸微風(fēng)。低頭帶笑輕輕唾,掩斂纖腰面發(fā)紅。”(第一冊(cè)第158頁)捕捉到一個(gè)富有戲劇性的場(chǎng)景,即女性裙角被風(fēng)吹開的瞬間。作者贊美女子如湘波一樣的裙子,又設(shè)想風(fēng)掀起裙角後,女性纖足暴露於風(fēng)中的細(xì)微感受,最後摹寫女子低頭駡裙時(shí)既嗔又窘的情緒,以及掩斂纖腰的動(dòng)作和羞紅的臉龐。《覓釵》的內(nèi)容更加香艶:“一覺巫陽薦夢(mèng)回,鳳冠聲徹曉光來。鬆雲(yún)散盡鴛衾薄,移枕頻聞覓玉釵。”(第一冊(cè)第159頁)雞唱之後,一位春夢(mèng)初回的女性鬢落釵垂,嬌臥鴛被之中,帶著夢(mèng)後的迷亂感摸索在睡眠中掉落的玉釵。詩歌近距離地刻畫深閨女性的生活細(xì)節(jié),充滿誘惑力,讀來令人生出綺麗的幻想。一位女詩人竟然可以如此細(xì)緻、自在地體寫女性色相,這在當(dāng)時(shí)是一種突破。這種用客觀視角品鑒女性之美的創(chuàng)作歷來是男性的特權(quán),但吳綃通過體式的學(xué)習(xí),從方法上把握了宮體詩人和晚唐綺艶派詩人的創(chuàng)作秘訣,這在某種程度上破除了禁忌感,使她在詩國(guó)之中像真才子一樣坦然地欣賞、描繪女性之美。
要之,吳綃《嘯雪庵集》中的綺艶風(fēng)格集中體現(xiàn)在三種詩歌體裁上,分別是體物工致、設(shè)色艶麗的詠物七律,涉及女性情愛的艶體歌行以及艶情題材的七絶,這也是晚唐溫、李一派極具特色的三種詩體。吳綃善於從體式入手效法前人,頗能抓住晚唐綺艶詩風(fēng)的神髓。在這些詩歌中,吳綃廣泛地涉及女性和情愛的主題,但她不是用言志的態(tài)度去抒發(fā)自身作爲(wèi)女性的憂樂,而是本著緣情、體物的態(tài)度,用客觀化的視角鑒賞女性的色相,體寫女性的姿容,這爲(wèi)女性詩歌的疆域開拓出了新的維度。而吳綃之所以能作出這種開拓,除了開放的時(shí)代背景和寬鬆的生活環(huán)境之外,更是她善於向深厚的詩史傳統(tǒng)開掘,善於從齊梁詩風(fēng)的遺産中學(xué)習(xí)技巧和思路的緣故。
三、 吳綃詩歌對(duì)社會(huì)生活的反映
吳綃生命的最後十幾年是在羈旅中度過的,以其夫許瑤的故去爲(wèi)界,又可將其分爲(wèi)兩段:第一段是隨夫遠(yuǎn)宦。她的隨宦之旅曾遠(yuǎn)至邯鄲、廣武、鄜州,後來一度到達(dá)蜀中,這給了她走出閨閣的機(jī)會(huì),拓展了她的生活空間。吳綃這一時(shí)期的詩歌不僅記録了幽冀大地的河山勝景、風(fēng)俗物候,更罕見的是,她在詩中表達(dá)了與丈夫分擔(dān)政務(wù)的願(yuàn)望和士大夫式的出處觀,這些思想與她的女性身份和仙道信仰纏繞在一起,造成了一個(gè)交織著理想和幻滅的複雜混合體。這些詩歌氣度宏闊清雄,與虞山時(shí)期的作品大爲(wèi)不同,後編爲(wèi)《嘯雪庵新集》。
隨許瑤知廣平府時(shí),吳綃創(chuàng)作了《平干署中作》組詩三首,第一首曰:“閨閣山林十載強(qiáng),娛情活計(jì)一書囊。每慚五斗折腰士,愧殺千金買賦娘。廣放胸襟容世態(tài),微開醉眼看興亡。此來不爲(wèi)黃堂助,欲破迷城繼子房。”(第一冊(cè)第185頁)這首詩集中展現(xiàn)了她對(duì)閨閣之外更爲(wèi)宏闊的生活場(chǎng)景的期待。首聯(lián)發(fā)聲已自不凡,閨閣而兼之以山林,又以書娛情,一個(gè)通脫清朗的女性形象已經(jīng)初具輪廓。頷聯(lián)寫其志向,因自己憂念政事,所以解綬去職的陶彭澤也不值得作爲(wèi)自己的偶像了。劉阿嬌千金買賦,邀君王之寵,這原是女子本色,吳綃卻以之爲(wèi)愧,可見其心性與尋常女子迥異。頸聯(lián)寫其心境:“廣放胸襟容世態(tài),微開醉眼看興亡。”這種超越現(xiàn)實(shí)、靜觀世界的清醒感即使在男詩人中也難得一見。前三聯(lián)已覺一聯(lián)比一聯(lián)聲氣雄壯,尾聯(lián)扣題,更將胸中的宏圖大志一吐爲(wèi)快。平干署乃是廣平治所,吳綃宣稱,此來平干志不在賢內(nèi)助,願(yuàn)以張良爲(wèi)法,建立破敵制勝式的大功勛。儘管歷史上不乏女性勸誡丈夫勤於政務(wù)的佳話,也有不少精英女性能夠利用自己的學(xué)識(shí)爲(wèi)丈夫出謀獻(xiàn)策,但多數(shù)女性仍傾向於將自己的形象隱藏在閨閣之內(nèi),吳綃這首詩卻充滿不讓鬚眉的氣概,其宏圖大志令人震驚。同期,許瑤也創(chuàng)作了一首《平干署中》,正可與吳綃作品形成對(duì)比,詩曰:“滏水蒸如釜,疏源復(fù)導(dǎo)流。遠(yuǎn)簫聰夜性,新緑凈秋眸。吉月明神告,邠風(fēng)上古遊。何當(dāng)除害馬,浸假任呼牛。”(15)(清)許瑤:《竹廣詩集》卷五,上海圖書館藏稿本。首聯(lián)點(diǎn)出自己的河務(wù)工作,中聯(lián)贊美中原風(fēng)物,尾聯(lián)有節(jié)制地抒發(fā)了自己的報(bào)國(guó)情懷,中規(guī)中矩。相形之下,他的作品反倒像是吳綃的陪襯了。
對(duì)吳綃來説,憂心政事已經(jīng)成爲(wèi)她生活裏縈繞不去的一抹恒常底色。九日扶病登高,她沉浸在“萬幅荊關(guān)圖,齊懸於此地”的勝景中,心胸稍一爲(wèi)之開闊,不久又轉(zhuǎn)而慨嘆“雨露被四方,蘭臺(tái)尊獨(dú)立。滄桑莫可期,身世總?cè)缂摹?第一冊(cè)第191頁)。即使是在公署中獨(dú)坐片刻,也會(huì)生出“晚薪已積憑誰問,故劍空存未遇時(shí)”(第一冊(cè)第185頁)的喟嘆。《嘯雪庵新集》中還有《廣平春日閲操和韻》詩,她見軍容整肅、兵甲鮮明,深幸這支勁旅可承擔(dān)起安邊定遠(yuǎn)的責(zé)任:“吾聞平干古趙國(guó),鼎士叢臺(tái)誇袨服。遺風(fēng)至今多探丸,椎埋剽劫紛追逐。西鄰太行高突兀,邃谷深巖狡兔窟。曾喜渠魁能革心,頗恨餘妖猶竊出。不識(shí)軍營(yíng)步伍齊,遠(yuǎn)屠鯨鯢服蛟螭。漳滏安瀾太行寂,常爲(wèi)帶礪護(hù)神畿。”(第一冊(cè)第195頁)以上詩歌皆可見出關(guān)心政務(wù)在吳綃生活中占據(jù)的重要位置。吳綃對(duì)政事超乎尋常的熱情在當(dāng)時(shí)已經(jīng)被陳焯注意,他在序言中提道:“顧念蘭陵柄用方始,行參大政,潤(rùn)色昇平,興朝郊廟樂章必由手定。夫人誼繫唱隨,亦應(yīng)譜安世之歌,被諸管弦,如唐山夫人者。”(第一冊(cè)第148頁)陳焯將吳綃比作唐山夫人,此舉耐人尋味,他似乎在特意抹去吳綃刺眼的鋒芒。因爲(wèi),曾全録《嘯雪庵集詩》的陳焯知曉,吳綃的志向絶不局限於“興郊廟樂章”而已,但心無芥蒂地接納一個(gè)女性在政治上的勃勃雄心,對(duì)他來説或許是困難的。
吳綃分享丈夫與朝廷的政治紐帶的意願(yuàn)是如此強(qiáng)烈,以致於當(dāng)許瑤遭遇仕途挫折時(shí),她也表現(xiàn)出深切的失落感。《辭富貴》詩約寫於順治十八年(1661)許瑤因江南奏銷案罷官之後,詩中有這樣的句子:“厚祿豈不榮,黃金非所須。多謝羅與綺,無煩飾我軀。載拜謝青瑣,何勞光吾廬。雖慚非明智,助理或有餘。要使千里境,窮黎謳袴襦。此志信落落,亦自哂疏迂。獨(dú)位人所羨,銅陵誰復(fù)逾。滄桑難固保,灰劫類魚罛。以茲卻富貴,懷舊發(fā)嗟吁。”(第一冊(cè)第192頁)許瑤罷官之後,吳綃惋惜的不是官職、榮祿或者綺羅黃金的喪失,而是自己充任丈夫助理,廣施善政,最終使窮黎稱頌的夙願(yuàn)終究無法達(dá)成了。對(duì)於在政務(wù)上所懷的抱負(fù),吳綃的態(tài)度是“此志信落落,亦自哂疏迂”,有時(shí)她也不免懷疑自己這份志向過於孤特、不同凡響,嘲笑自己迂腐、疏闊。這些詩句都真實(shí)地呈現(xiàn)出一位走出閨闈,渴望獲得社會(huì)生命的女詩人複雜又矛盾的心曲。
康熙三年(1664),隨著許瑤的故去,吳綃步入人生的最後旅程。她在詩歌中描繪的晚景頗爲(wèi)凄涼,《畫卷自敘》説:“遘閔以來,舊居不守。”(第一冊(cè)第219頁)可知在丈夫去世後,她失去家宅,從此藐然孤身,梗泛萍流。厄運(yùn)還不僅如此,《上郡司馬》詩有句云:“冤婦悲東海,窮嫠哭杞梁。強(qiáng)遭梟取子,訟枉鼠穿墻。”(第一冊(cè)第222頁)連用東海冤婦、杞梁妻自比,可知她晚年無子,無所依傍;又疊用《鴟鴞》《行露》之典,可見她屢受迫害,冤獄纏身的處境。此際,吳綃除了在虞山活動(dòng)外,還因訟事久客金陵,這可以視爲(wèi)她之前羈旅生涯的一種延續(xù)。
生命晚期的吳綃依然活躍在閨闈之外,積極地與社會(huì)各界人士交流,不過性質(zhì)已經(jīng)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説之前踏出閨闈對(duì)她來説含有一種主動(dòng)探尋的意味,那麼此時(shí)在閨閣外拋頭露面則屬情非得已。爲(wèi)了洗雪冤獄,她不得不奔波呼告,在名公巨卿之間周旋。除若干懷古詩外,吳綃在這一階段寫得最多的是獻(xiàn)謁、酬贈(zèng)、題畫詩,她的應(yīng)酬對(duì)象五花八門,家族親眷、知心朋友、詩壇勝流、政界公卿、方外之人,無所不包,這一時(shí)期的作品後來結(jié)爲(wèi)《嘯雪庵題詠二集》。
此期吳綃的投贈(zèng)對(duì)象中的名公,以詩壇論有吳偉業(yè)、陳焯、周亮工、宋琬、袁于令、黃媛介、陳結(jié)璘;以政界論有中丞林玉礎(chǔ)、邑侯李漱巖、副戎李玉廷、郡侯吳瑤如、少司馬張蘧林、總?cè)至耗车鹊取?duì)其中的不少人,吳綃不惜反復(fù)贈(zèng)詩,再三致意。不過,無論酬贈(zèng)的對(duì)象是詩人或公卿,無論是單純的獻(xiàn)謁詩還是有其他主題,她的詩歌內(nèi)容總離不開對(duì)冤情的分訴,對(duì)遭遇的悲嘆,對(duì)援救的渴望以及對(duì)施救者的感激。例如《和周櫟園藩侯扇頭原韻》組詩,前三首全力贊美周亮工的政績(jī)、文名、清譽(yù),最後一首轉(zhuǎn)而引入自身遭遇,希冀能始終得到對(duì)方的蔭護(hù),詩曰:“一萍漂泊嘆瞻烏,幸識(shí)山公已不孤。自問鸇毆甘兔伏,豈期犀燭拜龍圖。芝顔乍覿疑天上,樗質(zhì)蒙恩濫坐隅。從此帡幪知有賴,可能終照覆盆無。”(第一冊(cè)第200頁)又如《戊申中秋林孝廉道長(zhǎng)新構(gòu)初成賦詩奉贈(zèng)》:“大廈翬飛燕雀賀,蕭條旅館愁風(fēng)露。能送兼金修草堂,如展西江濡涸鮒。明珠欲報(bào)愧窮途,聊把深誠(chéng)托緗素。”(第一冊(cè)第201頁)在誇贊對(duì)方新居富麗瀟灑外,也對(duì)林孝廉的資助表示了感激。《丁未秋避跡鄉(xiāng)間偶遇瞿夫人邀歸談心數(shù)日方別》先記録了與陳結(jié)璘的深厚友情:“珍重至言唯鏤骨,黯然銷別共沾裳。”尾聯(lián)又轉(zhuǎn)向感恩:“他年此日銜環(huán)到,不負(fù)恩深畯喜堂。”(第一冊(cè)第228頁)在其他主題的詩歌中尚且千方百計(jì)地傾訴自身的遭遇,至於那些專門寫來投贈(zèng)公卿的獻(xiàn)謁詩,吳綃更在其中放聲呼告:
憶昔東海罹奇殃,雷霆九夏挾飛霜。我公舉手話枯骨,群邪解駁回春陽。(《贈(zèng)蘧林張少司馬》)(第一冊(cè)第202頁)
憶昔煢婺蒙覆盆,霜飛九夏控?zé)o門。我侯抱牘不忍署,枯槁幸爾賒殘魂。沉冤未雪皮骨盡,一萍逐浪難依根。寄跡長(zhǎng)干月常見,索索寒風(fēng)振衰柳。(《長(zhǎng)干旅次贈(zèng)漱巖李邑侯》)(第一冊(cè)第205頁)
獨(dú)悵煢婺跡,飄淪異土邊。巢傾雙淚涸,盆覆寸心悁。喜遇神明宰,新操長(zhǎng)養(yǎng)權(quán)。迢遙瞻舜日,俯仰戴唐天。(《上邑侯新任》)(第一冊(cè)第210頁)
閨閣詩人作品中最常見的是個(gè)人的悲歡、生活的苦樂或家族命運(yùn)的興衰,以詩鳴冤、剖白當(dāng)?shù)赖膬?nèi)容,是吳綃對(duì)女性詩歌題材的開拓。吳綃還通過詩歌把進(jìn)退失據(jù)的生存狀態(tài)揭示出來,《嘯雪庵題詠二集》中《贈(zèng)陳不易》詩曰:“嗟哉我生值數(shù)奇,頻年蹤跡信萍移。茫茫前路向誰是,進(jìn)退觸藩舉足疑。”(第一冊(cè)第205頁)以詩記録訟事向外界展示,這在女性詩史上實(shí)屬罕見。
回顧吳綃人生的晚期階段,可以看出她的生活空間遠(yuǎn)超閨閣之外:先隨夫遠(yuǎn)宦中原和蜀地,熱心分享丈夫與朝廷的政治紐帶,寫作憂念政事的詩歌,抒發(fā)士大夫式的出處觀。丈夫去世後,她身陷訴訟,漂泊無依,不得不寫詩剖白冤獄,投贈(zèng)當(dāng)?shù)溃瑏K把晚年的不幸遭遇忠實(shí)地寫進(jìn)詩內(nèi)。在吳綃手中,詩歌不僅是抒情寫志的載體,更成爲(wèi)她與社會(huì)溝通的工具。
四、 集部作品與説部傳聞交錯(cuò)織就的才女形象
中國(guó)文學(xué)史上最著名的閨閣作家,其作品的流傳總是伴隨著種種傳聞逸事,李清照、朱淑真可算最爲(wèi)典型的例子。吳綃作爲(wèi)明清之際虞山最負(fù)盛名的女詩人之一,在説部中也留下不少故事。這些故事中的吳綃形象和她在作品中塑造的自我形象差別巨大。從《嘯雪庵集》和同時(shí)代的詩文評(píng)中,我們讀到的是多才多藝,眼界寬廣,有卷耳之懷、樛木之仁的“吳中第一女才子”(16)王端淑在《名媛詩緯》中評(píng)吳綃曰:“有才色,自詩文書畫以及百家技藝無不通曉,即緇黃內(nèi)典亦皆究心。蓋千古聰明,絶代佳人也。爲(wèi)吳中女才子第一。”,但在説部作品中,吳綃卻被賦予了不同的面貌。
婁東無名氏康熙五年編訖的《研堂見聞雜記》記載了關(guān)於吳綃的兩則逸事。文章以“常熟許文玉之室吳氏,能詩書,負(fù)倜儻不羈之才”(17)(清)婁東無名氏:《研堂見聞雜記》,《中國(guó)野史集成》編委會(huì)、四川大學(xué)圖書館編:《中國(guó)野史集成》,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第37冊(cè),第39頁。開篇,後文卻未圍繞吳綃的詩書才華展開,它記載的故事離經(jīng)叛道,從另一個(gè)角度描畫著這位才女的形象。第一則逸事是里中的一場(chǎng)糾紛:康熙初年,許家人病死,有人暗中撥弄稱此事爲(wèi)朱家所使。“於是吳氏從二百家人,至其家,風(fēng)卷而縛其主,歸系死者足,榜笞無數(shù)”。朱氏在縣公幫助下得脫,許瑤束手,吳綃卻不肯罷休,往吳門投簡(jiǎn)於副都統(tǒng),“握手甚歡”,次日控之於祖大將軍,朱氏就縛。不久,朱氏訴之總督郎公、京口劉大將軍,吳綃以萬金賄劉。後總督郎公之牒下之蘇松道臣,吳綃毫不退縮,“輕舟就訊”。第二則逸事指摘吳綃的生活,稱她“艶妝濃裹,每遇春花秋月,從女奴十,往來山水,盤礴登眺。旗亭蕭寺,揮毫染筆,觀者如堵墻,色不一動(dòng)”。又把吳綃和柳如是相較:“吳之學(xué)不如柳,然才名相埒。其風(fēng)流跌蕩,則同爲(wèi)天地間一異物也。”最後諱莫如深地寫道:“吳少年事甚多,不敢筆之於書。”(18)《研堂見聞雜記》,第39頁。
吳綃形象在説部和集部文獻(xiàn)中差異雖大,但兩類文獻(xiàn)之間並不是毫無關(guān)聯(lián)的,説部逸事往往能在基本事實(shí)上和集部作品保持一致,但在事情走向和事件性質(zhì)上卻更爲(wèi)浮誇,更具聳動(dòng)性。比如,就《雜記》所載糾紛之事來看,核之以吳綃作品,可知她確曾捲入訴訟,但其處境在兩類文獻(xiàn)中大相徑庭:《雜記》中的吳綃翻雲(yún)覆雨、肆意妄爲(wèi),爲(wèi)占上風(fēng)不惜一擲萬金,而在吳綃筆下,她的自我形象卻是無所倚傍、陳冤難雪。就生活方式來看,《雜記》評(píng)吳綃“風(fēng)流跌蕩”,這或許能與吳綃早年的綺艶詩風(fēng)搭上些許關(guān)係,但評(píng)序類文獻(xiàn)一般都能甄辨出吳綃冶艶的風(fēng)格來自對(duì)晚唐溫、李和李賀的師法,未見聯(lián)繫吳綃所謂“少年事”來評(píng)論其詩作的情況。通過對(duì)比可見,《研堂見聞雜記》中的逸事就像給吳綃詩歌所作的誇張性箋解,它既不是徹底的虛妄之談,但也不能和吳綃的詩詞完全吻合,它和後者形成一種扭曲的呼應(yīng),虛虛實(shí)實(shí)之間,使作爲(wèi)才女的吳綃更有魅力,更具話題性。從此之後,這些逸事和吳綃作品糾纏在一起,共同傳播於士林之間。
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曾經(jīng)盛行一時(shí)的《嘯雪庵詩集》漸漸沉入故紙堆,可是説部中才女吳綃的逸事卻幾經(jīng)渲染,歷久不衰。有些逸事甚至漸漸脫離了主體,獲得自己的一套滋生邏輯,後來吳綃甚囂塵上的“婚外戀情”,正是在《研堂聞見雜記》“少年事甚多”之類逸事的基礎(chǔ)上一步步滋長(zhǎng)起來的。在婁東無名氏《研堂見聞雜記》之後,虞山王應(yīng)奎對(duì)馮班一首《無題》詩的解讀爲(wèi)吳綃婚外戀情的傳播史添上重要一環(huán)。馮班《次和遵王無題詩一百韻》中有“小院開魚鑰,名花破粉鈿。追遊多勝侶,行樂及時(shí)年。渡口橫波急,中庭半鏡全。凝愁誰縈滯,私約更輕愆。醇酒三年醉,餘酲五斗蠲。鳳聲驚翠竹,雁柱軋香弦。席軟龍鬚密,簾輕玳甲編”(19)(清)馮班:《鈍吟老人集外詩》,上海圖書館藏吳卓信跋並臨馮武、王應(yīng)奎、錢硯北評(píng)校康熙刻本。等句。詩中女性生活輕浮,且有私約之行。王應(yīng)奎認(rèn)爲(wèi)此詩即影吳綃而作,其評(píng)注曰:“大都爲(wèi)高陽。”其實(shí)從文體角度來看,這類五言排律《無題》的創(chuàng)作始自晚唐韓偓《香奩集》,炫耀辭藻、堆砌華美意象是其題中之義。詩人們又常以唱和競(jìng)爭(zhēng)爲(wèi)樂,動(dòng)輒十幾韻,有逞才意味,並非具有諷喻性質(zhì)的嚴(yán)肅寫作。此詩後附陸敕先注:“先鈍吟爲(wèi)遵王所戲,謂公定不耐此長(zhǎng)篇。因援筆而書,頃刻立就,文不加點(diǎn)。”這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作者作詩時(shí)的遊戲心態(tài)。但是,王應(yīng)奎以深諳虞山掌故著稱,他指認(rèn)馮班此詩爲(wèi)吳綃作,這種説法可能隨著馮氏詩集的流播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乾隆二十六年(1761),一部吳簫和陶世濟(jì)的情書集《贈(zèng)藥編》橫空出世,此編共收往還情書92封,把一段不倫之戀構(gòu)建得既首尾完整又情節(jié)豐滿。《贈(zèng)藥編》以鈔本傳世,不著編纂者,書後有魚元傅跋。據(jù)《海虞詩苑》,魚氏篤志好古,凡邑中名人著述,廣爲(wèi)搜輯。其跋《贈(zèng)藥編》曰:“夫閨閣限閫,內(nèi)外間截慎密至矣。故墻茨之什,聖人所以著之於經(jīng),其旨嚴(yán)矣。若乃淫亂性成,以隱秘罔聞,遂致肆惡不反。如吳氏者,國(guó)人亦共惡之。”(20)(清)魚元傅:《贈(zèng)藥編跋》,國(guó)家圖書館藏清鈔本。此吳氏究系何人?據(jù)《贈(zèng)藥編》小引:“吳簫者,字素音,別號(hào)韻仙,金閶之望族女也,適虞爲(wèi)商人婦。”(21)(清)無名氏:《贈(zèng)藥編·小引》,國(guó)家圖書館藏清鈔本。除“金閶望族女”這一家世信息與吳綃實(shí)際情況相符外,這位吳簫的名、字、號(hào)、婚嫁對(duì)象全部謹(jǐn)慎地與吳綃本人的真實(shí)情況保持微妙的差異。這種處心積慮的設(shè)計(jì),加上整部尺牘集完整無缺的往還結(jié)構(gòu),跌宕起伏的情節(jié)發(fā)展,怎麼看都更像是出自後人的精心杜撰。
儘管如此,後世很多讀者仍將它當(dāng)作詩人吳綃的情書來閲讀和接受。《贈(zèng)藥編》中的吳簫,行爲(wèi)大膽,言語淫艶。她熱烈追求真愛,百折不回的個(gè)性神似杜麗娘,當(dāng)陶世濟(jì)對(duì)戀情表現(xiàn)出遲疑和回避時(shí),吳簫的回應(yīng)是:“弟反覆懇言,只爲(wèi)一情字,生死旦暮,只爲(wèi)一情字。豈無榮辱之戀,恩愛之貪者,固不敢負(fù)此兩字,一概拋擲,以報(bào)盟兄。”(22)(清)吳簫:《贈(zèng)藥編·訴翁》,國(guó)家圖書館藏清鈔本。鬱憤之情綿綿滾滾,讀來令人有蕩氣迴腸之感。隨著《贈(zèng)藥編》的流傳,此杜麗娘式的吳簫也漸漸融入了詩人吳綃的形象之中。
幾經(jīng)渲染之後,有關(guān)吳綃的傳聞逸事産生了更持久的效應(yīng),人們知曉她的風(fēng)流韻事往往早過閲讀她的作品,遂使詩人吳綃與説部傳聞中的吳綃糾纏不清,有時(shí)後一種形象甚至掩蓋了她作爲(wèi)詩人的本來面容。近代很多大家在研究中都曾經(jīng)將兩類吳綃形象混淆,或不加區(qū)分地交叉相證,如夏承燾《天風(fēng)閣學(xué)詞日記》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條記載:“午與一帆合觴斐雲(yún)、佩秋、榆生、欣夫、劍心於榮康酒樓,費(fèi)十金。席間斐雲(yún)談董綬金事甚可笑。又談明末蘇州女子吳綃情書。”(23)夏承燾:《夏承燾集·天風(fēng)閣學(xué)詞日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冊(cè),第126頁。可見當(dāng)時(shí)在場(chǎng)的諸位詞學(xué)家未清晰地意識(shí)到此吳簫並不等同於彼吳綃。又如鄧之誠(chéng)《清詩紀(jì)事》曰:“《研堂見聞雜記》謂吳綃有放蕩之行、墻茨之言,所不必道,而把持官府,則實(shí)有之。《二集》中多投贈(zèng)當(dāng)?shù)乐鳌?24)鄧之誠(chéng):《清詩紀(jì)事初編》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39—340頁。作者不信《雜記》中所述吳綃的放蕩之行,但仍試圖以吳綃的詩歌去印證傳聞中“把持官府”的吳綃形象。其實(shí)兩類文獻(xiàn)中的吳綃很難粘到一處,二者之間應(yīng)該保持一定的區(qū)分度,不該不加審查地互相牽合。
明清時(shí)代,隨著女性寫作的普及,很多閨閣之作被梓爲(wèi)別集、選集和總集進(jìn)入流通的環(huán)節(jié),與此同時(shí),有關(guān)女性的説部文字也出現(xiàn)激增。據(jù)王士禎《香祖筆記》:“先兄西樵先生,撰古今閨閣詩文爲(wèi)《然脂集》,多至二百卷。詩部不必言,文部至五十餘卷,自廿一史已下,瀏觀采摭,可稱宏博精核,而説部尤創(chuàng)獲,爲(wèi)古人所未有。”(25)(清)王士禎:《香祖筆記》卷八,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34年,第81頁。從“説部尤創(chuàng)獲,爲(wèi)古人所未有”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清代文人對(duì)於搜集説部文字的自覺和自矜。明清才女的詩人和作者形象是在被傳聞逸事渲染的漸進(jìn)接受過程中形成的一種混合體。在研究明清女性文學(xué)時(shí),集部作品和説部敘述之間複雜的呼應(yīng)與排斥,是應(yīng)該注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