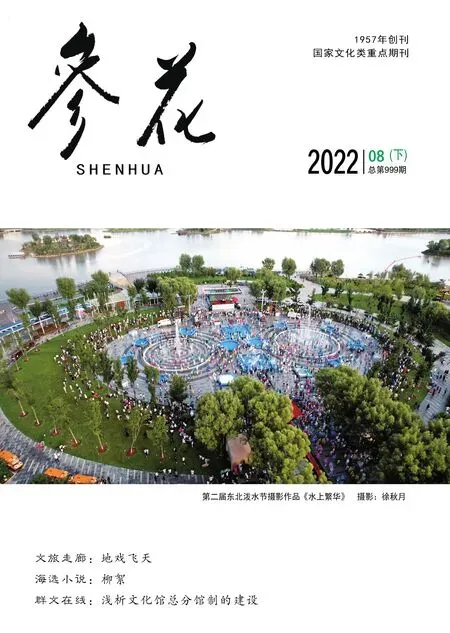牽著那根繩
◎潘愛英
一生中或許總有些經(jīng)歷和牽絆,以執(zhí)念的光照進夢幻與清醒,稍微輾轉(zhuǎn)反側(cè)便會閃現(xiàn)。
姐姐離開家鄉(xiāng)在省外城市生活已二十多年,這些光陰是她當前人生的二分之一,她卻總說時常會在夢里看見孩提時放的那頭牛。
那時還是在生產(chǎn)隊,放牛娃看牛是可以為家里掙微薄工分的。姐姐看的那頭牛是一頭年輕的水牛,青黑的皮毛還帶著稚氣,彈性十足不帶一點皺褶,尺來長的兩角桀驁不馴地彎挺。小水牛很喜歡和其他水牛斗架,經(jīng)常把拴著的繩索斗爛。常常是在放出去后,天不怕地不怕,很快就會跑到七八歲的姐姐找不見的地方。每次跋山涉水費很大力氣夜幕降臨后才找到它,姐姐都會和它生氣,罵它:“你不知道自己會走丟啊?不知道會迷路啊?走那么遠要是回不來怎么辦?”它還瞪著一雙無辜的大眼睛,懵懂地看著姐姐。姐姐越發(fā)生氣地拿小石子砸它,見它還是不明所以不知道錯的樣子,姐姐又會心疼地抱著它的角哭起來。
生產(chǎn)隊用牛耕田的大人們,有的專挑年輕力壯的牛用。對牛挑肥揀瘦,自然對放牛娃也會說風涼話。但每當小水牛被套上犁耙,被大人用竹梢抽打著拼命干活時,姐姐都不忍心看。每當在哪里看見有豐盛的草,姐姐都會暗暗記在心里,想著小水牛吃個饜足的樣子就開心。
那年農(nóng)歷四月初八,鄉(xiāng)里民俗相傳這天是牛的集體生日,管牛的“神仙”會放下很多牛們最喜歡也最稀罕的好東西在人間野外,誰的牛吃到這些東西保證一年健康無恙。因此,每個放牛娃便都會記得在這天凌晨就把牛早早地放出去吃草。由于年幼的姐姐睡忘了時間,把牛放出去時天已快亮。接回小水牛時,發(fā)現(xiàn)牛眼角有兩行淚痕,姐姐相信這是因為自己把小水牛放出去遲了,沒吃到“神仙”降下的美味佳肴,小水牛傷心流涕。姐姐心里充滿了對小水牛的愧疚。
本想在來年再補償小水牛的,可還沒到第二年的四月初八,小水牛在生產(chǎn)隊大人們的合計中不見了蹤影。向自以為是的大人們打聽牛的去處,一定是無功而返的。姐姐想過小水牛會被賣到哪個農(nóng)戶手中,也會想不知道那家人對小水牛好不好,一定有一個放牛娃牽著小水牛的繩帶它吃最茂盛的草吧……幼小的姐姐除了擔心小水牛在陌生的地方會迷路外,還對想象中的那個放牛娃充滿了羨慕和嫉妒。
包產(chǎn)到戶后,生產(chǎn)隊分牛是按照抓鬮的辦法確定每戶人家得到老牛還是壯牛的。我們家分到了一頭中年的母黃牛。我之所以清楚它是頭中年的牛,那是和別人家的相比,我們家的牛,尾巴往前的盆骨瘦得向兩邊凸出甚至有些嶙峋。別人家的壯年牛,皮毛發(fā)亮到全身曲線一體,像緞子一樣順溜光滑。而后我也接替姐姐成為一名早出晚歸的牧童。
母黃牛溫順,有一雙看不出悲喜的大眼睛。那時我剛剛上小學,意識里沒有其他鄉(xiāng)鄰那樣把牛放進深山吃肥草,還能挑一擔柴回家的勤奮。經(jīng)常是和隔壁的小伙伴把牛放在離家不遠的河對岸或田野,不敢去太遠的地方。反正我把牛兒牽到哪兒,牛兒就會吃在哪兒。偶爾它偷吃了一點路邊正拔節(jié)的稻子,我會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因為我想我的牛吃得好一點飽一點。
初春有紫云英的季節(jié),是牧童輕松的時候,也是牛兒最幸福的時候。茂盛如地毯一樣鋪在稻田里濕漉漉的紫云英,是稻田的有機肥,更是牛兒最喜食的。
夜幕降臨的時候,村口傳來“咚——咚——咚——”的節(jié)奏聲,就像籃球拍在地上的回響。有小伙伴奔走相告,誰誰家的牛吃了斑蝥,正在救治。斑蝥是一種生活在田塍和土墻間的昆蟲。牛兒吃草時不小心驚動了它,就會釋放出一種毒素,使牛的肚子越來越脹直至脹死為止。大人們每每發(fā)現(xiàn)牛兒中了斑蝥的毒,便會趕著牛兒滿村走,不停地用草鞋在脹成鼓的牛肚子上拍打。而這種傳統(tǒng)的土辦法救回牛命的只在少數(shù)。第二天看著沒有了牛的孤單小伙伴,心里便充滿了同情,同時也后怕,慶幸自己的牛還好沒吃到斑蝥。對于斑蝥,放牛娃是一致譴責和痛恨的。
我家的黃牛在田里拉犁耙干活慢,但能生牛崽。忘了到我們家多久后,黃牛做了媽媽。小黃牛長得和她媽媽一樣漂亮,奶聲奶氣斷斷續(xù)續(xù)地喊著“哞、哞”。雖然沒長牙但經(jīng)常會銜著幾根草磨牙,我會找些細嫩的紅薯根逗它,給它磨牙,有時它甚至把我的手指頭也當成磨牙棒,跑過來用濡濕的小嘴唇咬我的指頭。牛媽媽的奶水少,父親有時會買來奶粉,用奶嘴灌給小牛吃。后來大概到了斷奶的時候,每次小牛兒鉆到媽媽身下想要吃奶,牛媽媽都會用后腿踢它。每當這種時候我就想父親多買一些奶粉給小牛吃。但那個年代別說牛,人也才剛剛過上溫飽的日子。我只能經(jīng)常抱著小牛和它說話,用自己的少不更事去安撫另一個稚嫩的生靈。
一天下午,把牛媽媽和小牛一起放在了河對岸,因為天突然下起了雨,我便自己過河回了家。黃昏的時候,雨突然滂沱而下,河里的水瞬間就漲了起來,我急忙等在河這邊呼喊牛兒回家。不一會兒就見到牛媽媽和小牛隨著村子里的其他牛出現(xiàn)在對岸河畔蹚河回來。
快到河中間的時候,水已漫過了牛媽媽的脊背,只能看見小牛仰著的頭浮在水面上。我揪心地使勁喊:小牛你別被水沖走了,你要跟著你姆媽。那一刻我不知有多自責把牛兒放到河對岸去。慶幸的是牛媽媽一直用自己的身子擋在上游,小牛在媽媽的護衛(wèi)下,有驚無險地游了過來。我用手把小牛身上的水一行一行篦干,八九歲的人生中第一次有了一種叫心疼的感覺。抱著它的頭我自言自語“再不讓你這樣危險了”,擦干眼淚放下心領(lǐng)著它們回牛欄。不知道當時小牛清澈的眼中是不是倒映了我的愧疚和擔心。此后在下雨的時候,放牛就特別小心翼翼,而小牛也在漸漸長大。
在小牛長成牛犢的某一天,放學回家去放牛時,我發(fā)現(xiàn)牛欄里只剩下了牛媽媽。我問母親小牛去哪兒了,母親有點支支吾吾。我猛然想到小伙伴家中小牛被賣的情形。鄉(xiāng)里人在牛長大后,是用牛繩拴牢穿過牛鼻子的嚼子牽牛,而牛犢則是用一個類似于馬轡頭的繩結(jié)套住牛頭牽著。那次小伙伴家的小牛犢被賣時,我看見小牛犢被陌生人牽著轡頭,它掙扎著怎樣也不配合,甚至用還未長全的角頂來頂去,就想留在牛媽媽身邊,后來被強行拉走后,還總是倔強地不停回頭朝著牛媽媽呼喚“哞——哞——”。想著我的小牛被陌生人牽走的樣子,不禁一邊傷心地哭著,一邊不依不饒地質(zhì)問母親:“我的小牛是不是也這樣了?說呀……”
母親被我糾纏煩了,說:“我們家只需要一頭牛,賣小牛的錢正好供你們讀書……”家中清貧,姐弟五個都在上學,小牛的身價正好換回我們讀書的錢。這是我幼年時少有的“理直氣壯”地沖撞母親,當時覺得自己太小,為父母賣牛的事感到既無奈又生氣,賭了好多天氣沒和母親說話。其實又能如何?村中小伙伴也有和我一樣的,都是哭哭鬧鬧后由著父母去,那不過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不懂人世間悲辛為何物。
再后來,我初中快畢業(yè)的時候,家中徹底缺少一個放牛娃,母牛也在一個我放學回家的周末,被父母告知賣給了陌生人。從此,牛和田野遠離了我的生活。
還記得小時候在我們家對面千米遠的公路邊就有個磚瓦廠。那時由于沒有機械和泥,都是用牛踩的。磚瓦廠買來的都是有力氣的水牛,水牛在磚瓦廠的勞動強度比在農(nóng)民手里要強上很多倍,每日在沒至膝上介于澇和硬之間的深泥里不停地踩,直到把陶泥與水和勻稱,可以進入瓦的磨具為止,接著進入下一輪。可很多水牛等不到這時就由于體力透支而殞命,所以要不了幾天就會聽人說:“磚瓦廠又倒牛了!”
若干年之后回老家,經(jīng)過磚瓦廠舊址時,姐姐突然說道:“小時候每聽到這磚瓦廠倒牛的消息,我會偷偷傷心,害怕是我的那頭小水牛被賣到了這里……”那一刻,我們都不約而同地沉默了。
這些年看到豐茂的水草,我和姐姐一樣,還是會想起童年時我們放過的牛。即便是如今偶遇割草機在公園割草時,那些斷裂后散發(fā)出的青澀草腥味,像牛吃草時的味道,依然使我瞬間想起小時候在蠓蠅飛舞頭頂?shù)囊巴猓c牛在一起的那種自由和滿足。
自幼年時牽起那根牛繩,便一端是牛,另一端是我們,姐姐的夢便是心有所系。牛兒治愈了清貧年代物資缺失的童年,溫暖著姐姐離家多年的夢里鄉(xiāng)愁,它是過去時代農(nóng)村孩子的寵物,更是讓“人之初”的我們品嘗到別離的憂傷。那些關(guān)于牛的往事以脊梁的樣子橫亙在人生的山峰,無論多久,一回頭總能看見。而在曾經(jīng)是放牛娃的我們的半生路程中,就算最感疲乏的時候,也不愿意用“累得像牛一樣”來形容。只有放過牛的人才知道,人永遠比不上牛吃苦耐勞不知索取的精神,那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給予人世間無與倫比的付出。
如今在街邊有時會看到一些以雍容華貴姿態(tài)抱著洋寵物的孩子,總會令我想起與牛在一起時的溫情,以及農(nóng)村孩子蓬頭垢面的卑微與自在。或許那些孩子的父母和我一樣,童年里有一只叫“賽虎”或是“來旺”的中華田園狗狗,搖著尾巴跟隨,每天牽著或騎著的水牛或黃牛,風雨無阻地與自己一同依偎放養(yǎng)在廣闊的鄉(xiāng)野天地。而在逃離了襤褸的鄉(xiāng)土后,又總一次次在清醒或夢幻中被那根牛繩牽引,憶起那堅守著一個家庭興衰的脈動,教會幼小的我們愛與被愛的忠誠,仰望一種生而為人最值得擁有的任勞任怨、開拓奉獻的品質(zh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