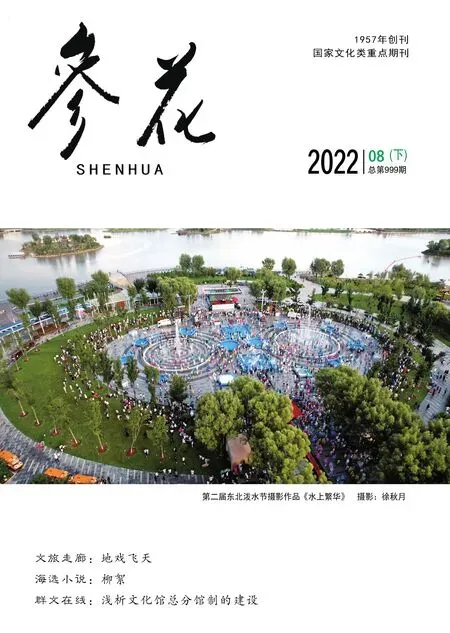鹽背佬兒寫對聯
◎嚴共昭
有個壩子,叫徐家壩。說它是壩子,就因為雞心嶺至大寧鹽場的古鹽道上,就那么一處略微開闊的峽谷。壩子里散落著幾十戶人家,大戶徐姓,專為鹽夫開辦了幺店子,壩子也因此叫徐家壩。
六月的大寧河,豐盈流溢,激流拍岸,濤聲澎湃。岸邊的徐家大戶,人進人出,喧鬧聲、犬吠聲、雞鳴聲,響徹山谷。就像一曲交響樂,鬧熱了整個壩子。
龔海濤一行五人,估計徐家在辦喜事,為不打擾他們,便在院壩左側的石坎上歇息,等待徐老板出來,安排晚飯和宿營。矮小、肥胖卻滿臉紅光的徐老板,見是老雇主來臨,企鵝似的迎了上去:“真是對不起,今天家里辦喜事兒,曉得近兩天你們要來,我都提前聯系好了,你們就委屈一下,隨我去張家住一宿吧,店子錢我來出。”幾個鹽背佬兒來到院壩,用打杵歇好背子,蹬著八字步,山一樣巋然不動。他們并沒看見,徐老板合不攏的大嘴和猛然間皺起的額頭,更沒聽見徐老板說了些啥。原來是寫婚聯的先生,吸引了他們。徐老板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又是抓頭,又是跺腳,“個老子的,你們說句話啊!”
幾個鹽背佬兒,終于開口了,你一句我一句,說得哈哈大笑。
“喜字的嘴巴好大呀,像一個山洞。”“迎字的腿子像瘸子,站都站不穩了。”“你沒看那副對子,上面全是雞腳腳!”
院壩中間,擺放著一張用門板搭起的案子,秀才邊寫對子,邊安排幫忙的小伙子,用石頭壓好對聯。就剩家神了,他伸伸懶腰,心里想著熱鬧的牌場子。他是遠近有名的秀才,窮家小戶是請不動他的。每次寫完對子,都會滿意地自我欣賞一番,然后在一片贊賞聲中步入牌場。就在這時,幾個平利八仙的鹽背佬兒來了,對他滿是嘲笑,秀才氣得臉紅脖子粗,一甩手,走人了。徐老板氣得鴨母浮水樣手足頓挫:“你們這是做啥子,趕快給他道錯,把他給我請回來!”幾個鹽背佬兒不但沒有道錯的意思,反倒笑得死去活來。徐老板怒目圓睜,渾身打戰,手指鹽背佬兒:“不給我請回來,你們就給我寫!”
“好啊,寫就寫,就選個字兒寫得最丑的吧!老龔,你去!”
徐老板張大嘴巴,貓著腰:“你們真會寫啊!”
幾個鹽背佬兒放下背子:“拿紙來啊!”
老龔拉開八字步,擺開架勢:“寫對聯啊,是有講究的,首先要寫中堂,然后是大門,如果把中堂放在后面,會得罪祖先的……”
本來書畫都要凝神靜氣,可寫對聯對于老龔來說,只是小兒科,說話間家神已寫好,筆筆圓潤渾厚,粗細錯落得體,字字靈動欲飛,大小搭配有致,圍觀者無不豎起大拇指:“鹽背佬兒還會寫對子,真是了不起!”
“那么高的文化還背鹽,真是可惜啊!”
愛吹牛的老肖,總能在最佳時刻,極其夸張地把熱鬧推向巔峰。老肖把手舉過頭頂,左右擺動著,示意大家靜一靜:“其實啊,我們這幾個,他的文化最低,你看他老實巴交的樣子,像個文人嗎?你們還說他背鹽可惜了,這點文化在我們陜西就只能當背佬兒。”
鬧了半天,徐老板才在驚訝中醒來,“哎呀,你看我嘛,都忘了給先生裝煙了,狗娃子額,趕快給客人倒茶!”板凳換成了椅子,瓜子、糖果也上了,“你們慢用啊!”徐老板滿臉堆笑,忙進忙出,好像早就忘了秀才被氣走的事。
幾個鹽背佬兒被奉為座上賓,吃得酒醉飯飽,老肖拍拍鼓鼓的肚皮:“徐老板,我們去張家哦!”
徐老板十分尷尬,“這有地方,莫多心嘛!”
鳥兒嘰嘰喳喳,鬧熱了整個壩子。喝多了的鹽背佬兒,卻懶得起床,多少年沒睡過懶覺了,正好享受享受。其實,要不是因為徐家壩的婚俗,沒吃到新娘的喜糖喜煙不能離去,無論如何,都該上路了。
“咋得了啊,挨千刀的!”院子里一片嘈雜,像被捅了馬蜂窩。幾個鹽背佬兒,睡意全無,匆匆起床。原來,門上、窗子上的對聯,不翼而飛,有人說那個秀才,天黑了還悄悄來過,說不定是他扯去當字帖了。
“趕緊去買紙!”徐老板氣得泡泡顫。
看來,想走也走不了啦,新娘進門前必須把對子貼上啊。天公也不作美,這天下午就稀里嘩啦地下起了瓢潑大雨,一下就是三天,鹽背佬兒們急得雙腳跳。老肖找到徐老板:“要不是給你寫什么對聯,我們都上雞心嶺了,耽誤了工夫,家里人也著急,你看咋辦啊!”
徐老板滿臉堆笑:“好說,好說,這兩天的工錢我補上,天晴了我找幾個人把你們送上雞心嶺!”
吃了,喝了,還有工錢,最難爬的山道也當上了甩手掌柜,幾個鹽背佬兒就像考中狀元一樣,滿頭滿臉全是喜氣。上了雞心嶺,便是下坡路,歸心似箭的鹽背佬兒,很快消失在密林深處,而鹽背佬兒寫對聯的新鮮事兒,卻在鹽道上一路傳開。再次踏上艱險的秦巴古鹽道,已是秋高氣爽。紛紛飄落的秋葉,勾起了老龔無盡的愁緒。母親病了,兒女們要上學,一家老小的生計,都靠他這瘦弱的雙肩,可自己天生體弱,背一次鹽,就累得像大病一場,該是如何是好啊。可他萬萬沒有想到,他的鹽背佬兒生涯,就此畫上了大大的句號。
“那個寫對聯的鹽背佬兒來了!”孩子們奔走相告。原來,老龔走后要寫對聯的人,就招呼孩子們,一旦發現他,趕快轉告。就這樣,一家寫完了,寫二家,婚聯、挽幛、春聯、門牌、家書,一直忙到臘月底。
“明年再過來哦!”積雪的嚓嚓聲,伴隨著沿途百姓的送別聲,就像好聽的山歌,聽得老龔渾身是勁,路也不像以前那樣難走,那樣遠了,好像雞心嶺就在眼前,家也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