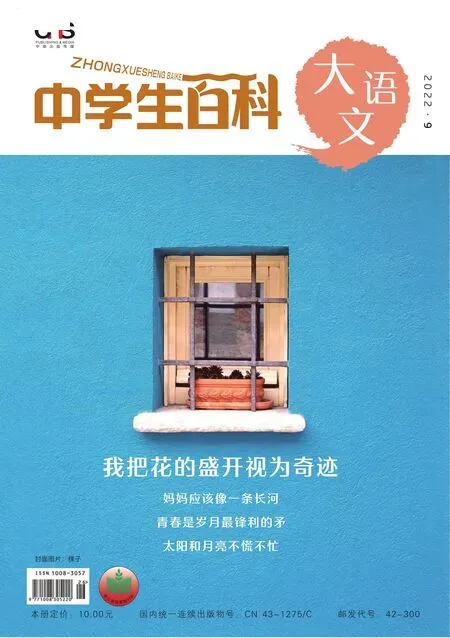從體內(nèi)破土而出的春天
文|仇士鵬
我對(duì)竹筍的印象,一直是勵(lì)志和積極的。
在黑暗中積累了一季的力量,竹筍用根握緊了大地的脈動(dòng)。正所謂厚積而薄發(fā),當(dāng)春雨灑落,它便猛地抬頭,捅破大地,一躍而上。或許從螞蟻的視角來看,那就如一座座巍峨的金字塔拔地而起,直入云霄。
高中時(shí)一位同學(xué)很喜歡竹筍,不僅在課桌、墻邊貼滿了竹筍的卡通照片,還寫下座右銘“像竹筍一樣,一鳴驚人”。他也是這么做的。
在高一,他算是班里的“拖油瓶”,時(shí)常掛在成績(jī)單的最后一名。那應(yīng)當(dāng)是他生命里的冬天。他學(xué)習(xí)基礎(chǔ)很薄弱,聽課時(shí)經(jīng)常掉線,但他并沒有自甘墮落,和頑劣者沆瀣一氣,而是如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竹子一般,牢牢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無論我什么時(shí)候看他,他都在低頭刷題。終于,在高二摸底考的時(shí)候,他沖入了班里的前二十;在高三,更是直接邁入了年級(jí)前十。那時(shí)候,他已經(jīng)從一根不起眼的竹筍,長(zhǎng)成了翠色欲滴的青竹。
他很喜歡吃竹筍,尤其喜歡吃竹筍炒肉,素雅和葷腥相遇,鮮味便在猛烈中有了更加悠久的余韻。《詩經(jīng)》有言:“其蔌維何?維筍及蒲。”竹筍雖是幼年期的竹子,卻有極佳的口感。“長(zhǎng)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只有親口品嘗了竹筍的滋味,才能真正明白蘇東坡流連忘返的原因,才會(huì)理解陸游“味抵駝峰牛尾貍”的感嘆。竹筍炒肉和酸辣土豆絲作為當(dāng)年我們食堂里的常客,也成了我們青春回憶里一枚盤子大小的印章。想來,竹筍確實(shí)很像那時(shí)候的我們,青澀而又灰頭土臉,未來的光芒都還在體內(nèi)深藏,我們自以為的伶俐,在如今看來也是如此笨拙而又天真。
“嘴尖皮厚腹中空”,竹筍著實(shí)其貌不揚(yáng)。母親時(shí)常對(duì)我開玩笑說:“你以后要像竹筍一樣,做事有沖勁,但又不招搖。”她說,不能像花花草草那樣,個(gè)子長(zhǎng)不高,心思全都放在花香上了。看看竹筍,不妖不艷,踏踏實(shí)實(shí),長(zhǎng)大后還十分虛心。當(dāng)然,還要有足夠厚的臉皮。每次下雨后,竹筍就一個(gè)趕著一個(gè)地冒了出來——它們只會(huì)把謙遜留給大地和陽光,卻絕不會(huì)把生存的機(jī)會(huì)拱手讓人。早一點(diǎn)破土,多長(zhǎng)高一點(diǎn),就能吸收到更多雨露。
母親說她以前因?yàn)楹π撸e(cuò)失了某次上臺(tái)的機(jī)會(huì),單位領(lǐng)導(dǎo)因此便沒能發(fā)現(xiàn)她這匹“千里馬”。她經(jīng)常對(duì)我念叨,不管心里多么不好意思,也要像竹筍那樣,該出手時(shí)就出手。不知道竹筍聽到母親的評(píng)價(jià)會(huì)是何種表情?或許在那滿是泥濘的外皮下,也有一張因害羞、緊張而紅撲撲的臉吧。
我最喜歡的,卻是看父親挖竹筍。
長(zhǎng)時(shí)間生活在高樓上,我和竹林之間早已經(jīng)沒有了默契,在竹林里走來走去也發(fā)現(xiàn)不了被泥土抱在懷里的竹筍。而父親不一樣,在鄉(xiāng)野中土生土長(zhǎng)的他,目光一掃,便能找到筍的痕跡,鋤頭一刨,就把竹筍挖了出來。在我看來,這簡(jiǎn)直就是無中生有的魔術(shù)。所以每次和父親上山,都像是一場(chǎng)邂逅驚喜的旅程。我雖然只是一個(gè)旁觀者,也能分到一點(diǎn)竹林的恩澤——當(dāng)母親用山泉水把父親挖到的竹筍做成湯,我一口口地飲,似乎又和自然達(dá)成了默契。因?yàn)檫@時(shí),春天好像也從我體內(nèi),破土而出了。
作者領(lǐng)讀
標(biāo)題《從體內(nèi)破土而出的春天》,既是對(duì)竹筍生長(zhǎng)過程的抽象形容,又帶有喜悅的情感傾向,并能和文末呼應(yīng)。許是考慮到可能以偏概全,考試時(shí)用的是更穩(wěn)妥的《竹筍印象》。但從寫作的角度,我仍建議對(duì)標(biāo)題精雕細(xì)琢,因?yàn)闃?biāo)題是第一印象。一個(gè)彰顯寫作水平、知識(shí)積累和文化修養(yǎng)的標(biāo)題能讓人眼前一亮。此文若最初以《竹筍印象》為標(biāo)題,未必能被選中。
寫下這篇文章,是一個(gè)意外。那天我看到一段挖竹筍的短視頻,這種在城市中已經(jīng)消失匿跡、漸漸退居時(shí)代舞臺(tái)的邊緣卻極具生存美學(xué)的活動(dòng),立刻喚起了我的鄉(xiāng)愁。透過視頻的像素依舊能感受到的雨后濕漉漉的清風(fēng),青蔥葳蕤的新綠,頓時(shí)讓我想到了童年和青春,想到了古典、浪漫與美好的一切。借著這份情感的沖擊,我有了寫作的念頭。我試圖通過文字,找到“從體內(nèi)破土而出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