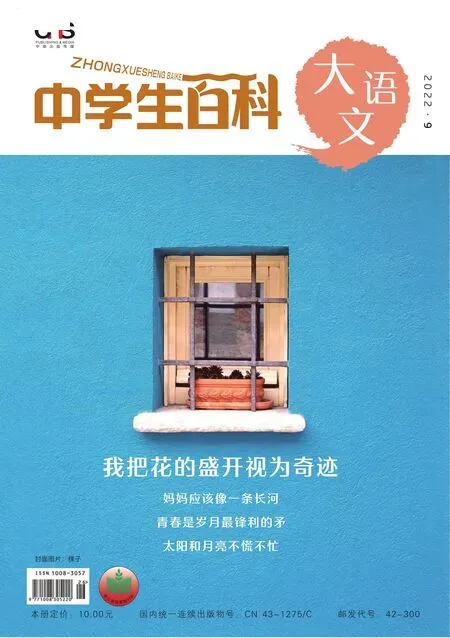青春是歲月最鋒利的矛
文|仇士鵬

我曾無數次在網上刷到北大的課堂與實驗室,尤其是在韋東奕火了后,經常能刷到他的教學視頻,但我從來不看;在一家網絡課程平臺上有很多清華北大的課程,但我從來不學。
有一個潛在的聲音告訴我:沒必要!我們是兩個世界的人,雖然共存于同樣的天地之間,但我們并不會相遇,并不會產生交集。無數人終其一生都不會進入“清北”的校園里,哪怕只是旅游。我也是其中的一個。
剛剛,我卻生出了深深的遺憾,因為刷到了北大夜奔的視頻——操場上豎著大屏幕,播放一個歌手的演唱會片段,清亮的音色在空曠的操場上盤桓著,隱隱的回聲賦予了它更悠揚的韻味。黑壓壓的人群在操場上一圈圈地奔跑,所有的喘息聲都收攏在輕快的節奏中。
在北大官方發布的回放視頻里,他們聚在一起高舉著手機,打開閃光燈,齊聲唱著《當我們一起走過》。身后的高樓變得無比遙遠,每個人的眼中都有明亮的光點。這才是我高中時所暢想的大學時光,也是我在渾渾噩噩中走到今天才驚覺錯過了的最好的青春。我后悔了。
想來,只有對青春的懷想,才能擊潰一個在社會中練出了厚厚盔甲的成年人。
看過一則視頻——在美國邁阿密的一場庭審中,身材魁梧的嫌犯原本背著手,昂著頭,擺出一副無所謂的表情,甚至還有幾分不屑。但當女法官突然問起,他是否在某所中學讀過初中時,他迅速認出了臺上的法官居然是曾經的同學。他先是尷尬一笑,然后用手捂住了臉。在法官陳述他以前是多么善良、多么優異時,他低下了頭,揉著眼睛,搓著臉。那一刻,他的冷酷和蠻橫變得不堪一擊。
曾經,我們在一起踢球,在一起讀書,可后來,我們漸行漸遠,失去了聯絡,失去了相伴的腳步。仿佛畢業是一個岔路口,連通著兩個互不接壤的世界。無法改變的是,我們的生命總歸有著一塊小小的重合,飛鳥與螞蟻認領同樣的青春的印記。可正是這種一樣,將現在的不一樣襯托得愈發刺眼。
我的初中同學高二就保送了清華,我的本科同學也保研去了清華,一個師弟轉博成功,跟了院士……我的身邊從不缺少魚躍龍門的故事,他們是平凡的傳奇,也是尋常的奇跡。而“他們”這個詞中,從不包含“我”。
原本一起聽著《當我們一起走過》的人,如今有的在北大校園里用響亮的青春高歌,天上沒有星光,地上卻有無數冉冉升起的星子。而有的人在一間小小的宿舍里,撐著金魚般的眼睛,修改被退稿的論文。有的人未來有無限的可能,有的人年紀輕輕,就仿佛能望見生命的盡頭。
所以我遺憾我的自甘墮落,遺憾我的懶惰與懈怠,遺憾我沉迷在一些無謂的庸俗的快樂里。當別的麻雀努力練習鳳凰的飛行技巧時,我卻一點點把自己喂得肥胖,直到跌落在地,成為圓滾滾的土雞。無數個“如果”在喉嚨里冒著泡,卻只能一個個地咽下。
所以我想說,為了在一個有大屏幕和音響的操場上,為了在溫柔的晚風里,和一群人奔跑和歡唱,請你在現在的青春拼盡全力地奔跑。當你再次聽到“天上風箏在天上飛,地上人兒在地上追”,你應當是一只快樂的風箏,而不是像我這樣灰頭土臉,在彌散的灰塵中上氣不接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