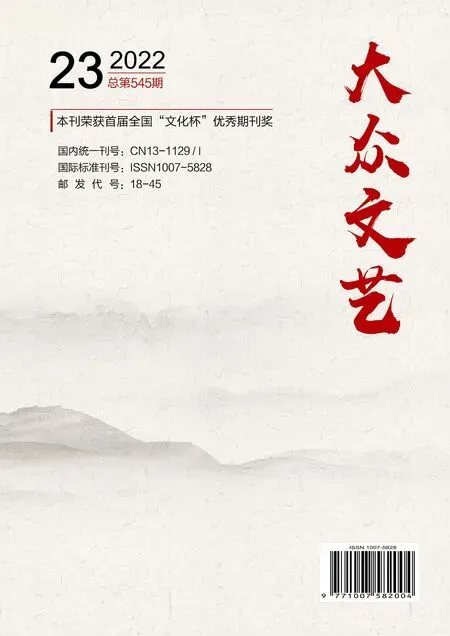仰鉆先匠 外師造化
——淺談張友憲的創作歷程
溫澤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江蘇南京 210000)
李可染曾說學習山水畫需要三點,一是學習傳統,并廣泛吸收中外藝術的長處;二是到生活中去、到祖國的壯麗山河中去寫生;第三是集中生活資料,進行創作。[1]張友憲老師繼承傳統,多年來在中國畫傳統領域深耕,學習中國畫傳統中的美術發展史、傳統美學與傳統技法,傳承中國藝術精神,又不陷傳統窠臼。在面對西方藝術思潮沖擊下,他以造化為師,游歷中外,學習西方印象派與抽象表現主義等藝術流派,博采眾長后終自成一家。
一、堅守正脈
中國文化重視“道統”,“道統”一詞是由朱熹首先提出的,用來指代儒家傳道的脈絡和系統。同樣,在繪畫領域同樣重視“道統”,即將繪畫觀念與歷史上的師承譜系結合在一起。明代董其昌在《畫禪室隨筆》中提出“畫分南北二宗”,至此畫史譜系逐漸構成。中國繪畫藝術以文人畫為代表,文人畫自唐代王維始,發展到清初,南宗一脈籠罩畫壇,其逐漸被稱為“正脈”。張友憲老師說:“有人稱贊我的畫,為堅持中國畫繪事之正脈者……”,從他的畫跋中,可知他崇尚趙孟頫、元四家、吳昌碩、黃賓虹、劉海粟等,這些古今大師,基本上是沿著文人畫派系傳承下來的,張老師堅守的便是這一“正脈”。
中國畫之所以為中國畫,與筆墨本身所形成的審美價值密不可分。張友憲老師曾談論繪畫作品中藝術品與工藝品的差別,差別就在工藝品沒有繪畫性上。中國畫不是靠畫,而是靠寫。其中“寫”字又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層是書寫性,即書法用筆;第二層是宣泄性,“寫”“瀉”二字,古時通用,即情感發泄之意。具備了這兩點,就具有繪畫性。而書寫性和渲瀉性,是不穩定的,具有變化性,作畫有了繪畫性,其作品自然千姿百態。而工藝性制作,講究制作程序,及程式化的藝術語言,作品美觀不成問題,但其作品總難免會有似曾相識之感。
“寫”的第一層意思中,張友憲強調以書入畫的藝術主張。張友憲老師稱:“畫道之功,歸乎用筆,用筆之道,千古不易,此中國畫所以有別于西洋畫。”中國畫的核心在“寫”,故古代畫論強調“以形寫神”,而非“畫”神,只有通過“寫”才更好的傳神。唐代張彥遠說:“骨氣、形似皆本于立意而歸乎用筆,故工畫者多善書。”南齊謝赫在《古畫品錄》中提出“繪畫六法”,其中便含“骨法用筆”,“骨法用筆”是“六法”中相當重要的一法,同時是中國繪畫的特征,骨法歸之于用筆,是用筆的結果,也就是骨的表現方法在于用筆。五代后梁荊浩在《筆法記》中提出“氣、韻、思、景、筆、墨”為“畫之六要”,以及“筆之四勢”:筋、肉、骨、氣,由此建立了評判用筆優劣的標準,更為中國畫用線造型提供了參考標準。北宋郭熙在《林泉高致》中也談到了書畫相通,曰:“人之學畫,無異學書。”他還提出為了繪畫過程中用筆熟練,可以“近取諸書法”。張彥遠以人物畫立論,郭熙是以山水畫闡釋。到了元代,趙孟頫力主書法入畫,他將“書法結合”進一步擴展到了花卉竹石領域。他在《秀石疏林圖》卷后題詩云:“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應八法通。若也有人能會此,須知書畫本來同。”趙孟頫本身書法造詣極高,他用筆跡蒼勁的飛白法寫石,用筆法沖鋒、點劃凝重的篆法寫木,寫竹更是要和各種書法相通,他對“書畫同源”的論述更加鞭辟入里。
中國畫的這些用筆用墨的技巧被張友憲老師所承襲,張老師在其著作《二乾書屋畫跋》中反復提及以書入畫的主張,認為“惟有書法用筆產生的線條才能稱之為‘中國畫的線條’”,繼而將竹作為創作的對象,以磨練筆法,張老師畫芭蕉、起筆流暢、意在筆先,行筆沉澀、力透紙背,收筆時卻戛然而止,這在筆法中叫做“硬斷”。同時,張老師作畫,筆在紙上摩擦有聲,宛若“筆落春蠶食葉聲”,可見筆墨功力達到了很高的境界。
第二層中的宣泄性,就是通過作畫宣泄某種情感。這與古代畫論中的“逸氣說”相通,倪瓚“聊以寫胸中逸氣耳”不就是通過畫竹抒發自身的情感嗎?“逸”字溯其緣起,東漢黃慎《說文解字》:“逸,失也,從辵兔,兔謾訑善逃也。”最原始的含義是逃跑,后引申為隱逸、超逸,特指精神境界的超脫。魏晉時期,“逸”字曾被廣泛應用于人物品藻、文學評論中,第一個將“逸”應用到書畫領域的是唐代李嗣真,他在《書后品》中評價鐘繇、張芝、王羲之、王獻之四位書家說:“鐘張羲獻,超然逸品”,其后唐朱景玄、宋黃修復用“逸品”品評畫家,但“逸品”畫風并未占據繪畫領域的主導地位。直到宋元時期,倪瓚提出“逸氣”“逸筆”,至此才確立了“逸”最高審美標準的地位。倪瓚認為作畫是個人主觀情緒的表現,是一種生命價值的體現和精神世界的訴求。因此歷代畫論在談論文人畫本質時,都傾向于審美主體感情的抒發,認為畫乃“心性之學”,“逸”字逐漸成為文人畫所代表的藝術精神。張有憲老師也是十分推崇“逸氣說”,他稱畫畫是“興之所至,如鬼使神差,抒之以情,得之于法”[2]繪畫是即興而作,要注重內心情感的表達,“為畫而畫不成畫,有感發泄劣亦佳”這亦可理解為張友憲老師對傳統繪畫美學的一種繼承。
二、融匯中西的筆墨探索
張友憲老師立身于傳統正脈,理性地從西方繪畫經驗和藝術觀念中汲取營養,融匯中西的筆墨探索之路。從二十世紀初開始,中國畫家們對中國畫的態度可分為傳統派、中西結合派和全盤西化派三個派別。張友憲老師無疑處于傳統派中最頑固之列,但他同樣受到中西結合派影響。張友憲老師于20世紀80年代畢業于南京藝術學院中國畫專業,師從劉海粟校長的研究生董欣賓,劉海粟在《上海美專十年回顧》中曾提及創辦上海圖畫美術學校的信條和宗旨,其中第一條便是“我們要發展東方固有的藝術,研究西方藝術的蘊奧”這樣的經歷使得他對西方藝術并不排斥,反而持欣然接受的態度。此外徐悲鴻提出“素描為一切造型藝術之基礎”,來源于西方的素描是研究形象的科學,它可以準確地反映客觀事物,對中國畫的發展大有裨益,它可以成為中國畫家“以形寫神”的手段。故張友憲老師格外重視素描,被譽為“國畫界少有的素描高手”,他的許多幅素描作品都表明了他對西方藝術大師的敬重,尤其還曾精心研究過文藝復興時期的達芬奇、拉斐爾等大師的素描作品,并大量練習過西方繪畫中的明暗、透視、解剖等技巧。
他還提出:“印象派、波洛克,這里面有很好的東西啊,只要有用,拿來就用,管他是中是西!”。張友憲老師喜歡印象派大家塞尚、高更及梵高的作品,他將這些大家所繪名作的精神融匯于自己的創作實踐中,《凡高》(圖1)、《教堂鑲嵌畫》(圖2)兩幅作品便是學習了梵高的用筆方法,采用短小的筆觸排列和個性化的色彩表現,借助筆觸特別是線條的運動趨勢感表現他的感受。他吸收了印象派作品最大的特點:即把所有物體都看做色彩的狀態,在遠處觀看時,看到的是不同顏色混亂的點,而在遠處觀看是,那些混亂的點便會呈現出色彩集合,給人以光的感覺。

圖1 《凡高》

圖2 《教堂鑲嵌畫》
此外,張老師身上還有著抽象表現主義的影子。西方抽象表現主義追求用自由的、純粹的繪畫元素來表現和闡釋這個世界,波洛克創造出“滴畫法”,用木棍等可以利用的材料蘸取顏料,將顏料拋起,任其自然落下,就好像中國畫中的潑墨畫一樣。張老師的《比利時街景》(圖3)、《極樂的特雷莎》(圖4)等作品就是利用了該畫法,看似是任由水墨、顏料自然落在畫作上,其實畫面中的每一筆都飽含著他的情感和思想,最大程度地表現繪畫時內心的活動,從而達到藝術的純粹。

圖3 《比利時街景》

圖4 《極樂的特雷莎》
張友憲老師的繪畫是以固有文化為基礎,在他的作品中,既重視造型又不拘于造型;既堅守傳統陣地又能中西兼容,蘊含著他對中國傳統美學、西方印象派、表現主義的融合。無論作品的表現意圖如何,他都始終將傳統中國畫所注重的意境、氣韻和情趣的表現置于首位,同時又在形象的刻畫及色彩的處理上,吸收借鑒西畫之長。
三、師法自然與歐洲寫生
20世紀以來,外來文化大量引入,同時我們的中國畫也面臨著較大的危機,甚至“中國畫已到了窮途末日的時候”這一說法成為了畫界的時髦話題。當代中國畫處在一個危機與新生的分界點,其危機的表現包含四個方面,1.用筆墨形態的形式語言來作畫,使得中國畫的形式規范愈發嚴密,造成一些畫家停止了在繪畫觀念上的創新,為傳統所囿,不能自出手眼,僅能使用千篇一律的技藝去追求所謂的意境。2.技法表現僅停留在特技和制作層面,使用各種特殊材料來表現畫面效果,如揉紙、噴涂等等,僅僅依靠這些方法而不尋求有意義的創造,其作品也僅能稱得上工藝品。3.以歷代繪畫大師為師法對象或乞求用他們的技法為基礎進而得以提升,他們并沒有從根本上理解傳統中國畫的精神,僅僅學習前輩畫家的某種技法,然后七拼八湊地搬到自己的作品中。4.以自然為師法對象企圖在感受造化中謀以突破,他們作畫的表現內容也趨于雷同,無外乎三山、五岳、高原、大漠,中國已然遍地都是他們的足跡,作畫效果也漸趨平淡無味。中國的畫家們曾努力拓寬傳統文人畫的取材范圍,如海派畫家趙之謙,畫熱帶、亞熱帶的芭蕉、荔枝等,拓寬了傳統花卉題材;齊白石更是將草蟲、算盤等傳統文人畫眼中十分俗氣的事物納入他的畫題。
為了應對中國畫的危機,擴寬中國畫表現領域,現當代大量畫家赴歐洲寫生,以中國畫的表現形式描繪域外事物,自20世紀50年代始,傅抱石、李可染、關山月、劉懋善等,先后出訪國外寫生,創作了一批表現異域風格的杰出作品。張老師也積極赴域外寫生創作,他將東方的水墨與西方的色彩相融合,構建了一條異國風韻畫的長廊。
中國畫面對西畫的沖擊,遂著意起“寫生”。從現代繪畫中的“寫生”語義來看,指面對客觀對象的作畫方式,該詞來自于西方繪畫體系,重寫實。其實“寫生”的繪畫傳統在中國古代早已有之,如五代畫家荊浩“隱居于太行山之洪谷……嘗攜筆寫生數萬本。”唐代畫家張璪提出了“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繪畫思想,其中“造化”是指自然事物,“心源”是指內心感悟,提醒畫家要注重對外在自然事物的真實感受與體驗,更重寫意。北宋范寬亦強調師法自然造化,他認為:“前人之法,未嘗不近取諸物。”與其師法前人,不如以自然為師,這與韓幹:“臣自有師,陛下內廄馬,皆臣之師。”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們認為自然中的真實物象就是最好的老師,因此不必循前人之法。元代趙孟頫也曾說:“久知圖畫非兒戲,到處云山是我師”。明代王履游華山,見到大自然奇秀之景后感悟到繪畫應師造化,他在《華山圖序》中說“吾師心、心師目、目師華山”,繼承了先輩重視師法造化的傳統,力推寫生,師法造化,清代石濤有“搜盡奇峰打草稿”的名言,他在《黃山圖》中題道:“黃山是我師,我是黃山友”,石濤之所以名垂畫史,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游歷名山大川。這些記載說明我國古代畫家主張藝術來源于自然,強調師自然。
千百年來,中國畫藝術經久不衰,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件事師法造化的緣故。劉海粟在《畫學上必要之點》一文中,提倡個性解放,主張寫實,師法自然,注重創造等。李可染廣泛游歷中外,進行寫生創作,為他積累了“體悟自然、精讀自然”的體驗,他在《桂林寫生教學筆錄》中提出:“中國的山水畫,自明清以來,臨摹成風,張口閉口擬某家筆意,使山水畫從形式到內容都失去了生命力……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生活,丟掉了造化這個傳統。”[3]張友憲老師深知“外師造化”是藝術創作的源泉,他的《二乾書屋畫跋》將“心師造化,悟道寫生”單獨列為一章節,在其畫跋中也是對該理論反復涵詠,“習畫中竹法,又師門前之竹耳。”既學習前人畫竹技法,又以門前竹子為師,師法自然。他還寫道:“融肉身于造化,存法眼在自然。”張老師認為惟有深入自然對照物象寫生,才能在寫生中追求物我相融的狀態以及在創造中表達自己的情思,他說:“寫生這種作畫方式對我似乎特別適合……有什么交流比面對面交流更直接與真實?寫生更利于明其位置、通其精神。”[4]張老師深知對景寫生在中國畫創作中的重要,這可以直接和所作物象進行情感溝通、生命交流。因此他游覽數國內名山大川,黃山、敬亭山、太行山、五臺山等,甚至歐洲梵蒂岡、巴比松、米蘭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跡,這使他完成了“對景寫生”到“對景創作”的轉變。目之所見,化為內心之自然流露方為“外師造化”的真正要義。
結語
正如李小山所言:“這個時代所最需要的不是那種僅僅能夠繼承文化傳統的藝術家,而是能夠作出劃時代的貢獻的藝術家。我們應該創造這樣一種氣氛:使每個畫家在可以自由探索的基礎上,拋棄嚴格的技術規范和僵化的審美標準,創造出豐富多彩的藝術形式來。”[5]張友憲老師在“師古人、師造化、師心”的道路上,以扎實的藝術功底和知識儲備實現自己的藝術抱負,他既沒有抱住‘國粹’不放,也沒有“全盤西化”,在這個亂花迷眼的時代,正是因為這份勇氣和堅持,才最終讓他在中西方藝術長廊中閑庭信步,泰然自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