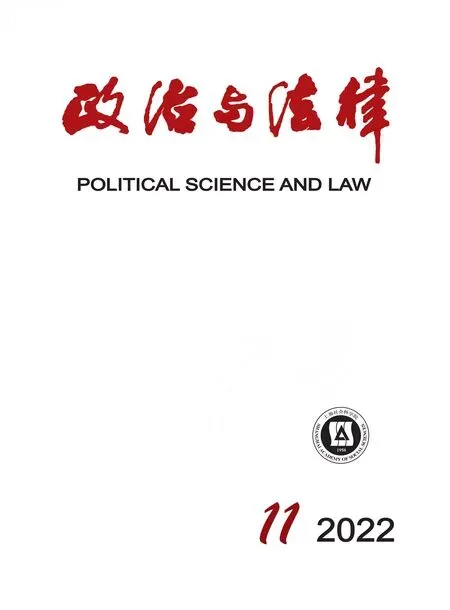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履行判斷和責任承擔*
——基于834份裁判文書的分析
李 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北京 100191)
一、問題的提出
作為現代金融法的一項重要制度,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核心要義是將適當的金融產品或服務銷售給合適的客戶。我國法在2005年《商業銀行個人理財業務管理暫行辦法》第37條、2008年《證券公司監督管理條例》第29條、2015年《證券投資基金法》第98條、2018年《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資管新規》)第6條、2019年《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以下簡稱:《九民紀要》)第72條至第78條、2019年《證券法》第88條等規范中明確規定了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但是,其中存在不少內容沖突、適用分歧、理論誤解。
我國法目前關于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規定政出多門,分散零亂、要求不一的現象明顯。譬如,對集合資金信托計劃、資產管理計劃、投連險、證券投資基金等同質金融產品存在不同的監管規則。〔1〕參見季奎明:《論金融理財產品法律規范的統一適用》,載《環球法律評論》2016年第6期。又如,在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內容上,《資管新規》《證券法》《證券投資基金法》等規定了不同的具體范疇。這些規范的種種不足,無疑直接給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司法適用帶來不同裁判尺度和標準。盡管對某一法律制度存在差異化認識和司法上的適用分歧是一種客觀現象和常態,但統一適用法律、規范裁量權的行使仍是當事人權益保障和公平正義實現的價值追求。
總體而言,既有研究對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探討較為多元、豐富,特別是主張統一風險評級標準、出臺統一管理辦法、強化損失賠償計算方式的懲罰屬性等建議,〔2〕參見任自力:《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規范邏輯》,載《法律適用》2022年第2期;馮輝:《實質法治理念下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法律構造》,載《法學》2022年第7期。無疑是解決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制度痛點的良方。與此同時,目前的討論又存在如下不足:其一,在內容上,目前理論研究偏向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制度前端內容,對義務履行、責任承擔等后端內容仍有待進一步探究。其二,在方法上,目前研究多偏重國際經驗引介,其中不少內容為我國法律所借鑒、汲取,但對本土的實證研究關注不夠,特別是對新近司法適用動態研究偏少,也缺乏圍繞該義務履行判斷的具體研究。〔3〕譬如,有實證研究是以商業銀行代銷理財業務或者履行對象作為研究對象。參見王銳:《適當性義務責任主體范圍演進的實證研究》,載《中國應用法學》2021年第4期。又如,有研究以45個樣本作為研究對象。參見黃輝:《金融機構的投資者適當性義務:實證研究與完善建議》,載《法學評論》2021年第2期。其三,在進路上,既有研究多通過分析目前制度不足,偏向從立法論視角提出改進建議,而在解釋論框架下對司法適用困境及其成因、解釋、消解的研究,仍有待深入。
從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最新司法適用來看,涉及的爭議點有未根據客戶風險承受能力推薦銷售相應風險等級產品、〔4〕參見“陳水鑫與上海鉅派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等其他合同糾紛案”,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2021)滬0115民初10966號民事判決書。承諾保本保收益的欺詐銷售、〔5〕參見“李娜與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邳州支行、鄭天平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案”,江蘇省邳州市人民法院(2019)蘇0382民初8940號民事判決書。未盡說明義務、〔6〕參見“石淑蓮與北京盛世華納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等合同糾紛案”,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13584號民事判決書。客戶投資經驗是否可以減輕或免除賣方責任承擔〔7〕參見“李信德與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新街口支行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案”,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蘇01民終10111號民事判決書。等,但歸納起來,仍圍繞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義務性質、義務履行主體范圍、履行內容及其判斷、民事責任。基于此,筆者于本文中將在既有研究基礎上,通過解釋學方法論,進一步細化、聚焦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履行判斷和責任承擔,探析相應司法適用、理論成因、解釋路徑;在具體研究方法上,采取案例分析等實證研究,挖掘法院裁量思路及其不足,并結合比較法研究,明晰制度定位,以期有助于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司法適用的統一。
二、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司法適用的宏觀樣態及其評析
筆者在“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庫”中,以“適當性義務”作為關鍵詞檢索,共獲得1167份裁判文書,其中有效樣本834份。〔8〕最后檢索更新時間截至2022年7月31日。在這1167份文書中,存在管轄權異議、重復案件、裁定重審、刑事犯罪駁回起訴等與適當性義務適用無關文書333份,不在本文分析范圍內,筆者予以剔除。通過分析這些案件,可探析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司法適用的基本樣態。
(一)義務性質:一般認定為法定義務,主張系先合同義務或合同義務的較少
司法實務對于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性質的認識,分歧明顯。相應爭議主要存在于先合同義務和法定義務之間,認為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為一項合同義務且存在相應違約責任的比較少。其一,將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作為一項法定義務的,占比55.27%;其中,不少法院進一步明確,違反這種法定義務,承擔的是侵權責任,〔9〕如“徐禎弘與平安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豐臺支行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案”,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8)京02民終7731號民事判決書。或者直接依據《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等監管規范中強制性規則做出裁判,并未明確民事責任性質。〔10〕如“曹剛與上海鉅派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等委托理財合同糾紛案”,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2021)滬0115民初35314號民事判決書。其二,采取先合同義務立場的,占比30.10%;法院主要是從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內容看,賣方機構適當性義務是先合同階段的誠信義務,即先合同義務,如違反則承擔締約過失責任。〔11〕參見“深圳前海凱恩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徐建芬金融委托理財合同糾紛案”,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粵03民終26388號民事判決書。其三,有法院認為賣方機構不適當推薦高風險理財產品,履行合同義務存在瑕疵,承擔違約責任,〔12〕如“劉某與廣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方某支行合同糾紛案”,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6044號民事判決書。占比14.63%。

表1 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性質的司法認識分歧
上述裁判呈現的問題如下。
其一,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常發生在合同締約階段,為一項先合同義務,若違反該義務則構成締約過失責任,進而通過締約過失責任規制合同締約階段中的金融產品不當銷售行為。但是,先合同義務本身為一種法定義務,故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立足于法定義務的定性,并不能當然排斥該義務是一種先合同義務。因為現代合同法理論不同于傳統合同法理論,為保護締約的信賴利益,現代合同法以法定義務方式確立了在締約前的先合同義務。更為重要的是,這層性質的界定影響違反該義務的民事責任以及損害賠償的確定。違反作為先合同義務的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承擔締約過失責任,賠償范圍為信賴利益損失,原則上不超過合同訂立時因合同不成立、無效或被撤銷產生的損失,以及不超過合同有效或成立時的履行利益;〔13〕參見謝鴻飛:《合同法學的新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頁。違反作為法定義務的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承擔侵權責任,依侵權救濟路徑展開。
其二,雖然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法定性在司法實踐中得到很多認可和運用,但對于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法定性的判斷,主要是立足于公法層面的法定性,而非私法上的法定性。〔14〕也有研究指出,投資者適當性義務最初是商業道德義務和私法義務,伴隨著金融創新,其成為監管制度中的公法義務。參見翟艷:《我國投資者適當性義務法制化研究》,載《政治與法律》2015年第9期。譬如,《證券投資基金法》第98條規定了適當性義務,但該法在第11章“基金服務機構”和第14章“法律責任”中的第137條規定違反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行政責任。由此可見,該法確立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主要還是立足于公法責任。在公法層面,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是對賣方機構的一種行為監管,且不同監管規則對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有著不同的內容規定。申言之,不只是基金等證券產品銷售存在上述問題,類推觀察其他未在法律層面得到明確的金融產品(如萬能險、投連險、變額年金等)的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亦是如此,相應規則主要限于行政規章、通知、指引等規范性文件中的內容。若違反,主要是進行行政處罰。〔15〕譬如,《人身保險銷售誤導行為認定指引》(保監發〔2012〕87號)第6條規定了七種典型的欺騙行為,如夸大保險責任或者保險產品收益、對保險公司過往經營成果進行虛假宣傳等行為,可認定為《保險法》第116條或者第131條規定的“隱瞞與保險合同有關的重要情況”的行為,依照《保險法》進行處罰。盡管《九民紀要》規定了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違反和救濟方式等具體規則,可對司法裁判產生一定的實質影響,但該紀要形式上并非“司法解釋”,不能作為裁判依據。《資管新規》同樣不能成為金融產品和服務的購買者請求法院予以司法救濟的直接依據。《證券法》第88條也只能適用在典型的證券產品領域,無法適用于銀行理財等其他金融投資商品。
(二)履行主體和義務內容
1.履行主體:以銀行為主的銷售主體
金融產品銷售過程中,通常存在買者(客戶或投資者)、金融中介機構、產品發行人三類主體。對于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履行主體,產品發行人作為合同一方當事人,為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履行的適格主體,并無分歧。但在實踐中,金融產品通常由中介機構進行銷售,其中又以銀行銷售為主。譬如,在樣本案例中,以銀行作為銷售機構的,有380份裁判文書,占45.56%。排列其后的為證券公司、基金公司,也包括一些資產管理公司等其他機構。盡管目前我國法上的規范體系已明確了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但對于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履行主體范圍有一定分歧。典型爭議在于,金融中介機構并非合同當事人,其是否須在締約階段承擔這項嚴苛的義務。譬如,樣本案例中有賣方機構主張,在代銷關系下,其與投資者不直接建立合同關系,不應適用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規則;〔16〕如“徐禎弘與平安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豐臺支行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案”,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8)京02民終7731號民事判決書。并且,違反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是違反了先合同義務,責任性質為締約過失責任,而締約過失責任主體應為簽訂合同的當事人,將責任擴大至銷售機構,不當解釋了《民法典》第500條。〔17〕參見“盧莉、嘉實財富管理有限公司委托理財合同糾紛案”,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2020)滬0115民初4150號民事判決書。由此可見,履行主體(特別是金融中介機構)承擔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理論來源及其責任承擔需要研究者進一步回應。

表2 樣本案件中的賣者主體類型
2.義務內容:多聚焦于“客戶與產品匹配”和“風險揭示”的履行爭議
在目前的規范體系下,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具體內涵該如何認識,會影響是否充分盡到該義務的判斷。以基金銷售的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主要規則為例,不同規范設置了不同的內容范圍(如表3所示)。在法律、部門規章等規范體系視角下,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包括了解客戶、了解產品、客戶與產品相匹配、風險告知等四項內容,其中,《九民紀要》規定的內容最為全面。

表3 基金銷售的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相關主要規則

《證券公司監督管理條例》(國務院令第653號,2014年修訂)第29條√× √ ×《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銀保監會2018年第6號)第26條×× √ √《基金募集機構投資者適當性管理實施指引(試行)》(中基協發〔2017〕4號)第3條 √ √ √ ×《資管新規》(銀發〔2018〕106號)第6條 √ √ √ ×《證券法》第88條 × × √ √《九民紀要》(法〔2019〕254號)第72條 √ √ √ √《公開募集證券投資基金銷售機構監督管理辦法》(證監會令2020年第175號)第17條 √ × √ ×
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規范層面的規定存在差異,司法實務同樣存在內容范圍和履行要點的理解差異。如有人認為,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包括告知說明義務和適當推薦義務,其核心內涵應為風險匹配;〔18〕參見“深圳德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寶英等委托理財合同糾紛案”,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21)粵03民終3484號民事判決書。也有人認為,風險告知說明義務是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核心。〔19〕參見“深圳前海凱恩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徐建芬金融委托理財合同糾紛案”,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粵03民終26388號民事判決書。這種認識差異影響到法院對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履行方式和程度的判斷。譬如,在834個樣本案例中,主要糾紛在于風險揭示和客戶與產品匹配推介義務的履行。有648個案例涉及“風險揭示義務”或“告知說明義務”,主要圍繞風險揭示義務的履行方式和程度問題;500個案例涉及“客戶與產品匹配”,主要是低風險承受能力與購買高風險產品損失引起的訴訟。此外,涉及“了解客戶”和“了解產品”的,分別占比50.00%、46.64%,其爭議是由于賣方機構未能履行風險評估手續而引起的。由此可見,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義務內容是該義務履行判斷的關鍵要素,不同范圍界定將造就不同判斷尺度及相應的法律責任。
(三)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履行的司法判斷:以形式標準為主
如何判斷是否盡到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是金融機構在銷售金融產品或服務過程中義務履行的關鍵議題。對此,司法實踐呈現了三種不同的裁判思路。

表4 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履行的司法判斷標準
其一,形式標準。該標準主要是法院通過投資者是否書面簽字確認或抄寫風險內容,或者金融銷售機構是否履行風險評估等外在客觀的形式審查適當性義務履行與否。從案例樣本推測,實務中,對于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履行,比較多的法院采取形式標準進行判斷,采用該標準的占比達62.47%。其主要思路在于,投資人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在客戶須知和業務回單上簽字確認并購買相應的基金,即應享有投資收益或承擔相應虧損。〔20〕參見“朱保源與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寧明秀西路支行證券投資基金交易糾紛上訴案”,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桂01民終2443號民事判決書。
其二,實質標準。采用該標準的占比14.99%,其主要思路是不以“客戶風險承受能力調查表”“客戶風險承受度評估報告”等評估材料的簽字確認為義務履行的依據,力圖探求客戶實際的風險承受能力、交易真實的意思表示。換言之,即使存在簽字確認等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履行外觀,若產品與客戶不匹配,則未盡到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21〕參見“胡招蓉、德邦創新資本有限責任公司金融委托理財合同糾紛案”,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2020)滬0115民初15501號民事判決書。如有法院指出,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是旨在保護金融消費者購買產品或接受服務時的信賴利益,對該項義務的履行應當予以實質審查而非形式審查。〔22〕參見“深圳德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寶英等委托理財合同糾紛案”,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21)粵03民終3484號民事判決書。
其三,綜合標準。采用該標準的占比22.42%,主要是在形式判斷基礎上,增加對客戶投資風險承擔能力的考量,從理性人能夠理解的客觀標準和投資者能夠理解的主觀標準,來考察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履行。〔23〕參見“巫謝桂霞、深圳宜投基金銷售有限公司等金融委托理財合同糾紛案”,廣東省深圳市前海合作區人民法院(2020)粵0391民初1111號民事判決書。譬如,上海金融法院在相關案件上采取綜合標準,并指出客觀方面包括風險測評、風險揭示簽字確認、電話回訪錄音等信息,主觀方面主要涉及過往投資經歷等信息。〔24〕參見“陳倚丹與上海國金理益財富基金銷售有限公司財產損害賠償糾紛”,上海金融法院(2021)滬74民終1011號民事判決書。
由此可見,司法裁判的不同標準將影響適當性義務的履行程度,并產生“同案不同判”現象,有違法律適用的公正性和權威性。
三、司法適用分歧的理論成因與制度定位
(一)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來源的理論思考與質疑
司法機關對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性質的認識分歧,歸根結底,仍是對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理論基礎或來源存在不同理解。傳統商品交易遵循“買者自負”原則,賣方無須承擔此種義務,但為何在金融產品銷售領域,賣方須承擔該項嚴苛的義務,理論上的相關學說主要有代理理論(the agency theory)、受信義務(fiduciary duty)、招牌理論(the shingle theory)、誠信原則(good faith)等。〔25〕此外,還有投資組合理論(Portfolio Theory)、有效市場理論(The Theory of Efficient Markets)等視角的論證。See Stephen B.Cohen,The Suitability Rule and Economic Theory, 80 Yale Law Journal 1604, 1607-1615(1971).
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最初產生于證券行業,以證券經紀商為規范對象。如在美國法上,調整客戶與經紀商之間關系的法律規則大多來自傳統代理法,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也是如此。〔26〕See Louis Loss, The SEC and the Broker-Dealer, 1 Vanderbilt Law Review 516, 516(1948).代理理論將客戶與證券經紀商形成的法律關系界定為代理關系。這是一種合同關系,強調經紀商作為代理人的注意和忠實義務,也為其履行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提供法理基礎。但是,代理人的義務側重于執行被代理人指令(意思表示),并不要求其須“了解產品”和“產品與客戶匹配”,以及“風險揭示”等內容;特別是在自營業務中,交易商(dealer)并非代理人,代理人所承擔的義務不適用于交易商,也就不能解釋其承擔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合理性。
受信義務理論對此進行了補充。該理論認為,如果某項交易中,委托人基于受托人有信任,對其進行管理財產或行使的權力委托,并且委托人風險源自該委托關系,則受托人承擔受信義務。〔27〕See Tamar Frankel, Fiduciary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4.在自營業務中,交易商與客戶之間的交易契合這層交易結構,其承擔受信義務,要求以客戶利益最大化為目標,推薦證券產品。在該種交易情形中,交易商被賦予交易控制權或濫用被信賴的地位,客戶的委托風險也隨之放大——故受信義務理論又被稱為“特殊境況理論”(the special circumstance theory),而違反受信義務也成為不適當銷售責任承擔最常見的普通法基礎。〔28〕See Roger W.Reinsch, J.Bradley Reich & Nauzer Balsara, Trust Your Broker: Suitability, Modern Portfolio Theory, and Expert Witnesses, 17 St.Thomas Law Review 173, 180(2004).不過,這種私法層面的調整并不足以熨平雙方當事人在專業能力等方面產生的不公平褶皺,故需公權力監管的介入,以矯正利益失衡。
招牌理論對此進行了補充。招牌理論認為,交易商一旦掛出他的招牌(hangs out his shingle),就被默認其能與公眾進行公平地交易(deal fairly with the public),〔29〕See Louis Loss, The SEC and the Broker-Dealer, 1 Vanderbilt Law Review 516, 518(1948).并且有合理的依據相信其所推介的證券對于其顧客而言是合適的。〔30〕See Clifford E.Kirsch ed., Suitability, Variable Annuities and Variable Life Insurance Regulation, Practising Law Institute, 2018, p.35.該理論基礎主要來自證券監管理論,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將這些適合性義務作為券商的基本義務要求,并遵從證券交易法下的10b-5規則(Rule 10b-5)和聯邦證券法下其它反欺詐條款。招牌理論將適合性義務作為一項法定義務,擴大該義務的履行范圍,如金融機構適合性義務的履行主體不再限于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的成員,而是擴大至美國金融業監管局(FINRA)的監管對象。〔31〕See Clifford E.Kirsch ed., Suitability, Variable Annuities and Variable Life Insurance Regulation, Practising Law Institute, 2018, p.14.但該理論是從對金融機構行為監管的角度解讀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并未將金融交易雙方作為一個整體加以探究。〔32〕參見任自力、劉佳:《論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理論基礎與規則完善》,載《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
上述理論從多個維度為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提供了基礎來源,各有側重、互有補充,亦各有不足。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理論主要源自美國,對我國相應理論探討和司法適用亦產生諸多影響和借鑒,但基于國情差異和路徑依賴,上述理論在目前我國法的規范體系下并不能得到有效解釋和適用。
首先,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不應當視為合同義務。從代理理論來觀察適當性義務,其主要困惑在于客戶與銷售機構的法律關系。在代銷關系中,代理人與發行人之間是一種委托代理關系。代理人從事代理行為的法律后果歸屬被代理人,但被代理人的義務是否能夠直接轉為代理人的義務,存在疑問。〔33〕參見“盧莉、嘉實財富管理有限公司委托理財合同糾紛案”,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2020)滬0115民初4150號民事判決書。如果將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視為合同義務,并在代理合同中明確代理人對客戶的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違反即須承擔違約責任,就不無疑問;但合同中未予規定,代理人對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承擔是否能夠作為合同默示條款,要求其履行,則存在更多困惑與爭議。同時,證券公司在一些產品交易中,可能存在身份重合。其既有可能作為發行人的代理人,形成代理關系,代理發行人與投資者簽訂金融產品交易合同,又有可能作為經紀人代投資者買賣證券,形成經紀關系。〔34〕參見李飛:《〈民法典〉時代保險經紀人的法律地位》,載《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經紀關系和代理關系存在不同權利義務配置規則,此種情形,也帶來法律適用上的困境。此外,以合同關系來觀察,并不能解釋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在合同締約階段業已存在的合理性,也不能顯現客戶與賣方機構之間存在一定的信賴關系。
其次,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不宜以受信義務理論作為理論基礎。在內容上,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和受信義務各有側重。基于受信義務理論,違反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承擔侵權責任。〔35〕See Stuart D.Root, Suitability--The Sophisticated Investor--And Modern Portfolio Management, 1991 Columbia Business Law Review 287, 329-330(1991).我國不少學者主張引入信義義務,并作為適合性原則的依據;〔36〕參見邢會強:《金融機構的信義義務與適合性原則》,載本書編委會編:《人大法律評論》2016年卷第3輯,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8頁。甚至有觀點將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等同于信義義務。〔37〕參見張敏捷:《投資者適當性原則研究》,載《理論與改革》2013年第5期。不過,筆者認為,受信義務理論不宜作為適當性義務的理論基礎。盡管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和受信義務都是平衡交易雙方利益的利器,存在交易基礎結構的相通性,如基于金融機構本身資質、專業能力吸引客戶,具有一定的交易信賴關系,存在較大控制權,提供投資建議或推薦,〔38〕See Michelle Lichtor, How Suitable is the Language of Suitability in the Modern Era, 39 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 201, 202(2013).但我國法上目前缺乏明確的受信義務制度。受信義務制度產生于英美法系衡平法中,相應內涵依據衡平法的公平公正理念產生和發展,內容本身存在不確定性、開放性和動態性。受信義務或信義義務等術語并未被明確規定于我國法,即使在《公司法》《信托法》等領域亦是如此。并且,我國法中的“忠實義務”“勤勉義務”等義務是否等同于受信義務,仍存在爭議。譬如,政府機關曾在答復中采用“類似”而非“等同”的表述,〔39〕參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關于《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和《關于到香港上市的公司執行〈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的補充規定》致香港聯交所的函”,體改函生〔1993〕74號。這說明它們的內涵并非完全重合。實踐中易將受信義務中的勤勉管理內容作為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履行要求,混同二者,值得注意。〔40〕參見“陳水鑫與上海鉅派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等其他合同糾紛案”,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2021)滬0115民初10966號民事判決書。此外,課予受信義務的目的在于防范受托人可能侵占或濫用所受托財產或權力的風險(the fiduciaries’ misappropriation of entrusted property or power),以及受托人疏于履行職責而產生損害的風險(performance of the fiduciaries’ services),〔41〕See Tamar Frankel, Fiduciary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07.面向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間的關系,多發生在合同履行期間;而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制度功能在于防范產品和客戶的不匹配風險,面向買方和賣方之間的關系,主要存在于合同締約階段。
最后,招牌理論為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法定性提供了部分理論基礎,能夠為監管者監管經紀商、交易商金融產品推介提供理論依據。在我國金融“分類經營、分業管理”原則下,證券公司、銀行、保險公司業務分明,但在金融混業經營趨勢下新型復合型金融產品層出不窮,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履行主體的指向并未得到法律的有效明確,如保險理財產品就有這種情況。〔42〕參見李游:《投資連結保險的監管路徑及其審思》,載清華法律評論編委會編:《清華法律評論》第十卷第二輯,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44-169頁。在招牌理論下,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作為一項默示的法定義務,保險公司實質跨業經營,發行這類產品,也須承擔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但是,若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理論基礎局限在公法監管層面,作為私法意義上的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法定性就不能有效普遍適用于司法裁判。即使立足于金融消費者保護的基本立場,論證賣方機構承擔私法意義上的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也存在多種解釋進路及其不同法律適用效果。譬如,可以通過認定違反這些行政規章的義務規范是效力性規范還是管理性規范,進而做出判斷。又如,有法院將違反公法上的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視為違反強制性規定,從而導致金融交易合同的無效;也有法院借助“社會公共利益”條款認定違反行政規章的合同無效之邏輯,有別于“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43〕參見李建偉:《行政規章影響商事合同效力的司法進路》,載《法學》2019年第9期。此外,金融商事交易往往存在“一對多”的特點,其交易合同效力不宜簡單以違反強制性規則認定無效,否則有損交易安全。
(二)誠信原則作為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法定性法理來源的本土定位及其合理性
代理理論、受信義務、招牌理論等作為域外典型理論,在我國現行法的規范體系下難以獲得自洽解釋,故需要進一步探究更為合理的理論基礎。筆者認為,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應當作為一項法定義務(而非合同義務)加以解釋,其不能因為當事人另有約定而不被適用,否則該制度將形同虛設。回歸本土資源后,應以誠信原則作為該義務的理論基礎,相應地對履行主體和義務內容進行擴大解釋,這樣可以消除目前司法適用混亂的問題。
首先,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法定性以誠信原則為基礎,其合理性如同先合同義務法定性基礎,但不宜作為先合同義務性質加以解釋。就先合同義務而言,德國法學家耶林早已指出,法律所保護的,并不只是一個業已存在的契約關系,正在發生中的契約關系亦應包括在內。〔44〕Jherings jb.41(1961), S.lf.轉引自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1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第72頁。所以,基于締約信賴利益保護和誠信原則,法律規定了先合同義務的法定性。這就說明,以誠信原則為基礎,同樣可以產生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法定性。申言之,從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產生來看,該義務誕生于證券經紀業務,是適用在投資者對券商信賴的領域,有賴于經紀商的投資建議而進行投資決策。為保護這種信賴利益和交易上的公平,法律上設置了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同時,誠信原則作為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法定性法理來源的合理性,還可以從風險社會治理的現實需求獲得。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法定性是在符合市場交易規律的前提下,合理增加金融機構的審慎和注意義務,從根本上防控交易風險、減少交易成本,避免事后解決糾紛的高成本、低效率和分散化,實現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和精準治理的兼顧。〔45〕參見馮輝:《實質法治理念下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法律構造》,載《法學》2022年第7期。這也是契合我國當下著力防范化解金融領域系統性風險的重要工作之一。此外,從金融統合法的發展趨勢來看,美國法、英國法、日本法、韓國法等域外法對金融投資商品產品進行橫向規制,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作為法定義務的適用領域不再局限于證券法,在保險業、信托業等領域亦可適用。〔46〕參見李游:《“買者自負”的適用邏輯與金融消費關系的“不平等”》,載《北京社會科學》2019年第7期。由此可見,誠信原則作為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法定性的理論來源具備合理性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和先合同義務的理論基礎均為誠信原則,兩者都是法定義務,但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不宜作為先合同義務加以解釋。其一,在履行主體上,先合同義務受合同相對性的約束,履行主體范圍限于以締結合同為目的的雙方當事人之間。盡管《德國民法典》等域外法拓展了傳統締約過失責任承擔主體,〔47〕譬如,《德國民法典》第311條第3項明確規定:“含有第241條第2款所規定的義務的債務關系,也可以對自己不應成為合同當事人的人發生。該第三人特別地要求對自己的信賴,并因此而大大影響合同磋商或合同訂立的,尤其發生此種債務關系。”參見陳衛佐譯注:《德國民法典》(第5版),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21頁。但我國《民法典》第500條仍將締約過失責任承擔主體限定于“當事人”。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履行主體不應局限于合同當事人,特別是,司法爭議中的金融產品代銷機構,〔48〕參見“盧莉、嘉實財富管理有限公司委托理財合同糾紛案”,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2020)滬0115民初4150號民事判決書。是金融產品銷售的主要參與主體,也是該義務的履行主體。《九民紀要》第72條、第74條將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履行主體表述為“賣方機構”和“金融服務提供者”,值得肯定。其二,在義務內容上,《民法典》第500條規定的締約過失責任承擔在適用范圍上主要明確為惡意磋商、故意隱瞞等情形。但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履行過程中,要求了解客戶、產品及其匹配,特別是風險揭示,并提供謹慎的投資建議(give prudent advice)。〔49〕See Roger W.Reinsch, J.Bradley Reich & Nauzer Balsara, Trust Your Broker: Suitability, Modern Portfolio Theory, and Expert Witnesses, 17 St.Thomas L.REV.173, 175(2004).其三,在損失承擔上,締約過失責任的賠償范圍以受害當事人的信賴利益的損失為限,包括直接利益和機會損失,〔50〕參見黃薇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合同編釋義》,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91-92頁。而根據《九民紀要》第77條,違反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損失賠償額為客戶所受的實際損失,包括損失本金和利息,甚至在有欺詐情形時,可要求懲罰性的損失賠償。
其次,在誠信原則要求下,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法定性更能支撐金融產品交易結構的生成邏輯和基本要求。
一方面,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是一種公權力介入、矯正買賣雙方交易失衡的利益平衡制度,是課予金融機構的一項嚴苛剛性的法定義務。傳統商品交易中買賣雙方并不存在明顯的信息不對稱,貫徹買者自負原則。〔51〕See Alan M.Weinberger, Let the Buyer Be Well Informed? - Doubting the Demise of Caveat Emptor, 55 Maryland Law Review 387, 394(1996).對于交易地位懸殊等因素造成實然交易地位的不平等,法律是通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來傾斜保護消費者的。在金融商品交易中,金融商品的復雜化使得買賣雙方實際經濟地位、磋商能力出現明顯的不平等,打破了傳統交易關系的假設。〔52〕參見李游:《“買者自負”的適用邏輯與金融消費關系的“不平等”》,載《北京社會科學》2019年第7期。有法院在判決中明確,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系基于實質公平原則,鑒于個人投資者經驗不足,投資理財的門檻較高,且銀行等賣方具有營利性,為防止交易不公平現象的存在以及保護個人投資者的合法權益,法律法規以及規范性文件對銀行在與投資者進行交易時的注意義務進行全面規范,以實現矯正的正義。〔53〕參見“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陽北路支行等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案”,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19)京03民終10501號民事判決書;馮輝:《實質法治理念下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法律構造》,載《法學》2022年第7期。由此可見,法律設置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要求將合適的產品銷售給適當的客戶,其制度目的無疑是強化投資者保護目標的需要,〔54〕See Gail Pearson, Reading Suitability against Fitness for Purpose - The Evolution of a Rule, 2010 Singapor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29,129-130(2010).也是追求公平公正交易(just and equitable principles of trade)的典型表現。〔55〕See Stuart D.Root, Suitability--The Sophisticated Investor--And Modern Portfolio Management, 1991 Columbia Business Law Review 287, 290(1991).因此,誠信原則作為適當性義務法定性的理論基礎有助于對金融交易中信息獲取能力與專業能力均處于弱勢的客戶群體提供傾斜性保護。
另一方面,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旨在將合適產品推介給適當的買者,這必然是交易誠信原則的具體體現。金融產品合同多為格式合同,交易的公平有賴于賣方機構的誠實信用。這也是現代法律所面臨的艱巨任務。〔56〕參見王澤鑒:《債法原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19-120頁。基于誠信原則,《民法典》第500條規定“惡意磋商”或“故意隱瞞”或“其他違背誠信原則的行為”,行為人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實踐中不少爭議的產生是由于金融機構在銷售金融產品中,不完全履行風險告知義務,誤導性陳述、不完整陳述甚至虛假宣傳誘導客戶。這就凸顯了誠信原則對于整個金融產品銷售行為規范的重要性。譬如,對于“充分揭示風險”的理解,如果進行了風險評估,是否就應認定賣方機構已盡到充分提示義務。〔57〕參見“成宏與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揚州分行金融委托理財合同糾紛案”,江蘇省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蘇10民終1953號民事判決書。通常而言,對客戶的風險評估僅意味著“了解客戶”,并不意味著風險揭示和提醒,甚至不少金融產品銷售機構基于增加業績考量而有意隱瞞風險信息,進行誘導性銷售,故在誠信原則視角下,能夠對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進行更合理考察。
最后,以誠信原則為解釋通道,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法定性有助于對既有規則沖突進行恰當的體系解釋,實現對履行主體、保護對象等內容的應然解釋和規范目的。就保護對象而言,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是“賣者盡責”的重要內容,但并非所有投資者均是該制度的保護對象(保護對象不包括專業投資者)。〔58〕如美國法、日本法將專業投資者排除。See FINRA Rule 2111;并參見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第36條。筆者于本文中引用的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見 http://www.japaneselawtranslation.go.jp/law/detail/?x=57&y=23&co=1&ia=03&yo=&gn=&sy=&ht=&no=&bu=&ta=&ky=%E9%87%91%E8%9E%8D%E5%95%86%E5%93%81&page=44&re=01,2022年9月10日訪問。然而,在目前規范體系下,投資者分類不一,如普通投資者和專業投資者、〔59〕參見《證券法》第89條、《證券期貨投資者適當性管理辦法》(2020年修正)第7條。合格投資者和公眾投資者、〔60〕參見《上海證券交易所債券市場投資者適當性管理辦法》(2022年修訂)第6條、第7條。合格投資者和不特定社會公眾、〔61〕參見《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銀發〔2018〕106號)第4條。個人投資者和機構投資者、〔62〕參見《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股票交易特別規定》(上證發〔2019〕23號)第3條、第4條。個人投資者—普通機構投資者—專業機構投資者等。〔63〕參見《上海證券交易所投資者適當性管理相關規則的通知》(上證發〔2017〕35號)第6條、第13條。這些混亂的投資者類型劃分無疑給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履行造成障礙,也容易與合格投資者制度混同(合格投資者制度中的“合格投資者”主要是指符合進入某個資本市場領域所設置的準入門檻和基本條件的投資者)。盡管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制度不同于合格投資者制度,兩者在規范目的、適用范圍、制度內容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但投資者達到資質或者滿足合格投資者的標準,是否影響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履行,存在爭議。譬如,有法院將客戶作為合格的投資者,歸入專業投資者范疇,認為與普通投資者相比,其對于投資的風險及相關規則應更為清楚,故賣方無不法侵權行為。〔64〕參見“劉斌與德邦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證券糾紛上訴案”,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8)滬02民終7807號民事判決書。
從案例樣本投資者群體特點來看,客戶均為自然人,無機構投資者,前者中又多為中老年的中小投資者,更易引起爭議。譬如,原告主張,自己年齡已過60歲,申購基金的手續卻極其簡單,大部分申購文件都是窗口遞出,指引簽名,難以辨別產品類型、判斷風險大小,但法院對此種主張易予以忽略。〔65〕參見“徐禎弘與平安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豐臺支行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案”,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8)京02民終7731號民事判決書。甚至有法院認為,原告具有很強的風險識別能力和風險承受能力,不存在被誤導購買案涉基金的可能性。〔66〕參見“劉艷娥、廣發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案”,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粵01民終7659號民事判決書。事實上,客戶財產數額的多少雖然很大程度上反映其風險承擔能力,但風險承擔能力高并不意味著客戶不需要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制度保護。并且,財產數額不能直接改善這層交易不平等的實然狀態,在司法實踐中,爭議的發生也都是具有一定財力的自然人(以老年人為主)虧損而引起的。因此,明確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和合格投資者的不同制度面向,并在混亂的投資者分類的監管規則中,以誠信原則作為解釋金融監管規則司法化的有力通道,有助于為公法意義上的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規則司法化提供理論基礎和解釋進路。要求誠實不欺、如實告知交易信息,使得普通投資者、個人投資者、普通機構投資者均被納入保護范圍,僅排除具備平等交易能力的專業投資者。
四、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履行判斷與責任承擔
誠信原則是填補法律漏洞、平衡法律利益的利器,但其內容的抽象性也使得法官擁有較大自由裁量空間,存在加劇原有法律關系不公的風險,故有必要對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履行判斷及其責任承擔做進一步探析。
(一)既有司法裁量標準的反思和“要件審查+實質檢驗”關聯裁量的提出
1.對既有的三種司法裁量標準的反思
如前所述,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履行的司法判斷標準各有利弊。就形式標準而言,該標準能夠便于金融銷售機構舉證其已完成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履行,也便于法院裁判,但容易陷入“重形式、輕實質”的義務履行,甚至存在“一刀切”現象。比如,即使在基金認購資料中,采取了加粗字體等特別提示“基金有風險、投資須謹慎”,投資者的簽名確認也不意味著其已明白所購產品的投資風險。特別是部分銷售機構可能簡單地將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履行視為購買基金的一個流程或前置程序,容易出現夸大收益率情形,難以如實告知產品所存在的投資風險。〔67〕如“劉奇與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馬鞍山路支行委托理財合同糾紛案”,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區人民法院(2018)皖0111民初9098號民事判決書。就實質標準而言,部分法院能夠拋棄僵化的形式標準,從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內容的實質層面來進行評斷,值得肯定。如有法院對超過65歲的客戶進行風險承受能力評估時,強調應當充分考慮客戶年齡、相關投資經驗等因素。〔68〕參見“于亞坤、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陽沈河支行金融委托理財合同糾紛案”,遼寧省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遼01民終4184號民事判決書。但是,這種裁判思路對金融機構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金融機構以投資者能夠理解的方式向投資者告知產品的運作方式以及可能產生的最大風險。〔69〕參見“深圳前海凱恩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徐建芬金融委托理財合同糾紛案”,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粵03民終26388號民事判決書。然而,法院在采取實質標準時,并未指明賣方機構應當審查的具體事項及其程度。
上述不同司法標準進一步體現的是商事效率和交易公平、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沖突與選擇。在形式標準下,賣方機構和法官均更關注商事效率和形式正義,即追求外觀主義。因為外觀主義是商法的一個重要標簽,是調整商事關系中的重要方法,商事交易頻繁迅速,一般都不會對相對人進行詳細調查,而只信賴外部表象。〔70〕參見施天濤:《商事關系的重新發現與當今商法的使命》,載《清華法學》2017年第6期。金融產品銷售是典型商事關系的體現,故相應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履行判斷采取形式標準也容易得到理解,但這又容易陷入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履行形式化的虛偽正義,使制度規范目的落空。隨著社會理念由形式理性轉向實質理性,金融消費者傾斜保護理念的逐漸興起和發展,司法裁判的價值追求不再局限于形式正義,更多關注實質正義。〔71〕參見李游:《“買者自負”的適用邏輯與金融消費關系的“不平等”》,載《北京社會科學》2019年第7期。我國近些年的司法政策也是不斷警示外觀主義的不當擴大化適用,強調探求真意。如《九民紀要》“引言”即要求“通過穿透式審判思維,查明當事人的真實意思,探求真實法律關系”。因此,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履行的實質標準是通過“實質重于形式”的裁判路徑矯正失衡的金融交易關系,契合傾斜保護客戶的訴求。不過,實質標準會增加賣方機構是否履行義務的不確定性以及交易成本,最終交易成本又會轉移至客戶,不利于促進財富增長和實現合同目的。因為促成商事交易、降低交易成本才是合同當事人的目標。〔72〕See David Charny, Hypothetical Bargains: The Normative Structure of Contract Interpretation, 89 Michigan Law Review 1815, 183(1991).
就綜合標準而言,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合理的履行需要結合形式標準和實質標準。法院應當從形式和實質兩方面的視角審查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履行,既關注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履行可能存在的形式化,也注意影響投資者決策的重要因素,兼顧賣方盡責和買者風險自負的利益平衡,相對而言較為合理。不過,綜合標準的判斷方法、要素內容、責任承擔,都有待進一步厘清。
2.“要件審查+實質檢驗”兩階段關聯裁量的綜合判斷
承前所述,筆者更認同綜合判斷,并擬在既有判斷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要件審查+實質檢驗”兩階段關聯裁量的綜合判斷方法。申言之,在“要件審查”階段,法院偏向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履行內容的形式審查。對于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具體履行,諸多規范提出了程序性規則要求。譬如,《公開募集證券投資基金銷售機構監督管理辦法》(證監會令2020年第175號)第17條規定,基金銷售機構應當提示投資人閱讀基金合同、招募說明書、基金產品資料概要,提供有效途徑供投資人查詢,并以顯著、清晰的方式向投資人揭示投資風險。因此,如果賣方機構的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履行出現形式或程序性瑕疵,明確違反監管規則,出現客戶與產品風險不匹配、未對客戶風險評估、不具有從業資格等情形,則可直接判定賣方機構違反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承擔侵權責任。于此情形,不需要進入“實質檢驗”階段的裁量。
然而,如果賣方機構無明顯形式或程序性瑕疵,交易外觀上完成了相應的風險測評,產品與客戶風險承擔能力匹配,而客戶對賣方機構的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履行仍存在爭議,則法院不能采取形式標準,依據賣方機構的測評結果來定紛止爭,否則會陷入一種論證的邏輯困境:投資者主張金融機構的行為不當,法院卻根據金融機構的行為來證成金融機構的行為具有正當性。〔73〕參見曹興權、凌文君:《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司法適用》,載《湖北社會科學》2019年第8期。換言之,在這種情形下,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履行判斷進入“實質檢驗”階段。該階段需要從實質公平視角進行審查,考量賣方機構是否具備足夠的注意義務等合理性基礎,去了解客戶的重要事項(如客戶年齡、財務狀況、投資目標、風險承擔能力等等信息),證明其是將合適的產品銷售給適當的客戶,以此來判斷賣方機構是否充分盡到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申言之,參考域外法經驗,可從合理基礎適用性(reasonable-basis suitability)、特定客戶適用性(customer-specific suitability)和數量適用性(quantitative suitability)等維度觀察、判斷。〔74〕See FINRA Rule 2111.也就是說,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履行具有“質”的適當性和“量”的適當性兩個維度,“質”的維度在于賣方機構盡到合理的審慎調查、有合理的基礎相信其推薦的產品對于特定投資者是適當的,“量”的維度在于賣方機構推薦的產品數量也應當適合客戶。〔75〕參見黃輝:《金融機構的投資者適當性義務:實證研究與完善建議》,載《法學評論》2021年第2期。因此,法院在“要件審查”的基礎上,通過對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實質檢驗”,可充分探析賣方機構義務是否充分履行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
綜上,與目前司法標準相比,“要件審查+實質檢驗”兩階段關聯裁量方法吸收形式標準和實質標準的合理因素,改進綜合標準,同時兼顧程序和實體規則,平衡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的不同價值追求,有助于實現賣方機構與客戶之間利益的有效衡量。
(二)“要件審查+實質檢驗”兩階段關聯裁量的內容展開
為實現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履行“要件審查+實質檢驗”兩階段關聯裁量的規范化和精細化,以下筆者將從了解客戶、了解產品、客戶與產品相匹配、風險揭示等四方面內容展開分析。
其一,“了解客戶”的履行審查,是盡到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與否的基礎。在“要件審查”階段,關鍵在于是否對客戶進行了風險評估,從而了解客戶的財務狀況、風險承受能力等信息,對客戶進行分類,并將客戶識別為普通投資者或者專業投資者。如客戶為專業投資者,則不需要承擔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如客戶為普通投資者,則需要進一步對其風險承擔能力等關鍵信息進行調查。目前司法實踐中,法院主要依據是否對客戶進行明確的形式調查或評估,如風險評估書沒有客戶簽字確認,〔76〕參見“楊麗、平安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陽分行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案”,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遼01民終14338號民事判決書。或者未能證明對客戶財產、收入等方面進行調查評判。〔77〕參見“深圳前海凱恩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徐建芬金融委托理財合同糾紛案”,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粵03民終26388號民事判決書。因此,如果出現這些明確的風險評估等程序性要件缺失,則賣方機構違反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承擔不作為侵權責任。
但是,賣方機構對投資者風險能力測評問卷等材料不盡一致,且對同一客戶,不同機構的測評資料,可能會產生不同評估結果,進而產生爭議(如投資者主張賣方機構的風險承受能力評估問卷不能實質性地達到風險測評目的〔78〕參見“深圳德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寶英等委托理財合同糾紛案”,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21)粵03民終3484號民事判決書。),觸發“實質檢驗”。所以,在“實質檢驗”階段,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履行主體應注意到我國對投資者風險承擔能力類型的不同劃分及其可能的不合理性。一方面,投資風險評估可能不具有參考價值,如評估時間與客戶現狀存在較大時間差引起的爭議,〔79〕參見“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陽北路支行等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案”,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19)京03民終10501號民事判決書。又或者存在明顯的不合理性,譬如,實踐中評估問卷在具體問題設計、問題分值確定及分值分配等方面均缺乏明晰的標準,科學性嚴重不足。〔80〕參見任自力:《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規范邏輯》,載《法律適用》2022年第2期。另一方面,對于投資者風險承擔能力,即保守型、穩健型、平衡型、進取型、激進型等投資者風險類型,存在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如中國證券業協會《證券經營機構投資者適當性管理實施指引(試行)》(中證協發[2017]153號)第9條將普通投資者劃分為C1、C2、C3、C4、C5五級。這種混亂的規則配置,既要求賣方機構履行適當性義務時特別注意,也需要法官對該種爭議謹慎權衡、考量“了解客戶”的評估是否契合客戶真實的情形。
其二,“了解產品”的履行審查,是盡到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與否的前提。在“要件審查”階段,關鍵在于是否如實掌握產品基本信息及其風險等級情況。對于“產品”的范圍,《九民紀要》第72條明確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指向的是銀行理財產品等高風險等級金融產品,以及期貨等高風險等級投資服務。這其中的“高風險等級”究竟是一種強調還是一種限定,并不確定,從而為適用范圍上可能發生的爭議留下了隱患。〔81〕參見馮輝:《實質法治理念下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法律構造》,載《法學》2022年第7期。從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規范目的解釋,了解“產品”的范圍,應進行擴大解釋,換言之,《九民紀要》對“高風險等級”僅是強調而不是限定。對于“了解產品”的要件審查主要依據相應的監管規則。譬如,就產品的基本信息而言,《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第26條明確產品類型、投資組合、估值方法、托管安排、風險和收費等重要信息。
但是,這種形式審查存在著難以解決金融機構本位色彩濃厚、評級流于形式等問題,不利于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而這些問題可通過實質審查予以解決。〔82〕參見雷希:《論金融機構風險評級司法實質審查的確立及其規則建構》,載《湖湘論壇》2022年第2期。故出現“了解產品”履行爭議時,則進入“實質檢驗”階段。“實質檢驗”的重點在于,對于產品的風險等級,是否對該信息予以特別提示和明確。目前我國對產品風險等級存在“五級”或“六級”等不同劃分,如中國證券業協會《證券經營機構投資者適當性管理實施指引(試行)》(中證協發[2017]153號)第14條將產品或服務風險等級劃分為R1、R2、R3、R4、R5 五級,也有金融機構采取“極低、低、較低、中、較高和高六類分級”。〔83〕參見“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陽北路支行等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案”,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19)京03民終10501號民事判決書。同時,在“了解產品”內容上,依據《商業銀行個人理財業務管理暫行辦法》第20條,產品發行人、銷售者是具備專業資質、經過業務培訓的從業人員(如培訓時間不少于20小時),需要熟悉產品風險等級、產品期限、歷史業績、投資策略等信息。因此,法官在“實質檢驗”階段,應當將賣方機構作為專業人員予以考量,不能以此作為履行抗辯。
其三,“客戶與產品相匹配”的履行審查,是盡到適當性義務與否的核心內容與目標,也是“了解客戶”和“了解產品”內容的邏輯延伸。在“要件審查”階段,主要審查是否根據客戶風險承受能力向其推薦相應風險等級的產品或服務。否則,將高風險產品銷售給低風險承擔能力的客戶,將有違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了解客戶”和“了解產品”在形式上均存在明確的風險評估和類型劃分,故在匹配的外觀審查上,參照相應評估結果來進行審查是否“匹配”。但是,這種“匹配”外觀審查仍有待進一步考量。緣由在于目前投資者和產品的風險類型劃分不一,并不一一對應和匹配。以中國銀行“原油寶”事件為例,有關產品被定性為R3(平穩型)風險等級,但其作為風險最大的期貨投資,是一種高風險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并不適合風險承受能力較低的客戶購買,故存在產品管理不規范、銷售不合規等問題,〔84〕參見《中國銀保監會依法查處中國銀行“原油寶”產品風險事件》,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947272&itemId=915,2022年9月10日訪問。賣方并未盡到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
“客戶與產品匹配”并不能止步于形式評估的匹配,出現該爭議時,則進入“實質檢驗”。北京金融法院在2021年十大典型案件“才某與中信信托有限責任公司合同糾紛案”中指出,既往投資經驗是否可以免除金融機構的適當性義務,應綜合考量既往投資金融產品的屬性、類別、投資數額以及投資期間等因素,根據自主投資決定是否受到影響進行判斷。〔85〕參見《北京金融法院亮出一周年成績單首批十大典型案例新鮮出爐》,https://bjfc.bjcourt.gov.cn/cac/1648195938829.html,2022年7月22日訪問。從域外法來看,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第40條確定了根據締結合同的目的、客戶知識、經驗、財產狀況等因素綜合考量客戶購買金融商品的適當性。因此,在“實質檢驗”階段,應探究“匹配”的合理性基礎,即實質考量財產標準、投資經驗等重要評估要素,實現客戶的意愿、能力(willingness and capacity)與風險承擔相匹配。〔86〕See Stephen B.Cohen, The Suitability Rule and Economic Theory, 80 Yale Law Journal 1604, 1634(1971).
其四,“風險揭示”的履行審查,是實現客戶與產品匹配的特別警示。在“要件審查”階段,主要在于是否存在欺詐或誤導性銷售,是否明確告知產品或服務可能的投資風險,并進行相應的解釋說明,以確保客戶在充分知情的基礎上做出投資決策。如前所述,“風險揭示”或“風險告知”是否為適當性義務的核心內容,存在爭議,〔87〕參見“深圳前海凱恩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徐建芬金融委托理財合同糾紛案”,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粵03民終26388號民事判決書;吳弘、呂志強:《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辨析——新〈證券法〉及〈紀要〉視角》,載《上海金融》2020年第6期。但這種認識分歧,在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履行上,沒有本質上的差異影響。因為“客戶與產品匹配”的履行上,勢必也需要風險告知,而“風險揭示”的履行是進一步強化客戶對產品風險的認知,是一種特別警示,二者相輔相成。
在“風險揭示”的履行實踐中,通常采取形式標準,即以客戶是否簽字或抄寫風險告知書或電話回訪為評價依據。但是,即使“以充分、必要、顯著的方式”揭示產品本身所具有高風險的特殊性和具體體現,簽字同意達成的契約也只是一種形式化的合意,不能僅依此種形式上的合意就認定已充分履行風險揭示義務。〔88〕參見“徐禎弘與平安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豐臺支行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案”,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8)京02民終7731號民事判決書。例如,銷售人員向客戶以明示或暗示虛假承諾某產品保本保收益的方式誘導購買,這就有違“風險揭示”的履行。〔89〕參見“李娜與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邳州支行、鄭天平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案”,江蘇省邳州市人民法院(2019)蘇0382民初8940號民事判決書。因此,如發生這種爭議,則進入“實質檢驗”階段。
買賣雙方簽訂合同中關于風險提示、風險免責等內容條款屬于格式條款。對于格式條款內容,根據《民法典》第496條,免除或者減輕其責任等與對方有重大利害關系的條款,需要采用引起對方注意的文字、符號、字體等特別標識。尤其在新科技互聯網金融時代,不少金融機構通過網絡平臺銷售,客戶自助終端操作,使用大量專業化術語、復雜科技化服務工具,產品的風險提示容易引起爭議。〔90〕參見“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德勝科技園支行與李昭財產損害賠償糾紛”,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9)京02民終5844號民事判決書;“于亞坤、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陽沈河支行金融委托理財合同糾紛案”,遼寧省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遼01民終4184號民事判決書。故在“實質檢驗”階段,不能僅以合同書簽字或者視頻資料來證實“風險揭示”的履行,而更應該從客戶的具體情況,根據其認識水平、財務狀況等方面如實告知投資風險。一方面,盡可能使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披露,如域外法上采取“通俗易懂規則”(the“plain English rule”),要求在組織結構、語言、封面設計、概要內容以及風險因素等方面采取簡易表述。〔91〕See SEC: Plain English Disclosure (Release No.33-7497), https://www.sec.gov/rules/final/33-7497.txt, 2022年7月24日訪問。另一方面,告知的信息應具有重大性,而非全部信息,一味追求“多而全”的方式對客戶投資決策并無實益。
對于上述“實質檢驗”階段的義務履行判斷,相應判斷標準是依據專業人員標準,而非普通人標準。因為銷售高風險金融產品本身作為一種絕對商行為,具有營利性、職業性特點,且面向不特定的社會公眾,相應主體也應負有更高的注意義務。〔92〕參見李游:《公司擔保中交易相對人合理的審查義務》,載《政治與法律》2018年第5期。換言之,違反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作為一種特殊侵權行為,與侵權責任法中專家責任的注意義務同理。這種“注意”的標準以專業人作為參照,需具有高度的風險預見性,審慎推介,不能以能力、經驗等不足作為抗辯理由。并且,從“賣者盡責、買者自負”的交易邏輯來看,應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即《九民紀要》第75條規定的是否盡到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由產品的賣方機構舉證。所以,基于上述對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履行判斷,若賣方機構能夠舉證證明其盡到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則相應投資風險由客戶承擔。這也是“賣者盡責、買者自負”的應然之義。如未能舉證證明履行該義務,則賣方機構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
(三)未盡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責任承擔
如前所述,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作為一項法定義務,對其的違反將引發一種侵權責任。從樣本數據上看,賣方機構責任承擔上可能為一種比例責任(24%的樣本)或者全部賠償責任(28%的樣本)。根據《民法典》第1165條,承擔侵權責任需要滿足行為、損害、因果關系、過錯等四個構成要件。

表6 賣方機構責任承擔比重
對于行為要件,是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履行主體未盡該義務的行為,主要依據前述“要件審查+實質檢驗”兩階段關聯裁量來判斷是否違反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其中,違反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主體是賣方機構,不僅包括產品或服務的發行人,而且包括銷售者。司法實踐中,代理人不能以此作為抗辯。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是法定義務(而非合同義務或先合同義務),發行人和銷售者承擔連帶責任。即使發行人與代理人之間存在委托代理合同關系,符合《民法典》第167條,代理人(銷售者)和被代理人(發行人)應當承擔連帶責任。被代理人對投資人是否符合適當性要求負有審慎審查義務,代理人未盡到該義務,也應承擔連帶賠償責任。〔93〕參見“前海開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錦安基金銷售有限公司委托理財合同糾紛案”,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粵03民終19093、19097、19099號民事判決書。
對于過錯要件,賣方機構承擔未盡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侵權責任,須主觀上存在過錯,〔94〕承擔無過錯責任,須由法律明確規定。比如,《證券法》第85條規定信息披露義務人的賠償責任,即為一種無過錯責任。其包括過失和故意兩種情形。就過失的主觀狀態而言,目前主要是依據客觀標準判斷是否存在過失,即是否違反法律法規明確規定的義務或者是否違反了一個合理人的注意義務。〔95〕參見黃薇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侵權責任編釋義》,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6頁。在前述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履行“要件審查+實質檢驗”兩階段關聯裁量中,“要件審查”主要是根據賣方機構是否根據適當性規則對“了解客戶”等內容進行評估,其側重的是形式或程序性審查。如果違反即構成重大過失。在“實質檢驗”階段,則是依據專業人的行為標準來判斷其主觀狀態,檢驗其是否達到金融產品銷售人員的業務水準。如果違反即構成一般過失。就故意的主觀狀態而言,違反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可歸責性就更加顯然。實務一般表現為惡意欺詐、誘導客戶購買高風險產品。于此情形,則存在是否引入《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懲罰性賠償的爭議。就《九民紀要》的規定而言,賣方機構的行為構成欺詐的,區分不同情況進行處理,如以預期收益率、貸款市場報價利率等計算損失賠償數額,而不是依同期銀行利息率計算。這就體現對故意或欺詐的主觀狀態下的懲罰性質。因為故意是行為人能預見或放任導致損害后果的狀態,尤其構成惡意欺詐時,是一種有意識地引起、強化或維持他人不正確設想的行為,旨在使另一方“上當受騙”,〔96〕參見[德]維爾納?弗盧梅:《法律行為論》,遲穎譯,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644頁、第646頁。存在高度的可苛責性特征,需懲罰性規則加以遏制和阻卻。
對于損害要件而言,需要違反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對客戶造成損失,否則賣方機構侵權責任難以成立。《九民紀要》第77條規定,未盡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導致金融消費者損失,應當賠償金融消費者所受的實際損失。司法實踐對“實際損失”的認定,存在不同認識。如有的法院認為,實際損失為投資者損失的本金和利息,利息按照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同期定期存款基準利率計算;〔97〕參見“楊帆與中信建投證券合同糾紛案”,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67447號民事判決書。也有的法院認為應采用損失填補原則賠償金融消費者因此所受的實際損失,實際損失則是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第30條的規定。〔98〕參見“劉艷娥、廣發證券財產損害糾紛案”,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粵01民終7659號民事判決書。筆者認為,《九民紀要》規定的實際損失較為合理,并在賠償損失數額上考量當事人的過錯程度。如客戶對損失不存在過錯,那么賣方機構承擔全部責任,即承擔損失的100%。如客戶對損失存在過錯,則從雙方的過錯程度來權衡責任承擔;〔99〕參見“蘇峻、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鼓樓支行金融委托理財合同糾紛案”,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蘇01民終7576號民事判決書。或根據造成結果的原因力大小確定原被告的責任承擔。〔100〕參見“楊富萍與中國建設銀行侵權糾紛案”,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區人民法院(2018)湘0211民初3550號民事判決書。于此情形,賣方機構可能承擔損失的90%、70%、50%等不同比例的責任。〔101〕如“姚靜飛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案”,浙江省寧波市海曙區人民法院(2020)浙0203民初9080號民事判決書。賣方機構存在賠償比例的差異,除了考量客戶過錯程度外,主要還要評估賣方機構的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履行瑕疵程度,如存在明顯欺詐、故意誤導性銷售等情形,則表明過錯明顯,可能按照預期收益率等來計算損失。
對于因果關系要件,違反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行為與客戶損失需要存在因果。在“一因一果”侵權案件中,案件事實較為簡單,因果關系較易舉證和判斷。但在“多因一果”等案件中,相應舉證和判斷較為復雜。譬如,客戶的實際損失可能是由賣方機構未盡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而引起,但實際損失可能還受到資本市場本身的波動因素等方面影響。目前我國法上的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規則并沒有明確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分配。《九民紀要》第75條也只是規定金融消費者應當對其遭受的損失等事實承擔舉證責任,賣方機構對其是否履行了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承擔舉證責任,沒有明確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司法實踐中,通常對因果關系要件并未詳細闡明,如果存在未盡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行為和客戶損失,一般推定二者存在因果關系,即采取“相當因果關系說”。譬如,若無賣方的不合理推介,客戶就不會購買,相應損失亦無從發生,故不適當推介與客戶的經濟損失之間構成法律上的因果關系。〔102〕如“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財產損害糾紛案”,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19)京03民終10501號民事判決書。但若損失為市場正常波動的結果,與賣方推介行為之間沒有因果關系,則該風險應由客戶自己承擔。〔103〕參見“舒新華、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陽分行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案”,河南省濮陽市華龍區人民法院(2021)豫0902民初1379號民事判決書。從強化客戶權益保護的法益衡量視角出發,進行法的續造,〔104〕參見[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79頁;[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黃家鎮譯,商務印書館2020版,第517-518頁。這種做法是合理的。如果存在不合理的損失計算,可由賣方機構抗辯、舉證。
此外,也應注意,在金融交易領域,投資者保護是主要的規范目的,而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是“賣者盡責”的重要內容,但也容易成為投資者規避投資風險責任承擔的托詞。在實踐中,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履行爭議既有可能由于金融銷售機構本身未如實履行該義務所產生,又有可能因為投資者不愿承擔投資風險責任而主張損害賠償,故違反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民事責任中還應明確免責事由。其一,客戶自甘風險。如果賣方機構盡到了適當性義務,金融消費者拒絕聽取建議或者金融消費者具有相應的投資能力、違反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并不影響其自主決定時,賣方機構就不應該承擔責任。〔105〕參見“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玉泉路支行與肖某糾紛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20)京01民終8093號民事判決書。其二,違反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不影響客戶投資決策。如果根據投資者的既往投資經驗、受教育程度等事實,金融機構能夠證明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違反并未影響投資者的自主決定,也應當認定免責抗辯事由成立,由金融消費者自負投資風險。〔106〕參見“劉艷娥、廣發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案”,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粵01民終7659號民事判決書。其三,其他客戶自身原因所致。譬如,客戶自己故意提供虛假信息導致其購買產品或者接受服務不適當。
五、結 語
隨著金融創新的推進,越來越多的新型金融產品或服務相應出現。這些金融產品或服務通常結構復雜,存在較大投資風險,不易被大眾所理解。故現代金融法規定了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要求將金融機構適當的產品推介、銷售給合適的投資者,從而保護投資者權益。但是,該制度自引進我國以來就存在爭議,特別是在司法適用上,“同案不同判”現象明顯,評斷尺度不一。
在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法律性質上,司法適用存在先合同義務、合同義務、法定義務的不同認識。履行主體上,實踐中多以銀行作為產品的銷售主體。履行內容上,四項具體內容,彼此關聯,密不可分。了解客戶和了解產品是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履行的前提和基礎,客戶與產品匹配是義務履行的核心和目標,而風險揭示是實現產品與客戶匹配的特別警示。在履行判斷上,多采取形式標準。司法實務的分歧背后反映出對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理論基礎存在定位差異,從而出現對制度內容的適用分歧。在解釋論下的困境破解上,應以誠信原則作為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理論基礎,將該義務作為法定義務,擴大履行主體和內容,采取“要件審查+實質檢驗”兩階段關聯裁量的綜合判斷,并明確相應侵權責任及其免責事由。
在立法論視角下,對于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應當加強如下制度統一適用的規則建設:其一,目前我國法上的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規則較為混亂,政出多門,同質產品適用規則差異明顯,應出臺面向金融投資商品的橫向規范,提供規范統一適用依據。其二,在了解客戶、了解產品的風險測評和類型等級上,實踐中不同金融機構測評內容和結果存在不合理、不科學現象,應建立統一的測評內容和劃分標準。其三,將金融消費者保護作為規則制定和適用的目標價值,厘清客戶、投資者、消費者等之間的內涵差異,明確違反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損失賠償的懲罰屬性和賣者的免責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