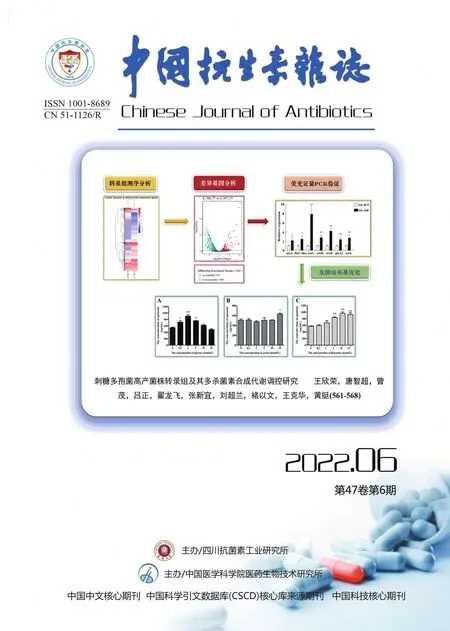銅綠假單胞菌的耐藥趨勢變化及治療進展
陳美玲 何曉靜 菅凌燕
(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盛京醫院藥學部,沈陽 110004)
銅綠假單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PA)為非發酵革蘭陰性桿菌,其對外界環境適應力強,潮濕環境中能長期生存,污染醫用水源或醫療器械后,易形成生物被膜難以清除,是院內下呼吸道感染病例中常見的致病菌。盡管菌株的分離率和抗菌藥物敏感性數據因地域和時間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但中國、美國和歐洲的臨床監測結果均顯示,PA是醫院獲得性肺炎(hospital-acquired pneumonia, HAP)和呼吸機相關性肺炎(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VAP)患者中分離的主要多重耐藥革蘭陰性病原體[1]。一項包括5個國家、12家急癥醫院機構的臨床回顧性隊列研究結果顯示[2],PA感染所致的HAP和VAP患者院內死亡率分別高達40.1%和41.9%,這與接受不恰當初始治療患者的占比高密切相關。本文擬對PA的耐藥現狀、院內PA感染肺炎的治療用藥推薦以及具有發展前景的治療方案進行概括。
1 PA耐藥表型
2012年,學者Magiorakos等對“耐藥”定義如下:在推薦進行藥敏測定的每類抗菌藥物中,至少對1個品種不敏感(包括耐藥和中介)。PA的耐藥菌株常進行以下表型劃分:多重耐藥PA(multidrugresistant PA,MDR-PA):對抗菌譜范圍內的3類或3類以上抗菌藥物不敏感;廣泛耐藥PA(extensively drug-resistant PA,XDR-PA):指細菌僅對1~2種抗菌藥物敏感(通常指多黏菌素);泛耐藥PA(pandrugresistant PA,PDR-PA):對目前臨床上代表性的各類抗菌藥物均耐藥的菌株。值得關注的是,目前PA耐藥性研究的相關定義,多沒有將新型抗菌藥物如頭孢洛扎-他唑巴坦和頭孢他啶-阿維巴坦等納入待測藥物中。
2 PA耐藥趨勢
1997—2016年公開發表的“SENTRY”全球抗菌藥物監測項目[3]結果顯示,PA各耐藥表型的百分比均在2005—2008年達到峰值,推測該結果可能與同期ST235克隆的流行有關。國際上已發現3個主要的MDR/XDR-PA高風險克隆:ST175、ST111和ST235。其中,與O11血清型相關的ST235毒力最強且分布最廣泛,在世界五大洲的許多國家均有報道。2008年后,PA多重耐藥率有所下降,代表性地體現在4個地區(北美、歐洲、拉丁美洲和亞太地區)其對美羅培南敏感性的增加。但一項大規模國際多中心PA院內肺炎的回顧性隊列研究[4]結果顯示,MDR-PA的患病率仍高達30.5%。參照美國臨床實驗室標準化協會(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CLSI)抗菌藥物折點,PA的臨床重點監測藥物敏感率可大致劃分為以下3個梯度。黏菌素(敏感率99.5%)以及以阿米卡星(敏感率93.1%)和妥布霉素(敏感率88.8%)為代表的氨基糖苷類抗菌藥物是目前PA敏感性最高的藥物;其次,是以頭孢吡肟(敏感率83.1%)和頭孢他啶(敏感率80.8%)為代表的頭孢菌素類抗菌藥物;而以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敏感率77.4%)為代表的青霉素類抗菌藥物、美羅培南(敏感率77.4%)為代表的碳青霉烯類抗菌藥物以及環丙沙星(敏感率75.7%)為代表的喹諾酮類抗菌藥物敏感率低于80%。
我國PA對于臨床重點監測藥物的耐藥率總體呈現出下降趨勢。中國CHINET連續15年的細菌耐藥性監測結果(http://www.chinets.com)顯示,PA對于碳青霉烯類藥物的耐藥率在2007年達峰值后,保持小幅下降走勢。2019年,最新的研究數據表明PA對多數藥物的耐藥率低于30%,可大致劃分為以下3個耐藥梯度。首先,敏感性最高的是多黏菌素類抗菌藥物以及氨基糖苷類抗菌藥物,耐藥率分別為多黏菌素B0.8%、黏菌素1.1%、阿米卡星4.6%和慶大霉素10%;其次,是以左氧氟沙星和環丙沙星為代表的喹諾酮類抗菌藥物以及頭孢他啶、頭孢哌酮-舒巴坦和頭孢吡肟為代表的頭孢菌素類抗菌藥物,耐藥率處于10%~20%;而耐藥率最高的是以替卡西林-克拉維酸和哌拉西林為代表的青霉素類抗菌藥物、亞胺培南和美羅培南為代表的碳青霉烯類抗菌藥物以及單環β-內酰胺類抗菌藥物氨曲南,菌株耐藥率超過20%,其中替卡西林-克拉維酸(耐藥率38.9%)、亞胺培南(耐藥率27.5%)和氨曲南(耐藥率27.2%)位居前三。另一項中國革蘭陰性菌2015—2018年監測報告顯示,近5年MDR-PA檢出率為31.8%~35.6%,XDR-PA檢出率為9.1%~10.2%,且耐藥標本多來源于呼吸道。綜上,我國PA多重耐藥菌株檢出率與國際多中心MDR-PA院內肺炎的回顧性結果基本一致,耐藥變化趨勢亦同步于國外學者的研究結果,表現為對抗菌藥物的敏感性有所提升,其中以多黏菌素和阿米卡星的耐藥率最低,但作為PA主要治療用藥的β-內酰胺類、碳青霉烯類以及喹諾酮類抗菌藥物的耐藥率仍居于較高水平,臨床應尤其關注其合理用藥方案。
3 國內外HAP/VAP治療指南和專家共識的用藥建議
3.1 MDR-PA下呼吸道感染治療
對于MDR-PA下呼吸道感染,現有指南及專家共識的用藥推薦以具有抗PA活性的β-內酰胺類+喹諾酮類/氨基糖苷類抗菌藥物的早期聯合治療為主。但是,不同國家和地區HAP/VAP管理指南的首選方案存在一定差異。2014年,我國《PA下呼吸道感染診治專家共識》[5]中指出,氨基糖苷類與β-內酰胺類抗菌藥物的聯用效果略強于氟喹諾酮類;與我國指南觀點一致,歐洲呼吸學會聯合歐洲危重病醫學會、歐洲臨床微生物與感染性疾病學會以及拉丁美洲胸科協會共同發布的《HAP/VAP管理指南(2017版)》[6]認為,聯合使用廣譜β-內酰胺和氨基糖苷類抗菌藥物作為初始治療方案,患者預后效果更佳,尤其是當感染菌株為耐藥革蘭陰性桿菌時。與上述觀點不同的是,2016年,日本傳染病協會聯合日本化療學會制定的《呼吸道傳染病治療指南(2016版)》[7]提出,尚未證實與β-內酰胺類和氨基糖苷類抗菌藥物聯用相關的顯著療效增強。同年,美國感染病學會和美國胸科學會發布的《成人HAP/VAP臨床實踐指南(2016版)》[8]考慮到氨基糖苷類抗菌藥物肺泡濃度可能不足,因而不推薦常規聯用氨基糖苷類。鑒于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推薦差異,PA感染治療用藥選擇還需結合每個國家或地區的菌株耐藥性、臨床治療效果、藥物不良反應(如氨基糖苷類的耳、腎毒性;喹諾酮類藥物可能損害肌肉骨骼和神經系統等)以及患者自身情況等綜合考慮。
對于MDR-PA感染,我國《PA下呼吸道感染診治專家共識》[5]中還給出了其他有參考價值的藥物聯合治療方案,包括抗PA活性的喹諾酮類+氨基糖苷類抗菌藥物、雙β-內酰胺類聯用、磷霉素+抗PA活性的抗菌藥物以及針對PA生物被膜相關慢性感染的14元/15元環-大環內酯類藥物+抗PA活性的抗菌藥物等。此外,我國《成人HAP/VAP診斷和治療指南(2018版)》[9]中推薦了以多黏菌素為基礎的聯合方案,包括多黏菌素+抗PA活性的β-內酰胺類/環丙沙星/磷霉素。值得學者們關注的是,雙β-內酰胺類聯用方案因涉及同類抗菌藥物聯合使用,美國和中國HAP/VAP管理指南均多次強調可能有治療效果,但需慎用。雙β-內酰胺類聯用時,比較特殊的情況是單環β-內酰胺類抗菌藥物氨曲南因作用于細菌細胞壁的不同靶位,可與另一種β-內酰胺類聯合應用。目前我國指南中雙β-內酰胺類聯用的推薦多包含氨曲南,其中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氨曲南[5]、頭孢他啶+氨曲南[10]、頭孢吡肟+氨曲南[9]的聯用方案與美國指南的推薦一致。但是,2017年發表的《XDR革蘭陰性菌感染的中國專家共識》[10]中推薦的頭孢他啶+頭孢哌酮-舒巴坦和頭孢他啶+哌拉西林-他唑巴坦,也表現出較好的協同作用和安全性,因此雙β-內酰胺類的聯用組合值得進一步探索。
3.2 XDR/PDR-PA肺部感染治療
我國《PA下呼吸道感染診治專家共識》[5]推薦在MDR-PA的兩藥治療方案中加入多黏菌素,即3種藥物聯合治療XDR/PDR-PA肺部感染。與之相比,《XDR革蘭陰性菌感染的中國專家共識》[10]還包括了多黏菌素+利福平方案,以及一個不涉及多黏菌素的三藥聯合方案:氨曲南+頭孢他啶+阿米卡星。此外,近年來關于抗菌藥物吸入治療的有利證據也在不斷增加。2016版美國指南建議[8],對于初期治療無效患者的方案中可考慮加入吸入性抗菌藥物。次年,我國發表的《XDR革蘭陰性菌感染的中國專家共識》中也推薦[10],多黏菌素靜脈滴注+碳青霉烯類+多黏菌素霧化吸入的三藥聯合治療方案。2018年,我國《成人HAP/VAP診斷和治療指南(2018版)》[9]更是突破性地給出了聯合吸入性抗菌藥物治療的明確指征,并建議XDR/PDR-PA引起的肺炎,可在靜脈用藥的基礎上,霧化吸入氨基糖苷類(如妥布霉素、阿米卡星)或黏菌素。2019年,《多黏菌素臨床應用中國專家共識》[11]則進一步建議HAP/VAP患者,MDR-PA感染采用靜脈應用抗菌藥物聯合霧化吸入多黏菌素輔助治療,XDR-PA感染采用多黏菌素靜脈注射聯合霧化吸入治療。
3.3 氟喹諾酮類和氨基糖苷類抗菌藥物的劑量探討
在抗PA活性的β-內酰胺類+喹諾酮類/氨基糖苷類的主要治療方案中,氟喹諾酮類和氨基糖苷類均為濃度依賴性抗菌藥物,殺菌效果和臨床療效取決于Cmax,多為日劑量單次給藥。目前,我國對于PA感染的氟喹諾酮類臨床推薦劑量為左氧氟沙星500 mg qd ivgtt,環丙沙星400 mg q12h ivgtt。2014年,我國《PA下呼吸道感染診治專家共識》[5]中氨基糖苷類藥物的推薦劑量為阿米卡星15 mg/kg qd ivgtt,妥布霉素和慶大霉素7 mg/kg qd ivgtt。由于我國推薦劑量低于國外,過去常懷疑存在潛在劑量不足危險。但2016版日本指南[7]對于兩類藥物的推薦劑量亦較謹慎,為左氧氟沙星500 mg qd ivgtt,環丙沙星300mg q12h ivgtt,僅帕珠沙星500~1000 mg q12h ivgtt劑量較高;以及阿米卡星15 mg/kg qd ivgtt、妥布霉素和慶大霉素5 mg/kg qd ivgtt。考慮到中國人群與日本人群的親緣關系,現行劑量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隨著細菌耐藥趨勢的不斷加劇,抗菌治療的成功不僅是控制感染,抑制菌株耐藥性增長也是關鍵環節。根據突變選擇窗(mutant selection window,MSW)理論,當抗菌藥物濃度處于MSW范圍內,即最小抑菌濃度(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和防突變濃度(mutant prevention concentration,MPC)之間時,藥物雖然發揮了抗菌作用,但單次耐藥突變菌株易被選擇性富集,加劇菌株耐藥問題。根據該理論,通過選擇低MPC、窄MSW的藥物,或通過聯合用藥、調整給藥方案來關閉或盡量縮小MSW,可達到減少耐藥突變菌株富集的目的。以氟喹諾酮類抗菌藥物為例,學者Zhao等[12]的體外PK/PD研究結果顯示:PA對氟喹諾酮類耐藥機制中以gyrA基因突變和MexC表達上調為主,環丙沙星較左氧氟沙星有更強的殺菌能力和誘導耐藥能力;與單用左氧氟沙星相比,頭孢他啶與左氧氟沙星的聯合不僅能增強對PA的殺菌活性,在延緩細菌耐藥、抑制耐藥菌增殖方面也有更好的表現[13]。綜上,為達到氟喹諾酮類抗菌藥物的最佳PK/PD指數(AUC/MIC和Cmax/MIC)靶值,同時滿足抗菌藥物濃度高于MPC值,使耐藥突變菌株必須同時具有≥2個突變才能發生選擇性富集,選擇合適的藥物進行聯合用藥也是有效的方法,而不僅僅是提高單藥劑量。
4 耐藥PA的治療研究進展
過去,人們對于碳青霉烯類抗菌藥物的廣泛使用加速了PA耐藥性的發生和發展。碳青霉烯類抗菌藥物所具有的優勢,如酶穩定性、廣譜性以及高效性,反而使得一旦發生耐藥往往提示菌株多重耐藥,而成為當前臨床抗感染治療的難題。2017年,世衛組織根據對新型抗菌藥物的迫切需求程度,將碳青霉烯類耐藥的鮑曼不動桿菌、銅綠假單胞菌和腸桿菌科細菌列為一類重點(極為重要)。碳青霉烯類耐藥PA(carbapenem-resistantPseudomonas aeruginosa,CRPA)的兩個主要耐藥機制,包括產生碳青霉烯酶和膜通透性下降。
4.1 抑制碳青霉烯酶的藥物
4.1.1 氨曲南和β-內酰胺酶抑制劑的新組合
氨曲南是目前唯一對B 類金屬β-內酰胺酶(metallo-β-lactamases,MβLs)水解穩定的β-內酰胺類藥物,將其與β-內酰胺酶抑制劑進行組合,于產碳青霉烯酶的耐藥革蘭陰性菌而言,是可予以期待的治療方案。針對產MβLs的腸桿菌科細菌,通過聯用氨曲南和頭孢他啶-阿維巴坦來實現抑酶譜的互補,即阿維巴坦滅活A類、C類或D類β-內酰胺酶恢復氨曲南敏感性,已被證實在嚴重感染且無常規治療選擇的患者中是高效的。因此,在成功構建快速準確的氨曲南-阿維巴坦藥敏試驗后,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已將其納入難治性感染的擴展抗菌藥敏試驗(the expanded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EXAST)計劃[14]。學者Davido等[15]報道了成功使用氨曲南聯合頭孢他啶-阿維巴坦治愈僅對阿米卡星和黏菌素敏感的產NDM-1和AmpC高表達的PA感染肺炎患者的臨床案例。盡管在之后的研究中,氨曲南-阿維巴坦對PA的體外抗菌活性遠低于腸桿菌科細菌,但該結論主要源自低氨曲南MIC值的PA菌株研究,存在片面性[16-17]。另一方面,在很多情況下,氨曲南與克拉維酸(阿莫西林-克拉維酸或替卡西林-克拉維酸)的聯合也展現出良好的抗PA活性,且該組合擁有絕對的價格優勢[17-18]。值得學者們關注的是,通過聯合給藥所獲得的療效可能部分歸功于雙β-內酰胺類聯合,因此后續的研究應直接以氨曲南-酶抑制劑為對象。綜上,更多的氨曲南-酶抑制劑組合(包括氨曲南-克拉維酸/舒巴坦/他唑巴坦/阿維巴坦等)對CRPA感染的療效應該在更廣泛的臨床耐藥菌株研究中進行探索。
4.1.2 具有發展前景的MβLs抑制劑
目前,已有許多學者發表了MβLs抑制劑治療CRPA的研究成果。其中,以鉍劑和環狀硼酸鹽具有較好的應用前景。①鉍劑:學者研究發現抗幽門螺桿菌藥物鉍劑,可通過置換金屬酶活性中心的鋅離子,來抑制MβLs活性[19]。相較于全新化合物而言,鉍劑發展為MβLs抑制劑的優勢在于其熟知的生產工藝、可評估的成本效益以及擁有一定的臨床數據基礎如細胞毒性、人體耐受劑量等;②環狀硼酸鹽:環狀硼酸鹽作為β-內酰胺水解過程中形成的四面體氧負離子中間體的類似物,已被證明能同時抑制絲氨酸β-內酰胺酶(serine β-lactamases,SβLs)和MβLs[20]。雖然,已有研究提出雙環硼酸鹽可能對嗜麥芽窄食單胞菌(MβLs L1)無效,但其廣譜抑酶性是毋庸置疑的。目前,雙環硼酸鹽(taniborbactam,VNRX-5133)與第四代頭孢菌素頭孢吡肟的聯合已處于第一階段臨床試驗[21]。開發同時對SβLs和MβLs起效的廣譜抑制劑具有重要意義,但兩類酶結構和機制上的差異使其富有挑戰性,而環狀硼酸鹽的發現為后續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4.1.3 涉及碳青霉烯類的雙β-內酰胺聯用組合
涉及碳青霉烯類的雙β-內酰胺聯用組合需要引起重視。由于過去對雙β-內酰胺聯用組合的研究大多集中在20世紀80年代,缺乏碳青霉烯類抗菌藥物在組合中治療PA的研究結果,且大多數聯合療效研究未在PA多重耐藥菌株上進行。因此,目前學者發表的涉及碳青霉烯類的雙β-內酰胺聯用組合,展現出的耐藥PA治療優勢,值得國內外學者今后在動物感染模型和臨床患者中深入探索。
涉及碳青霉烯類的雙β-內酰胺聯用組合主要包括以下兩類:①雙碳青霉烯類療法:雙碳青霉烯類療法(double-carbapenem therapy,DCT)或可應對CRPA菌株。為對抗產KPC肺炎克雷伯菌,DCT方案被提出,后續在臨床應用中得到驗證,并將療效歸因于一種碳青霉烯藥物(主要指厄他培南)“滅活”碳青霉烯酶,以及對目前為止相關文獻報道的薈萃分析結果都證明了該方案的安全性和有效性[22]。目前,國內已有DCT成功治療耐藥PA的臨床研究報道[23-24]。由于PA對厄他培南具有天然耐藥性,這可能與其較弱的外膜透過能力相關,因此選擇聯用亞胺培南和美羅培南作為治療組給藥方案,也取得了較好療效。雖然這兩個臨床研究證實了DCT方案對PA肺炎患者的療效,但不足之處在于沒有對PA耐藥表型進行劃分,且對照組僅為頭孢哌酮的單藥治療,在后續的研究中應將對照組改進為臨床療效較好的聯合方案;②β-內酰胺+碳青霉烯類:2019年,學者Siriyong等[25]在MDR-PA大蠟螟幼蟲(無脊椎動物)全身感染模型中驗證了雙β-內酰胺類聯用的療效。其中,2個涉及美羅培南的新組合(頭孢他啶+美羅培南和氨曲南+美羅培南)對MDR-PA的有效性明顯增加,且青霉素結合蛋白(penicillin-binding proteins,PBPs)抑制譜的比較結果否定了以往的“增效假設”,這兩種雙β-內酰胺聯用組合的增強功效不能用更強或更廣泛的PBPs抑制來解釋。
綜上,目前普遍認同上述兩類組合的增效原理為一種藥物可優先或以更高的親和力與β-內酰胺酶活性部位結合,因此隔離了酶的水解能力。今后,學者可在現有研究成果基礎上,關注外膜滲透性佳而酶穩定性低的同類衍生物,以更好地作為耐藥革蘭陰性菌治療的輔助用藥,通過間接提高聯用藥物的酶穩定性而發揮“增效”作用。
4.2 增加PA膜通透性的藥物
PA耐藥機制多涉及限制藥物進入細胞或增強胞內藥物的外排,因此聯用具有膜破壞特性或是抑制外排泵的藥物,可增加細菌對其他抗菌藥物的敏感性。多黏菌素和抗菌肽可損害PA細胞膜完整性的“增敏作用”已有大量文獻證實,二者的共同優勢在于聯用產生的協同作用包括本身的強抗菌活性以及間接增加另一種抗菌藥物的胞內濃度,有時還涉及主動外排的抑制。因此,除與常規抗菌藥物的聯合外,多黏菌素或抗菌肽的存在也讓原本無或弱抗PA活性的藥物(如利福平、利奈唑胺、四環素等)在多重耐藥菌株感染的治療中發揮重要作用。但臨床應用中,多黏菌素的毒副作用和潛在的異質性耐藥以及抗菌肽的高生產成本和蛋白酶不穩定性等限制,使得優化二者的結構以取長補短成為下一步研究的關鍵。
(1)多黏菌素:已有學者的研究結果表明[26],新型多黏菌素B類似物SPR206腎毒性低,對臨床分離株的體外抗菌活性高(多菌種、多種標本來源、多種耐藥性的綜合評估),且與黏菌素和多黏菌素B相比,SPR206對鮑曼不動桿菌、銅綠假單胞菌和腸桿菌科細菌的MICs低2~4倍。因SPR206所表現出的廣譜高效低毒性,目前該化合物已進入I期臨床試驗[27];(2)抗菌肽:許多研究團隊在已知的抗菌肽結構-活性關系基礎上,結合關鍵的兩親性特征,致力于探索有活性的短肽化合物。近兩年,學者Domalaon團隊[28-29]在短肽鏈基礎上成功開發出二脂質超短肽模擬物,并在體外臨床耐藥菌株中成功驗證其有效性,他們創新性地將脂質側鏈一分為二,在保證疏水性的同時避免因脂質側鏈過長出現溶血現象。綜上,結構優化是一種可行的探索方案,若結合現代化合物模擬篩選軟件可提高研發效率、節約成本。
4.3 碳青霉烯類抗菌藥物給藥模式的優化
初始治療方案與預后關系密切,對于危及生命的重癥感染患者尤其重要。目前,延長輸注療法(prolonged infusion therapy,PIT)是碳青霉烯類抗菌藥物治療重癥感染的首選給藥模式。但PIT初始殺菌效果不佳,這可能與Cmax的降低和Tmax的延遲相關。因此,研究者設計出了優于PIT的優化兩步給藥療法(optimized two-step-administration therapy,OTAT),其具有足夠的%fT>MIC,且擁有較高Cmax和較短Tmax,可同時兼顧初始殺菌效果和殺菌持久性。在OTAT給藥模式中,首先通過靜脈推注快速且最大限度地達到藥物的負荷劑量濃度,隨后立即緩慢滴注給予剩余劑量以保持有效的藥物暴露濃度,來覆蓋特定病原體的高耐藥菌株。根據MSW理論,抗菌藥物濃度超過MPC的時間被認為是防止細菌耐藥的重要參數之一,因此OTAT預期能比PIT更好地抑制耐藥性發展。
對于MICs≥16 μg/mL的美羅培南耐藥菌株感染,美羅培南高劑量緩慢滴注治療(2 g q8h,3 h PIT)或者美羅培南的聯合用藥方案,二者的療效均有限。臨床實踐中,CRPA菌株往往表現出較高的美羅培南MIC值,學者Song等[30]搜集整理了2019年歐洲藥敏試驗委員會數據庫的微生物敏感性數據,其中4841株PA對美羅培南MIC值≥16 μg/mL(16 μg/mL:81.78%;32 μg/mL: 8.10%;64 μg/mL: 9.15%)。他們進一步采用PK/PD模型并結合蒙特卡羅模擬設計給藥方案,發現對于下呼吸道和胸膜感染,以50%fT>5×MIC為最佳藥效學靶標,同樣是美羅培南2 g q8h,但給藥模式改為5 min內靜脈推注1.5 g,再將剩余的0.5 g在5 h內緩慢滴注,則對MIC值高達32 μg/mL的PA菌株仍具有良好的殺菌作用,即美羅培南單藥采用OTAT給藥模式足以治療約90%的高耐藥菌株感染。2020年,學者Huang等[31]對35位膿毒癥和膿毒性休克患者的研究表明,亞胺培南的兩步(30 min內靜脈推注50%劑量,剩余50%劑量在90 min內緩慢滴注)和延長(2h PIT)給藥方案PK/PD指數的靶值達標率相似,但兩步組顯示出更短的Tmax。綜上,盡管目前OTAT相關研究成果尚不充分,但其理論基礎和現有數據提示,通過改變碳青霉烯類抗菌藥物給藥模式,來提高抗碳青霉烯類耐藥菌株的效率也許是可行的,在不久的將來,對OTAT在動物模型乃至臨床患者中的療效進行評估是很有必要的。
5 PA肺炎治療的未來發展趨勢
臨床實踐中,通過合理使用抗菌藥物來控制菌株耐藥性快速增長的作用,尚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我們甚至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會出現超級耐藥菌株的發生和流行。為應對菌株“可累加”的耐藥性,積極探索新療法是至關重要的。目前已經獲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在探尋新靶點的研究中,發現抑制群體感應系統可降低PA的致病性和耐藥性、作用于革蘭陰性菌細胞外膜上高度保守的3型分泌系統的心血管疾病治療藥物丹參酮、干擾細菌鐵代謝的金屬鎵以及新型鐵載體頭孢菌素-頭孢地爾等。此外,通過研發新劑型來提高抗菌藥物生物利用度,如奈米替星納米顆粒和環丙沙星干粉吸入劑等也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關注。同時,創新的“雞尾酒療法”將傳統抗菌藥物與增效佐劑(如三氯生-妥布霉素)或噬菌體聯用、IgA免疫治療以及特殊的抗菌材料等也具有較好的前景。開發新型抗菌藥物及其替代品是一項長期的研究過程,雖然上述治療方案已在體外或動物模型中表現出較佳的抗PA作用,但后期需要更加關注如何提高臨床安全性和可實施性。
6 小結
銅綠假單胞菌是院內下呼吸道感染的主要致病菌,自2008年后其多重耐藥率有所下降,表現為對多數抗菌藥物的耐藥率低于30%,其中以多黏菌素和阿米卡星的敏感率最高。對于PA院內感染肺炎,各國HAP/VAP管理指南和專家共識的主要推薦方案為抗PA活性的β-內酰胺類+喹諾酮類/氨基糖苷類抗菌藥物。近十年,盡管PA對碳青霉烯類抗菌藥物的耐藥率呈現緩慢下降趨勢,但仍高于其他抗菌藥物,過去臨床治療中對于碳青霉烯類給藥方案的過分依賴所遺留下來的CRPA問題,依然是公共衛生的巨大威脅。本文總結了碳青霉烯類耐藥菌株應對方案的研究進展。同時,區別于傳統抗菌療法的研究也是不容忽視的,無論是新靶點、新劑型、增效佐劑還是免疫療法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但新藥的研發是一個嚴謹、漫長的過程,需要廣大研究者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