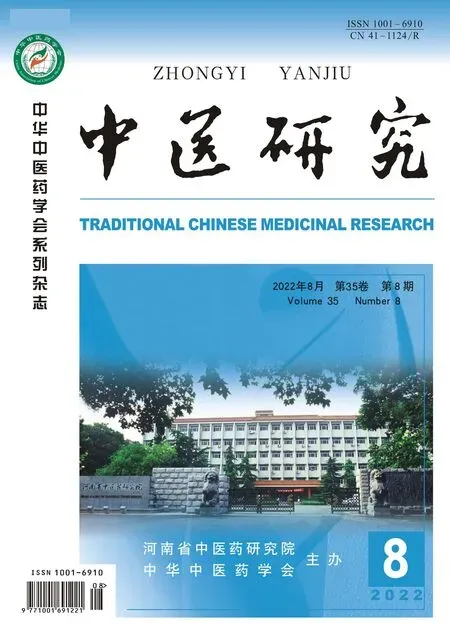宋金傷寒研究中對“六經之為病”的認識*
程傳浩,張海燕,白 楊,李青雅
(河南中醫藥大學,河南 鄭州 450046)
“六經之為病”即《傷寒論》中三陰三陽六病的提綱條文,即“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陽明之為病,胃家實是也”等6條,在《傷寒論》研究中常被視為六經辨證綱領。筆者發現,在宋金時期的傷寒研究中,“六經之為病”并未受到宋金醫家的廣泛重視,反而更加側重于《素問·熱論篇》《傷寒論·傷寒例》逐日傳變的論述,視之為綱領,與明清醫家高度重視“六經之為病”形成鮮明的對比。本文就此現象對現存宋金時期傷寒著作進行考查,總結其對“六經之為病”的認知,并與“熱論”“傷寒例”進行比較,分析其產生的背后原因,以總結此時期傷寒研究的特點,對分析傷寒學術、學派演變的脈絡有一定的意義。
1 《素問·熱論篇》《傷寒例》及“六經之為病”相關內容的比較
《素問·熱論篇》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項痛,腰脊強。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脈俠鼻絡于目,故身熱目疼而鼻干,不得臥也。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脈循脅絡于耳,故胸脅痛而耳聾……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脈布胃中絡于嗌。故腹滿而溢干。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脈貫腎絡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脈循陰器而絡于肝,故煩滿而囊縮。”從經絡角度對傷寒逐日傳變進行分析,并提出三陽宜汗、三陰宜下的治法。《素問·熱論篇》曰:“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于臟者,故可汗而已。”又曰:“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1]
“傷寒例”逐日傳變出自宋本《傷寒論》中“傷寒例”篇。“傷寒例”中“逐日淺深”傳變的條文為“尺寸俱浮者,太陽受病也,當一二日發,以其脈上連風府,故頭項痛,腰脊強;尺寸俱長者,陽明受病也,當二三日發,以其脈俠鼻、絡于目,故身熱、目疼、鼻干、不得臥;尺寸俱弦者,少陽受病也,當三四日發,以其脈循脅絡于耳,故胸脅痛而耳聾”“尺寸俱沉細者,太陰受病也,當四五日發,以其脈布胃中,絡于嗌,故腹滿而嗌干;尺寸俱沉者,少陰受病也,當五六日發,以其脈貫腎,絡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尺寸俱微緩者,厥陰受病也,當六七日發,以其脈循陰器、絡于肝,故煩滿而囊縮”[2]。“六經之為病”即《傷寒論》中論述三陰三陽六病條文,分別為“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陽明之為病,胃家實是也”“少陽之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太陰之為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硬”“少陰之為病,脈微細,但欲寐也”“厥陰之為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食則吐蛔,下之利不止”。“熱論”和“傷寒例”明顯有經絡辨證的印跡,內容相近,都以傷寒為外感熱病,三陰三陽均表現為熱證。但在傳變日數上,“傷寒例”將“熱論”的單日傳變改為約略的雙日傳變,又增加了脈法內容,以脈法為綱,脈證結合,可視為對“熱論”的補充與完善。在治法上三陽宜汗、三陰宜下兩者亦同,可見“傷寒例”與“熱論”是一脈相承的。而“六經之為病”不論是六經證候的復雜性,還是治法的多樣性上,與前兩者明顯不同,如《傷寒論》六經皆有表里、陽明主里、三陰經多虛寒。故而六經之為病更能符合《傷寒論》六經之提綱。此外,“六經之為病”不以“傷寒”起句,直述三陰三陽“之為病”;不述日數而直言脈證,亦不述六病治法。可見,“六經之為病”條文與“熱論”“傷寒例”相比,有明顯的不同之處。宋金醫家研究傷寒多以《傷寒論》為主體,而又以“熱論”“傷寒例”為綱,其間辨證、治法存在諸多抵牾之處,可于“六經之為病”窺其肯綮。那么宋金醫家又是如何認識并處理其間關系就值得深究。
2 宋金醫家著作對“六經之為病”條文的認識及處理
宋代時期傷寒研究著作現存者共14部[3],同時期北方金代亦有《傷寒明理論》《注解傷寒論》《傷寒直格》《傷寒心鏡》《傷寒醫鑒》《傷寒心要》等傷寒研究著作,因其大多有承襲關系,本文選其代表性著作《傷寒微旨論》《傷寒總病論》《類證活人書》《傷寒明理論》《注解傷寒論》《傷寒百證歌》《傷寒百問歌》《傷寒補亡論》為研究對象,進行考查。
2.1 《傷寒微旨論》
《傷寒微旨論》是北宋醫家韓祗和于元祐元年(丙寅,1086年)所撰,以韓氏對《傷寒論》的研究心得為主要內容,又涉及《黃帝內經》《難經》中關于傷寒的論述。韓氏繼承“熱論”以傷寒屬熱證的認識,對傷寒病因提出“伏陽學說”。韓氏重視“熱論”的綱領性意義,在“病源篇”中以“熱論”逐日傳變為綱,釋“傷寒之為病,只受于三陽三陰”之理。在“總汗下篇”中,認為“熱論”所述“三陰三陽受病之日,乃是圣人立條目之法”,治法以汗下為主,“凡治傷寒病,若能辨其汗下者,即治病之法得其十全矣”。對于“傷寒例”,韓氏以為“黃帝作三陽三陰證在前,仲景述三陽三陰脈在后”[4],兩者本質上是一脈相承的。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韓氏對“六經之為病”的內容及條文,全文均未提及。
2.2 《傷寒總病論》
《傷寒總病論》是龐安時約于元符三年(1100年)撰寫的,是作者研讀《黃帝內經》《難經》《傷寒論》,經歷數年而撰成。此書述六經證治,重視“傷寒例”的綱領性地位,三陰三陽六病均以“傷寒例”為綱,其間未論及“太陽之為病”條文,陽明病提及“胃家實”三字[5],少陽證中于“傷寒例”條文下,列“少陽之證,口苦,咽干,目眩也”[5]26;三陰證中在“傷寒例”下列出了“六經之為病”的內容[5]32,與“傷寒例”同列。可見龐氏已重視到“六經之為病”,但整體上仍置于“傷寒例”框架之下,如在治法上循“傷寒例”三陽宜法,三陰證入腑應行下之法;太陰病“宜大承氣湯下之”[5]36,少陰病“大承氣湯下之”[5]38,厥陰證既用“桂枝麻黃各半湯”又“宜承氣湯下之”[5]40。同時,亦保留引用了太陰證“當溫之,以四逆輩”,厥陰證烏梅丸等方[5]44。可見,龐氏對“六經之為病”的處理是以“傷寒例”脈證、治法為主綱,又選擇性保留了“六經之為病”及三陰溫法的部分內容。在處理兩者的抵牾時,龐氏以“傷寒例”為主,兼納部分“六經之為病”,而無辨析。
2.3 《類證活人書》
《類證活人書》成書于1108年,作者為朱肱。卷首“經絡圖”中即以“傷寒例”為主體,設六經證候答,間接引用仲景六經病欲解時及《傷寒論》相關方劑,可見其以“傷寒例”為傷寒之主綱。但對于“傷寒例”的證候表現,又依“六經之為病”而有所增益,如太陽病部分增加了“發熱惡寒”[6]3,少陽病增加了“或口苦舌干,或往來寒熱而嘔”[6]7,太陰病增加了“手足自溫,或自利不渴,或腹滿時痛”[6]11,少陰病增加了“或口中和而惡寒”[6]12,均出處“六經之為病”相關條文。然于陽明病下獨不引“陽明之為病,胃家實是也”[6]13。此外,在卷三、卷四中,“問陽證”“問陰證”中提到了太陽的“發熱惡寒、頭疼腰痛而脈浮”[6]28,陽明的“不惡寒反惡熱,汗出,大便秘”[6]29,少陽的“發熱而嘔,或往來寒熱”[6]33,少陰的“微細心煩,但欲寐,或自利而渴”,厥陰的“消渴,氣上沖,心中疼熱,饑不欲食,食則吐蛔,下之利不止”等[6]34,亦出自《傷寒論》中“六經之為病”部分。可見,朱氏已經重視“六經之為病”的內容及其重要意義,但不能將其與“傷寒例”做區分明辨,僅采用了并列、糅合的方式混于一體,明顯更重視“傷寒例”的綱領性作用。
2.4 注解《注解傷寒論》《傷寒明理論》
《注解傷寒論》《傷寒明理論》為金人成無己所著,書成后傳入南方,為宋人推崇而刊行。《注解傷寒論》開仲景《傷寒論》注解之先河,其意義在于突破了宋人研究傷寒病的模式,轉為研究《傷寒論》本身。即使如此,成無己于《傷寒論》認知的整體學術思想上仍承襲前人,如對于“傷寒例”逐日傳變脈證條文時,與前人認知相較并無創見。在注“六經之為病”原條文時亦未高度重視,注解時復引“傷寒例”為釋;“陽明之為病”,則引用華佗“熱毒入胃”之說;“少陽之病”,引《黃帝內經》《甲乙經》膽經證候。成無己對于“三陰之為病”的注解是遵從“熱論”“傷寒例”的認識,以為三陰病屬熱證。“至四五日,少陽傳太陰經,邪氣漸入里,寒邪漸成熱,當是時也,津液耗少,故腹滿而嗌干。至五六日,太陰傳少陰,是里熱又漸深也”[7],以為三陰皆為陽熱而漸深。如“太陰之為病”,成無己認為“太陰為病,陽邪傳里也”,并以熱證病機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8]8。成氏特意將太陰腹痛與陰寒腹痛進行鑒別。“陰寒在內而為腹痛者,則為常痛”,而“陽邪干里”則為“時腹自痛”[8]53。如“少陰之為病”,成無己注為“少陰為病,脈微細,為邪氣傳里深也。衛氣行于陽則寤,行于陰則寐。邪傳少陰,則氣行于陰而不行于陽,故但欲寐”[8]54,亦當指從熱證而非陰寒。“厥陰之為病”,成無己認為“邪傳厥陰,則熱已深也”[8]55,亦從“熱論”。可見,成氏對于三陰病六經之為病的認識服從于“熱論”及“傷寒例”中六經皆熱的認知,雖注“六經之為病”而不脫熱論、傷寒例之巢窠。
2.5 《傷寒百證歌》
此書為許叔微于南宋紹興二年(1132年)撰成,參考朱肱《類證活人書》,將《傷寒論》中關于證候、方治的內容以七言歌賦形式編為五卷一百證(癥),以便后世學者習誦。許氏對于《傷寒論》中“八綱辨證”的思想著力甚深,然因襲于朱肱,未能突破“熱論”“傷寒例”的認知框架。如卷一“三陰三陽傳入歌”,首引“傷寒例”,如太陽病中“尺寸俱浮者,太陽受病,當一二日發。以其上連風府,故頭項痛,腰脊強”,余經皆如此。對于仲景“六經之為病”內容,存見于卷二、卷三的傷寒癥狀中,如第八十三證“口燥咽干歌”中,引“少陽之為病”;第七十三證“腹滿歌”中,引“太陰腹滿必時痛”;第七十四證“陰證陰毒歌”中,引“少陰之為病”“厥陰之為病”相關內容。但未將其作為提綱處理,而且此幾處顯然將“三陰之為病”的表現當作熱證來認知處理的。
2.6 《傷寒補亡論》
此書為郭雍于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成書。編次“自岐黃以及近代諸書,凡論辨問答證治,合一千五百余條,總五萬字,分七十余門”[9]。該書設問自答,系統總結、討論、梳理了郭氏之前傷寒、熱病中的各種學術問題,是一部傷寒研究階段的總結性著作。此書對傷寒病的認識仍以“熱論”“傷寒例”為宗旨,而“六經之為病”則依然未做深究。如在第二十二問中,系統論述了六經循行、六經日數、六經意義、六經脈狀等主要問題,獨不論及“六經之謂病”。在“六經統論”中,皆從熱論經絡傳變及三陽宜汗、三陰宜下之說,其涉及“六經之為病”處,將其附于“傷寒例”逐日脈法之后,以“又曰”方式復引“六經之為病”。可見郭氏已經重視到六經之為病的條文,但將其附于“傷寒例”條文之后,可見更重視“傷寒例”。總體而言,郭氏仍以仲景“傷寒例”為主,堅持六經病皆為病熱,三陽宜汗,三陰宜下,同時又根據仲景條文做了補充。如厥陰病中,治法方藥就匯總了大承氣湯、桂枝麻黃各半湯、烏梅丸、四逆湯、理中丸、苓桂術甘湯等治法。
2.7 其他著作
宋金時期的其他著作如《活人書括》《傷寒類證》《傷寒要旨》《傷解惑論》《傷寒百問歌》《傷寒直格》《傷寒心鏡》《傷寒十勸》《傷寒醫鑒》《傷寒心要》《傷寒類書活人總括》等書,大多因襲前人之論,受朱肱《類證活人書》影響最大[10],或不論“六經之為病”,或襲前人而將其糅合于“傷寒例”中,并無突破性認識。北方金人又受劉完素《傷寒直格》影響較甚,亦守傷寒從屬于“熱論”之論[11]。
3 宋金醫家未重視“六經之為病”的原因
綜上所述,宋金傷寒著作中多以“熱論”“傷寒例”為傷寒之綱領,對“六經之為病”,或不論涉,或以“或曰”“又曰”的方式附于“熱論”“傷寒例”之下,或糅合于“傷寒例”之中。而“熱論”“傷寒例”與整個《傷寒論》諸多矛盾、抵牾之處,宋人明顯未予以重視。如經絡受病證候與“六經之為病”證候的矛盾,“傷寒例”脈法與“六經之為病”脈證的矛盾,“熱論”“傷寒例”盡為熱病與三陰三陽寒熱并現的矛盾,“逐日汗下”治法與三陽有汗下、三陰汗下溫的矛盾。宋金醫家或已意識到這些問題,但未能深究而有所突破,可能有以下原因。
3.1 研究對象的不同
宋人研究傷寒時,其對象主要是傷寒病,而不是《傷寒論》本身,這一點前人早有論述。宋人研究傷寒病時,雖以《傷寒論》為主體,但以廣義的傷寒熱病為主,包括溫病乃至時病在內。這種研究對象的不同決定了宋金醫家更側重于“熱論”為主要框架的辨證體系,將《傷寒論》條文置于廣義外感熱病的范圍之上,對《傷寒論》條文選擇性引用,同時有所增刪,增以其他醫書、醫論及方劑,又增加溫病[12]及婦兒科內容。
3.2 研究方法的影響
早期的醫著如《諸病源候論》《外臺秘要》《太平圣惠方》等前人著述是以廣納諸論的文獻匯集方法為主,以時間先后為序整理相關內容,則必然以《素問·熱論》為淵藪,其他醫家則為支流。《傷寒論》顯然只是眾多醫家中的一家,故在對待傷寒諸多問題上,仍要從屬于“熱論”等經典理論的局限。宋金醫家研究傷寒時,受以上著作體例及研究方法影響較大[13],故不能舍“熱論”而就“六經之為病”。此外,不辯駁、批判前人,因循經典的遵經思想,亦是造成此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14]。
3.3 認為“傷寒例”為仲景所述
“傷寒例”不但在《諸病源候論》《外臺秘要》《太平圣惠方》中有述錄,而且亦錄于政府主持校訂的宋本《傷寒論》中,作為綱領性內容列于六經病之前。在宋金醫家眼中,“傷寒例”出自《傷寒論》原文,是仲景所述,有高度的權威性,故不否定而必遵從之。
3.4 對《傷寒論》研究的側重
宋金醫家對《傷寒論》本身的研究上亦多側重于證候學,尚未深入理法方藥。如朱肱開《傷寒論》“類證”研究專著之先河之后,《傷寒百證歌》《傷寒類證》《傷寒百問歌》《傷寒類書活人總括》等以傷寒癥為主要研究內容,或設問答,或編為詩賦,便于記誦[15]。故而宋金階段,醫家研究《傷寒論》主要側重于證候學[16],而其他問題尚未及之,這是學術發展的階段性側重所致。
4 明清醫家對“六經之為病”的重視
隨著對傷寒病及《傷寒論》研究的深入,一些醫家意識到宋金醫家的局限之處。如龐安常著《卒病論》、朱肱著《活人書》、韓祗和著《微旨》、王實著《證治》,雖皆互有闡明之義,但未能盡張仲景之深意。方勺《泊宅編》載朱肱《類證活人書》遭時人指摘之事,曰:“肱之為此書,固精贍矣。嘗過洪州,聞名醫宋道方在焉,因攜以就見。宋留肱款語,坐中指駁數十條,皆有考據,肱惘然自失,即日解舟去。”[17]
宋金諸家將“熱論”“傷寒例”六經與《傷寒論》六經混為一談,給深入研究仲景的辨證論治規律帶來了極大的困難,“熱論”“傷寒例”與“六經之為病”為代表的辨證論治體系的矛盾為醫家揭示。為解決此問題,部分醫家將“傷寒例”視為王叔和撰次《傷寒論》時加入的個人認識,而非仲景原文,以此斥責“傷寒例”之非,保證仲景六經辨證的整體精神。元朝王履最早指出王叔和“惜其既以自己之說混于仲景所言之中,又以雜脈雜病紛紜并載于卷首,故使玉石不分,主客相亂”,認為王叔和整理《傷寒論》時將自己的觀點與仲景思想混為一談[18]。明朝方有執承王履之說,認為“傷寒例”等內容為“太醫令王叔和附以己意”所加入,非仲景原文。在此基礎上直接刪“傷寒例”,錯簡重訂,使《傷寒論》的研究擺脫了“熱論”的束縛,從傷寒病的探討轉向辨證論治方法的研究[19-20]。即使主張維護舊論的張志聰、陳修園諸傷寒家也主張刪去叔和序例,可見“傷寒例”與“六經之為病”的學術邏輯的不可調和已成共識。明末喻嘉言直斥叔和之非,“其序例一篇,明系叔和所撰”,并作“駁正王叔和序例”,以為叔和“造不經之說,混亂經常”,“以此網羅英賢,悉入彀中,其授受之途,蓋已千年長夜矣”[21],“龐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祇和、王實之流,非不互有闡發,然不過為叔和之功臣止耳,未見為仲景之功臣也”“林、成二家,過于尊信叔和,往往先傳后經,將叔和緯翼仲景之辭,且混編為仲景之書”[21],明顯在批評宋金時傷寒研究缺陷。明末清初柯琴亦認為:“夫叔和不于病根上講求,但于病名上分解,故序例所引內經,既背仲景之旨,亦舛岐伯之意也。”[22]與之相應的就是“六經之為病”條文的地位得到提升,成為三陰三陽辨證的綱領。如方有執《傷寒論條辨》將“六經之為病”條文移至六病頭條,如認為太陽之為病,“此揭太陽之總病,乃三篇之大綱”;陽明之為病,“胃實反得以揭陽明之總”。此后喻氏《尚論篇》、柯琴《傷寒論注》、尤氏《傷寒貫珠集》等均作此調整,視“六經之為病”為六經辨證的提綱。由此以“錯簡重訂”為端,開始了傷寒學派的爭鳴階段,以“六經之為病”為代表的六經本質的討論,使傷寒研究突破了“熱論”“傷寒例”關于外感熱病的限制,擴大至臨床雜病方面的運用,如柯琴最早提出“夫一身之病,俱受六經范圍者,猶周禮分六官而百職舉,司天分六氣而萬物成耳,傷寒不過六經中一癥”“夫熱病之六經,專主經脈為病,但有表里之實熱,并無表里之虛寒”。同時溫病學派亦因此而脫離傷寒研究,自立門戶[23],亦是傷寒學研究發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