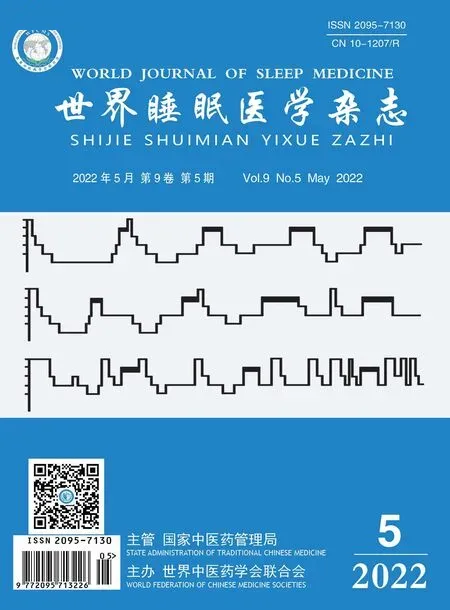軀體癥狀障礙與慢性失眠障礙的關系及研究進展
羅元博 朱玫娟 柴小軍 羅杰
(1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上海,200127; 2 上海國際醫學中心睡眠中心,上海,201318;3 上海太平康復醫院睡眠康復中心,上海,201315)
軀體癥狀障礙(SSD)和慢性失眠障礙(CID)一直困擾著人們的生活,截止至2018年,全球范圍內仍沒有較為準確的SSD患病率統計數據[1]。2017年,中國普通人群的CID檢出率達到了15%,60歲及以上人群高達35.9%[2-3]。這2種疾病嚴重影響了人們的正常生活,有關SSD與CID和抑郁、焦慮之間的關系以及其病理生理等研究也越來越多[4-5]。在一篇關于德國大學生SSD與CID共病率的現況研究中發現,當CID共病于抑郁或焦慮時,SSD的患病率更高[6]。在其他的文章中,我們也發現了很多指向SSD與CID之間聯系的證據。我們認為,有CID的患者應被考慮并存SSD的情況;反之,被懷疑和診斷SSD的患者,應注意是否存在CID;CID可以作為SSD診療效果和復發的主要指標。
1 軀體癥狀障礙和慢性失眠障礙研究的現狀
1.1 軀體癥狀障礙與慢性失眠障礙的基本概念與主要臨床表現 SSD與CID的概念主要參考于DSM-V[7]。全球范圍內仍未有較為準確的SSD患病率數據,但諸多學者相信普通人群SSD的患病率會高于普遍認同的4%[1],SSD的發病率在成人中為5%~7%;2017年國內一項關于門診患者SSD患病率的多中心調研發現綜合醫院門診患者的SSD患病率達33.8%[8]。2017年我國的普通人群中CID的檢出率達到15%[2]。
美國醫學會發表的SSD評估量表-8(SSS-8)中的第八條,以及健康問卷軀體癥狀嚴重性量表-15(PHQ-15)中的第十五條均為“睡眠困難”[9]。國內調研顯示,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PSQI)得分與SSS-8得分成正相關(P<0.05),發現睡眠質量越差,軀體化癥狀、焦慮癥狀、抑郁癥狀越明顯;同時睡眠起始時間(入睡時間)越長,軀體化癥狀越明顯[10]。
本篇綜述從臨床表現,病理生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以及心率變異性(HRV)等方面詳述SSD和CID之間的聯系及研究進展。
1.2 軀體癥狀障礙與慢性失眠障礙的臨床表現聯系
SSD和CID均為精神疾病[7]。精神疾病目前還是依靠臨床表現作為診斷標準,疲憊、焦慮感等都是SSD和CID患者所共有的常見癥狀,且SSD的常見癥狀中便有CID[7,9],這也提示二者的聯系。因此,2種疾病臨床表現出的聯系就顯得尤為重要。
1.2.1 情緒變化 情緒變化常見于SSD和CID[11-12]。通常認為,SSD最常見的臨床表現為慢性的軀體疼痛[13],其會使患者產生情緒變化,許多學者認為這一變化與CID帶來的情緒變化是共通的。
Evans等[13]認為慢性的軀體疼痛帶來的正面情緒及負面情緒會影響CID。其中正面情緒的作用還有待考證,但Subhadra[13]發現負面情緒起到了慢性軀體疼痛和CID的中介者(mediator)的作用,負面情緒的增多使慢性軀體疼痛患者伴發CID的風險增大。
其他學者也發現SSD患者的負面情緒更多,更容易沖動[14],且更難以表達情緒[15]、識別情緒[16];腦電圖顯示,CID患者對情緒的敏感性也有下降[17],且CID患者中也有更多的負面情緒[18]:注意力難以維持[19],沖動性加強[20],低水平情緒表達[21],情緒識別能力下降[22]等。借助fMRI,亦有發現SSD和CID均存在默認模式網絡(DMN)的功能連接(FC)信號增強的現象[23-26],而DMN與情緒的調控有密不可分的關聯[27]。
情緒變化作為二者的共通點或許說明二者存在一定共同的病理機制,比如多巴胺影響沖動[28-29],fMRI下背外側前額葉皮質和頂葉內側溝的信號降低會影響注意力[30];其次,負面情緒的緩解或許在SSD與SD的治療中能有更大的作用;雖然正面情緒缺乏對于CID的影響暫時缺乏臨床證據,但有學者指出正面情緒增多可以阻滯疼痛通路[31],進而改善睡眠,正面情緒的作用仍應受我們重視。
心境障礙作為已有一定病理基礎的病理性情緒變化,它和SSD與CID之間的聯系也應為我們所重視。CID與SSD和抑郁的關聯[6,32-34],和焦慮的關聯[4,7,35]都已被都多方證實,或許從心境障礙的病理基礎出發來研究SSD與CID的病理可以有更多的收獲。
1.3 軀體癥狀障礙和慢性失眠障礙在病理生理上的聯系
1.3.1 痛覺通路 軀體疼痛是SSD最常見的癥狀[7],67%~88%的慢性疼痛患者伴有CID,至少50%的CID患者伴有慢性疼痛,我們不應忽視疼痛與CID間的關聯[36-37]。有學者認為睡眠和疼痛之間的作用為雙向[53],有研究發現夜間人體對疼痛更為敏感,繼而疼痛興奮生理和心理兩方面,從而再次影響患者睡眠[38-39],且有多項研究表明,CID會延長疼痛時間[40-41]。正如DSM-V的SSD的病因中便有“對疼痛的高敏”一條,而CID患者正是符合這一病因的SSD高危人群。在此我們通過阿片受體與褪黑素這兩方面總結了其中CID和SSD的聯系。
1.3.2 阿片受體 阿片受體與CID之間的關系一直是研究的熱點[41]。Wang等[41]在研究小鼠的術后痛與短期快速動眼期睡眠剝奪(REMCI)關系的實驗中,發現當且僅當REMCI與手術同時發生的時候,mu受體和kappa受體才會有顯著下降,小鼠此時會出現術后痛延長,但Kv1.2并無顯著改變。Wang等[41]總結,REMCI本身并不會導致痛覺通路的改變,而是會加重或者延緩疼痛消失。
1.3.3 褪黑素 在CID的病因中,褪黑素的缺乏是目前的一個熱點假說。早期便有研究表明,褪黑素在睡眠節律的調控中起重大作用,并可以起到助眠的效果[42]。褪黑素的前體是5-羥色胺,而5-羥色胺的缺乏正是目前公認的抑郁癥病因,在Hardeland[43]的文章中便有提及關于情緒失調人群中褪黑素總量減少的現象,這也支持了抑郁癥和CID之間的聯系。褪黑素除了在睡眠方面的作用外,還能參與調控焦慮[44]、疼痛[45],這些都是和SSD與CID密切相關的癥狀。在針對肌纖維痛的組合用鎮痛藥的文章中,學者發現褪黑素不論是單用還是聯合用藥,均能顯著提升患者的纖維肌痛影響評估量表評分[46-47];在針對頭痛以及IBS的治療中,褪黑素也有顯著療效[48-49]。
Chen[49]在一項小鼠實驗中發現,褪黑素有選擇性調控小三叉神經神經元Cav3.2通道,從而達到鎮痛的效果作用。研究者總結出褪黑素鎮痛機制為:經MT2偶聯Gβγ蛋白調控的蛋白激酶C信號通路所調控,從而降低三叉神經神經元興奮性以鎮痛。這一結論支持了褪黑素在肌纖維痛、頭痛以及IBS中的鎮痛作用[48-50]。夜間睡眠時,會釋放大量的褪黑素,通過鎮痛的機制防止疼痛干擾睡眠[51],而CID患者夜間的褪黑素分泌不足,弱化原本的鎮痛效果,導致疼痛加劇,影響第2天的疼痛。
1.4 關于情緒變化中多巴胺的研究 Volkow等[52]在一項關于睡眠剝奪和多巴胺(DA)的對照試驗中發現,睡眠剝奪可能存在下調D2,D3受體的作用;對照未剝奪睡眠樣本,睡眠剝奪樣本使用的利他林藥效下降。利他林的藥理機制是阻滯多巴胺轉運體,從而增加DA濃度,這個對照實驗說明了CID可能存在下調D2,D3受體的機制。在CI的癥狀學研究上,Fernandez-Mendoza等[53]發現CID與過度喚醒之間的關聯,而喚醒與保持喚醒狀態正是DA的功能。
我們在上文3.1情緒變化一節中提到,研究發現CID與SSD在情緒變化上均有致使沖動這一項[14,20],而沖動有主由DA調控[28-29],或許SSD患者中的DA水平也會有所改變,或者CID所致的DA受體水平下降或許也會間接影響SSD。CID對DA的具體機制,以及DA對疼痛的定性研究至今仍未有重大突破,或許這些可以作為未來的一個研究方向。
2 功能性磁共振
借助fMRI掃描SSD和CID患者大腦,均發現有DMN FC的增強[25-26]。FC代表著2組神經生理數據之間的統計學相關程度;DMN描述的是靜息狀態下大腦的功能,其功能包括調控情緒[24,27]。有研究顯示,健康人群的DMN FC信號與疲憊、睡眠能力相關[54],在CID患者中,Yu等[26]發現前DMN(aDMN)FC信號增強,而后DMN(pDMN)信號減弱,這點與其他研究相同[55];在健康對照組中,aDMN與pDMN則保持著良好的平衡,aDMN FC下降,pDMN FC升高[23]。在SSD患者中,有文章顯示DMN與SSD的病理可能呈強相關[56],aDMN與pDMN的功能失衡也出現在了SSD患者中[24],且SSD患者在DMN內側前額葉皮質及左角回有增強的神經活動[25,57]。有部分學者提議將這一失衡作為CID或者SSD的影像學指標來參考,或許這可以作為CID和SSD之間的共通點進行研究。
3 心率變異性
研究進一步發現SSD和CID影響情緒表達和情緒識別的機制均為自主神經功能紊亂[58],進而借助HRV來進一步研究[59-63]。HRV常用的指標有連續正常心搏間期均方差的平方根(RMSSD)、低頻帶(LF)、高頻帶(HF)等。LF混合了交感與副交感神經作用,與壓力反射有關;HF代表了副交感神經作用,與呼吸作用有關[62]。在SSD患者中,LF與PHQ-15評分存在強正相關,尤其是女性患者,而男性患者的RMSDD相關度更高[63];對照于健康人群,CID患者在N1期睡眠前出現了顯著增大的LF功率[60]。關于SSD患者自主神經方面的研究至今非常少,主流推測為副交感神經主導軀體化癥狀,由于女性相較于男性更多為副交感主導,所以其LF與PHQ-15的聯系更為緊密[63];此外,SSD作為一個與焦慮癥狀密不可分的疾病,認知行為治療(CBT)顯示出了極好的療效[64],而CBT可以有效提高廣場恐懼癥患者的HRV[65],即也就是穩定其自主神經系統,或許這也提示了SSD與自主神經的關系。在睡眠起始障礙性失眠患者中,他們N1期前的LF功率明顯增大,心率明顯高于正常對照組,直到他們進入N2期后心率才大幅下降;從治療上來看,CBT、放松療法可以緩和CID患者的副交感興奮,從而緩解癥狀,這一點在生理上也與HRV的邏輯一致[66]。以自主神經系統的紊亂為共通點,這也能解釋為什么SSD、CID、焦慮及其他心境障礙疾病會有這么多的交集點,而其中SSD與CID共同出現的LF功率增大提示二者共通的自主神經紊亂。但需要注意,LF作為反應交感與副交感神經混合作用的指標與這2種疾病最為相關,或許也提示我們SSD與CID的神經異常需從交感與副交感兩方面入手。
4 小結
SSD和CID之間的聯系,其背后的生理病理機制已經逐漸為人們所知,當然,SSD和CID之間本質差別也不能因此忽視。SSD和CID之間的作用是雙向的,SSD患者情緒的變化對CID的影響;CID患者阿片受體數量的減少以及褪黑素減少致使的鎮痛效果減弱,DA水平的變化致使患者過早喚醒;抑郁和焦慮在SSD和CID之間所起的橋梁的作用及其背后的機制;fMRI及HRV所提示的相同的參考值,可以作為軀體癥狀障礙和慢性失眠障礙領域研究的參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