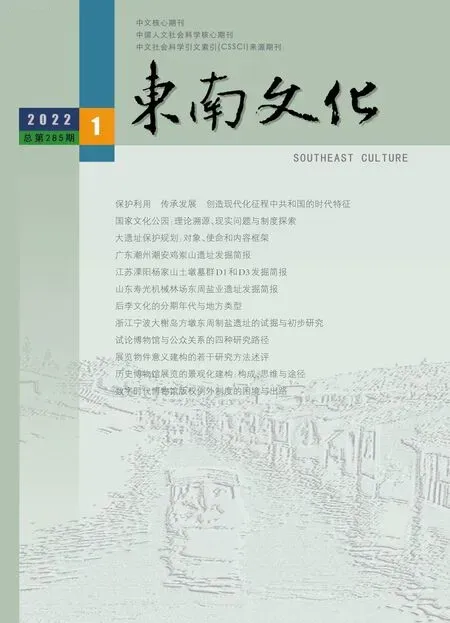晚清民國博物館理論補述
王運良
(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河南開封 475001)
內容提要:鴉片戰爭之后國門洞開,中西文化在不斷碰撞中時時交流融匯,國人逐漸認識到陳列、展覽、博物館的實質內涵與功用所在,并有諸多實踐。同時經過中外縱橫考察與對比,學者開啟了博物館理論研究的先河,建構了博物館學科及專業領域研究的理論框架,對博物館的功能與作用、建設與管理、發展歷史等作了見仁見智的研究。這其中除了張謇、蔡元培、陳端志等學者外,尚有諸多人士也為此積極努力,他們各自的建樹不僅進一步豐富并見證了博物館在中國早期發展階段所取得的理論性成果,更揭示出博物館建設與社會發展、國家命運、民族前途的內在密切關系。
一、引言
晚清民國時期是中國博物館初創與發展的早期階段,這一時期盡管社會動蕩不安,但是國人關于博物館的實踐從未停止,相關的理論思考與探索也是墨耕不輟,其中除了張謇、蔡元培的理論思想以及費畊雨、費鴻年、陳端志、曾昭燏、李濟、傅振倫等人的著述在今天已得到系統梳理并廣為人知之外,尚有諸多人士對其時的中外博物館相關理論作了深入探討與積極引介。惜迄今似無較為全面、系統的挖掘與整理,甚至并不為人所熟知,故筆者對此作一嘗試,以求多方面呈現晚清民國時期中國博物館實踐進程中的理論建樹及其意蘊所在。
歷史資料顯示,在晚清民國時期,見于各類媒體報端、公務文件,由國人建成開放或籌備建設、納入計劃、提議設立的博物館,其總數已過百座,諸如通州博物館、教育博物館、中國交通博物館、水工博物館、鄉土博物館、郵票博物館、衛生博物館等。這些博物館尤其是當時建成并對外開放者,無不引起國人之廣泛關注,觀眾也絡繹不絕,相關的理論探究應運而生,從而為今天留下了諸多寶貴遺產。
二、對于博物館功能的探析
中國博物館的功能在其誕生之時并未像西方博物館一樣經歷了“搜藏—研究—教育”的邏輯進程,而是基于近代中國特殊的社會背景,直面民族危機,慨然承擔起民族復興的歷史重任,其踐責的路徑是充分發揮文化、社會教育功能,提升國民綜合素養,促進國民的文化自覺、經濟振興與民族精神復蘇。
博物館搜集、保存并展示歷代實物,這些實物呈現著民族的個性、凝聚著民族的精神。曾任河南博物館館長的王幼僑最先論述了博物館與民族復興的關系,他認為“復興民族,首要改善民性;改善民性,必明了歷代民族種種情形之不同;欲知歷代民族情形之不同,非就歷代實物上做以證明不可”[1]。由此,博物館“在人文上可以發揮民族的精神,恢復民族的道德,激勵一般的民族意識……博物館之使命,實與民族復興有至密切之關系”[2]。諸多博物館收藏并傳遞文物的藝術之美,曾任上海市博物館籌備委員兼藝術考古部主任的歷史學家鄭師許指出“由美術鑒賞而改變了人生觀,因理解人類過去的生活而惹起愛鄉的觀念,養成愛國的精神,尤其是博物館對于社會教育的最高功績”[3]。博物館展示人類歷史發展軌跡,碑學大家、書法家祝嘉認為博物館是教育的利器,“可以供給不識字的人以知識”“可以喚醒民眾,使民眾油然而生愛國家愛民族的念頭”[4]。文化是城市的內核與靈魂,博物館建設自然應成為都市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曾任上海博物館館長的歷史與博物館學家楊寬指出,都市文化建設應特別著眼于博物館建設[5],中國博物館事業的落后使社會教育不能落到實處,所以,在加緊博物館建設的同時也應做好藏品的搜集、陳列和研究工作,端正民眾對博物館的認識;“博物館必須做到‘深入淺出’,才能發揮巨大的功能”[6]。圖書館學家、翻譯家程伯群認為博物館對于文化的貢獻很大,其地位甚至超過圖書館;博物館是文明的載體,了解中國文化必須研究中國歷史上的發明及事跡,這一點只有到博物館里才可以做到[7]。廣東現代考古事業的開創者胡肇春將現代化博物館定義為博物館的“大眾化”,并要求博物館“把復雜精密的科學、神秘難明的史前人類、變化萬千的動植物生活、至美至善的高深藝術……用最有條理的設計布置、最清晰最引人入勝的說明、最激發人心的暗示、最充足最便利的機會、最周密簡易的方法”,使觀者“時時刻刻感覺到博物館為民眾的大學、為獲取智識的祁鄉”,所以,現代化博物館是以其新目的即“要充實一般民眾的知識和生活”;新態度即“以智識的公仆自任,設法開展及深植其影響”;新方法即“盡量利用所保藏的物品,使物盡其用”為社會作出自己的貢獻[8]。曾任職于上海博物館與同濟大學的考古學者蔣大沂認為博物館應摒棄私利、專求公利,盡力為公眾搜集材料、為公眾整理材料、向公眾陳列材料[9]。博物館學家韓壽萱呼吁全社會充分認識現代博物館的功用,而不能視之為太平時代的點綴物、國家體面的必需品;現代博物館是最能妥善保存古物的機關,是走出十字街頭為大眾謀實際幸福者[10]。
不同性質、不同專題的博物館同樣能夠發揮相應的教育功能。楊寬指出,世界上的博物館已呈現出兩種發展趨勢,一為專門化、一為大眾化,無論何種博物館,在社會教育上都發揮較大的效用,因此,英、荷、美等國還設立了“戶外博物館”“路旁博物館”[11]。考古及博物館學家荊三林指出民俗博物館“是整個人類生活的一種寫照,可以輸入文化知識,可以普及教育,又可供一般學術家的參考,甚而可以因人民的生活而改良社會,這種博物館才是我們中國現在所需要的,而且是最需要的、一種效力最大的博物館”[12];并認為通俗的地方博物館的功用重在進行“完全的一個地方的社會教育”[13]。對于科學博物館,他認為其“是制造文明的場所”,也是發展地方文化、普及教育的大本營,中國就是因為科學不發達,導致不能物盡其用、地盡其利而貧窮落后,所以中國需要建設類似于歐美的科學博物館,推動民族進步與發展[14]。科學家與教育家陳邦杰則直言中國西部科學博物館的創立對于國家民族十分重要,應在全國推廣[15]。地理學家胡煥庸探討了建設邊疆博物館的重要性,指出我國東北諸省、新疆、西藏等已構成邊患,應在首都建立一座邊疆博物館,“此與國家政治外交文化經濟諸端,均有重大關系,一切開發邊疆、充實國力之大業,均將以此為發軔點,其功用固遠在一般普通博物館之上”[16]。曾任上海警察博物館館長、浙江警官學校教官的警政研究專家阮光銘在主持上海港警察博物館籌建時指出,警察博物館是搜集并分類陳列有關警政的各種文物器具、模型圖片的一種有意義的機構,既可以為警政學術探討提供各種資料,也可以為警察自身進修之助,故而“警察博物館在警界范圍內之不可付諸闕如,正如學校在社會的重要性一樣”[17]。發表于《工業安全》的《安全博物館的使命》一文認為,“工業災害的預防、勞工衛生的改善和其他福利設施的進步,以利用博物館最為重要,且是最有效的方法”,“紐約、米蘭、倫敦等都有安全博物館,并各自通過陳列、演講、研究、實驗等,有效促進了工業安全、增進了工人福利。故,安全博物館的使命既在于陳列過去、反映進步,更在于展望未來、指導實踐,對于工業發展和國民經濟均承擔著重要職責”[18]。胡肇春也指出,抗戰勝利之后需要在全國設置“建設博物館”,首都設總館,各地設分館。各館均屬教育部,負責國家社會教育之大部分責任,“尤以普及民眾識字運動,傳授民生日用科學知識,養成技術干部,改善日常生活,增進國民健康為首要任務”;還須緊密跟蹤國家科學發明,“務求一切新的發明發現迅速傳習到民間”[19]。孫志良(生平不詳)認為小學舉辦小型博物館對于增進兒童識別力、促其養成勤勉習慣、節省教師搜集教學標本的時間、免除教學標本再購費用、培育兒童對自然的愛護之心等均有裨益[20]。
與此同時,國人對博物館功能的解讀并未囿于自身的閉門思考,也積極關注國外博物館教育功能的發揮及其研究,并通過翻譯引介相關研究成果,進一步豐富了國人的相關認識。著名教育家楊汝熊的譯作《博物館與學校》指出,博物館已成為“一種具有逐漸增加的責任和廣大的機會之教育機關”,且對博物館教育效能有兩種不同見解:一種觀點認為博物館只能對兒童發揮作用;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博物館是學習之無限可能的地方”,因為其搜藏涉及的思想、宗教、日常生活和態度等方面內容都是學校極少涉及的。美國自然史博物館、菲爾德博物館等博物館開展的館校合作成效顯著,可謂博物館發揮教育效能的典型案例[21]。陳至誠(生平不詳)翻譯的關于日本地方博物館建設的文章闡述了地方博物館網建設的意義與作用,并指出近代博物館的特征在于有社會教育的機能,需要從上至下建立全國博物館網,尤其需要在全國鄉鎮先行建立地方小博物館網,使民眾充分認識到博物館的教育意義,并激發青年人明了地方、愛護地方、開發地方的責任感[22]。這些譯作不僅有利于拓展國人對博物館社會教育功用的認知,更有益于加深時人對博物館與個人、社會、民族、國家發展關系的體悟,進而為特殊時期中國博物館的發展營造有益的社會環境。
三、對于博物館建設的探討
博物館發揮重要的教育作用,自然離不開合適的場地,而場地內的各種設施及其布置也至關重要。
早在1924年,《科學》就有文章指出,太陽光線對陳列品傷害最大,例如西德尼經由試驗得出結論,“陳列室不辟窗戶,全用電光,利益實多,惟不宜于弧光”;盧卡斯指出,“吾輩博物館家既不能制造出透明不過化學放線之玻璃,以濾去日光中之破壞原質,自不得不借重電光解決此問題”,所以博物館建筑必須仰仗人造光源[23]。此可謂國內最早對博物館采光問題的關注。
博物館建筑不同于一般的公共建筑,周盛德(生平不詳)對博物館建筑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認為博物館建筑的各個部分“皆有異于尋常建筑”,同時也是“最宜聚精會神”之處,因此,其建設首要在于“主持者之得人”,其次在于“主持者和建筑師應各知所應為之事”。內部構造尤應先行詳慎規劃,進出口應求其大,演講廳數量、規模、環境應能滿足實際所需,事務室、保存室、總務室、機房、儲藏室等均應妥善設計安置,并保證各自的安全[24]。談福綏(生平不詳)則從博物館選址、性質、采光、各展覽室的連接、各部門位置、扶梯、升降機、內部裝飾等21個方面闡述了現代博物館的設計要素[25]。蔣大沂剖析了博物館的“館”,指出一個地方有一座好的博物館是當地民眾無上的幸福,這既需要館舍內有為大眾服務的“前臺”,也需要有專業人員工作的“后臺”;陳列室和倉庫應注意防塵、防有害光線,陳列室應有充足光線、內部不宜太曲折;演講廳、閱覽室、陳列室應有減弱腳步聲音的設備;全館應備齊防火防盜設備;建筑裝飾不應喧賓奪主,還要留出足夠的拓展空間[26]。他又指出,保存、研究、傳播文物古跡,是所有博物館的責任,所以舉辦者、經費撥付者要積極推動、支持博物館及時搜集藏品[27]。
關于自然博物館的建設,曾任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館長的王念劬指出,博物館應有山林廣場,以供鳥獸之棲處、以備花木之樹藝、以資農作實驗之模范[28]。關于科學博物館,荊三林認為其藏品分類可依照三種標準分類,即用途性能、品質類屬、所在地域;工作內容包括資料(物品)的搜集與制造、資料保管與研究、陳列、說明與演講及標號、實驗與說明;館內可分設總務部、動物部、科學歷史部、植物部、地質礦物部等;還要特別注意人才招攬、館址確定、經費籌集、建筑設計、對外合作等[29]。關于小學舉辦小型博物館,孫志良認為其場所可先簡后繁、從小到大;展品須由師生共同搜集;藏品整理與保管、引導參觀、環境保持等工作應有專人負責[30]。此外,王幼僑指出博物館應注重民族部及其研究范圍,更宜以復興民族為要圖,利用館內所藏器物,對民族歷史作系統考證,探討傳統之事實,以此促進提高民族意識、恢復民族道德、激勵民族精神[31]。
博物館對于學校教育是重要的補充,楊寬認為博物館是學校的公共教室[32],應盡可能做到四“博”:藏物之“博”、搜集方法之“博”、業務之“博”、教育對象之“博”,如此才能成為現代的、活的博物館[33]。博物館如果能時常舉辦特種展覽會,不但可以使觀眾感到耳目一新而多次光顧,還會引發民眾對某一領域的特殊興趣,更能使學者得到充分的研究資料。對此,楊寬概述了上海市博物館相繼舉辦的中國建筑、苗黎風俗、古代玉器、唐瓷瓦窯、抗戰文獻等不同專題的展覽會及其較好的社會效果[34],認為展覽會進一步拓展和提升了博物館的業務。
考古及博物館學家佟柱臣指出,博物館無論何時何地舉辦展覽,均應考慮中國大眾的消化能力,同時也要為專家提供所需的資料;為使博物館在社會教育上發揮更大、更久的效力,可以實行免票制或象征性地收取最低票價;對于鄙遠之區,宜用游動式展覽,同時播放相關影片;博物館內部應成立各專門研究室,定期出版刊物與報告;大館對小館、省館對各縣館都應盡力扶持[35]。曾任武昌文化圖書館學專科學校教務主任、蘇州社會教育學院教授兼圖書館博物館學位系主任的圖書館學家汪長炳指出,博物館在建設之初必須明確四項原則,即“步調須與客觀環境配合”“方針須與各項建設配合”“內容須與用者需要配合”“技術須與所負任務配合”,還要有與國家發展相符合的詳細計劃以及專門人才的積極參與等[36]。曾任國立西北大學圖書館館長的圖書館學家李永增認為一座現代博物館應符合四個重要標準:豐富的收藏、科學地整理藏品、公開展覽、適宜的建筑[37]。
這一時期同樣有對國外相關研究成果的引介。李永增翻譯的《博物館的理想建筑法》一文從基址面積、建筑樣式、儲藏室與售賣處、大廳、盥洗所、用具室、辦公室、中心廳、飲食店、參考室、紀念品等44個方面闡述了如何建設理想、合用的博物館建筑[38]。圖書館學家黃元福翻譯的《小型博物館建筑與設備》從前期準備、設計原則、擴展計劃、光線、天窗、防護功能、防火等多個角度分析了小型博物館在建筑營造、設備安置等方面應注意的事項[39]。曾任職于故宮博物院的趙儒珍的譯作《現代博物館之形式與功用》提倡通過設置無障礙房間、可移動墻壁、可調節人造或自然光,建設“可伸縮性的博物館”;還提倡多建“四郊博物館”,這些博物館可以是一個或多個中樞博物館的分館,兩者分工不同又互相連接[40]。
總之,博物館作為教育的重要場所,如果選址不當、光線失宜、結構欠佳、設施缺漏、尺度失調,展品就不能得到完美呈現,教育功能也不能有效發揮。晚清民國時人也正是基于對國內外博物館諸多的實地或文獻考察與比較,日漸認識到博物館場館建設及其內部設施布置、藏品搜集研究利用的重要性,從而有了系列思考與探索。
四、對于博物館經營管理的研究
在認識到博物館的功用及其應具備良好的場所之后,還需要科學經營管理博物館。缺乏科學、全面、有效的經營管理,同樣不能持續有效發揮博物館應有的功能,這是博物館軟件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關系著博物館的成敗,因此也是晚清民國時人關注的重點內容之一。
博物館的經營管理首先需要明確目標與自身定位,其次需要不斷豐富館藏和加強相關科學研究,同時還要通過各種渠道廣開社會服務之門、與社會各領域展開廣泛合作。天民(生平不詳)在《教育雜志》的《學校博物館之施設》中指出(小學)學校博物館設置目的在于“實際教授上之要求”“處世常識之付與”“發明、發現、創作能力之練磨”“產業思想之養成”“鄉土之理解”。他還闡述了學校博物館陳列材料的選擇與搜集,應圍繞博物館設置目的進行,需要廣大教師的持續努力,積極聯絡公署、工廠、商店等,鼓勵兒童將自有物品帶到博物館等;闡釋了陳列方法也應多樣、靈活,除了在日常教育中有效利用博物館展覽,“家族談話會、卒業生會等也是促進利用的途徑”[41]。曾任教于多所大學的吳家鎮從意義、沿革、組織、內容與教學、種類、改進等多方面對教育博物館作了綜合研究。他指出,教育博物館誕生于1817年的法國,此后,英、德、加等歐美諸國紛紛建立,數量達到了八十余座;教育博物館的陳列內容多包括校舍、校具、教具等實物模型、照片,教育報告、教科書、教育品目錄、校規,學生成績品,教育史材料,實驗儀器設備等;其性質是以學生為直接對象,以服務教學為主要目標;我國的教育館有各縣的通俗教育館、二次全教大會之教育館等,其立意更廣,但應增設導覽、表演人員,加強與學校、家庭、社會的聯絡,并通過演講、表演、邀請觀展、舉辦全體運動會等方式,以一館所在實現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齊豐收[42]。
桑采荑(生平不詳)從征集、陳列、研究三方面論述了博物館完成社會教育使命的基礎、途徑與方式,指出博物館內容的充實全在陳列品的豐富和精湛,需要社會的大力協助;館內的陳列也需要參觀者積極提供改良意見和建議;博物館的研究同樣需要學界的積極合作,實現“學術救國”,博物館是重要的陣地[43]。曾任上海大夏大學社會教育系主任的馬宗榮系統分析了博物館的意義與職能、起源與發展、博物館種類、行政組織、博物館的建立及其設施、博物館的教化事業,指出世界博物館在歷史發展中,其社會化的因子有三:“盧浮宮為代表的大型皇室收藏對外開放、大學及各學校附設博物館的勃興并對民眾開放、博物館陳列方式的改善”。此外,他認為博物館可依據不同標準進行分類,諸如中央的、地方的,普通的、專門的,成人的、兒童的,公立的、私立的等;博物館的行政組織可采用館長制,下設學藝部、事務部,外設評議委員會;中國博物館的建設首先要研究其整體布局,應在各省、市以及大專院校分設不同種類的博物館,各縣設立鄉土博物館,名勝古跡設立戶外博物館,還應提倡興建私立博物館[44]。
程伯群不僅論述了博物館事業與文化建設的重要關系,還認為博物館可分為普通博物館、參考博物館、海洋博物館、工業博物館、農業博物館等;博物館的管理有國立、市立、私立之別;應用技術涵蓋了繪圖、標本采集、標本制造、品質鑒別等[45]。陳邦杰闡述了中國西部科學博物館關于各類資料的搜集、研究、陳列、演講、表演傳播等工作內容,提出全國各城鎮也應設立地方性科學博物館[46]。韓壽萱指出,應通過促進博物館收藏合理化、闡發博物館教育必要性、加強博物館陳列意義化、形成博物館人才專門化等途徑,不斷完善中國現有的博物館[47]。
五、結語
隨著中國博物館在晚清民國時期的產生與發展,張謇、蔡元培開啟了博物館理論研究的先河,費畊雨、費鴻年、陳端志、荊三林、曾昭燏、李濟等建構了博物館學科及專業領域研究的理論框架,與此同時,有更多的業內外人士如楊寬、王幼僑、胡煥庸、周盛德、吳家鎮、李永增等,對博物館的功能與作用、建設與管理、發展歷史等作了見仁見智的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見,由此使中國博物館早期發展階段的理論探索完整呈現。縱觀這些研究,它們有一個共同特點:緊密結合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實際,一方面多角度闡釋博物館的實質內涵及其在開啟民智、普及常識、促進教育事業、增進文化自識、復蘇民族精神乃至振興民族經濟等方面的重要功能;另一方面以博物館發揮這些功能應有的基礎與可用的途徑為核心,詳細探討如何在借鑒歐美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開展“現代化”博物館的建設與經營管理。所以,這些研究不僅具有自身鮮明的時代烙印,而且也呈現了這一時期中國博物館自身的獨特個性。由此可進一步言之,對這些研究的梳理,不單旨在盡可能厘清近代中國關于博物館理論的所有貢獻,更在于揭示博物館文化與國家命運、民族前途所具有的深切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