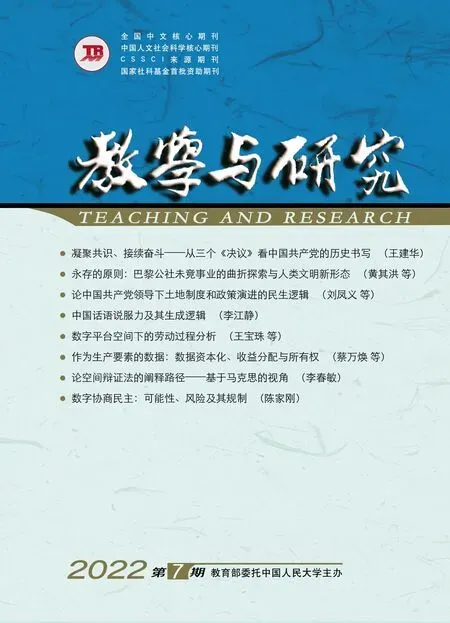論空間辯證法的闡釋路徑
——基于馬克思的視角
李春敏
“空間辯證法”是當(dāng)代空間哲學(xué)的一個基礎(chǔ)性范疇,對“空間辯證法”的闡釋不僅關(guān)涉當(dāng)代空間哲學(xué)元理論的建構(gòu),從空間維度拓展社會批判理論的視野,更關(guān)涉我們?nèi)绾侮U釋由空間哲學(xué)所指引的現(xiàn)實關(guān)切,因為“在今天,遮擋我們視線以致辨識不清諸種結(jié)果的,是空間而不是時間;表現(xiàn)最能發(fā)人深思而詭譎多變的理論世界的,是‘地理學(xué)的創(chuàng)造’,而不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1)[美]愛德華·W.蘇賈:《后現(xiàn)代地理學(xué)》,周憲、許鈞譯,商務(wù)印書館,2004年,第1頁。而對于馬克思主義而言,對“空間辯證法”的探討將直接關(guān)系到我們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空間維度這一重大理論問題的把握。馬克思的“空間辯證法”表明:歷史唯物主義不僅不欠缺空間維度,而且“空間的生產(chǎn)”本身就是馬克思?xì)v史辯證法的應(yīng)有之義。馬克思開辟了獨特的空間辯證法的闡釋路徑,在其中,空間不只是科學(xué)意義上的客觀空間,更是特定的社會歷史過程的構(gòu)造物,是具有社會歷史性的“自然空間”“歷史空間”“社會空間”和“烏托邦空間”;相應(yīng)地,馬克思視野中的空間辯證法同時呈現(xiàn)為自然的辯證法、歷史的辯證法、社會的辯證法和烏托邦的辯證法,并由此展現(xiàn)了一種很有歷史洞見的、既不同于近代空間知識論又在本質(zhì)上區(qū)別于后現(xiàn)代主義和人文地理學(xué)的“大空間”的視野,本文將嘗試對馬克思空間辯證法的闡釋路徑進(jìn)行探討。
一、自然的空間:自然的辯證法
在馬克思的視野中,自然的辯證法是空間辯證法的第一條闡釋路徑,自然既是時間-歷史的,又是空間-地理的,它具有空間的形態(tài)和特性,呈現(xiàn)出地理和場域的向度。在其中,自然以環(huán)境、生態(tài)、景觀及地理等不同的面貌呈現(xiàn),自然作為一種空間,既具有自然屬性,又具有社會屬性。前者是自然科學(xué)視野中的自然,是作為物理空間的自然,而空間辯證法視野中的自然是具有社會屬性的自然,是在特定的社會歷史過程中呈現(xiàn)的自然,它既以“自在的自然”為前提,同時又區(qū)別于“自在的自然”。
馬克思重點關(guān)注具有社會屬性的自然空間,即“人化的自然”。“人化的自然”與“自在的自然”既是馬克思探討自然空間的兩個基本范疇,同時,二者的區(qū)分本身呈現(xiàn)了一種闡釋自然空間的方法論視野。在其中,自然空間一旦被納入人的對象化活動的視閾中,就不再是“自在的自然”,而呈現(xiàn)出人的維度,是人的主體尺度加諸其上的自然空間。馬克思在批判費爾巴哈直觀主義的自然觀時,就指出:“他沒有看到,他周圍的感性世界決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yè)和社會狀況的產(chǎn)物,是歷史的產(chǎn)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jié)果”(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5、55、55-56、57、161頁。。作為人類活動產(chǎn)物的自然空間的現(xiàn)實形態(tài):小到我們的居住空間,大到我們認(rèn)知圖景中的“世界”,現(xiàn)實的人就身處于這樣的自然空間之中。在這里,“人化的自然”既不是作為純粹客體的自然,同時又在本質(zhì)上區(qū)別于“思辨的自然”;既不是純粹直觀的自然,又不是近代機械論視野中的自然,而是歷史的自然、社會的自然、感性的自然、實踐的自然、人類學(xué)的自然。由此,自然的辯證法就不應(yīng)闡釋為單向度的純粹自然的演進(jìn)過程,而是人與自然空間之間不停歇的相互作用。一方面,自然空間作為人的類存續(xù)的前提條件,給予我們空氣、陽光、水和各種人的現(xiàn)實活動所必需的資源,人無法離開自然而生存,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將自然作為“人的無機的身體”(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5、55、55-56、57、161頁。,“人靠自然界生活。這就是說,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處于持續(xù)不斷的交互作用過程的、人的身體。”(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5、55、55-56、57、161頁。在這里,人與自然具有同一性,自然條件直接影響到人類的生活資料和勞動資料的生產(chǎn)。“撇開社會生產(chǎn)的形態(tài)的發(fā)展程度不說,勞動生產(chǎn)率是同自然條件相聯(lián)系的。這些自然條件都可以歸結(jié)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種等等)和人的周圍的自然。外界自然條件在經(jīng)濟(jì)上可以分為兩大類: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魚產(chǎn)豐富的水域等等;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如奔騰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屬、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較高的發(fā)展階段,第二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9頁。另一方面,人現(xiàn)實地利用和改造自然空間,使自然空間呈現(xiàn)主體我的需要、意志和情感,馬克思將“最蹩腳的建筑師”和“蜜蜂”作類比(6)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0頁。,致力于呈現(xiàn)的就是一種基于人的自然辯證法。當(dāng)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jìn)行生產(chǎn)”(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5、55、55-56、57、161頁。時,自然的辯證法便呼之欲出,人將“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作為“關(guān)系”,這一行動本身,構(gòu)成人的主體性的基本維度。“動物不對什么東西發(fā)生‘關(guān)系’,而且根本沒有‘關(guān)系’;對于動物來說,它對他物的關(guān)系不是作為關(guān)系存在的。”(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5、55、55-56、57、161頁。在這個意義上,人又將自身從與自然的同一性中解放出來,將自然空間作為人的對象化活動的客體,謀求一種客體的主體化。人類與自然空間的這種交互作用本身,才是自然的辯證法的真正要義。因此,無論是自然主義還是人類中心主義在本質(zhì)上都是反自然的辯證法的。
由此,自然的辯證法必然是在人與自然空間的現(xiàn)實關(guān)系中呈現(xiàn)的,人與自然空間的關(guān)系形態(tài)主要有以下幾個基本向度:一是人與自然空間的直接同一,這是一種人與自然空間的狹隘的關(guān)系形態(tài),這種關(guān)系形態(tài)是以人的依賴關(guān)系為基礎(chǔ)的。在其中,人類尚沒有足夠改造自然的現(xiàn)實能力,人匍匐在自然的神威之下。二是人對自然空間的全面征服,這同樣是一種人與自然空間的狹隘的關(guān)系形態(tài),這種關(guān)系形態(tài)是以物的依賴關(guān)系為基礎(chǔ)的。其中,自然空間完全成為人的工具,人的活動呈現(xiàn)為對自然的宰制。在上述兩種關(guān)系形態(tài)中,人與自然空間的狹隘關(guān)系是以人與人之間的狹隘關(guān)系為中介的。“人們對自然界的狹隘的關(guān)系決定著他們之間的狹隘的關(guān)系,而他們之間的狹隘的關(guān)系又決定著他們對自然界的狹隘的關(guān)系,這正是因為自然界幾乎還沒有被歷史的進(jìn)程所改變”(9)。三是人與自然空間的和諧共生,這種關(guān)系形態(tài)是對前兩種關(guān)系形態(tài)的揚棄。共產(chǎn)主義作為這種和諧共生關(guān)系的社會空間,真正實現(xiàn)了自然主義與人道主義、自然的屬人性與人的自然性的統(tǒng)一,其中,自然的辯證法得以真正呈現(xiàn)。
在上述探討中,馬克思所探討的自然空間有三重指向:一是經(jīng)濟(jì)維度的自然空間,它是人的物質(zhì)實踐活動的前提,是作為“生產(chǎn)物質(zhì)生活本身”(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1、158頁。的現(xiàn)實條件的自然空間;二是政治維度的自然空間,它是政治權(quán)力加諸其上的自然空間,是覆蓋主權(quán)和政治管轄的自然空間,是作為一種政治符號的自然空間,是建構(gòu)共同的政治認(rèn)同和集體行動的自然空間;三是文化維度的自然空間,它直接關(guān)涉人作為一種“類存在物”的空間歸屬,是差異化的非同質(zhì)的自然空間,是建構(gòu)精神家園的自然空間、是地方性的象征空間。三者之間相互深刻地關(guān)聯(lián)著,現(xiàn)實的自然空間同時具有以上三個指向。
馬克思關(guān)注人與自然空間之間關(guān)系演進(jìn)的動力學(xué),指出這種動力學(xué)只能落腳到人的對象化活動中,人與自然空間關(guān)系的演進(jìn)過程是與人的對象化活動深刻關(guān)聯(lián)在一起的。一個明證是當(dāng)代科技正在不斷拓展人類視野中的自然空間的邊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對自然空間的理解在不斷拓展和深化,前資本主義空間視野中的“神秘的自然”空前清晰地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從我們的身體空間,到當(dāng)代天文學(xué)不斷解鎖的新的宇宙空間,都是人的現(xiàn)實的對象化活動的結(jié)果。我們對自然的認(rèn)識關(guān)系和實踐關(guān)系都與前資本文明不可同日而語。“我們可能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意識到自己根本上是空間的存在者,總是在忙于進(jìn)行空間與場所、疆域與區(qū)域、環(huán)境與居所的生產(chǎn)。”(11)[美]愛德華·W.蘇賈:《后大都市——城市與區(qū)域的批判性研究》,李鈞等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8頁。在空間辯證法的視野中,自然空間不是某種給定之物,恰恰相反,自然空間的現(xiàn)實生成是特定社會過程的環(huán)節(jié),這個環(huán)節(jié)是待揚棄的,是作為后續(xù)環(huán)節(jié)的中介。在這里,“處理空間問題的方法不能夠僅僅包括一種形式的、邏輯性的方法;它應(yīng)該而且同樣地能夠是一種辯證的方法,對社會和社會實踐中的空間的矛盾加以分析。”(12)[法]亨利·列斐伏爾:《空間與政治》,李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9頁。在這個意義上,自然的辯證法不只是對現(xiàn)存自然空間的描述,更具有一種未來性的向度,它指向的是一種流動的生成論的自然圖景。在這個過程中,人與自然空間的對抗和沖突始終以不同的形態(tài)存在,這種對抗和沖突一方面造成了人與自然關(guān)系的危機,另一方面推動人與自然關(guān)系向新的形態(tài)發(fā)展。馬克思呈現(xiàn)了資本視野下人與自然空間的辯證法,其中,自然空間被資本宰制,資本與科技呈現(xiàn)為一種共謀關(guān)系。馬克思指出,只有在資本的條件下,科技在生產(chǎn)中的直接運用才表現(xiàn)得如此普遍。只有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學(xué)為直接的生產(chǎn)過程服務(wù),“只有資本主義生產(chǎn)才第一次把物質(zhì)生產(chǎn)過程變成科學(xué)在生產(chǎn)中的應(yīng)用”。(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76頁。由于科技對自然的開發(fā)和利用納入了資本的軌道,科技理性的過度膨脹必然帶來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的潛在危機,自然空間岌岌可危,這提示了資本的內(nèi)在的反生態(tài)性。而資本條件下人與自然空間關(guān)系的危機是新的人與自然關(guān)系的中介,這一關(guān)系形態(tài)隨著資本邏輯的消解將被揚棄。
二、歷史的空間:歷史的辯證法
歷史的辯證法是空間辯證法的第二條闡釋路徑,也關(guān)涉馬克思空間辯證法必須申明的根本立場,即空間辯證法不能脫離時間-歷史的視野,馬克思的歷史哲學(xué)是空間辯證法和歷史辯證法的統(tǒng)一。具體來說,一方面,歷史闡釋無法離開空間,空間本身是歷史敘事的現(xiàn)實載體。我們的歷史意識包含著各種地理結(jié)構(gòu)、空間規(guī)劃和地方性秩序等空間要素,離開了這些空間要素,歷史就變成不可言說之物。因此,沒有所謂絕對的、一般的歷史,只有具體的、現(xiàn)實的歷史,即特定的社會空間中呈現(xiàn)的歷史。處在同一個歷史階段的不同民族和地域往往表現(xiàn)出深刻的空間差異性,這種空間差異性必須被納入歷史闡釋的視野中,才能呈現(xiàn)真正有生命力的歷史科學(xué)。歷史“一般”只是在多樣的差異化的歷史空間中表現(xiàn)出來的一種具體的同一性,離開了差異化的歷史空間,歷史“一般”就是一種空洞的抽象。事實上,缺失空間向度的歷史敘事正是馬克思所批判的“歷史編纂學(xué)”的路徑,它本質(zhì)上是一種單向度的歷史敘事,歷史表現(xiàn)為一種均質(zhì)的線性進(jìn)程,歷史的過程不過是一種必然性的展開,是消弭了各種空間差異性的歷史。另一方面,空間敘事內(nèi)含歷史向度,沒有歷史維度的注入,空間就淪為一個外在于社會歷史過程的被動的地理容器,導(dǎo)向一種實證主義的地理學(xué),這是近代以來空間知識論的主導(dǎo)敘事,只要我們追問:如此這般的地理學(xué)是如何被生產(chǎn)出來的?如何理解它與現(xiàn)實的社會歷史過程的關(guān)系?這種空間敘事就會陷入本質(zhì)性困境中,空間生產(chǎn)的社會意蘊被遮蔽了,空間的本質(zhì)無法得以澄清,在這個意義上,離開了歷史視野的空間敘事無法把握空間生產(chǎn)的真正內(nèi)核。由此,空間辯證法就與歷史辯證法處于本質(zhì)性的深刻關(guān)聯(lián)中。具體來說,每一個特定的歷史過程都有自己的空間視野,都有空間生產(chǎn)的特定形態(tài),都會生產(chǎn)特定的地理學(xué)。
上述探討涉及歷史唯物主義亟需澄清的一個重大理論問題,即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空間化改造,這本質(zhì)上是一個偽問題,歷史唯物主義并不欠缺空間的維度,我們所要做的是使這種維度得以呈現(xiàn),還“空間”于“歷史”。歷史唯物主義不是只有歷時性的時間維度,更有并時性的空間維度。馬克思開創(chuàng)性地呈現(xiàn)了在多樣化的歷史表象后的客觀的歷史結(jié)構(gòu),歷史唯物主義本身呈現(xiàn)了一種很有洞見的空間視閾。歷史是以空間的方式展開的,每一個特定的歷史時點都對應(yīng)著特定形態(tài)的空間生產(chǎn),這種空間生產(chǎn)是由特定的物質(zhì)條件和交往方式來決定的。馬克思指出:“歷史的每一階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質(zhì)結(jié)果,一定的生產(chǎn)力總和,人對自然以及個人之間歷史地形成的關(guān)系,都遇到前一代傳給后一代的大量生產(chǎn)力、資金和環(huán)境,盡管一方面這些生產(chǎn)力、資金和環(huán)境為新的一代所改變,但另一方面,它們也預(yù)先規(guī)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條件,使它得到一定的發(fā)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質(zhì)。”(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2頁。歷史的載體是這些空間性展開的現(xiàn)實生活過程,體現(xiàn)在:每一代人都會生產(chǎn)自己的空間敘事,建構(gòu)特定的社會空間形態(tài),都有特定的空間實踐方式,包括特定的場所記憶、環(huán)境條件、地理景觀和空間隱喻等,都會建構(gòu)具有各自時代性的生存圖景,而歷史的演進(jìn)過程就是不同的歷史空間的轉(zhuǎn)換過程,是舊的歷史空間的瓦解和新的歷史空間的生成過程。馬克思的歷史哲學(xué)通過對歷史的空間結(jié)構(gòu)的闡釋,呈現(xiàn)了歷時性演進(jìn)中的歷史空間的“認(rèn)知圖繪”,在其中,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均具有空間維度,指涉特定歷史過程的空間秩序。
這樣,空間辯證法必須在特定的歷史性展開的社會過程中得以呈現(xiàn),離開了這個過程,空間辯證法便喪失了獨立的外觀。在這個意義上,空間的辯證法就是社會-歷史的辯證法,空間生產(chǎn)的矛盾本質(zhì)上就是現(xiàn)實的社會歷史過程的矛盾。空間辯證法旨在呈現(xiàn)歷史空間生產(chǎn)的動力學(xué),致力于回答如下問題:特定歷史進(jìn)程中的空間是如何被生產(chǎn)出來的?又是如何內(nèi)在性地生產(chǎn)出自身的對立物的?由這種對立物所指引的空間生產(chǎn)的未來性如何?以資本主義的空間生產(chǎn)為例,它本質(zhì)上是由資本的積累塑造的,資本的積累過程就是不停歇地“用時間來消滅空間”(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6頁。的過程,是不斷消除空間壁壘,實現(xiàn)交換關(guān)系的空間解放的過程。民族-地方的空間視野不斷被全球-世界的空間視野所取代,這就是資本條件下的空間生產(chǎn)的特定形態(tài)。空間本身成為商品,并作為資本運動的特定環(huán)節(jié),現(xiàn)實地參與到資本體系的生產(chǎn)中,空間或作為資本流通的重要參量,或成為資本積累的現(xiàn)實載體。具體來說,資本運行過程中的空間主要有幾個向度:交換關(guān)系的空間解放、作為勞動客觀條件的“空間”、生產(chǎn)要素的空間整合、作為資本流通的“空間”(16)參見李春敏:《馬克思的社會空間理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5-162頁。,而無論在哪一種情形中,空間都不再是一個抽象的被動容器。在這個過程中,資本內(nèi)在性地生產(chǎn)出空間的沖突。具體來說,資本的空間延展帶來了社會空間的普遍物化,從作為一種微觀空間的身體到全球化空間,由此生產(chǎn)出諸種異化的空間。空間不是感性的差異化空間,而是同質(zhì)的商品空間,人與空間是疏離的對抗性關(guān)系,空間成為統(tǒng)治人的工具,空間多維的社會意蘊被遮蔽,空間的生產(chǎn)由此喪失它的真正內(nèi)核。這種沖突是由資本內(nèi)在地生產(chǎn)出來的,同樣,空間生產(chǎn)的未來性也是由這種沖突內(nèi)在地指引出來的,即重建空間生產(chǎn),必須揚棄資本的邏輯,重塑空間的生產(chǎn)與人的感性的多維關(guān)聯(lián),釋放差異化的空間活力,使空間生產(chǎn)重新回歸對使用價值的關(guān)注和對人的空間需要的滿足。
三、社會的空間:社會的辯證法
社會的空間不是一個實體性的空間,而是作為一種關(guān)系形態(tài)的空間,社會的辯證法呈現(xiàn)的是作為個體的人與外在的社會環(huán)境之間的相互作用。這種關(guān)系體現(xiàn)為個體的人與社會之間既彼此關(guān)聯(lián),又相互沖突。一方面,個人是社會的主體,“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chǎn)物。”(1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8頁。社會本身是人的對象化活動的空間延展,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空間,呈現(xiàn)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空間并存及交互作用,是作為復(fù)數(shù)的人的生存情境。另一方面,社會空間一經(jīng)生成,又是外在于人的,作為約束人的環(huán)境和條件,賦予人的存在一種形式規(guī)定,正是這種“形塑”建構(gòu)了人的社會性。具體來說,社會空間的“形塑”主要有兩個向度:一是社會空間作為人的解放的現(xiàn)實條件。馬克思的解放敘事內(nèi)含一種空間向度,對應(yīng)著一系列的場所記憶、地理重構(gòu)、地緣政治和空間策略等,以《共產(chǎn)黨宣言》為例,“仔細(xì)考察就會發(fā)現(xiàn),關(guān)于地理轉(zhuǎn)型、‘空間定位(spatial fixes)’和不平衡地理發(fā)展在資本積累的漫長歷史中的作用,《宣言》包含了一個獨特的論證。”(18)[美]大衛(wèi)·哈維:《希望的空間》,胡大平譯,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6年,第23頁。在這個意義上,人的解放就是人賴以生存的社會空間的解放,人的解放與社會的解放本質(zhì)上是統(tǒng)一的。二是社會空間本身作為奴役人的社會條件。社會空間成為人的解放的枷鎖,相應(yīng)地,人的現(xiàn)實解放的過程就是不斷打碎舊的社會空間,建構(gòu)新的社會空間的過程,是社會空間不斷轉(zhuǎn)換的過程。
馬克思將人的本質(zhì)闡釋為人的社會性,人的歷史發(fā)生學(xué)只能在社會的意義上才能被闡釋。“人的自然”本身是一種“社會的自然”,后者不僅指向人的自然身體,馬克思指出:“五官感覺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歷史的產(chǎn)物”。(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6頁。自然身體本身是特定的社會歷史過程的產(chǎn)物,更指向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構(gòu),因為“意識一開始就是社會的產(chǎn)物,而且只要人們存在著,它就仍然是這種產(chǎn)物。”(20)人身處于其中的社會空間本質(zhì)上是一種社會關(guān)系的網(wǎng)絡(luò)體系,是人與人之間并存關(guān)系的空間載體。在這里,關(guān)系的生產(chǎn)就是空間的生產(chǎn),馬克思賦予這種生產(chǎn)以存在論意蘊,它是人的主體性的基本維度。馬克思指出:“凡是有某種關(guān)系存在的地方,這種關(guān)系都是為我而存在的;動物不對什么東西發(fā)生‘關(guān)系’,而且根本沒有‘關(guān)系’;對于動物來說,它對他物的關(guān)系不是作為關(guān)系存在的。”(21)正是基于關(guān)系視野,確切地說,是能動建構(gòu)起來的關(guān)系視野,從現(xiàn)實上塑造了人的本質(zhì)的社會性。馬克思在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經(jīng)濟(jì)學(xué)家蒲魯東先生非常明白,人們是在一定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中制造呢絨、麻布和絲織品的。但是他不明白,這些一定的社會關(guān)系同麻布、亞麻等一樣,也是人們生產(chǎn)出來的。社會關(guān)系和生產(chǎn)力密切相聯(lián)。隨著新生產(chǎn)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chǎn)方式,隨著生產(chǎn)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guān)系。”(22)人的自我生成囿于純粹的意識領(lǐng)域是無法完成的,而是要訴諸于社會的形式,在現(xiàn)實的社會空間中才能完成,將人的自我生成作為一種純粹的思想活動,訴諸于抽象的實體、主體、自我意識,這恰恰是思辨哲學(xué)的窠臼。在這個意義上,社會空間的生產(chǎn)與人的自我生成本質(zhì)上是同一個過程。
社會空間作為一種關(guān)系形態(tài)的空間,從這種關(guān)系的內(nèi)容來劃分,可以具體分為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政治關(guān)系和文化關(guān)系,三者形成特定的空間結(jié)構(gòu)。其中,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確切地說,是人們在生產(chǎn)中的地位和相互關(guān)系處于基礎(chǔ)性的地位,而政治和文化關(guān)系受到現(xiàn)實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的制約,三者共同建構(gòu)了一定歷史階段的社會形態(tài)。在空間辯證法的視野中,社會形態(tài)本身就是一種空間構(gòu)型,不同的階層、人群共同體處身于其中,對應(yīng)著空間中的不同位置,通過這些位置,即空間中的“點”,我們能夠描繪出不同階層的生存境遇,這些位置就是人的生存經(jīng)驗的一種空間隱喻。社會關(guān)系的空間圖式不是凝固的,而是不斷流動的空間圖景。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正是致力于呈現(xiàn)一種社會關(guān)系的“空間圖繪”,包括這一空間圖式變化演進(jìn)的辯證邏輯。
社會的辯證法旨在表明:人與社會空間的沖突,本質(zhì)上不是人與一個外在于自身的他者的沖突,而是人與自身的沖突,是人與自身的對抗,社會空間的變遷本質(zhì)上是人對自身的否定的環(huán)節(jié)。當(dāng)社會空間呈現(xiàn)為一種異化于人的本質(zhì),社會空間的變遷就會發(fā)生,舊的社會空間瓦解,新的社會空間生成,而新的社會空間同樣不會成為終點,同樣潛藏著人與社會空間之間的沖突和對抗,同樣是待揚棄的。因此,空間辯證法通向的不是一種僵化的理想的空間構(gòu)型。毋寧說,空間辯證法開啟的是一種人與社會空間之間不停歇的對抗,以及由這種對抗所指引的“消滅現(xiàn)存狀況的現(xiàn)實的運動”(23)。因此,在空間辯證法的視野中,所有的社會構(gòu)型都具有暫時性,以及由這種暫時性所指引的未來性,這種對抗既有經(jīng)濟(jì)向度的,又有政治與文化向度的,三者彼此確證,經(jīng)濟(jì)上占統(tǒng)治地位的階級,同時在政治和文化上亦具有統(tǒng)治性的話語權(quán)。“支配著物質(zhì)生產(chǎn)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chǎn)資料”(2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1、161、222、166、178頁。,不同階級之間的關(guān)系是一種社會意義上的空間關(guān)系,并對應(yīng)著空間實踐的不同形態(tài)。
四、烏托邦的空間:烏托邦的辯證法
烏托邦的空間是具有價值維度的空間,它同樣不是一個實體性的空間,而是一個差異化的精神空間,是給現(xiàn)實的空間生產(chǎn)注入想象維度的空間。它既是現(xiàn)實的社會空間的折射,同時,又反過來作用于現(xiàn)實的社會空間,對烏托邦的空間與現(xiàn)實的社會空間之間關(guān)系的呈現(xiàn),是空間辯證法的重要維度。
具體來說,烏托邦的空間主要有四重指向:情感投射的空間、文化想象的空間、審美體驗的空間和意義建構(gòu)的空間。作為情感投射的空間,烏托邦的空間指向空間生產(chǎn)的文化-心理維度。它是與客觀的物理空間相對的,人與社會空間的關(guān)系不僅是認(rèn)識和實踐關(guān)系,更伴隨著情感與體驗關(guān)系。人在空間的生產(chǎn)中投入熱情、注入渴望、表達(dá)多樣性的情感需求,在空間的生產(chǎn)中建構(gòu)家園意識,探尋精神的棲居處。作為文化想象的空間,烏托邦的空間指向一種精神秩序的建構(gòu)。其中,空間的生產(chǎn)不是純粹的技術(shù)性活動,而是多重的精神世界的呈現(xiàn),是推進(jìn)對自我的深層理解的空間,是生產(chǎn)希望和理想的可能性空間。烏托邦空間的豐富性表征人的積極存在,而烏托邦空間的匱乏往往以隱性的方式指向現(xiàn)存秩序的困境。作為審美體驗的空間,烏托邦的空間是作為審美活動載體的空間,是詩性的空間、藝術(shù)的空間。其中,空間不是單向度的功能性空間,更承載美的價值。作為一種豐富的美學(xué)文本和多維的象征空間,并以美學(xué)的方式關(guān)切現(xiàn)實世界。作為意義建構(gòu)的空間,烏托邦的空間致力于呈現(xiàn)人與現(xiàn)實世界多維的意義關(guān)聯(lián),是注入人文關(guān)懷的空間,是建構(gòu)價值認(rèn)同和促進(jìn)社會動員的空間。在現(xiàn)實的空間生產(chǎn)中,與其說人是在與實體性的空間打交道,不如說,人是在與一個意義的空間打交道。“從我們建構(gòu)的空間中就可以洞悉我們靈魂的模樣,就能夠抵達(dá)我們的自由與限制。我們建構(gòu)了什么樣的空間,就代表著我們需要什么樣的精神土壤。”(25)李春敏:《大衛(wèi)·哈維的空間批判理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18年,第201頁。以上四重指向彼此不是割裂的,而是深刻關(guān)聯(lián)在一起。
烏托邦的空間具有批判和超越雙重維度,批判的維度指烏托邦空間本身是作為現(xiàn)存的空間秩序的他者,是對現(xiàn)存社會空間的一種批判性重構(gòu),是現(xiàn)存秩序的自否定的產(chǎn)物。作為現(xiàn)存秩序的“規(guī)訓(xùn)者”,烏托邦的空間旨在呈現(xiàn)現(xiàn)存空間秩序的有限性;超越的維度是指烏托邦的空間致力于建構(gòu)一種可能性的空間,它指引出一種未來性和成長性的空間,烏托邦的空間是對現(xiàn)存的社會空間的一種反叛。由此,烏托邦的空間連接著一種解放敘事,作為一種否定的空間,烏托邦的空間蘊藏著隱性的社會動員和集體行動的力量。事實上,每一種社會空間的生產(chǎn)都同時伴隨著烏托邦體系的生產(chǎn),前資本主義的烏托邦體系是基于“人類的地方性發(fā)展和對自然的崇拜”(26)。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地方性視野的有限性不斷被突破,自然只是資本建構(gòu)的普遍的有用性體系的環(huán)節(jié),在這個體系之外,自然不再表現(xiàn)為一種“自為的力量”(27),因此喪失了烏托邦的維度。“資本按照自己的這種趨勢,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見,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現(xiàn)象,克服流傳下來的、在一定界限內(nèi)閉關(guān)自守地滿足于現(xiàn)有需要和重復(fù)舊生活方式的狀況。”(28)除了相對于資本而言的“有用性”,“再也沒有什么東西在這個社會生產(chǎn)和交換的范圍之外表現(xiàn)為自在的更高的東西,表現(xiàn)為自為的合理的東西”(29)。
具體來說,資本主義創(chuàng)造了一個打著物化烙印的想象體系,一個充斥著物的幻象的烏托邦空間,其中包括致富的想象、平等的想象、自由的想象、自我實現(xiàn)的想象、物的繁盛的想象等。一方面,這些“想象”及其指涉的欲望體系是資本文明的產(chǎn)物,是資本體系得以存續(xù)的精神條件。以致富欲望為例,在資本的條件下,“因為每個人都想生產(chǎn)貨幣,所以致富欲望是所有人的欲望,這種欲望創(chuàng)造了一般財富。因此,只有一般的致富欲望才能成為不斷重新產(chǎn)生的一般財富的源泉。”(30)與一般的致富欲望對應(yīng)的是一種新的貨幣哲學(xué),“貨幣作為發(fā)達(dá)的生產(chǎn)要素,只能存在于雇傭勞動存在的地方;因此,只能存在于這樣的地方,在那里,貨幣不但決不會使社會形式瓦解,反而是社會形式發(fā)展的條件和發(fā)展一切生產(chǎn)力即物質(zhì)生產(chǎn)力和精神生產(chǎn)力的主動輪。”(3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3、393、393、393、173、173頁。另一方面,這些“想象”又以隱性的方式干預(yù)現(xiàn)實的資本過程,表現(xiàn)在這些“想象”隨著資本的歷史運動而破產(chǎn),其結(jié)果是資本本身不再支持這種想象,它的真實的幻象的邏輯呈現(xiàn)出來。由此,經(jīng)由想象體系催生一種替代性方案的可能性,資本體系的瓦解首先是關(guān)于資本的想象體系的瓦解。具體來說,與“物的世界的增值”并行的是“人的世界的貶值”(32),人自身被納入資本建構(gòu)的普遍有用性的體系之中;相應(yīng)地,人在被資本的權(quán)力同質(zhì)化的過程中,不斷喪失感性的豐富性,與普遍物化的社會生活相對應(yīng)的是人的烏托邦體系的匱乏。其中,以交換關(guān)系為基礎(chǔ)的消費和占有關(guān)系成為人與世界關(guān)系的主導(dǎo)形態(tài),物的體系本來是作為中介,現(xiàn)在它成為統(tǒng)治一切的神,資本不斷在創(chuàng)造關(guān)于物的豐富性的神話,營造一種所謂的“消費的盛宴”;而人自身卻不斷湮沒在物的泥沼中,資本由此建構(gòu)了一個“見物不見人”的虛假的世界和虛無的世界。共產(chǎn)主義作為揚棄資本邏輯的社會空間,同樣也生產(chǎn)與這一空間相匹配的想象體系,這一想象體系將重新建構(gòu)關(guān)于財富、自由、平等的話語。
馬克思視野中的空間既是自然的空間、歷史的空間,又是社會的空間、烏托邦的空間;相應(yīng)地,馬克思的空間辯證法同時呈現(xiàn)為自然的辯證法、歷史的辯證法、社會的辯證法和烏托邦的辯證法四個向度。因此,以上四條闡釋路徑彼此深刻關(guān)聯(lián),具體來說,自然的空間既是歷史的空間,又是社會的空間,同樣,歷史的空間也是自然的空間和社會的空間。馬克思批判傳統(tǒng)歷史觀所呈現(xiàn)的“自然界和歷史之間的對立”(33)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1、173頁。,重申將“人對自然界的關(guān)系”從歷史中排除出去,這種對歷史的闡釋本質(zhì)上是非歷史的。而社會的空間就是“人化的自然”,是嵌套于特定歷史過程中的空間構(gòu)型。因此,社會的空間既是自然的,又是歷史的。烏托邦空間作為一種精神空間,內(nèi)在于自然的空間、歷史的空間和社會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