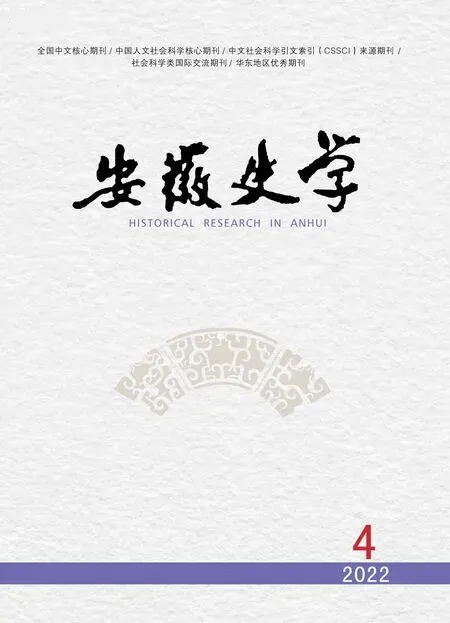拒援臨淮:同治二年李鴻章與曾國藩的戰略分歧
顧建娣
(中國社會科學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同治二年(1863)三月,苗沛霖降而復叛。四月初二日,清廷通告討伐苗沛霖,令親王僧格林沁、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安徽巡撫李續宜、唐訓方、漕運總督吳棠各撥重兵,四面兜剿,并命前漕運總督袁甲三在籍協同剿辦。但此時李續宜丁憂在籍,所部由曾國藩調遣;湘軍在皖兵力又為皖南太平軍牽制;僧格林沁堅持待鎮壓直隸、山東等地捻軍事畢再回皖。討苗只得先由曾國藩一人負責。曾國藩派蔣凝學、毛有銘、成大吉、周寬世率部援壽州,派太湖水師統領李朝斌帶10營赴滬,替換署江南提督淮揚水師統領黃翼升,由黃翼升帶水師六、七營入淮,“掃清澮、渦、淮、淝、汝、潁諸巨川,俾苗逆不得盡收水濱之利”。(1)《近日金陵江北江西及援壽剿苗軍情片》(同治二年五月十二日),《曾國藩全集》第6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197頁。
但曾國藩檄調黃翼升水師不符合李鴻章的戰略意圖。同治元年六月十四日,李鴻章與黃翼升巡查上海、江南各處水道,發現“松江以西,與蘇州接壤,南與嘉興接壤,湖河泛漲,支流港汊,千百縱橫,岸低橋少,水戰最宜。將來夾攻蘇、浙,必須由此取徑。”(2)《察看泖淀各湖水路情形片》(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李鴻章全集》第1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頁。當日向曾國藩匯報:“蘇、嘉、青、昆各來路竟有汊河數十條,處處可通,實無總口可以收束。岸低無橋,若駛入江浙腹地,賊必首尾難救,將來平吳方略,此處定要一支好水師,愈多愈妙,愈小愈靈。敬求吾師籌及。”(3)《上曾制帥》(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李鴻章全集》第29冊,第98頁。即李鴻章找到了由滬進攻蘇南太平軍的方略。李鴻章建議,太湖水師不若改由泖湖、淀山湖沖入,無陸師尚可自立,有陸師更好依附。如果李朝斌赴滬,黃翼升所部則“不虞單弱,仍可分余力回顧靖江以上防務”。(4)《上曾制帥》(同治元年七月十九日),《李鴻章全集》第29冊,第103—104頁。曾國藩遂將原定太湖水師由東壩攻入蘇南的路線,改從上海進兵,由泖湖、淀山湖攻入蘇州、嘉定、湖州三郡縣。同治元年七月初九日,李鴻章向彭玉麟言:“昌歧所部,分扼淀、泖各湖,實嫌其少,將來攻蘇州、進太湖,取徑甚捷,亦最中要害,似未可令移他處。”(5)《復彭侍郎》(同治元年七月初九日),《李鴻章全集》第29冊,第102頁。同日對左宗棠言,李秀成自率三四千人赴援金陵,“此去必敗,敗則江南各郡縣可先得手,似不爭金陵成功之早遲。”(6)《復左中丞》(同治元年七月初九日),《李鴻章全集》第29冊,第101頁。可見,李鴻章早在同治元年六月已有明確的由滬進攻蘇州之意,并形成較成熟的進攻方案,已籌及淮揚水師和太湖水師的兵力部署,對進攻結果也有預判。更重要的是,李鴻章已開始實施此戰略計劃。同治二年四月十四日,淮軍攻克昆山、新陽,進逼蘇州,戰守之間,兵力愈顯單薄。李鴻章尤盼李朝斌水師“速到,速清嘉屬各鄉鎮,扼住水口,直搗湖心,則兵事、餉事及兩省全局脈動筋搖。”(7)《上曾中堂》(同治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李鴻章全集》第29冊,第228頁。因曾國荃部攻破雨花臺,江北太平軍紛紛南渡,欲救蘇州和金陵。湘軍乘太平軍紛亂之機,于同治二年五月連破江浦、浦口、七里洲、九洑洲,截斷太平軍水上通道,預備合圍金陵。軍事形勢確實對湘淮軍有利,苗沛霖卻在此時再次叛亂。曾國藩屢調黃翼升赴臨淮,而李鴻章堅不應命,一定要等淮軍攻下蘇州再放人。對于李鴻章拒援臨淮及其影響,學術界尚未予以充分關注,本文試對此進行探析。
一、李鴻章拖延應對
曾國藩檄調黃翼升赴援臨淮,打亂了李鴻章的戰略計劃。所以,李鴻章不愿意服從調度。起先,李鴻章采取的是拖延戰術,稱要等李朝斌到滬,才能派黃翼升出滬。其致黃翼升信中言:“李質堂尚無到滬準期,揆帥咨函欲請麾下統率六營由揚州入洪澤湖、臨淮,直打至周家口,肅清澮、渦、淮、淝、汝、潁諸河,以扼苗捻紛竄之路,屬弟敦促成行。議論絕大,規畫甚遠,弟亦何敢阻擋。惟各營分扼蘇州附近湖河,正當要地,且老兄為西路統帥,籌防督剿,亦未便臨敵抽調。現在質堂未到,暫從緩計。俟常、江之間軍情少定,閣下或回滬一商,屆時質堂果來,亦可三面言明,再行稟復揆帥,尊意以為何如。”(8)《復黃軍門》(同治二年五月十一日),《李鴻章全集》第29冊,第231頁。
黃翼升的反應,據李鴻章說自“得調淮之信,憂惶無措”,只愿與李鴻章“合伙,不愿分離,真死生患難之交”,且“官紳士庶、大小將領相顧愕眙,似于東南全局大有關礙。……淮揚水師戰事至今春乃得放膽,若以太湖水師易之,而令熟悉地勢人情之師船他往,誠恐輿論未協,軍事因而阻滯也”,還強調黃翼升的作用:“各湖河來路均系前敵要地,常熟、江陰之間……賴有昌歧主持調度,或可立足。水陸將士,和協一心,皆昌歧之力居多。”因此,李鴻章建議,“李質堂尚未駛過九洑洲,可否飭調該鎮帶六營赴臨淮,其四營來滬,或派員暫統,或交昌歧兼管。果全來滬,抑或由鴻章商辦。”如果一定要調黃翼升赴臨淮,“或奏令鴻章偕往,或即不派太湖水師東下,仰候鑒裁。”(9)《復曾中堂》(同治二年五月十四日),《李鴻章全集》第29冊,第231—232頁。曾國藩對此回復道:“滬甘而淮苦,人人皆知。質堂之不愿赴淮,與昌歧同。昌歧之義應赴淮,則自十年保淮揚鎮實缺,已定之矣。閣下若必留昌歧共剿蘇垣,則請于昌歧部下……東華等酌派一人,帶三四營駛赴長淮,一助義渠,共誅苗逆。質堂本太湖水師,名實不符,鄙人不能因昌歧梗令而改派質堂也。”(10)《復李鴻章》(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三),《曾國藩全集》第26冊,第659頁。
面對曾國藩的強硬態度,李鴻章只好緩和下來,說:“質堂尚未來滬。昌歧固畏淮苦,此間實系萬不可少之人。前吳紳有公呈吁留,附呈鈞鑒。王東華勇略俱優,但淮揚各營頡頏已久,未必服統,俟質堂到后妥商奉報。”(11)《上曾中堂》(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李鴻章全集》第29冊,第236頁。而李朝斌五月二十二日函致李鴻章,稱須赴皖募勇以補傷亡缺額,到滬似尚需時。黃翼升又可拖延些時日。
此時苗沛霖于六月初四日陷壽州,圍蒙城。唐訓方奏請厚集援軍,保淮北之土,固豫東門戶。曾國藩除了調蔣凝學等陸師衛蔽豫、鄂、皖各境,又飛咨彭玉麟、楊岳斌選派舢板80號,速赴臨淮。待黃翼升到后,再各回本汛。六月十五日,苗沛霖猛撲臨淮。唐訓方之軍前后受敵,只盼湘軍水師和吳棠續派黃開榜水師炮船百余只趕到,再聯合進攻。
而李鴻章致曾國荃信中言:“苗逆陷踞壽春,必將上略光、固,暫無專軍剿辦,宜俟江南報捷后合力圖之。昌歧見圖江陰、無錫,甚不愿分師遠出。”(12)《致浙江撫臺曾》(同治二年六月十六日),《李鴻章全集》第29冊,第239頁。可見,李鴻章、黃翼升的戰略目標是一致的,即先圖江南。李鴻章對其兄李瀚章言:“亟盼李朝斌太湖水師到滬,可直下東西洞庭山,以牽制各郡縣筋脈。……昌歧所部分扼蘇、嘉、常三郡,水陸三四百里間處處吃勁。昌翁又與季弟共當一路,和衷共濟,極賴維持,是何啻剜肉醫創也。”(13)《致李瀚章》(同治二年六月十八日),《李鴻章全集》第29冊,第241頁。六月十四日,淮軍攻克吳江、震澤。李鴻章一面向曾國藩報喜:“從此水師可下太湖,而嘉興與蘇州不能通氣”;一面訴苦:“惟水路縱橫二百余里,一片湖蕩,僅有淮揚師船四營分布。程鎮所部分逼蘇城,又須置守江、震,兵力太單。”(14)《上曾中堂》(同治二年六月十六日),《李鴻章全集》第29冊,第240頁。“昌歧業與劉銘傳、三舍弟約攻江陰,多方擾之,西路無淮揚水師,輔車無助,誠恐決裂。”得知吳棠已派黃開榜前去助剿,唐訓方“似可自固”,李鴻章更不愿抽調淮揚水師了:“昌歧聞北去甚餒……倘因抽撤偏師,致隳全局,亦師門所不取也。大舉征苗,似須金陵、蘇、杭有一得手,分陸軍勁旅一支,與淮揚水師頡頏而前,其勢方足以制苗。此時希部退扎,即昌歧帶六營助守臨淮,其所以勝于黃開榜者幾希?……鴻章非敢違令,徇昌歧與吳紳之私而忘桑梓與義渠中丞之急,惟所值軍情時勢有萬難松勁者,不敢不再三瀆陳。”(15)《上曾中堂》(同治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李鴻章全集》第29冊,第243頁。七月初三日,李鴻章再懇求曾國藩“勿再催迫。該軍牽綴蘇、常,于金陵大局非無裨益。”(16)《上曾中堂》(同治二年七月初三日),《李鴻章全集》第29冊,第246頁。
二、李鴻章直接抗命
同治元年七月初五日,李朝斌抵滬,至此太湖水師已全到滬。但李鴻章仍不放黃翼升赴援。七月初九日,李鴻章報告曾國藩,李朝斌不愿將船扎散,而蘇州、松江、嘉定境內河湖交錯,若李朝斌全軍下太湖,北面全空,后路必斷,故淮揚水師有不可遽撤之勢。
此時曾國藩的壓力很大。清廷希望曾國藩另籌一軍,赴潁上搗苗練老巢,諭旨問能否于江北陸師內抽調勁旅,或援蒙城,或由定遠馳抵懷遠。曾國藩復奏稱,何紹彩陸師四營及彭玉麟、楊岳斌所派舢板80號大概已趕到臨淮,此外無軍可援蒙城并赴潁上。曾國藩又奏請以黃翼升親統一半淮揚水師駛往臨淮,一半留滬鎮壓太平軍,江南提督印信則暫由李朝斌接署。清廷允準。
但李鴻章以“蘇州東面圍逼漸緊,各水營離城均不過數里”為由,堅不應命,李朝斌又不愿分船、分扎,至少須三五營并扎一處。七月十七日,李鴻章回復曾國藩:“吾師責令昌歧遠去,不但太湖無船,即嘉郡來路、蘇州協剿亦必不能兼顧……如成命不可少回,昌歧起程少遲,貽誤之罪,實在鴻章,愿為分任其咎。”(17)《上曾中堂》(同治二年七月十七日),《李鴻章全集》第29冊,第248頁。李鴻章告知黃翼升:“如必定淮揚六營赴淮,此間大局一壞,弟不敢獨任其咎。……揆帥如必奏參麾下遲誤,弟當分過,并已專函陳明矣。吾二人在此并非不做事,若明知有礙大局而姑徇帥意,問心殊有不安。”(18)《復黃翼升》(同治二年七月十八日),《李鴻章全集》第29冊,第249頁。七月二十五日,李鴻章又致函黃翼升,稱:“江陰軍情如此吃緊……吾兄臨淮之役宜從緩議。如帥怒不止,鄙人甘當其咎,不得專怪吾兄也。陽利見、張光泰、張元龍三營現扎要地,萬不可撤。……如遽撤水師,則吳江、蘇州、外跨塘各陸營未能孤立,此間大局一壞,誰任其過。如揆帥奏參,弟亦當據實奏陳耳。”(19)《復黃翼升》(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鴻章全集》第29冊,第250頁。李鴻章已準備在奏折中和曾國藩對簿朝堂了。
但皖北軍事很不順。苗沛霖夾淮而軍,阻塞淮河河道,懷遠、蚌埠糧路已斷。七月二十三日,唐訓方前敵糧盡,突圍而出。壽州、蚌埠一帶遂為苗占,臨淮危如累卵。湘軍陸師無一足恃,水師又以河窄水涸,愛莫能助。臨淮倘不能支,則潁州、六安、固始、三河尖,在在可危。清廷認為,“臨淮為皖北屏蔽……必須竭力固守,方可沿長淮南北次第進兵,翦除苗逆。”(20)《清穆宗實錄》卷74,同治二年七月甲戌,《清實錄》第46冊,中華書局1987年影印本,第511頁。曾國藩又催促李鴻章:“苗逆盡可緩打,而臨淮則不可不急救”,請李鴻章“籌發糧藥,速昌岐西行,至要!至感!”(21)《復李鴻章》(同治二年七月十六日),《曾國藩全集》第27冊,第61頁。而黃開榜所帶師船,精銳已多損失,不得已而退守。吳棠建議:“欲拯臨淮之急,必須一生力軍由宿、蒙直搗懷遠北路,則該逆急于回顧,臨淮要地或可保全,且將來削平苗逆之策,尤必數道進兵,方可制賊死命”。(22)奕訢等修:《欽定剿平捻匪方略》卷196,清同治十一年鉛印本,第12頁。清廷認為有理,命唐訓方接應僧格林沁所派陳國瑞一軍由蒙城進攻懷遠北路,命曾國藩派兵進攻壽州,使苗練不得專攻臨淮,又責曾國藩“雖云顧瞻淮甸,徒切殷憂,而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總當于萬難設措之中,力籌援應之策。”(23)《附錄廷寄著飭固保皖南并聯絡策應諸軍救援臨淮合剿皖北苗黨》,《曾國藩全集》第6冊,第370頁。曾國藩復奏稱:“留守臨淮者,兵力過單,別無可濟之師,殊少自全之策”。(24)《附陳近日江南皖南江西淮甸各路軍情片》(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曾國藩全集》第6冊,第369頁。“江南諸軍不能赴淮”,“俟皖南軍事略松,仍當另籌一旅,馳往會剿”。(25)《遵旨復陳江南防務緊迫暫難全力援淮及相機馭使李世忠折》(同治二年八月十三日),《曾國藩全集》第6冊,第385頁。清廷不得已諭令督辦江北軍務江寧將軍都興阿派兵赴援臨淮,又讓曾國藩相機檄調李世忠增援。都興阿派2000人赴援,清廷恐不敷使用,又命幫辦江北軍務富明阿帶兵續援。富明阿于八月二十九日帶勇2300名、開花炮6尊并存米一千余石由揚州馳赴臨淮,李世忠亦親督5000人來會。八月,苗練猛攻蒙城,渦河南北清軍各營于八月十二夜全數潰退,守城者僅李南華等練勇千余人。曾國藩請求調降補同知金國琛赴皖綜理周寬世等四軍營務,仍往來固始、三河尖等處會辦皖、豫交界剿苗事宜。清廷允準。援臨兵力雖厚,而“一國三公”,作戰不力,導致“苗焰甚熾,且分黨擾及壽南、廬西一帶,甚為可憂”。(26)《復厲云官》(同治二年九月初五日),《曾國藩全集》第27冊,第155頁。
彭玉麟和楊岳斌水師七月到達后,雖將麕聚淮河兩岸的苗沛霖炮劃二百余號剿獲凈盡,但在乘勝登岸撲壘時,受傷陣亡者不少。曾國藩十分心痛,將受傷炮船撤回,另派20號船赴援臨淮。楊岳斌得知水師損失,又知苗沛霖在臨淮上游河邊釘樁置鎖,多扎陸營,層層攔截,十分擔心水師退路被斷,遂以內河水涸為由,要求撤回水師。曾國藩勸其切勿速行撤退。楊岳斌等又以“煤米告罄,衣服不足,各勇饑病,已滿兩月定期,亟須飭調出江,協剿東壩”為由,連咨曾國藩,“催令黃翼升即率所部數營于十月中旬趕到臨淮接防”。(27)《黃翼升不能赴援臨淮片》(同治二年十月初四日),《李鴻章全集》第1冊,第369頁。而黃翼升所部在江陰之戰和大橋角之戰中失利,被裁撤一營。李鴻章直接致函彭玉麟,說明情況:“昌歧所部現止十一營,分扼江、震、蘇、錫三四百里間,處處吃緊,萬難抽調,仰祈我公仍留撥赴臨淮三營協力防剿,候江南情形稍松,再籌數營往替。昌軍屢挫之余,即能勉力抽撥二三營北去,若更為黃開榜之續,弟與老兄皆不放心也。”(28)《復彭侍郎》(同治二年九月初九日),《李鴻章全集》第29冊,第259頁。
但曾國藩在彭玉麟、楊岳斌二人的壓力下,不得不催促淮揚水師赴臨淮換防。九月二十日致函李鴻章,稱“昌岐檄令即日赴淮,再遲不能不參。”(29)《復李鴻章》(同治二年九月二十日),《曾國藩全集》第27冊,第177頁。李鴻章仍請待蘇州、無錫克復后再行分調,稱太平軍僅剩胥門一條去路,如果要分軍臨淮,“非六營則昌歧必不肯行,去六營而僅余五營,不獨鴻章才拙,無術能支,即吾師與厚、雪二帥親臨調度,恐亦無以易之。”因此與曾國藩商量:“丁泗濱等糧藥既缺,能否先調出江,俟蘇、錫得手,前路河道較少,鴻章即遵示催令昌歧酌帶數營前去,似于兩面大局有裨。……協攻蘇州與協守臨淮,事體宜分輕重,賊勢要看緩急。”“蘇、錫得失之關我與賊勝負之機,決在十、冬兩月內,一簣之虧而敗前功誤大事,師與厚、雪二公必不出此,伏乞鑒察轉致為幸。”(30)《復曾中堂》(同治二年十月初三日),《李鴻章全集》第29冊,第265頁。
黃翼升得知曾國藩欲參劾的消息后,要遵令拔隊,李鴻章無計可施,未同曾國藩商量,便上奏朝廷請求暫留黃翼升協攻,也“有詞可謝厚、雪二公”。(31)《上曾中堂》(同治二年十月十一日),《李鴻章全集》第29冊,第267頁。折中稱“現在江浙三城以蘇州為關鍵,各路賊勢以蘇、錫為最多,況蘇城六門已圍其四,無錫官軍迭獲勝仗,攻剿正緊。若合水陸之力剿除忠、侍各股,則蘇州、無錫兩城可漸得手,即金陵、杭州兩處亦大松勁。若于四面水鄉中抽去一枝水師,則罅漏甚多,門戶自開,不獨蘇、錫難攻,且長忠、侍各賊內竄之志,關系全局,實非淺鮮”,請求將淮揚水師“暫留協攻,俟蘇州、無錫克復,再飭分帶數營前往臨淮,即毋庸兼顧蘇、滬”。(32)《黃翼升不能赴援臨淮片》(同治二年十月初四日),《李鴻章全集》第1冊,第369頁。清廷默許。十月十一日,李鴻章去信告知曾國藩已奏請留黃翼升協攻。而此前十月初九日,曾國藩再致信李鴻章,語氣嚴厲:“昌岐此次再不應調,實不能不參辦。渠接限五日啟行之檄,尚未呈復。向例總督奏派署提督者,從無不報交卸之理,昌岐并此提督印吝不交出,尤不可解。閣下五、六、七月各緘均稱待李質堂軍到齊,即令黃部換防赴淮,至八月以后忽變前說。鄙意前此昌岐十營能支持年余之久,今添太湖全軍,留淮揚半軍,斷無反不能支之理。楚軍歷年之規模,彭、楊與唐之公議,迫我以不得不參。參折中必將前后情節逐節縷晰,免傷和衷之誼。”(33)《復李鴻章》(同治二年十月初九日),《曾國藩全集》第27冊,第203—204頁。
李鴻章于十月二十二日收到此信,“震悚無地”,將責任全攬過來,“前限五日啟行之檄,鴻章以忠、侍各逆竄擾,各路正在難支,不敢轉發,以亂軍心,此鴻章之罪也”;對于曾國藩指責黃翼升不交印,李鴻章稱:“昌歧署提督年余,印存敝營代用,渠并不管,即卸交質堂,質兄亦仍不管。鴻章軍事煩冗,忘催兩公備文交卸,亦鴻章之罪也”;對于曾國藩指責李鴻章前后措辭有別,李鴻章稱:“蒙調此軍以來,鴻章每函必懇暫留,其說不一,先私情而后公事,總之懇留協剿。今蘇、錫垂成之局,更難松勁,仍懇吾師檢閱前后函稿。”最后,李鴻章表明態度:“此軍從鴻章最久而親,蘇省攻剿至急且大,而吾師必欲苦逼,應請暫勿參奏,先檄質堂將各防接替(彼固不肯分船,船單亦實不敷);而昌歧不行,鴻章不遣,再將昌歧與鴻章一并參辦,死亦甘心”,又據理力爭:“蘇省水路,楊、彭、唐諸公皆未親歷,而遽科鴻章以擁兵自衛之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語有之乎。吾師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纖芥致傷天和。鴻章與昌歧從游有年,豈是梗令之人,處斯時地,下游人人皆謂不可抽調,而上游則人人皆曰必宜撤換,究竟遠者真乎,近者偽乎,祈再察訪蘇省公論為感。倘荷慈鑒允,俟蘇、錫克復,或亦不遠。”(34)《上曾中堂》(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李鴻章全集》第29冊,第270頁。此時李鴻章已決意抗爭到底,任憑曾國藩處置。
其實曾國藩內心并不愿意參劾,一直在等李鴻章復信。十一月初二日,曾國藩收到復信,得知李鴻章親督諸軍直抵蘇州城下,迭獲勝仗,贊曰“氣機極好”;十一月初三日,又收到程學啟稟,得知淮軍已于十月二十五日攻克蘇州,甚感“快慰”,遂致信彭玉麟為李鴻章說項:“頃聞蘇城已于二十五日克復。果能如此,則昌岐梗調之愆似尚可恕,此后調回淮陽〔揚〕訊〔汛〕地,更無他辭可托。少荃此次來信,再三引咎,亦實有不得已之苦衷,渠請鄙人海涵,更希閣下曲諒。原函抄呈一覽。丁、王二十前定可出江。”(35)《復彭玉麟》(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三日),《曾國藩全集》第27冊,第261頁。
十一月十四日,李鴻章再致信曾國藩,先道歉:“十月二十二日于督隊煩冗時草復一緘,旋思詞意乖忤,氣質未平,必干盛怒,屏營惶悚,無以自解。”繼匯報蘇州克復后情況,解釋為何未及時匯報:“蘇城復后,加以降眾二十萬在內,遣散安置,煞費心力。戈登常勝軍及英提督伯郎、翻譯梅輝立等簸(撥)弄是非,橫騰口舌。鴻章雖即入城,鎮定駐守,從容部署,而心緒惡劣,不欲告人,是以函丈在遠,但以咨奏奉申,未及詳晰上達。今各事粗定,眾喙皆息,始敢為左右一言之。”(36)《上曾揆帥》(同治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李鴻章全集》第29冊,第272頁。十一月二十四日,曾國藩接到該信,很為李鴻章自豪:“此間近事,惟李少荃在蘇州殺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戈登雖屢稱欲與少荃開仗,少荃自度力足制之,并不畏怯。戈登亦無如之何,近日漸就范圍矣。”(37)《致澄弟》(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曾國藩全集》第21冊,第230頁。因李鴻章拒援臨淮的怒氣也就消了。其致左宗棠信中言:“弟派太湖水師十營助攻蘇、滬,而調淮揚水師六營由滬赴淮以援義渠之急。函牘十返,少荃竟不遣一營入淮。鄙衷不無介介,以蘇州兵事方殷,未與深論也。”(38)《復左宗棠》(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七日),《曾國藩全集》第27冊,第274頁。
李鴻章在與曾國藩拼力抗爭之后,最終達到了自己的戰略目的。十一月十四日,黃翼升“帶五營由蘇啟行,過滬補領餉藥,即鼓棹長往”臨淮。但此時僧格林沁已親自督兵,用炸炮連破苗壘,于十月二十六日將蒙城解圍,苗沛霖在對戰中被砍斃,苗據城池先后收復,黃翼升“此去竟成贅疣也”(39)《復彭侍郎》(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二日),《李鴻章全集》第29冊,第277頁。,于同治三年二月初二日全軍回滬。
三、李鴻章抗令成功的原因
李鴻章堅決抗令不遵,清廷未怪罪,曾國藩也未參劾。究其原因,在于他的目標和清廷、曾國藩的最終目標是一致的,就是盡快平定太平天國,不讓洋人內地助剿。只要李鴻章能達到這些目標,于曾、李分歧,清廷不會苛責李鴻章,曾國藩也無法深究。
曾國藩對待洋兵助剿的原則是:“會防不會剿”,“會防上海則可,會剿它處則不可。近而嘉定、金南,遠而蘇、常、金陵,皆它處也,皆腹地也”。(40)《復李鴻章》(同治元年三月三十日),《曾國藩全集》第25冊,第181頁。曾國藩同意中外會防上海,亦出于無奈。同治元年二月初二日,曾國藩奏稱:“自寶山、奉賢、南匯、川沙失守后,上海已岌岌可危,至今月余,巋然幸存,蓋發逆畏忌西洋,不敢驟樹大敵。而目下情勢,舍借助洋兵,亦實別無良策。”“上海僻處東隅,論籌餉為要區,論用兵則為絕地。假使無洋人相助,發匪以長圍裹我,官兵若少而弱,則轉瞬又成坐困之勢;若多而強,則不宜置此無用之地。再四思維,不得所以保全之法,擬仍借洋人之力,開誠布公,與敦和好,共保人財。”(41)《遵旨統籌全局折》(同治元年二月初二日),《曾國藩全集》第4冊,第67頁。
清廷從薛煥奏折中得知上海有英法兩國協同戰守,還有美國人華爾在松江與太平軍接仗,“甚為得力”;從京師總理衙門處得知,已與各國駐京使臣熟商,“勸導協力守御,尚形踴躍”,所以也同意曾國藩的意見,“舍借洋兵,更無良策,惟能暫而不能常”,因“滬瀆餉源較裕”,仍須李鴻章等“撥派勁旅往守,以保萬全,并可潛化洋人輕藐之心。”(42)《附錄廷寄答遵旨通籌全局折》,《曾國藩全集》第4冊,第84頁。
會剿腹地的主張先由江浙官紳提出。署蘇松太道吳煦與江浙士紳希望借洋兵規復鄉里。先有江南官紳殷兆鏞等呈請借助洋兵,規復蘇、常各屬城池。清廷認為“該紳士等情殷桑梓,或非無見”,諭令薛煥酌度情形辦理。后又有恭親王奏稱,江蘇士紳潘曾瑋帶同浙人龔橙,由滬航海來京,訴稱鄉間被陷,懇請借用英、法等國官兵,速籌規復。清廷諭令總理衙門向各該國駐京公使籌商,但私下并不愿意洋人助剿內地:“上海為洋人通商之地,借助尚屬有詞。若攻剿內地賊匪,輒欲用外國兵力……一切供應之煩,亦恐萬難搘拄……固難重拂輿情,亦須顧全國體”,于同治元年二月二十四日諭令曾國藩悉心籌酌“此事是否可行”,迅速馳奏。(43)《清穆宗實錄》卷20,同治元年二月丁丑,《清實錄》第45冊,第546頁。未等收到曾國藩復奏,三月初二日,清廷又同意洋人助剿蘇常,稱“近復據英、法兩國駐京公使聲稱:賊匪與洋人構釁。此時在滬洋人,情愿幫助官軍剿賊,并派師船駛往長江,協同防剿”。清廷據此判斷,“如該洋人實系與逆匪尋仇,并無他意,則事機難得。該大臣等務當飭令沿江上下游師船,與該洋人聯絡聲勢,冀收速效。并當加意拊循,使其樂于助順,毋令再為賊匪所誘”,強調“此實因勢利導,一時權宜之計”。(44)《清穆宗實錄》卷21,同治元年三月甲申,《清實錄》第45冊,第565頁。曾國藩在收到清廷這兩通諭旨后,于三月二十四日復奏,重申“助守上海則可,助剿蘇、常則不可”,因為“以今日之賊勢,度臣處之兵力,若洋人遽爾進攻金陵、蘇、常,臣處實無會剿之師。如其克復城池,亦尚難籌防守之卒。……假使轉戰內地,但有西兵,而無主兵,則三吳父老,方遷王師而慰云霓之望,或睹洋人而生疑懼之情。至臣……既以借助外國為深愧,尤以無兵會剿為大恥”;至于清廷所謂“事機難得”,曾國藩認為,“自當因勢利導,彼此互商,嘉其助順,聽其進兵。我中國初不干求,亦不禁阻。……惟地形有遠近,兵勢有次第,仍請飭下總理衙門照會英法公使,目前若進攻金陵、蘇、常,臣處尚無會剿之師。”(45)《籌議借洋兵剿賊折》(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四日),《曾國藩全集》第4冊,第141—142頁。清廷接到曾國藩復奏后,同意“洋兵進剿蘇、常,必須中國有兵相隨為主”,與洋兵會剿蘇常之事“不可行”,該紳士潘曾瑋等“迫于不得已,只計目前之利,未遑計及后患”,諭令已到滬的李鴻章“與英法之兵力籌守滬,以保餉源”,要防法國兵冒昧入江助剿。(46)《清穆宗實錄》卷24,同治元年四月己未,《清實錄》第45冊,第655—656頁。李鴻章也不愿意與洋人會剿內地,同治二年四月,在聽聞李泰國購買洋船欲助剿金陵時,對左宗棠說:“賊勢實衰,十年老巢乃必借外人以收功,后患將不可知。”對常勝軍,也打算在適當的時候裁撤,“鄙人受命敗軍之際又以力薄不敢淘洗,幸英兵頭戈登接管,尚循禮法,月糜餉五萬,東征西剿,亦尚效命,除非蘇、常肅清,方可分別安置裁撤也”。(47)《致浙閩制臺左》(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李鴻章全集》第29冊,第228頁。
李鴻章到滬之前,滬上防守力量有江蘇巡撫薛煥統領的練勇四五萬人和以廣勇為主的水師,還有租界的洋人軍隊。為了對付太平軍,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上海成立了中外會防局。李鴻章曾說過自己的擔憂:“長江通商以來,中國利權,操之外夷,弊端百出,無可禁阻。英、法于江浙各口力助防剿,目前小有裨益,但望速平此賊,講求戎政,痛改數百年營伍陋習,我能自強,則彼族尚不至妄生覬覦,否則后患不可思議也。鴻章才力暗弱,憂患久經,遽膺重任,軍事、吏事、夷務、餉務竭蹶不遑,終虞顛覆,貽知己羞”。(48)《復戶部大堂羅》(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李鴻章全集》第29冊,第212頁。到滬后,在滬的英海軍提督多次提出中外合力攻剿太平軍,李鴻章秉曾國藩之意,對此要求皆不應答。曾國藩告誡李鴻章,初到上海要以“練兵學戰為性命根本”,不要急于出戰,以防一戰不利,前功盡棄。“縱或洋譏紳懇,中旨詰責,閣下可答以敝處堅囑不令出仗。二三月后各營隊伍極整,營官躍躍欲試,然后出隊痛打幾仗。”(49)《復李鴻章》(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四日),《曾國藩全集》第25冊,第169頁。李鴻章嚴遵曾國藩訓令,“以選將、練兵、籌餉為政事,點名、看操、查墻為工夫”(50)《上曾制帥》(同治元年四月初二日),《李鴻章全集》第29冊,第84、83頁。,導致洋人懷疑李鴻章“不肯與他會同辦事,形諸詞色,謂即將守滬西兵撤歸本國,……如中國不肯會辦,只得罷兵”,李鴻章只得“婉言慰藉,可從則從,斷不與之失和,上海總要他保護方好。……但求外敦和好、內要自強”。(51)《上曾制帥》(同治元年五月初二日),《李鴻章全集》第29冊,第88頁。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后,淮軍“營官皆有躍躍欲試之意”,除了“程學啟欲與洋人合打,他皆不愿。”(52)《上曾制帥》(同治元年四月初二日),《李鴻章全集》第29冊,第84、83頁。
同治元年四月,李秀成派聽王陳炳文、納王郜永寬帶軍進攻嘉定,自統十余萬人抄撲太倉清軍后路。二十八日,英法提督將兵撤出嘉定,嘉定重為太平軍占有。洋兵為太平軍聲勢所懾,“從此不肯出擊”。五月二十一日,李秀成調陳炳文及郜永寬部五六萬人攻打虹橋清軍營盤,四面圍裹。李鴻章在三月曾向曾國藩言及,“鴻章所帶水陸各軍專防一處、專剿一路,力求自強,不與外國人攙雜”(53)《上曾制帥》(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五日),《李鴻章全集》第29冊,第79頁。,此次見“洋人擁兵數千,坐守洋涇浜,令人莫測其意指”,“思到滬兩月,未曾痛打一仗,恐為外人所輕;若前營被踏,或被賊營中阻,則全局即壞”,于是趁太平軍扎營未穩,督率淮軍以排炮轟擊。太平軍損失慘重,泗涇、松江附近太平軍被迫全數撤離。李鴻章對曾國藩稱此仗為“極痛快之事,為上海數年軍務一吐氣也。……有此勝仗,我軍可以自立,洋人可以懾威,吾師可稍放心,鴻章亦敢于學戰”,更理直氣壯地說,“彼未出一兵助剿,我則何從讓功”(54)《上曾制軍》(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二日、六月初三日),《李鴻章全集》第29冊,第92、93頁。,并說此戰讓“市商新聞紙津津樂道,夷兵與弁勇敬讓加禮。何提督前來敝營,詞意和順”。(55)《上曾制帥》(同治元年六月十四日),《李鴻章全集》第29冊,第96頁。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慕王譚紹光率領太平軍準備進攻上海李鴻章大營。二十八日圍北新涇,八月初二日進至城西六七里。淮軍以劈山炮、抬槍、洋槍進攻,水陸師相互配合,猛轟太平軍,又有洋兵從徐家匯炮擊,太平軍傷亡較虹橋之戰更大,不得不退出上海。此戰中,“洋人坐觀成敗,少荃雖萬分危急,從不求洋兵出隊相助”。(56)《復左宗棠》(同治元年八月十四日),《曾國藩全集》第25頁,第480頁。李鴻章經此戰,對與太平軍作戰更有把握:“忠逆部下勁旅,只陳、譚為最。陳敗于虹橋,譚敗于七寶、北新涇,此外即有大股來犯,當較差”。(57)《上曾制軍》(同治元年八月初四日),《李鴻章全集》第29冊,第110頁。但此后太平軍未能再對上海發起進攻。
當淮揚水師和太湖水師戰斗力增強,與陸師配合逐漸默契之時,李鴻章開始進兵江南。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二月,利用太平軍叛徒,收復常熟、昭文。同治二年四月,收復昆山、新陽。曾國藩稱“偉矣哉,近古所未有也!”對李鴻章稱贊有加:“程鎮進圖蘇州,于理于勢,皆可得手。向嘗疑上海非用武之地,又頗疑左右力薄而遽遠謀,或非所宜,定至今日,乃知勝算非碌碌者可及耳”(58)《復李鴻章》(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三),《曾國藩全集》第26冊,第583頁。;“少荃臨陣督戰,迥非書生面目,五月、九月兩次大捷,至今令人神(往)”,“目下淮營已能于楚師外另立一幟”。(59)《復劉秉璋》(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曾國藩全集》第26冊,第237頁。認為洋兵“實亦不甚足畏”,“不講隊伍,專講利器,似難制勝也。”(60)《復李鴻章》(同治元年閏八月十六日),《曾國藩全集》第25冊,第550頁;《復官文》(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曾國藩全集》第26冊,第144頁。
隨著淮軍不斷深入江南腹地,清廷也看到了攻克蘇州的希望,對李鴻章的軍事行動給予更大的支持。曾國荃雨花臺大營被太平軍圍攻危急的時候,曾國藩奏調程學啟應援,李鴻章不放,清廷沒有責怪;臨淮軍情緊急,曾國藩奏調黃翼升淮揚水師應援,李鴻章堅決不應命,清廷也未責怪。最終,李鴻章督率淮軍于同治二年十月攻下蘇州,達到了清廷和曾國藩希望的“會防不會剿”、不讓洋兵染指內地的目的。在處理“殺降”的問題上,英法等國最終沒有干涉,而常勝軍最終被遣散。
李鴻章利用太平軍在戰略上的漏洞和軍備上的不足,取得戰斗勝利。而太平天國因為丟失江南這一重要的財賦之區和根據地,很快失敗。拒援臨淮一事表明,在清政府和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略布局上,李鴻章利用太平軍進攻上海造成的危機,先讓淮軍在上海立足,再頂住壓力,以淮揚水師和太湖水師配合陸師,攻下蘇州,為自己和淮軍贏得一大筆資本,最終成為清廷扶植的對抗曾國藩的人選之一。后來,淮軍正如曾國藩所愿,代替湘軍擔任北上鎮壓捻軍任務,李鴻章隨后又取代曾國藩任平捻欽差大臣,借此一步步登上權力頂峰。而清廷盡管在同治元年正月曾說過,對曾國藩的一切規劃,言聽計從,實際上在李鴻章的做法符合清廷利益的原則下,則采取了比較靈活的做法,并不機械地只支持曾國藩的戰略部署,在放權給曾國藩的同時,也放權給李鴻章,借此培植了能抗衡曾國藩湘軍的淮軍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