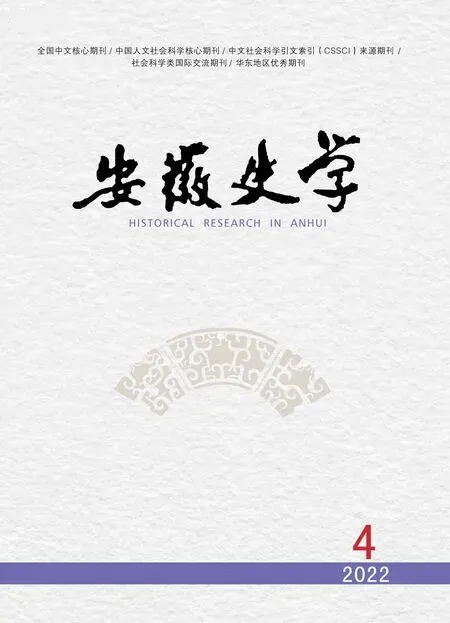沈家本恤幼人道思想探析
姬元貞
(清華大學 法學院,北京 100084)
憐恤弱小是人類共同的情感,不論是出于善良本性還是道德束縛,在古代中國體現在儒家傳統文化的理念——“恤幼”之中,而在西方則體現于人道主義之中。以沈家本為代表的清廷修律大臣們逐漸將這些理念用現代律法的形式表達出來,初步形成了近代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體系。
關于沈家本法律思想的研究興起于上世紀80年代初,時至今日有關沈家本思想的論文、著作依然不斷涌現,并被賦予不同的時代意蘊。現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有關清末變法修律的研究。主要有沈厚鐸的《玉骨冰心冷不摧——中國法律現代化之父沈家本》;(1)沈厚鐸:《玉骨冰心冷不摧——中國法律現代化之父沈家本》,《中國法律評論》2018年第1期,第143—148頁。霍存福的《沈家本“情理法”觀所代表的近代轉捩——與薛允升、樊增祥的比較》;(2)霍存福:《沈家本“情理法”觀所代表的近代轉捩——與薛允升、樊增祥的比較》,《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8年第6期,第99—115頁。曾爾恕、黃宇昕的《中華法律現代化的原點——沈家本西法認識形成芻議》;(3)曾爾恕、黃宇昕:《中華法律現代化的原點——沈家本西法認識形成芻議》,《比較法研究》2003年第4期,第93—104頁。段凡的《論沈家本司法人道主義思想及其歷史意義》;(4)段凡:《論沈家本司法人道主義思想及其歷史意義》,《法學評論》2017年第2期,第172—182頁。李貴連、俞江的《論沈家本的人格平等觀》;(5)李貴連、俞江:《論沈家本的人格平等觀》,《環球法律評論》2003年第3期,第309—321頁。等。第二,有關沈家本刑法觀的研究。主要有姜曉敏的《晚清的死刑廢除問題及其歷史借鑒》;(6)姜曉敏:《晚清的死刑廢除問題及其歷史借鑒》,《法學雜志》2013年第12期,第109—116頁。李交發的《簡論沈家本的廢除死刑觀》;(7)李交發:《簡論沈家本的廢除死刑觀》,《現代法學》2005年第1期,第189—192頁。徐忠明的《古典中國的死刑:一個文化史與思想史的考察》;(8)徐忠明:《古典中國的死刑:一個文化史與思想史的考察》,《中外法學》2006年第3期,第257—276頁。等。既有研究多著眼于“禮法之爭”的過程和刑法修律改革等法律整體變化,類似“與未成年人相關的刑事司法制度”等法律具體改革的研究還較為少見。伴隨著當下我國刑事責任年齡的調整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訂,本文擬追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體系歷史本源,考察中西交匯背景下,沈家本的恤幼人道思想如何在清末變法修律過程中影響近代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體系的思想邏輯和形成路徑。
一、沈家本恤幼思想之傳統文化根源
雖然“未成年人”這一抽象概念在中國古代并沒有被明確提出,但是對未達到一定年齡的“幼”“小”者,各朝各代都有相關刑事司法方面的特殊保護機制。沈家本對傳統恤幼法律制度有深入考究,其思想主要體現在代表作《歷代刑法考》中。在該著作中,有關古代恤幼制度的研究,散見于“刑法分考”“赦”“律令”“明律目箋”等篇中,其中“刑法分考七”“赦五·述赦四”“明律目箋一”“明律目箋三”等篇目列舉了元、宋及明代的恤幼法律規范。其中“刑法分考十”“刑法分考十四”“刑法分考十六”等篇目分別闡述“屯戍”“杖”“贖”中對未成年人的減刑政策。“赦一·原赦”“赦八·赦例二”“赦九·赦例三”“赦十二·論赦二”等篇目更是詳細分析了《唐律疏議》和《宋刑統》等律典有關老幼的特赦條文。
沈家本對中國傳統恤幼法律制度的考據與傳統中國的“仁政”思想是一脈相承的。顯然,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未成年人一直被當作弱勢群體來特殊對待,并作為統治階層推行仁愛的舉措。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9)楊伯峻:《孟子譯注》,中華書局2018年版,第16頁。《管子·入國》開篇便點明“慈幼”與“恤孤”的主旨,“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10)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033—1034頁。沈家本認為,這些表述都與未成年人保護有關。另外,中國古代社會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以“仁政”思想為主導,這種“仁政”在未成年人刑事保護方面,主要體現為倡導“恤幼”思想,以及對未成年人犯罪采取一系列寬宥之刑罰措施。沈家本高度評價中國古代“仁政”“德教”思想,并認為:“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也”(11)沈家本撰,鄧經元、駢宇騫點校:《歷代刑法考》,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025、2024、1801、628頁。,“臣等竊維治國之道,以仁政為先,自來議刑法者,亦莫不謂裁之以義而推之以仁”。(12)沈家本撰,鄧經元、駢宇騫點校:《歷代刑法考》,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025、2024、1801、628頁。沈家本對普通民眾尚且如此,對待“幼”“小”更是以“仁政”為先。所以我們有必要追根溯源,從中國古代圍繞未成年人犯罪減免處罰等恤幼思想的特征進行深入剖析。
(一)對未成年人犯罪免除或減輕處罰
沈家本的恤幼思想來源于傳統法律思想,其曾言:“老小不加刑,其法甚古。”(13)沈家本撰,鄧經元、駢宇騫點校:《歷代刑法考》,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025、2024、1801、628頁。翻檢歷史資料可以發現,沈家本探究的恤幼問題在漢代相關律令中就有體現。西漢時期,惠帝即位初年就有規定,未滿十歲的未成年人觸犯應當被刑罰制裁的律條時,不再按原罪處罰,均以髡刑(剃頭發)代替。(14)班固:《漢書·惠帝紀》,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85頁。成帝鴻嘉元年(公元前20年),新律令規定:年齡未達七歲的未成年人,在彼此殘殺格斗過程中殺人或者犯其他應被斬首的死刑罪時,可以“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15)班固:《漢書·刑法志》,第1106頁。,這說明犯重罪的未成年人并不能完全免除刑事責任,但可以通過“上請”的方式減輕處罰,免除死刑。“上請”是中國古代“仁政的體現”,一般皇親、貴族等身份顯赫之人才有此殊遇,可見漢代對未成年人特殊關愛程度之深。
唐代法律規定,十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犯“反、逆、殺人”等重罪的,可以有“上請”的機會,這與前述漢代“不滿七歲犯死刑罪可上請”相比,顯然從年齡和罪名兩個維度擴張了“上請”的適用范圍。唐律對“上請”程序的適用對象也有明確規定,皆為身份尊貴之人,可見唐律對待十歲以下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政策非常寬仁;而“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即有人教令,坐其教令者”。這種規定可以推斷出,唐律已經非常明確地規定七歲為完全免除刑事責任的年齡,并且認為七歲以下無判斷是非的能力,如果有成年人教唆其犯罪,需要追究該成年人的刑事責任。(16)長孫無忌等撰、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頁。沈家本在《歷代刑法考·赦五》中摘錄了《宋真宗紀》的記載:“慮囚,老幼疾病,流以下聽贖,杖以下釋之。”(17)沈家本撰,鄧經元、駢宇騫點校:《歷代刑法考》,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025、2024、1801、628頁。可見,沈家本認為除了法律規定的減免刑罰,“赦”也體現出對“幼”“小”的充分寬恕。
明清兩個朝代,延續了唐代的“恤幼”理念,律典多處規定,對未成年人犯罪應從輕處罰。據《明實錄》記載,明太宗曾明確反對將二位年十五歲犯強盜罪者處以死刑。永樂二年(1404年)二月,刑科給事中奏,有一起強盜案涉及到是否追究涉案未成年人的問題,他們認為:“臣等揆理論之,彼雖年幼,既能行劫,亦當被刑,不宜免死 ”,但“上不從”,曰:“童稚未成人者,本無知覺。向非成人者誘之,豈能自為盜耶?朕特推此情矜之。爾豈肯屈法濫恩?”(18)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太宗實錄》卷28,上海書店出版社1984版,第510頁。可見,明太宗反對大臣們對二童行刑,認為未成年人沒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應對其寬宥處理。
沈家本認為,未成年人不具備辨別是非的能力,其所應承擔的課稅徭役和刑事責任都應與其年齡相對應:“夫此相長相強之義,固專為役事而言,而刑事亦可類推矣。”(19)沈家本:《歷代刑法考》,鄧經元、駢宇騫點校,第1340、2235頁。因此,沈家本對古代未成年人犯罪減免刑罰的做法深入研究,并從中國傳統恤幼理念中提取精華,深刻認識到未成年人犯罪所受懲罰應與成年人犯罪明顯區分,只承擔符合其年齡的責任。
(二)以人性化的方式對未成年人執行刑罰
中國古代,除了對未成年人在刑罰種類和程度上寬宥外,在刑罰執行過程中也給予較為人性化的關懷。首先,從兩漢開始,未成年犯罪人在收監、刑罰執行過程中可以不戴刑具,稱為“頌系”,注云:“頌,讀曰容。容,寬容之,不桎梏。”(20)班固:《漢書·刑法志》,第1108、1106頁。一方面,大多未成年人在監獄或執行過程中也許不具有危險性,沒有戴刑具的必要;另一方面,這也是對未成年人犯罪者一種體恤之情。同“上請”一樣,漢代一定級別以上的官員犯罪才可以免戴刑具,足以見得中國古代在刑事政策細節上對未成年人的特殊關照。例如,漢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規定:“八歲以下”犯罪者應當囚禁審訊的,免于戴刑具,“鞫系者,頌系之”;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也有同樣的規定:“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鞫系者,頌系之。”(21)班固:《漢書·刑法志》,第1108、1106頁。唐代同漢代一樣,在刑罰執行過程中,也有不戴刑具等人性化的寬宥之策。例如,《唐六典》規定,對待八十以上、十歲以下、有疾病、懷孕以及侏儒病的人,“皆頌系以待弊”。(22)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6《刑部郎中》,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188頁。從漢“八歲以下頌系之”到唐“十歲頌系”,可見唐代法律對未成年人犯罪進一步寬宥。
明代《大明律》中也有“老幼不拷訊”的規定:“凡應八議之人,及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若廢疾者,并不合拷訊,皆據眾證定罪。”(23)懷效鋒點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216頁。這意味著年齡十五歲以下者甚至有不拷訊的優撫待遇,這比前代未成年人可不戴刑具更為寬厚。明洪武元年(1368年)還規定,十五歲以下未成年人在被關押期間,應與其他成年囚犯分別關押,“不許混雜”。(24)萬安中:《論中國古代監獄管理制度的沿革及其特征》,《廣東社會科學》2000年第6期,第101頁。這一分別關押的措施顯然是對未成年人的保護,一來可以避免未成年人遭受其他成年囚犯的欺凌,二來能夠避免未成年囚犯沾染更多成年囚犯的不良習慣,有利于對未成年人的再教育。
沈家本在論證中、西法之間“供、證”關系時,也提到“老幼不拷訊”,“中法供、證兼重,有證無供,即難論訊。……雖律有眾證明白即同獄成,及老幼不拷訊,據眾證定罪之文。”(25)沈家本:《歷代刑法考》,鄧經元、駢宇騫點校,第1340、2235頁。雖然沈家本是在討論“證”在法律近代化過程中的重要性,但也從側面證明沈家本的仁恤思想,承接中國自古“老幼不拷訊”思想,進而延續于修律改革中;肯定對幼小者的矜恤之情,并擴大到刑事司法規則中。
(三)以金錢處罰替代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制裁
未成年人犯罪用錢財來代替刑罰的歷史由來已久,沈家本在《歷代刑法考》的“刑法分考十六”中梳理“贖”的發展時也提到“幼”的贖刑適用問題。溯其本源,唐代“恤幼”思想在法律上的體現較為突出,有關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規則完備詳實且有可操作性,發展出了以金錢處罰替代刑事制裁的“收贖”方法。《唐律疏議》對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有專門“老小及疾有犯”條,這一條款名稱及主要內容被后代沿襲。該條規定:十五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犯流罪以下罪行的,可以用“收贖”的懲罰方式代替,即用金錢贖罪。《唐六典》中也有類似規定:“凡贖者,謂在十五以下”和“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盜與傷人者”,“并以贖論”;(26)李林甫等:《唐六典》卷6《刑部郎中》,第187頁。《元史·刑法志》“名例”篇載,七十歲以上的老者和十五歲以下的未成年人不能承受杖責的,可以用贖刑替代。(27)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元史·刑法志》,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9、2111、2096頁。
元代針對成年人犯罪的“征燒埋銀”制度要求犯罪者除本應承擔的刑事責任外,另需額外承擔民事賠償責任。但是,未成年犯罪行為人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免除刑事責任,只付“燒埋銀”。《元史·刑法志》“殺傷”篇載:“諸十五以下小兒,過失殺人者,免罪,征燒埋銀。諸十五以下小兒,因爭毀傷人致死者,聽贖,征燒埋銀給苦主。”(28)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元史·刑法志》,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9、2111、2096頁。顯然,十五歲是一個重要的刑事責任年齡點,主觀上沒有傷害他人的故意,疏忽大意致人死亡的不承擔刑事責任,但需承擔民事責任以彌補受害者;主觀上有傷人故意,如果受害人死亡,需以贖刑進行刑事處罰,同樣也要給予受害者及其家庭以補償。《元典章》刑部卷之四“年幼不任加刑”中記載有如下案例:汪驢兒系八歲孩童,用土塊擲打十歲趙引兒,趙引兒還手卻不慎打中五歲的汪黑廝,汪黑廝最終因破傷風死亡。對于這件事,“有司”認為:由于趙引兒是孩童,所以他誤傷汪黑廝的罪責可以不予追究,由其父支付受害者家庭銀五十兩,作為喪葬費予以安撫。(29)陳高華等點校:《元典章》刑部卷四,典章四十二,中華書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2頁。此案例就是對前述《元史·刑法志》中“殺傷”篇“燒埋銀子”相關規范的具體適用,證明未成年人誤傷致人死者不承擔刑事責任,但對受害者家庭要進行民事賠償。
此外,元代對未成年人在累犯及共同犯罪情況下也持寬宥態度。《元史·刑法志》“盜賊”篇,關于未成年累犯規定如下:“諸年未出幼,再犯竊盜者,仍免刺贖罪,發充警跡人。”意思是說,對未成年人屢次盜竊者依然持從寬的態度,仍免去刺字,可以用贖刑替代,并將其納入“警跡人”(需要監督警戒的人)的范圍。關于未成年人參與的共同犯罪,其規定:“諸竊盜年幼者為首,年長者為從,為首仍聽贖免刺配,為從依常律。”(30)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元史·刑法志》,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9、2111、2096頁。意思是,在共同犯盜竊罪中,即使未成年人為主犯,成年人為從犯,未成年人也依然免去刺字和發配的刑罰并可以用金錢來贖罪。沈家本也在《歷代刑法考》中引用了《元史·刑法志》的這一規定。(31)沈家本:《歷代刑法考》,第224頁。
明律只是將唐律中“老小廢疾”條改為“老小廢疾收贖”,內容基本相同。(32)薛允升撰,懷效鋒、李鳴點校:《唐明律合編》,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4、52頁。《大清律例》的“老小疾廢收贖”條規定:十五歲以下犯流罪的可以收贖;十歲以下殺人(謀、故、斗毆)應被判處死刑的,有上請的機會,傷人的,也可以收贖;七歲以下雖然犯死罪但不需要承擔刑事責任。(33)張榮錚:《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118頁。結合該條下的解釋條(第一百一十條):“七歲以下致斃命之案,準其依律聲請免罪。至十歲以下斗毆斃命之案,如死者長于兇犯四歲以上,準其依律聲請。若所長止三歲以下,一例擬絞監候,不得概行雙請。至十五歲以下,被長欺侮,毆斃人命之案,確查死者年歲亦系長于兇犯四歲以上,而又理曲逞兇,或無心戲殺者,方準援照丁乞三仔之例聲請,恭候欽定。”(34)張榮錚:《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118頁。這條判例是依據雍正年間發生的未成年人斗毆案子所形成的,是對“老小疾廢收贖”條的細化。此“條例”不僅考慮到年齡,也考慮到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的年齡差和犯罪原因。
沈家本在引用該判例時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修改后成文為:“七歲以下致斃命之案,準其依律聲請免罪。至十歲以下斗毆斃命之案,如死者長于兇犯四歲以上,或長于兇犯不及四歲而理曲逞兇,準其依律聲請。若所長不及四歲而又非理曲逞兇,一例擬絞監候,不得概行雙請。”(35)沈家本:《沈家本未刻書集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76頁。可以看出,沈家本擬擴大本判例的適用范圍,注重考慮未成年人之間產生沖突的原因,即考慮犯罪原因——“理曲逞兇”和年齡的結合。這就說明沈家本的恤幼思想較之傳統恤幼思想更為具體且周全。沈家本刪去“援照丁乞三仔之例”八字,將判例規范化,也更加靠近近代西方的法典編纂體例、規則。
(四)刑事責任年齡的認定遵循“從幼從輕”原則
中國古代的恤幼思想還體現在刑事責任年齡認定方面,遵循“從幼從輕”原則,即對未成年人進行刑事處罰時,是以犯罪行為實施時的年齡為標準,而非以犯罪行為被發現時的年齡為標準。《唐律疏議》中“犯時未老疾”條規定,實施犯罪行為時年齡較小,進行刑事審判時年齡已大,按照實施犯罪行為時的年齡予以從輕或減輕處罰。(36)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第93頁。按照唐代刑事責任年齡的劃分,七歲犯死罪的未成年人,即使八歲再進行審判認定,也不予追究責任;十歲實施殺人行為或犯其他重罪,十一歲時才被發現,依然可以獲得“上請”的機會;十五歲時犯非重罪的罪行,十六歲時被發現,“收贖”的代償性懲罰措施依然可用。(37)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第93頁。這種以犯罪行為發生時的年齡為判斷標準的原則,不僅體現出唐代立法的先進性,也充分表現出對“小”“幼”者的特殊保護。
唐代以后的朝代借鑒沿用了唐律有關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宋刑統》延續了《唐律疏議》的大部分內容,對未成年人的憐恤政策也不例外,包括承襲唐律的“從輕從幼”原則。《元史·刑法志》“盜賊”篇規定:“諸幼小為盜,事發長大,以幼小論。”“其所當罪,聽贖,仍免刺配,諸犯罪亦如之。”(38)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元史·刑法志》,第2096頁。幼時實施的犯罪行為,成年之后才被發現并審判的,按照實施犯罪時的年齡認定 。
沈家本在考證古代恤幼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還從深層次發掘了中國傳統文化“老小”憐恤思想的根源,他認為,從《禮記·曲禮》的“悼(七歲)與耄(八十、九十)雖有罪,不加刑焉”,到《尚書大傳》“老弱不受刑”(39)沈家本:《歷代刑法考》,第1800頁。,以及后世寬仁恤幼理念皆是儒家傳統文化的延續和承接。
二、沈家本恤幼人道理念之西法借鑒
20世紀初中國內憂外患的情勢,讓參透中外局勢的沈家本意識到融通中西的重要性,于是他開始籌備“修訂法律館”,組織翻譯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法律并整理中國律文舊籍。同時聘請西方法學家為法律顧問、派遣留學生赴日本等國考察學習,清廷也派官員出席萬國監獄會議等(40)周穎:《萬國監獄會議之少年決議——以近代中國少年司法啟蒙為視角》,《青少年犯罪問題》2016 年第1期,第79頁。,這些都為學習西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修律變法奠定了基礎。
在西方人道主義思想中,對少年兒童的特殊關愛本質上是人道主義的體現。人道主義的概念最早來源于拉丁文,意為“人的,仁愛的”,拉丁語 Humanitas 是指“人道、人情以及教育、教養”等涵義。(41)謝大任主編:《拉丁語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262頁。資本主義初期,形成了“人道主義”的詞匯 ,即英文中“Humanism”這一專有名詞。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人道主義”成為一種社會思潮,資本主義國家逐漸將這種理念運用到包括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等內容的法律領域當中。
(一)考察歐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機構
從20世紀初期開始,世界上很多國家和地區都逐步建立起相對獨立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體系,這引起了以沈家本為代表的清廷修訂法律大臣的關注,除了組織學者翻譯引介歐美、日本相關法律文獻,還組織官員赴歐美、日本參觀未成年人法庭和監獄。此期,歐美發達國家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機構以各種形式呈現,主要體現為:
一是設置教育感化機構,以教育感化代替懲罰。早在第一次工業革命前后,歐洲各國就出現了一系列兒童福利政策以及教育感化機構。1823年,法國設立收容未成年人犯罪的感化教育職業學校(42)賈洛川:《罪犯感化新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頁。,1908年,英國將在成年監獄服刑的未成年人移出并單獨設立青少年感化院,對青少年進行特殊的管理和教育。(43)劉強:《英國青少年社區刑罰執行制度及借鑒》,《青少年犯罪問題》2012年第3期,第105頁。這說明此一時期的西方國家已經逐步將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思想融入到其司法體系之中。挪威的兒童福利政策已經存在100多年,早在1896年就制定了《兒童福利法案》,其主要涉及的對象為有犯罪行為或存在不良行為的青少年,根據該法案的規定,對這些“問題”少年的教育引導應當取代對他們的監禁懲罰。
二是設置專門的“少年法庭”,以對未成年人進行特殊關照。1908年英國頒布了《兒童法案》,在普通法院中設立少年法庭專門審理涉及青少年的案件,將青少年所涉行為細分為不同種類,并以此進行針對性矯正。同年,德國也設立了第一個專門審理青少年犯罪的法庭,1911年又建立第一所青少年監獄,1923年頒布《少年法院法》。美國伊利諾斯州于1899年頒布《少年法院法》,并于同年建立起第一個少年法院,隨后美國部分州相繼建立起專門審理青少年犯罪的法院。1876年美國費城萬國博覽會上,中方參會人物李圭驚嘆于美國少年司法的專業化程度,并寫出《環游地球新錄》一書,將參觀所見未成年人監獄和專門法庭以及對未成年人教育感化狀況記錄其中。有關專門監獄和法庭,“公堂審案處,內有監房,分男、女、幼童三等,各約五六間”;(44)王韜等:《漫游隨錄·環游地球新錄·西洋雜志·歐游雜錄》,岳麓書社1985年版,第272、247、248頁。有關教育感化機構,“費城有習政院。凡童稚男女,父母已故,無依倚者;或有父母而不能教者;或子女不肖不受教者,皆由院中收留,使習正道,俾免流于不齒,誠善政也。其制男女自八歲起至十六歲止無依倚者,由地方紳民報院收留,不能教不受教者,由其父母稟官酌擬年分發院收留”。(45)王韜等:《漫游隨錄·環游地球新錄·西洋雜志·歐游雜錄》,岳麓書社1985年版,第272、247、248頁。他在評價中流露出羨慕贊譽之意:“聞此院各省皆有之,非獨費城也。各國亦皆行之,又非獨美國也。觀夫習政院與輕重犯監獄,皆主于化人為善也。”(46)王韜等:《漫游隨錄·環游地球新錄·西洋雜志·歐游雜錄》,岳麓書社1985年版,第272、247、248頁。
沈家本對歐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體系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這種感化教育對未成年人犯罪有較好的約束效果。他指出懲治教育始于德國,管理之法類似于監獄管理,但又以學校的名義命名,這便是強迫教育。各國效仿且都有顯著的效果。所以沈家本建議清廷也應采用這種方法,設置類似的學校,對未成年人區別其犯罪情節輕重,并以此決定教育時間長短,便能達到感化的效果。”(47)《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進呈刑律草案折(并清單)》,懷效鋒主編:《清末法制變革史料》下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71—72頁。
(二)日本成為清廷模仿歐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體系的橋梁
日本近代未成年人司法體系的發展主要以歐美等國為藍本。日本早期受儒家文化影響,對未成年人犯罪適用一系列寬刑政策;后又受西方國家“拯救兒童運動”思潮的影響,建立民間感化院;1900年頒布的《感化院法》規定感化院既收容觸犯法律的青少年,也收容還未實施犯罪行為但有較大可能觸犯法律的青少年。感化院由私立機構逐漸變為公立機構,由福利性機構轉變為強制性機構。(48)尹琳:《日本少年法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5頁。
向歐美各國學習的日本對中國未成年人司法變革影響頗深,主要體現在《大清新刑律》和《大清監獄律草案》中。日本的“微罪不起訴制度”與“感化院運動”是日本刑事政策轉變的標志(49)周穎:《近代中國少年司法的啟動》,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57頁。,對清末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也產生了一定影響。其中,對清末少年刑事司法改革有直接影響的是日本的小河滋次郎。小河滋次郎是沈家本聘請來中國協助指導監獄改革的授課老師之一,他撰寫的有關監獄學方面的論著也較為廣泛地被清政府翻譯學習。(50)孫雄:《監獄學》,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72頁。如前所述的刑事責任年齡劃分主要體現在《大清新刑律》中,而對未成年人的感化教育思想則主要體現在《大清監獄律草案》中。(51)周穎:《近代中國少年司法的啟動》,第62頁。“未滿18歲之處徒刑者,拘禁于特設監獄,或在監獄內區分一隅拘禁之。”該草案雖然未被頒布實行,但其中的分別監禁制度和以感化教育為原則的制度均能體現日本教育感化思想對清末未成年人司法體系建立的影響,這種影響在民國時期的相關法律條文中亦有體現。
總之,在西方人道主義思潮的影響下,歐美各國開始建立起少年司法體系,感化教育機構和少年專門法庭的設立讓保護弱小的人道主義關愛理念具體化、規范化。日本在學習歐美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體系的過程中,也摸索出了適合本國的少年司法體系,這些都深刻影響了清末中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體系的走向。
三、恤幼人道思想對近現代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體系形成之影響
西方人道主義理念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恤幼思想,成為清末修訂法律時保護未成年人、構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體系的理論基礎。沈家本既重視對西方法律思想的學習借鑒,也重視對中華傳統儒家文化的傳承延續。沈家本強調中西法律思想的融匯,認為:“旁考各國制度,采擷精華,有補于當世。”(52)沈家本:《歷代刑法考》,第2242、1332、1340、1331—1337、1340、1338—1340頁。對西學的研究讓他意識到脫離西方法學視閾的單純修律是行不通的,融會中西、取各自之精華才是變法修律之道。這種匯通中西的思想,具體到未成人刑事法律體系上,體現為沈家本對西方刑事責任年齡和感化教育的移植引進。沈家本結合中西,最終形成的恤幼人道思想對近現代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體系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刑事責任年齡概念在法律中得到確認并逐漸系統化;其二,構建未成年人教育感化體系。
(一)“丁年”與“刑事責任年齡”的接軌
沈家本《歷代刑法考》中的“丁年考”篇,對“丁年”進行了解釋,認為其類似現代“刑事責任年齡”的概念。沈家本在《歷代刑法考·丁年考》中,引用古籍解釋“何為童”“何為幼”“何為未成人”,對“丁年”概念進行了區分和界定。《曲禮》:“童子不衣裘裳”,疏曰:“童子,未成人之名也。”《釋名》:“十五曰童。”《冠禮》曰:“棄爾幼志。”是十九歲以前曰幼。在此基礎上,沈家本得出結論:古者二十而冠,凡未冠者為未成人,則曰幼,曰童,不得謂丁也。(53)沈家本:《歷代刑法考》,第2242、1332、1340、1331—1337、1340、1338—1340頁。由此,“冠”與“未冠”、“幼童”與“丁”被系統梳理、界定出來。
沈家本對中國古代唐律中的刑事責任年齡規范進行了詳細解讀,具體體現在《歷代刑法考·丁年考》中對刑事責任年齡的總結。(54)沈家本:《歷代刑法考》,第2242、1332、1340、1331—1337、1340、1338—1340頁。沈家本在《歷代刑法考·丁年考》中按照刑事責任年齡十六歲至二十五歲不等,列舉出各朝各代的“丁年”;同時也對西方的刑事責任年齡進行了詳實梳理。沈家本認為,按照《周禮·鄉大夫》中的記載,周朝時已經用身高來判斷年齡,并以此作為判斷其是否應承擔相應法律責任的標準,“六尺年十五,七尺年二十”;沈家本還認為,“丁年” 的說法大概源于晉代,其概念也大致如此,即不論是何朝代,達到一定年齡就需要承擔賦稅徭役的義務,同時享受被授予田地的資格權利。(55)沈家本:《歷代刑法考》,第2242、1332、1340、1331—1337、1340、1338—1340頁。沈家本強調,中西方在劃分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的理念上頗為相似,中國古代的“丁年”與西方“承擔罪責的年齡”均是需要承擔一定責任的年齡門檻,那些年齡未達到一定標準的人“辨別是非之心尚未充滿,故無責任”。(56)沈家本:《歷代刑法考》,第2242、1332、1340、1331—1337、1340、1338—1340頁。他還對西方多個國家新舊法律中的“絕對無責任”“相對無責任”“減輕時代”和“刑事丁年”進行了詳細的列表總結,其中,最低的刑事丁年為十二歲,最高的為二十三歲。(57)沈家本:《歷代刑法考》,第2242、1332、1340、1331—1337、1340、1338—1340頁。綜合中西方對刑事責任年齡的認定標準,沈家本最終在《大清新刑律》中確定“丁年”為十二歲,并強調:“犯罪之有無責任,俱以年齡為衡。”(58)《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進呈刑律草案折(并清單)》,懷效鋒主編:《清末法制變革史料》下卷,第71頁。這應該是我國近代有關刑事責任年齡最早的法理闡述。
實際上,對于刑事責任年齡的認定,從1907年《大清刑律草案》確定的十六歲,到1911年公布的《欽定大清刑律》(即通常說的《大清新刑律》)確定的十二歲,經歷了數輪激烈的“禮法之爭”。起初,《大清刑律草案》第十一條為“凡未滿十六歲之行為不為罪,但因其情節,得命以感化教育”(59)高漢成主編:《〈大清新刑律〉立法資料匯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3,220、226、284、290、356、360、363、374、384、397、429、434、441,628—632頁。,但之后學部、直隸、湖廣、閩浙等地的簽注清單均表示,不按照罪行輕重區分,直接將刑事責任年齡設定為十六歲過于寬柔,十六歲以下之人“亦有知識、臂力發達之時,若狂悖橫行概不為罪,流弊滋甚”(60)高漢成主編:《〈大清新刑律〉立法資料匯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3,220、226、284、290、356、360、363、374、384、397、429、434、441,628—632頁。,無法達到對未成年人犯罪教育的目的。于是,1910年《修正刑律草案》結合多國經驗將年齡降為十五歲,但各方又認為十五歲“尚涉過寬,難保不別滋流弊”。(61)高漢成編著:《〈大清新刑律〉立法資料補編匯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72頁。最后,經過陳樹楷、陸宗輿等眾多議員又一輪論辯研討(62)高漢成主編:《〈大清新刑律〉立法資料匯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3,220、226、284、290、356、360、363、374、384、397、429、434、441,628—632頁。,《欽定大清刑律》正文最終確定“凡未滿十二歲之行為不為罪,但因其情節,得命以感化教育”。(63)高漢成主編:《〈大清新刑律〉立法資料匯編》,第720、226、284、429、480頁。十二歲的刑事責任年齡甚至沿用到1912年頒行的《中華民國暫行新刑律》中,并認為,十二歲“最為適中,茲擬采用其制”。(64)高漢成編著:《〈大清新刑律〉立法資料補編匯要》,第272頁。可見,將刑事責任年齡設定為十二歲對中國近代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影響甚為深遠,這個年齡的確定也經過多方驗證,具有一定合理性,也符合當時的社會共識。
(二)近現代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體系的初步形成
沈家本認為,對未成年人應更注重教育而非懲罰。所謂:“丁年以內乃教育之主體,非刑罰之主體”,因為未成年罪犯如果同成年罪犯一樣被“拘置于監獄”,易受成年罪犯影響,出獄后的再教育會更加困難;(65)李貴連:《沈家本傳》,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頁。而且,“未成年所貴乎教者,正以其識慮之未充滿,而是非或有未當也。”(66)(67)李貴連:《沈家本傳》,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頁。沈家本:《歷代刑法考》,第1341頁。所以,對未成年人而言,刑罰更應是“最后之制裁”。(68)李貴連:《沈家本傳》,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頁。沈家本針對未成年人“教”“罰”的辯證關系,指出:“幼者可教而不可罰,以教育涵養其德性而化其惡習,使為善良之民,此明刑弼教之義也”。(69)沈家本:《歷代刑法考》,第1341頁。這種表述可以看出沈家本對未成年人犯罪感化教育的重視。同時,沈家本還建議,朝廷應學習西方的教育感化之法,設立感化院和少年監獄。可見,沈家本結合了中國傳統恤幼文化與西方人道主義思想,進而提出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護理念。
沈家本在其主持修訂的《大清刑律草案》中提出,應效仿西方建立感化教育院,對未成年人犯罪進行提前預防和教育。但各省對于是否建立這樣一個機構意見并不統一。兩廣、兩江、東三省在簽注清單中都表示“俾施教育而資感化,命意甚善,宜可照行”。(70)高漢成主編:《〈大清新刑律〉立法資料匯編》,第720、226、284、429、480頁。但如何建立,表示支持的省都沒有給出明確的建議。甘肅、直隸則在簽注清單中提出反對意見,“置諸感化場施以特別教育,是純用感化而非懲戒,斷非中國所宜”。(71)高漢成主編:《〈大清新刑律〉立法資料匯編》,第720、226、284、429、480頁。反對者認為,中國不可以直接設立西方模式的教育感化機構,否則會使實施嚴重犯罪行為的未成年人成為法律懲罰的漏網之魚,于社會無益;“恐觸法者既毫無懲戒于前,而施教者亦萬難補救于后,弊端百出,莫可究詰,此萬不可行于近日者也。”(72)高漢成主編:《〈大清新刑律〉立法資料匯編》,第720、226、284、429、480頁。基于此,朝廷在《修正刑律草案》中對各省各部提出的反對意見予以反駁,認為:“感化教育乃減少犯罪之良策,各國行之其效卓著,不論何時何國俱可采用,從未聞有以民智未睿為口實而避之者。”(73)高漢成主編:《〈大清新刑律〉立法資料匯編》,第720、226、284、429、480頁。最后,在《欽定大清刑律》中還是保留嘗試感化教育的想法,但因其規定過于籠統,感化院的建立過程不盡如人意。
與感化院籌建同時開展的,還有改良舊式監獄和規劃設立未成年人監獄。雖然沈家本力推的感化院的實施情況并不順利,在“禮法之爭”中被各方認為“為時尚早”,但為民國時期幼年監獄的設置奠定了一定基礎。1910年《大清監獄律草案》第二條論證了設立少年監獄的必要性:“幼年犯罪之人,血氣未定,往往一入監獄,傳染種種惡習,不惟不能改良,且愈進于不良。”所以,應該“特設或區劃拘禁場所,拘禁十八歲以下、刑期兩個月以上的少年犯,對之進行懲治教育”。(74)尤志安:《晚清刑事司法改革整體性探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51—252頁。
清末設立感化教育機構和專門少年監獄的想法影響著民國時期少年司法發展的方向。中華民國成立后,政府擬寫司法計劃書并送地方征求意見(75)民國司法部公報處、司法院秘書處等編:《司法公報》第1冊第4期,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版,第407頁。,其中包括設立少年專門法庭、籌備建立教育感化院的規劃。(76)《司法計劃書》,首都圖書館藏。但該計劃實施之初便因人才、經費等問題不斷變通、展緩,1913年司法總長許世英因宋教仁案等原因對袁世凱不滿辭職(77)民國司法部公報處、司法院秘書處等編:《司法公報》第2冊第10期,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版,第467頁。,其司法計劃遂基本擱淺。1922年,北洋政府頒布了《感化學校暫行條例》,雖然該條例并不能被全面貫徹落實、較之他國的相關法律也顯得單一且薄弱,但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體系未完善時也可視為具有進步性的過渡性文本。《感化學校暫行條例》的頒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各地專門教育機構及少年監獄的建成,如1934年南京國民政府設立的“濟南少年監”,1935年建立的“武昌少年監”等。(78)朱勝群編:《少年事件處理法新論》,臺北三民書局1976年版,第46頁。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進行了司法工作規劃,擬定《司法部訓政時期工作安排》,其中包括對少年司法體系的建立和完善。(79)民國司法部公報處、司法院秘書處等編:《司法公報》第55冊第32號,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版,第751—767頁。1936年,南京國民政府借鑒日本《少年法》制定出臺的《審理少年案件應行注意事項令》,對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規則做了規制,并較為詳細地規定了“少年法庭”的組織形式和審判程序。(80)李相森:《論民國時期的少年司法制度建設》,《青少年犯罪問題》2015年第4期,第86頁。遺憾的是,該草案同樣未被實施,但為以后的少年司法建設奠定了基礎。
梁漱溟說:“一民族真生命之所寄,寄于其根本精神,拋開了自家根本精神,便斷送了自家前途。”(81)梁漱溟:《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黃克劍、王欣編:《梁漱溟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頁。沈家本認為,脫離西方國家的部分先進理念,單一延續中國傳統法律,是無法立足并推廣于世界的。(82)沈家本:《歷代刑法考》,第2223頁。沈家本會通中西的恤幼人道思想,將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仁”融入其中,又兼收西方人道主義的感化教育理念,已有百余年歷史,并成為當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歷史源頭,從根本上、長遠地影響著我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體系的樣貌。這就需要我們深化對近現代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起源、衍變規律的認識,從沈家本恤幼人道思想中尋找中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實踐中法律適用的歷史解釋方法,以預防、教育、懲罰相結合為原則,增強相關法律規范的可操作性,完善當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