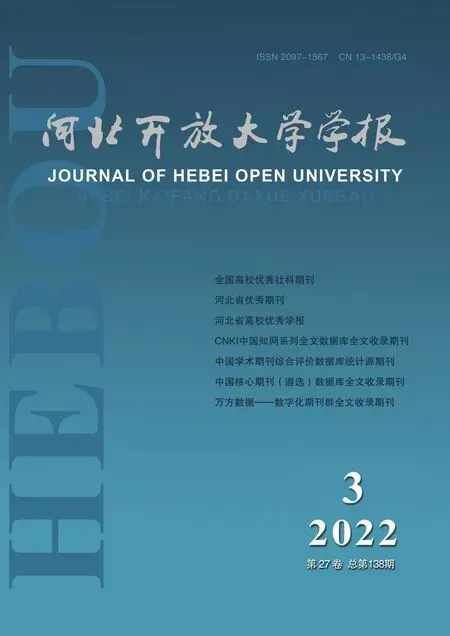監察留置措施與刑事強制措施銜接問題初探
賈廣宇,劉玉彬
(河北師范大學 法政與公共管理學院, 河北 石家莊 050024)
一、留置措施的內涵與性質
就目前來看,在我國的刑訴法、行政法中都沒有“留置措施”的相關概念,國家監察法的出臺,對留置措施的基本內涵及性質作出了相關規定。
1.留置措施的基本內涵
(1)留置措施的法律授權。2016年12月通過的《關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開展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的決定》中第一次出現了“留置權”這一概念,在試點地區成立監察委,主要有監督、調查以及處置三項權力。與此同時還規定了包括談話、查詢、調取、查封、勘驗、留置等十二項辦案措施。《監察法(草案)》結合試點地區所反映的問題而積累的經驗,首次就監察留置措施的審批流程、留置期限、留置條件以及被留置人相關權利保障等作了進一步詳細規定,使監察留置措施的雛形由模糊逐漸走向清晰。
(2)留置措施的適用條件。一是對象條件。首先,監察法規定對于涉嫌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的被調查人員采取留置措施時應滿足相應被調查人員的違法行為已經達到了“嚴重的程度”。也就是說,對于一般的違紀人員不會采取該項措施。
二是證據條件。只有監察機關已經初步掌握了被調查人員的部分犯罪事實及犯罪證據,但仍處于事實不清、證據不明需要進一步調查核實的基礎上,才會啟動留置措施。
三是實質要件。適用監察留置措施的情形主要分為四種,具體包括涉案重大且復雜,需要及時控制涉案人員;當被調查人員存在逃跑、自殺的可能性,如不及時采取措施將其控制可能會給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財產帶來傷害和危險的情況;被調查人可能會實施串供或者轉移、偽造、毀滅證據的可能,導致后期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后果;最后一項概括性兜底條款,為了保證監察委調查活動的順利開展,對于其他有礙調查的行為,賦予監委會較大的自由裁量權。
2.留置措施的性質定位
留置措施取代雙規措施作為反貪污腐敗的新生權力,使反貪腐程序逐漸趨于法制化、嚴格化,但是留置措施作為一項外部強制措施與黨內紀律雙規措施不能簡單等同。其次留置措施具有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性與刑事訴訟法中拘留、逮捕措施性質類似,但相比較而言,留置措施的嚴厲性要更強一些,且留置措施是國家各級監察機關對貪污腐敗人員進行調查活動的措施并非偵查措施,由此可見,監察留置措施與黨內紀律措施以及刑事強制措施有著不同的性質定位。
(1)留置措施與黨內紀律措施。習近平總書記曾提出用“留置”取代“雙規”,但是目前的監察法中并沒有將“雙規”刪除,由此看來,與紀檢監察相關的法律及與黨紀相關的法律到底是否會廢止“雙規”措施,還有待觀察。但能夠確定的是,留置與“雙規”不可能并存。從法律程序上看,留置措施與“雙規”都是為了保障調查程序的有效開展,二者的實施都為調查并收集證據提供了便利,且二者都能夠在某種程度上限制相關人員的人身自由。但是留置措施絕不能簡單地等同于“雙規”措施,“雙規”作為黨內紀律措施,是對黨內違紀人員采取調查的一種內部措施,是維護黨內紀律和管理紀律的需要。而留置措施是針對特定對象存在職務違法與職務犯罪的行為所采取的一種外部強制措施,因此不能將監察留置措施等同于“雙規”。
選擇在2013年1月到2017年1月這個時間范圍內,在我院接受治療的呼吸道傳染病患兒,一共有710例患兒,他們所生的疾病包括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和水痘等一系列相關病癥,其中有380例患兒患有嚴重的麻疹,有150例患兒患有流行性腮腺炎,有180例患兒患有水痘,其中在所有患兒中有250例患兒為本省戶籍,有460例患兒為外省戶籍。
(2)留置措施與刑事強制措施。目前,懲治職務違法犯罪和貪污腐敗的工作仍在如火如荼地開展,留置措施基于其自身的特性,必定會成為打擊職務違法犯罪和貪污腐敗的一把利器。盡管留置措施與拘留、逮捕相類似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強制性,但在行使主體、行使條件上并不相同,因此留置措施不是刑事強制措施。
綜上所述,監察留置措施既不屬于“雙規”,也不屬于刑事強制措施,他更傾向于一種集強制性、嚴厲性、主動性、專門性等特征于一體的復合型監察措施。
二、留置措施與刑事強制措施銜接的必要性
1.懲治貪污腐敗的需要
縱觀當今司法實踐活動,反貪反腐仍是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反腐敗行動既是維護憲法和法律權威的體現,同時也關乎國民的命運與幸福。在監察留置措施出臺之前,“雙規”作為首項能夠深入調查了解那些比較敏感和嚴重的職務違法犯罪的強制措施,為國家的反貪腐工作作出了巨大貢獻。但由于“雙規”在運行過程中缺乏堅強的法律支撐,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也存在不合理適用的現象,甚至逾越了國家法律保留的范疇,存在違憲、違法的嫌疑。基于如此的現實情況,黨中央提出以“留置措施”取代“雙規措施”的要求[1],以法律規范留置措施,共同推進法治格局的構建,以實現對國家貪腐情況的治理走向法治化,推動了“雙規措施”的法治化進程,同時也是中國反腐進程的里程碑式創舉。
2.尊重保障人權的需要
社會主義法治社會核心要求應當是保障人權,與沒有明確法律規范的“雙規”相比而言,留置措施能較好地保障被調查人員的相關權利。根據監察法草案意見稿對被留置人員的相關權利的規定可以看到,被采取留置措施的被調查人員的基本權利都應當得到相應的保障。
程序正義與實體真實并重符合我們所追求的法治社會要求,留置措施雖然是一項具有嚴厲性的羈押性措施,但這并不代表留置措施會被權力機關肆無忌憚地濫用,反觀當今貪污腐敗的嚴峻現狀,如果沒有這樣嚴厲的強制性調查措施進行制約和保障,怎能讓那些目無王法、僥幸逍遙法外的犯罪分子落入法網,受到其應有的法律制裁?又如何讓這項在萬眾矚目下出臺的措施實現刑法的威懾力和預防作用呢?由此看來,盡管在一定程度上監察委對留置措施的適用存在較大的自由裁量權,但賦予其此項權利是必要的,綜上,我們應該把關注的焦點放在在日后的法治進程中應當如何完善這項措施,使其能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既能夠對違法犯罪的人予以嚴懲,又能從真正意義上保障被留置人員的合法權益。
3.節約司法資源的需要
縱觀我國試點工作反腐實踐的案例,監察委在調查過程中獲得的證據,其中,由于言辭證據本身存在易獲得但其真實性無法被保證的特點而不能直接轉化為刑事訴訟環節的證據以作為定案依據,所以言辭證據在轉化過程中被排除這決定了對相應證據要進行二次取證的問題,這個過程無疑會浪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等司法資源。其次,一些證據類型基于其自身的特點,可能不易保留,或者調查人員的保存不當而導致證據滅失則引起后續的取證困難問題。為了反腐敗工作的有效推進,以及盡量避免證據滅失等問題的出現,在實際中,檢察機關可能會提前介入,出現聯席會議以及聯合辦案的情況,這在一定程度上有規避法律之嫌,損害被調查人的合法權益。同時,也不利于監察機關相關職能的履行。重復取證必然會浪費大量的司法資源,由此可見,兩法銜接從客觀上來講方便了證據的統一適用,也節省了寶貴的司法資源。
三、留置措施與刑事強制措施銜接中的問題
1.留置措施向刑事強制措施轉化過程存在的問題
(1)程序銜接場所設置欠合理。就目前的司法實踐來看,監察留置的地點主要有以下兩個:首先是將之前被采取“雙規”措施的地點進行改造作為當下的留置場地[2],其次是在公安部門看守所內專門設置留置場所。在監察留置場所的相關法律規定中并沒有清晰明確地對留置場所進行細致規范,不同的地區在留置設施與管理的制度上必然有差異。看守所基于其拘留的性質的不同而被劃分出了不同的區域,既有刑事犯罪的關押場所,也有治安管理羈押的地點。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采取留置措施的對象是國家公職人員,這就決定了對涉嫌職務犯罪的被調查人采取留置措施的場所的安全性和保密性的要求較高。
(2)留置措施單一性存在弊端。目前,從監察制度中12種調查措施的性質上來看,僅留置措施一項屬于剝奪人身自由的強制性羈押措施,其在運行過程中缺乏必要的替代措施。[3]單一的監察留置措施無法滿足監察機關辦案多元化的現實需要,作為唯一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可能會被監察機關過分地依賴和不合理地適用甚至變相采用繼而對不該適用留置措施的被調查人適用,極不利于其合法權益的保障。這就要求各級監察委員會要嚴格規范留置措施的適用。
(3)被調查人辯護權缺乏保障。據目前的法律規范以及司法實踐經驗來看,還沒有監委會在采取留置措施期間允許律師介入的情況。盡管留置措施并沒有允許律師介入的相關規定,但在社會司法實踐中,一般的犯罪嫌疑人都有為自己選取辯護人或接受法律援助以保障自己辯護權的行為,舉輕以明重,在刑事訴訟中,即便是特別重大的貪污賄賂犯罪也允許犯罪嫌疑人請律師為其合法權益提供辯護,留置措施下的調查對象是涉嫌職務違法犯罪的具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國家公職人員,其在被羈押過程中的辯護權當然也需要被保障。在監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如果基于職務犯罪偵查權轉變為調查權而將這項具有歷史性進步的保障性規定磨滅,則顯得不合理。
2.刑事強制措施向留置措施轉化過程存在的問題
(1)留置措施的二次適用不利于保障人權。監察機關將案件移交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檢察機關有權對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案件退回補充調查,但銜接上出現問題。另外,雖然留置與逮捕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剝奪人身自由的特征,但留置措施從嚴格程度上來看較逮捕更高,從程序銜接的角度來說,刑事強制措施是留置措施的后續程序,具有層次遞進關系,如二次適用留置措施,將面臨移送涉案嫌疑人、重新辦理手續、轉變關押場地等不必要且浪費司法資源的環節,在此過程中涉案嫌疑人的相關權利該如何保障又是一大難題。
(2)羈押場所的反復流轉規定不明。根據2018年新《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對于監察機關移送起訴的己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對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留置措施自動解除。從監察程序與司法程序的有效過渡的角度來看,這項制度設計初步實現了兩程序的有效銜接,但由于監察法剛出臺不久,其中對很多細節尚未作出明確規定。例如,對于已經采取拘留或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到底該不該將涉嫌違法犯罪的人員隨案退回并再次適用留置措施?針對此類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并沒有作出一個清晰的規定,從2016年試點地區適用留置措施第一案來看,留置措施的執行場所主要有以下兩種:一種是繼續利用“雙規”羈押場所;另一種則是將公安部門的看守所作為限制被調查人人身自由的場所,在這種情況下,將案件由監察程序轉為司法程序時,犯罪嫌疑人隨案被移轉至看守所內;若被移送的案件需要退回補充調查,則要將犯罪嫌疑人由公安部門的看守所隨案移送至留置措施的羈押場所嗎?
(3)期間的計算以及刑期的折抵尚不明確。我國《刑事訴訟法》和《刑法》中規定:拘留、逮捕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監視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國家監察體制改革以后,調查職務犯罪的權力歸屬于監委會,監察留置是一項典型的限制人身自由的羈押措施,不同的強制措施基于其本身的強度不同,所以程序的流轉應當將期間的計算方式以及刑期的折抵作出明確規定。
四、規范留置措施與刑事強制措施銜接的建議
1.合理設置留置場所
首先,明確被調查人員的羈押地點。若監察留置措施始終沒有確定的場所那可能會存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調查活動進行的嫌疑,由此建議留置措施的執行場地可以參照之前“雙規”所采取的辦案場所,在指定地點進行調查活動,基于被調查人身份的特殊性,可考慮在專門的賓館等環境相對輕松,不會給被留置人員過分壓力的類似場所進行,某種程度上可以讓被調查人員放松警惕,說出實情。
其次,完善留置場所相關基礎設施。雙規措施從出臺至今,經歷了由不完善到完善的發展過程,從當前來看,“雙規”措施的物品配備已經相對齊全,如藥物、車輛以及錄音錄像的設備等。另外其也為被羈押人員安排了定期體檢,時刻關注其身體狀況。留置措施的配套設施可借鑒“雙規”措施的相關設置。基于被調查人員身份的特殊性,可以為被羈押人員配備看守人員若干,輪班值崗,全程監護被調查人員的動向、情緒以及身體狀況,必要情況下可以輔助記錄。
2.多元設置監察措施
作為監察機關唯一帶有強制羈押性質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其單一性存在缺陷,這對監察法的進一步完善提出了要求。
第一,為監察留置設置前置措施與后續程序。監察留置措施在某種程度上也能實現如拘留和逮捕兩種強制措施相類似的司法強制功能,但留置措施的適用程序較為復雜,從審批到落實環節較為繁多,由此可見,對于緊急的狀況,可以先行適用拘留措施暫時控制涉案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后續可考慮轉接逮捕程序。[4]此類情況下,需要監察機關與公安機關有效溝通和配合。
第二,采取非羈押性強制措施輔助辦案。除了一些緊急案件需要盡快控制相關涉案人員的人身自由需要公安機關的輔助辦案,或許我們還可以采取一些不具有限制人身自由性質的措施來進行案件調查。設置此類強制措施本著尊重保障人權的原則,讓被調查人員盡可能地放下防備心,某種程度上來講可能會更有助于案件調查。有學者提出,如不對其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一旦其竄逃,再行控制將會產生很多麻煩。但其實我們也可以通過加強對邊境出入的管理,限制其隨意出入境,嚴格監督該類人員的活動范圍。
3.合理規范羈押期限
監察留置措施的嚴厲性體現在對被調查人人身自由的限制和剝奪,從保障人權的角度來說,國家對該類措施的實施一定要有相應的、明確且合理的限制。否則會對法治社會應有的秩序造成嚴重的影響。因此,對監察留置措施羈押期限也可以首先設置一個最低時限,對于存在特殊情況的可以適當作出延長規定。
4.保障被調查人的辯護權利
監察留置措施作為一項強制措施具有限制被調查人人身自由的性質[5],此時,被調查人員的人身權利更值得被關注。限制自由期間允許律師介入是保障其合法權益以及實現法治公平的很好體現,有利于還原案件的真實性。《國家賠償法》中規定了被調查人員享有一定的申訴權,但是該法律的相關規定中卻沒有提及是否允許律師介入的問題。有學者認為,留置期間允許律師介入是理所應當的,首先,律師應從監察機關調查辦案開始參與案件;其次,應當給予律師充分的辯護空間,充分保障被調查人的辯護權。律師介入留置環節一定程度上也會助力非法證據的排除。由此看來,應當在留置期間為保障被留置人員的辯護權允許律師介入。
5.完善退回程序的法律規范
新《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2款規定:對于監察機關移送起訴的己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對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留置措施自動解除。關于司法程序向監察程序倒流的情況,基于刑事強制措施中的拘留與逮捕措施較監察留置措施而言更嚴格,適用要求更高。當涉嫌違法犯罪的人員已經被采取拘留或逮捕等強制性措施時,在退回程序上應采取“案退人不退”的原則[6],即相關案件由司法程序退回到監察程序,基于保障人權的考慮涉案的犯罪嫌疑人將不再隨案轉移羈押場所,而是在看守所內繼續羈押。另外,就當今現實情況來看,監察留置措施在場所設置、人員素質水平、設施完善程度等方面均不如刑事強制措施的規定明確詳細,由此建議監察機關可以參照刑事強制措施的各方面配套設施來完善留置措施的制度細則,當然監察機關也可以與刑事司法機關協作聯動辦案,提高效率,節約司法資源。
留置措施作為一項新生調查措施,在當前中國反腐的大背景下應運而生。針對監察留置措施與刑事強制措施銜接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主要從完善立法的角度提出了相應的建議,國家監察體制的改革,必然也離不開司法機關的科學配置,但司法機關應當從何時介入?以何種身份介入?這些問題或許還需要進一步的探討。在社會主義法治改革的進程中,監察留置措施必定要在法治軌道上運行才能更平穩、更高效。由此,在監察留置措施制度細化的過程中,一定要以《憲法》為根本,以刑訴法為標桿,從監察法入手,以保障人權為出發點,力爭形成一套構架合理、監督有效、銜接順暢的國家監察措施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