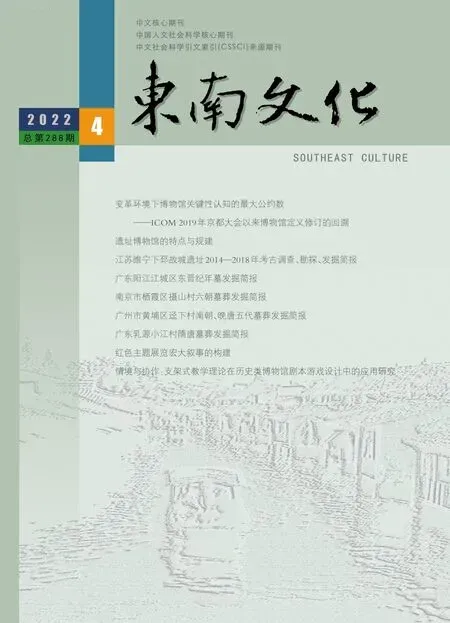紅色主題展覽宏大敘事的構建
張露勝
(山東博物館 山東濟南 250014)
內容提要:隨著博物館展覽的敘事轉向,宏大敘事理論在紅色展覽的策劃中顯得愈加重要。宏大敘事是將歷史事件及實物史料串聯成為具有因果聯系的歷史必然,是對歷史發展規律的探索與認知。其理論旨在研究宏大敘事對歷史事件的選擇和闡釋原理,闡述其與歷史真實“還原”與“超越”的辯證關系,探索敘事的故事性和整體性在紅色展覽實踐中的應用,構建紅色展覽宏大敘事的理論框架。紅色展覽可采用宏大敘事,借助藝術化手段,將歷史通過文字、圖片和展品呈現出來,讓歷史的敘事融入觀眾的認知框架,從而為公眾理解歷史提供更為形象、直觀的途徑。
近年來,博物館、紀念館等公共文化場館在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愛國主義精神方面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眾多紅色主題展覽(以下簡稱“紅色展覽”)相繼推出,讓更多珍貴的資料和史實為公眾所了解,同時也發揮了“引導人民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1]的重要作用。與傳統的以物為中心的展覽不同,紅色展覽更強調展覽的敘事性,將孤立的歷史事件及實物史料串聯成為具有必然因果聯系的歷史片段,是這一類展覽的基本特征。歷史事件不會自動成為展覽展示的內容,需要采用宏大敘事的方式進行選擇和闡釋。紅色展覽的“敘事轉向”是用史學理論的敘事方法描述一段歷史,或以時間軸貫穿,或以類別統攬。這種跨學科的實踐運用使得紅色展覽更具主體性與教育性,也為公眾理解歷史提供了更為形象、直觀的途徑。
敘事可以稱為“講故事”,它將特定的事件依時間順序納入一個能被人們理解和把握的語言結構,從而賦予其意義[2]。宏大敘事并非展覽語境的原生概念,而是后現代史學理論的主要內容,是一種歷史的呈現方式,在人類發展演進的大背景下探索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然后再以必然性規律解釋歷史事件。宏大敘事與歷史敘事又有明顯的區別:宏大敘事旨在闡釋歷史,探索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再以規律解釋歷史事件;歷史敘事旨在呈現歷史,有主觀意識地選擇和闡釋事件,敘事的方式多種多樣。我國紅色展覽所體現的宏大敘事代表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著重以自上而下的視角審視歷史的演變,通過宏大敘事類展覽展現近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一般性規律,體現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不斷取得勝利的必然性。紅色展覽追求的宏大敘事幾乎特指中國近現代史的“主流敘事”,由“鴉片戰爭—洋務運動—甲午戰爭—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進而與中國共產黨史相對接,描述從農民起義到工人運動、從落后挨打到民族覺醒,從“反帝反封建”、階級民族雙線交叉敘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以及社會主義建設階段。紅色展覽根據主題大多選取上述體系的一個或幾個部分,通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運動、軍隊建設、地區革命史、行業發展史等不同視角,闡述各個主體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發展歷程,其中整體敘事思路基本遵照宏大敘事的模式展開。
紅色展覽以宏大敘事為視角,綜合運用文本、圖片、實物、多媒體等方式形成合理的歷史流線,達到歷史與展示的統一。展覽的宏大敘事邏輯與歷史學的敘事有所區別,如何運用唯物史觀從大量無序的偶然事件中選取符合主題的典型事件,構成符合因果必然的時間流線,是紅色展覽主題的核心要求,更是發揮其在黨史學習教育、革命傳統教育、愛國主義教育等方面作用的必然要求。
一、歷史真實需要轉化為宏大敘事
紅色展覽的組成元素需要選擇和組合,事件與事件之間的闡述構成了它們相互間的聯系。唯物史觀認為歷史事件之間存在必然的聯系,歷史敘事的目的或者說紅色展覽的目的就是建立重要事件之間的聯系,組成歷史發展的完整鏈條。歷史的科學性以及展覽的客觀性體現在它完全依賴客觀事實、反映歷史真實事件,同時又強調闡釋聯系作用。
宏大敘事的展覽方式具有主觀能動性,是對歷史真實的正確闡述。歷史真實依據自然科學的原理和標準建立了其客觀性。因為人類社會發展普遍規律的客觀性,歷史學才成為一門學科。然而自然科學的客觀性是基于人們對客觀規律的共同認知,這些規律并不隨人們的認知而改變,但作為展覽敘事基礎的歷史文本卻容易被多種因素影響。我們在歷史認知過程中的研究對象并非是曾經發生過的、客觀的歷史事件本身,而是記錄和敘述歷史事件的文本,我們只有借助于歷史敘述者的文本這一中介,才有可能觸及歷史的本體。可以這樣認為,人們對歷史進程的認知是對歷史敘述結果的研究,研究的是一種敘述的活動,不僅包括研究敘述的內容,而且包括研究敘述的活動本身[3]。因此,展覽的宏大敘事所描述的是建立在歷史本體上的歷史敘述的“真”。歷史研究的目的是無限接近歷史本源。紅色展覽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主觀性的敘事活動,是探索歷史真實的過程。
紅色展覽的敘事文本是對歷史真實的“還原”與“超越”,因為它不可避免地出現對歷史事件的主觀闡釋。展覽策展人必須合理闡釋材料,以便建構符合歷史形象的認知,客觀地反映歷史發展進程。歷史事件的記錄存在著既太多又太少的兩面性。一方面,一段時期的事件記錄中會有很多事實,在以敘事方式再現某一歷史進程時,不可能把全部事實都包括進來[4]。對事件的選擇是紅色展覽敘事必須要做的事,排除與敘事目的無關的一些事實,保留能反映展覽意圖的重要事件。另一方面,當紅色展覽在努力重建歷史上特定時期發生的事件時,事件與事件之間總會缺乏必要的、過渡性的重要事件來構成宏大敘事的因果鏈條,這就需要在敘事中對某一事件或系列事件進行適當地闡釋。闡釋就是用宏大敘事展現的一般規律去解釋事件之間蘊含的必然聯系,從而闡明這些事件何以發生。
歷史事件本身并不能構成宏大敘事,需要使用闡釋的方法將一個個看似孤立的事件串聯成具有聯系的故事,這些故事才能構成宏大敘事。事件的闡釋具有明顯的主觀選擇性,可以是悲劇性結局,也可以是喜劇性結局,但沒有哪個歷史事件本質上就是悲劇或喜劇,只有從某個特定角度或將其置于由一系列事件建構的語境中,才能看出其在這個語境中的悲喜劇因素。歷史上某一事件從一個角度看是悲劇事件,而從另一角度看反而是喜劇事件。例如,西漢司馬遷記錄商末紂王帝辛沉湎酒色、窮兵黷武、重刑厚斂、拒諫飾非。這一事件如果周族后裔站在周王滅商的立場上,明顯是紂王昏庸無道,上天選擇周武王治理天下并成就了周王朝,是一部史詩;如果站在商朝遺老的立場,帝辛嚴格祭祀、開疆拓土,但最終未能守住帝業,是一部明顯的悲劇史;如果站在當代人視角,遵從朝代更替演變的規律,則認識到商周的朝代更替是生產力、階級矛盾、統治制度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們無從驗證歷史事件究竟是什么樣,歷史敘事則取決于策展人根據哪種情節結構構造它們。同一個事件可以成為悲劇或喜劇故事的組成部分,是悲劇還是喜劇則取決于展覽對情節結構的選擇,取決于視角、立場,這也是構建紅色展覽宏大敘事的理論基礎。
宏大敘事與歷史真實是兩個相互的概念。宏大敘事的素材來源于歷史真實,并經過選擇和闡釋,但宏大敘事又超越歷史真實,畢竟它強調歷史事件的一般規律。紅色展覽是學術研究的成果體現,將紅色展覽闡釋為展覽文本的敘事方式并不完全等同于還原歷史真實,但具備科學性和客觀性。闡釋的任務就是發現那些嵌在雜亂無章的事件中的真實故事,經過合理的組合,盡可能真實、完整、合乎邏輯地重述它們。
二、紅色展覽宏大敘事的故事性與整體性
紅色展覽需要將事件闡述為故事,將不同故事融入更大的歷史進程中,用鮮活、感人的故事組成敘事的骨肉,形成歷史發展的趨勢。事件是客觀的,而故事需要闡釋和發現。宏大敘事需要用一個個故事去解釋和證明更早的歷史意義及規律。故事性敘述需要在宏大敘事的整體性中把握,即便是同一個事件也可以成為許多不同歷史敘述的不同因素,在對這段歷史敘述進行特定主題描寫時,其故事的性質將決定這個因素所扮演的角色。假如我們對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示威游行進行梳理和描述,這一事件可以是“五四運動”爆發的起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可以是法國巴黎“和平會議”(Paris Peace Conference)的結果,可以是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轉折的關鍵節點。顯然,一個事件的故事性敘述需要整體考慮其故事因素的“功能”,以及在不同故事序列中的作用和地位。
在宏大敘事中構建某一段敘事,就不可避免地面臨如何組織事件發生的前因后果這一任務,包括“如何發生”“為什么以這種而非那種方式發生”“后來又發生了什么”“結局是怎樣的”[5]。這些問題構成了事件與事件之間的關聯,將敘事塑造成一個有著前因后果的完整故事,這種敘事策略決定了宏大敘事如何展開。同時,“它的總體意義是什么”“它的主旨是什么”等指出了敘事的整體性問題,需要在展覽的整體構建中揣摩這個典型事件所處的位置和所占的地位。紅色展覽中常有表現黨的群眾路線和群眾工作方面的內容,對抗日戰爭時期的歷史常會選擇“沂蒙紅嫂”這樣一組典型敘事,反映了水乳交融的軍民魚水情,代表了沂蒙山區女性群體對革命事業的支持。對于沂蒙紅嫂中的明德英、祖秀蓮、張淑貞等紅嫂,紅色展覽一般通過圖片、實物、影像構成各自的敘事,而這些獨立的敘事由于其背景、時代、地域、事跡中的共性形成了以沂蒙紅嫂為形象的歷史敘事。沂蒙紅嫂敘事發生在抗日民主政權建立之后,此時日本侵略軍對敵后根據地進行了殘酷掃蕩,由于我方部隊和政權得到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最終在1945年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以沂蒙紅嫂為代表的群眾路線事件串聯起抗日政權建立與抗戰勝利兩個事件,形成了抗日戰爭勝利的因果鏈條,構成了一組完整的宏大敘事。沂蒙紅嫂敘事的選擇與闡釋從史實上、邏輯上建立起抗日政權建立與抗戰勝利兩個事件的關聯,體現了宏大敘事的整體性。
展覽敘事作為一種講故事的話語模式,需要將多種元素融入到展覽的故事模式中,從而賦予紅色展覽所要表達的意義。博物館、紀念館的紅色展覽多以實物為基礎,觀眾更關心的是展品究竟呈現了怎樣的故事、被放入到怎樣的敘事中、與周圍的展品形成了怎樣的歷史序列。整個展覽敘事流程既不同于自然科學的客觀性,也與歷史真實有一定區別,需要結合兩者的特征讓宏大敘事中的故事更具科學性與真實性。整體性是展覽敘事所要達到的目標,需要將大量不同時期、地點的展品與紛繁的圖版、場景揉合,表達一個完整的核心觀念。展覽中的事件元素或文獻資料如果只是被隨意地擺放陳列,那么觀眾對這段歷史的認識也僅停留在表面,無法對事件的前后關聯及其在主題中的意義獲得系統性歷史認知,觀眾只能獲取過去的片段,而無法將展示的事件形成一種理解。如果說史書是將雜亂的過去轉變為敘事,那么紅色展覽也必然要求將這些展品(即“過去的碎片”)轉變為可以被觀眾理解的故事。在宏大敘事中,關于展覽結構的整體與部分的策略,通常會采用轉喻與提喻的方式。轉喻的特征是將部分的闡述視作整體的代表,紅色展覽中表現抗戰勝利的內容通常會選擇展示一個或幾個有代表性的勝利成果,比如日本天皇裕仁(Hirohito)簽訂《終戰詔書》的場景、日偽軍向八路軍投降的巨幅照片、大量繳獲的武器等都被視作抗戰勝利的標志,敘事的部分被賦予整體性的意義。提喻與轉喻相反,是從整體引申到部分。如在紅色展覽初始便對整體敘事提出“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判斷命題,然后通過展覽呈現的一個個歷史事件或事件組合去驗證命題,并且這些歷史事件在驗證過程中也體現了其在宏大敘事中的作用。
紅色展覽就是將史料、展品、空間結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將觀眾的關注點集中于展覽本身而不是一個孤立的空間或幾個毫無關聯的展臺,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將這些展示元素賦予相應的歷史意義。這些挑選和闡釋過的元素逐步被梳理出具備因果必然性的歷史脈絡,然后完整地呈現給觀眾,讓更多的史學研究成果進入觀眾的視野,甚至可以推動公眾層面對歷史乃至當代的思索。紅色展覽的內容設計可以借鑒藝術創作的開放性,這樣能夠使展覽有更大空間表達主題,更聚焦于表達的整體性和敘事故事的合理性。
三、紅色展覽的藝術性表達
如果將展覽敘事的范疇擴展到藝術層面,這種敘事方式會賦予策展人更多的自主性,方便他們組織展品、事件和時間線。與歷史學的方法不同,藝術是借助一些手段或媒介,通過塑造形象、營造氛圍來反映現實、寄托情感的一種文化方式。它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礎上更強調策展人的主觀性,更強調展覽帶給觀眾的感受,將歷史的故事通過當代的表達和展示,給人以當下的思考。以“人”的視角組織歷史中的各個“點”,讓那些孤立的展品和歷史事件匯入展覽的歷史脈絡,那么一個展覽就不再是器物和事件的堆砌,而是一段完整的敘事,觀眾的參觀就是重溫歷史,歷史事件和展品證明了敘事的邏輯性。紅色展覽所展示的歷史脈絡代表了展覽敘事的呈現方式,觀眾對這段歷史脈絡的接受和認同也代表了對展覽策劃的認可。
藝術化同時也是宏大敘事的表現手段。材料甄選和闡釋是展覽的準備階段,若要讓敘事更好地呈現在公眾面前,需要用藝術手段組織材料并將其呈現出來。紅色展覽需要明確的主題色彩和宣傳手段,轉喻、提喻的手段常常能達到引導故事的發生和延伸、表達出展覽本意的效果。關于同樣的事件,不同的敘事策略能夠達到不同的宣傳效果,可通過故事化或英雄化的藝術手段發揮烘托氛圍、弘揚主題的作用。紅色展覽除了敘事方式的藝術化,還需要展示方式的藝術化。如果文本敘述主題突出、符合邏輯,那么就需要將這些文本用藝術化的形式展示出來。場景復原、藝術品創作、多媒體展示、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VR)等方式都可以將文本進行實物化呈現,讓公眾對描寫的歷史有更直觀的、更深入的感受。這些呈現方式都要與敘事策略保持一致,包括展示項目的體量及其在整個展覽中的比例、典型事件展示的位置及其在整體展線中節奏控制、多媒體設備的位置布點等方面。有些事件可能在文本中的內容不多,但對于展覽的主題渲染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這就需要用新手段、新形式擴大這一部分的展示面積,突出這一事件在展覽中的地位,而不局限于敘事文本。比如很多涉及解放戰爭勝利內容的紅色展覽,常用群眾支前事件揭示戰爭勝利的原因及正當性。相較于三大戰役展出的圖版資料和文物、實物,支前的內容似乎不像戰場那樣風云激蕩、氣魄雄偉,但是它代表了解放戰爭的群眾基礎,體現了農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很多紅色展覽為了突出它的重要性,采用雕塑、場景、多媒體等方式表達,用大量圖片講述支前事件中涌現的英雄模范和感人事跡。
紅色展覽并不是枯燥的說教,而是集主題性與藝術性于一體的宣傳展示。宏大敘事需要通過靈活的表達方式讓更多公眾接受,需要運用當代的技術手段提升宣傳能力。如果以藝術視角審視展覽敘事,除了能夠還原歷史的遺存與風采,還可以借史喻今、反思當下,讓觀眾在觀展之余對歷史有更深層次的認識。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紅色資源利用好、把紅色傳統發揚好、把紅色基因傳承好”[6],“要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要打造精品展陳,生動傳播紅色文化”[7]。這對如何用好宏大敘事、辦好紅色展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宏大敘事是對歷史發展規律的探索與認識,紅色展覽是宏大敘事的呈現結果,展覽正是用藝術手法將歷史通過文字、圖片和展品呈現出來,讓歷史規律融入觀眾的認知框架。通過創新紅色展覽的敘事方式,講述紅色文物承載的歷史記憶,關注重大歷史展覽的時代表達,達到促進黨史學習教育、革命傳統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的目的,讓紅色文化直抵人心,構筑傳承紅色基因、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精神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