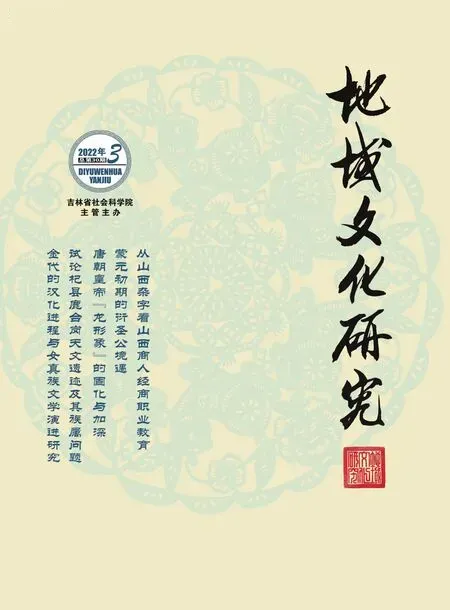清朝皇帝罪己詔評(píng)議
簡(jiǎn) 東
一、罪己詔的歷史由來(lái)與主要形式
關(guān)于罪己詔的起源,有前人認(rèn)為是始自禹、湯罪己。這一說(shuō)法因年代久遠(yuǎn)很多資料已不可見(jiàn),同時(shí)又經(jīng)后人的附會(huì)神化,已然無(wú)從確切考證。目前,在古代傳世文獻(xiàn)里能夠找到的罪己詔最早雛形,是《尚書(shū)》中的《湯誥》和《秦誓》兩篇。《湯誥》講的是商滅夏后湯布告天下以安民心,并檢討自己以往的過(guò)錯(cuò),來(lái)獲取更多的理解和支持;《秦誓》記述的則是在勞師遠(yuǎn)征慘敗、數(shù)萬(wàn)將士有去無(wú)回的情況下,秦穆公悔過(guò)罪己的事。尤其是《秦誓》的篇末說(shuō),“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這事實(shí)上點(diǎn)明了一國(guó)之君與國(guó)家安危之關(guān)系,即君主要對(duì)國(guó)家安危興亡負(fù)責(zé)。《呂氏春秋》中也有商湯罪己的記述,并且其文字更為詳細(xì)而又具有范本意義。它在記述該事件時(shí)用到了“余一人有罪,無(wú)及萬(wàn)夫……”的概述方式,這逐漸成了后世罪己詔中常用的格式化語(yǔ)言。另外在其他的典籍中也曾流露君主的罪己意識(shí),如《詩(shī)經(jīng)·周頌·小毖》中的“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該篇講的是周成王在平定管、蔡之亂后,擔(dān)心再有家國(guó)禍患、黎民困苦的發(fā)生,反思亂起之因繼而作詩(shī)自誡。這兩句詩(shī)要表達(dá)的意思就是“缺少輔佐我心焦,只能獨(dú)自操心勞”①程俊英:《詩(shī)經(jīng)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36頁(yè)。,反映的是君主兢兢業(yè)業(yè)、自警求治的心態(tài)和愿望。其實(shí),中國(guó)歷史上第一次明確地頒布真正“罪己詔”的人是漢文帝。公元前179年,漢文帝不同意大臣們?cè)缌⑻拥慕ㄗh,就頒詔說(shuō):“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愜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圣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①班固:《漢書(shū)》卷4《文帝紀(jì)》,北京:中華書(shū)局,1962年,第111頁(yè)。即如果我現(xiàn)在立太子,就更加重了我的不道德。事后不久漢文帝接著又頒布了一道罪己詔。然而,歷史上被認(rèn)為分量幾乎最重的罪己詔則是漢武帝的《輪臺(tái)罪己詔》,這也是中國(guó)歷史上第一份內(nèi)容宏富并保存完好的罪己詔。它被認(rèn)為是宣告結(jié)束了武帝晚期“擾勞天下”的窮兵黷武,指導(dǎo)西漢政權(quán)迅速轉(zhuǎn)變內(nèi)外方針,重新回復(fù)到與民休息及重視發(fā)展經(jīng)濟(jì)的軌道,從而避免了民耗日重、國(guó)疲政亡的惡果。因此,此詔極具歷史意義和文獻(xiàn)價(jià)值。
古代帝王罪己詔資料的出處,除“二十六史”中的帝王本紀(jì)之外,還有《資治通鑒》《續(xù)資治通鑒長(zhǎng)編》《續(xù)資治通鑒長(zhǎng)編補(bǔ)遺》《續(xù)資治通鑒》以及宋代《冊(cè)府元龜》、明清歷朝實(shí)錄、清代《東華錄》和歷代的記事本末等史籍。中國(guó)歷史上共有82 位皇帝下過(guò)罪己詔。一份若按出自漢文帝公元前179年算起,到最后一份所在的1916年,整個(gè)時(shí)間跨度為2095年;如果以“二十六史”為限,第一份出現(xiàn)在公元前179年,最后一份的頒布時(shí)間應(yīng)為1895年,時(shí)間跨度是2074年,則平均近8年就有一份罪己詔頒發(fā)。有學(xué)者曾統(tǒng)計(jì),在“二十六史”中共有264份帝王的罪己詔,②韓靜:《罪己詔中的儒家思想探析》,《遼寧行政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2年第2期。其中因?yàn)?zāi)異而罪己的占比最多,約占四成;其他類(lèi)型的罪己詔,都有普遍的自謙性,但能準(zhǔn)確地把握住“人禍”而罪己的則不多。另經(jīng)筆者重新統(tǒng)計(jì),各朝下過(guò)罪己詔的皇帝數(shù)目分別為:兩漢皇帝(包括呂后)有15位、三國(guó)時(shí)期3 位、兩晉7 位、南朝14 位、北朝1 位、隋朝1 位、唐朝8 位、五代6 位、兩宋7 位、遼代1 位、金代1位、元代4位、明代3 位、清代7位。若從其所占整個(gè)朝代的比例來(lái)看,清代則頗高:12位皇帝中有7個(gè)下過(guò)罪己詔。這在整個(gè)中國(guó)歷史上表現(xiàn)得非常突出,是一個(gè)不容忽視、值得深刻分析的歷史現(xiàn)象。
還需說(shuō)明的是,從廣義上來(lái)講,古代帝王們的罪己詔,除了公布于天下、帶有明確“罪己”相關(guān)字眼的詔書(shū),還包括祭告天地、太廟、社稷以悔過(guò)的活動(dòng)以及當(dāng)面、小范圍、非正式的“口諭”等更加靈活的形式。狹義上的罪己詔僅指第一重意思。本文為減少表述方面的爭(zhēng)議,同時(shí)盡可能參考更為規(guī)范的文本,故這里取狹義上的罪己詔形式進(jìn)行研究。但另需明確,雖然這類(lèi)詔書(shū)也并非完全出自皇帝本人之手,真正由皇帝擬發(fā)的詔書(shū)更是少之又少,一般情況下多經(jīng)相關(guān)閣臣、僚屬潤(rùn)色甚至代筆,但是最后詔書(shū)仍進(jìn)呈皇帝親自“御覽”“圣裁”,加蓋印綬,以璽為信。所以可以說(shuō),這就是皇帝本人的意愿態(tài)度,何況詔涉“罪己”,關(guān)乎自己和王朝的形象、信譽(yù)以及現(xiàn)實(shí)作用和后世評(píng)價(jià),必須慎之又慎。本文所討論的罪己詔,其發(fā)布者清代諸帝(除宣統(tǒng)帝外)又都是在自己親政后頒發(fā)的,因此更能視之為皇帝本人的意志。
二、清代諸帝的罪己詔述略
經(jīng)整理,清代歷任皇帝頒發(fā)過(guò)罪己詔的一共有7 位,每位皇帝頒詔情形如下③注:限于篇幅這里僅做重點(diǎn)節(jié)錄,并不將所有罪己詔文本列出。:順治皇帝罪己詔。據(jù)《清世祖實(shí)錄》載,其下罪己詔共有三次。第一次在順治十一年(1654)十一月,福臨以地震屢聞、水旱迭告、民生艱難而躬省自責(zé),頒詔大赦天下。第二次是在順治十七年(1660)正月,福臨再次躬省引咎,詔令大赦天下。第三次是順治十八年(1661)正月,福臨臨終前以罪己詔的形式頒布遺命,列十四款罪狀自咎。盡管此次詔書(shū)的內(nèi)容后來(lái)可能為孝莊太后與輔政大臣所修改,但行文整體上仍與其一貫風(fēng)格相符。此詔書(shū)全文如下:
朕以涼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茲矣。自親政以來(lái),紀(jì)綱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謨烈,因循悠乎,茍安目前;且漸習(xí)漢俗,于淳樸舊制日有更張,以致國(guó)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朕自弱齡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賓,教訓(xùn)撫養(yǎng),惟圣母皇太后慈育是依,大恩罔極,高厚莫酬,惟朝夕趨承,冀盡孝養(yǎng),今不幸子道不終,誠(chéng)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皇考賓天時(shí),朕止六歲,不能衰經(jīng)行三年喪,終天抱恨,帷事奉皇太后,順志承顏,且冀萬(wàn)年之后,庶盡子職,少抒前憾,今永違膝下,反上廑圣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宗皇諸王貝勒等,皆系太祖、太宗子孫,為國(guó)藩翰,理應(yīng)優(yōu)遇,以示展親。朕于諸王貝勒等,晉接既正東,恩惠復(fù)鮮,以致情誼暌隔,友愛(ài)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滿(mǎn)洲諸臣,或歷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宣加倚托,盡厥猷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國(guó),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為戒,反委任漢官,即部院印信,間亦令漢官掌管,以致滿(mǎn)臣無(wú)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朕夙性好高,不能虛己延納,于用人之際,務(wù)求其德于己相侔,未能隨材器使,以致每嘆乏人。若舍短錄長(zhǎng),則人有微技,亦獲見(jiàn)用,豈遂至于舉世無(wú)材,是朕之罪一也。設(shè)官分職,惟德是用,進(jìn)退黜陟不可忽視,朕于廷臣中,有明知其不肖,刀不即行罷斥,仍復(fù)優(yōu)容姑息,如劉正宗者,偏私躁忌,朕已洞悉于心,乃容其久任政地,誠(chéng)可謂見(jiàn)賢而不能舉,見(jiàn)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國(guó)用浩繁,兵餉不足,然金花錢(qián)糧,盡給宮中之費(fèi),未常節(jié)省發(fā)施,及度支告匱,每令會(huì)議,即諸王大臣會(huì)議,豈能別有奇策,只得議及裁減俸祿,以贍軍需,厚己薄人,益上損下,是朕之罪一也。經(jīng)營(yíng)殿宇,造作器具,務(wù)極精工,求為前代后人所不及,無(wú)益之地,靡費(fèi)甚多,乃不自省察,罔體民艱,是朕之罪一也。端敬皇后于皇太后克盡孝道,輔佐朕躬,內(nèi)政聿修,朕仰奉慈綸,追念賢淑,喪祭典禮概從優(yōu)厚,然不能以禮止情,諸事太過(guò),豈濫不經(jīng),是朕之罪一也。祖宗創(chuàng)業(yè)未嘗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國(guó)亦因委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為戒,設(shè)內(nèi)十三衙門(mén),委用任使與明無(wú)異。致?tīng)I(yíng)私作弊更逾往時(shí),是朕之罪一也。朕性耽閑靜,常圖安逸,燕處深宮,御朝絕少,以致與廷臣接見(jiàn)稀疏,上下情誼否塞,是朕之罪一也。人之行事,孰能無(wú)過(guò),在朕日理萬(wàn)機(jī),豈能一無(wú)違錯(cuò)?惟肯聽(tīng)言納諫,則有過(guò)必知。朕每自恃聰明,不能聽(tīng)納。古云,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朕于斯言,大相違背,以致臣士緘然,不肯進(jìn)言,是朕之罪一也。朕既知過(guò),每自刻責(zé)生悔,乃徒尚虛文,未能者改,以致過(guò)端日積,愆戾逾多,是朕之罪一也。太祖、太宗創(chuàng)垂基業(yè),所關(guān)至重,元良儲(chǔ)嗣,不可久虛,朕子玄燁,佟氏妃所生也,年八歲,岐嶷穎慧,克承宗祧,茲立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釋服,即皇帝位。特命內(nèi)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為輔臣,伊等皆勛舊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天忠盡,保翊沖主,佐理政務(wù),而告中外,咸使聞知。順治十八年正月壬子。①趙爾巽等:《清史稿》卷5,北京:中華書(shū)局,1976年,第161-162頁(yè)。
康熙皇帝罪己詔。康熙十八年(1679)七月壬戌因京師地震而頒發(fā):
“朕御極以來(lái),孜孜以求,期于上合天心,下安黎庶……地忽大震,皆因朕功不德,政治未協(xié),致茲地震示警。悚息靡寧,勤求致災(zāi)之由……大小臣工弗能恪共職業(yè),以致陰陽(yáng)不和,災(zāi)異示儆……用是昭布朕心,愿與中外大小臣工共勉之。”①趙爾巽等:《清史稿》卷6,北京:中華書(shū)局,1976年,第200-201頁(yè)。
乾隆皇帝罪己詔。弘歷在成為太上皇的第二年(1797)十月丙辰,乾清宮大火,②趙爾巽等:《清史稿》卷16,北京:中華書(shū)局,1976年,第571頁(yè)。連放在交泰殿的“天子御寶”也遭到了“回祿之災(zāi)”。為此弘歷才破例“下詔自省”。
嘉慶皇帝罪己詔。第一次在嘉慶八年(1803)閏二月,嘉慶帝外出回宮時(shí)途徑順貞門(mén)險(xiǎn)遭一男子持刀行刺,此人旋被侍衛(wèi)擒拿。后查明此人曾為內(nèi)務(wù)府旗人家奴,自供述因失業(yè)才鋌而走險(xiǎn)刺駕。颙琰事后驚怒交加,嚴(yán)審無(wú)異后即下旨將其凌遲處死。同時(shí)又下詔罪己,述君臨天下八年來(lái),視“舉朝臣工皆同朕之兄弟侄、至親骨肉”,不解何以出此兇犯?最后還是采取了反躬自省:“朕所慚懼者,風(fēng)化不行,必有失德,始有此警予之事;當(dāng)謹(jǐn)身修德,勤政愛(ài)民,自省己咎。”③趙爾巽等:《清史稿》卷16,北京:中華書(shū)局,1976年,第586頁(yè)。第二次是在嘉慶十八年(1813)。是年九月十五日,七十多名天理教徒闖入紫禁城燒搶打殺,雖然很快就被旻寧等王室宗親平息了事變,但它引發(fā)了京師內(nèi)外的極大驚恐。正在木蘭秋狝的颙琰聞?dòng)嵁?dāng)即終止了活動(dòng),連發(fā)上諭令京師官員追查、嚴(yán)懲這些教徒,并于九月十七日在回京路上頒發(fā)了著名的《朱筆遇變罪己詔》。詔書(shū)全文:
朕以涼德,仰承皇考付托,兢兢業(yè)業(yè)十有八年,不敢暇豫。即位初,白蓮教煽亂四省,黎民遭劫,慘不忍言。命將出師,八年始定。方期與吾赤子永樂(lè)昇平,忽于九月初六日,河南滑縣又起天理教匪,由直隸長(zhǎng)垣至山東曹縣,亟命總督溫承惠率兵剿辦。然此事究在千里之外,猝于九月十五日變生肘腋,禍起蕭墻。天理教逆匪七十余眾,犯禁門(mén)、入大內(nèi),戕害兵役,進(jìn)宮四賊,立即捆縛。有執(zhí)旗上墻三賊欲入養(yǎng)心門(mén),朕之皇次子親執(zhí)鳥(niǎo)槍連斃二賊,貝勒綿志續(xù)擊一賊,始行退下。大內(nèi)平定,實(shí)皇次子之力也。隆宗門(mén)外諸王大臣、督率鳥(niǎo)槍兵,竭二日一夜之力剿捕,搜拏凈盡矣。我大清國(guó)一百七十年以來(lái)定鼎燕京,列祖列宗深仁厚澤,愛(ài)民如子,圣德仁心,奚能縷述。朕雖未能仰紹愛(ài)民之實(shí)政,亦無(wú)害民之虐事。突遭此變,實(shí)不可解,總緣德涼愆積,唯自責(zé)耳。然變起一時(shí),禍積有日。當(dāng)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實(shí)中外之所同。朕雖再三告誡,舌敝唇焦,奈諸臣未能領(lǐng)會(huì),悠忽為政,以致釀成漢唐宋明未有之事,較之明季梃擊一案,何啻倍蓰。思及此,實(shí)不忍再言矣。予唯返躬修省,改過(guò)正心,上答天慈,下釋民怨。諸臣若愿為大清國(guó)之忠良,則當(dāng)赤心為國(guó),竭力盡心,匡朕之咎,移民之俗。若自甘卑鄙,則當(dāng)掛冠致仕,了此一身。切勿尸祿保位,益增朕罪。筆隨淚灑,通諭知之。④《清實(shí)錄·仁宗實(shí)錄》冊(cè)31,卷274,北京:中華書(shū)局,2008年,第33076頁(yè)。
咸豐皇帝罪己詔。咸豐三年(1853)正月初八,咸豐皇帝因太平天國(guó)亂起下罪己詔。
光緒皇帝罪己詔。光緒二十六年(1900)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慈禧均以載湉的名義下罪己詔。慈禧還在光緒二十七年(1901)十二月癸亥頒發(fā)的懿旨中,將自己犯了錯(cuò)誤和引咎自責(zé)之意公開(kāi)告知天下臣民:“以當(dāng)時(shí)委曲苦衷示天下,并誡中外諸臣激發(fā)忠誠(chéng),去私心、破積習(xí),力圖振作”。①趙爾巽等:《清史稿》卷24,北京:中華書(shū)局,1976年,第934頁(yè)、第937頁(yè)。
宣統(tǒng)皇帝罪己詔。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fā),湖北、湖南、陜西、山西、云南相繼宣告獨(dú)立,攝政王載灃追悔莫及,同月30日以溥儀的名義下詔罪己,言執(zhí)政三年以來(lái)用人不當(dāng)、治理無(wú)術(shù),高官多用親貴、顯違憲政;鐵路國(guó)有及向外國(guó)借款修筑等事實(shí)蒙蔽于小人,動(dòng)違輿論,以致引起各省之亂,全國(guó)沸騰、人心動(dòng)搖,“此皆朕一人之咎也”。“茲特布告天下,誓與我國(guó)軍民維新更始,實(shí)行憲政。凡法制之損益,利病之興革,皆博采輿論,定其從違。以前舊制舊法有不合于憲法者悉皆罷除。”②趙爾巽等:《清史稿》卷25,北京:中華書(shū)局,1976年,第999頁(yè)。
三、清帝罪己詔的具體內(nèi)容與思想內(nèi)涵
上述清代諸帝的罪己詔無(wú)一不是產(chǎn)生于具體的特定情境之下,其中尤以順治、嘉慶兩帝罪己次數(shù)為多且最具典型性。順治當(dāng)國(guó)時(shí),清王朝剛剛在全國(guó)范圍內(nèi)建立政權(quán),根基未穩(wěn),國(guó)內(nèi)面臨著一系列問(wèn)題,又天災(zāi)多發(fā),所以其承受的是王朝初期幾乎一切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guò)的難題;嘉慶在位時(shí),清王朝剛好處在政權(quán)轉(zhuǎn)型的岔路口,要么僵化疲軟、盛極而衰,要么忍受陣痛、完成變革,所以其應(yīng)對(duì)的是王朝中期普遍有過(guò)的關(guān)乎生死存亡的機(jī)遇與挑戰(zhàn)。
通常,中國(guó)古代的諸多帝王如果到了生命的最后關(guān)頭,自認(rèn)有功者就矜伐其功,有過(guò)者則勇?lián)哼^(guò),那么他們的臨終之言往往能夠名垂青史。所謂“鳥(niǎo)之將亡,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蓋其言至誠(chéng)也。而承認(rèn)己過(guò)者更為不易。如順治帝自14 歲親政就開(kāi)始了“地震屢聞,水旱累見(jiàn)”的歲月,種種困難和矛盾交織在一起,使這個(gè)立志做明君賢王、求治心切的少年天子長(zhǎng)期生活在自責(zé)之中,他逐漸把一切災(zāi)難原因都?xì)w于自己,下詔罪己。臨終又發(fā)出罪己傳位詔,列舉了自己治國(guó)不力、不孝不悌、用人不明、損下益上、不恤民力、任用宦官、疏于溝通、自恃聰明、知錯(cuò)不改等方面的14款罪。結(jié)合歷史來(lái)看,這14款自罪有很多有待商榷之處,福臨頗有些言重,而其背后的思想動(dòng)機(jī)卻很耐人尋味。不過(guò)直到現(xiàn)在,后世仍有很多人對(duì)這道遺詔存疑,認(rèn)為詔書(shū)內(nèi)容并不完全是順治帝本意,而是經(jīng)過(guò)了孝莊太后和群臣的改動(dòng)。此詔頗長(zhǎng),且絕大多數(shù)文字屬自罪自悔之語(yǔ),羅列罪名達(dá)14款之多,而后才是指定繼承人及任命輔政四臣這樣的關(guān)乎后世朝局的重要信息。但即使是如此重要的人事安排,卻不過(guò)只有寥寥數(shù)語(yǔ)。就此而言,若說(shuō)是順治帝親擬,確實(shí)令人費(fèi)解狐疑。在歷史上,凡皇帝遺詔,雖說(shuō)還是以大行皇帝的名義和口吻發(fā)布,并包含大行皇帝生前已囑托事項(xiàng)諸內(nèi)容,可歸根到底,詔書(shū)還要經(jīng)后人再擬,而身后的朝局與政見(jiàn)畢竟無(wú)法控制,由是詔書(shū)表述與其本意不可避免地產(chǎn)生差異,甚至齟齬、背離。此般情形,到康熙帝決定采取生前預(yù)立遺詔之舉措時(shí)愈顯明晰。康熙帝之所以欲在生前擬好遺詔,正因“自昔帝王,多以死為忌諱。每觀(guān)其遺詔,殊非帝王語(yǔ)氣,并非中心之所欲言。此皆昏瞀之際,覓文臣任意撰擬者”③《清實(shí)錄·圣祖實(shí)錄》冊(cè)6,卷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北京:中華書(shū)局,2008年,第5639頁(yè)。。但是,縱然有上述經(jīng)過(guò)改述的疑竇與因素存在,順治帝的罪己遺詔還是有值得研究的重要價(jià)值。曾有學(xué)者指出,“順治屢下罪己詔諭,形成鮮明的自罪風(fēng)格。尤其他臨終時(shí)以罪己詔的形式擬定自己的遺詔,前無(wú)古人后無(wú)來(lái)者,在中國(guó)歷史上絕無(wú)僅有”①成積春:《論順治“罪己”》,《社會(huì)科學(xué)戰(zhàn)線(xiàn)》2006年第3期。。仔細(xì)審讀可發(fā)現(xiàn),這些罪狀中關(guān)于孝悌之道、愛(ài)惜民力、實(shí)行仁政等表述顯然都是受到了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影響。事實(shí)上,這反映出不僅是福臨個(gè)人,更是清初整個(gè)統(tǒng)治階層的政治體認(rèn),在某種程度上已默認(rèn)儒家王道政治觀(guān)為衡量其統(tǒng)治得失的尺度。尤其是福臨個(gè)人,親政以后便對(duì)漢族儒家文化興趣濃厚,對(duì)天人感應(yīng)論、儒家帝王思想也有了較深的體悟。他曾苦讀經(jīng)史,所讀之書(shū)是“四書(shū)五經(jīng)”中的一部分和《左傳》《史記》等經(jīng)典。②據(jù)《清實(shí)錄·世祖實(shí)錄》所記,福臨所讀之書(shū)有《尚書(shū)》(冊(cè)3,卷72,順治十年二月壬戌,北京:中華書(shū)局,2008年,第2065頁(yè))、《孝經(jīng)》(冊(cè)3,卷96,順治十二年十二月癸未,北京:中華書(shū)局,2008年,第2242頁(yè))、《易經(jīng)》(冊(cè)3,卷107,順治十四年二月戊寅,北京:中華書(shū)局,2008年,第2326頁(yè))等。又據(jù)陳垣先生引《北游集》所書(shū),順治帝還讀過(guò)《左傳》《史記》等經(jīng)典書(shū)籍。(《陳垣集·湯若望與木陳忞》,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00年,第272頁(yè)。)因此他具備了一定的儒家文化素養(yǎng)。同時(shí),親政后的他還不斷被漢族儒臣諫習(xí)圣學(xué)以“弼成圣德”“光圣治”,效果很理想。例如,順治九年(1652)九月,福臨曾親赴太學(xué)祭奠先師孔子,還特意宣布以“如日中天”的圣人之道治國(guó),這實(shí)質(zhì)就是在向天下臣民尤其是漢官申明以儒治國(guó)的決心。另外,在當(dāng)時(shí)漢臣諫阻親迎喇嘛的事件中,福臨真正感受到了儒家思想特別是其天人感應(yīng)論在維護(hù)皇權(quán)方面的巨大威力。漢臣勸諫福臨克己修省,對(duì)百姓“積誠(chéng)以動(dòng)之,悔過(guò)以感之”③《清實(shí)錄·世祖實(shí)錄》冊(cè)3,卷69,順治九年十月壬寅,北京:中華書(shū)局,2008年,第2034頁(yè)。;修成君德,以“二帝三王之學(xué)為學(xué)”,使“天命自相與流通”④《清實(shí)錄·世祖實(shí)錄》冊(cè)3,卷69,順治九年十月庚申,北京:中華書(shū)局,2008年,第2038頁(yè)。。終于,在順治十一年(1654)十一月他就頒發(fā)了一道罪己詔,指出“朕以藐躬托于王公臣僚之上,政教不修、經(jīng)綸無(wú)術(shù),一夫不獲,咎在朕躬”。⑤《清實(shí)錄·世祖實(shí)錄》冊(cè)3,卷87,順治十一年十一月壬寅,北京:中華書(shū)局,2008年,第2176頁(yè)。這可視為順治罪己觀(guān)念基本形成的標(biāo)志。
罪己行為產(chǎn)生于當(dāng)時(shí)王朝初期特殊的政治背景與順治帝的個(gè)人經(jīng)歷中,是順治對(duì)自我政治責(zé)任的體認(rèn),是在紛亂的政治矛盾中訓(xùn)導(dǎo)大臣、安撫百姓的一種手段,更是其個(gè)人壯志難酬的一種情感宣泄。同時(shí),這種在儒家圣王觀(guān)念導(dǎo)向下的君主政治行為自然會(huì)給施政方針?lè)椒◣?lái)有利的效用。罪己的動(dòng)力正是帝王光耀祖業(yè)、治平天下的宏大愿望。福臨曾言:“朕思天為天下而立君,為君者代天敷治,必使民物咸若,治臻上理。”⑥《清實(shí)錄·世祖實(shí)錄》冊(cè)3,卷99,順治十三年三月丙午,北京:中華書(shū)局,2008年,第2263頁(yè)。他確實(shí)也在以“勤于圖治”努力踐行。不過(guò)還應(yīng)看到,福臨罪己雖有一定的積極影響,但也產(chǎn)生了某些消極作用。這些消極的方面和儒家的禮樂(lè)教化思想其實(shí)是有所齟齬的。儒家也強(qiáng)調(diào)“過(guò)猶不及”。如福臨習(xí)慣性自我貶損,長(zhǎng)期不稱(chēng)“圣”、不受朝賀,這必然給他治平天下的信念和動(dòng)力帶來(lái)逆向效應(yīng),順治末年其沉迷佛事、怠于政事與此亦有關(guān)系。
還需指出的是,如果擴(kuò)大問(wèn)題的關(guān)注視野,不難發(fā)現(xiàn),清代前期的帝王罪己行為也是官方“圣王制造”舉措的一部分。康熙二十年(1681)后,清廷官方逐漸開(kāi)始大力推進(jìn)本朝圣王制造工程。例如,相關(guān)學(xué)者的研究表明,《太祖高皇帝圣訓(xùn)》就與重修《太祖實(shí)錄》同時(shí)完成,關(guān)鍵目的在于重塑太祖努爾哈赤的圣王形象。“通過(guò)對(duì)圣訓(xùn)做文本細(xì)讀可知,其中部分言論有前代文獻(xiàn)為基礎(chǔ),但重述之際頗做修飾;亦有部分言論為康熙、乾隆時(shí)期增入。清朝統(tǒng)治的全面鞏固是此工程大規(guī)模啟動(dòng)的基本背景和條件,也因此一工程而大幅度升階,不僅強(qiáng)化了清朝皇統(tǒng)加入中原政統(tǒng)系列的合法性,也深化了清朝統(tǒng)治的道統(tǒng)合法性,構(gòu)造出君師合一的新政治文化語(yǔ)境。”①趙軼峰:《制造圣王——讀清〈太祖高皇帝圣訓(xùn)〉》,《故宮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10期。而這種新政治文化語(yǔ)境,也即儒家的王道政治。
和順治不同的是,嘉慶時(shí)清朝由盛轉(zhuǎn)衰。承平日久中,人口膨脹、物價(jià)上漲,游手好閑之徒大量滋生,又逢天災(zāi)人禍,百姓生計(jì)艱難;官員疲怠庸碌無(wú)為,又層削深重,吏治腐敗;軍備廢弛,紀(jì)律松散;財(cái)政空虛又經(jīng)濟(jì)疲軟。尤其是社會(huì)風(fēng)氣敗壞,士大夫階層的文化引導(dǎo)失靈,官民大多精神空虛。在此背景下雖然颙琰勤于圖治、力求改變?nèi)找嫠ヂ涞默F(xiàn)狀,但無(wú)論是“咸與維新”還是“法祖守成”,這兩種看似極端的治國(guó)路徑卻都顯得除弊乏術(shù),反使盛世的落霞余暉也漸消散。13歲即被定為太子的颙琰接受了20多年的儒家帝王教育確實(shí)培養(yǎng)了他溫柔敦厚、沉穩(wěn)謙謹(jǐn)?shù)男愿瘢瑫r(shí)也使其優(yōu)柔寡斷,遇事溫暾延宕。帝師朱珪教的“養(yǎng)心、敬身、勤業(yè)、虛己、致誠(chéng)”一直被他作為座右銘,即位之初他就恪守祖訓(xùn)“惟以敬天、法祖、勤政、愛(ài)民為保邦制治之大經(jīng)”②《清實(shí)錄·仁宗實(shí)錄》冊(cè)32,卷374,嘉慶二十五年庚辰七月庚午,北京:中華書(shū)局,2008年,第34397頁(yè)。,以弘揚(yáng)儒家忠孝之道。后來(lái)更是認(rèn)為法祖方能守成,維持盛世。這種保守的方式正是來(lái)源于儒家仁孝禮制,也極合颙琰溫柔敦厚、沉穩(wěn)謙謹(jǐn)之性格。學(xué)者陳連營(yíng)認(rèn)為,颙琰從小受儒家思想影響,時(shí)刻遵守傳統(tǒng)規(guī)范,不敢打破常規(guī),缺乏開(kāi)拓性思維,因此有礙制定新政策,使很多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得不到解決,也加劇了清中期的危機(jī)。③陳連營(yíng):《試論嘉慶帝守成思想的形成原因》,《河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1999年第2期。
具體來(lái)看,在上文的《遇變罪己詔》中,當(dāng)時(shí)嘉慶帝、臣民的反應(yīng),社會(huì)思潮變化,乃至嘉慶朝的政務(wù)及其思想都可見(jiàn)出。詔書(shū)里句句是自省自責(zé),處處透露出無(wú)奈委屈。他不僅以固有的儒家思想與道德反省自身,也將邪教大行民間、世道沉淪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歸于上層官員不能盡責(zé)教化民眾:“為人上者,不能彰明教化、宣揚(yáng)禮義;司牧之官,唯知尸祿保位,視民如草芥,德不修、學(xué)不講,乃有奸徒煽惑,假邪說(shuō)以誣民。”④《清實(shí)錄·仁宗實(shí)錄》冊(cè)31,卷284,嘉慶十九年甲戌二月甲午,北京:中華書(shū)局,2008年,第33187頁(yè)。在他看來(lái),儒家的禮義教化、講學(xué)修德才是社會(huì)歸化的治本之法,若想徹底取締邪教,只能從思想意識(shí)上用力。要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教化民間,以《圣諭廣訓(xùn)》教導(dǎo)民心,才能最終“使民知正教之益邪教之害,漸歸于倫常禮義”⑤《清實(shí)錄·仁宗實(shí)錄》冊(cè)31,卷275,嘉慶十八年癸酉九月庚寅,北京:中華書(shū)局,2008年,第33059頁(yè)。,并監(jiān)督地方落實(shí)情況。若以《遇變罪己詔》為出發(fā)點(diǎn)勾連文獻(xiàn)而展開(kāi),我們還會(huì)發(fā)現(xiàn),颙琰在儒家思想的強(qiáng)勢(shì)影響下相對(duì)忽略了當(dāng)時(shí)特殊的人文環(huán)境。他在私欲橫流、道德意識(shí)虛靡的情況下依舊廣施“仁慈”,卻實(shí)際上加劇了私欲的不斷放縱。比如扳倒和珅時(shí)因怕“一一根究,連及多人”,認(rèn)為“若能遷善改過(guò),皆可為國(guó)家出力之人”。⑥《清實(shí)錄·仁宗實(shí)錄》冊(cè)28,卷38,嘉慶四年己未正月戊寅,北京:中華書(shū)局,2008年,第29533頁(yè)。所以他主張不嚴(yán)懲其他涉案官員,對(duì)已到案官員甚至也從輕處罰。這使其錯(cuò)過(guò)了有效整頓吏治的良機(jī),從一開(kāi)始的縱容就預(yù)示了日后惡果。颙琰的悲劇也正在于在頹勢(shì)難挽的大勢(shì)中還要以儒家更僵化瑣屑的努力做無(wú)奈的垂死掙扎。其實(shí),不管從個(gè)人還是國(guó)家角度而言,颙琰都算是個(gè)合格的皇帝,他克己勤政、寬仁勤儉,氣質(zhì)上也溫文爾雅,但在位不逢時(shí),王朝中衰的各種復(fù)雜狀況使他畏首畏尾、疲于應(yīng)對(duì),只能囿于最保守的治道。當(dāng)他最后回顧自己一生的執(zhí)政時(shí),寫(xiě)道:“升平日長(zhǎng)久,風(fēng)俗漸浮蕩。官吏多怠疲,聽(tīng)訟事曲枉。以致下刀頑,犯上肆擾攘。實(shí)由予不明,舉措失刑賞。”①故宮博物院編:《清仁宗御制詩(shī)》(影印版),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292頁(yè)。這其實(shí)也是罪己之言,不僅承認(rèn)了朝代的衰象,更流露出一代帝王的自責(zé)與無(wú)奈。由是觀(guān)之,通過(guò)《遇變罪己詔》不僅可以加深對(duì)嘉慶帝的研究,更可由此深入探究清中期政治社會(huì)的癥結(jié)問(wèn)題,以及把握儒家文化在整體衰落社會(huì)中的影響問(wèn)題甚至于王朝中衰的本質(zhì)特征、傳統(tǒng)社會(huì)最后走向崩潰的根本原因。
在諸多罪己詔里,隨處可見(jiàn)儒家向來(lái)倡導(dǎo)的“仁”與“禮”。清朝也正是延續(xù)了中國(guó)傳統(tǒng)幾千年來(lái)一直實(shí)行的以“禮樂(lè)”為核心的制度體系。同時(shí),縱觀(guān)有清以來(lái)儒學(xué)的各種思潮,以程朱為代表的理學(xué)、宋學(xué)在與心學(xué)、漢學(xué)的較量中一直得到官方的默認(rèn)、支持,尤其是以熊賜履、李光地等為代表的名儒頗受皇帝青睞,可以說(shuō)程朱理學(xué)一脈長(zhǎng)期都是清廷官方主流理論和意識(shí)形態(tài)。在其學(xué)說(shuō)里,“仁”是道德上的約束,是社會(huì)主要價(jià)值觀(guān);而“禮”在宏觀(guān)上既包括政治組織形態(tài),也包含文化價(jià)值形態(tài),在微觀(guān)上則是在制度和具體規(guī)范上做出的一系列行為準(zhǔn)則。但統(tǒng)治階層倡導(dǎo)的仁禮及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觀(guān)點(diǎn)理念等也都屬于上層社會(huì),是統(tǒng)治階層希望達(dá)到的一種理想境界,而對(duì)處于社會(huì)底層的民眾來(lái)說(shuō)效果并不顯著。但國(guó)家、社會(huì)、家庭三者又以“禮”為方式聯(lián)系在一起實(shí)行宗族家長(zhǎng)制,以家庭為結(jié)構(gòu)的社會(huì)則時(shí)刻受到牽絆。它所強(qiáng)調(diào)的是穩(wěn)定,因而任何形式的創(chuàng)新、個(gè)性化都將視為社會(huì)的危害。所以罪己詔也從側(cè)面反映出了清代整個(gè)社會(huì)的日益僵化。
在此基礎(chǔ)上,罪己實(shí)際是基于兩個(gè)基本觀(guān)念:一是對(duì)“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信條的認(rèn)同,君主意識(shí)強(qiáng)烈,認(rèn)為自己是天下共主,有責(zé)任使天下太平,以至于“一夫不獲,罪在朕躬”;二是相信“變不虛生”“天人感應(yīng)”的理論,強(qiáng)調(diào)天災(zāi)人禍皆由人事。這樣,在樹(shù)立起君主權(quán)威的同時(shí)也對(duì)君主應(yīng)擔(dān)負(fù)的責(zé)任做出了要求,罪己則可視為儒家政治思想的附屬物。帝王在必要時(shí)發(fā)布罪己詔,以安撫民眾、緩和矛盾、凝聚人心。其本質(zhì)是以百姓的認(rèn)同心理來(lái)增進(jìn)權(quán)力的正當(dāng)性和有效性,這樣權(quán)力才能借民意轉(zhuǎn)化為天意而更好地發(fā)揮作用。以民為本是上述兩個(gè)基本觀(guān)念的進(jìn)一步要求,雖然歷史上孟子提出的這種民本思想遠(yuǎn)在董仲舒“天人感應(yīng)”論之前,但這后出之論卻極大豐富了前者的內(nèi)涵,并夯實(shí)了前者實(shí)施的必然性。強(qiáng)調(diào)民本的言論還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人無(wú)水鑒,當(dāng)以民鑒”,“天視自我民視,天聽(tīng)自我民聽(tīng)”等,統(tǒng)治者將民眾作為國(guó)本,將民心作為鏡子以觀(guān)政治活動(dòng)之得失。當(dāng)國(guó)政有所失之時(shí),帝王則發(fā)詔罪己使“民心悅,天意回”,否則便如《荀子》中說(shuō)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雖然罪己詔也有著政治作秀的成分及一定的欺騙性,但也不能將其與其他政治騙術(shù)等而視之。因?yàn)樗拇_濃縮著帝王對(duì)自身或王朝問(wèn)題的反省,更不乏真切的懺悔,彰顯出一種對(duì)“圣王德政”渴望。
四、罪己詔中的儒家思想效應(yīng)辨析與價(jià)值評(píng)議
前文也說(shuō)過(guò),罪己詔雖是官方性的,然剔除帝王們無(wú)奈之舉和作秀成分,還是有很多真實(shí)的因素,帝王下詔時(shí)的心情大都也確為自責(zé)、悔恨的。無(wú)論是否為大臣代筆,但畢竟是在全民面前自省,還會(huì)留載史冊(cè),因而自然會(huì)對(duì)帝王起到一定的鞭策、砥礪作用。罪己詔具有的帝王自省功能依然值得今人思考。它啟示今人應(yīng)給自己劃定權(quán)力的邊界和行為的禁區(qū),時(shí)刻警惕各種“無(wú)所畏懼”的自負(fù)和虛妄,常懷謹(jǐn)慎敬畏之心。由此,后人對(duì)罪己詔行為也有很多表示贊賞、推崇的,這些也正是儒家思想效應(yīng)的體現(xiàn)。例如,錢(qián)穆先生在他的《黃帝》和《國(guó)史新論》中提到罪己詔時(shí)認(rèn)為,中國(guó)古代帝王發(fā)布罪己詔的做法是與君權(quán)對(duì)舉的①錢(qián)穆:《錢(qián)賓四先生全集·國(guó)史新論》,臺(tái)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社,1998年,第108頁(yè)。;馬克斯·韋伯在其《儒教和道教》中把中國(guó)帝王的罪己詔跟西方的charisma(魅力)理論相比較后認(rèn)為,如果一個(gè)皇帝不能對(duì)自己的政過(guò)進(jìn)行反省的話(huà),他的charisma就會(huì)流失掉②[德]馬克斯·韋伯:《儒教和道教》,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95年,第77頁(yè)。。錢(qián)穆、韋伯二人的觀(guān)點(diǎn)其實(shí)已經(jīng)很好地詮釋出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微言大義。而早在漢朝時(shí),王符在其《潛夫論·明暗》中就說(shuō)過(guò)“君之所以明者,兼聽(tīng)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③王符著,汪繼培箋:《潛夫論箋校正》卷2,北京:中華書(shū)局,2014年,第70頁(yè)。罪己詔正是這樣一種“兼聽(tīng)則明,偏聽(tīng)則暗”的具體操作。
其實(shí),現(xiàn)在討論罪己詔行為的時(shí)候,往往是將其置于治世問(wèn)題的語(yǔ)境中,并將儒家思想效應(yīng)局限于社會(huì)效應(yīng)、政治事功之下,而相對(duì)忽視了罪己所關(guān)涉的個(gè)體自我話(huà)語(yǔ)。這就又涉及儒家思想效應(yīng)與自我心性之學(xué)的關(guān)系問(wèn)題。《論語(yǔ)·憲問(wèn)》中曾有言“古之學(xué)者為己,今之學(xué)者為人。”杜維明先生曾談到,在孔子那里,父母、社會(huì)、國(guó)家并不是唯一的尺度,他其實(shí)很早就強(qiáng)調(diào)了為己之學(xué),個(gè)人作為重要維度已被納入考量之中。《大學(xué)》中有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講的就是個(gè)人的身心整合問(wèn)題。所謂個(gè)人的身心整合,便是致力于不斷磨合齟齬,使人的內(nèi)部心靈世界和外部物質(zhì)世界彌合統(tǒng)一。在這個(gè)磨合的過(guò)程中,人能夠覺(jué)悟到自己是在學(xué)。因此,“為己之學(xué)”可被視為儒家的身心性命之學(xué),或者說(shuō)是其修身哲學(xué)。身體不僅僅是單純地被人所占有,還被個(gè)體意義上的人用于自我表達(dá)。而人在此過(guò)程中不斷地學(xué)、不停地完善自己,表明人作為個(gè)體可以從身體——主要是心靈意識(shí)到自我是變動(dòng)不居的,自身發(fā)展是一個(gè)隨時(shí)變化、永不停滯的動(dòng)態(tài)過(guò)程,而非一個(gè)內(nèi)部閉合的靜態(tài)結(jié)構(gòu)。罪己行為就恰恰反映出這樣的一個(gè)動(dòng)態(tài)過(guò)程與深層心理。另外深入來(lái)看,儒家的“為己之學(xué)”除了倡導(dǎo)主體上內(nèi)省修己以外,還注意到了對(duì)客體的協(xié)調(diào)。它承認(rèn)人是在諸多外力的限定下才成為某個(gè)具體的人,而所有限定人的外力都可能激發(fā)個(gè)人力量的釋放。況且,個(gè)體的自我亦不是絕緣孤立的。《中庸》里所講的道就不同于希臘哲學(xué)里于最平衡之兩端取其中,而是在動(dòng)態(tài)的過(guò)程中不斷地調(diào)適、把握平衡。這也正是考慮到了個(gè)人心靈與所面臨事情間的交互影響產(chǎn)生的各種不同力量,各種不同力量又使得個(gè)人常出現(xiàn)諸多不同的偏差。個(gè)人則需要在這個(gè)自我調(diào)適的過(guò)程中,使自己本心、良知所代表的常態(tài)得以駕馭并超越復(fù)雜多變的現(xiàn)狀。而罪己恰恰就是對(duì)各種限定力量的一種反觀(guān)反思,促使帝王喚醒自己的本心、良知所代表的常態(tài),實(shí)現(xiàn)自我和王朝一定程度上的調(diào)適。既已肯定了主體、客體各方效應(yīng)的作用,那么儒家就在事實(shí)上確立了這樣一種認(rèn)知:處于結(jié)點(diǎn)位置個(gè)人的意義,一定是在人際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中得以樹(shù)立并實(shí)現(xiàn)的。眾所周知儒家倡導(dǎo)了解他人、尊重他人,其實(shí)這也是著眼于對(duì)更深層次、更廣闊意義上自我尊重的獲得。也如《論語(yǔ)·學(xué)而》中所言,“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誠(chéng)然,儒家摒棄了狹隘的個(gè)人主義和極端的集體主義,在動(dòng)態(tài)平衡中尋求到了一種立己達(dá)人的人格主義,而罪己行為正恰如其分地體現(xiàn)了這點(diǎn),是君主個(gè)人和普天臣民間的一種交互、會(huì)通。以此在儒家理論里延伸考察就會(huì)發(fā)現(xiàn),實(shí)現(xiàn)這一會(huì)通、和諧的動(dòng)力資源就是孟王心學(xué)強(qiáng)調(diào)的惻隱之情。同情的力量人人皆有,否則個(gè)人就會(huì)如同行尸走肉般麻木不仁,更談不上獲取真正的自我發(fā)展。君王自然也不例外,甚至于此而言要求應(yīng)更高。惻隱之情于個(gè)人是“仁心”,于社會(huì)政治就是“仁政”,可以說(shuō)其在中華民族兩千多年來(lái)文化心靈的建構(gòu)中貢獻(xiàn)巨大。尤其是“仁心”,也即前文所述的本心、良知所代表的常態(tài),具有人類(lèi)個(gè)體共同的通感價(jià)值。簡(jiǎn)言之便是仁者為人。按儒家思想體系所指引,君王對(duì)“仁心”“仁政”應(yīng)有著雙重的強(qiáng)烈訴求,并且擁有“仁心”是實(shí)施“仁政”的前提與基礎(chǔ)。
綜上可知,“為己之學(xué)”的傳統(tǒng)在中國(guó)歷史悠久,先秦、宋明儒學(xué)皆多有論及。首先這是“身心之學(xué)”,探討身體和心靈關(guān)系以及個(gè)人的修身;其次它也是“性命之學(xué)”,在個(gè)人修養(yǎng)基礎(chǔ)上疏導(dǎo)人性和命運(yùn)的發(fā)展;再次這還是“君子之學(xué)”,提升自身道德境界方可立己達(dá)人、臻于和諧;最后,它甚至亦可被稱(chēng)為“圣人之學(xué)”,其正是通向內(nèi)圣外王最高追求的必由之路,而內(nèi)圣外王又是儒家君王觀(guān)的理想范式。儒家思想“為己”的一面一般不為人所熟知,因?yàn)榇蟊娫诮邮苋寮宜枷霑r(shí)太偏重人際關(guān)系的層面,過(guò)于關(guān)注儒家的政治作用、社會(huì)效應(yīng),并未意識(shí)到儒家心靈哲學(xué)中自有其向內(nèi)追問(wèn)自我的強(qiáng)烈意識(shí)。正如《周易》中的“君子以恐懼修省”,曾子所說(shuō)的“吾日三省吾身”,以及朱熹說(shuō)的“人孰無(wú)過(guò),過(guò)而能改,善莫大焉”一般,自省首先是個(gè)人意義上的,得從個(gè)人修養(yǎng)做起,這是罪己的最基本要求。以此為起點(diǎn)才能一步步實(shí)現(xiàn)“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xué),為萬(wàn)世開(kāi)太平”的宏大至高的境界目標(biāo)。通過(guò)自省才能覺(jué)悟到我是靠我來(lái)塑造的,罪己詔行為正深刻顯示出了儒家“為己之學(xué)、身心性命之學(xué)”的一面,這恰恰也是儒家傳統(tǒng)資源和思想效應(yīng)中在杜維明先生看來(lái)最有精神價(jià)值、最能夠普及的思想。①杜維明:《為什么要“學(xué)做人”——關(guān)于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xué)大會(huì)主題的思考》,《重慶與世界》2018年第16期。甚至現(xiàn)在也有很多學(xué)者相信儒學(xué)的本位并非治世之學(xué),而是心性之學(xué)。仁愛(ài)布施的過(guò)程確實(shí)是由近及遠(yuǎn)的,由自己為起點(diǎn),進(jìn)而才可推己及人,也才能最終做到“上下與天地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