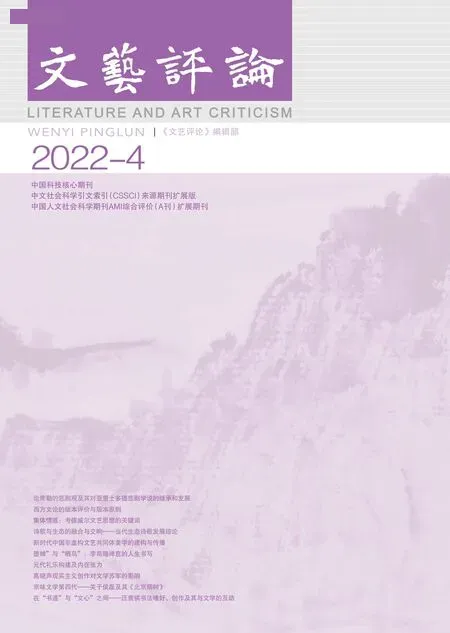詩歌與生態的融合與交響
——當代生態詩歌發展綜論
○汪樹東
中國作家中,詩人對大自然尤為敏感,尤為熱愛。大部分當代詩人都親近自然,熱愛自然,具有或自覺或不自覺的生態意識。他們對身邊的生態問題頗為關注,當江河湖海被污染時,他們會奮力疾呼;當森林被伐童山濯濯時,他們會拍案而起;當百獸凋零飛鳥遁跡時,他們會長歌當哭;當霧霾彌漫藍天淪陷時,他們會冷嘲熱諷。當然,他們也頗能夠感知大自然的神秘節律,能夠超越現代人自然冷漠癥,濃墨重彩地描繪自然之美,為早已被祛魅的大自然再次復魅。因此本文所論的生態詩歌,是指詩人能夠自覺感受到現代生態危機,超越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建立起親近自然、敬畏生命的生態整體觀,致力于書寫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倡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詩歌。1978年以來,大部分詩人都曾創作過若干首生態詩歌,甚至出現了于堅、吉狄馬加、雷平陽、李少君等這樣長期持續創作生態詩歌的著名詩人,而華海、侯良學、沈河、哨兵、徐俊國等詩人更是專注于生態詩歌的創作,《悼念一棵楓樹》《避雨之樹》《哀滇池》《拒絕末日》《我,雪豹……》《尋找一棵大樹》《水立方》等生態詩歌堪稱當代詩歌的經典篇章。整體上看,題材多樣、藝術風格繁復的生態詩歌已經成為中國當代生態文學發展史中的重頭戲之一,賦予了當代新詩全新的生態風景。同時,生態詩歌也為中國新詩重塑了生態維度、地方維度,重新接通了古典山水田園詩歌的歷史文脈,對生態文明的建設也頗有助益。
一
整體通觀1978年以來近四十年的生態詩歌發展史,我們大致可以把它分為三個各有特點又前后相續的歷史階段,即1978-1989年的發生階段、20世紀90年代的發展階段、20世紀頭20年較為繁榮的階段。
20世紀80年代我國面臨的生態危機主要是歷史上的大破壞和當時日益加速發展的經濟造成的。歷史上的大破壞,主要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到改革開放前在極左思潮下全國各地罔顧生態規律大肆砍伐原始森林、開墾草原和濕地、圍海圍湖造田、獵殺野生動物以及無節制的礦產開發和道路建設等造成的生態破壞,例如大煉鋼鐵就對全國森林造成毀滅性的破壞。而改革開放以后,面對一窮二白的經濟狀況,大力發展經濟成為我國的當務之急,為了發展經濟,各地往往不顧生態規律,也不顧及環境保護,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環境的快速惡化相伴而生,生態危機比比皆是。在此階段,徐剛、沙青、岳非丘等人的生態報告文學率先崛起,極力揭露生態危機的現狀,但是當代生態詩歌尚處于萌芽發生階段,創作了較重要的生態詩歌的詩人有牛漢、昌耀、海子、于堅等,較有代表性的生態詩歌有牛漢的《華南虎》《悼念一棵楓樹》、昌耀的《鹿的角枝》、于堅的《南高原》《避雨的樹》、海子《活在珍貴的人間》《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等。
改革開放初期,當代詩壇上活躍著的是一大批當初被打成“右派”而后歸來的詩人,重要的有艾青、牛漢、曾卓、綠原、公劉、邵燕祥、流沙河等人,這些詩人多關注較為宏大的社會歷史,具有較為強烈的歷史反思精神,同時也葆有難能可貴的理想主義精神,但是他們普遍缺乏詩意歌詠大自然的持久興趣,生態意識也處于朦朧之中。當然也有例外,例如牛漢、昌耀就寫出了頗有生態意識的詩歌。牛漢在1970年曾被下放到湖北咸寧“五·七”干校,從事極為艱苦的農業勞動,身心均受到較大的摧殘,但是他同時也看到了大自然生命的創傷,每每感同身受,從而滋生出強烈同情自然生命的生態悲憫意識。例如他的《華南虎》一詩寫桂林動物園被囚的華南虎,寫它的絕望和反抗,寫對自然生命的同情,感人至深,也促使每個人反思自己對待其他自然生命的殘暴態度。他的詩歌《悼念一棵楓樹》在那個時代里也是絕無僅有的生態文學的華美篇章,詩句中彌漫著詩人對另一種自然生命的深切理解、賞識和熱愛,以及為它的遭遇而滋生的悲愴。他的詩歌《麂子》則寫出詩人為麂子這樣的自然生命擔憂的生態情感。至于他的《鷹的誕生》《半棵樹》《巨大的根塊》《毛竹的根》《奇跡——廬山好漢坡所見》《車前草》等詩歌均能夠呈現自然生命的內在性和自在性,贊美它們的頑強生命,彌漫著慷慨激蕩的生態強音。到了20世紀80年代,牛漢還關注到了華南虎滅絕等生態問題,例如他的詩歌《虎嘯的回聲》就寫到廣東一個自然保護區由于濫伐森林導致華南虎遠走他山的生態悲劇。
昌耀也曾于20世紀50-70年代被流放于青海邊緣藏區,與那些藏族牧民為伍,朝夕與大自然相對,慢慢地滋生出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的生態意識。例如他在詩歌《莽原》中寫道:“遠處,蜃氣飄搖的地表,/崛起了渴望嘯吟的筍尖,/——是羚羊沉默的彎角。//在最后的莽原,/這群被文明追逐的種屬,/終不改他們達觀的天性:/或如松鼠痛飲于光明之枝。/或如河魚嬉游于波狀之物。/捕捉那迷人的幻夢,/他們結成箭形的航隊/在勁草之上縱橫奔突,/溫柔得如流火、金梭……/莽原,寵愛自己的嬌兒。//正是為了大自然的回歸,/我才要多情地眷顧/這塊被偏見冷落了的荒土?”[1]昌耀擺脫了當代的主流意識形態的看法,并不把那些游牧的藏族人視為落后、不文明,相反,他發現藏族人在游牧中與大自然和諧相處,是真正令人眷戀的種族。昌耀正是深受藏族人眾生平等、敬畏生命的傳統生態文化的影響,他才重新發現了青藏高原上自然生命的神圣性,因此他產生了一種惜生護生的生態意識,例如他在詩歌《寓言》中曾為自己誤殺一只蜜蜂而慚愧。他也非常崇敬自然生命,例如詩歌《一百頭雄牛》就贊美青藏高原上的牦牛,崇敬它們那種遺世獨立的悲壯精神。
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朦朧詩詩人中很少具有生態意識。對于北島、顧城、舒婷、楊煉等詩人而言,真正重要的是現實社會,是人、人性、人道、人的命運,是對社會正義的訴求,對理想愛情的追尋。即使對于崇尚童心的顧城而言,大自然也沒有成為興趣的中心,更不要說生態意識的啟蒙了。但到了第三代詩人那里,開始出現了兩位有代表性的具有生態意識的詩人,即于堅和海子。于堅漫游于云南大地,深受云南少數民族萬物有靈、敬畏自然的生態智慧的滋潤,在大自然中脫胎換骨,靈性重生,因此他的許多詩歌都是歌詠云南山川大地之壯美的,著名的有《南高原》《避雨之樹》等。尤其是《避雨之樹》謳歌了那株像大自然母親一樣的亞熱帶榕樹,堪稱當時生態詩歌的最美篇章。而他的《那人站在河岸》等詩歌則較早表現了河流污染問題,也是當時生態批判的詩歌力作。至于海子創作出了生態詩歌,則與他的鄉村生活經驗和梭羅的影響有關。他出生于安徽懷寧鄉村,從小與大自然生活在一起,從內心里親近自然、熱愛自然,他對現代城市文明、工業文明懷有一種本能的抵觸傾向。此外他非常喜歡荷爾德林、梭羅、葉賽寧等作家,也受到他們的生態思想的影響。他在詩歌《活在珍貴的人間》中曾寫道:“活在這珍貴的人間/太陽強烈/水波溫柔/一層層白云覆蓋著/我/踩在青草上/感到自己是徹底干凈的黑土塊//活在這珍貴的人間/泥土高濺/撲打面頰/活在這珍貴的人間/人類和植物一樣幸福/愛情和雨水一樣幸福”[2]。海子喜歡的人間,不是喧囂的城市,而是鄉村,是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人間;幸福也是來自與大自然融合為一。至于他的詩歌《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更是歌詠一種與大自然相融為一的詩意棲居的生態理想。
當然除了上述這些較為重要的詩人詩作之外,20世紀80年代還有不少詩人自覺或不自覺地創作過一些生態詩歌,例如艾青的詩歌《盆景》反對現代人強制扭曲植物的形狀以滿足人的畸形審美趣味,葉文福的詩歌《天鵝之死》批判俗人獵殺天鵝的罪行,白樺的《雪山杜鵑——過白馬雪山所見》謳歌云南白馬雪山上的凌寒而開的高山杜鵑花等等,不一而足。此外,詩人渭水的幾首生態詩歌也值得關注。渭水曾寫過不少社會抒情詩,主要有《1986:阿茲特克世界大戰場》《1988:奧運會啟示錄》等,在20世紀80年代產生過一定的社會影響。他對重大社會問題反應及時,抒情姿態激烈,當他關注生態問題時,他就寫出了生態批判意味濃郁的生態詩歌。例如他的詩歌《大難之后:中國的沉思——大興安嶺火災一周年祭》寫了1987年大興安嶺森林火災,嚴厲批判了導致火災蔓延、釀成人禍的官僚主義體制,提醒森林的消失會造成的人類災難。他的長詩《挑戰》則寫人類生存面臨的各方面挑戰,尤其是生態危機的挑戰,呼喚現代人的生態意識的覺醒,重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美好狀態。但是需要說明的是,渭水處理這些生態題材時,雖然表達了強烈的生態憂患意識,不過概念化痕跡過于明顯,個人的生命體驗尚未有效地注入其中,因此藝術魅力大打折扣。
我們必須承認,20世紀80年代沒有出現更為專注、藝術成就更好的生態詩人,也沒有出現較為集中的生態詩集,生態詩歌的概念還沒有被提出,生態意識也只是混雜在詩人對大自然的親近、對環境污染的敏感中。徐剛憑借《伐木者,醒來》這樣的生態報告文學震撼了國人麻木的神經,呼喚國人重視保護森林,甚至影響了我國的林業政策;高行健憑借《野人》這樣的生態戲劇在當代實驗戲劇中引起極大的轟動,“救救森林”的吶喊響徹劇壇;孔捷生的《大林莽》、阿城的《樹王》、張煒的《三想》等生態小說則深入歷史、反思現代化,樹立了極為自覺的生態意識,并產生了極大的社會影響。但是相對而言,此階段的生態詩歌還沒有出現真正的經典之作,社會影響力也頗為有限。
二
到了20世紀90年代,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一步加速,環境污染、生態危機更為突出;空氣污染加劇,酸雨、霧霾、沙塵暴對于許多地方而言都成了見慣不驚的常態;江河湖海污染加劇,河流消失、湖泊萎縮、濕地銳減,沿海地區赤潮頻見,水生態全面惡化;森林進一步減少,野生動物銳減,草原沙化日漸加重;垃圾泛濫,垃圾圍城日益嚴重,隨著農藥、除草劑和化肥的大量使用,農村地區的環境污染也日益明顯……當然,與此同時,隨著全球環境保護運動的風起云涌,尤其是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的巨大影響,中國作家的生態意識進一步覺醒,對生態的書寫更為自覺,當代生態詩歌的發展明顯進入了更為自覺的發展階段。更多的詩人加入生態詩歌創作隊伍,建立了更為自覺的生態意識。除了于堅之外,李瑛、韓作榮、李松濤、沈葦、吉狄馬加、倮伍拉且等詩人都創作了富有個人特色的生態詩歌。更具有社會影響力的生態詩歌作品開始頻繁出現,例如于堅的《哀滇池》、李松濤的《拒絕末日》、韓作榮的《尋找一棵大樹》等。而且生態詩歌的題材也出現了較大的拓展,舉凡江河湖海污染、森林被伐、野生動物遭獵、洪水泛濫、江河斷流等生態問題,都有詩人及時準確地書寫。詩歌刊物、文學刊物也在推動生態詩歌的創作,例如《詩刊》就曾多次舉辦“大地之歌”“土地與未來”“綠色地球杯”等詩歌征集活動,《綠葉》《生態文化》《中國綠色時報》《中國環境報》等報刊也頻繁地刊登生態詩歌。首先值得關注的是于堅、李松濤、渭水的生態詩歌創作。于堅到了20世紀90年代相繼推出幾首重磅的生態詩歌,如《哀滇池》《棕櫚之死》等。長詩《哀滇池》控訴了云南昆明滇池的水污染,寫出了詩人故鄉淪陷的悲哀和恐懼,個人經驗和時代經驗匯合,生活細節和歷史現象交織,深刻的生態哲思和豐沛的藝術想象相融,巍然屹立于當代生態詩歌史上,構成標志性的存在。而李松濤的長詩《拒絕末日》曾獲得首屆魯迅文學獎,以其對華夏大地上的土地沙化退化、水污染、森林遭毀、野生動物瀕危、人口爆炸等生態問題的全面揭露而震驚世人。雖然該長詩存在著較為鮮明的概念化傾向,但是它的生態憂患意識彌足珍貴。渭水則依然堅持著20世紀80年代政治抒情詩式的進路,不過把關注點再次投向了生態問題,因此創作了長詩《水的哭泣——獻給世界“地球日”二十周年暨新世紀的開拓者》(《詩刊》1992年8月號),指出現代人需要注意水對于文明和生命的重要性,并為現代文明卻造成可怕的水危機而感到震驚。詩人具有非常恢弘的眼光,把往古今來、宇宙八方都納入視野之內,最終呼吁“為了整個地球整個人類更加干凈/我們該重新/擦亮這同樣泛著粼粼水波的眼睛/重新/走向文明”。不過,該詩依然存在概念化嚴重的弊病,缺乏獨特的意象,缺乏動人的想象,缺乏春風化雨的細膩詩意。
其次,值得關注的是出現了非常典型的專注于生態詩歌創作的詩人江天和他的生態詩集《楚人憂天》。江天的詩集《楚人憂天》于2001年獲得第九屆中國人口文化獎詩歌類一等獎,被視為“有利于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江天具有較為敏銳的生態意識,對現實社會中的各種生態環境問題都極為關注,例如他的詩歌《杜鵑之啼血》寫森林被伐、鳥兒喪失棲息地的生態悲劇,《云雀的請愿》寫農民過多使用農藥導致云雀也無法生存的環境問題,《海狗》寫人類因為要吃海狗鞭而虐殺海狗,《鯨魚》寫鯨魚集體自殺,《都市垃圾》寫城市垃圾泛濫,《造紙廠》寫造紙廠排放污水,等等。應該說,江天的生態詩歌的生態視野較為開闊,對20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的各類生態環境問題都有所涉及,而且具有一種較為宏大的全球性視野,在中國當代生態文學發展史較早聚焦于生態詩歌,試圖以詩歌的力量來喚醒人們的生態意識,但是江天的生態詩歌也存在著較為鮮明的問題,關鍵在于這些詩歌過于拘泥于切實的生態環境問題,缺乏必要的詩意提煉和想象力的飛揚,也缺乏具體生動的生活經驗的充實與支撐,對生態意識的理解流于常識,無法達成對生態問題的殊異化、個體化的理解,從而出現鮮明的藝術局限。
再次,韓作榮此階段創作的生態詩歌的生態視野較為開闊,藝術魅力獨具,值得關注。韓作榮是當代著名詩人,他的詩集《韓作榮自選詩》曾獲得首屆魯迅文學獎。他具有較為自覺的生態意識,許多詩歌堪稱典型的生態詩歌,《野生動物園》和《尋找一棵大樹》都是當代生態詩歌史中的重要篇章。他的《殺魚》反思日常生活中對待雞、魚這樣家養動物的殺食暴力問題,《一條水溝的改造》寫城市里的環境治理問題,《裘皮店》反思對野生毛皮動物的獵殺問題,《麻雀》寫一只偶然闖入詩人家里的麻雀的極度恐慌,進而反思人與自然之間的遙遠距離。除了短詩之外,韓作榮的《野生動物園》《尋找一株大樹》是特別值得關注的兩首生態長詩。前者反思了現代人對待野生動物的野蠻態度。后者則反思了華夏大地上森林消失、大樹消失的生態困境,詩人寫道:“是誰,是哪一雙罪惡的手/用文明的鋼牙噬殺了一株偉大的生命/當巨樹轟然倒下/樹的痙攣與震顫,會使一座大山崩潰/與根的分離,使巨樹成為尸體/它白色的血漿還沒有流盡/一群食蟲鳥便霧一樣飛來尋找食物/山林里失去一株大樹/枝椏間的云彩已化為雨滴/將林地涂抹成酣暢淋漓的水墨/可樹的影子已深深地沉入泥土/讓土地更為沉重/林地間留下了無法彌補的空白/和我的心靈一起,因缺失而虛妄/在森林,一株過于高大的樹是孤獨的/群樹因失去大樹會更加孤獨/甚至風再也不能在最高處喧嘩/只能在樹叢中嗚咽”。[3]詩人親近大樹,崇拜大樹,從大樹那里獲得一種心靈的撫慰,因此當大樹死去,他才長歌當哭。韓作榮的《尋找一棵大樹》和牛漢的《悼念一棵楓樹》在當代生態詩歌史中遙相呼應,高標出塵,獨領風騷。
此外,詩人沈葦也創作了不少生態詩歌。他大學畢業后到新疆烏魯木齊工作,在新疆大地上四處漫游時也產生了較為自覺的生態意識。他的詩歌《開都河畔與一只螞蟻共度一個下午》寫新疆開都河畔的一只螞蟻,洋溢著眾生平等的生態思想,“我俯下身,與螞蟻交談/并且傾聽它對世界的看法/這是開都河畔我與螞蟻共度的一個下午/太陽向每一個生靈公正地分配陽光”[4]。的確,人總是從人類中心主義出發,自以為是萬物之靈長,傲視其他所有自然生命;但是從太陽角度來看,人與自然萬物都是平等的,太陽向每一個生靈公正地分配陽光,這種太陽般的公正也就是生態正義。在詩歌《鱷魚》中,沈葦更是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審美立場和倫理立場,去發現鱷魚這樣的自然生命的美與善。沈葦的詩歌《鱷魚》和于堅的詩歌《對一只烏鴉的命名》一樣,超越了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桎梏,體現出對自然生命的生態中心主義立場,從而發現了自然生命的內在本性和豐沛詩意。
當然除了上述的詩人詩作之外,20世紀90年代還涌現了一大批生態詩歌佳作。例如著名詩人鄭敏的詩歌《誰征服誰?飛魚與云團的對話》寫出了詩人在萬里高空上對人與大自然之間的關系的生態思考。在詩人看來,面對天地日月這樣的生命之源,人類不能傲慢地想著征服,“沉默是人類最高的智慧,/靜聆自然的聲音/靜觀星辰們的旋轉/人終于找到自己的位置/不再問道:/誰征服誰?”[5]人類不能妄想征服大自然,而只能承認自我的渺小,謙卑而感恩地踏實生活。著名詩人李瑛也創作了不少生態詩歌,例如他的詩歌《羚羊》贊美藏羚羊的矯健與野性,詩歌《一只山鷹的死》贊美山鷹的莊嚴與英武,詩歌《生命》憐惜那些遠離大海、被晾曬在繩子上的死魚,詩歌《一只死去的藏羚羊》則為一只被獵殺的藏羚羊而悲傷,對人類污染西北高原表達了憤怒的批判。著名詩人雷抒雁的詩歌《斷流》則寫黃河斷流,感嘆世道淪喪、生態退化。四川詩人啞石的《青城詩章》也是這個階段生態詩歌的重要收獲。啞石在20世紀90年代曾短暫隱居四川青城山,師法王維,深入自然,感悟自然大道的運行規律,體悟天人合一的佳妙境界,發而為詩,便成了《青城詩章》中那些生氣彌漫、妙悟自然的生態詩篇。此外,還出現了若干位少數民族詩人開始進行較為自覺的生態詩歌寫作,例如彝族詩人吉狄馬加、倮伍拉且,他們多信奉本民族的萬物有靈論,致力于發現萬物的內在靈性。《吉狄馬加詩選》《詩歌圖騰》兩部詩集中的生態詩歌所在多有,極為生動地呈現涼山彝族人的生態智慧觀。
相對于20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生態詩歌的確獲得了長足的發展。生態詩人日見增多,生態詩作日漸繁盛。《哀滇池》《拒絕末日》等生態詩歌無論是在詩壇上還是在社會上影響力都很大。更重要的是,詩人們的生態意識更為成熟,越來越多的詩人能夠擺脫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偏見,以生態整體主義視角審視人與大自然的關系,例如于堅的《哀滇池》就明確地在生態整體主義立場上提出敬畏自然的生態主張。此階段詩人們的生態視野也更為開闊,生態憂患意識更為顯豁,例如江天、渭水、李松濤等詩人的生態詩歌創作就極大地拓展了當代詩歌的生態視野,讓所有生態問題都能夠得到及時的詩歌觀照。于堅、啞石等詩人主動地開始承接古典山水田園詩歌的生態智慧,吉狄馬加、倮伍拉且等少數民族詩人則主動去尋覓本民族的傳統生態智慧,從而使得當代生態詩歌出現了較為鮮明的本土化特色。
三
相對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生態問題成為新世紀頭20年代最為突出的社會問題之一。SARS病毒爆發、汶川大地震、南方冰雪災害、舟曲地震和泥石流災害、玉樹地震、幾乎覆蓋全國的霧霾、年年頻見的洪災和旱災再加上2019年以來的新冠疫情,來自大自然的各種災害橫掃人類社會。更兼網絡的普及,人們更容易獲得各種資訊,因此絕大部分人都開始覺察到了生態危機的全球性爆發。與此同時,我國政府也積極地宣傳生態文明建設,強有力地把生態文明確定為國家發展的基本方向之一。因此,生態詩歌也像其他生態文學體裁一樣進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繁榮階段。
首先,值得關注的是,華海非常專注于生態詩歌的創作,并帶領許多志同道合的廣東清遠詩人組成了清遠生態詩歌群落。華海已經出版了《華海生態詩抄》《靜福山》《華海微詩集》《藍之島》等生態詩集和生態散文詩集《紅胸鳥》,還編輯了兩部生態詩評論集《當代生態詩歌》《生態詩境》,還主編有《庚子生態詩歌選本》等生態詩集。他的“靜福山”系列組詩在當代生態詩歌中占有較重要的位置。更重要的是,他借助“清遠詩歌節”的平臺,繼續鼎力推進當代生態詩歌的創作和研究,例如2015年第二屆清遠詩歌節就以“山水田園詩歌的變革與走向”為主題,2018年第五屆清遠詩歌節則以“詩歌中的生態焦慮和夢想”為主題,2019年第六屆清遠詩歌節暨國際生態詩歌筆會聚焦“山水清音 澄明之境”,邀請國內多位知名詩人、學者參與研討、對話,極大促進了當代詩人生態意識的覺醒和深化。在華海的倡導和示范下,有不少清遠詩人越來越關注生態詩歌,例如唐德亮、唐小桃、湯惠群、李銜夏、梁晶晶、溫建文等。他們對清遠的筆架山、靜福山、北江、江心島等地域的生態較為關注,他們的生態詩歌寫作具有鮮明的在地性,他們也普遍具有較為自覺的生態意識。應該說,清遠生態詩歌群落漸漸顯示了生態詩歌的地方化、流派化的傾向。這是目前國內第一個流派性質的生態詩歌團體。
其次,吉狄馬加倡導的青海湖國際詩歌節也極大地促進了新世紀詩人生態意識的覺醒。2007年8月,由中國詩歌學會與青海省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首屆青海湖國際詩歌節在青海舉行,以“人與自然和諧世界”為主題舉行了詩歌高峰論壇。吉狄馬加在《青海湖詩歌宣言》中說:“現在,我們站在離太陽最近的地方,向全世界的詩人們呼喚:在當今全球語境下,我們將致力于恢復自然倫理的完整性,我們將致力于達成文化的溝通和理解,我們將致力于維護對生活的希望和信念……我們永遠也不會停止對詩歌女神的呼喚,我們在這里,面對圣潔的青海湖承諾:我們將以詩的名義,把敬畏還給自然,把自由還給生命,把尊嚴還給文明,把愛與美還給世界,讓詩歌照亮人類生活!”[6]吉狄馬加在詩歌宣言里非常強調自然倫理的完整性,強調敬畏自然,這無疑與新時代生態詩歌的倫理旨趣不謀而合,因此對于敦促中國詩人的生態意識的覺醒而言具有振臂高呼的重要意義。
再次,出現了集團式的中國生態詩歌團隊。2009年8月16日在北京大學燕園賓館2219房間,中國生態詩歌團隊宣布成立,主要成員有華海、侯良學、紅豆、姜長榮。他們提出要用生態的視角打量世界,用詩歌發出生態的警報,呼吁人們拋棄人類中心主義,反思現代文明。中國生態詩歌團隊隨后注冊了生態詩歌的博客,不斷吸引全國各地的生態詩人加入,不時更新生態詩歌博客。團隊成員華海、侯良學都成為了中國當代生態詩歌的代表性詩人,出版了多部生態詩歌集,紅豆也出版了生態詩集《液體的樹》,為中國當代生態詩歌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又次,許多重要詩人在新世紀都傾力于生態詩歌創作,并創作了許多富有藝術魅力、社會影響較大的力作,例如吉狄馬加、雷平陽、李少君、李琦、李元勝、閻安、宗鄂等。吉狄馬加的長詩《我,雪豹……》《裂開的星球》把彝族神話傳說與現代生活熔于一爐,批判了現代人對待大自然的急功近利的惡劣態度,構筑了一種氣魄宏大、視野開闊、眾生平等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和生態整體觀,堪稱當代生態詩歌的新經典。雷平陽從第一部詩集《雷平陽詩選》開始就非常關注生態問題,他的詩歌《殺狗的過程》把人類對待其他自然生命的暴虐態度寫得令人毛骨悚然,從而呼喚人與自然生命的和諧相處。至于雷平陽的《大江東去帖》《昭魯大河記》等詩歌對云南自然生態的詩意展現,氣象雄渾,境界壯麗。雷平陽在他的生態詩歌中有意復活云南大地的萬物有靈論,抵御現代化的鋼鐵步履,捍衛大地倫理的完整性。而著名詩人李少君也是具有自覺生態意識的詩人,他的《我是有背景的人》《神降臨的小站》等詩作極好地把握了人在大自然面前的合適位置,跳脫出人類中心主義的狂妄,收獲了意想不到的生態詩意。李少君有意接通古典山水田園詩歌的歷史文脈,多以山水詩歌致敬詩仙李白,把山水自然視為精神的教堂。著名詩人李琦的生態意識勃然生成于四處漫游之際,她親近自然,融入自然,禮贊自然,《一棵樹的修行》贊美那些能夠傲寒而立的北方之樹,《大海蒼茫如幕》贊美大海浩瀚的厚重和無與倫比的魅力,《那拉提》贊美新疆那拉提草原的出塵之絕美。李元勝則借助對昆蟲之美的探訪深深地楔入大自然,他的詩集《無限事》中生態詩歌比比皆是,例如《青龍湖的黃昏》寫詩人融入自然的高峰體驗,《散步》寫人與大自然的交互影響,《紫色喇叭花》寫喇叭花的美,《喀納斯鎮的獨自散步》寫新疆喀納斯的巧奪天工的美,《雨林筆記》寫詩人對熱帶雨林的熱愛,這些生態詩歌就像晨光中的粒粒露珠一樣晶瑩剔透,沁人心脾。而閻安的詩集《自然主義者的莊園》中散布著不少構思精巧、生態意識鮮明的生態詩歌,例如《有鶴的懸崖》寫風景區中的垃圾污染,《砍樹的人》批判那些砍樹破壞生態的人,《我想去的地方》則表達了詩人歸隱自然的生態理想。宗鄂也頗具有生態意識,他的詩歌《悼念一片桑樹》寫桑樹被伐讓故鄉裸露游子痛心的生態悲劇,《干涸的河流》寫河流斷流的生態悲劇,《發菜》寫過度摟發菜造成草原沙化的生態悲劇,《早市》則從菜市場中被宰殺的雞鴨看到家養動物的生存悲劇。從這些詩人詩作可以看出,到了新世紀,生態詩歌無論在思想上還是藝術上都已經成熟,詩人能夠駕輕就熟地掌握生態題材,選取的視角也極具個人化特色,因此避免了大而化之的概念化弊病。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新世紀開始出現了若干非常專注于生態詩歌創作的詩人,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就。除了上述的華海、侯良學、紅豆之外,還有比較典型的生態詩人,如敕勒川、沈河、哨兵、徐俊國、津渡、張二棍等。敕勒川長期在內蒙古生活,頗受蒙古族敬畏天地的傳統文化的影響,他的詩集《細微的熱愛》中生態詩歌較多,多描繪詩人敬畏自然、熱愛生命的生態情感。沈河長期生活在福建三明,從事林業工作,他的詩集《也是一種飛翔》《相遇》中多關注福建三明的生態,構建了一個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的青印溪,在當代生態詩歌發展史中占有一定地位。哨兵長期在湖北洪湖生活,非常關注洪湖的生態問題,他的《江湖志》《清水堡》《蓑羽鶴》《在自然這邊》等詩集中大部分詩歌都是地方感鮮明、富有生態關懷、藝術魅力較高的生態詩歌,他的長詩《水立方》主要展示了20世紀90年代到新世紀初期洪湖的生態惡化問題,可以與于堅的長詩《哀滇池》遙相呼應,堪為當代生態詩歌的典范之作。徐俊國曾長期在山東平度農村生活,延續了陶淵明、王維、孟浩然式的山水田園詩風,不過他更關注的是當前鄉村的生態問題,是如何與大地上的自然萬物重修舊好,因此他的詩歌《鵝塘村紀事》《燕子歇腳的地方》《自然碑》中也出現了大量同情弱小的自然生命、謳歌大自然的生態詩歌,《道歉》寫詩人對萬千自然生命的愧疚之情,《小學生守則》頒布要尊敬自然生命的新守則,《自然碑》則寫珍稀動物滅絕的生態問題。津渡則長期生活在杭州灣地區,喜好觀鳥,熱愛自然,他的詩集《山隅集》《穿過沼澤地》《湖山里》中也頗多生態詩歌,多描繪詩人觀鳥、旅行時的生態體驗,具有自覺的生態整體觀。詩歌《穿過沼澤地》可以視為津渡的代表性生態詩歌,主要描述詩人在沼澤地觀鳥時的體驗,行文流暢,若行云流水。津渡在詩歌《穿過沼澤地》中寫道:“我與萬物之間的相互磨損/我借助了你們,在塵世間站立/在高高的天穹下,沼澤/一只碩大的眼球上不停地游走/孤苦地徘徊,漂泊,終于/全部轉換為無盡的喜悅”。[7]由此可見,詩人津渡在大自然中才體驗到生命真正的喜悅。張二棍是近年迅速崛起于詩壇的青年詩人,他的詩集《曠野》《入林記》《搬山寄》中也頗多生態詩歌,這與他來自鄉村、從事地質工作有關。他寫生態詩歌也多關注那些備受人類壓榨、凌辱的弱小自然生命,寫出了它們的含辛茹苦、血淚悲劇,從而呼喚現代人能夠尊重生命,與大自然和諧相處。他的《一個人的閱兵式》《瑟瑟發抖就是反抗》《庭審現場》等詩歌都是角度新穎、震撼人心的生態詩歌。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新世紀同樣出現了不少生態意識鮮明、藝術風格獨具的少數民族詩人,除了吉狄馬加、倮伍拉且在此階段繼續創作了不少生態詩歌之外,還有藏族詩人列美平措、剛杰·索木東,普米族詩人魯若迪基,蒙古族詩人斯日古楞、斯琴朝克圖,苗族詩人吳凌,白族詩人何永飛等。他們的不少生態詩歌都能夠深入本民族傳統文化中,面向全球性生態危機的可怕現實,呼喚生態意識的覺醒,例如斯琴朝克圖的《把地球留給孩子們》,魯若迪基的《一個山民的話》,列美平措的《許多景致將要消失》等等。倮伍拉且致力于在詩歌中重塑大涼山的生態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書寫彝族人的萬物有靈論,抒發眾生平等、萬物一體的生態高峰體驗,例如他的《常常有那樣一個時刻》等生態詩歌形神兼備、意蘊深遠。魯若迪基則在生態詩歌中傳達普米族的韓規文化,呈現小涼山的地域特性,他的《斯布炯神山》《果流》等詩歌不但表現出詩人濃郁的戀鄉情結,而且呈現出生態詩歌鮮明的在地性。何永飛則對云南大理白族人生活展開了動人的生態審美書寫,他的詩歌《海舌》寫大理洱海的美及其面臨的生態危機,《萬物有靈》寫白族人對萬物有靈的信仰,《對神招供》寫自然萬物其實都是神的化身從而也表現出泛神論式的生態詩意。縱觀新世紀頭二十年的生態詩歌發展,當代生態詩歌的確出現了詩人薈萃、佳作迭出的繁榮景象。相對于此前的生態詩歌多處于不自覺的狀態,此階段的許多生態詩人不但從事生態詩歌創作,而且具有較為自覺的理論意識。例如華海曾的《關于生態詩歌的對話》《敞開綠色之門:生態詩歌——對自然的聯接、體驗和夢想》等文章對生態詩歌的定義、特性就曾做出較為明確的厘定,尤其是他把批判性、體驗性和夢想性視為生態詩歌的核心特質,具有較大的創新性。至于吉狄馬加的《青海湖詩歌宣言》則可以視為當代生態詩歌的理論覺醒的標志。此階段的生態詩人也具有更為開闊的全球性生態視野,例如吉狄馬加的《裂開的星球》就是典型例證。而與全球性生態視野并行不悖的是,此階段生態詩人大多培育出鮮明的地方意識,例如雷平陽、沈河、華海、哨兵、徐俊國、津渡等無不如此。更為重要的是,雷平陽、李少君、華海、哨兵、津渡等生態詩人均有極為自覺的傳統文化意識,他們的不少生態詩歌就好像古典山水田園詩歌的后現代復活,極大地提升了當代生態詩歌的本土性和藝術性。
結語
整體觀照近四十余年的當代生態詩歌歷程,我們可以發現生態詩歌經歷了從最初的零星綻放到新世紀的大面積崛起的過程,社會影響也越來越大。如果我們披覽一下歷屆魯迅文學獎中獲獎詩集,我們可以發現生態詩歌在許多詩集中占比較高,獲獎詩人具有較為自覺的生態意識。例如第一屆魯迅文學獎中,李松濤的《拒絕末日》、李瑛的《生命是一片葉子》、韓作榮的《韓作榮自選集》、沈葦的《在瞬間逗留》;第四屆魯迅文學獎中,于堅的詩集《只有大海蒼茫如幕》;第五屆魯迅文學獎中,李琦的《李琦近作選》、雷平陽的《云南記》等詩集;第六屆魯迅文學獎中,閻安的《整理石頭》、李元勝的《無限事》等詩集;第七屆魯迅文學獎中,張執浩的詩集《高原上的野花》等。這些詩集中,生態詩歌較多,而且藝術水平較高,許多詩人常常能夠從人們習焉不察之處發現生態意識的盎然詩意。
當然,更為重要的是,當代生態詩歌具有多方面的積極價值:
其一,當代生態詩歌為中國新詩重塑了生態維度。中國新詩長期以來多崇奉現代化的主流價值觀,相信進步、發展、科技、民主等通約價值,但是對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態關系、對自然生命素來缺乏足夠的思考和觀照。而當代生態詩歌真正徹底地反思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顛覆了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確立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基本立場,提出尊敬自然、敬畏自然、敬畏生命的生態倫理觀,從而為中國新詩刷新了生態維度。
其二,當代生態詩歌為中國新詩重振了地方維度。中國新詩也曾一度喪失了地方維度,多被現代化、革命意識形態的時代大潮裹挾而去。但是當代生態詩歌卻重回地方,呈現了特定地方的生態現狀和理想,例如于堅、雷平陽對云南的詩意書寫,吉狄馬加、倮伍拉且對四川大涼山的深情描繪,魯若迪基對小涼山的耐心撫摸,啞石對四川青城山的詩意品味,華海等詩人對廣東清遠的詩意構造,沈河對福建三明青印溪的精妙刻畫,哨兵對湖北洪湖的詳細踏勘,徐俊國對山東平度鵝塘村的耐心觀察,津渡對杭州灣濕地的精美描繪,等等,都是當代生態詩人復活地方的重要努力,他們以生態詩歌有力地阻止了非地方化的異化泛濫。
其三,當代生態詩歌重新復活了古典山水田園詩歌的文學傳統。古典山水田園詩歌雖然與當代生態詩歌存在著較為鮮明的差異,但是其中蘊含著親近自然、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態智慧,這種生態智慧如今在當代生態詩歌中得到較為完美的賡續。許多當代生態詩人都對傳統山水田園詩人保持著高度的敬意,例如于堅之于李白、蘇軾,雷平陽之于杜甫,李少君之于李白,啞石、華海之于王維,哨兵、徐俊國、津渡之于王維、孟浩然等。他們盡可能地復活了古典山水田園詩歌的寶貴遺產。
其四,當代生態詩歌極好地促進了當代生態文明建設。無論是當代生態詩人的生態批判,還是當代生態詩人對地方的關注、對傳統生態智慧和西方生態倫理的詩意表達,都可以極好地促進讀者重建人和自然之間的和諧關系,促使讀者積極地反思現代文明,為生態文明的轉型做出應有的文學貢獻。
詩人于堅曾在《便條集·9》中寫道:“把春天說成神廟把樹說成神衹/只是一個非法的比喻/我只有比喻而已/也許會有人因此改變想法/收起斧子開始傾聽”[8]。生態詩歌也是一種比喻,它試圖改變的是現代人對待自然的態度,希望現代人放棄那種對待自然永無饜足的功利主義、敲骨吸髓式的利用、支配和征服,能夠“收起斧子”,開始傾聽大自然的聲音,也傾聽生態良知的聲音,謹言慎行,節制欲望,物質簡樸而精神豐盈,與自然萬物和諧地詩意地生活在大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