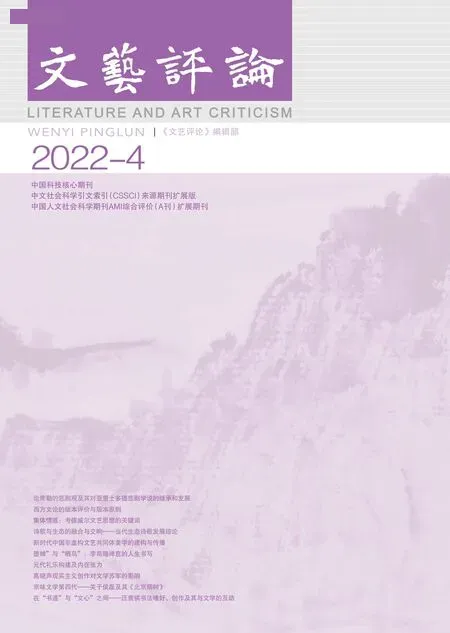西方文論著作的版本評價與版本原則
○曾洪偉
有學者指出:“對圖書版本的優劣高下和價值大小做出一個正確的評價,是版本鑒別的最終目的,是最重要的版本意識之一。正是這種版本需求,推動著版本學的產生和不斷發展。所以版本評價在版本學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1]而版本評價不僅對于版本學本身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且它對于學術研究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版本選擇最終是為知識/文化的傳承、傳播和學術研究服務的,良好的版本或者說善本無疑能為高質量的學術研究和優秀文化遺產的留存、傳續、保護奠定扎實的物質、知識基礎。因此,從版本學科、學術研究和文化傳承等諸角度講,版本評價與版本遴選都彰顯出其重要的學科、學理、學術、文化價值,其工作的意義對于學界和社會可謂功莫大焉。本文所論涉的“西方文論”主要是指20世紀西方文論,“版本”是指由西方文論原語著作和其相應的譯語著作所構成的版本譜系(在本文中主要是指中外版本譜系)中的文本。對于西方文論著作版本的科學、合理評價應該體現為一種綜合評價,即包含內部和外部的評價;而對于西方文論研究而言,其核心評價應該是(內部評價之中的)學術評價。
一、內部評價:版本評價的主要維度
由于國內學界目前尚缺乏自覺的文論版本(譜系)意識,因此,更缺少有意識的、清晰的、具體的版本評價方法與遴選原則(建構),而在版本的使用中,也主要是基于一種無意識的、隨意性較強的版本選用。面對文論著作在歷史上和跨文化交流中生成的紛繁復雜版本,學界亟需構建科學的、系統的版本評價方法,以為消費者、讀者和學者進行版本選擇指明方向,為其開展文論閱讀和研究奠定基礎。
為比較客觀、公正地評價文論版本,總體而言,筆者認為應該采取全面與重點兼顧、平衡的原則和方法:即一方面,要從多個維度綜合考察版本的質量與價值,這樣可以避免以偏概全;另一方面,在比較、厘定版本的優劣和高下之時,又要聚焦重點方面予以集中考量,避免審而不決、評而不定。
具體而言,則是結合版本的實際,參照中國古代、現代和國外的版本評價標準,同時合理吸取后現代文本觀念,解構版本評價中的作品/原著/作者本位和“唯我獨尊”的地位,打破文本中心的視野局限與觀念囿限,全面開放評價系統,提倡內部評價(注重版本內部因素)與外部評價(注重版本外圍因素)相結合,使版本評價走向多元化、多樣化,即建構多元、多方的評價體系。這就包括從作者/譯者系統(作者/譯者的聲譽度、權威性等),出版者系統(出版社的知名度),作品系統(原著與譯著的正副文本情況,譯次、版次、印次、印數、價格、裝幀、設計、年代等),讀者/消費者/書評家/翻譯批評家/研究者系統(接受/應用情況,評價情況,引用情況等),市場—社會系統(作品銷路、市場反饋、圖書獲獎等),后現代觀念系統(解構文本中心、權威和傳統慣習),時間—歷史和空間—地域系統(跨時空翻譯、傳播、傳承情況),版本(譜系)系統(版本和譯本形態情況,譜系內涵大小)等多角度考量版本。它們在版本的評價中所占權重不一,但又緊密相關,不可或缺。本部分主要探討以版本本體為中心的版本評價一般方法,而從其他系統或層面對版本進行評估的方法,則在后面結合西方文論版本案例進行闡述。
版本評價,無疑其重心和中心還是應該在版本本身(或者從它出發、以它為旨歸),它是消費者購買、讀者閱讀、學者研究的對象和根本。那么可以從哪些方面對文論版本進行評價呢?結合西方文論版本的實際,筆者認為,可以從學術、藝術、技術、文物價值等維度考察評議。
第一,學術層面。這是指版本的內涵層面,包含正文本和副文本,文字和圖像等內容。這是一個版本或譯本的最為核心的內在和圈層,是決定版本或譯本質量高低與價值大小的最為重要的因素和權重,同時也是接受者最為看重的部分。對于版本的學術內容的考察,主要應注意如下方面:
(1)內容是否完整?這既指版本/譯本相對于先前版本/原著在正文本、文字內容上的完整性,也指版本/譯本在副文本、圖像內容上的完整性。其本質是指版本的一種互文性、對應性和忠實性。而后兩者(即副文本、圖像內容)往往是被刪節的對象:由于受重視程度不夠,或價值評判不高,它們或在文本保存和復制的行為中被刪除、遮蔽,或在翻譯和出版的過程中被刪去、更替。而正文本和文字內容在翻譯過程中也存在節譯或漏譯的現象。這諸種情況必然會導致殘本或節本的出現。無疑,無論從版本學的版本完整性要求還是從學術研究的求真性訴求來看,殘本或節本都是必需要盡量避免的,而全本或足本則是版本活動追求的目標與結果。
(2)內容是否準確?這既指各個版本本身所包含內容的真實性,也指版本譜系中原語版本之間、譯語版本之間、原語和譯語版本之間對應信息的忠實性和準確性。若一個版本錯訛甚多,無疑是不能稱得上好的版本的。這種錯訛包括語言文字上的和內容信息上的,而后者又包括事實引用訛錯和內容翻譯訛錯。原語版本的訛錯主要集中于語言文字上,而譯語版本訛錯則主要出現在內容翻譯上。由于在客觀上翻譯作為一種跨文化的語言轉換活動的困難性,翻譯作為一種“改寫”的藝術的學科屬性,翻譯實現絕對“忠實”“等值”“等效”“信達雅”目標的不可能性,以及主觀上翻譯主體語言水平、理論水平、翻譯水平的限制與參差不齊,使得文論譯本或多或少難以實現相對于原著的內容精準性。再加之理論翻譯相對于一般文學翻譯的較高難度性,漢譯版本的訛錯性和不準確性幾率就大得多。這從當下一些文論翻譯批評典型案例即可見出[2]。總體而言,外文原著版本往往校審精準,印制精細,差錯率低,文字訛誤較少,而中文譯本往往較多,再加之翻譯過程中或主觀或客觀原因造成的翻譯失誤,漢語譯本的文字和內容準確性相對較低。而同一作者/譯者的原語/譯語版本之間隨著版次的增加,由于修訂的原因,其文字和內容的準確性往往在不斷提升,從而趨于完善。而不同譯者的譯語版本之間的文字和內容準確性則需要結合原著具體分析。因此,版本(尤其是譯本)的準確性是不同程度的,它可以無限逼近原著,但卻永遠難以等同原著。但無論如何,版本內容的準確性是版本評價的一個重要指標。
(3)內容有無超越或創新?即一個版本相對于其他版本的相異之處:或版本內容質量(經過新的校訂和修改)得到進一步提升(語言更精準、更通順、更優美,文字訛錯更少見,內容更完善),或新增有價值的新內容(如序跋,導讀,注釋,圖像等),使版本在新時代或新語境下煥發出新的生命與活力。其本質是指版本的創生性或創新性。這是新版本生成的重要原因或理由:若一個版本/譯本不具有超越性或創新性,則其無生成的必要。由于這符合、順應學術或知識創新的要求與趨勢,因此可以作為衡量版本價值的一個重要指標。
其實,在一個文論版本譜系之中,無論是原語版本之間、譯語版本之間,還是原語與譯語版本之間,都潛隱著一種文本競爭關系,其本質是文本生產者(無意識或有意識)的“影響的焦慮”,正是這種心理機制促成了版本和譯本的不斷生成。原著作者在面對自己先前版本、譯著作者在面對原著和自己先前譯著和他人譯著時都會產生一種創新的焦慮感,渴求在眾多文本中脫穎而出,或占有一席之地;作為本能的心理防御,作者和譯者不得不充分發揮其“創造性叛逆”精神,發揮其創作、創新、翻譯主體性,通過修訂、改寫、增刪正副文本等創作手段,以及誤譯、增譯、省譯、改譯等翻譯手段,開辟屬于自己的創新空間和領地,以超越自己、超越他人,推出新的版本或譯本。但是只有其中的強者或強者文本才能最終實現創新并超越自己、本著或他人、他著,而其中的弱者或弱者文本則因在創作、修改、翻譯活動與結果中未能成功實施創造或創新,而未能超越自己、本著或他人、他著。所以,由此不難判斷,在一個版本譜系之中,雖然著者、修訂者、譯者在學術創新理念的驅動之下,生產創新為旨歸的版本,但并非所有版本都是成功實現(較大程度)創新的強者版本,而是還有諸多未實現創新或創新程度不大的弱者版本,而其版本價值與學術價值無疑是相對較低的。這在開展版本評價時需要特別注意區分和判別。
第二,藝術與技術層面。這是指版本的形式方面。一個版本可以具有多重身份和屬性:從學術的角度看是作品,從藝術的角度看(有可能)是藝術品,從技術的層面看是產品,從市場的角度看是商品,從消費者的角度看則是消費品。如果說作者或譯者主要負責版本的學術內容的話,則版本的藝術和技術層面內容或事務則由設計者和出版者負責。在他們眼中,版本是藝術品、產品,但由于他們最終面對的人群是讀者和消費者,因此版本(最終)也是商品和消費品。為吸引讀者和消費者積極購買,他們必須基于“讀者/消費者至上”“讀者/消費者友好”的理念,從形式上盡量吸引、說服讀者和消費者,即注重版本的藝術化/性和技術化/性。如果兩個版本在學術的層面上相比不相上下的話,則在藝術和技術層面藝/技高一籌者為上。從藝術和技術的層面評價版本,主要是看其審美價值的高低大小和印刷制作的精良與否,等等。而這些又在書籍版本的開本、版式、紙張、用墨、字體、字號、字間距、行間距、(書體和封面)設計、裝幀、色彩、圖像的使用、經久耐用性、價格等方面具體體現出來。從文論書籍的實際情況來看,不同的版本,即使內容完全相同,其上述諸方面都會存在或大或小的差異(重印本也如此),因此這可以成為版本比較和版本評價的重要指標因素。但是版本的審美評判和質量評價又是因人而異、言人人殊的,其相對性、差異性很大,因此,難以在上述方面設定具體量化標準,而只能作綜合性的判斷。從總的情況來看,由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差異,原語版本比譯語版本的藝術性更強,技術更先進,因而也更值得國內書業界、裝幀設計界、印刷界同行學習;而從歷時的角度來看,當代版本(尤其是國外版本)總體上比先前版本在審美、技術、環保等理念上更趨于開放、開明和前衛(倡導以讀者、消費者為中心;理論可以不是灰色的、嚴肅的,也可以是多姿多彩的、活潑的;可以不僅僅是文字的表達與述說,也可以是語圖互文的),藝術色彩更濃厚、更豐富多元,印刷工藝更先進、更環保、更綠色,產品設計更精美。
第三,文物價值層面。指文論書籍版本的歷史價值。這主要是從作為物質的書籍角度而言的。其本質是指版本的古舊性(富有歷史感)、稀缺/見性(不易獲得性)、珍貴性(名人賦值)等屬性。具體說來,是指因版本年代久遠(如俄國形式主義文論的論著距今已有百余年的歷史),或不易獲得(如某些外文原著版本或中國港臺漢譯本等),或是作者手稿,或經名人收藏(如留有名人題記、批注、贈言、寄語、簽名、手跡、印章等)等原因而增添了版本的文物價值性。而具有這種價值的版本無疑是版本中的“珍品”。“文物價值”雖然主要是針對古代書籍版本而言的(此前主要是一個關于古籍版本的評價標準和概念),但從歷史發展和長遠的角度來看,隨著西方文論歷史的向前延伸,在歷史的回望中其版本的文物性也會隨之增強;同時,不同于古代書籍版本的“稀缺/見性”主要是指在一種/一國文化之中而言,西方文論版本的“稀缺/見性”還包括跨語言文化、跨越地理空間的不可易得性或不可多得性。因此,西方文論版本也是有其文物價值獨特性的。鑒于此,“文物價值”可以作為衡量和評判西方文論版本的一個指標和概念。
對西方文論著作版本進行評價,除了促進版本(學)自身的健康發展與建設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即是評出版本譜系中質量相對較好、價值相對較高的版本,亦即“善本”,為學術研究服務。何謂文論“善本”?筆者認為,總體來講,“善本”是指一方面既一定程度忠實于原著(語言文字和內容等),但另一方面又有所創新和變化,體現了個人特色、時代特色和異域文化特色的版本。即它應該是傳承與創新、發展的結合。因此,文論“善本”是一個動與靜、變與不變、堅守與開放辯證統一的概念。再加之版本(譜系)的無限生成性、發展性和開放性,因此“善本”(的評定)只能是相對的、動態的:沒有最好的“善本”,只有更好的“善本”。具體說來,文論版本本體范圍內的“善本”是指版本譜系中內容相對完整準確且有所超越,具有較高審美價值,印制較為精良,文物價值較高的版本。
在作版本選擇和進行西方文論研究時,既要優選/首選善本,同時又要具有開闊的版本史、版本譜系視閾和寬闊的文化—社會視野;既要估量版本的學術價值,同時又要估察其藝術與技術價值,還可以顧及、看視其歷史文物價值,當然核心還是學術價值。
二、外部評價:版本遴選的外圍視角
如前所述,版本的選擇除了可以從版本本身(即版本系統)——如版本的學術、藝術、技術、文物價值等層面(包含翻譯層面),這是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層面(對學術研究而言,尤其是學術層面)——出發進行評判以外,我們還可以從版本之外的系統,如譯者(身份)、讀者(反饋)、市場(銷量)、作品(版次和翻譯方式)等角度予以評判。這些是判斷版本(質量與價值)的外圍因素。相比學術等內部因素,它們具有直觀表面、易于操作、簡便快捷等特點,同時又具有情況的復雜性、多面性甚至矛盾性:正因為如此,由之得出的評判結果也可能具有不統一性、不穩定性和不可靠性等特點。因此,它們可以作為(普通讀者或需要快速)判斷版本優劣高下的重要參考因素,但不能作為決定性因素;而在實際的、專業的、可靠的版本評價中,必須將其與具體版本的內部因素的評價相結合,相互參照,綜合評定,才能得出最后的、準確的、科學的結論。
(一)譯者的身份
一般認為,學界知名學者或譯者的譯本往往比較可靠或更好,或者說是“權威譯本”或“善本”,但情況也并非完全如此。例如,方維規根據其對學界的觀察和閱讀經歷不無揶揄地指出,學界的一些優秀理論譯作往往不是知名的譯者翻譯的,反而是出自一些“無名小卒”、普通譯者:“……新近的中國書市上很有一些值得稱道的優秀譯作,它們出自一些名不見經傳的譯者,而不是那些以多取勝的名牌復印機。”[3]這里的“名牌復印機”即是指知名譯者,“他們已經很有名氣,甚至成了談論某些西方理論的‘一方諸侯’”。[4]其嘲諷和不滿之意溢于言表。又如,從具體的翻譯實例來看,“權威”譯本或學界推崇的譯本也不一定盡善盡美或絕對可靠,也存在不如非“權威”譯本之處。以伊格爾頓的《20世紀西方文學理論》(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的譯本為例,雖然該著在中國已有多個漢譯本,但學界一般認為伍曉明的譯本為權威譯本;而若仔細對比,也可以發現伍曉明譯本也并非毫無瑕疵,其他人的譯本也并非一無是處。下面我們擷取兩段原文及相應的譯文作為對比。
原文1:If one wanted to put a date on the beginnings of the transformation which has overtaken literary theory in this century,one could do worse than settle on 1917,the year in which the young Russian Formalisist Viktor Shklovsky published his pioneering essay‘Art as Device’.[5]
伍曉明譯文:想為20世紀中發生于文學理論的變化的各個開端確定一個日期的人,可以比決定其為1917年做得更糟。就在這一年,年輕的俄國形式主義者維克多·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發表了他那篇開拓性的論文《作為手段的藝術》(Art as Device)。[6]
王逢振譯文:如果人們想為本世紀文學理論的重大變化確定一個開始的時間,最好是定在1917年。這年,年輕的俄國形式主義者維克托·什科洛夫斯基發表了他的拓荒性論文《藝術即方法》(Art as Device)。[7]
原 文2:Methodologically speaking,literary criticism is a non-subject.If literary theory is a kind of‘metacriticism’,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criticism,then it follows that it too is a non-subject.[8]
伍曉明譯文:從方法論上說,文學批評是一個“非學科”(non-subject)。而如果說文學理論是一種“元批評”(metacrticism),即對于批評的批評反思的話,那么結論就必然是,文學理論也是一個非學科。[9]
王逢振譯文:從方法論上來說,文學批評不是一門學科。如果文學理論是一種“總批評”(metacriticism),是一種對批評的批評反映,那么它同樣也不是一門學科。[10]
從上述譯文來看,無論伍譯還是王譯,內容上都體現出了對于原文的忠實,即完整、準確地表達了原文的意思;但在譯語文字的表述上,伍譯主要采用了異化策略,譯文比較生硬、歐化,讀起來不夠通順、自然,尤其是對原文1的翻譯“想為本世紀中發生于文學理論的變化的各個開端確定一個日期的人可以比決定其為1917年做得更糟”,和對原文2的翻譯“文學批評是一個‘非學科’”,讀后令人費解。而相比之下,王譯則采用歸化翻譯策略,譯文比較符合漢語表達習慣,語言流暢,明白易解,可讀性強。
在英語教學中適當增加文學課,對學生來說是一筆財富,適當了解外國文學對英語語言的學習有促進作用。學生通過學習外國文學可以了解一些知識背景,社會背景,語言背景,進而了解外國的文化。
當然,筆者在這里并非全盤否定伍譯本和大多數權威譯本,它們從整體上講還是值得信賴的。但是,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僅僅依據譯者的身份來判斷譯本的質量不一定可靠。
(二)讀者的反饋意見
例如,針對采訪者黃新炎對于鄭克魯先生翻譯波伏娃《第二性》一書的調查結果:“我在當當網上看到,《第二性》第一部目前有9924人評論,第二部有8223人評論,可見該書影響之大”[11],鄭克魯先生認為網絡讀者的評價很重要:“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在網上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對譯本(《第二性》)的評論,體現了讀者的意見。讀者都說好的譯本,應該差不到哪里去”[12],“民意說哪個譯本好,就差不到哪里去”[13]。的確,譯本作為一種讀者和消費者購買的商品和消費品,其質量要經得起用戶的檢驗,要贏得消費者的良好口碑。因此,譯本質量的高低是可以參考網絡用戶評論的,有時還可以作為重要的評價指標。
但必須注意的是,當前在網絡商品銷售上也存在著不良的風氣,即商家為促進商品的銷售,提升銷量,會雇用職業刷單者或網絡水軍,充當吹鼓手,發布虛假好評;同時用戶之間也存在著跟風評論的情況。因而,從這個角度來講,網絡評價也不一定完全可靠。
(三)市場的銷售狀況
書籍既是一種知識、思想產品,同時也是一種文化、物質商品,在我們一般的認知之中,如若它在市場上受歡迎程度高、銷售狀況佳,則其質量和價值應該不會低。對理論著作和譯本而言也是如此。“《第二性》是一本學術書,沒有想到的是出版之后銷路非常好。我在北京聽北師大一位研究生說,一開始以為《第二性》(譯本)不好讀,打開之后發現,行文非常流暢。理論書寫得這么可讀,是很不容易的,因為該書涉及的知識面非常廣泛。”[14]
但是,在許鈞先生看來,作品的市場銷量好不一定就代表翻譯質量高。“現在有很多經典作品不斷在重新翻譯,一本書有幾十個版本,質量也參差不齊……其實那些市場上賣得最好的不一定是最好的翻譯版本,但是很多人卻不知道。”那么“什么是好的翻譯?在許鈞看來,好的翻譯有個簡單原則就是經得起讀”,“好的作品是經得起讀的,它的語言有藝術性,前后有一種文氣能夠貫通,語言有節奏感。行家還要看譯文是否經得起與原作對應,經得起與原文的比較,無論是精神風貌,還是語言特質,要忠實于原著”[15]。因此,從市場的銷售數量也不能完全、準確地判定譯本的質量,而根據上述兩位學者和譯者的觀點來看,譯本的可讀性和讀者的閱讀體驗也是十分重要的評判條件。
(四)作/譯品的版次
一般而言,版次(或印次)與譯次是一致的或同步的,即有了新譯文,必然會推出新版本,而新版本一般對應著新譯文。而且從理論/道理上講,往往新版本比舊版本要好,因為前者會基于后者而作出修訂和完善。但是,從理論譯本和版本的實際情況來看,重譯本、再版本或后來的譯本(版本)不一定比先前的譯本/版本要好。
例如,重譯本不一定就好。鄭克魯先生指出:“經典作品需要重譯,因為以前的不少譯本還不夠好,即使是重譯本,也有譯者不負責任的。不少讀者只看原作者是誰,買書時分不清哪是好譯本,哪是差譯本。”[16]
再版本不一定就好。例如,王逢振先生翻譯伊格爾頓的《20世紀文學理論》(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一書先后出版了2個漢譯版本,但其再版本卻非重譯本,雖然“更換了出版社,重新設計了裝幀,甚至書名也改了,但是內容仍然是原來的,鑒于原作已經做了修訂,譯本也應該與時俱進,特別是譯本再版時原著第2版已經出版10年了。讀者買了新出版的譯本,讀到的卻是舊版的原著,讀者很可能有被誤導的嫌疑,這樣的再版不應該被推崇。”[17]的確,如果原著已經出版了新版本,且在內容上已經有了較大更新,作為新出譯本,應該反映這種變化,否則不能滿足學術閱讀和研究“求新”的訴求。因此,通過對比漢譯本與英文底本的對應情況(即譯者是否選擇了最新或最好的版本進行翻譯),亦可判斷譯本的優劣;若底本選擇不當,一般而言,其再版本評價也不會太高。
(五)譯作的翻譯方式
即直譯還是轉譯。學界或譯界一般認為直譯比轉譯要好,因為前者在翻譯過程中所產生的文字和內容誤讀、扭曲、變形、損耗、訛誤要少。例如黃新炎指出,“有網友在當當網上留言,盛贊《第二性》:‘同其他由英文版本翻譯過來的譯本不同,這個版本是從法文版直接翻譯過來的,也是法國版權方唯一授權版本,內容方面沒有刪減,翻譯更生動有趣、更忠實于原著內容。’”[18]這就暗含著讀者大眾對于直譯方式的認同。而促使和激發鄭克魯先生重譯/直譯該著的重要原因則是先前轉譯本的問題嚴重:“上世紀80年代我看到湖南文藝出版社節譯的《第二性》,感覺譯文質量太差,當時我手頭沒有原文,無法核對,也就無法引用。”[19]由此可以看出學界和讀者對于直譯本和轉譯本有著不同的價值評判與認知。
但是,在實際的翻譯中,有學者指出,直譯本也不一定就好。“(奧爾巴赫的)《摹仿論》(Mimesis: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在2002年已經有了據德文原著翻譯的中譯本(見吳麟綬等譯《摹仿論》,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引者注)。如果對中英兩個譯本進行簡單比較,我們會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著發人深省的差異。首先,《摹仿論》的批評特色在于以原語言著作作為分析藍本。英譯本全部保留了原語言引文,并隨后附上了英文翻譯。可是令人遺憾的是,中譯本將上述所有引文全部變成了中譯文。須知,原著引文是本書的重要特點之一,隨意刪除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它的完整性。其次,英譯本有著名學者薩義德撰寫的長篇導讀,而中譯本既沒有前言,也沒有后記。此外,國內只有一篇書評對此書有較為深入的論述。第三,中譯本的出版時間比英譯本要晚半個多世紀,而且與英譯本相比,它在中文學界所產生的影響幾近于無。[20]其實,奧爾巴赫與他的同胞、文學文體學研究之父斯皮策代表了西方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傳統。當下學界,西方各種新學舊學理論不斷被無節制地引入,而《摹仿論》卻乏人關注。同樣重要的學術資源,我們為何厚此薄彼?但愿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引進的《摹仿論》英譯本能彌補一點缺憾。”[21]
綜上,在該例中,大陸直譯本不佳的原因在于刪除了原著特色內容和重要副文本,破壞了其完整性,且沒有英譯本的影響大;而且甚至可以說,臺灣張平男根據查斯特(Willard R.Trask)的英譯本將該著轉譯的漢譯本(《模擬:西洋文學中現實的呈現》,臺北市:幼獅文化,1980年)也比大陸版影響更大。
因此,關于直譯本與轉譯本的優劣高下問題,的確不能一概而論,而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六)其它外部因素
除了上述主要的外部因素之外,我們還可以根據原著/譯著版本的版次、印次、印數的多少、是否獲獎(如美國國家圖書獎、魯迅文學翻譯獎、傅雷翻譯出版獎、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各省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等)、是否成為學術研究對象并獲肯定、是否出版社約稿、譯者的中文功底、出版社的級別與聲譽、圖書館藏機構的級別、館藏的版本等初步判斷著作的質量與價值。
因此,文論版本/譯本的遴選具有標準和操作的復雜性,既涉及到內部和外部等多個因素,而且每一個評判標準都可能具有不確定性(如上述5個外部因素),評價具有很大的矛盾性和張力性,評判者在遴選時必須注意標準的內外結合,宏觀與具體結合,一般與特殊結合,主要與次要結合,深入版本/譯本作具體對比和細致分析,通過綜合比較,以最核心的學術指標為主,對版本/譯本做出主導性判斷。切忌泛泛而論,或僅僅依據一個指標而得出版本/譯本優劣高下的結論。而且根據版本評校的實踐來看,很少有版本/譯本是完美無缺、完勝其他版本/譯本的,因此,所謂文論善本只能是相對而言的,而非絕對的,是一般而言或在主要方面略勝一籌的版本/譯本。善本也需要參照、汲取其他版本/譯本的優點和長處進行進一步完善并發展。
三、“準”“新”“善”“全”“深”:文論研究的版本原則
總的來說,結合西方文論研究實踐,并借鑒其它文學研究領域的成果[22],筆者認為,在西方文論研究中,我們應該遵循“準”“新”“善”“全”“深”的版本原則。其具體內容為:
首先,必須遵循版本精確所指的原則(即“準”),同時還必須兼顧參照最新版本原則(即“新”)。對于譯本,還必須遵循優選善本(即“善”)、參照眾本(即“全”)的原則。
在當前的西方文論研究中,由于研究者的版本意識淡薄,常常出現版本錯指和亂指的現象,前者即指標注并不存在的著作版本,后者即指標注的版本雖然存在,但實際上是另一個版本(或其他版本)的信息。同時,還有一種普遍現象,即版本任選,但結論統指,也就是說,研究者在研究時往往選取西方文論著作眾多版本中的一版(往往是第一版)展開研究,但卻因或主觀(缺乏清醒自覺的版本意識,未進行系統的版本變遷、譜系梳理)或客觀(由于信息、資料引進渠道不暢通,版權問題的延宕,導致外文西方文論原著獲取、引進、翻譯不及時[23])的原因,而忽略了其他版本的存在或與其它版本之間的差異,從而將根據其中一版得出的結論指向或強加于其它版本。因此,在進行西方文論研究時,我們必須要明確、精準地指出所論著作的版本信息,根據該版本所得出的結論也應該指向和僅限于該版本,而不能不加考察、不加區分地跨版本、串版本下結論。
與此同時,我們在以版本譜系中的其中一個版本作為研究對象時,還必須參考譜系中的最新版本,以保證研究證據和結論的真實性、可靠性、正確性。因為好的學術著作應該是“新”的、“真”的:所謂“新”,不僅指學術著作的創新性(這一點對于西方文論經典名著而言是毋庸置疑的),同時還指能及時反映作者的新思想、新觀點;而所謂“真”,則是指該著應該能真實、準確地反映著者在這些思想、觀點上的變化。由于西方文論家在著述時受意識形態等非學術因素干擾相對較小、較少,因而其著作以及其修訂本一般都能真實地反映作者成熟的意志,即其新思想、新觀點。相對于新版本,舊版本由于無法及時地反映出著者理論思想的最新變化,因而一般說來它比新版本價值低。因此,在研究一部具有版本譜系的西方文論著作時,為保證研究結論的新穎性和前沿性,我們應該首選該著的最新版本,以及時跟進和把握作者理論、思想、觀點的最新發展動態(這樣才符合學術研究求“新”的特點);而在研究最新版本之前的其他版本時,也應該把這些版本置放于該著的版本譜系之中,以從歷史、全面、聯系、動態的角度來研究它們,避免因以靜態、停滯、片面、孤立、狹隘的觀點來審視時得出錯誤的結論而不自知[24]。
對于譯本,由于在實際的版本考察中,我們發現既無十全十美的譯本,亦無一無是處的譯本,因此建議在選用譯本時,應該在考察全部譯本的基礎之上,以譜系中的善本為底本,同時參考其它譯本,通過取長補短的方式,吸取、綜合優秀譯文,從而獲得最佳的版本效果。關于漢譯善本的“真”“新”“美”問題。其“真”不僅僅是指真實、全面、準確地傳達原著內容,同時還指忠實地表達其風格;其“新”既指在內容上及時反映了作者理論思想觀點的新變化,又指在語言、文字、副文本等方面有新改進和新提升。另外,漢譯善本不應該僅僅具有“真”“新”的特性,還應該具有“美”的特點,亦即從讀者閱讀接受的角度來看,譯本應該譯文地道、流暢、優美,深受讀者喜愛、歡迎,否則譯語佶屈聱牙、晦澀難解、邏輯不暢,僅有內容上的“真”、“新”的譯本也算不上真正的善本(“善本”之本意即為“好的版/譯本”,這也包括語言上的“美”)。
其次,無論是在西方文論史的書寫中還是在西方文論的研究中,我們必須對每一部(經典)文論著作所生成的本土和異域版本譜系或圖譜心中有數,對這些中外版本演變所形成的“小歷史”“微觀史”“小世界”應了如指掌,有深入細致的認知(即使我們不一定要對其譜系和歷史進行書寫與展示),此即所謂“全”和“深”。亦即文論史的寫作者、敘述者和文論研究者應該“放眼全譜”“胸納眾本”,而不能僅關注或論說某單一版本。簡言之,學術主體應該對著作的版本譜系作“全景觀”“整體觀”,對作者的文論思想和觀點的嬗變歷程應有“全局感”和“縱深感”。同時,鑒于當前學界對于西方文論版本譜系缺乏有意識的研究的現狀,筆者也呼吁學者們對其展開專門、系統和深入的研究,以為相應的文論史寫作和文論研究提供學術參考。
這并非夸大其詞或繁冗多余,而是由西方文論版本(譜系)在歷史上、事實上的豐富性、復雜性和價值意義重要性決定的。因為西方文論著作的版本譜系往往是受多種因素影響、經過多種流變模式而生成的,如基于相同/不同文化語境、不同翻譯路徑、不同傳播媒介、不同模仿方式的流變/傳播模式等。多種流變模式導致西方文論著作版本(變文、異文)大量產生,使各版本之間在正、副文本層面存在著復雜、多元的差異,并折射出其與不同時代、地域、社會、文化、文藝學術思潮、讀者受眾之間的互動關系,也展示出正、副文本中核心術語、關鍵詞、理論意涵的歷史文化變遷。這些最終都不同程度地影響著西方文論文本的研究。
另外,版本在時間上的流變和在空間上的異變,一定程度導致了文論著作的經典化和世界化。一方面,版本在時間維度上的嬗變,持續推動文論著作的經典化;另一方面,版本在空間維度上的跨地域、跨空間、跨語言、跨文化、跨國別異變與傳播(如多個國際—外語語種版本和多個國內—(少數)民族語言版本),促成世界文學理論的生成。細察文論著作的版本史可以看出,世界文學理論的形成幾乎總是與多版本(含譯本)如影隨形、相伴而生的,或者說后者增強了理論的世界性。而最終,版本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上的流變,共同導致世界文學理論經典的生成。這無疑是版本流變在客觀上所生成的重要意義與價值之所在。
再者,文論著作及其所承載的理論進入了文論史(即大歷史、宏觀史、宏大敘事模式的初版本史)序列,同時該著的中外版本譜系自身又形成了一個小歷史(即一個小的書籍史和理論嬗變的微觀史),文論大歷史或主流/干史因小歷史的枝繁葉茂而顯得生機勃勃。這是此前的學界很少意識到或察覺到的(或者說小歷史被大歷史遮蔽了)。因此要改變粗疏、宏觀、簡單的西方文論史觀和史(詩)學思維,要充分認識到其作為“枝葉”的小歷史的復雜性、豐富性、價值與意義性。[25]
而若仔細探查和深入考古,文論著作版本所構成的既開放又封閉的小歷史系譜則折射出內容豐富多彩、形態搖曳多姿的多種亞歷史/子歷史,如該著的書籍史,修訂史,翻譯史,傳播史,閱讀史,闡釋史,批評史,接受史,審美史,思想史,觀念史,經典化歷史,理論演變史,時代和社會變遷史,等等。而這一部部經典文論著作所生成的微觀歷史,又會對長期以來粗線條的、呈宏大敘事的西方文論(主流)歷史書寫構成有效補充,使其更顯具體、豐富、充實、生動,更有寬度、深度和厚度,其可讀性、親和力更強。因而其價值不可小覷。而文論著作自身獨特的話語聲音和個性化身份也由此得以浮出宏觀歷史的地表而得到凸顯,并在接受者心目之中形成清晰、生動的理論印象和詩學面孔,而不致被長期湮沒而失語。而若再進一步細究,可以看出,在每一部著作的系列版本所構成的小歷史中,其中每一個版本自身又形成了一個獨自的、獨特的文化場域、封閉體系和生態系統,是一個獨立的生命有機體(雖然在主體上它是與其他版本血脈相連、精氣相通,歸屬同一個家族譜系),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探究。
還有,從版本小史可以近距離地感知和感受歷史的溫度、深度、厚度、精細度和速度以及理論的生命力,文論家的生活觸感與生命體驗;同時,從版本小史亦可以以小見大,洞幽燭微,可以從一個個版本一窺更為宏大和更為廣闊的社會景觀、歷史風貌、時代畫卷和風起云涌、眾聲喧嘩的20世紀理論及其變遷、際遇、關系和命運。
總而言之,我們在研究一部西方文論著作時,不應該只關注其中一個版本,而應該胸懷多個版本,以文論“善本”為基準,全面透視和掃描整個版本譜系;把單個的版本研究放在整個版本譜系的背景下進行,這樣研究者心中就既有整體,同時又能在全面、發展、互文、關聯的語境中聚焦、研究個案。最后其研究就不會出現以偏概全、停滯不前,或落后于版本及作者思想的發展,甚至得出錯誤結論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