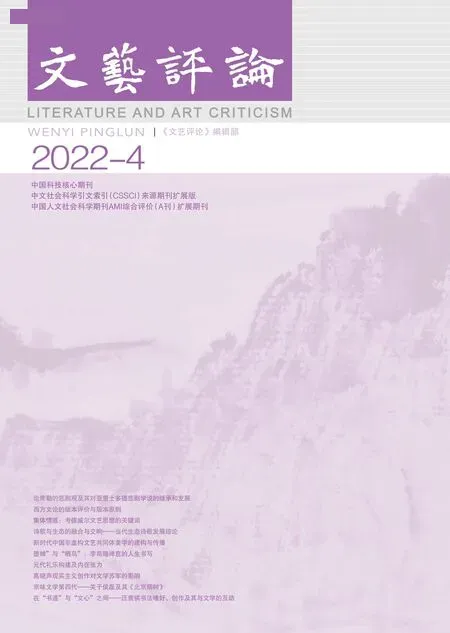論席勒的悲劇觀及其對亞里士多德悲劇學說的繼承和發展
○謝芳 高政
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不僅是一位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德國劇作家,而且還致力于悲劇理論的探討,其悲劇學說在西方悲劇理論史上具有獨特價值和特殊意義。盡管國內學者已對席勒的悲劇思想有所闡釋,但卻未將其與亞里士多德的悲劇學說進行比較研究。本文擬對席勒有關悲劇與現實的關系、悲劇的特征、悲劇接受心理、悲劇的功能等問題的論述進行梳理,探討其對亞里士多德悲劇學說的繼承和發展,并結合席勒所處的時代及其所受的哲學影響等進一步分析其悲劇觀形成的原因,以期對席勒的悲劇觀有更為深入的認識。
一、悲劇與現實的關系
按照席勒的觀點,藝術既是對自然(現實)的模仿,又是對自然(現實)的經過藝術加工的模仿。席勒認為,藝術模仿自然,但此種模仿應將現實生活中雜亂無章的材料作為素材,對其予以藝術加工,從而達到使接受者獲得愉悅的目的。他在《悲劇藝術》(1792)一文中寫道:“藝術通過摹擬自然來實現自己的目的,它完成了實際上使快樂得以產生的條件,并為這一目的,把自然中四分五裂的設施,按照一幅一目了然的藍圖結合起來,以便把自然僅僅視為次要目的的東西,當作最終的目的來完成。”(36)[1]
在席勒看來,作為戲劇藝術的一個種類的悲劇不僅是對現實中人的行動的模仿,而且是對人的行動的詩意的模仿。根據他的論述,悲劇在表現人物的感受和激情的同時,還表現由一系列事件構成的人物行動。他指出:“悲劇是一系列事件的模仿,即一個情節行動的模仿。”(47)席勒認為,悲劇以表現令人感動、使人快樂的行動為目的,為達到上述目的,悲劇作家應該按照自己的需要對所得到的素材進行藝術加工,亦即對人的行動進行詩意的模仿:“悲劇是一個值得同情的情節行動的詩意的模仿……悲劇的目的是詩意的目的,這就是說,它表現一個行動,為的是感動別人,并且通過感動使人快樂。倘若它根據這個目的來處理給它的素材,那么,模仿的時候,它就有它的自由;它有權力,甚至于可以說它有責任使歷史的真實性屈從于詩意的規則,按照自己的需要,加工得到的素材。”(48)
可以說席勒有關藝術模仿自然的看法與亞里士多德的“摹仿說”有著一脈相承之處。亞里士多德在文藝史上首次提出藝術摹仿真實的現實世界的觀點。亞里士多德的“摹仿說”繼承了他的老師柏拉圖的理論,但與柏拉圖不同的是,亞里士多德反對柏拉圖所認為的“現實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摹本,而藝術則是理念世界的摹本的摹本”[2]的觀點,而是轉向唯物主義,肯定現實世界的真實性,進而肯定藝術摹仿真實的世界。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也論及此種摹仿的心理基礎:“人從孩提的時候起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對于摹仿的作品總是感到快感。”[3]此外席勒的“悲劇模仿人的行動”的觀點也繼承了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指出:“悲劇是對于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摹仿。”[4]
在對悲劇與現實的關系問題的論述中,席勒與亞里士多德的不同之處主要在于:1.席勒進一步深化了亞里士多德所認為的悲劇創造性地再現現實的觀點。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悲劇并非表現現實中發生過的事,而是遵循可然律或必然律的原則表現有可能發生的事。盡管亞里士多德所指出的可然律或必然律實際上也涉及劇作家對劇中事件的藝術加工,但是席勒在論及悲劇與現實關系時所說的“詩意的模仿”則更為關注劇作家的創造性及其對藝術規律的遵循,因為他不僅是一位戲劇理論家,而且同時也是一位創作經驗豐富的劇作家。他在1797年4月4日致歌德的信中談及如何處理悲劇素材時也寫道:“藝術的關鍵在于創造一個富有詩意的故事情節……”[5]2.席勒更為強調劇作家的藝術加工、詩意創造應以使接受者(觀眾)受到感動、獲得愉悅為目的。雖然亞里士多德也認為“人對于摹仿的作品(藝術)總是感到快感”[6],“它(悲劇)給我們一種它特別能給的快感”[7],但是他并未將悲劇創作與悲劇的此種功能如此緊密聯系,而是主要借此來反對柏拉圖否定文藝快感的觀點,以此肯定文藝的審美價值。而席勒對藝術加工、詩意創造的最終目的的強調則表明他在探討悲劇的本質問題時不僅僅停留在對悲劇的文學特性的把握上,而是同時也考慮到了悲劇必須面對觀眾表演的特征,亦即悲劇接受,這無疑也是席勒有關悲劇本質問題探討中的一個獨到之處。
二、悲劇的特征
以下我們將從悲劇與敘事文學及抒情詩的差異、悲劇人物、悲劇情節這幾個方面梳理席勒有關悲劇特征的論述。
(一)悲劇與敘事文學及抒情詩的差異
席勒在界定悲劇的特征時,對其與敘事文學和抒情詩的差異進行了探討。他認為,悲劇與敘事文學均可表現人物的行動(一系列事件),二者的不同之處主要在于:悲劇由演員直接表演現在發生的事,舞臺上不存在敘述者,這有助于激發觀眾的興趣和情感,而敘事文學則由敘述者講述過去發生的事,其產生的效果則與悲劇相反。在席勒看來,悲劇和抒情詩的區別則主要在于是否能夠模仿行動。他認為,悲劇不僅可以通過模仿表現人物的感受和強烈的情感,而且也可以表現促使其產生和表露出來的事件,即人物行動;抒情詩雖然也能夠模仿詩人本人和理想人物的情感,但卻不能模仿其行動。
從席勒有關悲劇與敘事文學差異的論述中亦不難看出亞里士多德觀點的影響。亞里士多德認為,悲劇用表演的方式表現一個行動,史詩則用敘述的方式描述過去發生的事情;與史詩相比,悲劇能在更短的時間內表現一個行動,更能引起觀眾的快感。可以說席勒也同亞里士多德一樣指出了悲劇表現行動(事件)的特征、其對觀眾所產生的更強烈的影響以及敘事文學中敘述者的存在及其所描述事件的“過去”性質,只不過亞里士多德更強調悲劇和史詩在表現人物行動時時間上的差異,而席勒則更強調悲劇表演較之敘事文學所具有的當下性。席勒有關悲劇與抒情詩差異的闡述則進一步深化了亞里士多德的觀點。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僅僅提及抒情詩表現個人情感,但席勒卻從“對人的行動的模仿”這一角度出發探究了抒情詩與悲劇的本質區別,并且明確指出:抒情詩不像悲劇那樣模仿人的行動,只能模仿其情感。可以說席勒有關悲劇與敘事文學和抒情詩差異的上述探討也對此后德國戲劇理論的發展產生了一定影響。黑格爾(1770-1831)便接受了席勒的部分觀點,如抒情詩只描寫內心生活、戲劇體詩表現人物行動等,并且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更為深入、詳盡地闡釋。限于篇幅這里就不展開論述。
(二)悲劇人物
按照席勒的觀點,悲劇所表現的人物應是具有普通人特征的有感情、有道德、有弱點的善惡交織的人,而且悲劇還應表現人物的痛苦及其對痛苦的反抗。
席勒認為,悲劇人物首先應顯示出生活中普通人的特性。他在《悲劇藝術》中寫道:“我們同情的對象(指悲劇人物)必須完完全全和我們同類。”(46)按照席勒的論述,這個“對象”亦即“在‘人’這個字的全部意義上的人”(49)。在席勒看來,這樣的人應該表現出感情和道德:“只有像我們自己這樣的有感情有道德的生物,才能激起我們的同情。”(49)而沒有道德的兇惡精靈,不為感情所困擾的靈秀之士(reine Intelligenzen)依席勒之見都不能引起觀眾的同情。根據席勒的說法,悲劇人物還應具有“人的弱點”(49),理想的悲劇主人公應具有善惡交織的性格。他指出:“悲劇詩人特別喜歡善惡交織的性格是有他的道理的,他的理想的主人公正是介于完全墮落和完美無缺的人物之間。”(50)
席勒在論述悲劇模仿人的行動時還寫道:“悲劇是一個情節行動的模仿,這個行動把受苦中的人,展現在我們面前,其目的仍在于引起觀眾的同情。”(49)他在《論激情》(1793)一文中進一步指出,悲劇藝術不僅要表現人的痛苦(Leiden),更重要的是要表現人對痛苦的反抗。在他看來,痛苦是一種感性之物,而悲劇藝術的目的是超越這種感性之物,表現人對痛苦所進行的反抗,從而表現人的理性和內心的自由。悲劇人物所遭受的痛苦的強弱決定了其反抗力量的強弱,所以悲劇人物應該受到巨大的苦難,表現出強大的反抗力量并進而采取行動。
以上所論及的席勒有關悲劇人物應為具有普通人特征的有感情、有道德、有弱點的善惡交織的人的觀點顯然與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完全不同,而這又與他所處的時代密切相關。從古希臘起至17世紀,西方悲劇多以神、圣人、帝王、貴族、英雄為主人公。亞里士多德認為悲劇主人公應該出身高貴,來自于上層貴族階級。他在《詩學》中指出:“這種人(悲劇主人公)名聲顯赫,生活幸福,例如俄狄浦斯、堤厄斯忒斯以及出生于他們這樣的家族的著名人物。”[8]16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結束了中世紀的神學統治,開始肯定人性,這一時期悲劇中的人物身份不再只是神或圣人,但絕大多數仍為帝王和貴族,如莎士比亞悲劇中的人物。17世紀的法國古典主義崇尚皇權,悲劇人物只能以王公貴族的身份出現。而在18世紀的啟蒙運動中,代表階級利益的思想家批判封建意識形態,抨擊教會,提倡平等、自由和民主,引領人們掙脫封建專制的束縛、沖破宗教迷信的羅網,使人類走出蒙昧的狀態,從而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辟道路。這一時期的歐洲戲劇理論家如法國的狄德羅(1713-1784)和德國的萊辛(1729-1781)均否定古典主義以王公貴族為悲劇主人公的原則,狄德羅提倡市民戲劇,萊辛提倡市民悲劇,他們都主張由普通人來擔任戲劇(悲劇)主人公。而在18世紀后半葉的德國,確實也產生了萊辛的《愛米麗婭·迦洛蒂》(1771)以及席勒的《陰謀與愛情》(1784)等表現市民和貴族之間矛盾沖突的著名市民悲劇。由此可見,席勒主張悲劇主人公的身份應是普通人的觀點與狄德羅和萊辛的觀點完全一致,并且帶有歐洲啟蒙運動的時代印記。此外,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悲劇應摹仿比一般人更好的人,“這樣的人(悲劇人物)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入厄運,不是由于他為非作惡,而是由于他犯了錯誤。”[9]而席勒則指出悲劇人物應為與普通人一樣有感情、有道德的善惡交織的人。席勒的上述觀點可以說仍然體現了發端于文藝復興時期、延續到18世紀的啟蒙時期的人文主義思想。人文主義反對以神為本的舊思想,抨擊教會鼓吹的禁欲主義,頌揚塵世歡樂和幸福,主張以“人性”對抗“神性”,肯定人的感情,強調人的品德,并且認為人是有弱點的,“人是具有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軀”[10]。而上述思想無疑在席勒有關悲劇人物的論述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席勒有關悲劇應表現人物痛苦的論述與亞里士多德“悲劇人物應遭受痛苦”的觀點有著一脈相承之處。在亞里士多德看來,突轉、發現和苦難是悲劇情節的不可或缺的三個成分,而苦難則包括悲劇人物所感受到的“劇烈的痛苦”[11]。席勒有關悲劇應表現人物對痛苦的反抗的主張則具有獨到之處,他所提出的人對痛苦的反抗可以展現出人的理性和內心自由的觀點同樣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在席勒所生活的18世紀,以新興資產階級為代表的啟蒙主義者高舉理性的旗幟,在政治、社會、宗教和文學等領域進行思想啟蒙。他們主張在理性的引導下摧毀神權、王權和特權,實現人的權利、自由和平等。他們還希望把潛藏于每個人中的理性召喚出來,使人掙脫任何外在權威的束縛,走出不成熟的依附和奴役狀態,成為敢于運用自己理性的獨立和自由的人。[12]啟蒙時期的上述思想傾向顯然對席勒悲劇觀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三)悲劇情節
按照席勒的觀點,悲劇中的各個事件之間應該具有因果關系,各個事件聯系起來構成一個完整的情節行動。他在《悲劇藝術》中寫道:“悲劇是一個完整的情節行動的模仿。一個個別的事件,無論它多么含有悲劇性,還不能構成悲劇。必須把若干互為因果的事件,按照目的,構成一個整體……”(47)席勒認為,只有完整的情節行動才能發揮悲劇情節的兩個作用:第一,它有助于真實地表現人物的性格、激情等,完整地展示人物內心的變化發展。第二,完整的情節行動一方面可以促使觀眾產生同情心,另一方面可以使觀眾的心靈活動產生持續的變化,并且在使觀眾產生強烈情感的同時增強觀眾的道德感。在席勒看來,完整的情節行動所表現出的人物性格、激情、心理等的真實性有助于使觀眾置身于劇中人物所處的情境,產生受苦的想象,并且對劇中人物產生同情。按照席勒的說法,觀眾為了擺脫觀看悲劇時的痛苦的感情會產生一種道德感,而這又能給予觀眾快感。對于這一問題我們將在下文探討席勒有關悲劇功能的闡述時作更加深入的分析。
在對悲劇情節的論述中,席勒所提出的悲劇中的各個事件之間應該具有因果關系,各個事件聯系起來構成一個完整的情節行動的看法,可以說仍以亞里士多德的觀點為基礎。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指出:“(悲劇)情節既然是行動的摹仿,它所摹仿的就只限于一個完整的行動,里面的事件要有緊密的組織,任何部分一經挪動或刪削,就會使整體松動脫節。”[13]不過席勒對完整的情節行動所產生的作用的闡釋卻較之亞里士多德更為深入。席勒指出完整的情節行動有助于真實、完整地刻劃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而這一點則是亞里士多德——他認為情節布局較之人物描繪更為重要——所忽略的,原因在于啟蒙時期的戲劇理論家較之古希臘時期的更為強調人的地位和價值。此外,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僅僅提及完整的情節行動更能引起觀眾的憐憫與恐懼之情,而席勒則不僅強調它可以促進觀眾產生同情,而且也論及它對觀眾心理變化和道德感的影響。
三、悲劇接受心理——悲劇藝術四要素
席勒在《悲劇藝術》中指出:“一切同情心都以受苦的想象為前提;同情的程度,也以受苦的想象的活潑性、真實性、完整性和持久性為轉移。”(41)在他看來,悲劇要引起足夠的同情,需要使觀眾對悲劇人物的苦難產生活潑、真實、完整、持續的想象。而觀眾的受苦的想象的活潑性、真實性、完整性和持續性便是席勒所提出的悲劇藝術四要素,其所涉及的實際上是觀眾觀看悲劇時的心理。以下我們有必要對其作進一步的闡釋。
(一)活潑性。席勒認為,受苦的想象可以通過兩條途徑獲得,一是“經人敘述或者描寫”,一是“親眼看見”。第一條途徑需要人們通過自己的想象,在眼前浮現出人物的動作和場景。這種途徑只能產生薄弱的印象,不能完全震撼人們的心靈,并且導致其注意力分散,想象其他的事情,進而會削弱人們受苦的想象和感動。而第二條途徑(即悲劇表演)則可使觀眾身臨其境、親身感受,它通過最短的路徑直接打動觀眾的內心,使觀眾獲得更加直觀、具體的感受,對悲劇人物所遭受的苦難產生更強烈、更生動的想象,產生更強烈的同情和感動。席勒指出:“想象越活躍活潑,也就更多引起心靈的活動,激起的感情也就更強烈……”(41)
(二)真實性。按照席勒的觀點,生動活潑的印象還應具有真實性,才能使觀眾產生足夠的同情。而觀眾受苦想象的真實性有賴于悲劇人物(承受痛苦的對象)與觀眾的相似之處,此種相似之處越大,越能引起觀眾的同情。因為這種相似之處使觀眾能夠與悲劇人物互相交換角色,并且感受他們的處境。在席勒看來,此種相似性便是普遍人性。他指出:“這種相似之處涉及心靈的整個基礎。”“倘若這種相似之處涉及全人類都該具有的普遍的和必然的形式,那么,這種真實性就可以和客觀真理同樣看待。”(43)在席勒看來,特定的人性雖然具有主觀真實性,但是觀眾只有處在特定的情況下才能對其產生同情,因此,悲劇應該采用體現普遍人性的題材,從而使觀眾感到與劇中人物的相似性,并對其產生足夠強烈的印象:“它(指悲劇)的最豐富的題材,始終是絕對真實的東西,在人和人的關系中純粹人性的東西,因為悲劇只有采用這種東西,才能保證產生的印象具有普遍性,而且不至于削弱印象的強烈程度。”(44)而觀眾對劇中人物的強烈印象顯然同樣有助于前者對后者產生同情。
(三)完整性。在席勒看來,悲劇應該完整地描述悲劇人物所處的外部環境、內心感受以及它們的因果聯系,這不僅可使悲劇描述顯得真實,而且也能使觀眾充分體會到其與劇中人物所處外部環境和內心感受的相似之處,并進而產生受苦的想象。席勒指出:“如果沒有這種完整性,對于描述的真實性也根本不可能做出判斷來,因為我們必須充分認識環境的相似之處,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對感覺的相似做出正確的判斷,也只有外部和內部的條件互相結合起來,才能從中產生激情。”(44)此外,席勒還認為,悲劇應該以表演的形式,即以使觀眾“親眼目睹”的方式,而不是敘述的形式,表現完整的悲劇行動,直接激發觀眾受苦的想象。
(四)持續性。席勒認為,悲劇應該使觀眾持續地沉浸在受苦的想象中,從而使他們獲得高度的感動。按照他的說法,觀眾受苦的想象是一種強制狀態,十分容易消失,因此必須防止這種情況發生。為此悲劇應該盡量避免單靠刺激感性印象的方式使觀眾保持受苦的想象,因為這種方法不能持久地維持觀眾的同情,反而會使其因感受功能受到過猛的刺激而導致其心靈的自動反抗,即使觀眾喪失同情。按照席勒的說法,劇作家應該不時打斷觀眾受苦的想象,甚至用相反的感受來轉換觀眾的痛苦感受,從而使此種感受再次出現時更為強烈。他指出:“如果要使心靈……持續束縛在痛苦的感受上面,就必須把這種感受非常聰明地不時打斷一下,甚至于用截然相反的感受來代替,使這種感受再回來的時候威力更大……”(45)席勒認為,感覺轉換是使觀眾克服感覺疲勞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劇作家應該將主要情節和次要情節相結合,以次要情節轉換觀眾受苦的感受,以被打斷的主要情節“逐漸推進”“層層加深”地激起觀眾最高的感動。
席勒從觀眾的心理感受出發,以引發觀眾受苦的想象和同情為目的,并且結合自己的戲劇創作經驗,總結出了悲劇藝術不可缺少的四要素。包括亞里士多德在內的席勒之前的西方戲劇理論家均未在這方面作出過如此深入地探討,可以說悲劇藝術四要素論是席勒對西方悲劇理論的一大貢獻。
四、悲劇功能
在席勒看來,悲劇主要有以下兩種功能:
第一,悲劇引發人(觀眾)的同情和感動。他在《悲劇藝術》中寫道:“而特別把同情的快樂作為自身目的的藝術,是在最一般意義上的悲劇藝術……悲劇藝術是在那些特別能引起人們的同情與感動的情節中摹擬自然。”(36)在席勒看來,以下兩種情況會引起觀眾強烈的不快之感,削弱觀眾對悲劇人物所產生的同情:其一是悲劇人物由于自身不可原諒的過失或者智力薄弱、膽小怕事導致的不幸,其二是悲劇人物品行敗壞,所做的窮兇極惡的事情導致了巨大的痛苦。按照席勒的說法,下述兩種情況則有助于激起觀眾的同情:1.災難的發生是由于“環境所迫,不得不然”(38)。這意味著悲劇人物的痛苦不是由于他做了不道德的事,而是由外在的客觀環境所造成的。因為受難者沒有違背道德,所以受難者遭受的苦難所引起的觀眾的同情便不會減弱。如果受難者和引起苦難的人都沒有違背道德,那么二者均會使觀眾產生更強烈的同情。2.悲劇人物的行動恰恰是由于符合道德才引發了災難。席勒認為這種情況較之上一種情況能引起更多的感動。他指出:“還有一種感動超過這種感動(即以上第一種情況引起的感動),那就是災難的原因不僅不和道德相悖,甚至于還正因為合乎道德,才可能發生這場災難……”(39)席勒以高乃依的《熙德》為例對這種情況予以了分析。在該劇中,男主人公羅德里格與女主人公施梅娜相愛,但雙方的父親因爭奪太師職位結仇,羅德里格的父親被施梅娜的父親打了一記耳光。羅德里格為維護家族榮譽,表達對父親的孝心,奉父親之命與施梅娜的父親決斗并且殺死了他。而施梅娜同樣由于榮譽感和孝心請求國王處死羅德里格。二人雖是戀人關系,但他們為了履行各自的道德義務,不惜犧牲自己的愛情,自愿受苦。在席勒看來,《熙德》的男女主人公能引起觀眾最高的敬意和最大程度的同情。
第二,悲劇引發人的快感,使人獲得愉悅。席勒在《悲劇藝術》中寫道:“然而悲劇的目的是詩意的目的,這就是說,它表現一個行動,為的是感動別人,并且通過感動使人快樂。”(48)他認為,生活中快感的根源在于追求幸福的沖動的滿足和道德規律的實現:“我們知道的快感的根源,不外二種:追求幸福的沖動的滿足和道德規律的實現;一種快樂,如已證明不是出于第一種根源,就必然出于第二種根源……”(34)在席勒看來,藝術必須通過道德的途徑才能使人產生快感,他在《論悲劇題材產生快感的原因》(1791)一文中指出:“引起這種愉快(源于道德本性的愉快)是一種必須通過道德手段才能達到的目的,因此藝術為了完全達到愉快,它的真正目的,就必須通過道德的途徑。”(17)他認為,藝術所給予人的快感是一種精神上的快樂,一種理性的自由的快感。這種源于道德本性的快感不同于感官上的快樂,而感官上的快樂不屬于藝術。根據席勒的說法,悲劇題材雖然使觀眾在感情上痛苦,但卻在道德上感到快樂。他通過實例探討了以下幾種使人得到悲劇快感的情況:如悲劇人物寧愿讓烈火燒死,也不想辜負愛人以換取王位;悲劇人物寧可犧牲生命,也不違反道德,他的生命作為達到道德的手段而存在;罪惡之徒對所犯的罪行感到后悔,受到良心譴責而感到痛苦。席勒認為有些悲劇人物的行為雖然違反天性,逾越一種較低的道德,但卻符合一種更崇高、更普遍的道德原則,這也會使人產生道德上的快樂:如兒子為了履行公民的義務而忽視母親的請求,身為司令官的父親為了祖國的利益而犧牲兒子的生命,身為共和主義者的哥哥為了共和國的利益而殺死心愛的野心勃勃的兄弟等。
顯而易見,席勒在論及悲劇功能時所說的悲劇可以引發同情和快感的觀點,與亞里士多德對悲劇功能的闡釋大體相似。亞里士多德認為,悲劇引起人的“憐憫與恐懼之情”,而這又能給予人快感。只不過除了“憐憫”(“同情”)這種情感,亞里士多德還指出悲劇可以引發觀眾的恐懼之情。此外,他還強調了悲劇的凈化作用,認為悲劇“借引起憐憫和恐懼來使這種情感得到陶冶”[14]。(按照一般的解釋,這是指觀眾在觀看悲劇時所產生的憐憫與恐懼可使其此類情感得到宣泄,從而使其獲得心理健康)與亞里士多德不同的是,席勒不僅對阻礙和有利于觀眾產生同情的情形做了較多分析,而且也對悲劇之所以使觀眾產生快感的原因予以了深入闡釋,而這無疑又充分體現了席勒對亞里士多德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席勒上述兩方面的探討基本上均涉及道德層面,對道德法則給予了高度關注,而道德法則在他看來實際上代表著理性的力量,從中不難看出啟蒙時期德國哲學家康德(1724-1804)對其思想上的影響。按照康德在其倫理學著作《實踐理性批判》(1788)一書中的觀點,道德法則是一種先驗的理性原則,是普遍的、無條件的、人人都應遵從的“絕對命令”。
結語
本文從悲劇與現實的關系、悲劇的特征、悲劇接受心理、悲劇功能這四個方面闡釋了席勒的悲劇觀,探究其對亞里士多德悲劇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并對其悲劇觀形成的原因予以分析。在對悲劇與現實關系的論述中,席勒進一步深化了亞里士多德提出的悲劇創造性地再現現實的觀點,更為關注劇作家的創造性及其對藝術規律的遵循——因為作為戲劇理論家的席勒同時也是一位創作經驗豐富的劇作家,并且更為關注悲劇接受,主張悲劇模仿應以令人感動、使人愉悅為目的。席勒在界定悲劇的特征時,比亞里士多德更為強調悲劇表演較之敘事文學所具有的當下性,并且從“對人的行動的模仿”這一角度出發探討了抒情詩與悲劇的本質區別。席勒有關悲劇人物應為具有普通人特征的有感情、有道德、有弱點的善惡交織的人的觀點顯然與亞里士多德所持有的悲劇主人公應“名聲顯赫”、出身高貴、“比一般人更好”的觀點完全不同,而這又與席勒所處的提倡平等、自由和民主,強調以“人性”對抗“神性”的啟蒙運動時代密切相關。如果說席勒有關悲劇應表現人物痛苦的論述與亞里士多德的看法有著一脈相承之處,那么他所提出的悲劇應描繪人物對痛苦的反抗,從而展現人的理性和內心自由的主張同樣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席勒對悲劇情節的論述以亞里士多德的觀點為基礎,但卻對完整的情節行動的作用作了較之亞里士多德更為深入的闡釋。在悲劇接受心理方面,席勒總結出的悲劇藝術四要素具有獨創性,是對西方悲劇理論的一大貢獻。在悲劇功能方面,席勒有關悲劇可以引發觀眾的同情和快感的論述與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大體相似,不過席勒從體現理性力量的道德的角度出發——從中不難看出康德哲學對其思想上的影響,對阻礙和有利于觀眾產生同情的情形做了較多分析,而且對悲劇之所以使觀眾產生快感的原因予以了深入探討。總的來看,席勒的悲劇觀既繼承了亞里士多德的悲劇學說,又對其有所發展,并且具有獨到之處,而這些顯然與其悲劇創作經驗、其所處的時代及其所受的哲學影響等因素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