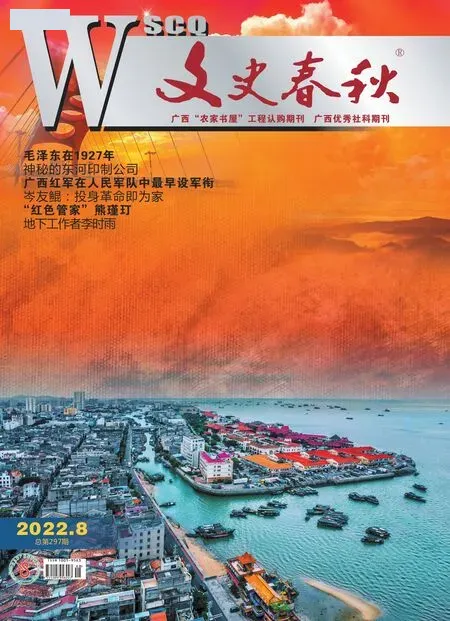巴金與『人間三部曲』的創作
● 顏坤琰
抗日戰爭時期,巴金旅居重慶,惜時如金,筆耕不輟,成績不菲。累累碩果中,“人間三部曲”——中長篇小說《憩園》《第四病室》《寒夜》是巴金文學創作的又一座高峰,令文學界和廣大讀者矚目、贊賞,可謂寫絕了“大時代的小人物,以小人物折射了大時代”。
《憩園》
1941年1月初和1942年5月初,巴金先后兩次從重慶回到故鄉成都,第一次住了50天,第二次住了3個月左右。重歸故里,有兩件事讓他難以忘懷。一是五叔之死,那是第一次回家后不久的事。在親屬陪同下,他到停柩的破廟里看了一眼,不是去行告別禮,而是去看他的下場。五叔早年長得清秀,人也聰明,受到祖父特別的寵愛。他早年喪母,交了壞朋友,染上吃、喝、賭的惡習。祖父知道后,痛罵他一頓,讓他跪在地上自扇耳光。為了過關,他賭咒發誓要痛改前非,出門又依然故我,最后被妻兒從家里攆了出去。他不愿也不會自食其力度日,仍舊偷、騙、討、混,直到成為真正的慣賊被關了起來,最后瘐死獄中。二是祖屋的變遷。他家的祖屋在成都正通順街,屋后的花園就叫“憩園”。這房子早已賣出,并且數易其主,曾做過中學的校舍,當時是保安處處長的公館。門楣原本沒有題字,后來題為“怡廬”,再后來改題為“藜閣”。大門前一對石獅子被搬走了,“國恩家慶,人壽年豐”的對聯也沒有了,但大門內照壁上的“長宜子孫”4個篆體字還是原封不動。面對著這幾個字,回想起這個大家族子孫的種種結局,巴金感慨萬千。重回故鄉的感觸,促使巴金創作《憩園》。
1944年5月8日,巴金與蕭珊在貴陽花溪完婚后,他便送蕭珊去重慶旅游,自己則留在貴陽,準備做完“鼻中隔矯正”手術后去桂林繼續寫作。在貴陽期間,巴金開始了《憩園》的創作。此時,蕭珊連連來信,催促巴金回重慶,說是老朋友馬宗融、靳以期待他們的重聚。于是,6月下旬,巴金收拾行囊,帶上正在撰寫的《憩園》手稿,匆匆地踏上旅途。
巴金的寫作習慣是文思泉涌時,恨不得一口氣就把小說寫完,《憩園》的寫作也不例外。即使在旅途中,他也不放棄任何一點可用之機。筑渝道上,他隨身攜帶一錠墨、一支小楷筆和一疊當作稿紙用的信箋,每到一站,巴金就在客棧里找個碟子或茶碗蓋,倒點水,磨起墨,繼續寫《憩園》。車子經過婁山關,到達桐梓縣城時,夜幕降臨。當晚,巴金借住在車站附近的一戶人家,簡單的晚餐后又急忙點燃一支隨身攜帶的蠟燭,展開手稿繼續筆耕,直到三更。

成都巴金故居原址
陳丹晨所寫的《巴金全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記載,當時巴金搭乘的郵政車抵達長江之濱的重慶海棠溪汽車站時,已是傍晚。巴金見到了正在車站翹首以待的蕭珊,她追上剛剛停穩的汽車,在車窗外微笑著,不停地向巴金招手。到重慶后,巴金曾去北碚與馬宗融、靳以聚會,白天幾個朋友一起暢談離情別緒,晚上巴金在沒有電燈照明的旅館里,依然對著昏黃搖曳的燭光,專心致志地寫了起來,直到蠟燭燃盡。他雖然意興不減,但想找一支新燭竟不可求。
巴金回重慶后,住在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擔任該社的義務總編輯。白天坐在辦公室處理出版社的一些雜務,接待來訪的朋友,晚上,巴金就在樓梯下的那間小房子里不停地寫作。他們的好友楊苡曾來出版社看望他們,同行的還有她的丈夫、詩人趙瑞蕻。大家便擠住在出版社里。趙瑞蕻與經理田一文同睡,蕭珊和楊苡同睡,巴金自己則在辦公室通宵達旦地寫作。
《憩園》完稿后,巴金將手稿拿給蕭珊、田一文閱讀,希望他們提出修改意見。之后,巴金又對手稿再三斟酌修改。重慶市圖書雜志審查處對該手稿進行了嚴格審查,“裝訂成一本的西式信箋的每一頁上都蓋了審查處的圓圖章”(李存光:《巴金研究資料》上冊,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小說《憩園》,便是根據這個手稿排印的。
《憩園》借著一所公館的線索,寫出了舊社會前后兩家主人的不幸故事。由于作品中的“憩園”是以巴金的故居李公館為藍本,老主人楊老三的原型就是巴金的五叔李道沛,因而,他著筆的時候,對失而復見的故居和死于非命的五叔感情十分復雜,憤恨中夾雜著感慨,鞭撻中蘊含著惋惜。巴金所抨擊的是一種傳之久遠而許多人卻不知其害的傳統觀念,一種觸目驚心而又為許多人習以為常的沉重的生活習俗。從這個意義上說,《憩園》既是《激流》在20世紀40年代的續編,又是一部新的《家》。作品的主旨并不在于揭露封建專制的罪惡,也不僅僅是為頹敗中的舊封建家庭唱挽歌,巴金曾多次重申,自己的創作意圖是給人間添一點溫暖,揩干每只流淚的眼睛,讓每個人歡笑。
《第四病室》
1944年秋,巴金的朋友趙家璧因在桂林的出版事業慘遭兵燹,轉而來到重慶準備重振旗鼓。巴金答應為他寫一部長篇,以表支持。于是,巴金停下剛剛開了頭的《寒夜》,動手另撰新作——《第四病室》。《第四病室》取材于他前一年在貴陽中央醫院第三病室里的經歷。
當時,巴金住的小屋條件極差,居住和寫作環境實在不盡如人意,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經理吳朗西和夫人柳靜便邀請巴金搬到沙坪壩去住。
吳朗西不僅在沙坪壩正街開辦互生書店,他還是沙坪壩消費合作社的總經理,又是四川和成銀行沙坪壩辦事處的主任。為解決員工的住宿問題,吳朗西在沙坪壩廟灣建造了合作新村。合作新村共蓋有兩棟房舍,一棟是平房,另一棟是樓房。吳朗西家住在平房的一個院子里。
在吳朗西夫婦的多次邀請下,巴金于1945年5月初遷來廟灣,柳靜把樓房底層的大房間騰給他們居住。巴金回憶當時的情景說:“房間是泥土地,樓下一大間,空蕩蕩的,我白天寫,晚上也寫,燈光暗,蚊子蒼蠅都來打擾。我用葵扇趕走它們,繼續寫下去。字寫得大,而且潦草,一點也不整齊。這說明我寫得急,而且條件差。我不是在寫作,我是在生活,我回到了一年前我在中央醫院三等外科病房里過的日子。”(閻煥東:《巴金自敘》,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此時,趙家璧的良友復興圖書公司已經辦起來了,他不能失信于這位相交多年的朋友,于是,巴金在這里夜以繼日地寫作。在緊張工作之余,他們也常和吳朗西的一雙兒女玩耍,放松一下心情,緩解疲勞。當時買不到稿紙,巴金便買了兩刀記賬用的紙,這種紙質量低劣,只能寫毛筆字。但巴金寫得很順暢,如行云流水般的歡快,因為他寫的都是親身經歷過的情景,不加修飾,不添枝葉。巴金盡可能寫得樸素、真實。他只把發生故事的貴陽中央醫院第三病室改成“第四病室”,其余的皆原汁原味,甚至連醫生、護士用床位號碼稱呼病人的習慣,巴金也保留下來。
巴金在小說中塑造了一位善良而有人情味的年輕女醫生楊木華,她尊重患者,把病人“看作一個人,一個朋友,一個兄弟一樣的人”。楊木華是巴金理想中的人物,她的形象寄托了巴金的希望,也使那充滿凄涼郁悶的病室中“閃爍著一線亮光”。
巴金是把《第四病室》當作中國社會的縮影來寫的。他有意通過這部作品,揭開抗日戰爭后期大后方黑暗社會的爛瘡。作品描寫的病人們的種種遭遇和痛苦,正是當時國民黨統治區人民苦難生活的寫照,正如巴金后來所說:“這小小的病室跟蔣介石統治下的地區是分不開的:在這里發生的事在外面也一樣地發生。”(李存光:《巴金傳》,團結出版社,2018)
巴金花費近兩個月的時間完成了《第四病室》的寫作。7月下旬,巴金夫婦又從沙坪壩廟灣回到市區的民國路。
《寒夜》
1944年初冬,桂林淪陷,正面戰場迎來了湘桂大撤退、侵華日軍攻占貴州獨山的嚴峻形勢。重慶頓時人心惶惶,巴金南下桂林的計劃也化為泡影,因此,他只得在重慶埋頭工作。當時,他住在重慶民國路21號文化生活出版社樓梯下一間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里,正在校對一部朋友翻譯的高爾基的長篇小說;有時也為幾位從桂林逃難出來的朋友做點小事。
在秋冬之際的一個寒夜,空襲警報剛剛解除一兩個小時,巴金開始了長篇小說《寒夜》的寫作。此時,蕭珊已到成都老家探望親人,巴金獨處陋室,潛心寫作。
巴金早就在心里醞釀著要寫一部講述知識分子在大后方遭遇的小說。這題材是他近年來從自己的生活中感受到的,他對此太熟悉了。他的朋友一個接一個地在貧病交加中離世,巴金在悲憤之余思索著這究竟是為什么。王魯彥長期患肺病,還要拼命寫作、教書、編刊物以養活一大家子人,巴金最后一次見到他時,這位43歲的壯年漢子走路卻要拄手杖,嗓音已經喑啞,聽說去世前他已不能說話,只能用搖鈴代替語言,最后寂寞地死在桂林鄉下。陳范予把一生都奉獻給了科學研究與教學,他患病后期,生活不能自理,咽喉劇痛,聲音啞失,形銷骨立,無錢醫治,最后病逝于武夷山。巴金還聽說他的一位表弟在患肺病后期,因不堪忍受病痛折磨,幾次要求家人讓他自行了斷殘身。這些身世凄涼、一生為社會默默奉獻的友人的面影,時時在他腦際浮現,令他難以忘卻。巴金自己又何嘗不是在那黯淡、陰冷的屋子里,從早到晚編書、校對、寫作,像他那些朋友一樣,在坎坷艱難的人生路上消磨著自己?他想,如果他早年患過的肺病這時復發,不也會面臨和這些朋友一樣悲慘的結局嗎?他感到不寒而栗。
《寒夜》描寫的是1944年冬季到1945年年底重慶一名小職員汪文宣凄慘的家庭悲劇。小說人物是虛構的,背景和某些事件、情節卻是真實的。巴金說:“我寫汪文宣,寫《寒夜》,是替知識分子講話,替知識分子叫屈訴苦,在當時的重慶和其他的國民黨統治區,知識分子的處境很困難,生活十分艱苦……那一段時期的確是斯文掃地。我寫《寒夜》,只有一個念頭: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巴金:《關于〈寒夜〉》)巴金的寫作條件極差,住在樓梯下只有幾平方米的小屋里,晚上又常常停電,必須預備蠟燭來照亮書桌;午夜還得拿熱水瓶向叫賣“炒米糖開水”的老人買一點白開水解渴。他睡得遲,但老鼠卻不讓他安生,整夜不停地在那三合土的地下打洞,弄得他輾轉難眠。白天屋子外面傳來的叫賣聲、吵架聲、談話聲、戲院里的鑼鼓聲,混成一部惱人的交響樂,即使關在小屋里,巴金也難得安寧。雖然周遭環境如此惡劣,但巴金仍然心無旁騖地勤奮寫作。
1945年1月14日,疾病纏身的好友繆崇群病逝于北碚。巴金前去他的新墳憑吊,痛感又一位摯友的離世。繆崇群是一位散文作家,出版過幾本集子,與巴金交往甚篤,他長期患著肺病,當時住在北碚,在官辦的正中書局工作。據說他生病躺在宿舍時,連一口水也喝不到;在醫院斷氣時,也無人在場。巴金覺得繆崇群也是一個汪文宣,他要把這些朋友的身世作為素材寫入書中。《寒夜》主人公汪文宣,在一個“半官半商”的圖書公司里當校對,這個圖書公司就是以繆崇群工作過的正中書局為模子。巴金筆下的汪文宣,就是像繆崇群這樣忠厚、善良的小知識分子,工作辛苦,薪酬、地位都很低,受盡損害和侮辱,卻不敢反抗。他寫的汪文宣一家的故事,正是當時這些貧困知識分子家庭生活的集中表現。
寫作《寒夜》時,巴金把自己置身于作品的環境氛圍之中,汪文宣仿佛就是他的鄰里,他們同住在一幢大樓里,走過同樣的街道,聽著同樣的市聲,接觸同樣的人物。在這座大樓的大門口,在民國路和附近幾條街道,人們躲警報、喝酒、吵架、生病……這一類凡人瑣事,每天都在巴金身邊發生。物價飛漲,生活困難,民不聊生,戰場失利,人心惶惶……不論走到哪里,甚至坐在小屋內,巴金仿佛也聽得到一般小人物的訴苦和呼吁。他好像活在自己的小說中,整個故事似乎就在他的周遭進行著。在這動蕩不安的社會中,知識分子的遭遇和他們的心態,巴金是十分熟悉的:冷酒館是他熟悉的,咖啡店是他熟悉的,“半官半商”的圖書公司也是他熟悉的……小說中的每個地點他都熟悉,所以他寫得很真實。巴金每天都要在民國路一帶來來回回走好幾遍,邊走邊思索,他在回想這8年的生活,回想最近友人發生的事情,好像在經歷著一幕幕悲歡離合的苦戲。他感到了幻滅,感到了寂寞,于是他便回到小屋里,像若干年前寫《滅亡》那樣,借紙筆傾吐自己的感情,所以寫得很暢快,也很順暢。但沒寫幾頁就因時局突變,他必須去參加一些不能缺席的抗日救國運動與社會活動而輟筆,《寒夜》的寫作不得不中斷。
《寒夜》全書30章,巴金在重慶究竟完成了多少章節?“小說的三分之二是回到上海之后完成的”(陳瓊芝:《生命之華·巴金》,鷺江出版社,2003),這樣說來,巴金在重慶寫了大約10章。但巴金自己則說:“直到這年(1946年)六月,我第二次回上海見到健吾,他提起我的小說,我把已寫好的八章重讀一遍,過幾天給他送了去。《寒夜》這樣就在八月份的《文藝復興》二卷一期開始連載了。”(巴金:《關于〈寒夜〉》)巴金是1946生5月21日乘飛機離開重慶回上海的,兩周后他就將經過校改的手稿交到李健吾手上,應該說這前8章是巴金在重慶完成的,約為這部小說的四分之一。整部書稿于1946年12月31日在上海殺青。
《寒夜》是巴金創作生涯中最后一部長篇小說,作品以抗日戰爭后期的重慶為背景,用沉痛悲涼的筆調,描寫了一個在“半官半商”的圖書公司的總管理處做校對工作的小職員汪文宣的家庭悲劇。它通過一個渺小的讀書人的生與死,對社會現實做了真實冷靜的描寫、細致入微的病理解剖。《寒夜》結構縝密,是抗日戰爭勝利前后國民黨統治區社會底層知識分子苦難生活的真實寫照,同時也是巴金此時失望而沉重的心情的真實坦露,是他在藝術上達到爐火純青、老道圓熟的扛鼎之作,它跟《家》和《憩園》,稱得上是巴金創作的3座高峰,也是他自己最喜歡的3部作品。巴金后來表示:“《寒夜》明明是在宣判舊社會、舊制度的死刑。我指出蔣介石國民黨的統治已經徹底潰爛,不能再繼續下去。舊的滅亡,新的誕生;黑暗過去,黎明到來。”(周立民、李秀芳、朱銀宇編:《〈寒夜〉研究資料選編》上冊,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