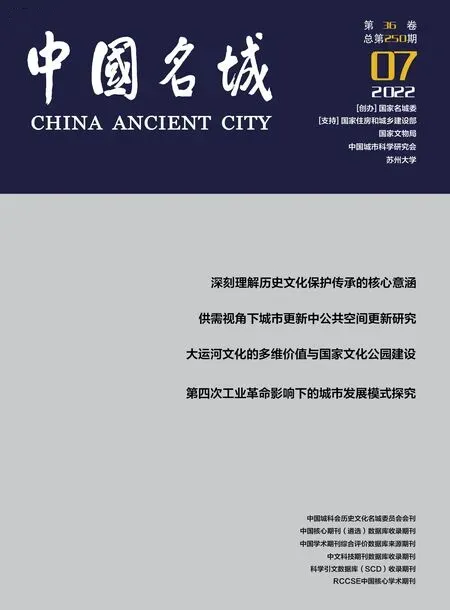文化地景的跨界建設(shè)
——以山東三德范遺產(chǎn)保護(hù)為例
楊建平,吳宗杰
引言
近幾十年來,隨著城鎮(zhèn)化的快速推進(jìn),大量的傳統(tǒng)村落急速消亡。鄉(xiāng)村文化的保護(hù)利用與恢復(fù)重構(gòu)已成為非常緊迫的現(xiàn)實(shí)問題。關(guān)于鄉(xiāng)村文化保護(hù)與利用模式的研究視角有:社區(qū)保護(hù)理論、鄉(xiāng)村建筑與景觀保護(hù)、旅游開發(fā)等。其中文化景觀的研究多集中在鄉(xiāng)村地域文化景觀的特征、景觀的變化、景觀的保護(hù)三大方面,針對(duì)如何構(gòu)建文化景觀研究較少。國家新型城鎮(zhèn)化戰(zhàn)略明確提出要傳承和弘揚(yáng)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推動(dòng)地方特色文化發(fā)展,保存文化記憶,讓人們“記得住鄉(xiāng)愁”。在此背景下,鄉(xiāng)村文化研究開始更多地轉(zhuǎn)向地方性與地方認(rèn)同、地方依戀城市(鄉(xiāng)村)記憶和“鄉(xiāng)愁”等研究話題。關(guān)于文化地景的構(gòu)建也有了新的探索,例如何方對(duì)青山胡同進(jìn)行了記憶在地化的研究,通過用書寫地方文化的方式來建構(gòu)地方意義,營造鄉(xiāng)愁空間與文化地景。
本文以齊長城為背景,挖掘并描述了從錦陽關(guān)到三德范沿線村落的鄉(xiāng)村文化景觀。以國家級(jí)傳統(tǒng)文化村落三德范為樣本,探討鄉(xiāng)村文化地景的書寫方式與構(gòu)建思路。
三德范是章丘唯一的國家級(jí)傳統(tǒng)村落,在章丘南部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該村莊面積大,姓氏繁多,歷史構(gòu)成不一。章萊官道穿村而過,是商旅、軍事和文化的走廊。域內(nèi)廣宗城是最早可追溯的建制城邑,可上溯至南朝(公元420—589年)劉宋皇朝。三德范則被認(rèn)為是春秋戰(zhàn)國時(shí)期遺留下來的地名。明清以來,在這塊土地上,逐漸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祠祀場所,其建置可與一邑之城相比。村中保留有清朝時(shí)期修建的圍子墻,其功能可視同城墻。巷道民居則是在此框架里形成的“肌理”。研究從社稷建置與胡同里巷入手,讓文化記憶在視覺景觀的書寫里得到表達(dá)。在每項(xiàng)地景的文化敘事上,突破傳統(tǒng)遺產(chǎn)學(xué)中無形與有形的界限,以“文化記憶在地化”作為一種新的書寫和表征方式,讓無論是文獻(xiàn)記載的,還是口耳相傳的歷史記憶、真實(shí)故事或者是虛構(gòu)的傳說都得到實(shí)實(shí)在在的場所寄托。緊緊圍繞具體的“場所”,將歷史事件、人物、記憶、傳說等精神層面的東西,進(jìn)行一種視覺化的在地?cái)⑹拢蛊涑蔀橐环N書寫在大地上的遺產(chǎn)。
1 地景概念:由名勝到日常
地景的概念經(jīng)歷了由作為“風(fēng)景”的代名詞到探索文化作為地景的發(fā)展過程,其研究主體也由作為審美對(duì)象的景觀轉(zhuǎn)化為景觀背后的文化內(nèi)蘊(yùn)。從20世紀(jì)80年代開始,文化地景的遺產(chǎn)價(jià)值開始顯現(xiàn),并進(jìn)入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的范疇。1992年,在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遺產(chǎn)委員會(huì)第十六屆會(huì)議上, 具有突出普遍價(jià)值的“文化地景”被納入《世界遺產(chǎn)名錄》。伴隨著西方遺產(chǎn)保護(hù)觀念從以物為本到以人為本的轉(zhuǎn)變,文化地景的范疇也變得更廣,不但包含紀(jì)念物與歷史名勝,而且包含日常生活景觀。對(duì)后者的關(guān)注在世界文化遺產(chǎn)名錄中也有體現(xiàn),比如1995年菲律賓的科迪勒拉水稻梯田被作為文化景觀列入世界文化遺產(chǎn)名錄。
文化地景構(gòu)建是批判遺產(chǎn)研究的重要內(nèi)容。20世紀(jì)末,遺產(chǎn)學(xué)界開始批判性地審視遺產(chǎn)的意義、遺產(chǎn)與文化的關(guān)系,進(jìn)而重新思考遺產(chǎn)化的過程。遺產(chǎn)與文化地景不再是一成不變的研究對(duì)象,而被看作是一個(gè)過程,是“活的歷史”“活的遺產(chǎn)”,其概念包含人們的地方感、傳統(tǒng)知識(shí)及其傳承,文化生產(chǎn)中的平等、開放與創(chuàng)新以及對(duì)自然資源與文化傳統(tǒng)的守護(hù)。活態(tài)遺產(chǎn)是地方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資源這一理念也為遺產(chǎn)管理與利用開辟了新的思路。
在此背景下,國際上的遺產(chǎn)管理與實(shí)踐開始越來越多地關(guān)注遺產(chǎn)背后的價(jià)值觀、身份與地方感等問題。而文化地景作為一個(gè)過程,其構(gòu)建也越來越受到西方學(xué)者的關(guān)注。在1992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出的文化地景3種類型中,“逐漸形成的文化地景”即強(qiáng)調(diào)地景演變的持續(xù)過程。泰勒在東亞與東南亞地區(qū)關(guān)于文化地景的研究表明,在東亞與東南亞,文化地景折射的是人與環(huán)境的互動(dòng),反映的是與其價(jià)值觀相關(guān)聯(lián)的文化過程。其中地方的價(jià)值觀在地景的形成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兩者密不可分。中國學(xué)者段清波也指出:“文化遺產(chǎn)對(duì)人類而言具有更加深層次的思想價(jià)值和動(dòng)力價(jià)值。核心價(jià)值‘活起來’是文化遺產(chǎn)‘活化’的主要內(nèi)容、唯一途徑和根本目標(biāo)。”要讓核心價(jià)值活起來,首先要挖掘地方的核心價(jià)值,進(jìn)而構(gòu)建起真正反映地方文化的地景。
2 地方:文化的永恒支點(diǎn)
作為文化遺產(chǎn)、地理學(xué)和城市與自然景觀設(shè)計(jì)等領(lǐng)域的重要概念,在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發(fā)布的與遺產(chǎn)有關(guān)的文件里,“文化地景”被定義為“是自然和人類的共同作品,它體現(xiàn)了人類與其自然環(huán)境之間悠久而密切的關(guān)系”。“文化地景是經(jīng)由一個(gè)文化群體對(duì)自然景觀之作用而形成的。文化是作用者,自然是媒介,而文化地景是其結(jié)果。”文化地景將通行的物質(zhì)和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當(dāng)作“地方”來融合和詮釋,在《巴拉憲章》對(duì)“地方”的定義中,“地方”意指場所、地區(qū)、土地、景觀、建筑物(群)或其他作品,同時(shí)可能包括構(gòu)成元素、內(nèi)容、空間和景致。地景可以大到成片的山脈、河流,也可以小到一石、一木、一井。它可以是胡同里的一個(gè)拐角,也可以是歷史悠久的古建筑。地景的質(zhì)地或稱元素可以是建筑風(fēng)格、山坡植被、河道曲線,或者是門枕石、墻磚等的紋理。不管地景以何種形態(tài)存在,它有一個(gè)關(guān)鍵的特點(diǎn),就是總能找到一個(gè)可落地之處。這個(gè)“地方”可能經(jīng)歷了幾百年、幾千年,甚至上萬年的變遷,上面可移動(dòng)或不可移動(dòng)的文物不斷更替,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反復(fù)出現(xiàn)和消失,但“地方”卻是永恒的支點(diǎn),它來自遙遠(yuǎn)的過去,必將繼續(xù)走向未來。用地景而非遺產(chǎn)、古建筑、非遺、故事、傳說、文化等當(dāng)下流行的詞語去描述村落的歷史文化資源,是因?yàn)檫@些概念僅僅涉及文化的某一個(gè)方面,且有些很難落到場所規(guī)劃中。地景緊緊抓住“地方”、場所這一支點(diǎn),包含了上述所有文化特征,并給它以可落地、可利用、可物化、可創(chuàng)新的可能性,同時(shí)不失其歷史面貌和文脈。地景聚集了在這里發(fā)生和講述的一切歷史人物和事件、建筑、故事傳說、歷史記載、文物遺存,以整體貫通的方式再反哺“地方”,使其成為一種歷史景觀、一種可以持續(xù)利用和創(chuàng)新的鄉(xiāng)村文化資源、一種規(guī)劃設(shè)計(jì)的思路。比如在描述三德范北頭廟時(shí),既呈現(xiàn)了過去的建筑形態(tài)、宗教、民俗活動(dòng)、歷史人物、現(xiàn)存的石碑、文獻(xiàn)記載、相關(guān)典故和神話傳說,同時(shí)也展示當(dāng)下的樣貌、歷史變遷和今人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這里有物質(zhì)的也有非物質(zhì)的文化遺產(chǎn)、有文字的也有畫面的、有文物也有傳說,它們都以北頭廟這一場所為支點(diǎn),并期待能反哺“地方”,對(duì)這塊區(qū)域的未來產(chǎn)生實(shí)質(zhì)影響。
地是“萬物陳列之所在” (見《說文解字》),也是歷史、遺產(chǎn)、文化書寫的對(duì)象,即習(xí)近平總書記所言的“陳列在大地上的遺產(chǎn)。” 地景并非只是一種自然實(shí)體,之所以成為一個(gè)地景,是因?yàn)橛洃泴?shí)踐的結(jié)果。記憶實(shí)踐既是挖掘場所承載文化的過程,也是利用記憶塑造地景的過程。一旦文化記憶在某個(gè)胡同角落、建筑物、山川、田野被在地化,這一“地方”就成為地景,成為可觀、可視的歷史足跡。因此,地景的建構(gòu)和書寫是一種歷史文化與“地方”相遇和對(duì)話的過程,是作為歷史的時(shí)間和作為當(dāng)下的空間相互轉(zhuǎn)換的過程。“地方”在歐美人本主義地理學(xué)語境中被定義為一種“感知的價(jià)值中心”,是社會(huì)與文化意義的載體。主觀性與日常生活的體驗(yàn)是建構(gòu)“地方”最為重要的特征。“地方”與“地理空間”最大的區(qū)別,是它不僅是物質(zhì)上、視覺上的存在,而且還是記憶上、精神上的存在,是主觀的記憶在客觀空間上的轉(zhuǎn)換,是場所與精神的互嵌,是情與景、人與地的交融。每個(gè)“地方”都是獨(dú)特的,由經(jīng)驗(yàn)、情感和記憶這些特征“組成了意義的世界”。因此,文化書寫的重點(diǎn)是發(fā)現(xiàn)“地點(diǎn)”,并將地點(diǎn)注入意義,使其成為被人關(guān)注的文化景觀。
3 文化地景類型及意義探究
走進(jìn)村落巷道去識(shí)別或“尋找”地景是一項(xiàng)具有挑戰(zhàn)性的文化工程。多大規(guī)模,要有什么樣的歷史積累與景觀才能稱得上文化地景?這些問題需要基于大量的調(diào)研才能有所發(fā)現(xiàn)。研究報(bào)告為三德范的主要巷道列出了一系列地景項(xiàng)目,并在地圖上加以標(biāo)志。這些地景既有視覺上能吸引眼球的,以建筑物命名的物質(zhì)遺產(chǎn),如玄帝閣、人和門,也有以歷史地名命名的空間,如圩頭頂、官街、梢門外、宋家灣等。但更多的是不被人們所熟悉的地景,且以各種各樣歷史文化現(xiàn)象命名,包括歷史人物(陳善人宅)、家族(劉家瓦屋)、堂號(hào)(怡善堂)、歷史稱呼(登仕郎、古財(cái)主)、歷史事件(大食堂)、非遺(紅爐鐵鋪)、建筑風(fēng)格(二郎擔(dān)山)、植物(大槐樹)、石碑(矢志柏舟碑)等。不管以何種形式命名,均可以找到一個(gè)“地方”來寄托,其書寫將反哺“地方”形成各種各樣藝術(shù)化的歷史景觀。還有許多地景則是徹底廢棄的宅基地,無任何建筑存在,如姑子庵、花子崖、大清遺民院落、梢門以及其他無房宅院。為此歸納了以下幾種分類方式來識(shí)別鄉(xiāng)村文化地景。
3.1 已知地景與未知地景
已知地景是記憶延續(xù)至今,得到較好保護(hù)的場所,村中廟宇即屬此類,研究將此類地景置于社稷與建置篇中。這類地景的研究重點(diǎn)是挖掘更深層次的場所意義,并能根據(jù)當(dāng)今社會(huì)的變遷,對(duì)其原始意義進(jìn)行創(chuàng)新性的解讀。三德范的禹王廟原為南村居民聚集的一個(gè)禮儀場所,其主要功能為祈雨,但如今,這座禹王廟是濟(jì)南地區(qū)僅存的可以追思大禹、以成厥德的場所。在書寫時(shí),將該廟放在廟宇系列的首要位置,目的是突出孔子所推崇的夏禹之功德對(duì)今天德政教育的意義。因此,禹王廟解讀的重點(diǎn)在于探究三德范先賢如何從儒家經(jīng)典、孔圣之心確立禹王廟的正統(tǒng)意義。今天留存下來的壁畫,不是作為一種藝術(shù)作品來看待,而是當(dāng)作解讀儒家經(jīng)典的載體。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適應(yīng)當(dāng)今時(shí)代的需要,起到弘揚(yáng)善政、德政和儒學(xué)的作用。這賦予該廟,乃至三德范本身一種嶄新的景致與活力,可為今后該廟的利用和三德范文化的提升提供新的創(chuàng)意資源。至于求雨等過去的活動(dòng),由于時(shí)代變遷,就不作為該廟宇的主旨意義來書寫。報(bào)告描述的那些已知地景,并不僅僅展示其過去的作用,更主要的是結(jié)合當(dāng)下需要,重新挖掘其文化意義,一般來說已知地景都會(huì)進(jìn)行類似的深挖。
未知地景指的是一些文化意義尚未被感知的遺產(chǎn)場所,或者其重要性已被感知,但無從把握其文化意義、命名方式及今后歷史樣貌的場所。這類地景是本研究的重點(diǎn),研究報(bào)告的胡同里巷篇大部分都涉及此類地景。三德范圍子墻內(nèi)的各個(gè)古巷道目前處在廢棄的狀態(tài),村里雖已意識(shí)到這些巷道對(duì)三德范發(fā)展的重要意義,但不知道如何對(duì)其文化進(jìn)行梳理,也不知道需要開發(fā)什么樣的文化景觀。由于這些巷道缺乏歷史史料、碑文等的支持,夾雜著新舊不同時(shí)代的痕跡,要讓這里出現(xiàn)文化地景,就需要進(jìn)行大量的口述史研究,打破現(xiàn)有的遺產(chǎn)認(rèn)知,才能從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挖掘記憶和敘述素材。對(duì)荒蕪的空地進(jìn)行細(xì)致和深入的文化敘述,目的就是期待為今后規(guī)劃和利用提供文化藍(lán)本,打造屬于三德范特色的傳統(tǒng)巷道景觀。即使今后重建一些仿古建筑,也能注入背后的歷史故事和意義。例如針對(duì)陳家巷南北大片空地,講述了“大清遺民”馮汝田一家的記憶,展示中國鄉(xiāng)村民居是如何以“五服”為體系,形成親親尊尊的民居布局。這些“新發(fā)現(xiàn)”的地景很少出現(xiàn)在三德范的地方文獻(xiàn)中。希望研究能為理解相關(guān)區(qū)域文化精神提供敘事化的歷史靈韻。
3.2 主題地景與肌理地景
前者指的是可以確立一條胡同靈魂的地景,后者指能給胡同空間提供多樣性歷史描述的細(xì)節(jié)地景。三德范有10條巷道,每條巷道應(yīng)該有自己獨(dú)特的文化特色,而不是千篇一律地克隆一種風(fēng)格。主題地景旨在為每條巷道確立一個(gè)特色,或稱為“魂”,圍繞這個(gè)“魂”能出現(xiàn)一批特色景觀。比如在辛莊巷的書寫中,著重展示了胡同里曾經(jīng)的世醫(yī)、藥鋪與郎中。“醫(yī)”就成為了這條巷道的“魂”,期待通過營造世醫(yī)文化,將辛莊巷打造成康養(yǎng)平臺(tái)、養(yǎng)生四合院和中醫(yī)文化的傳播基地。張家巷在文化定位上則突出其士紳文化,如詩禮堂宅、登仕郎故居、淳爺故居等鄉(xiāng)賢地景作為重要描述的對(duì)象。太平巷突出鄉(xiāng)黨文化,著重描述巷道治理的事跡。齊家巷因有3個(gè)大家族的始遷祖都曾在此落腳,故突出作為故鄉(xiāng)的桑梓文化。陳家巷則以“五服”觀照下的鄰里文化為亮點(diǎn),描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鄰里布局。這些具有特色的主題定位并非刻意“設(shè)計(jì)”進(jìn)去,而是基于深入的場所歷史文化考證獲得,故本身符合這些巷道的歷史面貌。
肌理地景挖掘是為了突出每一條巷道景致的多樣性,補(bǔ)足胡同主題的細(xì)節(jié),同時(shí)呈現(xiàn)鄉(xiāng)村文化的方方面面。這類地景既是對(duì)主題地景的陪襯,也是某一獨(dú)特文化現(xiàn)象在胡同節(jié)點(diǎn)上的展示,如陳家巷的紅爐鐵鋪、大食堂、梢門外書場、紙?jiān)取_@些既有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落地景觀,反映了特定時(shí)代的懷舊文化。辛莊巷有二郎擔(dān)山的草屋風(fēng)格,也有“宋宅應(yīng)事”中描述的民宅風(fēng)水故事。此外還有齊家巷的巫醫(yī)、太平巷的紅色商人、張家巷的大影壁與地屋子等等。這些以某一獨(dú)特文化現(xiàn)象提煉的地景,賦予每一條胡同不同的聲音和色彩,同時(shí)也可以借助這些地景探討各種各樣的鄉(xiāng)村文化。
區(qū)別主題地景與肌理地景,主要目的是為了給胡同規(guī)劃和設(shè)計(jì)者提供一條靈魂性的主題線索,為打造各具特色的文化產(chǎn)業(yè)奠定精神支柱。主題地景使今后巷道開發(fā),不至于落入千篇一律的范式。與此同時(shí),在每條胡同主旋律下,又能百花齊放,每走一步都有一處獨(dú)特的景致,并借此探索一種獨(dú)特的鄉(xiāng)村文化現(xiàn)象。
3.3 無形地景與有形地景
前者是指該區(qū)域無任何歷史遺存,目前的狀態(tài)為空地,或者已經(jīng)徹底與歷史割斷并改變用途的“地方”。后者是指目前有某種有形歷史遺存可作為胡同延續(xù)的視覺基礎(chǔ)。這里要特別強(qiáng)調(diào)的是無形地景并非是沒有文化的“地方”。許多目前是空地的“地方”,很可能寄托著極為豐富的文化記憶。如三德范陳家巷胡同頂一帶,目前雖已無建筑遺存,但借助民國檔案資料以及當(dāng)事人或其后代的口述,我們?cè)佻F(xiàn)了這里曾經(jīng)的民居格局,深入刻畫了“睦鄰和眾以享升平之福”的鄉(xiāng)村自治空間,并以這個(gè)虛空?qǐng)鏊鳛檫@條胡同的文化主題。類似的無形地景還有廣宗故城、小寨、姑子庵、文昌閣、大槐樹、梢門、怡善堂等。這些場所已經(jīng)沒有任何歷史遺存可以辨識(shí),但其文化價(jià)值不低于廣泛認(rèn)知的古建筑。比如位于三德范北邊的廣宗故城,今雖井邑已非,但卻是該莊最重要的可以愴然懷古的建制場所。無形地景更好地說明文化記憶與場所的關(guān)系,即地景的形成依托的是看不見的文化記憶,精神的存在是文脈物化的前提。歷史街區(qū)的規(guī)劃、改造和更新不能僅僅依據(jù)有形遺產(chǎn),有形遺產(chǎn)地景一般比較容易把握,歷史上留下來的建筑、景觀可以作為解讀文脈、展示記憶的載體。這種有形遺存,在時(shí)間的侵蝕下,也呈現(xiàn)出千姿百態(tài)的歷史面貌,有些具有很完整的物質(zhì)原真性,如玄帝閣、禹王廟,有些是根據(jù)歷史完全重建,如龍王廟,但更多的是在歷史進(jìn)程中,不知不覺已經(jīng)有很大改變,甚至面目全非或僅存的某種空間格局,這種現(xiàn)象尤其體現(xiàn)在那些普通的巷道民宅里。這類地景的歷史信息需要小心解讀,在利用時(shí),更需要有以故為新的創(chuàng)新思維。將地景進(jìn)行上述類型的討論,并非只是為了賦予其特有的物質(zhì)屬性,主要目的是當(dāng)我們?cè)诮裉斓泥l(xiāng)村空間里行走,能更好地把握復(fù)雜的文化生態(tài),能將記憶與地方融為一體思考,在規(guī)劃和設(shè)計(jì)時(shí),充分把握其文化屬性。
4 文化地景的跨界實(shí)踐
地景被看作是依附于某一場地上的歷史文化景觀,它可以是建筑遺存,巷道肌理,也可以是山、石、樹、坡等自然景觀;可以是一種物化的視覺存在,也可以是某種空間感受。如果從地景文化建設(shè)的角度來探索鄉(xiāng)村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傳承、利用和創(chuàng)新,那么村落的發(fā)展和振興就是一次深度的地景再造,是物質(zhì)和精神的互通互融。地景建設(shè)需要極為細(xì)膩的歷史情感,也需要精細(xì)的藝術(shù)化創(chuàng)作。更重要的是,地景建設(shè)針對(duì)當(dāng)下的問題和難題,針對(duì)政府和老百姓的各種訴求展開。這要求打破一切界限,將物質(zhì)和非物質(zhì)遺產(chǎn)、歷史和場所、自然和人文、藝術(shù)和生活、文化與產(chǎn)業(yè)以及過去、當(dāng)下和未來等,以融合的方式整合在一起。簡單而言,就是要處理好以下幾個(gè)方面,使文化地景建設(shè)成為鄉(xiāng)村振興的一次跨界實(shí)踐。
4.1 過去與當(dāng)下
三德范作為國家級(jí)傳統(tǒng)村落、全國美麗宜居村莊和山東省歷史文化名村,過去留下來的一磚一瓦,甚至任何寫在這塊土地上的歷史痕跡都是村落發(fā)展與走向未來的財(cái)富和創(chuàng)新源泉。但這個(gè)過去是活在當(dāng)下的過去,是滲透在現(xiàn)代人生活里的過去,是走向未來的過去。如果把過去凝固在某一歷史階段里,使其與現(xiàn)代生活隔離,或者成為一種展陳過去的博物館,都不是鄉(xiāng)村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和利用的最終目的。傳統(tǒng)村落的過去,并不是收藏和展示的對(duì)象,也不是為了滿足當(dāng)前鄉(xiāng)村建設(shè)中涌現(xiàn)的各種村史館、民俗館、非遺館、鄉(xiāng)賢館和文化禮堂等的需要。過去是這塊土地走向未來的希望、靈感和資產(chǎn)。
鄉(xiāng)村文化、鄉(xiāng)村遺產(chǎn)好似一條在流動(dòng)著的、每時(shí)每刻都在變化的長河。《論語》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逝,往也,即過去。孔子感嘆既往人事不可追復(fù),時(shí)事往者如川之流夫,不以晝夜而有舍止。我們不能忘記這條河的源頭在哪里,如何流淌到今天,這就是地景之文脈。1919年春毛澤東曾游孔子故里,他后來講述這段經(jīng)歷給斯諾說:“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們濯足的那條小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鎮(zhèn)”。顯然青年毛澤東并沒有看到任何具有物質(zhì)原真性的物體,但他同樣被那小溪所吸引,并看作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這條小溪一直在變化,但2000多年持續(xù)下來的文脈也一直在流動(dòng)。因此要確保鄉(xiāng)村土地上的任何改造都能延續(xù)這一文脈持續(xù)流向未來。用歷史長河或文脈的意識(shí)去處理鄉(xiāng)村文化場所,使其能順應(yīng)時(shí)代變化、能感受到其生生不息的活力。
4.2 歷史與空間
把文化、歷史看作是書寫在大地上的遺產(chǎn),就是將歷史文化置于空間與場所中思考。今天興起的人文地理學(xué)和空間歷史學(xué)將歷史敘事轉(zhuǎn)換成了一種空間敘事。任何一個(gè)歷史場所都包含著豐富的、不同時(shí)代留下來的文化碎片,應(yīng)收集這些記憶碎片,對(duì)空間與場所進(jìn)行敘述化的深度描繪。所謂深度,雖然體現(xiàn)在時(shí)間(歷史)層次上,但是更重要的是空間里蘊(yùn)含的道義和情感。地景空間的歷史敘事,能將這些不同時(shí)代、不同形式的歷史碎片雜糅起來,用古今會(huì)通、文理并置的方式,塑造充滿歷史意義的空間故事。當(dāng)這些文化碎片被編織到村落的空間中時(shí),場所、景觀、遺跡乃至一石一木就被賦予了遺產(chǎn)靈韻。
5 文化地景的書寫與構(gòu)建
空間與場所繪描是文化地景建設(shè)的藍(lán)本。把文化記憶物化成具體的胡同景觀和生活場景,就是用一種生活化的、不斷生成的視角,將各種實(shí)物、圖片、記憶、文字、聲音等“文本碎片”,用“景觀”的方式重新書寫到大地上。文化書寫既是一個(gè)構(gòu)建地景的過程,也是一個(gè)意義凝練的過程,探索以下遺產(chǎn)書寫與地景構(gòu)建途徑,以期為后期遺產(chǎn)的保護(hù)與利用提供文化視角。
5.1 層積疊加的空間敘事
歷史敘事以空間和場所作為載體,形成故事情節(jié),所謂情節(jié)既具有一定的時(shí)間軌跡,也有人物事件的展陳,整條胡同可以形成一個(gè)故事情節(jié)。此外,文化書寫應(yīng)能反映場所的歷史層次。文化景觀的修復(fù)不是簡單地將其面貌恢復(fù)到某一個(gè)歷史節(jié)點(diǎn),而是要最大程度體現(xiàn)不同歷史階段留下來的記憶積淀,形成多層次文化感受。比如陳家巷的胡同博物館、大食堂,這些民居具有不同時(shí)代的文化烙印,文化敘述要體現(xiàn)不同時(shí)期的歷史記憶。這些歷史記憶有些來自當(dāng)?shù)鼐用竦目谑觯行﹣碜苑课莸臍v史資料,如房契等,對(duì)這些資料的整理要著力體現(xiàn)其背后的文化意義。敘述著力于空間的“深描”,將歷史置于空間中來思考,從而賦予歷史街區(qū)多樣性、復(fù)雜性和開放性的意義再生潛能。
鄉(xiāng)村文化資產(chǎn)往往以碎片化的形式留存至今,這些碎片既包括建筑遺存、文物、石碑等實(shí)物,也包括圖片、文獻(xiàn)、口耳相傳的記憶敘述、某種聲音和氣味。空間改造就要讓這些記憶碎片落地、扎根并發(fā)光。文化景觀的構(gòu)建不應(yīng)凝滯在過去,或簡單地做仿古建筑,尤其是克隆流行的古建筑風(fēng)格,要因地制宜、以故為新,讓地方歷史文脈成為場所的生命和活力。
5.2 文化地景的價(jià)值觀打造
打造美麗鄉(xiāng)村歷史景觀,不僅體現(xiàn)在視覺和美學(xué)意義上,而且更重要的是體現(xiàn)在道義上。任何能持續(xù)觸動(dòng)人心的地景背后必然蘊(yùn)含著天道時(shí)序之道德文章,無論是山水景觀,還是村落肌理都要彰顯其價(jià)值觀。鄉(xiāng)村地景,哪怕是一草一木,一定意義上都是傳統(tǒng)道義的物化和彰顯。《戰(zhàn)國策·齊策四》有記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這里是說柳下季的墓墟邊的草木也具有重要的文物價(jià)值。因此,在古人眼中,月榭風(fēng)亭不在其藝術(shù)之美,荒祠古墓不在其文物之珍,關(guān)鍵是有可以讓當(dāng)世仰慕和追憶的精神遺產(chǎn)。鄉(xiāng)村地景建設(shè)要踐行習(xí)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既要塑形,也要鑄魂”的要求。
在整理和敘述鄉(xiāng)村歷史景觀時(shí),我們著力在收集到的各種文化碎片中探微取義,發(fā)現(xiàn)擁有當(dāng)下意義的傳統(tǒng)道義觀,并視其為相關(guān)地景的靈魂。所謂探微就是發(fā)現(xiàn)看似平常的記憶碎片,并以細(xì)微的語言或遺產(chǎn)的表現(xiàn)方式觸及其背后的傳統(tǒng)文化道義,從而達(dá)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之目的。
鄉(xiāng)村風(fēng)貌,尤其是巷道肌理、民居風(fēng)格等歷史上一直受旌表文化的影響,它是鄉(xiāng)村文化自治的一部分。這一文化可溯源至《尚書》,所謂:“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fēng)聲”。《尚書》從源頭表述了里巷文化的歷史深度,里巷文化在周武王時(shí)期就已形成,《史記·殷本紀(jì)》記載周武王滅商后,“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其中“閭”就是里巷的大門,“表閭”之行被后人看作義舉,如三國魏鐘會(huì)《檄蜀文》云:“周武有散財(cái)、發(fā)廩、表閭之義。”旌表文化的物質(zhì)形式包括牌坊、門庭、照壁、上馬石以及建筑物上的裝飾。這些胡同肌理,寄托了忠孝流芳、觀者景行行止、見賢思齊,為美之心由此而出。故胡同地景能起到化民成俗的德化作用。
巷道遺產(chǎn)修復(fù)可看作是“表厥宅里”的文化工程,就是把歷史人物回歸到坊巷遺產(chǎn)的修復(fù)和轉(zhuǎn)化中去。將歷史人物的價(jià)值與忠、孝、節(jié)、義等古代坊巷的文化道義相接續(xù),取其精華,同時(shí)賦予其現(xiàn)代的涵義,其目的在于促進(jìn)、適應(yīng)當(dāng)下道德觀的建立。比如 “忠”可能會(huì)讓人聯(lián)想到“忠君”的思想而遭到排斥,而事實(shí)上,古人( 如晏子與孟子) 就曾將“忠于社稷”與“忠于君主”區(qū)別開來, 因此傳統(tǒng)文化中所謂的忠并不只有忠君之意。張岱年曾經(jīng)指出,“在社會(huì)主義時(shí)代,愛國主義應(yīng)是道德的第一原則,這一行為規(guī)范仍可用‘忠’來表示。”他提出,當(dāng)今中國可沿用“公忠體國”這一道德規(guī)范。事實(shí)上,這一表述也更能體現(xiàn)文化的延續(xù)。
三德范中心街上的馮昭著是一位抗美援朝的烈士,在敘述中將其回歸到“忠”的傳統(tǒng)價(jià)值觀中加以旌表,使其在中心街上的故宅成為“表厥宅里”的文化地標(biāo)。傳統(tǒng)美德主要體現(xiàn)在歷史人物的行事方式上,在研究的過程中,為三德范村的每條胡同都挖掘了一些人物,并將這些人物落地成為巷道景觀。他們的故居、足跡、事件發(fā)生地就成為講述人物故事的場所寄托。敘述使得這些塵封的人物在巷道中被再次激活,他們所承載的精神得以在坊巷中傳承。在地景構(gòu)建的過程中,旌表的形式要順應(yīng)時(shí)代的變化,成為胡同景觀的藝術(shù)化對(duì)象。希望這些人物能構(gòu)建起新的文化景觀,旌淑彰善,顯于當(dāng)下,傳于后世。
正如柳下季墓墟邊的草木也具有重要的文物價(jià)值一樣,植物,尤其是古樹名木,也是鄉(xiāng)村歷史景觀重要組成部分。但這些植物并不局限于植物學(xué)意義,而是注重其內(nèi)在寓含的道義。這一帶村落有悠久的種植花椒的歷史,花椒因其芳香、性烈而奪物,其枝條伸展廣遠(yuǎn),恰似《詩經(jīng)·椒聊》所喻,君子之美德似花椒芳香彌漫廣遠(yuǎn);君子之仁澤品性似花椒之葉,堅(jiān)而滑澤;君子之子孫繁衍眾多,似花椒枝條之長遠(yuǎn)而繁盛。植物作為一種遺產(chǎn)的展示,更多應(yīng)從古籍如《詩經(jīng)》中尋找其文化意象,顯現(xiàn)其文化意蘊(yùn)。
5.3 歷史空間的意義構(gòu)建
空間的概念較“地方”更為抽象,當(dāng)空間被賦予價(jià)值意義的時(shí)候,空間就成了“地方”。文化地景構(gòu)建的過程也是空間意義打造的過程,這一過程包括空間命名、場所標(biāo)志、空間文化意義挖掘。
命名是賦予空間意義,使之成為“地方”的方式之一,命名也是空間文化意義的提煉,荀子說過:“有循于舊名,有作于新名”,空間命名就是一個(gè)有循有作的過程。如考察發(fā)現(xiàn),三德范齊家巷過去曾為張氏、牛氏、齊氏三大姓氏始祖居住地,因此在研究報(bào)告中將這一塊空間命名為“桑梓苑”。詩經(jīng)《小雅·小弁》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是說桑樹和梓樹乃父母所植,必須恭恭敬敬。桑梓一詞暗含對(duì)先人的敬重,“桑梓苑”旨在表述慎終追遠(yuǎn)的文化意義。
村落內(nèi)部和四周有許多大大小小的記憶場所,但可能無法出現(xiàn)建筑物來表述記憶,如山坡、墻角、路基。這些地方則可以通過勒石立碑、制作銘牌、嵌入傳統(tǒng)符號(hào),或營造小公園等方式建立歷史場所的標(biāo)志系統(tǒng),使觀者進(jìn)入這一空間便能激活某種歷史記憶。有些當(dāng)?shù)氐牡孛哂羞h(yuǎn)古的文化含義,但不為人知,也可用場所標(biāo)志的方式加以凸顯。如張家巷頂部有一處被稱為“圩頭頂”的高地,除個(gè)別當(dāng)?shù)乩险咄猓渌硕嗖恢肋@個(gè)“圩”字的寫法。而yú作為一個(gè)古音,現(xiàn)在已基本不用,只有古籍中才能找到例證,如《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生而圩頂,故名丘。”“圩”又折射三德范圍子墻的文化。對(duì)其進(jìn)行標(biāo)志可以提升當(dāng)?shù)鼐用竦奈幕庾R(shí)與地方歸屬感。
通過對(duì)空間意義的挖掘,鄉(xiāng)村歷史景觀再造可成為促進(jìn)鄉(xiāng)村自治體系和自治能力建設(shè)的一部分。歷史上,閭巷一直是村民自治的基本單位,至今三德范還有許多關(guān)于閭巷的記憶。我們圍繞一些胡同聚落,著力挖掘守望相助的鄰里文化,從記憶碎片中,獲取鄉(xiāng)村自治的法治律度。比如,從村檔案館獲取分家書、地契等文書,并將其回歸到胡同空間里解讀。文書和其中的族人、街誼、家舅、執(zhí)筆、四鄰等角色,勾畫出在沒有政府與國家法律介入的情況下,鄉(xiāng)民如何自主建立信譽(yù)、公證體系,街坊、家族與法禮如何互動(dòng),形成道德意義上約束,解決各種糾紛。這些記憶的激活,既對(duì)鄉(xiāng)村道德建設(shè)具有重要啟迪,也使閭巷自治空間的意義得以彰顯,成為地景構(gòu)建的素材。
研究發(fā)現(xiàn),鄉(xiāng)村自治的意識(shí)當(dāng)下仍在接續(xù),村民們也不斷地在審視自己的家鄉(xiāng),從日常而不自知的生活環(huán)境和地方景觀中,重新了解自己的過去、理解當(dāng)下的生活、構(gòu)筑未來的愿景。例如目前的陳家巷博物館在一定意義上就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博物館由“生于斯長于斯”的三位巷道老人維護(hù)管理,他們將自己對(duì)巷道的情感傾盡其中,文物的收集、整理、展示過程也是他們個(gè)體記憶的復(fù)蘇過程。年輕一代也可在接觸這些文化記憶中,重建個(gè)人的記憶和價(jià)值,并與胡同的文脈源流產(chǎn)生情感上的互動(dòng)。博物館將鄉(xiāng)村記憶和巷道遺產(chǎn)保護(hù)與鄉(xiāng)村治理結(jié)合為一體,成為村民參與巷道文化構(gòu)建的平臺(tái)。
6 結(jié)語
鄉(xiāng)村歷史景觀建設(shè)是德化鄉(xiāng)里、樹之風(fēng)聲的過程。歷史空間的營造、歷史肌理的修復(fù)、文化地景的展陳、傳統(tǒng)符號(hào)的植入、鄉(xiāng)村業(yè)態(tài)的規(guī)劃無不體現(xiàn)“鑄魂”的使命和責(zé)任。因此鄉(xiāng)村地景建設(shè)應(yīng)體現(xiàn):“并建圣哲,樹之風(fēng)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xùn)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禮則,使毋失其土宜,眾隸賴之,而后即命。”(《左傳·文公·文公六年》)這句話置于當(dāng)今鄉(xiāng)村振興和遺產(chǎn)保護(hù)實(shí)踐中,就是要給鄉(xiāng)賢樹立風(fēng)氣教化;飾物旗幟能別親疏尊卑;善言遺訓(xùn)能植入景觀。能為鄉(xiāng)村治理樹立制度、貢獻(xiàn)準(zhǔn)則;能設(shè)立表率來引導(dǎo)儀表;告知祖上傳下來的典章制度;教育人們不要謀求私利;道鄉(xiāng)民以禮節(jié)法則;告誡人們遺產(chǎn)建設(shè)和利用都要因土地風(fēng)俗,因地制宜。于官、于士、于農(nóng)、于商都能依靠這份遺產(chǎn),為其所用。遺產(chǎn)的價(jià)值不僅停留在過去,而且屬于當(dāng)下;不僅高雅,而且通俗。遺產(chǎn)的書寫可以為遺產(chǎn)的利用帶來更多想象,為鄉(xiāng)村振興提供更多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