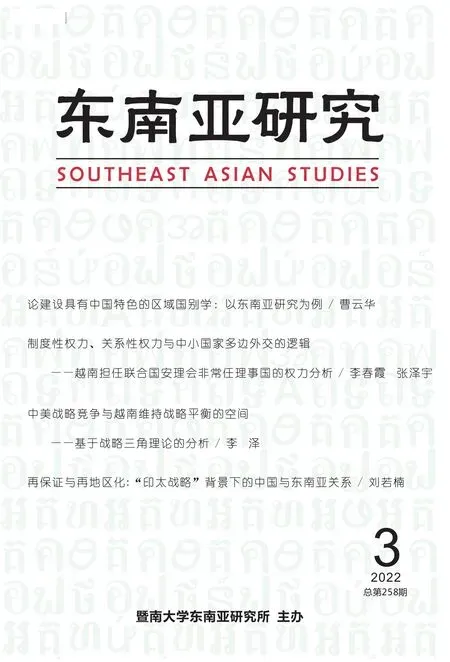日本的東南亞研究:學科特征和地區構想
畢世鴻
前 言
自20世紀步入全球化時代以來,包括東南亞在內的區域國別研究成為部分國家的“必修課”。在從事東南亞研究的域外國家中,日本的東南亞研究特色鮮明、引人注目。日本的東南亞研究發端于二戰前,正式起步于冷戰時期,21世紀以來更獲得了全面發展。東南亞研究相關學會的成立可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以東南亞整體、東南亞各國、各學科為研究單位的學會不斷增加,研究隊伍也持續擴大。此外,日本有關東南亞的研究機構和教育體系也快速發展。作為日本學界的最高機構——日本學術會議還設立了地區研究委員會,在科研經費的細目中新增了地區研究。上述舉措促使日本學界的東南亞研究人才輩出、成果豐碩。
關于日本東南亞研究的評述,中國學界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主要論及日本東南亞研究的發展歷程、機構、群體以及主要路徑和成果,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也留下了可以進一步拓展的研究空間。本文在梳理日本東南亞研究發展歷程的基礎上,分析其主要研究方法和學科特征,繼而闡明其地區構想、貢獻及所面臨的挑戰。
一 日本東南亞研究的興起與發展
發端于二戰前的日本東南亞研究,彼時的主要目標是服務于日本統治東南亞的國策。二戰后,日本東南亞研究學界決心擺脫政治的影響,逐漸顯現出其獨特之處,并培養了一大批東南亞研究學者,產出眾多重要成果。
(一)日本東南亞研究的發展歷程
二戰前,日本對東南亞的研究基本依靠東亞研究所、滿鐵調查部、太平洋協會等官方研究機構進行,基本都是對東南亞普通產業或當地政治社會情況的介紹,目的是為促進移民和侵占東南亞做準備,從而為日本軍國主義提出的“南進論”造勢助威。
二戰期間,日本依托南方軍政總監部調查部、一橋大學等機構,派遣研究人員對東南亞各地進行實地調查。日本東南亞研究作為“國策”淪為軍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的工具,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二戰后日本東南亞研究的基礎,并由此涌現出一批東南亞研究的權威學者。這批學者主要有赤松要、山田勇、板垣興一、山田秀雄、蠟山政道、東畑精一、杉山廣藏、馬場啟之助等人。在這些研究中,歷史學成果最多,尤其是對東南亞王朝的考證以及各地王朝和中國王朝的交流史研究。其中,山本達郎的《安南史研究I:元明兩朝的安南征略》可謂經典。
二戰后,日本重啟東南亞研究,以重構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的政治經濟關系,并通過研究東南亞來重新認識本國,這與歐美國家存在一定差異。20世紀50年代,日本東南亞研究和調查報告的主題幾乎都與戰爭賠償、技術合作、經濟開發和經濟計劃等有關。例如,板垣興一1957年發表《馬來亞橡膠種植發展史備忘錄》,后來還梳理了英國殖民統治馬來亞的相關史料,其成果是馬來亞經濟史研究的重要補充。川野重任的《土地改革的社會經濟意義——以東南亞各國為例》和瀧川勉的《菲律賓土地制度史緒論》則被奉為東南亞土地改革和土地制度研究的圭臬之作,為東南亞國家殖民地二元結構理論奠定了基礎。
此后,日本陸續成立從事東南亞研究的各類機構。這些機構主要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由官方設立,直接受政府部門領導,為政府相關部門決策服務,如1960年由當時的通商產業省設立的亞洲經濟研究所、1959年成立的隸屬于外務省的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1974年成立的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以及2001年創設的隸屬于文部省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的綜合地球環境學研究所;第二類是以公益財團法人的形式設立,進行政府及社會相關機構委托項目的研究。前述的亞洲經濟研究所以及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目前均已轉變為這種公益財團法人機構。第三類是在各大學內設立的各種研究所、研究中心以及與此相呼應成立的相關的學會、研究會等。如20世紀40年代設立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和社會科學研究所、1963年成立的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后為東南亞研究所)、 1975年成立的筑波大學地區研究科,以及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亞細亞大學亞洲研究所等機構均不同程度地開展與東南亞區域國別有關的研究,并大量派遣學者和學生前往東南亞國家長期開展田野調查。與東南亞研究有關的學會則主要有東南亞學會(前身為東南亞史學會)、亞洲政經學會、國際發展學會、亞洲市場經濟學會等,還有諸多涉及國別或學科的學會,日本東南亞研究由此迎來全面發展的新階段。這可能與20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經濟快速發展,企業大規模進軍東南亞所帶來的各種需求密切相關。
隨后,日本通過文理兼容的方式,使研究方法和理論范式更加多元,促進了對東南亞國家間的比較以及對區域國別研究的整體把握。同時,日本高度重視發展中國家研究,并在此基礎上對歐美學界的理論或模型進行批判性吸收,以擺脫歐美中心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浪潮中,日本更加凸顯對東南亞研究的“綜合性理解”,重視學科交叉融合,力求區別于國際政治和世界經濟等社會科學,區域國別研究得以占據與一級學科同等的地位。
受此影響,日本將包括東南亞研究在內的區域國別研究的組織化和制度化建設提上議事日程。2005年,日本學術會議專門成立了地區研究委員會,以發揮頂層設計和學科間協調等作用。隨后,該委員會陸續推出區域國別研究的人才培養、服務社會和信息發布、研究資源共享、可持續的區域國別研究體系建設等各方面的舉措,為進一步加強和促進區域國別研究提供了制度保障。相應地,日本政府對區域國別研究投入的經費預算也逐漸制度化。在科研經費的分類中,區域國別研究并不屬于人文社會科學,而屬于綜合性交叉學科領域。綜合性交叉學科要求研究人員同時掌握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必要知識,研究領域更加寬廣、多樣,例如地理學、環境學、社會安全體系科學、男女社會性差異等研究領域。在分配科研經費時,區域國別研究被視為“文理融合”的交叉領域。
(二)21世紀日本東南亞研究主要成果
日本東南亞研究群體龐雜,成果豐碩,受篇幅所限,本部分重點考察21世紀以來的主要學者及其學術著作,除了選取日本科研成果書目資料庫搜索引擎CiNii和主要出版社網站所登載的著作以外,也將《史學雜志》《回顧與展望》等評論動向和書評納入考察范圍。
關于東南亞歷史,日本學界針對東南亞大陸國家歷史的研究,在空間上以中央—地方關系、地方史及殖民統治對民族國家構建的影響為主,呈現出精致而豐富的歷史圖景。針對越南,桃木至朗從社會經濟和國家統治體制兩方面,詳細論述10-14世紀的李朝和陳朝;八尾隆生主要研究15世紀黎朝早期的歷史。針對柬埔寨,石澤良昭分析了前吳哥時期到15世紀吳哥王朝末期的地方勢力。小泉順子通過探討泰國近代史中“臣民”“家族”“傳統”等概念,提出應重構國別歷史的問題群。而笹川秀夫和俵寬司分別指出在法國殖民統治下,遠東學院所發表的柬埔寨和越南的史前史及古代史相關成果被當地領導人沿用,繼而孕育出獨立后的民族國家歷史。
相較于東南亞大陸地區,東南亞海島地區的歷史更為復雜。小野林太郎主要運用民族學和考古學的方法,研究加里曼丹島東側西里伯斯海域的產業文化。平山篤子和宮田繪津子著眼于宗教和商業,以16-17世紀的馬尼拉為研究對象,探討彼時西班牙與中國的合作關系。大橋厚子和太田淳采用經濟學和社會學等方法,考察18-19世紀初期爪哇島社會變化。菊池誠一等采用考古學、美術史學等交叉學科的方法研究東南亞海域史。羽田正主要采用世界史和考古學方法,以東印度公司為抓手,論述17-18世紀東南亞與世界各地的經貿往來及人文交流。
關于東南亞政治,諸多日本學者就東南亞各國政治體制的維持、變化、轉型以及東盟運行等方面進行了研究。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白石隆、黑柳米司、鈴木早苗側重于研究東南亞整體的政治發展和東盟的運行情況;水野廣祐、相澤伸廣、倉澤愛子主要研究印度尼西亞的政治轉型、華人問題和地方政治;原不二夫、山本博之、鈴木絢女則關注馬來西亞的政黨關系、民族主義和政經關系;五十嵐誠一、高木佑輔、山根健至著重研究菲律賓的政治轉型、政經關系和軍政關系;田村慶子、生田真人對新加坡的政治發展和區域一體化問題進行了深度研究;古田元夫、白石昌也、寺本實主要深耕越南的政治轉型、政經關系、國家與社會關系;村鳩英治、重冨真一、高橋勝幸在泰國的政治轉型、政經關系及政黨政治方面的研究成果頗有影響;根本敬、工藤年博、中西嘉宏一直關注緬甸的政治轉型、政經關系和軍政關系;天川直子、山田裕史對柬埔寨的政經關系和政黨政治進行了長期跟蹤研究;山田紀彥、菊池陽子主要研究焦點在于老撾的民族國家構建和政治發展。
關于東南亞社會、民族與宗教,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長期開展可持續性領域交叉型研究項目,對東南亞各國山民傳承下來的資料進行編譯,并出版叢書《不為人知的亞洲語言文化藏書》。在此基礎上,日本近年來陸續出版以山地民族為對象的民族志,其中泰國、緬甸邊境地區的山地民族是研究重點。在宗教研究方面,日本學者主要關注東南亞當地宗教運動和宗教制度在近現代民族國家構建中的作用,代表性學者有研究南傳上座部佛教的矢野秀武、飯國有佳子、伊藤友美,研究伊斯蘭教的久志本裕子、鹽崎悠輝、菅原由美,以及研究本土宗教和基督教的山本春樹等。
在東南亞經濟研究領域,末廣昭和大泉啟一郎等從宏觀視角論述了現代東南亞經濟的發展。柿崎一郎連續出版泰國交通史相關著作,開辟了全新領域。在社會經濟史方面,千葉芳廣從勞動力和商品流通入手,闡明馬尼拉經濟圈的變化。關于農業、土地及其生產,高谷好一全面研究了東南亞各地自然與土地利用之間的關系。坪內良博、高橋昭雄、坂田正三、箕曲在弘等分別深入研究了馬來西亞、緬甸、越南、老撾等國現代農業、農村的狀況及其與全球經濟的關系。北原淳、石川幸一、平川均等學者在東盟推動域內外自由貿易及一體化進程方面的研究成果頗豐。
二 日本東南亞研究的主要方法與學科特征
日本的東南亞研究重在探索不同于歐美的方法,即探索非歐美世界且不局限于民族國家,以實現研究方法上的東西融合,由此彰顯日本東南亞研究的綜合性和跨學科性。
(一)東西融合的研究方法
二戰結束初期日本東南亞研究雖然模仿美國并依靠其扶持,但也極力排除美國地區研究的政治影響,這體現出日本學界對侵略歷史的深刻反省。許多學者認為東南亞研究應立足于社會科學方法論,不能完全照搬美國范式,強烈提倡在學術研究領域為東南亞研究爭取一席之地。1963年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成立之際,該校校長平澤興曾告誡:“在進行東南亞研究時,最重要的就是保證研究的獨立性與公正性,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參雜政治因素。”日本東南亞研究由此發生了本質變化,不再順從統治集團的意志,開始重視學術研究及東南亞本身的固有屬性和脈絡,并致力于修復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矢野暢認為,必須從理論上確保東南亞研究“無論如何都不會從屬于國策”,必須擁有“固有的學術尊嚴”,即東南亞研究必須徹底與國策劃清界限。
日本學界鼓勵學者在對象國長期開展田野調查,重視對當地語言的信息收集,把政治經濟現象與對象國的歷史文化要素相結合來進行綜合理解。換言之,東南亞研究學者可謂“精通對象國情況的人”。通過深入了解東南亞特定地區,可以發現當地重要的問題和值得研究的課題。這既是深化東南亞研究的基礎,也是東南亞研究發展的動力。而在田野調查和研究過程中,與當地民眾擁有相近立場顯得非常重要。通過大量實踐,許多學者不斷產出重要研究成果。例如,末廣昭長期跟蹤調研泰國經濟統計數據,提出追趕型工業化、家族經濟等理論,成為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扛鼎之作。
近年來,日本學界更迫切地認識到東西融合問題的重要性。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兩點:一是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和政治轉型十分迅速。這導致以發展中國家政治經濟結構特殊性為前提的研究難以為繼,相反,越來越多的研究將歐美國家的分析方法應用于東南亞國家。同時,隨著東南亞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當地學者的研究水平也大幅度提升,日本等域外學者已經無法壟斷該地區的“知識”生產。二是數據的公開性和適用性大大提高。由于東南亞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積極公開各種統計數據,且隨著互聯網技術和統計學分析方法的不斷發展,即使不在當地長期開展田野調查,也能獲得各種數據和信息并進行精準分析。因此,在日本學界,以田野調查為基礎的傳統區域國別研究方法開始受到質疑。推動東南亞研究的代表性學者——亞洲經濟研究所首任所長東畑精一曾提倡“東南亞研究三原則”,即在當地停留一段時間,學習當地語言,熟知當地歷史。但由于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很多日本青年學者認為,東南亞國家已失去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性,且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現象也暴露出區域國別研究的局限性,跨國或跨地區問題成為重要研究課題。青年學者強烈希望前往歐美國家學習更加成熟或新的研究方法,并借此來說明東南亞研究的普適性。
同時,隨著比較政治學的國際化程度日益提升,其與東南亞研究的交匯點隨之增多,日本學者也開始青睞比較政治學及相關理論。一些學者甚至強調需要運用中距離理論等新研究方法,也有學者開始追求體系化的理論和定量分析,即忽略各地特殊性的統計學也成為目前日本東南亞研究的主流方法。自此,強調各地特殊性的案例分析及后殖民主義、后社會主義等研究取向逐漸淡出東南亞研究的視野。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政治轉型、地區沖突等問題日益突出。日本東南亞研究也隨之涌現出一批新的理論方法,過渡論、體制轉換論、和平共生論、民主論、公民社會論、合理選擇論等漸受重視。
(二)綜合性和跨學科性特征
日本東南亞研究的方法并不局限于社會學或歷史學等特定學科,而是多學科交叉,對同一對象展開跨學科研究,以加強對東南亞的綜合性理解,即東南亞研究的方法論是“綜合性”和“跨學科”的。末廣昭認為,東南亞研究并非與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等相并列的學科,而是理解他者的一種方法。坪內良博強調,東南亞研究就是“各種方法論的集合,旨在綜合理解該地區的特殊性”。立本成文甚至主張,只有超越單個學科的綜合性理解才是真正的東南亞研究。綜合理解東南亞是學者畢生追求的學術理想,但如果沒有正確的方法論作為指導,一味追求面面俱到,最終會陷入廣而不精的尷尬境地。而若過分執著于社會學或政治學等單個學科,則會成為井底之蛙,無法綜合理解東南亞整體面貌。盡可能減少這兩種弊端成為日本東南亞研究追求的目標。
為了實現對東南亞的“綜合性理解”,坪內良博主張,需要探索兩種可能性:一是自然科學各領域與人文社科各領域進行跨學科研究的可能性;二是對作為研究對象的生態、社會、文化進行綜合性理解和認知的可能性。通過這些認知和方法,力圖全面把握和理解東南亞各種現象。但上述方法具體如何實施,目前尚無標準答案。東南亞各地的生態、社會、文化之間的相互關系錯綜復雜,要想完全厘清幾乎是天方夜譚。為擺脫上述困境,日本學界提倡對東南亞這一“地區”進行劃分,在此基礎上利用交叉學科的方法開展跨學科研究,其觀點主要如下:
其一,東南亞研究的“地區”指的是共同的自然生態環境空間。所謂的共同“地區”是指整體的地理空間,這是地理學研究的對象。例如,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所非常重視自然生態環境,認為“地區”的定義和劃分都基于自然生態環境。高谷好一認為,“地區”的劃分源于生態環境的差異,這種差異小至民族國家,大至地球。但生態環境的變化速度和人類社會的演進速度完全不同。前者從人類史前時代開始,以100多年為周期才可完成漫長的環境變化。而后者到了現代,即便以10年為周期來計算人類社會的發展也勉為其難。因此,要想深刻理解現代東南亞政治經濟特征,就必須利用交叉學科的方法開展跨學科研究。
其二,東南亞研究的“地區”需要設定共同的、廣域的文明圈和文化圈。在此背景下,文明和文化意味著軟性的價值和信仰,而非硬性的形式或樣式,因而哲學、思想、宗教等人文科學非常適合開展東南亞研究。北原淳主張,隨著社會各領域功能的進一步分化,人文社科中的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宗教、文學、哲學等學科都得以發展。社會學與其他學科一樣,都是近代的產物,且統領所有學科的是古希臘哲學理念。東南亞的文明和文化豐富多樣,各學科之間缺乏共同價值,但日本的東南亞研究首先假定了類似于古希臘的東南亞共同文化圈,這成為其后東盟社會文化共同體建設的思想淵源。
其三,東南亞研究中的“地區”同時也指現代國家的領土、領海、領空范圍。這是政治學、經濟學等學科擅長的領域。在現代東南亞的社會變動中,殖民時期就已經基本確定疆域的民族國家發揮了巨大作用。在全球化時代,東南亞各國經濟聯系密切,民族國家不會輕易消失,且10個東南亞國家成立了東盟這一地區組織。古田元夫從東盟的擴大過程中發現了東南亞“海洋世界”與“陸地世界”的和解。此處所提及的民族國家、地區組織等可暫且歸為地緣政治范疇的地區。地緣政治意義上的“地區”是近現代的產物,這與自然生態學的“地區”相差較大。
概言之,日本學者普遍認為東南亞這一“地區”是文明文化圈、生態環境圈和政治軍事經濟圈的復合體。如果將“地區”視為特定區域內人民的生活環境,那么前兩者以相對漫長且間接的方式對地區施加影響,而后者則在短期內迅速影響地區。為此,日本東南亞研究強調應綜合考量東南亞的各種要素,即不能局限于狹隘的社會學,還要研究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等人文社會科學,以及環境學、農學等自然科學,具有綜合性和跨學科性。綜合地球環境學研究所持續強化文理融合研究項目,組織經濟、歷史、宗教、人口、水文、景觀、建筑、社會等學科專家開展跨學科研究,以解決超大城市病這一全球性問題,并進行消解貧民窟的實踐,出版《超大城市系列》,在理論研究和實踐創新方面取得不俗的成效。
三 日本的東南亞地區構想:整體性、多層性和分散性
迄今,日本研究了東南亞內部的各地區、各國和諸多領域,不斷深化東南亞研究的內涵,彰顯東南亞這一“地區”的整體性、多層性和分散性。
首先,就整體性而言,末廣昭主張,東南亞研究的目的和妙趣在于“整體性理解”,并非將研究對象(東南亞或泰國等)分成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來加以單獨理解。而從自然環境或生態環境來看,東南亞是典型的“森林”和“海洋”世界,也是“少人口世界”。高谷好一認為,森林密布的生態環境為東南亞世界的形成做出巨大貢獻。坪內良博繼而指出,由于東南亞自然和生態環境具有壓倒性優勢,所以與人類活動相比,二者對東南亞的整體塑造發揮了巨大作用,并遠超其他地區。日本學界普遍認為,自然和生態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東南亞的國家和社會,東南亞外部尤其是周邊的文明,例如印度教、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以及殖民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等也對東南亞施加潛移默化的影響。
具體而言,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在東南亞生態和環境研究方面取得矚目成就。該機構以綜合研究泰國的湄南河三角洲以及馬來西亞農村的水稻種植為契機,將各學科研究力量有機地組織起來,鼓勵自然科學和人文社科領域的學者頻繁接觸和交流,不僅組建了高效務實的跨學科研究團隊,形成特色鮮明的綜合性東南亞研究方法,更深化了日本對東南亞“整體性”的認知。在該機構對東南亞進行的調查中,涉及到自然科學和人文社科各個學科。自然科學主要包括諸如作物學、土壤學、水利學、森林生態學這樣的農學,牙醫學、病毒學、包含草藥在內的藥學、植物分類學之類的醫學和生物學,以及地理學等理學類學科。
對于跨學科的東南亞研究而言,自然科學領域學者的參與非常重要,隨著日本東南亞研究的不斷深入,逐漸形成既有方法與創新研究方法之間的有機結合,這體現出區域國別研究未來的發展趨勢。例如,1998年4月,京都大學成立亞非區域學研究科,該機構試圖采取各種方法實現全新的跨學科研究,進而催生出超越既有學科隔閡的區域國別研究。另一方面,雖然人文社科領域發生的變化沒有自然科學領域那般深刻,但其對東南亞“地區”的關注也得到增強,這將進一步深化日本對東南亞的整體性認知。從日本東南亞研究的發展趨勢來看,針對東南亞的區域國別研究(Area Studies)正朝著“區域國別科學”(Area Science)的方向轉變,即區域國別研究的作用不再局限于提供關于對象區域和國家的百科全書式的知識,而是嘗試構建跨區域的分析框架,例如基于人力動員的權力結構、以水稻種植為中心的社會組織、與外部世界的緊密聯系,以及包容性的血緣組織等。
其次,以上述整體性為基礎,若著眼于生態環境以及當地民眾的生活,東南亞又可劃分為若干個次級單位,次級單位還可進一步劃分為更細小的社會單位,此即東南亞“地區”的多層性。高谷好一將這些小單位命名為“世界單位”,他認為東南亞域內的世界單位主要有“大陸地區的山地世界”“泰國的三角洲世界”“海洋世界”“爪哇世界”等。高谷好一繼而強調,在研究東南亞域內的小單位如泰國湄南河三角洲農業、爪哇島灌溉系統時,如果忽視其周邊環境,那么即便其能夠成為區域國別研究的素材,也無法成為東南亞研究的核心。同樣,如果只關注東南亞或東南亞之中的“世界單位”,那么這些研究就可能空洞無物。對東南亞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明確該地區的范圍,同時也要重視區域國別研究的多層性。
如果將東南亞這一地區視為空間或地理范圍,就必須對其劃界,但劃界卻并非易事。矢野暢強調,學者根據國際政治的現實情況對東南亞地區進行劃分,但這些規則不只是二戰后美國的專利,也是現代歐洲的產物。東南亞這一概念本身就源于二戰和冷戰時期美國的全球戰略,基于歐美的世界觀及價值觀,這種地區劃分方式顯然站不住腳。坪內良博認為,根據氣候、植物、生物等生態環境劃界會相對容易,但如果將當地居民的社會文化也考慮在內,劃界就會變得困難重重。這是因為社會文化早已超越生態環境,不受其束縛,二者的界線并不一致。例如,一些學者基于印度教文化,試圖闡明吳哥王朝等東南亞古代王國的王權思想,卻難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可見,基于社會文化的劃界必然會擾亂地理界限,進而模糊地區的本質。地區的認定標準究竟應該基于生態環境還是人類社會文化,實在難以準確判斷。雖然生態環境與人類社會相互依存,但二者并非完全對應。因此在設定地區的范圍時,必須對該地進行綜合研究。
再次,不可否認,東南亞域內不同地區都具有獨立性,并呈分散性。東南亞在地理上分為大陸地區和海島地區兩大板塊,自古以來受印度、中國、阿拉伯、以及歐美等文化“中心”的影響,存在諸多王國,也有眾多少數民族部落,難以形成一個完整的東南亞層面的世界體系。白石隆認為,二戰結束前,東南亞的國家統一進程都比較緩慢,對后來建立更加復雜的現代民族國家也造成了負面影響。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較為復雜,外部因素是“少數民族”、“海洋世界”等的存在,內部因素則是多年以來的“分散結構”以及殖民統治下的分而治之政策。在東南亞國家追求民族獨立的過程中,民族主義是其擺脫殖民統治、開展獨立解放運動的精神支柱,亦是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原動力。但民族主義的意識主要存在于東南亞國家的精英階層和信息通暢的大中城市,在山區、離島和邊境等邊緣地帶的存在感較弱,因此在東南亞現代民族國家的邊緣地帶,仍有很多分裂獨立運動,流血沖突也屢見不鮮,例如菲律賓的棉蘭老島及緬甸北部地區等。
據此,山影進認為,應該將東南亞地區原有的分散性作為前提,在相互關聯性和網絡的基礎上重新構建地區概念。這說明開展地區間比較研究的重要性,進而促成了日本“綜合性”東南亞研究格局的形成。
概言之,就日本對東南亞研究的整體認知而言,最重要的是明確該地區的范圍,同時也要重視東南亞的多層性和分散性。在將“東南亞”視為整體性地區時,日本學者一般會突出其生態地理基礎,以此彰顯東南亞作為“地區”的特殊性。在某些場合,還會將東南亞劃分為若干次級單位,次級單位還可進一步劃分為更小的社會單位,即同樣重視東南亞“地區”的多層性和分散性。以此為基礎,一些日本學者試圖以“既零散又統一”的形式構建東南亞整體認知體系,并以各單位的共同基礎為背景,使之發揮合力。
四 日本東南亞研究面臨的挑戰
較之歐美國家的東南亞研究,日本的東南亞研究具有東西融合的研究方法和綜合性、跨學科性特征,且地區構想頗具特色,但也面臨諸多挑戰。
第一,日本東南亞研究面臨的首要難題是“要事實還是理論”,這個難題一直困擾著日本學界。即應該優先歷史事實,還是重視構建理論框架。盡可能收集詳細的歷史事實或數據對開展區域國別研究大有裨益。但有些學者認為區域國別研究既然是一個學科,就應該充分重視理論、模型等抽象概念,致力于將復雜的現象簡單化,而非僅僅收集數據。這種觀點顯然否定了盲目收集細致數據的做法,認為區域國別研究只能關注具有理論意義的領域,即區域國別研究的先決條件是“具有理論”。不尊重理論的學者只滿足于調查復雜的事實關系,而重視理論的學者只收集有利于其研究的數據或事實關系,以便在理論上自圓其說。例如,政治學者喜歡將復雜的事物簡單化,而歷史學者更尊重史實的細節,忽視背后的理論。如果研究同一個課題,政治學者就會批評歷史學者太拘泥于歷史事實,歷史學者也會批評政治學者輕視歷史事實。即便是關注東南亞現實問題的學者有時也會被調侃為“無專業”雜家,更遑論“跨學科”學者。學者如何保持上述兩種立場間的平衡,這是日本深化東南亞研究必須要解決的重要課題。
第二,學者分屬不同機構和學科,學科間對立難以調和。首先,大多數學者分散在大學不同機構之中,隨著日本科學研究預算整體削減,大學之間和大學內部的競爭激化,再加上輕視人文社科的風潮興起,沒有較大機構支撐的東南亞研究難以形成合力,發展堪憂。其次,對同一地區進行研究時,不同專業有時會得出相互矛盾的結論。例如在社會科學中,政治學和社會學的理論體系比較寬松,難以提出精確的模型或假說,其結論通常模棱兩可。相比之下,經濟學可以利用收入、儲蓄額、貿易量等可測量的變量進行計量分析,進而提出精確的模型。如果分別從政治學、社會學以及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同一地區或國家,結果可能會大相徑庭。政治學和經濟學究竟誰更正確,難以判斷。學者之間雖然相互尊重,可一旦跨界進入對方的研究領域,就會引發學科間的緊張關系。
第三,日本學者的一些學說難以反映東南亞國家現實。基于特定學說的政策主張即使再好,但如果不考慮東南亞當地民眾的接受程度,都無法實現。例如,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東南亞國家工業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受到質疑,有日本學者提出應大力發展環境友好且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相關理論層出不窮,例如“共同體”理論、“可能”理論、“授權”理論認為不應該過度依靠國家和政府,當地社區和民眾應當獨立自主。“以經濟發展為綱”的政策也引起了諸多環境問題和社會問題,有學者主張不應過度追求經濟發展速度,要重視“環境友好型發展”或“社會發展”。對此,北川隆吉擔心這些主張有如紙上談兵,未必都基于當地民眾的生活環境或感受,而是基于參與政策制定的活動家和官員的理念或思想,如果一味強行付諸實施,會與當地民眾的期望背道而馳。針對上述問題,山口博一強調,要想成為一名合格的東南亞研究學者,除了學科知識,還需要其他工具,即“對目標地區的關注、與當地民眾產生共鳴、居住在當地的經驗、對當地情況的了解、朋友和熟人關系、歷史和習俗知識、語言能力等”。
第四,日本東南亞研究成果水平雖然不低,但大多用日語發表,很少使用歐美語言,因此鮮為國際學界所熟知。很多日本學者雖精通東南亞地區、國家和社會的情況,但其有關東南亞的很多研究成果過于糾纏于細枝末節,無法縱覽全局。即便想縱觀全局,很多人有時也會不經意間局限在自己的狹隘領域內無法自拔。此外,或許是近年來田野調查變得容易,很多研究都過于倚重自己的田野調查數據,忽視參考東南亞及歐美學者的研究成果,這一問題也值得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