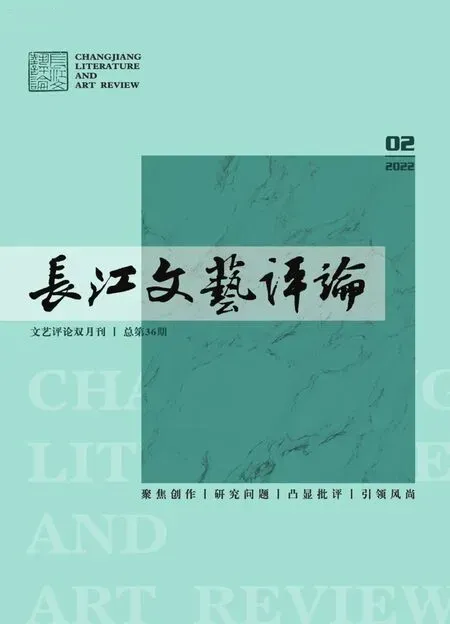見證武漢抗疫 建構歷史記憶
——關于劉醒龍的《如果來日方長》
◆陳國和
2020年初從武漢開始,蔓延全國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2020年1月30日世界衛生組織將其列為“世界衛生緊急事件”。(十七年前的SARS僅被列為“全球衛生突發事件”)。為防控疫情,2020年1月23日(除夕的前一天)武漢宣布“封城”,全國各地疫情防控應急響應提升至一級響應。武漢交通停擺、小區封閉、居民足不下樓,昔日熙熙攘攘的街道空寂無人,陷入一片恐慌之中。疫情打破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習慣,迫使人們以幸存者的眼光重新審視人生、審視自然、審視世界。劉醒龍的《如果來日方長》就是這樣一部具有堅定人民立場,見證、記錄武漢抗疫全過程的非虛構散文。
一、見證與謳歌
毋庸諱言,盡管當下武漢恢復了原有的活力,但新冠肺炎曾給武漢造成重創,全國十幾億人出行受限,停工停產近兩個月。這一創傷將長期影響我們的生活和歷史。該如何應對這場災難?見證創傷、接近真相成為劉醒龍毫不猶豫的選擇。創傷主要指生理、心理等遭受突然的、未曾預料的傷害,“一種經驗如果在一個很短暫的時期內,使心靈受一種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謀求適應,從而使心靈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擾亂,我們便稱這種經驗為創傷。”
一般說來,只有災難的親歷者記錄的真實災難故事才能稱為見證文學,也就是說見證文學必須具備兩個基本要素,第一,文學的寫作者必須為災難的親歷者;第二,親歷者講述的災難故事是他在遭遇創傷時的所見所聞所思,必須真實可信。親歷者對書寫內容的真實性負責。從這個角度看,《如果來日方長》可以列入見證文學的范疇。劉醒龍以現場目擊者、幸存者的身份進行創作,見證武漢的創傷,關注普通人遭遇災疫時的恐慌和無奈,表達了一名作家的悲憫情懷,在讀者中產生了極大共鳴。這種共鳴主要源于《如果來日方長》的日常生活書寫。
1980年代以來,日常生活就是中國當代作家日益嫻熟的書寫題材和書寫策略。但是在不同年代的創作潮流中,日常生活書寫被賦予了不同的意識形態內涵。1980年代中后期,以池莉、劉震云為代表的新寫實作家,通過感情的零度寫作、關注小人物吃喝拉撒睡的日常生活,從而達到解構、顛覆革命現實主義的目的。1990年代,韓東、朱文、邱華棟等晚生代以日常生活作為書寫內容,重視個人的自我經驗,與既定的文學體制“斷裂”,拒絕歷史書寫和藝術形式實驗,直面當下中國激烈變動的社會現實。新世紀以來,魏微、魯敏等“70后”作家聚焦當下生活的感受和溫情,展示卑微鮮活的生命形態,重構日常生活的美學形態。但是,《如果來日方長》的日常生活書寫與任何文學思潮無關,也不參與意識形態的訴求,是劫后余生的幸存者的見證書寫。《如果來日方長》繼承的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災難書寫的現實主義傳統,延續的是中國現當代文學苦難書寫的現代性敘事。這部20萬字的散文“從老母親在疫情高峰時患病起,到二叔因為疫情次生災害病故,盡可能從細微處入手,表現‘封城’之下一個武漢家庭,男女老少,力所能及,所思所想的生活情愫,以細流通江海的情懷。”“我們要做的不過是睜開我們的眼睛,離開形而上學的黑暗世界,離開虛構的‘內心世界’的深度。這樣,我們就會立即發現日常生活的最平凡事實里所包含的人類財富。”
《如果來日方長》的日常生活不是國家敘事,也不是革命敘事。《如果來日方長》所具有的真實情感,使讀者在閱讀時有鮮明的代入感。這是這部長篇散文能和讀者共情的主要原因。從這部長篇散文各章節的小標題就可看出作者日常生活敘事的書寫策略和觀察視角。如“今年水仙花不開”“你在南海游過泳”“問世間情為何物”“九七年的老白干”“情人節的菜薹花”“洪荒之力滿江城”“冥冥之中自有天理”。如文中記載了“封城”后的第十九天,也就是2月10日下午,硚口區一位七十高齡的老者因為高度疑似感染,加上患有尿道癥,和妻子說一句“我不想連累你”,就跳樓自盡。“人心之悲,從生到死。人心之累,從生到死。人心之痛,從生到死。從人心之生,到人心之死,可以是人還活著,心已僵死。”人生卑微、命運無常的慨嘆躍然紙上。《如果來日方長》把武漢人的委屈以及個人遭遇真實地記錄下來。同時,劉醒龍也是時代的記錄員,創傷經歷的個體性與公共性產生了極大共振。
《如果來日方長》不僅見證災難現場,還見證歷史氛圍。對于一直在抗疫現場的劉醒龍來說,不可避免地會有幸存者的心理體驗和精神創傷帶來的精神恐慌。這種情感體驗反過來強化了劉醒龍對人生和社會的無力感,反映了普通市民在遭遇災難時的虛無和恐慌。瘟疫的創傷、末日的體驗使得劉醒龍將書寫的重心聚焦于個體的命運,著重于遭受災難創傷的個體命運的掙扎。杰弗里·C·亞歷山大說:“當個人和群體覺得他們經歷了可怕的事件,在群體意識上留下難以磨滅的痕跡,成為永久的記憶,根本且無法逆轉地改變了他們的未來,文化創傷就發生了。”文學是人類文化記憶的主要載體,是表達情感,拒絕遺忘,見證歷史的重要方式。與疫區的武漢市民感同身受,共呼吸、共命運,劉醒龍用文字慰藉著這座城市,關懷著這些善良的人、平凡的事,以及那些需要被安慰的心靈。
當人們遭遇從未經歷過的災難時,通常的制度、手段和認知暫時失靈,人們往往陷入某種恐慌之中,需要尋找值得信賴的對象作為心靈支撐。劉醒龍和其他專家、學者如鐘南山、張文宏等一樣,承擔了這一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劉醒龍作為生命個體在面對生命威脅時,首先想到避免自我和他人生命的無辜消亡,及時清除雜音,給恐慌的疫區市民提供生活真相,安撫人們恐慌的情緒。也許劉醒龍并不是一個熱衷于公共事務的人,但是,作為作家,他關注民生和世道,關注個體的生活。
二、歷史與記憶
作為見證文學的《如果來日方長》強調個人性,從親歷者的經歷、情感及立場進入災難現場,形成敘述,進而深入到普遍性層面,與國家權威敘述、集體性敘述、宏大歷史敘述區別開來。
莫里斯·哈布瓦赫認為,“記憶事實上是以系統的形式出現的,而之所以如此,則是由于,記憶只是在那些喚起了對它們回憶的心靈中才聯系在一起,因為一些記憶讓另一些記憶得以重建。”哈布瓦赫將記憶理解成個體參與社會化的結果之一,強調記憶的社會性。揚·阿斯曼在哈布瓦赫“集體記憶”概念的基礎上提出了“交往記憶”與“文化記憶”這兩個概念。揚·阿斯曼所謂的“交往記憶”,是指對剛剛逝去的過去的回憶,同時這種記憶也是人們與同時代的人共同擁有的回憶,其典型范例就是“代際記憶”。顯然,劉醒龍的紀實散文屬于這類范疇。雖然《如果來日方長》屬于幸存者的個人書寫,但是,它記錄的是“同時代人的共同擁有的記憶”。某種意義上說,《如果來日方長》像災難的信息存儲于中樞,將各種信息進行綜合,經過思考后形成文字,從而書寫出武漢抗疫的“交往記憶”。
劉醒龍對“個人記憶被規劃、取代和抹殺”的命運保持高度的警惕,畢竟在歷史上,國家記憶、集體記憶總是覆蓋、改變著我們個人的記性與記憶。劉醒龍在散文中不斷記錄孫女的一些日常生活,對夫妻關系、親子關系也進行了形象的展示。在大家平時習焉不察的日常生活細節中發現生活的微光以及人間善的力量。物資如鹽、牙簽、衛生紙等在特殊時期都成為了平常人關注的重點。《如果來日方長》中兩種記憶、兩種歷史書寫話語權相互纏繞、彼此爭奪。劉醒龍作為現任湖北省文聯主席,首要任務是用文藝的方式為醫護人員鼓勁,給武漢疫區市民以希望。而同時作為普通市民、祖孫三代的頂梁柱,首先想到的是底層的真實處境,從普通市民、幸存者的角度,強化創傷記憶。
1990年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崛起,人們越來越世俗化,知識分子也不能例外。精致的利己主義者越來越為人們所詬病。當出現公共危機,需要知識分子發聲的時候,很多人鼓勵別人說真話,權衡利弊后自己卻選擇沉默,明哲保身。這些知識分子自覺放棄了對真相的追逐,放棄了知識分子的良知和應承擔的社會責任。武漢抗疫期間,情況依然如此。很多學者僅限于相互鼓勵對方熬過這段日子,沉默成為大多數人的明智選擇。《如果來日方長》在特殊時期能夠喚起人們對事件真相的關注,同時在溫和謹慎的語言中攜帶了創作者外柔內剛的立場,而這也是劉醒龍近年來小說創作傾向中越來越明顯的立場,如《蟠虺》等。這種文化實踐為挽回知識分子的名譽作出了突出貢獻,直接續接了魯迅、胡風、巴金所開創的現代知識分子的人文傳統。
真正高明的文學是作家對歲月和人生的私人化訴說,文學沒有必要采取意識形態的宏大敘述模式。劉再復認為“文學是充分個人化的事業,(不是‘經國之大業’),是心靈的事業,是生命的事業。文學應當走向生命,不應當走向概念、走向知識。生命語境緊連宇宙語境,生命語境大于歷史語境與家國語境。作家當然應當有較強文采的修煉,但更根本的是生命的修煉,境界的高低是生命煉獄后所抵達的精神層次。”劉醒龍的武漢抗疫書寫放棄了先驗的對世界本質的占有和構造,或者將所謂歷史的本質予以懸置。這些知識分子超越了政治、超越了利益,尊重內心和自我,在記憶書寫中見證創傷、拒絕遺忘,反思歷史,從而使得武漢抗疫書寫具有了人類意義。
三、反思與重建
《如果來日方長》凝聚了一種理性精神,呈現的正是作家的良心和現實關切。他的理性不迎合、不盲從、不偏聽,始終體現為家國天下的憂患意識和慈悲情懷,并且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建設性。
反思是理性的建構,憂患就是理性的表達,思想就是理性的升華。劉醒龍主要從倫理角度反思這場瘟疫,強調常識的重要性。關于武漢疫情的反思是緊隨疫情防控工作開始的,各行各業的知識分子都參與其中。如2月23日,《中國科學:生命科學》雜志在線發表了由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國強牽頭的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團隊撰寫的專題評述論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下的思考和建議》,論文從我國公共衛生防控體系、應急響應機制、科技創新、醫療供給與儲備等十大方面的問題進行系統梳理,并在此基礎上著重就加強公共衛生和疾病防控體系、完善應急防控體系、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公民知識普及力度、構建相關法律法規體系以及國家生物安全體系等提出相關建議。陳國強院士主要從技術層面對這次災難進行反思,這確實很有必要。這些建議也具有較強的現實針對性和建設意義。但是這次疫情不僅是自然問題,更是社會問題,僅從技術層面反思顯然不夠。
馬克思·韋伯將人的日常行為倫理分為兩種: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信念倫理是指“一個人按照信念倫理的準則行動”,不在乎結果;責任倫理是指“當事人對自己行為可預見的后果負有責任”。在世俗社會,人們的信仰、價值觀千差萬別。顯然,對此、對現世、在責任倫理越強,行動的目的—工具合理性就越強。責任倫理是建立在契約精神和個人信用之上的。顯然人們更相信劉醒龍以幸存者的視角,來觀察、書寫和反思疫情。《如果來日方長》這種書寫看似事無巨細,婆婆媽媽,實則直達人心。
在這場生命攸關、前所未有的重大疫情面前,公眾需要的是真實和共情的人性視角。這是劉醒龍自始至終秉持的立場。正如劉醒龍慨嘆:“當時1000多萬武漢人,留守家中,用身體的每一個細胞進行抗爭。武漢之美,美就美在即使天下之險迫在眉睫,人們還能憑著對一碗熱干面的熱愛,陳述這座城市的堅強。”這要求作家具有對時代整體觀察的視野,對世間萬物悲天憫人的情懷,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感同身受的洞察力。
知識分子的代表在于“行動本身,依賴的是一種意識,一種懷疑、投注、不斷獻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斷意識”。可以說,記錄災難、反思災難,建構創傷記憶是作家的責任和義務,是人文學者的良知和職業倫理。當然,這種責任倫理不僅僅體現在作家及知識分子身上,也不僅僅體現在醫護人員身上,還體現在其他人如快遞小哥、廚師、警察、清潔工、志愿者甚至政府機關的公務員等普通人身上。
字字見血的文字讓人間見證了劉醒龍的良心。知識分子也在反思中完成自我救贖。“不僅武漢戰‘疫’”,其實,中國知識分子一直在見證和反思民族苦痛史中成長、進行著自我救贖。“不同于以往,記錄這些同行,能讓人體會到那些微不足道的普通舉動背后,那種比漢江長江還要源遠流長的深情。”《如果來日方長》和巴金的《隨想錄》等一系列民族創傷記憶書寫一起建構歷史,拒絕遺忘,繼承了魯迅、胡風、巴金等人建構的現代知識分子人文傳統。
令人高興的是,盡管劉醒龍對人性之惡、民族之痛有通透的認識,但是,他對未來、對社會、對人類一直充滿信心,并積極尋找救贖之路,《如果來日方長》讓人看到黑暗中的光亮,如文中對小孫女的焦點敘事,就給讀者無限的希望,讓人喜愛、給人力量。毋庸諱言,如此近距離,急迫地書寫災難、見證歷史,部分篇什不可避免地顯得匆忙,很多問題深入不夠,等等,這些都影響了《如果來日方長》在藝術上的高度。但是,在武漢抗疫的危難時刻,劉醒龍一直在場,積極進行文化實踐,使我們有理由對現代的人文精神傳統保持信心,并期待劉醒龍更偉大的作品誕生。
注釋:
[1]【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高覺敷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216頁。
[2]【法】克洛德·穆沙:《誰,在我呼喊時:20世紀的見證文學》,李金佳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5頁。
[3]【法】亨利·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葉齊茂、倪曉輝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122頁。
[4]【美】杰弗里·C·亞歷山大:《邁向文化創傷理論》,《文化研究》第11輯,王志弘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頁。
[5]【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畢然、郭金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頁。
[6]揚·阿斯曼對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概念進行了修正,他認為記憶的主體依然是個體的人,但個體的記憶受制于組織其回憶的“社會框架”。在揚·阿斯曼看來,“如果一個人或一個社會可以記住的,僅僅是那些處于每個當下的參照框架內、可以被重構為過去的東西,那么被忘記的恰好是那些在當下已經不再擁有參照框架的東西。”見【德】揚·阿斯曼:《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金壽福、黃曉晨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頁。
[7]唐忠毛:《記憶理論視野中的文化傳承問題》,《南京大學學報》,2017年第6期。
[8]劉再復:《論八十年代——答廣州〈新周刊〉雜志董薇問》,《劉再復對話集——感悟中國,感悟我的人間》,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頁。原載《新周刊》,2005年第8期。
[9]【美】愛德華·W·薩義德:《知識分子論》,單德興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