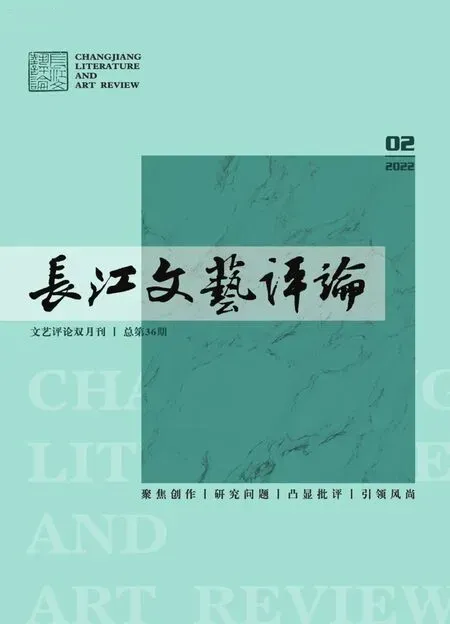革命者·偶像·“反英雄”
——試談改革開放以來哪吒動畫形象的時代嬗變
◆陶 冶 劉思彤
自改革開放以來,哪吒的神話故事先后經歷了五部國產動畫片的改編。這42年里,不僅中國從改革開放走到了新時代,國產動畫也經歷了從輝煌到低谷直至今天的“國漫崛起”。在這種時代變遷的背景下,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將所處不同時期的動畫文本中哪吒成長敘事的差異,全盤視為創作者主觀的藝術觀念所致,誠如饒曙光所言,動畫創作“本質上是一種文化活動,對其的根本性解釋需要從生產的時代語境中探索答案”。并且,動畫作為凝結了大量勞動的文化產品,恐怕時代的集體意識對作品的創作有著更大的影響。
革命英雄的新時期斗爭
1979年出品的動畫電影《哪吒鬧海》,其里程碑意義不僅體現在它是中國第一部寬銀幕動畫片,也是中國第一部在戛納參展的華語動畫電影,更為重要的是它身處剛剛結束“十年浩劫”,迎來中國社會轉型的“新時期”。一方面根據神話改編而來的《哪吒鬧海》成為反思“文革”期間“題材禁錮的媒介載體,積極回應著解放思想的時代方針”;另一方面,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的創作者們又通過對《封神演義》中相關情節“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改編,彰顯了這一時期中國動畫創作者“破舊迎新”的創作理念。
創作者們對該片進行了全齡化觀影的定位,《哪吒鬧海》的導演兼編劇王樹忱曾撰文回憶當初選擇這個題材的初衷,就是因為“它是少有的以小孩為主角的神話,這段故事給小孩和大人都合適”。同時,對于哪吒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導演表示“要讓人們感到他活著可愛,死了可惜,復活有理”,使作品呈現出一種兼具了正劇和悲劇的風格。這種新的藝術觀念具體表現在對國產動畫低齡受眾定位的突破,并在與時代的互映中構建起了觀眾的情感認同。
(一)反帝反封建的斗士
1979年的《哪吒鬧海》對明代《封神演義》中有關哪吒的故事情節較為顯著的改編,便是將哪吒大鬧東海的行為動機從頑皮惹禍改寫為救人心切。影片中作為一方天官的龍王卻要吃掉人間的童男童女,如此一來,影片中的正邪對抗其實是包裹了一些微妙的階級對立意味,無形中承接了“十七年”革命電影中的敘事邏輯。它繼續上演了“那些由無辜的受害者(陳塘關的百姓),勇敢的抗議者(革命者哪吒),清醒成熟的智者(支持哪吒復仇的太乙真人),與邪惡、非人的惡勢力(腐敗的權力專制龍王)之間的生死角逐”。當然,影片中與哪吒對立的是“舊”有的腐敗專政,因而它可以被合理地質疑和批判,這也是作為“新”的上層機制所給予藝術家有限的話語權力。而個體的抗爭總是要與國家的民族的解放連為一體,才能在這一時期進一步凸顯出意義,就像影片中的哪吒決心打敗龍王并非為己,而是為了拯救整個陳塘關百姓,他的“革命行動”始終圍繞著人民利益出發,繼續實踐著“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主流意識形態。
影片中所體現出的哪吒的革命意識也并非只是推翻專制的暴權,而是通過暗合在故事情節里的父子沖突,呈現出對封建落后文化一定的反思。影片中李靖身為哪吒的父親非但沒有肯定哪吒的救人之舉,反倒對哪吒呵斥“你怎敢傷害天庭龍種”,進一步彰顯了封建綱常倫理的愚昧性。而那個自己受了委屈還怕連累父親的哪吒,如此寫實地反映了長久以來被父權壓迫的子一輩無奈的心理,因而哪吒選擇以自刎完成了自己的“孝道”尤為令人痛心。當對抗龍王時威風凜凜的英雄哪吒,也因無法回避這種“父父子子”的情感糾纏而倒在血泊之時,反而將影片反強權反壓迫的斗爭精神推向了極致。誠如戴錦華在描述“新時期”涌現出的文化英雄那樣,哪吒“作為一種體制的批判者,以燃燒自己的方式而照亮了前方黑暗,成為了當然的這一時期的引路人”。如此,《哪吒鬧海》這一全齡化的成長故事,對于兒童來說,它無疑是再次講述了一個正義終將戰勝邪惡的童話寓言,而對于經歷文革傷痛,迎來思想解放的成年觀眾而言,顯然它是蘊含了啟蒙精神的典范。
(二)“大團圓”的人道主義
誠如王樹忱導演的筆述,影片中的哪吒是飽含了悲劇色彩的英雄,出于解救小伙伴的正義之舉卻讓他承受了生命的代價,而更顯悲劇性的是,這一結果又是由哪吒的父親間接導致的。在影片的高潮——“哪吒自刎”的情節點上,四海龍王以陳塘關百姓的性命相逼,而關鍵時刻哪吒的法寶又被父親收繳,致使其無力對抗龍王。
在這個敘事段落中,導演以哪吒的視點快速銜接了一些百姓們受苦的近景和特寫鏡頭,目睹了這一切的哪吒毅然決然地拿起了地上的刀劍。影片灰暗的色調將英雄赴死的悲壯氛圍烘托到極致。而叼著法寶奔向哪吒的梅花鹿也未能實現“最后一分鐘營救”,不甘屈服的哪吒就這樣成為了舊惡勢力壓迫下的祭品。到了影片后半段的情節,哪吒復活的眾望所歸,以及哪吒殲滅妖龍的大快人心,將影片前期的悲劇基調陡轉為“大團圓”結局,應驗了革命的前途——“社會主義事業必將取得最終勝利”神話預言。
全片最耐人尋味的是結局的那一幕,打倒了龍王的哪吒腳踩著風火輪,在小伙伴與疼愛他的管家的歡呼聲中歸來,作為英雄的他貌似又回到了人民群眾中去。可是隨即哪吒又騎著他的小鹿大步奔向了遠方,他去了哪里我們不得而知,但正是如此,給予了觀眾足夠多想象的空間。而且歸來這一幕全然不見了曾經將他束縛住的父親,是否也象征著哪吒已經擺脫父權的那層壓迫?這種聯想并非毫無根據,在中國社會轉型的“新時期”,“解放思想”的政治方針也一同帶來了70年代末人道主義思潮的興起,也使得藝術家們將創作的思考落在了如何反映“人”的價值和尊嚴這一點上。
影片中的哪吒經歷了九死一生的磨難才得以重新回歸,與遭受了十三年打壓,在“新時期”涅槃重生的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有著幾乎一致的境遇。換言之,創作者們將自己所處變革時代獲得的直接經驗,已經表露在了哪吒的“英雄旅程”里,而影片中的成長敘事,并非只是為了滿足藝術家個性的宣泄,而是盡可能地映照出時代的其他景觀。哪吒的成長之路喚起了部分創傷記憶,而其奔向自由的結尾則回應了人道主義思潮下,大眾對新生活的向往。這不僅是一次對群體情感經驗的總結,更是一次集體潛意識的流露。
少年英雄的新世紀蛻變
進入新世紀后,經濟全球化浪潮所帶來的卻是第三世界國家民族主體身份的危機,不僅一種反思和質疑全球化的思想在國內蔓延,而且傳統文化復興的民族化思潮也進一步滲透到了文藝創作的實踐中。在國產動畫領域,神話作為一種傳統文化資源被再次喚醒和激活,“哪吒”作為家喻戶曉的神話英雄也再一次呈現在了影視作品中。首先是2003年中央電視臺所播出的52集電視動畫片《哪吒傳奇》,曾為當年的央視創下了7.06%的高收視記錄。而2016年的《我是哪吒》更是打著“國內首部以哪吒為主角的3D動畫電影”的名號與觀眾見面。相比于前作《哪吒鬧海》,這兩部動畫片中最明顯的變化,是對哪吒以更貼近現代兒童的形象進行塑造,其“英雄之旅”也更像是一場兒童世界的冒險探索,盡管影片也還是一如既往地以主人公打倒反派、拯救世界為結局,但其成長的重心是凸顯身為“兒童”的主人公性格的蛻變和收獲。動畫片中哪吒的英雄蛻變更像是現代少年兒童成長生活的投射,換言之,這兩部動畫片中都有意將哪吒的“英雄之旅”與現代少兒的成長軌跡縫合,使得哪吒不僅被塑造為動畫片中的少年英雄形象,也力圖將其打造成為文本外部少兒觀眾的偶像。
(一)兒童教育的功能性期待
從哪吒的視覺形象上看,2003年《哪吒傳奇》儼然是沿襲了《哪吒鬧海》中剛出場時身著紅肚兜的小娃娃形象,一方面《哪吒鬧海》和《哪吒傳奇》中主人公的視覺年齡都指向孩童,這固然是對神話里哪吒原型的還原,但在2003年《哪吒傳奇》中哪吒的性格特征顯然更貼近于現代少年兒童。哪吒傳奇的導演曾坦言,在塑造哪吒這一人物時,是有意凸顯哪吒的孩童特征,要將其視為一個正在成長的小英雄。如此來看,“小”和“英雄”正是導演對哪吒形象塑造的重要指導理念。
一方面對“小”的強調使得正在成長中的哪吒被允許暴露一定的缺點,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哪吒傳奇》中那個起初有點驕傲自負的哪吒,那個因為貪玩弄丟了盤古石的哪吒。但“英雄”的所指,又強調對哪吒正面形象的塑造,并能通過電視機“合家歡”的效果達到教育青少年兒童的目的。換言之,創作者們實際上是以《小兵張嘎》的方式在塑造著哪吒的形象。另一方面,199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于進一步做好文藝工作的若干意見》中,進一步提出少兒文藝作品應當增強知識型和趣味性。這更在一定程度上引導了新世紀后動畫片創作方向的調整,消解了上個世紀的小英雄天生的“正義凜然”,而是呈現一個更能被少兒觀眾所認同的,與自己一起成長的“朋友”。
在革命記憶日漸遙遠的新世紀,時代的輕松氛圍也使得英雄背負的使命不復上個世紀的沉重感。與《哪吒鬧海》中那個需要反權威斗父權的哪吒相比,一種更無憂快樂的小英雄形象,呈現在了彼時的動畫熒屏上。新世紀以后哪吒“英雄旅途”的重點也相應地不只是描寫英雄如何歷經磨難為世人帶來正義與光明,而是強調其如何在冒險路上,長知識長本領,形成正確的道德品質。甚至在《哪吒傳奇》每集大寫的片頭中,都會出現“信義無價”這樣直接的“中心思想概括”。并且,“夸父追日”“女媧補天”等一些指向優秀品格的故事,也被雜糅到了《哪吒傳奇》中演繹,這無外乎也是社會對新一代少年兒童的教育期待,使得少年英雄小哪吒可以被清楚地認定為是新世紀的“社會主義接班人”。
(二)少年英雄的全球化想象
作為中央電視臺耗時三年,總投資上千萬元人民幣的力作,《哪吒傳奇》的導演在其創作闡述中,曾談到“我們長久以來渴望創造出具有中國風格、民族氣派的動畫片,塑造出中國的卡通明星,讓中國兒童歡喜,乃至受到世界兒童的喜歡。”話語背后是對國內動畫市場長期以來被美日動畫片所占領的一種文化焦慮。實際上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一系列引進的外國動畫片就受到了國內青少年兒童的極度喜愛,有調查顯示,在90年代北京電視臺播放的動畫片中,迪斯尼出品的動畫占到了百分之五十,美日動畫加起來的占比遠超國產動畫。因而對哪吒以更貼近現代兒童的特征塑造形象,幾乎已經上升到彼時國產動畫與國外動畫競爭中國兒童收視主導權的地步。
然而矛盾的是,當少年英雄小哪吒被視為是一種民族文化對外來文化的抵抗,并希冀他也能實現“文化走出去”之時,我們仍然能在《哪吒傳奇》中看到不少迪斯尼動畫的影子。尤其是該劇中作為哪吒成長道路上的伙伴“小浣熊”的加入,顯然是在1999年迪斯尼動畫《花木蘭》在國內上映以后,國產動畫中才出現這種主人公和他的動物小幫手設置。事實上,該片一方面希冀通過對傳統民族文化的挖掘,宣誓全球化下“自我”與“他者”的差異;而另一方面,又能在“自我”的身上不斷找到“他者”的影子。這種斷裂和矛盾,不只體現在新世紀以后國產電視動畫片的創作領域,在動畫電影的創作中也比比皆是。2011年上映的國產動畫電影《兔俠傳奇》中兔二的“英雄之旅”,和2008年美國夢工廠出品《功夫熊貓》中阿寶如出一轍,無一例外都是平民英雄歷險歸來、實現夢想的故事。
再看2016年動畫電影《我是哪吒》中小主人公離開家實現夢想,進而拯救世界,最終重回家庭收獲愛的情節,其實也并沒有跳脫20世紀90年代以來,迪斯尼動畫奉行的“兒童冒險+溫情路線”的敘事模型。誠如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所言:“人們只有分享共同的東西,才能在差異中彼此共存”,顯然,在全球化浪潮中,多元文化的碰撞之后的互相融合不可避免,對于國產動畫創作亦是如此。
另類英雄的新時代自信
在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主題的新時代,大國崛起所帶來的文化自信,也在2015的《西游記之大圣歸來》(以下簡稱《大圣歸來》)的市場逆襲之后涌入動畫電影的創作領域,某種程度上造就了今日所謂之“國漫崛起”。
《大圣歸來》的標志性意義,還在于國產動畫的創作終于可以呈現出一種由低幼化逐漸轉變為面向全年段受眾的趨勢。而其塑造的另類英雄孫悟空的形象,是與傳統英雄完全相悖的“反英雄”。顯然,這種“反英雄”的塑造到了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簡稱《魔童降世》)及2021年《新封神榜:哪吒重生》(以下簡稱《哪吒重生》)仍在延續。《魔童降世》的導演餃子在接受采訪中多次表明是《大圣歸來》給他帶來的信心,甚至在該片以50億票房榮登中國電影史第三位的當日,其官方微博還主動提及《大圣歸來》并予以致謝。而《哪吒重生》的導演創作之初就是想要以年輕一代的情感召喚一個全新的哪吒。這兩部作品與《大圣歸來》有著一致的內在敘事邏輯——講述一個現代人的成長故事。
(一)英雄自反與觀眾鏡像
2019年《魔童降世》中一個煙熏妝的丑哪吒,極大地顛覆了觀眾對哪吒的既有印象;而2021年《哪吒重生》中的哪吒更是化身為騎著摩托車的熱血青年。他們對于哪吒不僅只是顛覆前作中哪吒的視覺形象,而且在主人公身上還賦予了明顯的“反英雄”特征。
《魔童降世》中的哪吒被設定為魔丸出世,當面臨他人的誤會時,他并不會選擇忍氣吞聲,甚至會如反派般予以暴力相向;而《哪吒重生》中的主人公李云祥,盡管是迫于生計,但其確實一直從事著非法走私的活動。這兩部影片中的英雄主角形象所體現的復雜性恰恰就是成人世界灰色地帶的縮影,從而使之有別于傳統英雄故事里善惡分明的設定——顯然這種灰色的人物設定,就表明了影片創作之始便不打算面向低齡化群體。
兩位主人公身上所體現的不止于要褪去了英雄完美的外衣,暴露出一定的性格缺點,而是他們發出了一種共同的困惑——“我”是誰?這是在前三部哪吒神話改編動畫片中均未呈現的。顯然,這種“我是誰”的困惑恰恰也投射了銀幕前的觀眾對自我的追問——以80后和90后為主要消費群體的目標觀眾,恰恰是中國計劃生育背景下獨生子女的一代。有學者曾經這樣描述過這個群體的心理特征是:“因為缺乏兄弟姐妹,總是會顯得孤獨,又因為一直是家庭的中心,使得他們更關注于自我”。因此他們一開始就能夠體會到影片中主人公的孤獨和自我懷疑,對于人性曖昧不清的理解,對人與群體之間的隔閡,正是這部分群體共有的精神困境。
從角色認同的角度看,他們更能與影片中“反英雄”特征的主人公產生強烈的情感共鳴,而影片的“英雄之旅”所完成的根本上說恰恰是個體對于“我是誰”的解答過程。毫無疑問,幾乎所有的藝術作品本身都會存有藝術家個人的情感投射,而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魔童降世》和《哪吒重生》的導演都是80后,影片打動的也恰恰是銀幕前的80后觀影群體。或許也可以這樣理解為,在一個缺乏自我認同的時代,電影銀幕就成為了一面鏡子,銀幕中的與觀眾產生共鳴的“反英雄”,投射出的恰恰是觀眾自我認同的鏡像。
(二)個人情感與集體理想
“反英雄”并不是代表著反對英雄,只是淡化了先天的英雄主義,讓英雄從神性中回到普通人的身份上來。英雄作為人類集體無意識的一種心靈符號,無論在何種時代和社會語境下,它都能被有效地召喚出來。有學者認為,在當代社會,急劇的社會變遷會帶來人們對“英雄功能”的質疑。但與此同時,在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中卻呈現出一種積極的辯證法:“一方面是個體心理空間的擴大的同時也會帶來公共服務意識的生長”,個人往往還是會歸屬到集體中,找到自我的價值。
正如《魔童降世》中,哪吒是因為想改變他人的看法,所以開始跟著太乙真人學習了法術,欲通過降妖除魔來尋找自我價值,而他最后返回陳塘關,也是因為他被父親李靖愿意以命換命所感動,但影片最后呈現的還是哪吒拯救了陳塘關。影片的大結局是以一個全景鏡頭交代了陳塘關百姓對于哪吒的感謝和認可,而看到這一幕的哪吒也深受感動。可以說,哪吒拯救陳塘關所以他成為了英雄,同時回到集體中的他,也獲得了改變。
在《哪吒重生》中,李云祥打敗了東海龍王,實現了個人復仇,但同時他也阻止了海嘯的來臨,拯救了東海市的百姓們。這也是中國的英雄大片與好萊塢大片所呈現的完全個人英雄主義最大的不同。盡管新時代以來的國產動畫電影更多地彰顯了人性與情感的主體地位,但歸根結底,中國式的英雄敘事并不會凸顯個人與集體的二元對立,而是將個人與外部世界力量融合在一起。這是能繼續響應新時代的主流價值觀體系,同時又能讓觀眾產生認同型互動的英雄。
事實上,從2015年暑期的《大圣歸來》開始,近幾年涌現出來的頭部動畫電影中,都非常注重對個體微觀經驗的闡述,將高高舉起的英雄主義回歸到日常平淡的敘事中。“反英雄”人物塑造的有效性,其實是將個體的話語表達與現實生活中的景觀實現深度的套嵌,從而建構起觀眾對人物的情感認同。此時,英雄的深刻性得以彰顯———他/她不是某一個人或某一部分群體的鏡子,他/她最終仍然會回到主流價值的話語中,從而在集體認同中獲得“我是誰”的自我認同。
結語
從1979年的《哪吒鬧海》開始,國產動畫片中哪吒“英雄之旅”變遷的敘事邏輯,恰恰是從中國邁入改革開放以來,國產動畫創作與不斷更替的社會文化和市場環境的融合。而“哪吒”從革命英雄到少年英雄再到“反英雄”的變換,一方面體現了國產動畫創作努力探求與時代同步的文化自覺,另外一方面也帶來了今日國產動畫的創作實踐應該思考的現實問題,即夾雜在與好萊塢動畫和日漫競爭中的國產動畫,如何以傳統文化為根,同時又能適應當代受眾的文化心理。正如那些已經取得票房佳績的現象級國產動畫,既重拾了對中國悠久神話故事的改編,喚醒了國產動畫電影的傳統文化因子,同時又以對英雄情懷的當代性書寫被盛贊為是對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轉化。
首先,國產動畫英雄敘事的核心應落腳在對社會共同情感的表達上。《哪吒鬧海》中的革命英雄曾經呼應了新時期啟蒙思想和后革命下的“人性”反思,而《魔童降世》中“反英雄”敘事的成功,也是因為瞄準了新一代年輕觀眾對自我的關注,與銀幕中有著“缺失”的英雄的情感共鳴。
其次,國產動畫的創作在承接了美國迪斯尼、好萊塢超級英雄故事的敘事傳統后,一種新的本土動畫英雄敘事也正在生長出來。曾幾何時,當國產動畫電影使用好萊塢式的語法展開敘事,不免讓人質疑這是對西方主導的“現代性”文化霸權的默認。《魔童降世》后觀眾對“神話宇宙”的想象,也是國人對本土超級英雄電影的呼喚。
實際上,自2015年《大圣歸來》以來,國產動畫電影發展至今已經有足夠的技術自信,而新一輪的國產動畫創作中的“反英雄”將個體主義和集體訴求的融合敘事,更體現了將民族文化內涵與“他者”的成功敘事經驗有效融合之后建立起來的文化自信。那么“哪吒”之后,國產動畫的發展又該去往何處?大熱期待之下的《姜子牙》并未取得如期的票房,或許已經說明了,國產動畫才剛剛踏上自己的“英雄之旅”。
注釋:
[1]饒曙光,常伶俐:《挑戰與機遇:當代國產動畫電影的現象反思》,《長江文藝評論》,2018年第2期。
[2]褚亞男:《傳統文化資源與動畫創新策略研究——以20世紀80年代中國動畫電影為例》,《當代動畫》,2019年第2期。
[3][4][8]王樹忱:《〈哪吒鬧海〉的劇本改編和銀幕體現》,《電影通訊》,1979年第4期。
[5]戴錦華:《隱形書寫: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7頁。
[6]褚亞男:《傳統文化資源與動畫創新策略研究——以20世紀80年代中國動畫電影為例》,《當代動畫》,2019年第2期。
[7]戴錦華:《隱形書寫: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7頁。
[9]朱潔:《中國電影中人道主義思潮的流變——兼論新生代電影中的人道主義》,《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
[10][12]蔡志軍:《中國卡通明星——談〈哪吒傳奇〉中哪吒的人物塑造》,《電視研究》,2003年第10期。
[11]《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做好文藝工作的若干意見》,《新華每日電訊》,1997年5月23日頭版。
[13]楊利慧:《全球化、反全球化與中國民間傳統的重構——以大型國產動畫片〈哪吒傳奇〉為例》,《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
[14]【英】安東尼·吉登斯:《全球時代的民族國家》,郭忠華、何莉君譯,《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
[15]史春景:《不英雄的英雄孤獨的反英雄——〈局外人〉中莫爾索形象再次解讀》,《文學界(理論版)》,2012年第7期。
[16]白惠元:《英雄變格:孫悟空與現代中國的自我超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版,第11頁。
[17]沈杰:《志愿精神在中國社會的興起》,《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