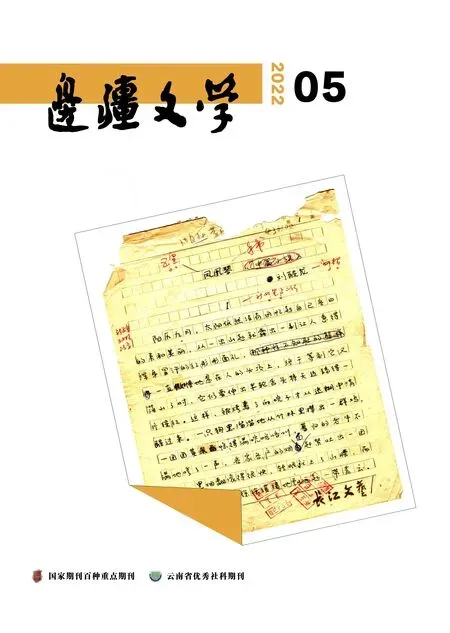鄱陽湖女人
米來
梅雨
立夏之后,青梅的果子還掛在樹上,雨季就來了。在一個午后,或者是半夜,從遙遠的地方滾過來一陣雷聲。過了兩天,雷聲從湖面上踏浪而來。風伴著雷,湖水漸漸洶涌。嫩綠的柳樹在風雷中伸展著柔軟的肢體,以驕傲的姿態起舞。風兒搖晃著青梅的果子,豐滿的桃子禁不住墜落到屋頂。樹葉颯颯作響,掃落屋檐的一塊舊瓦。風從縫隙里進來,穿過臥室的門,徑直進入夢中,又從夢中墜入湖中。怕它碎了,用雙手去捧,卻捧了個空。醒來驚坐,耳畔風聲、雨聲、梅子墜落的聲音不絕。恍然大悟,哦!梅子的季節到了。
第一場梅雨到來的時候,通常是下得熱烈奔放。配合著風雷閃電,雨水像簾子一樣蓋下來,天空因此低垂,湖面因此廣闊。黑色的屋脊在雨水中發出亮色,干涸的墻壁在雨中膨脹,樹木在雨水中成熟,土地承接著人們承受不了的雨水,讓它們自由自在地奔淌。
一場雨水之后,天氣忽然就悶熱起來。水在空氣里蒸發,霧一般的水汽裊裊升起。梅子漸漸成熟,從地上揀一顆起來,嫩綠的躺在紅嫩的掌心。攥緊了拳頭捏一捏,有些生硬。放進嘴里咬一口,酸澀異常。趕緊吐出來,可是滿嘴的酸澀已經侵蝕到內心。于是把梅子用瓷壇裝起來,撒上一把鹽,再撒上一把糖。把蓋兒封了,藏在床下,等待梅雨的過去。
也許是第一場雨下得太猛烈了,之后的雨水漸漸溫柔起來。像霧一樣的蒙蒙細雨,綿綿不絕地籠罩著天空。間或可以看見成形的雨線了,那雨水就像是從天空中垂下的掛面,清晰而又整齊。有時候起風了,銅錢一般的雨點砸在地面上,把青石板的路面也砸成密密麻麻的小坑。這梅雨的性格,既溫柔又纏綿。她那種似乎無休無止的勁頭,讓人愛不是,惱不得。
泡桐樹是梅雨最得意的作品,梅雨前的泡桐還是一棵幼苗,一場雨水下來,泡桐的葉子就肥大起來。泡桐貪婪地吸吮著雨水,它的身體因為雨水的滋潤而粗壯起來。夜深人靜的時候,在颯颯作響的雨聲中,可以聽見泡桐拔節而起的呻吟。清晨的時候,雨如果停了。滿地的泡桐葉躺在地上,那肥碩的葉片上,依然凝聚著顆顆圓潤的水珠。
北方來的人第一次經歷梅雨,會驚嘆自己被梅雨縮小了。衣袖比過去長了,褲腿邊也拖到了地上。南方人在梅雨中出入,袖子褲腿一齊挽得高高的。女人倘若被獨自羈絆在屋里,她會情不自禁的把指甲蓄得長長的,然后用那長長的指甲去摳門框。摳一下,門框留下一道痕,再摳一下,門框掉一塊皮。當梅雨期過去后,門框就像是被耗子啃過一樣,留下千瘡百孔的痕跡。
竹木的房子,還有家具,都在梅雨中發潮變霉。桌子的榫頭開始松動,木箱里的衣服發出腐爛的氣息。這種氣息在空氣里彌漫,直到泡桐樹開花了。一朵一朵的喇叭狀的泡桐花砸到地面,發出清脆的聲響。沒有人憐惜那潔白的泡桐花,只有幾只螞蟻抬著它在移動。泡桐花落是一個信號,意味著梅雨就要過去了。
這個時候,從床底下散發出一股酸酸的香味。人們記起了床底下的青梅,趕緊把壇子揭開,一壇青梅化作半壇水,半壇梅。梅子已經失去了翠色,那半壇水化作褐色的甘露,成為人們夏天解除酷暑的飲品。梅子熟了,梅雨終于過去了。
漁網
夏季的風,帶著湖草的清香、帶著湖水甜腥的氣息,無聲地彌漫著。赤腳的妮子,踩著被太陽灼熱的湖沙上了岸。沙灘上印下一串腳印,搖晃的船兒把湖水推過來,是一汪汪小水坑。一級級臺階,是粗沙巖上開采的紅石。沾著泥沙的腳板,在紅石上跳躍。妮子身后的臺階,在熱烘烘的氣流下,頃刻只留下一抹細沙。微風吹過,細沙如霧一般升起。
湖畔的人家,盤踞在高高的紅石臺階頂上。紅石、青瓦和翠柳,組成一幅漁村圖畫。圖畫中的柳樹,占據了大部分畫面的內容。一張張攤開晾曬的漁網,在陽光下閃爍著銀光。妮子的說笑聲從畫面后傳了出來,她捧了一把絲線,后面跟著拖了網架的女伴,三五一群地來到了柳樹下。織小網的將網繩纏在網架上,織大網的將網繩綁在樹身上。她們一手握盾,一手拿針。雙目凝視著手中的漁網,兩臂上下舞動。她們的眉眼在笑,她們的嘴巴在動,漁網隨著她們的動作也在慢慢地伸長。
一個妮子織網,是一幅畫。一群妮子聚在一起織網,則是一臺戲。一把竹針,就像一條鄱陽湖里的魚。織網用的絲線,就是鄱陽湖里的風浪。絲線有多長 ,波浪就有多寬。竹針在波浪里面穿梭,就像吐絲的蠶兒,漸漸攢成一張圍困自己的大網。妮子將網針握在手里,有一種握住魚兒的感覺。生活就像手中的網針,一不小心就會從手中滑落。可是定下神來,一切都握在手中。妮子的心緒,就像鄱陽湖的浪起伏,又像手中的漁網,錯綜復雜。
漫長的季節,是因為等待。經過一個季度休養生息,魚兒肥了,水也干了。魚兒從水面上露出腦門,仿佛在窺探織網的妮子。妮子的網已經織得很長很長,紅石臺階的湖畔上,那一片一片的漁網,仿佛把漁村都給網住了。
漁夫把漁網接過來,數一數漁網的網眼,量一量網眼的尺寸。岸上的動物有多少種,水中的水族就有多少類。捕大魚,用大網,捕小魚,用小網。漁網的絲線有的細如發絲,有的粗如棉線。漁網還分捕網、放網、拉網、罩網等,各因捕魚的需要而設。
漁網從妮子的手中完成后,到了漁夫的手中,還需要很多工夫。給漁網上瓢子,結甸子,還要上漿子。新漁網出湖,先要上漿。將幾十斤雞蛋,打進一個大木盆中。用勺子將蛋黃舀出,留下透明的蛋清。然后把新漁網放在湖中浸透,甩掉水分,然后將漁網投入裝有蛋清的木盆當中。把漁網在蛋清中一上一下地來回擺動,一條漁網要擺動半天的時間,漁網才能均勻地將蛋清全部“吃”進去。漁網“吃”飽之后,要讓漁網在木盆中休息一晚,讓它“醒醒”神。第二天,再將漁網掛在太陽下晾曬。曬干后的漁網,才可以下水捕魚。
妮子送走新織好的漁網,心兒就跟隨著漁網上了船。聽老一輩的漁人說,一條新漁網打的魚,可以抵得上幾條老漁網。尤其是漿得好的新漁網,撒到水里面,落水的速度就像刀切到水里面,無聲無息。被網住的魚兒,無論怎么使力,也掙脫不了漁網。于是她半夜里爬起床,推開后窗戶門,面對著繁星和一湖波浪,她的心又是焦慮又是期盼。自己織的漁網是否均勻?網上的網結是否結實?那絲線沒有用錯吧。于是她一夜的夢,盡在鄱陽湖的風浪中起伏了。
趕集
前一天就相約了伙伴,做好了準備。籮筐整齊地擺在院子里,扁擔豎立在門背后,繩子也圈成卷,靜靜地躺在籮筐邊。男人照樣喝了二兩酒,倒頭就睡,不久就發出很響的鼾聲。女人在旁邊推,卻推不醒。心里笑罵:醒的時候像老虎,睡著了像死豬。心里有點憋屈,有點傷感。忽然抬頭看見月亮,明晃晃的顯得格外敞亮,越發睡不著。為啥趕集的日子,月亮就格外亮呢?只有十六歲才會問的傻問題,忽然又纏繞上婦人的心。
天還是麻麻亮,妮子就坐在梳妝臺前梳辮子。站起身,長辮子垂到屁股下。坐下來,辮子就垂到地面上。把辮子絞了,留著它管啥用?影響干活呢。爹這樣說。是呢,城里人也不興留長辮子,嫌棄它土氣,每天費事梳理不說,還浪費錢買洗發水呢。娘也在一旁幫腔。妮子不回嘴,咬住嘴唇,兩汪淚卻在眼眶里轉。等到下到田間,爹娘果然沒有看見妮子的長辮子。可是到了十五趕大集,妮子把頭巾撤下,一頭烏黑的秀發瀑布一樣灑下來,把村前村后的眼睛都吸引了來。
鄱陽湖流域四十八村鎮,七天一小集,半月一中集,整月一大集。小集集中在幾個村,是一個小范圍的交易;中集放在鄉鎮,是一個集生活用品大全的大交易;而大集則除了生活用品外,還包括商業交易和娛樂大全的聚會。除了附近幾十個鄉鎮外,還有省府和外省市的輪船過來,因此時間都定在每月十五。
到了趕大集的這一天,人群從四面八方像流水一樣涌來。湖泊交錯的圩堤上,只見人們挑著擔子,挽著籃子,推著車子往集市上趕;寬闊的馬路上,摩托車、汽車、拖拉機的喇叭聲響成一片;渡口的湖灣里,泊滿了烏篷船和輪船。
穿西服打領帶的,夾著公文包的,指揮著一幫人收購大豆和花生。穿長靴子的,戴膠皮手套的,趟著水在大聲叫嚷收購銀魚;留著滿臉胡子的,長了一身橫肉的,則圍著一群生豬、雞鴨來回轉。他們大多數是外來的商人,帶著空車空船到集市上來收購他們需要的東西。來的時候干凈整齊,走的時候滿身的灰塵。
附近的居民在生活區擺滿了攤子,賣餛飩小吃的、賣甘蔗水果的,賣金銀手鐲的,賣衣物布匹的擠在一起。那高高掛起的花布,在太陽的照耀下,嘩啦啦抖動著,映紅了一條街。那些從商業區出來,賣掉了糧食大豆或水產的鄉民漁民,紛紛擠進了生活區。嘗嘗街邊小吃,扯幾尺新布,或者買個新彩電,高高興興的就回了家。
留下來的是一幫年輕人,他們要逛夜市。妮子到照相館化個妝,描個彎彎眉,燙個波浪發,穿上唐人裝,背后用一把大折扇做布景,留下一張十六歲的倩影。等到了人家來相親,就用這張照片做誘餌。到了晚上,相熟的女伴一塊去看露天電影,圍著篝火吃烤魚。
妮子一伙,后生一團,你往我這里扔骨頭,我往你那里扔炭火。被砸著的妮子發一聲叫,于是妮子們集體起來還擊。烤魚變成了手中的武器,烤魚從妮子的手里飛出,像雨點一樣砸到后生們的頭上。后生們既不跑也不躲,只將衣服翻過來,罩住一個腦袋。到烤魚砸完,那個惹禍的后生站出來,老老實實按照砸出烤魚的數目跟老板去結賬。
婦人還沉浸在半睡半醒的夢里,忽然男人的一聲吼把她喚醒。坐起身,揉揉眼,太陽升到半空中了。男人把一切收拾停當,正在院子里抽煙。誰叫今天是趕集的日子呢?他就是在當年趕集的日子認識的她。
黃金
金碗、銀筷、鐵鍋、銅壺、珍珠項鏈翡翠玉,是鄱陽湖女人一生的夢。盡管在現實中,她們首先考慮的是吃住行,但是只要有可能,這個夢就會從某個角落里冒出來。
娃兒在娘肚子里還沒出來,娘就給他縫衣服鞋帽。鞋是虎頭鞋,帽是老虎帽,老虎額頭上總有一個金線銹的王字。一套紅色的夾襖,用彩線和金繡一起,沿著紐扣的邊沿,繡上象征吉祥的圖案。娘將她所有的夢想,凝聚在一根繡花針和一根黃金線上。她用她的恬淡、從容、沉靜,來傳達她一個女人對生活強烈追求的愿望。
娃兒出生了,家里寬裕的,就給他打一個金項圈;家里不寬裕的,也給他打一對銀手鐲。項圈上,或者手鐲上,掛幾串鈴鐺。娃兒笑的時候,手舞足蹈,把鈴鐺搖得叮當響。娃兒哭的時候,舉手踢腳,同樣把鈴鐺弄得叮當響。娃兒爬動的時候,手腳并用,爬到哪里,哪里就一陣叮當聲和笑聲。
這個時候女人的笑,是無所顧忌、敞開心扉的笑。這個時候的女人,突然間接受了烈日下曝曬、風浪中搏斗的生活現實。她從過去那個含蓄、靦腆、膽怯的妮子,變成了一個勤儉、賢惠、耐勞的女人。
娃兒漸漸長大了,背起了書包,開始走出娘的視線。娘把虎頭鞋、老虎帽,還有金項圈、銀手鐲收了起來,壓在了箱子底下。娃兒是個男的,娘就悄悄地給他攢錢。如果娃兒考上了學校,就留著給娃兒做學費;如果娃兒要出門遠行做事,就給他做盤纏;倘若娃兒哪兒也不去,繼承爹娘的事業,娘就把積攢下來的錢,換成金項鏈、金耳環或者金戒指,留著給他做娶媳婦的彩禮。
如果娃兒是個女娃,娘也偷偷給她攢錢。無論她長大以后,是丑是美,有錢還是無錢,娘都要給她一份薄禮,一條赤金的項鏈,或者一塊厚實的金元寶,或者是一對祖傳的耳環,一個純金的戒指。在女娃出嫁的時候,娘倆相對流涕。在娘的心里,娃兒從此像斷了線的風箏,離她越來越遠。那根斷了的殘線,依舊還纏在娘的心頭。可系住女兒的那頭,卻只能在風中飄舞了。娘把對女兒的憂慮,化做一個行動,將一份薄禮壓在女兒出嫁的箱子里。
娘這個時候依然有夢,只不過她把她的夢,轉化為現實的勞動和耕耘。早晨的星辰,可以照見她的身影;深夜的月亮,經常伴隨她的腳步。就在她揮舞鋤頭的瞬間,或者是在她搖動船槳的剎那,在強烈的陽光下,有一道炫目的亮光從她的手腕上閃了出來。
不用奇怪,在鄱陽湖的流域,你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女人。她到湖邊洗衣,雙手在水中擺動時,有一對玉手鐲也浸在了水里。她在灶臺上做飯,握住鍋鏟的手上,有一只銀手鐲被磕得輕響。在大街上,集市中,金銀鋪子的前面,永遠擁擠著女人。年老的,年輕的,她們將一雙眼睛,深情地凝聚在一堆金銀上面。
世界上有很多種顏色,可是金銀的顏色最動人;世界上有很多動聽的聲音,也許金銀的聲音最動聽。在鄱陽湖女人的心中,對于金銀的夢想,一代一代的傳承。或許這不僅僅是一個夢,如果把它比作夢,那么這個夢就是能夠激發她們戰勝磨難,直面生活的夢。
鄱陽湖的女人,愛金銀,更愛生活。
夏夜
夏季的傍晚,夕陽西下的時候,那橘紅的天色顯得格外溫柔。淺淺的湖浪,輕輕地向湖畔推來。落暉滲透到風里,撒到岸邊竹樓的屋頂。竹樓里的門敞開著,穿堂風從屋里刮過,攜帶來清涼的氣息。在竹樓里躲了一天的人,終于鉆了出來。赤著胳膊的漢子,肩上搭一條毛巾,從自家屋后的石臺上,高高地躍入了湖中。
穿了蠟染衣裙的女人,提著一只小木桶。她站在高高的石臺上,用吊繩把木桶放入水中,看水中的漢子游過來,把水桶裝滿水。然后她緩緩地將水桶提起來,將鋪有紅石的地面一遍一遍沖洗。被烈日蒸烤了一天的紅石,被清涼的湖水一澆,立刻騰起一陣青煙。當地面被湖水完全濕潤之后,湖水就順著地面往下流淌。
女人沖完地面,漢子就上了岸。沖洗后的紅石,顯得潔凈而又清涼。于是人們把竹床搬到了屋外,并把小圓桌支了起來。女人端上幾碟咸菜臘魚,熬一鍋南瓜粥。一家人就著湖水,伴著垂柳,在夕陽的風中用晚餐。
當夜幕低垂,滿天的星星在天空閃爍。湖邊的岸上,那一家一家的竹樓后,懸掛著一盞盞馬燈。朦朧的燈火下,圍著一位老人,在談天說古。另一邊,擺了幾個棋陣,漢子們各自占據著棋陣的一角,相持不下。女人則撫摸著幼小的娃兒,輕輕哼著古老的催眠曲。
這個時候,有一點漁火在湖面上移動。當漁火靠岸的時候,有叫賣菱角的聲音傳來。正在假寐的娃兒一咕嚕的就爬了起來,瞪大了眼睛。女人用扇子拍打著娃兒道:哄了半天,原來是裝睡。賣菱角的聲音又傳了過來,娃兒開始央求,女人用指頭輕輕地戳一下娃兒的額頭,嗔道:就知道你想著菱角,看樣子不給你買你是不罷休的。說罷趿了拖鞋,就向漁火處走去。
賣菱角的是一對母女,看到來了人,妮子把草帽拉低了,罩住了半張臉。娘一邊高聲叫賣,一邊笑迎著客人。買菱角的女人過來,看到筐中飽滿的菱角,不禁嘴饞。拿一顆嘗嘗,咬一口,水汪汪的入口,甜糯糯的進喉。忍不住贊道:真是地道的菱角。賣菱角地笑道:本地南湖里采的,味道當然地道。買菱角的附和道:南湖里不僅菱角好,芡實和蓮子也好。我就是南湖人,和你妮子一般大時,我經常去采摘的。賣菱角的母女一聽,立刻和這女人親熱起來。她們嘮起南湖,話題就沒有完。到了最后,賣菱角的送了南湖女人一大兜菱角,南湖女人則邀請賣菱角的到自家去喝茶。
在喝茶的過程中,南湖女人站在自家石臺上叫嚷了幾聲,附近的女人都圍了過來。你一兜,我一籃,兩筐菱角頃刻被賣光了。女人把賣菱角的送下船的時候,還附帶送給妮子一塊布,送給妮子娘一條頭巾。
等到女人回到竹床旁,娃兒已經入睡,地上撒滿了菱角殼。女人把菱角殼打掃干凈,躺在清涼的竹床上,看著賣菱角的船兒遠遠的離去。柳條在頭頂晃動,湖水輕輕地拍擊著石臺。屋檐上懸掛的風鈴,在風中發出丁當聲。女人仿佛枕在波濤上,進入了少年時的夢鄉。
當夏夜悄悄流逝,當黎明靜靜來臨時,晨靄還沒有消逝。漁船還沒有起錨,湖浪搖晃著船兒,鷺鷥站在船舷打盹。河岸上的柳樹,依然在晨風中飛舞。早起的水鳥從水面上掠過,竹樓后的石臺上,人們依然在竹床上熟睡。靜謐的世界上,惟有風鈴的響聲與水鳥伴舞。
照相
鄱陽湖的妮子,長到十六歲的時候,或鮮艷如早晨的露珠,或飽滿如夏日里的蓮蓬,或淡雅如水面的菱花,或活潑如涌動的湖浪,或柔軟如沙洲的湖草。樸實中透著純真,活潑中充滿靈氣。為了留住這歲月的美好瞬間,妮子們往往選擇了照相館。
十六歲的生日,家里人沒有人留意,可是妮子的心卻興奮。在幾個月前,妮子就用織網的錢,偷偷地買了新衣裳。或者是高領的毛衣,或者是彩色的裙子。毛衣的顏色要鮮艷的,裙子的花色是新穎的。或許這種毛衣和裙子在平常不能穿出去,因為無論是上船或下地,這種衣裙都不方便。一件毛衣好幾百,一件裙子也是好幾百,那是妮子織了一個月網攢下的工錢,可是妮子一點也不心疼。
一生之中,能有幾個十六歲呢?穿上最好的衣裙,配上娘藏在箱子底下的金項鏈,畫一畫眉梢,把粗壯的長辮子垂到胸前,輕抿紅唇微笑,這是妮子對自己形象最美好的記憶。到了生日這一天,妮子比往常都起得早。爹娘有點詫異,但也不以為然,妮子向來勤快。等到爹娘上了船,或者扛著鋤頭下了地,妮子就輕掩房門,打一盆水,仔細地擦洗自己。
妮子換好了新衣裳,坐到了鏡子前。梳頭,化妝,左看右看,外面就有女伴叫喚。妮子假裝很自然地開了門,心里卻企盼同伴的驚羨。女伴們果然發出驚嘆,因為妮子的衣裳確實好看。于是妮子們相擁著出了門,來到了照相館。照相師一眼就看出了是妮子的生日,因為女伴們為了陪襯她,故意穿舊一些做綠葉。
妮子照完相,把新衣裳脫下來,照舊藏在箱子里。她懷著忐忑的心情,等待照片的出來。過了幾天,女伴們忽然上了門,說照相館里已經掛上了妮子的照片。妮子很激動,心里咚咚地跳,拽著女伴的手就往照相館跑。照相館的墻上,果然掛了一張擴大了的彩照。妮子站在自己的照片前,有點暈眩,又有點迷惑,怎么看都覺得照片不像自己。這時候的妮子,就覺得是自己被釘在了墻上。她想把照片要回來,可是又想讓照片繼續留在那里。妮子從此就像分裂成兩個人,一個在照相館的墻上,一個在她自己的身上。
妮子的照片吸引了很多人,從此就不斷有媒人來上門。爹娘發現妮子與往常有些不同,她仿佛變成了一個空殼,失去了靈魂。爹娘終于找到了原因,原來妮子的魂被釘在了照相館的墻上。爹娘最后把照片要回了家,交到了妮子手上。妮子把照片抱在懷里,又把照片掛在自己的閨房,后來擔心照片上了灰,又把照片藏進了箱子里。
妮子出嫁了,箱子里帶著那張讓她靈魂出竅的照片。后來她也生了妮子,妮子漸漸長大,娘的容顏卻漸漸衰老。已經變成老婦的她,漸漸忘卻了當年那張照片。當梅雨過后,妮子幫娘把箱子搬出來曬太陽的時候,發現了娘的照片。照片雖然已經發黃,可是依稀可以辨出和自己相似的輪廓。妮子仍然要問,這是娘嗎?娘沒有作聲,可是內心卻心潮澎湃。爹的眼角有了淚花,點點已經花白的頭說,這是你娘十六歲的生日照啊!妮子突然感悟到歲月的痕跡,青春如花,朝花夕逝,自己原來在延續娘的過去。
女紅
如果按照經濟學家的觀點,夫妻關系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那么就建議男人娶南方的女子為妻。因為南方的女子,不僅克儉勤勞,而且在持家方面頗有特長。南方女子的五官,不僅本身秀色可餐,還是食色的制造者和鑒賞者。其中值得稱道的,就是南方女子的女紅。
初到南方的北方人,可能會抱怨南方的雨下得太多。可是南方的人卻從不嫌雨多,盡管小溪、池塘、河道還有湖泊都被雨水灌得滿滿的。可是南方人還是笑著說,水帶財,財水財水,越漲越旺。
并不是因為迷信,因為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會變得豐盈起來。不說湖泊的魚蝦,也不說河畔的蓮藕。單單是地里種的葫蘆、南瓜、絲瓜、茄子、蘿卜、地瓜,仿佛都儲滿了水分,一個個變得水汪汪肥胖胖。就連樹上的葉子,架上的青藤,也變得翠綠粗壯,仿佛一擰就能擰出水來。
樹上結的桃子、李子、杏子、梅子,紅的紅、青的青、黃的黃;架子上趴著的梨瓜、香瓜、西瓜,一個個把藤兒墜斷;還有水中的蓮子、菱角和芡實,也粒粒飽滿。瓜果種得多的人家,就給有小孩的親戚家捎信:讓娃子放了假上我們家來,今年的瓜果吃不完呢!
西瓜吃不完,干脆就踩碎了,用籮筐浸到河里去漂洗。把浮出來的瓜瓤去掉,把沉淀到筐底的瓜子撈起來,曬干后炒瓜子磕。西瓜皮卻舍不得扔,把它們剮得薄薄的,上了蒸籠蒸熟,再用紗布包起來,榨干水分。然后切成碎片,拌上香油、食鹽、辣椒、香料,就是一道瓜皮名菜。
蓮子吃不完更沒關系,直接把它們放在太陽下曝曬,曬干后裝起來。想吃的時候,把蓮子放進石磨里走一圈,褐色的皮、白色的蓮肉、綠色的蓮心就分開了。蓮子皮可以做枕心,蓮肉可以生吃,也可以炒著吃燉了吃,蓮心可以入藥。紅棗、李子、桃子、梅子也和蓮子一樣,如果吃不了,可以曬成干,也可以腌制成醬。西瓜、甜瓜和梨瓜,可以榨成果汁,當成飲料喝。
一般來說,男人是張嘴的,女人是動手的。除了擺弄漁船漁網,侍弄田地外,女人私下里最喜歡的事情莫過于做女紅。女紅分為兩種,一種是干的,一種是濕的。干的是指縫衣服,繡花草;濕的指曬干菜,腌制瓜果。女人之所以愛女紅,不外乎兩個字,吃和穿。一個滿足于果腹,一個滿足于裹體,本無可非議,可是她們偏偏要作出許多文章。
因為要做女紅,所以女人的東西就特別多。比如繡花,不僅需要彩絲線、綢緞、繡筐繡架,還需要樣圖等等。而做濕女紅,需要的東西不僅多,而且很占地。比如腌制瓜果,需要很多很多的壇壇罐罐。女人們根據自己的喜好,挑選各種器皿。有人喜歡陶器,有人喜歡瓷器,還有人喜歡瓦罐。于是女人們變成了陶瓷鑒賞和收藏家,比如景德鎮的青瓷,她們一眼就能分辨出自哪個年代;一個缺了口的瓦罐,她們能說出瓦罐出自哪個窯。
南方女人就像蜜蜂一樣,春夏秋冬不停地忙碌著。春天繡鞋襪,夏天腌制瓜果,秋天下田地,冬天縫衣裳。偶爾的輕閑,會讓她們想起青瓷上的美人圖,還有腌制在壇子里的酸梅醬。忍不住用小指頭蘸一蘸,放進嘴里舔一舔,酸溜溜甜絲絲。于是做一罐酸梅湯,裝一瓶桃子醬,提一袋蓮子干。酸梅湯給男人解暑,桃子醬給孩子解饞,蓮子干送給婆婆清火氣。女人最后空了手往回走,一邊走還一邊傻傻的樂。她在想什么呢?可能還是女紅。
相親
妮子和女伴們坐在院子里織網,正打打鬧鬧,忽然三姨婆來串門,妮子們立刻噤了聲。有一個女伴沖妮子做了個鬼臉,妮子的臉騰的就紅了一片云。她的心“咚咚”地跳了起來,恨不得自己的耳朵能飛進屋里,聽聽三姨婆和娘在說什么。
其實什么也不用聽,三姨婆上門就是專為妮子來提親。三姨婆走后,娘把妮子叫進屋。可是妮子用手把耳朵堵住,什么也不想聽。娘知道妮子的心思,妮子不想聽人家怎么說,她要自己先看看人才行。娘只好找個借口,帶著妮子到沙洲上去割草。娘把口信帶給了三姨婆,三姨婆立刻領會了妮子娘的意思。
娘在前邊走,妮子在后面跟。這個時候,天邊就響起一片大雁的叫聲。大雁排成長長的一隊,就像一條柔軟的緞帶,從遠處飛了過來。領頭的大雁撲騰著翅膀,將半個身子俯沖下來,接著又騰飛而起,發出一聲高昂的鳴叫。仿佛經過排練一般,跟在它身后的第二只大雁立刻從隊伍中分離了出來。第三只大雁依然緊隨著原先的那只頭雁,第四只大雁跟在了第二只大雁的身邊。頭雁的一個動作,在剎那間讓一隊大雁分為兩列長隊。兩列大雁一會兒交叉成十字,一會兒匯成一個人字,一會兒又并行而飛。它們仿佛在用翅膀舉行一個儀式,用飛行表達互相之間的依戀,用這種形式來傾訴難分難舍的感情。
妮子正彎腰割湖草,抬頭就看到天空中的一幕。眼見一支大雁遠離而去,另一支大雁在后面戀戀不舍地追趕。漸漸的后面那支大雁慢了下來,它們在空中盤旋,發出凄涼的低鳴聲。大雁的叫聲觸動了妮子,想到娘把自己領到沙洲上來,就是為了要把自己嫁出去,禁不住眼淚婆娑而下。
妮子從娘肚子里生下來,就像鄱陽湖畔的一棵湖草。娘下地,把她背著;娘休息,順便給她喝一口水;當她開始走路的時候,就跟在娘的身后拔草;五六歲的時候,她就學會了洗衣做飯;等到她再大一點,她就會織網繡花上沙洲割草了。
三姨婆不是妮子的三姨婆,可是同村的人都叫她三姨婆,所以妮子也這么跟著叫。妮子第一次繡鞋墊,三姨婆就把她盯上了。妮子用白色的竹布做底,將帆布染成深藍鑲邊。再用紅、綠、藍顏色的紗線,在鞋墊上銹一支荷花,荷花下是滿塘的荷葉。三姨婆就搶過去看,一邊夸她的手工好。妮子繡花的時候,遠遠看見三姨婆過來,就把繡框藏起來。三姨婆笑瞇瞇哄她道:給我看看,將來給你說個好婆家。妮子又羞又氣,搶白道:誰讓你說婆家?我一輩子不嫁人。
不嫁人是妮子一時的氣話,沒有人會把這話當真。想到娘一心要把自己嫁出去,妮子的心就有點凄涼。娘在身邊開導她說:妮子大了,就像天上的大雁,總要單飛出去,過自己的日子。嫁人就像大雁找個伴,兩只大雁一起飛,總比單飛要強。可是妮子認為,大雁是大雁,人是人。嫁給一個不認識的人,對妮子來說充滿了風險。
妮子胡思亂想的時候,就覺得有人在暗處盯著她看。她回過頭去,卻不見人影,只聽唰唰割草的聲響。湖草倒下的時候,就像一陣風刮過來,把湖草刮倒一大片。妮子有些吃驚,又有些癡迷,想看看割草的人是誰,可是湖草遮住了視線。朦朧中只看見一個模糊的背影,還有那鐮刀的白光在舞動。
前邊忽然聽到三姨婆和娘說話的聲音,妮子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割草的聲音離她越來越近,妮子不由耳熱心跳,不敢抬起頭來。割草的人也不說話,只是不停地干活,呼哧呼哧的喘氣。兩個人碰了頭,互相看一眼,卻又相互走了開去。
妮子本想停住腳,問問他的姓名,住哪個村……也許割草人也想停住腳,和她說說話。可是兩個人都不知如何開口,就這么錯開了機會。妮子這時候把不想嫁人的話忘了個一干二凈,她希望娘和三姨婆能再給她一次機會,讓她了解了解割草人。
湖草
湖草被人關注的季節,就是湖草成熟的季節。就像鄱陽湖畔的黃毛丫頭,忽然長成紅唇鮮艷的妮子,吸引了一雙雙后生的眼睛。湖草一片一片的鋪開來,無邊無際的樣子,就像鄱陽湖綠波蕩漾的湖面。一陣風兒吹過來,湖草連綿起伏。一種青悠悠的湖草的味道,從草根下散發開來,彌漫在湖畔的空氣里。
其實,湖草剛剛從沙土里鉆出來的時候,人們就發現了她們。或許是在冬末的雪后,或許是在初春的細雨中。在潮濕的沙土上,忽然就冒出一叢叢鮮嫩的湖草。湖草挺立著矮小細弱的身子,隱藏在遠離人跡的沙洲上。可是人們還是發現了她們,并且把她們加以分類,將其中可以食用的一種稱之為蔞蒿。
湖畔的妮子都認識蔞蒿,她們挽著籃子,或者撐著船來了。把蔞蒿采摘回去,捋去葉子,去掉土根。把蔞蒿掐成一寸一寸的長短,用半肥半瘦的臘肉爆炒,再灑上一把紅辣椒。紅綠相間的蔞蒿下到盤子里,就一壺酒。家人圍坐一團,或者招待客人,青悠悠的蔞蒿,伴著濃濃的酒香,成為鄱陽湖的一道風景。蔞蒿炒臘肉,也就成為當地一道特色菜肴。
蔞蒿的生命很短,過不了十天半月,蔞蒿就不再脆嫩了。這個時候的蔞蒿,又變回了普通的湖草。經過漫長的梅雨季節,湖水漲起來了,把沙洲上的湖草淹沒。細小的湖草們,在水中輕盈地擺動。有些不甘寂寞的湖草,把修長的手臂伸出湖面,仿佛在波濤中起舞。這個時候的湖草,沉浸在夢一般澄澈的境界里。她的顏色是青翠的,她的身材是柔軟的。她將她青春的美,全部展示給水中的魚兒,天空中的白云。
夏季過后,湖水漸漸退卻。湖草從水中露了出來,由于失去了湖水的滋潤,她漸漸干枯。平常寂靜的沙洲,忽然就熱鬧起來,妮子跟隨著娘來收割湖草。娘割草的時候,手握磨得白晃晃的鐮刀,身子弓下去。空氣里一片鐮刀的聲音湖草斷裂的聲音。
妮子不喜歡這個聲音,盡管她手里也拿著鐮刀。當看到娘毫無表情地割草時,她的心就有一種被撕裂的感覺。娘曾經說過,妮子的命就像這沙洲上的湖草。湖草降生到這個世界上,不需要施肥,也不需要耕耘,更不需要呵護。風里雨里,沙里泥里,她們掙扎著生存。到了秋天,她們等待著人們收割。把湖草編成草帽、草筐、草繩、草鞋,或者把湖草變成一把火,用來取暖或燒飯。一年一年又一年,伴隨著湖水的漲落,湖草一茬一茬地接著生長。
妮子想著湖草,心里就有一種委屈。于是她遠離了娘,自己找了一塊湖草地。她彎下身割草的時候,鐮刀下得快,湖草卻放得輕。她手里握著割下來的湖草,心里就涌起憐惜之情。仿佛是為了安慰湖草,她把湖草放下的時候,不僅動作輕柔,而且還像繡花一樣,把湖草整整齊齊有規律的擺放。當沙洲上的湖草全部倒下時,在妮子割草的地域,可以看見用湖草碼成的菱形,或者是五星形,或者像荷花形的圖案。
娘抬起身子,用手臂揩掉額頭的汗水時,就發現了妮子割倒的湖草。娘心里有些著惱,又有些傷感。著惱的是妮子在耽誤時間,因為割湖草不是繡花。傷感的是妮子的舉動,讓她想起了自己年輕的時候。她本來想責怪妮子,可是責備的話到了嘴邊,最后又咽了回去。
當男人們撐著船兒,要把湖草收回家時,娘暗示男人把妮子割的湖草留到最后。可是妮子割的湖草還是被打成了捆,堆上了船。娘發現妮子的眼角,隱隱有了淚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