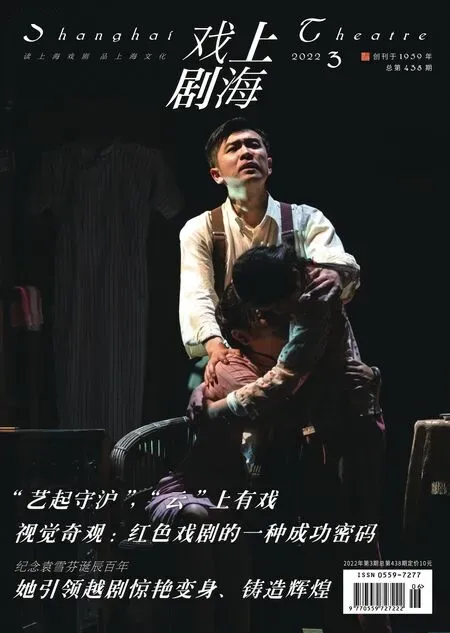傳統戲曲的現代夢與現代“痛”
(上海戲劇學院副教授):在過去幾十年里,“現代”這個詞在戲劇、戲曲領域是一個高頻詞匯。劇團演出的宣傳冊上,也會寫上“現代戲曲”。關于“現代”最常規的理解,就是題材意義上的現代,比如辛亥革命以來能夠反映現當代生活的這一類戲曲,叫作現代戲曲,還有一種理解是美學意義上的,即現代人創作的具有現代品格的戲曲。
(清華大學藝術教育中心講師):傳統戲曲在中國社會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審美功能,近代以來在西方文化的影響下,尤其是經歷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戲曲開始走向自覺革新的道路。在作為舶來品的話劇的影響下,中國戲劇的格局也開始從戲曲為主導變成話劇和戲曲二元共存模式。為了讓傳統戲曲藝術在新的時代語境下更好適應現代人的審美,不同時代的戲曲人在創作過程中融入了自身的思考,并試圖在藝術表達上有所突破。20世紀以來的戲曲生態發生了多種變化。首先是演劇空間發生了變化,從過去的戲樓茶樓到現在的鏡框式舞臺。其次傳統戲曲文本以抒情見長,現在出現了一些以情節沖突為主的劇本。再者,從表演角度來講也有了新的挑戰,傳統戲曲演員是程式功法與行當人物融為一體,通過程式塑造人物,傳統戲的傳承在師徒相傳中延續著這一表演模式,即便是在新編歷史題材中,功法技術仍然得以沿用,演員正是在這種環境下,不斷磨礪著自身的表演技藝,最終形成一種鮮明的表演特點,乃至確立一種流派風格。
(無錫市錫劇院導演):現代戲曲是當今多元文化雜糅下的一種價值取向,它不涉及對錯之分,只涉及當代人的審美習性和時代的節奏變換而形成的藝術觀念。對戲曲來說,這種傳統與現代的碰撞,說陣痛也好,難題也好,挑戰也好,它是多面的。但戲曲發展到今天,它必然要走向現代、走向時代,甚至走向未來。讓戲曲現代化,對于青年導演來講的話,這應該是他們畢生所追求的創作方向和審美追求。現在觀眾的審美習性不會只想看到“一桌二椅”的表現方式,更希望看到情節的曲折性、劇本結構的嚴密性,最重要的就是現代戲曲在表現人物的時候,要看到人物的復雜性。
(上海越劇院演員):不光戲曲面臨這個問題,影視劇、網絡劇近幾年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都更多加入了現代人的思維,讓受眾更快共情。前段時間出現很多穿越劇,就是想用當代人的思維把觀眾帶入到故事中的年代背景。我們的社交軟件從最早的QQ,到微博,到微信,再到抖音,都是非常快的變遷,尤其疫情以來直播非常多,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轉變。我覺得戲曲還沒有跟上這個節奏,當然戲曲比較復雜,做起來非常難。
不但是舞臺,新的傳播形式也對演員的表演提出了新要求。我之前排了一部越劇微電影《新生》,對我來說很有難度。雖然我演的人物有原型,但是沒有照片、沒有多少文字資料,對我來說是一個從無到有的創作。我一開口,導演就說不對,說你太古典了,感覺“像林黛玉”。而且越劇微電影也不是舞臺劇,要求演員通過鏡頭表現,導演說不要你用程式,就一個大特寫推你的眼睛,讓你表演。對于我來說蠻難的,要求完全不一樣了。
戲曲的現代化過程中,劇本創作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領域。從情節設定上看,傳統戲在情感高潮的營造上匠心獨具,如《游園驚夢》《聞鈴哭像》等,而人物間的意志對抗與情節沖突并不視為創作的重點。現代戲曲劇本的創作在西方戲劇的影響下,開始提升戲曲的文學性,重視情節沖突的設定,向“話劇+唱”的模式探索,田漢、馬少波等戲劇家都作出了重要貢獻。
近些年來,現代戲創作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有很大的提升,不同劇種的現代戲創作都有可圈可點之處,像評劇的《母親》,滬劇的《挑山女人》《敦煌女兒》,秦腔的《狗兒爺涅槃》,豫劇《村官李天成》《焦裕祿》等,都獲得了良好的評價,甚至在昆曲現代戲創作上也有所突破。
越來越多的理論家開始認為現代戲趨向成熟。所謂趨向成熟,是劇本的文學性方面得到很大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以京劇為代表的劇種表演性壓過文學性的局面。過去傳統戲曲里面人物相對比較簡單,是一個單純性格人物,現代戲曲中的人物開始出現對人性的多元化和深刻性的探索,并取得了不錯的效果。還有就是戲曲表達開始青春化,如青春版《牡丹亭》、越劇《甄嬛傳》受到年輕觀眾的喜歡。可以說,當代戲曲創作者正在不斷尋求突破,不斷拉近戲曲和年輕人的審美距離。
目前我也在傳承一些傳統劇目,比如說《紅樓夢》《皇帝與村姑》,都是非常規整地學習老藝術家的一招一式。我演過音樂劇場版《紅樓夢》、經典版《紅樓夢》、大劇院殿堂版《紅樓夢》,但是最受歡迎的還是經典版《紅樓夢》。看傳統劇目的一定是年紀大的觀眾嗎?不是的,也有很多年輕的觀眾,他們愛經典的魅力。
新編戲《甄嬛》是時髦的,當時電視劇還沒有拍,看完小說后我就覺得它很符合我們劇團的氣質,也符合我們流派、演員的氣質。我們的原院長、編劇李莉對它進行了改編,演出時一票難求,場場爆滿,至今已經演了100多場。應該說它在現代創作當中是一個比較成功的案例。
這部戲的創排對表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比如說林黛玉、祝英臺的年齡跨度不大,但甄嬛的年齡跨度就比較大。楊小青導演對我的要求是上半場要很明媚、很婀娜,但下半場要展現她作為皇后的身份感,導演讓我拋棄掉身上的婀娜感。為了展現出“二進宮”時的氣勢、狀態,我借鑒了話劇表演,臺詞往下壓,臺步重心往后,調整眼神。舞蹈老師沒有大改舞蹈結構,只是改變了節奏,但劇場效果就出來了,我想這比較像現代演劇的方式。
李旭丹講的很有代表性,舞臺上塑造甄嬛,過去沒有可參照的人物范本,她需要從無到有地創造這個人物。所謂守正創新,“正”是一以貫之的傳統,需要規矩地繼承。“新”就是藝術家如何把多種元素放在一起,在傳統基礎上進行變化和革新,使之符合觀眾喜歡的審美風格,對于大多數演員而言,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需要達到一定藝術水準,被觀眾認可就更難了。
歸根到底,還是怎么從我們的前輩那里繼承方法,然后在這個方法基礎之上形成自己的風格,再創造屬于你自己的角色。這是對于演員而言的。那么對于導演來說是,要怎么去實現這一點呢?
戲曲在當代面臨多種問題,戲曲是鄉土農耕文化,進入到現在的工業科技時代,要怎樣才能立足于當今?我認為立足點始終是“戲曲是建立在以表演藝術為中心的”這一個原則。戲曲美學精神就是虛擬、程式、抒情,甚至是多變的。
我用自己的創作實踐來具體講一下。2019年我在上海越劇院創作了一部小戲《大閽》。編劇莫霞寫的不是越劇擅長的才子佳人的戲,它的主人公是楚文王和守城門的鬻拳。這是兩個很陽剛的爺們,和越劇的柔美是不一樣的。導演首先要考慮劇種的氣質。這個劇本的精神氣質表現的是一種孜孜不倦的追求。當然我也沒有脫離以歌舞演故事的原則,但是我不像京昆那樣對程式要求那么嚴格,手在哪兒就是在哪兒,我讓它帶有越劇舞蹈的感覺,甚至帶有浙江人性格里面那種微妙的韌勁兒,找到人物最細膩的情感,我相信觀眾是愿意去接受的。
我再講一下我的小劇場楚劇《惜姣之死》,是一個傳統題材的改編。我在想閻惜姣追尋的是什么?追求愛情的道路有沒有錯?閻惜姣的選擇不能簡單說對錯,只是她追求的和當時的社會環境是有沖突的,但她在堅持追求一種精神,這跟當代人在氣質上是有某些相符的。我把她的心理空間放大,比如她看到宋江的信,我給了一排角光,當音效響起,光照到閻惜姣臉上,她臉上的色彩變成紅的、黃的,整個人是停滯的。在這一時刻,她覺得可以跟宋江談判了,此刻又回到原點,回到她的終極追求。我覺得觀眾能夠感受到某些有別于傳統的東西。
我們為了實現現代性,在題材選擇上有四種比較突出的傾向:一種就是直接寫當下的生活,寫當下生活毫無疑問是最靠近現代的;一種是對傳統戲曲題材進行重新改編;一種是對其他藝術門類的敘事文本的改編;再有一種是搬演西方戲劇——因為我們不夠“現代”,那么我們直接從西方的話劇或者小說來移植改編。
這四種途徑是目前我們都比較能夠接受的,或者說是我們比較熟知的,但是其成品到底有沒有成為現代戲曲,或者說能不能被我們的觀眾認可,還得打一個問號。比如《挑山女人》從外殼角度來講毫無疑問是現代的,但是其精神內涵卻不是。為什么這么講呢?因為劇中的女性還是以傳統的精神要求、道德標準去塑造的。這樣的案例還有很多,外表看似現代,但它的精神指向其實還是傳統的,甚至有些還是落后于我們這個時代的道德標準的。
盡管現代戲曲是我們共同的追求,但一旦作品掛上了“現代”兩個字,就預示著它跟時代接上了軌,跟當代的觀眾產生了對接,可是假如“現代”表達出了問題,精神指向出了問題,再現代的手段都不可能被觀眾接受。
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現代戲創作有一個觀念,向戲曲要技術,向生活要人物,但在這個過程中,如何讓現代人物也符合戲曲人物審美特征,如何把握人物的思想內涵,就牽扯到如何戲曲化的問題。現代戲曲在整個歷史進程中有一個基本的取向,就是啟蒙性。人的精神內涵是什么,如何在戲曲人物中探索人性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是創作上的難點。我們中國人喜歡講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壞人,這種思維慣性里也有倫理上的判斷。戲曲中人物好與壞基本是通過外在形式展現的,臉譜是一個典型特征。過去戲曲作為高臺教化的手段,本身就有鮮明的價值導向,過于陰暗的心理或者復雜的人物心理活動,并不適宜舞臺展現。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也涉及價值觀的變化。所以在現代戲曲舞臺上塑造一個現實生活中的人物,在創作上是有難度的。
我們曾經看過一些戲,它們向其他現代藝術借鑒了太多的手段,當它們在舞臺演出時,我們會懷疑這還是不是戲曲,或者說現代戲曲邊界是不是太寬了。作為導演,如何去把握這個尺度呢?
近期我去了江西的贛州,看了張曼君導演的采茶戲《一個人的長征》。曼君老師處理很高明的地方在哪里?首先她從文本創作開始就介入了,導演跟文本之間已經有交流了,她將自己的生命萌芽種在劇本里,將對民族的人道主義和精神的關懷融入在劇本里。思想落到戲里,不能直接告訴你,要通過故事讓你自己感受到。
這部戲的主角叫騾子,是一個農民,他有基本的生存訴求,要吃飽飯,要娶媳婦,打不打仗對他來說好像很遙遠。大部分觀眾會接受這個訴求。建立起這個關系以后,觀眾就會跟著他走了。然后這個人物經歷了跌宕起伏的命運。他一個農民到了戰場什么也不懂,唯一能種田的騾子也被炸死了。首長吩咐他一個任務,讓他把這20多根金條帶到某個地方。面對困難的時候,他沒有放棄任務,依然堅持跟著走。他無奈地拋棄了自己的愛情,甚至餓到飯都沒吃的情況下,也沒有打開身上棉絮包的金子。為什么?因為排長為了把糧食省給他吃,陷入沼澤死掉了,這是對他最大的觸動。最后他決定一個人繼續走上長征的路。這是一個人由不懂到懂、由幼稚到成長的過程,也是我們整個民族從苦難到無奈、從基本訴求到精神訴求的升華。我們民族的根在哪里?就是人的一種信念。
劇中穿插了很多贛南幽默的風采,很好笑,使得它的劇種氣質還在那里。在外部形式上,它也是尋求多變的,采茶舞的風格一開場非常鮮亮,但是舞臺又非常空靈,就幾扇門,用了皮影戲來表現騾子,用人來演樹、演月亮。這樣的手法也是符合戲曲的虛擬性、抒情性、程式性、假定性。曼君老師在這一點上,已經做得渾然天成、惟妙惟肖了。
我看了這么多紅色題材的戲,從來沒有看到一個戲像《一個人的長征》那樣,所有正面人物都死了。共青團員古小姐那么年輕,甚至不知道什么是革命,在同志面對危難的時候挺身而出,死亡之后在舞臺上像靈魂般出現,唱了一段她的理想,看了很震撼,現場很多人潸然淚下。舞臺上所有人死了都會再起來,慢慢走下舞臺。導演讓人物死得有尊嚴。
每次看完張曼君老師的戲,都感覺渾然一體,而且她在每個戲中都有不同嘗試,但是每個戲的風格是很統一的。她其實也是在探索戲曲到底有多少現代的可能性。現代戲曲不可能只有一種標準、一種方法。慚愧的是,很多戲曲理論領域甚至批評領域,實際上已經跟創作脫節了,我們總是帶著固有的標準去看待實踐者的創作。當帶著標尺去看創作的時候,我們往往看不到新的創造,這是我們需要彌補或者反思的地方。
(整理/鐘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