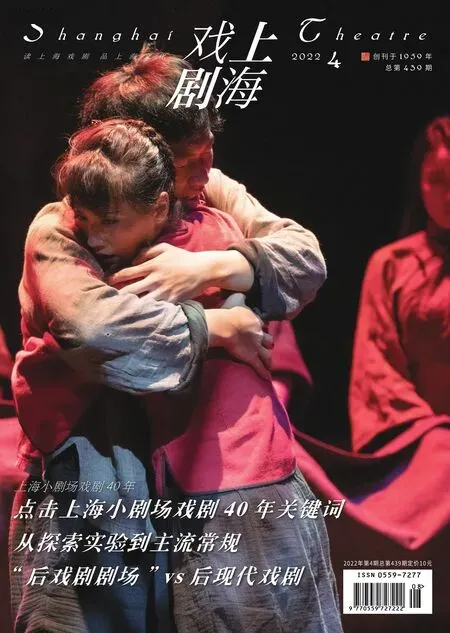“后戲劇劇場”vs后現代戲劇
□宮寶榮
德國戲劇學者漢斯-蒂斯·雷曼教授前不久與世長辭,朋友圈內一片哀悼。確實,在當代西方戲劇學者隊伍當中,沒有誰能比得上雷曼教授在中國的影響了。自從他的代表作被譯成中文以來,幾乎成為中國戲劇學者人手一冊的普及讀物,而在許多研究當代戲劇——不論是中國的還是西方的論著中,“后戲劇劇場”已是不可或缺的門面。“劇場”一詞更是鋪天蓋地,大有取代已有百余年歷史的“戲劇”之勢。
然而,這一切并非沒有問題。本人曾經就theater一詞的中譯名稱發表過幾篇文章,將該詞從“戲劇”譯成“劇場”的經過進行了梳理,同時表明了自己的立場。本文將圍繞“后戲劇劇場”與“后現代戲劇”兩者之間究竟是否存在本質上的不同略作探討,作為對雷曼教授的另一種紀念。
雷曼教授的書寫于1999年。3年之后,上海戲劇學院曹路生教授也發表了一部專著,書名就是《國外后現代戲劇》。由于兩部著作研究的對象與時段高度一致,正好成為筆者進行比較的對象。也許有人會覺得不太科學,因為曹著的樣本范圍較小,且以介紹為主,而雷著不僅樣本多,而且研究深入,自成一家。兩者之間的差別是客觀存在的,但這并不妨礙筆者借助比較來嘗試理解“后戲劇劇場”與“后現代戲劇”這兩個戲劇史上如此糾纏不清的概念。
不妨先來對比一下曹著和雷著中所討論的對象。曹著選取了福爾曼、凱恩特、巴爾巴、姆努什金、米勒、威爾遜、博奧、格洛托夫基、謝克納和泰摩爾十位當代歐洲戲劇家,“對他們的具有后現代主義特征的戲劇理論與實踐作了簡單介紹”。雷著則在前言的最后部分提供了一份長長的名單,上述曹著中的人物除了姆努什金、博奧和泰摩爾不在之外,其他都名列其中。此外,雷曼在第三章重點討論的康托(即凱恩特)、格魯伯和威爾森(即威爾遜)三人中有兩個是曹著的研究對象,兩者所研究的對象高度重疊乃是不爭的事實,亦即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當代戲劇中的重要現象與代表性人物。筆者認為,兩位不約而同地選擇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無疑是考慮到西方社會在經受了20世紀60年代的激烈變革運動,尤其是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之后所發生的根本性變化。眾所周知,整個60年代,進入后工業時代的西方社會風起云涌,反殖民、反越戰、反霸權等浪潮席卷各國,至“五月風暴”時期達到了頂點。雖然這場運動沒能改變歐美社會制度,卻在很大程度上顛覆了傳統的意識形態,而隨著福柯、德里達、萊奧塔、波德里亞等新一代理論家的登臺,所謂“后現代主義”應運而生。這股思潮對資本主義社會采取全面否定和批判的態度,反思現代化帶來的利弊以及以理性主義和啟蒙精神為基礎的整個現代社會。很快,否定人類中心主義、否定主體性、反理性、反等級、反異化,強調多元性、多樣性、差異性、不確定性、機遇性、零碎性、邊緣性等成為這一時期的顯學理論,也成為包括戲劇在內的后現代藝術的共同特征。
既然如此,雷曼為何不認為自己研究的對象屬于后現代戲劇范疇、不愿意使用“后現代戲劇”這一名稱呢?他在書中如此解釋道:“‘后現代主義’這一術語宣稱自己找到了整整一個紀元的定義。但是就劇場藝術實踐而言,大家叫作‘后現代’的許多特征都完全沒有在原則上表現出對于現代的否定——比如手段及引用形式的隨機性(無論表面上的還是真正的)、不受限制地應用、組合各種不同風格、‘畫面劇場’(das Theater der Bilder)、混合媒體與行為藝術等等。但是,這些形式的確表現出了對戲劇形式傳統的否定。”從中不難看出,雷曼對“后現代戲劇”概念不滿的原因有二:一是它過于寬泛,涵蓋了整個20世紀;二是它沒有明確表現出對“現代”的否定以及對傳統形式的否定。
確實,如果說“現代”的概念相對比較明確的話,那么“后現代”的界限似乎有些模糊,至少在20世紀末是如此。即使在今天,有人在討論這一名詞甚至還追溯到了19世紀。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尤其是研究的不斷深入,“后現代”的時間界定已經越來越清晰,越來越與雷曼書中的框架一致,即“后現代主義”在20世紀60年代產生,經過70年代到80年代的發展,至90年代影響擴至全球。事實上,無論是上述思想家、哲學家還是戲劇家,其學說和創作的時間范圍也基本處于這一時段。換言之,對21世紀的我們來說,“后現代”已經不再是一個寬泛無際的概念了。
那么,什么又是“后現代戲劇”呢?曹路生寫道:“在戲劇方面后現代主義戲劇被定義為非線性、非文學、非現實主義、非推論和非封閉的演出。德國柏林藝術學院教授尤根·霍夫曼明確地提出了后現代主義戲劇的三個特征:1.非線性劇作;2.戲劇解構;3.反文法表演。”根據霍夫曼的解釋,“非線性劇作”既無線性故事,又無以對話形式存在的確定人物,沒有確定的戲劇性或角色,也沒有時空限制,沒有開端與結尾和敘述脈絡;解構的對象包括人物、事件和對話,人物不再具有連貫的、邏輯的形象,線性故事被打斷、更改和碎化,對話則被尖叫、口吃或其他聲響所取代;“反文法表演”則指演員不再搬演現存劇本,而是根據大綱來演,甚至完全是即興創作。如果有文本,也會被肢解得支離破碎,追求的只是語言的音響和節奏等,不再追求有意義的形象和劇情,而只注重演員的肉體及其在空間中的占有,表現的“事件”更多的是自我指涉,而不必超越演出本身去解釋。筆者之所以將兩位的論述不厭其煩地引用,意在表明“后現代戲劇”其實在反“現代”方面不僅十分徹底,而且不遺余力。
麻文琦教授指出:“雷曼對‘后現代’在概念使用上的放棄,并不意味著他在哲學層面上與‘后現代’做了切割。恰恰相反,《后戲劇劇場》的寫作浸透了后現代哲學的精神。”可見,“后現代戲劇”也好,“后戲劇劇場”也好,不僅指涉的對象相同,而且精神實質也不無二致。不過,雷曼先生自成一家的創新學說,確實值得我們學習。
注釋:
①曹路生:《國外后現代戲劇》,江蘇:江蘇美術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第15頁。
②漢斯-蒂斯·雷曼:《后戲劇劇場》,李亦男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頁。
③曹路生:《國外后現代戲劇》,江蘇美術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第14頁。
④麻文琦:后戲劇劇場的“后現代性”——兼議“呼喚戲劇的文學性”問題,《戲劇》,2019年第4期,第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