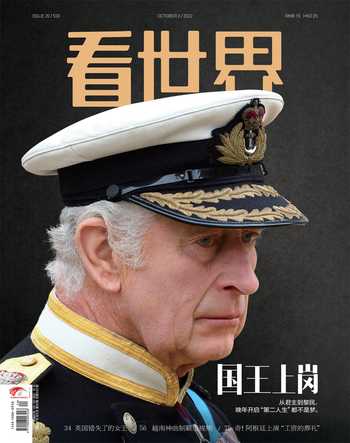死亡從來不“沉默”
何任遠

《魂斷威尼斯》劇照
患上了瘟疫的作曲家已經進入彌留狀態,他坐在威尼斯的海邊,面對著大海。在他的眼里,只有淺灘水里站著的美少年輪廓。經過一陣抽搐后,作曲家視野逐漸模糊,最終撒手人寰。
這一幕來自根據托馬斯·曼小說《魂斷威尼斯》改編的同名電影。其描述來自德國的作曲家古斯塔夫在威尼斯遇到了一個美少年,倆人除了對望之外沒有任何交流。為了能多看一眼這位美少年,古斯塔夫寧愿留在瘟疫肆虐的威尼斯,直到最終染上惡疾死去。
據稱,《魂斷威尼斯》主角的原型人物是奧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馬勒。托馬斯·曼撰寫這部小說的前夕,馬勒的健康每況愈下,最終在1911年于維也納離世。受馬勒的人生啟發,《魂斷威尼斯》中的主角生前最后一眼看到的是美少年在水中的背影。
在美和藝術的懷抱下走向人生終點,這個做法就很維也納了。
“死者肯定是維也納人”
在人們的固有認知中,德意志人性格嚴謹冷靜。實際上,在德國南部和奧地利這些信仰天主教的地區,人們向往感官的豐盈,面對死亡的時候更加追求極致。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甚至發展出一整套獨特又多姿多彩的殯葬文化。
維也納人希望不但死得輕松,更要死得快活、死得風光。

維也納殯葬博物館中展出的葬禮用的馬車

貝多芬(左)和莫扎特(右)在中央墓園的紀念雕塑
維也納人希望不但死得輕松,更要死得快活、死得風光。
維也納不僅有舉世聞名的金色音樂大廳和美泉宮,也有詭異而奢華的死亡文化。昔日帝都浮華的巴洛克建筑和美輪美奐的教堂,并非是為塵世間的人們提供歡樂,而是許諾“靈魂”升上天堂的過程中得以享受絢麗美景。在當地根深蒂固的天主教觀念看來,一個人生前多災多難不要緊,只要死后能上天堂,那人世間的苦難也就值了。
維也納當地一首民謠《死者肯定是維也納人》歌詞大意是:上帝在天堂一邊喝著美酒,一邊看著維也納的亡者靈魂在游蕩;在準確的時刻用準確的路徑找到天堂的大門,只有維也納人才做到。
過去的數個世紀里,作為神圣羅馬帝國、奧地利帝國和奧匈帝國的首都,皇室的一整套殯葬禮儀和用具已經發展得很成熟。在維也納殯葬博物館,人們可以看到哈布斯堡皇朝殯葬用的禮服、羅傘、靈車、宗教用品乃至平民用的棺木和挖墳用具。參觀者還可以躺入棺材,體驗“死亡”的時刻。
這個博物館的策展人、維也納著名的葬禮規劃師維特格·科勒在接受奧地利廣播公司的采訪中,解釋維也納殯葬文化的由來:“在19世紀中期,維也納的生活富足,人們有足夠的金錢去購買模仿巴洛克風格的奢華殯葬用品。”中文語境中所說的“哀榮備至”,可以用奧地利德語“Sch?ne Leich”來形容,那就是中產階級模仿皇室的殯葬儀式,除了有純黑色的馬車運送棺木之外,殯葬人員身穿奢華黑色喪服,長長的隊伍排列在維也納街頭。兩旁站滿了不但不避忌,甚至前來圍觀的市民。
科勒認為,維也納的逝者和市民在風光大葬中相互獲得“好處”:逝者希望通過豪奢的葬禮讓自己被人們記住,而市民則把葬禮視作“一部不用買票的大戲”。
維也納人熱衷土葬,并且希望從中央墓園獲得一席之地。那些在維也納長眠的偉大音樂家們—貝多芬、勃拉姆斯、約翰·斯特勞斯、莫扎特和舒伯特,都在中央墓園擁有精美的紀念雕塑。在哈布斯堡皇朝的陵園,人們可以看到四百年來歷代皇帝和皇后的厚重金屬棺材,以及棺材上夸張詭秘的雕塑。

瑪利亞·特蕾莎女皇和丈夫的下葬地點
其中,瑪利亞·特蕾莎女皇和丈夫的棺材的下葬地點,是整個陵園的亮點。這個重達7噸的雕塑在女皇去世前15年就打造好,最頂端是女皇和丈夫的半身雕塑,四個方位除了有哭泣天使雕塑之外,還有戴著哈布斯堡皇冠的骷髏頭—象征著無論君王平民,死亡最終是一道跨不過的門檻。
在當代維也納,殯葬策劃行業也別出心裁,創意滿滿。有一名爵士樂逝者生前留下遺言,希望葬禮樂隊敲鼓手可以把他的棺材蓋當鼓敲出節奏;有一名少年則把自己奶奶的骨灰用高壓煅燒的方式制作成一枚人造寶石,然后用環鑲在自己的肚臍上……各式各樣標新立異又不失體面的喪葬方式,委婉地表示即使死亡也奪不走逝者與親友之間的紐帶。
燃燒激情,直登極樂
德國南部和奧地利人對死亡的迷幻態度,并不只停留在物質上,還轉化為藝術作品,最終成為德意志文化探討人生終極問題的一部分。19世紀長期在德國南部活躍的德國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納,曾經創作過一部探討生死愛欲的歌劇《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這部長達三個小時的歌劇格調晦暗,低沉交織的管弦樂在三小時里延綿不斷,為的是在劇終營造出一幕高潮:愛之死。
在歌劇中,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這對癡男怨女原來是仇家,伊索爾德為了殺死特里斯坦,試圖偷偷把毒藥加進雙方的酒杯,然后倆人同歸于盡。陰差陽錯下,致命毒藥竟然被女仆換成了催情藥。從相互仇視到相互依戀,倆人分分合合,一直不得如意。相思成疾的特里斯坦被情敵流放到遠方后一蹶不振,千辛萬苦找上門的伊索爾德,看到情郎剛好死去。在愛情魔藥的作用下,伊索爾德撲倒在特里斯坦的尸體上,筋疲力盡地死在對方的懷里。
西方歌劇不乏著名的死亡情節,然而“愛之死”一幕堪稱經典:雙簧管吹奏出著名的“特里斯坦和弦”,簡單的幾個降調音符充滿欲望和曖昧。在小提琴的推波助瀾下,由女高音飾演的伊索爾德唱出了“愛之死”的唱段“如此溫柔如此輕盈,猶如他的微笑”。伊索爾德用高音喊出最后的音符,整個銅管樂組和弦樂爆發出轟隆的高潮樂聲,她的靈魂和特里斯坦的靈魂交纏在一起,歌劇也至此結束。
倆人的情愫起于杯中的催情藥,然而催情藥最終的效果卻跟致命毒藥無異:倆人還是同歸于盡,被情欲殺死。可是,沒有“毒藥”的推波助瀾,二人的生命不會如此絢麗誘人,也更加不會在末尾爆發出華麗的樂章。雖然結局都是同歸于盡,但是兩條道路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沿路風景:沒有激情的生命歷程將是一場平庸無聊的過場戲,而肉與靈的融合則完成圓滿的切換。
歌劇觀眾之所以忍受三個小時低沉陰暗的音樂,以及暗無天日的舞臺布景,為的就是等到在“愛之死”段落中感受生命通過激情達到的圓滿。
死亡從來不沉默
圍繞歌劇《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的藝術觀念乃至哲學理念,歷來演繹甚多。諸多著名指揮家和歌唱家,都在世界數一數二的歌劇院演出過。
長達三個小時的歌劇格調晦暗,為的是在劇終營造出一幕高潮:愛之死。
奧地利“指揮怪杰”卡洛斯·克萊伯的演繹被視為經典之一。在他留下的彩排錄影中,克萊伯好像跳芭蕾舞那樣展開雙臂,讓樂團跟隨自己的雙手高低起伏,發出越來越纏綿的聲音。他一邊指揮一邊對樂團說:“要表現出女性興奮的音樂線條……對于伊索爾德來說,死亡是一種美麗的體驗,不過臺下的觀眾都哭了。”

《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油畫
事業活躍期集中在20世紀70—90年代的“怪杰”克萊伯,跳出了演出經紀人制度主宰下音樂家頻繁出差和預先安排好幾年的“職業生活”。極端任性的克萊伯好幾年才指揮一次演出,“冰箱空了才想開音樂會”,一度向德國總統索要一輛奧迪車才答應在柏林演出。這位常年隱居于奧地利和斯洛文尼亞深山的指揮家,是中國道家哲學的信徒。有人從他的藏書中找出一本德語寫成的《莊子》選集,發現了一些跟生死有關的句子被畫上了重點線,其中有一句這樣說:“死亡從來不是沉默的,死亡比生存發出更大的響聲。”
想要通過音樂會來表達自己聲音的時候,在音樂中感受莊子生死共鳴的時候,他才偶爾出山演出。1999年指揮完人生最后一場音樂會之后,他又隱居了5年,在妻子離世半年后也撒手人寰。
相比克萊伯在斯洛文尼亞深山中“等死”,一些指揮家卻主動“尋死”。指揮家之間有這么一個說法:在指揮臺上突然死亡,在偉大的樂章中離開人世,是最好的歸屬。當然,這個終局“可遇不可求”。
2001年,意大利著名指揮家朱塞佩·西諾波里在柏林的一個音樂會演奏中心臟病發去世,讓樂迷感到惋惜,卻讓另外一些同行嫉妒。拉脫維亞指揮家楊松斯患有嚴重的心臟病,雖然被醫生多次告誡不能過勞工作,卻始終維持高密度的演出計劃,排練和演出更加用心。一次采訪中,楊松斯承認自己就是想有一天死在指揮臺上,而這一刻到來之前,他要把自己喜歡的曲目都趕緊安排時間演奏完。
年輕時曾得罪多個主流樂團而被迫漂泊多年的羅馬尼亞指揮家謝爾蓋·切利比達奇,在晚年吸取了東方禪學的智慧,找到慕尼黑愛樂樂團作為自己長期經營的藝術地盤。晚年的切利比達奇指揮慕尼黑愛樂樂團演繹西方作品時,散發出的那種緩慢和空靈的東方禪意,成為人們在他死后記住的最大亮點。

意大利著名指揮家朱塞佩·西諾波里
2000年患上胃癌的意大利指揮家克勞迪奧·阿巴多被切去了2/3的胃部,當年接任柏林愛樂樂團總監時那個意氣風發的中生代指揮大師,從此變成了一個佝僂的瘦弱老人。但患上絕癥后的阿巴多仿佛獲得了第二次藝術生命,他的指揮語言更加洗練精簡,樂團在他的打磨下變得更加具有透明的質感。英國《留聲機雜志》說,晚年的阿巴多站在指揮臺上,仿佛一個天主教圣徒那樣,用手指撫摸音樂線條,最終產生出他前半生幾乎沒有能力打造出的效果。
特約編輯榮智慧 rzh@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