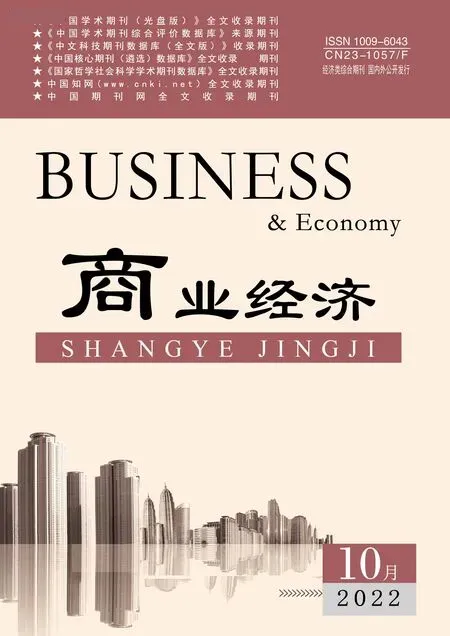數字經濟體系的構成與演化
葛 健 ,葉涓涓 ,王麗杰
(1.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北京 100032; 2.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北京 102488;3.國家能源集團新能源技術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 102209)
如今,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各國經濟發展的核心之一。2020 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39.2 萬億元,占GDP 比重38.6%,2021 年,中央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協同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轉型。數字經濟優勢凸顯,是我國穩定經濟增長的關鍵動力。
一、國內外數字經濟定義
信息時代,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催生出了大量新業態,為人們的生活提供了極大便利,推動了產業結構的變革,逐步催成了數字經濟的提法,然而,究竟何為數字經濟,目前仍未有統一嚴格的定義(石勇,2022)。基于不同視角,國內外學者提出了不同的觀點。早在20 世紀90 年代著名經濟學家唐·塔斯考特就曾表示數字化轉型將會成為未來經濟的發展趨勢(Tapscott,1996;陳堂和陳光,2021)。這是“數字經濟”概念的首次提出。Mahmod(2017)從電子商務的視角出發,認為數字經濟是依托通信技術和計算技術融合、技術和數據流動,進而實現電子商務和大范圍業務轉型的一種經濟趨勢;而Chouhan 等人 (2018)和Szeto(2018)基于數字化的角度出發給出了定義,與Mahmod 不同的是Chouhan 更多的是關注數字經濟對商業變革、勞動力、競爭以及宏觀經濟的影響。Lauscher(2019)從更為宏觀的角度表示數字經濟是一個時代,不僅是關乎網絡技術、智能制造的時代,更是人類使用新技術的時代,實現創造力、知識、智能的相互連接,突破了現有社會和財富發展形態的時代,重點是新經濟、新業態和新技術之間的聯系以及它們相互支持的方式;國內學者王智新等人(2021)則從技術的角度出發,認為數字經濟是一種依托于互聯網底層技術的新型經濟形態,涉及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和大數據等底層數字技術(俗稱為ABCD 技術)的應用,石勇(2022)在“數字經濟的發展和未來”一文中也強調了技術及其應用平臺對于推動新興經濟形態建設、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性。
相比之下,2020 年《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中對數字經濟的定義更為全面,囊括了數字化時代關鍵生產要素、核心驅動力的特征轉變以及數字化對加速重構經濟發展與社會治理模式的重要作用。數字經濟是一個內涵寬泛的概念,為其確定一個具體而又統一的定義仍存在難度(Williams,2021)。隨著數字化水平提高,人們對數字經濟的理解會不斷深入,數字經濟的內涵也會不斷得到擴充,呈現一種動態變化的趨勢。從完整度來看,就目前已有的定義,得出相應結論:以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數字技術為核心驅動力,以現有的信息網絡為重要載體,通過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不斷提高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構經濟發展與社會治理模式的新型社會經濟形態。
二、數字經濟的構成與發展
根據學者杜雪峰(2020)對發達國家主要戰略和重要舉措的梳理與歸納顯示,2010 年以后“數字經濟”相關戰略已逐步上升至國家戰略層面。就在這短短十幾年里,人類社會完成了諸多新產品、新服務、新業態、新生產組織模式與新商業模型的創造,數字技術滲透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全球經濟的主導力量,更是在疫情防控期間引導經濟復蘇的重要支撐。數字技術帶動經濟社會,實現產業變革和業務升級可以歸納為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兩方面。其中,數字產業化是數字經濟的基礎部分,涉及數字技術應用引發的新產品和新服務變革,重點是數字技術的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是數字技術對傳統產業的改造或現有產業中數字技術的應用,重點是數字技術對現有業務的升級改造 (李騰等,2021;杜慶昊,2021)是數字經濟的拓展部分。2019 年《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在“二化”的基礎之上,提出了“三化”(增加了“數字化治理”),2020 年又在此基礎之上擴展為“四化”(增加了“數據價值化”)。雖然,現有的研究中還是普遍將數字經濟分為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兩個部分 (蔣瑛等,2021)。鮮有學者將數字經濟分為“四化”。但在數字經濟的升級發展過程中數字化治理問題和對數據價值化的測度是不可忽視的,此外,還有數字孿生的概念產生也使數字經濟發展進入了新階段 (向玉瓊和謝新水,2021),數字孿生是數字技術發展的高級階段,數字孿生在各行各業的應用以及它的發展潛力是時下較為令人關注的話題。
(一)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
我國“十四五”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要加快推動數字產業化,推進產業數字化轉型,以打造新時代的數字經濟發展的新優勢。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作為數字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囊括了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應用成果,還涉及傳統產業與新一代信息技術融合的內容。一方面是新興技術的批量應用與產業化,另一方面在新興技術優勢基礎之上推動傳統產業實現數字化轉型。二者從本質上看不同但又并非完全獨立,而是彼此融合,相互促進,在借助數據的前提下實現信息交換與傳遞、洞察生產與商業的運行規律 (劉松,2020;杜慶昊,2021)。數字產業化的發展極大提高了社會生產過程中的數據處理能力,而產業數字化的發展又極大豐富了數據要素的類型(張昕蔚和蔣長流,2021)。二者雙輪驅動,同步并行,為加快推動數字經濟基本組成完善提供有利條件。根據馮素玲和許徳慧(2022)對我國2010 至2019 年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顯示,數字產業化能夠有效推動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進而帶動產業結構升級,對實現區域間經濟格局協調發展、緩解我國區域間發展不平衡現狀是利好的。通過數字產業化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實現由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的轉變。無論是數字產業化還是產業數字化在發展數字經濟過程中都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但二者的側重點又有所不同。數字產業化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更多充當“牽引者”的作用,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動力源泉。而產業數字化是傳統產業的升級改造,是在滿足原有產業組成的前提下實現產業結構由量變到質變的飛躍。為保障數字經濟繁榮,側重點要落實在產業的數字化轉型上,加大產業數字化在數字經濟中的占比,著重推動實體經濟轉型升級,有效提升我國實體經濟質量效益與核心競爭力。
(二)數字化治理
數字化應用廣泛,除了通過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在經濟層面構筑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外,數字化在社會治理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凸顯了可觀的應用前景。例如,為疏解政府治理、城市治理、全球治理提供新動力,逐步實現善治的更大場域協同、精準滴灌、多向觸達以及超時空預判(李新根等,2022)。面對日益復雜的社會治理局面和突出的社會矛盾,利用數字化優勢改善政府治理模式,能夠精準定位公眾需求,加快實現快速響應機制的完善,為解決傳統治理模式痛點和解決經濟發展與社會治理水平不適應、不平衡的矛盾提供新的思路。同時,通過政府網站信息公開,便捷的信息傳播渠道也為公眾表達自身訴求提供了機會和平臺(雷曉康和張田,2021)。數字化治理平臺應用與公眾多渠道訴求表達,“向下”和“向上”的雙重保障,更有利于提高社會治理的精細化水平。通過數字化治理平臺,打破了治理體系中的信息壁壘和信息孤島現狀,推動了政府跨部門、跨層級的數字識別、分析和研判,強化了部門間、層級間的協同聯動,促進社會疑難問題的高效解決(張鋒,2021)。例如,新冠疫情突發期間,在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技術的強大支撐下,“健康寶”幫助防疫部門快速定位具有潛在傳播風險的相關人員,實現病毒傳播鏈的溯源,方便了相關單位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完成管控和排查工作,將病毒傳播控制在最小范圍內。利用數字化賦能治理模式,還能避免傳統經驗決策方式的弊端,在海量的數據支撐下進一步提高決策的準確性和科學性。而且通過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興技術還能實現簡單問題的智能化決策,以降低從問題到反饋的間隔時間。對于復雜問題,則不能完全依賴智能化決策,還需借助人腦的思維方式并結合數據分析結果和問題的具體情況來提高決策的準確度。盡管如此,從整體上看,數字化治理模式還是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傳統治理模式的短板。
(三)數據價值化
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配置的體制機制的意見》顯示,“數據”已被列為要素之一并寫入文件,與土地、勞動力、資本等傳統要素并列成為第七大生產要素。相較于傳統生產要素,數據具有無限復制性和重復使用的特性(劉洋等,2020;陳勁和李佳雪,2020),且邊際成本幾乎為0,由此帶來了巨大的規模效益(尹西明,2022)。數據的價值化不僅重構了生產要素體系,通過與其他生產要素融合,還能釋放數字紅利。例如,數據與勞動力結合形成的知識可用于企業管理和日常決策(謝康等,2020;李海艦和趙麗,2021);數據與資本結合形成數字化資本,能夠降低傳統數字資產發行和流通的高昂成本。數據作為生產要素應用于生產活動、企業管理以及決策的制定,充分展現了數據價值化的內涵與外延。但需要厘清的是,數據本身并不存在價值,數據得以實現價值化依靠的是數據的使用價值。人們從海量的原始數據中提煉出有效信息,再將這些有效信息經過一系列的分析和歸納,最終用于生產和決策,提高了生產效率和決策的準確度,這就是數據價值化的體現。然而這也存在弊端,海量的數據以及數據的多樣性會造成數據使用價值密度低的問題,同時對數據的篩選和處理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根據工信部發布的“十四五”大數據產業發展規劃,目前存在大數據人才培養數量與產業規模不匹配不適應的問題,預計在2025 年,大數據核心人才缺口將高達230 萬人,會嚴重制約行業的發展。因此,需要加快并加強對相關技術人才的培養,以解決大數據產業面臨的人才缺口問題。通過提高產業中人才占比,加強對海量數據分析工具的運用,從而進一步提高數據的精細化程度,降低大顆粒度數據的采集與應用。進而提升對客戶需求洞察的準確度,及時對市場需求變化做出快速響應,充分發揮數據的潛在價值。
(四)數字孿生
數字孿生是通過數字化的方式建立物理實體的虛擬數字模型,利用物理模型、歷史數據等實現全過程仿真,真實再現物理實體的全生命周期運行狀態并兼具擴展功能(趙亮等,2021;陶飛等,2020)。簡單來說,就是通過數字化構建一個“數字孿生體”,借助孿生體來模擬真實應用場景,從而達到縮減成本的目的。數字孿生作為數字技術發展的高級階段,目前在多個行業都有試點應用。最早運用于航天航空領域,基于能夠實現物理層和信息層雙向映射的技術優勢,受到各行各業的廣泛關注(劉亮等,2022;陶飛等,2020)。應運而生了城市、建筑、電網、醫療、工業等數字孿生系統,為解決諸如資源分配不合理、安全隱患預測精度低、過度依賴人工經驗等問題提供了科學合理的客觀依據(李浩等,2021)。2021 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發展數字經濟必須要把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尤其是對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研究顯示,數字孿生在制造領域具有極大的應用潛力,通過建立產品的數字孿生模型并對其進行虛擬加工與反復驗證,能夠避免高昂的成本與漫長的試驗周期(孟松鶴等,2020)。實現在產品設計、工藝優化、質量管理、預測性維護、分析客戶體驗等方面的改善。制造業作為實體經濟中最重要和最基礎的部分,承擔國家經濟命脈之重任。而數字孿生能以數字化的形式在生產制造過程中實現全流程的動態仿真,覆蓋產品生命周期和產業鏈條的方方面面,對穩固國家經濟命脈、驅動經濟發展、推動未來智能制造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吳雁等,2021)。但根據目前的發展情況來看,制造業正面臨發展的瓶頸期,人口紅利效益衰減、原材料價格不斷上漲、員工隊伍老齡化等問題層出不窮。因此,要加快推動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提高制造業中的數字化人才配比,落實數字孿生技術在制造業中的應用,達到降低制造成本、吸納高新技術人才的目的,從而扭轉制造業的發展劣勢。
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作為數字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生產力重塑、激發經濟活力提供動力,是發展數字經濟的核心關鍵。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彼此之間也存在聯系,以數字產業化帶動產業數字化發展,來加快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平穩推進。而數字化治理在數字經濟當中更多起到的是保障作用,通過治理模式的數字化轉型來縮小社會治理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的差距,以更好的服務多領域、多行業、多區域融合發展。數據價值化則是數字經濟得以發展的基礎,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化治理都有賴于數據的價值化,是數字經濟的本質體現。而數字孿生,依照《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并不在數字經濟的構成當中,但嵌入數字經濟發展的方方面面,是數字技術發展的高級階段,也是產業數字化、數字化治理朝著更合理、更智能方向轉變的關鍵技術。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化治理、數據價值化、數字孿生彼此聯系、相互影響共同推進數字經濟時代朝著更加成熟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