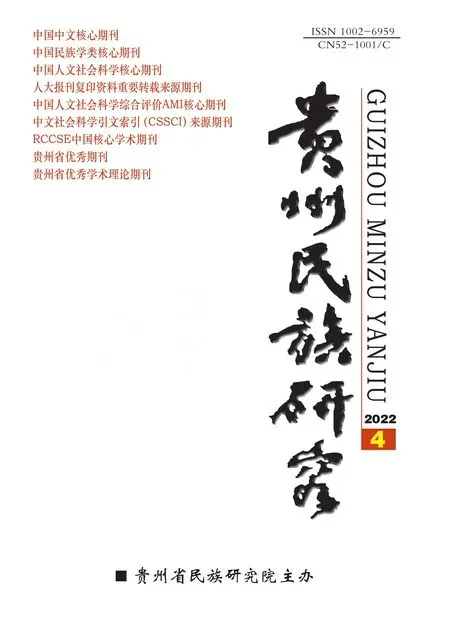中國邊疆學研究及邊疆學學科體系建設
宋才發
(廣西民族大學 法學院,廣西·南寧 530006)
中國邊疆學作為21世紀一門方興未艾的交叉學科和新興學科,加強其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既是當下民族學一級學科領域的熱點問題,也是國家邊疆安全、邊疆建設和邊疆發展的重大課題,更是新時代賦予邊疆學學人的重大歷史使命。
一、中國邊疆學研究現狀及相關學術理念
(一) 中國邊疆學研究的艱難起步及未來發展構想
作為歷史產物和現實存在的邊疆,既是當下邊疆建設與發展的客觀場域,也是邊疆學研究的具體對象。脫離抑或離開邊疆這個客觀的現實存在,就談不上對邊疆學的研究。“邊疆學”這個專門的語詞概念,最早見于1933年6月號《殖邊月刊》雜志。3年后的1936年1月,顧頡剛先生依據馮家升先生舊作修訂的《〈禹貢〉學會研究邊疆計劃書》,正式提出并使用“邊疆學”概念。又過3年后的1939年,楊成志先生在中山大學文學院率先向教育主管機構提出在國立中山大學設立邊疆學系的建議,制訂了《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邊疆學系組織計劃綱要》。據本人目前所掌握的資料考證,這是最早在中國高等學校提出設置“邊疆學專業”“邊疆學學科”的建議。盡管該建議案最終沒有獲得官方批準,但是希望把“邊疆學”建設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主張,畢竟由少數專家的構想變成了學界的共同心聲。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界又提出了“中國邊疆學”概念和學科構建問題。譬如,馬大正研究員提出要以“中國邊疆學”命名,認定中國邊疆學是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一門綜合性的學科。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邊疆學已邁過它幼年的起步階段,進入了青壯年厚積薄發的發展階段,甚至成為民族學一級學科研究領域的顯學。但是任何一門新興學科的形成抑或得到社會的公認,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如果學界在這個問題上不能形成拳頭、下一番苦功夫研究邊疆學的一些基本問題,譬如,建立一個核心問題以及與此相聯系的核心概念,那么,“中國邊疆學”就有可能還原為一般意義上的“邊疆學”,中國邊疆學不可能在“自說自話”的基礎上產生。有關中國邊疆學學科體系的構建問題,目前尚處于學術調研、學術討論的發展期抑或研究階段,距離真正搭建起一門較為規范的學科體系,還需要經歷長期的知識和成果積累,需要作出許多艱苦扎實的努力才行。中國邊疆學學科體系的構建,本質上是對當代邊疆治理、邊疆建設、邊疆研究現實需要的一種理論回應,構建邊疆學學科體系有它的實踐需要。創建和形成中國邊疆學多學科、開放性的學科體系,需要倡導一種可供本領域專家學者效仿的思維方式,引導同行專家學者在學科知識積累、學術研究方面集思廣益;需要創設本研究領域大家熟悉的研究范式,尤其需要通過大眾傳媒推介和傳播中國邊疆學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學科功能,在與其他相關學科的學術交流、學術切磋與學術交融的過程中,讓更多的其他領域專家學者接受和認同中國邊疆學學科體系的理念。
(二) 中國邊疆學研究的歷史背景以及邏輯起點
中國邊疆學研究具有優良深厚的學術傳統,歷經一代又一代學人的共同努力,把中國邊疆的歷史與邊疆的現狀結合起來研究,已經抑或正在突破傳統的邊疆史地研究的范疇。馬大正研究員在總結近代以來邊疆學研究篳路藍縷的艱難歷程后,認為自19世紀中葉肇始至今,邊疆學研究已形成并出現過3次高潮:(1) 自19世紀中葉到19世紀末,西北邊疆史地學興起是中國邊疆學研究第一次高潮的標志;(2) 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邊政學的提出與展開是中國邊疆學研究第二次高潮的標志;(3)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提出和論證中國邊疆學學科體系,標志著中國邊疆學研究進入第三次高潮。近代以來,由于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入侵和瘋狂掠奪,徹底打亂了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實際進程,使得中國成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家。依據中國歷史發展進程和歷史特點分析,中國邊疆學研究大體可以劃分為兩個不同的歷史階段:以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專制帝制、建立共和政體為歷史分界線,前期可視為王朝國家階段的邊疆學,后期可視為民族國家階段的邊疆學。作為具有科學獨特性和生命力的中國邊疆學,其邏輯起點不應當繼續在發黃的故紙堆里面去尋找,而應當在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中去尋找。邏輯起點絕對不是某種捉摸不定的、玄而又玄的東西,一定是也必然是固定的、能夠代表絕大多數人的東西。把中國邊疆學研究的邏輯起點定在民族國家出現之后,可以從時間的維度和空間的維度兩個視角把握邊疆學,既有利于達到和實現邊疆學的學科化,也有利于促使邊疆學研究的時空統一性,并且具備邊疆理論與實踐研究的參照系。張世明教授就曾指出:“邊疆學在眾多學科之間的邊界交匯起點這種‘學科化’也表現出一種‘邊疆性’……這種學科的‘邊疆性’使邊疆學吞吐融合各種學術養料,具有與相關學科核心領域不同的特色”。這是因為民族國家形態相對于其他形態的國家類型而言,包含有國家的主權性、民族性、公民性等特殊要素,成型的民族國家塑造了成型的國家疆域和邊疆領土。就其理論分析而言,邊界是邊疆學的關鍵詞和核心概念,邊界是指國與國之間的交界線。盡管“邊境”是“邊界”的近義詞,但是兩者之間具有本質的差別,邊境通常是指邊界線內側30~50公里范圍的區域。譬如,我國邊境就是與相鄰國家接壤的地級市、縣(旗) 行政管轄范圍內的領土。當下人們談論的邊疆戰略、邊疆治理、邊疆發展、邊疆安全和邊疆穩定,可以說都是由“邊界”引發和延伸出來的。邊疆學之所以視邊界為關鍵詞和核心概念,是因為在世界空間的有限性與國家利益的無限性之間,現實存在的和必然產生的諸多矛盾,需要和仰賴于通過邊界法治的方式去調整。所以,周平教授認為:“民族國家把一個國家疆域視為國家主權管轄的地理范圍,這個地理范圍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領土’。‘邊界’就是用來清晰界定國家領土的范圍界限。”正是由于有了民族國家這個政權實體,才使得邊疆具有重要而深遠的現實意義。
(三) 中國邊疆學研究的熱點問題和現實問題
馬大正研究員在《當代中國邊疆研究(1949—2014)》一書中,較為系統地梳理了自新中國成立到2014年我國邊疆學研究的發展狀況,對于學界在這個時間段里,出版的相關著作和學術論文進行了有價值的評價,介紹了學界構建中國邊疆學學科的學術思想、理論建樹和積極建議,較為準確地描繪了中國邊疆學的演進歷程和未來發展的趨勢,立體式地展示了中國邊疆學的厚度、深度和廣度。從當下邊疆學研究的重點領域考察,邊疆民族地區是邊疆和邊疆學研究的重點問題和核心區域。其中,西南邊疆又是研究的熱點區域。就邊疆研究的現狀和整體而言,西北民族地區邊疆屬于第二梯隊,東北與北部邊疆緊隨其后;對西北邊疆史地和西域問題的研究,是西北民族地區邊疆研究的核心問題。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來,民族地區尤其是邊疆區域的有效治理,則是中國邊疆學研究的出發點,邊疆的穩定、發展和繁榮是其落腳點。其實“邊疆學”與“中國邊疆學”,是兩個含義并不完全相同的概念。由于“邊疆”本身屬性較為復雜,涉及內容相對較為寬泛,研究學科背景和方法的交叉性,使得邊疆學的研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呈現出研究主體多元、研究主題多樣、內容泛化不聚焦的問題。邊疆學作為一門學科而言,它應當是人類對知識體系的探求過程,不只是要在國內學術范圍內立得住腳,而且還必須面向世界,在世界的學術范圍內立得住腳,是一門人類對“邊疆現象”作出理論闡釋的專門科學。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認為使用“邊疆學”的提法似乎更為妥當,因為邊疆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需要得到其他學科的支持才行。但是值得關注的是學者們在研究的過程中,多是為了使正在冉冉升起的邊疆學學科,在指向上以示與國外的邊疆學具有明顯的區別性。如果從這個視角考慮問題,使用“中國邊疆學”概念也不是不可以的。在中華王朝的歷史嬗變中,清王朝的國體和政體扮演了一個獨特的、卻足以支撐一種類型的作用。王朝國家多有向周邊地區開拓疆域的行為,以增進其統治權的意圖和傾向,即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朝國家關注邊疆的核心利益,多是“疆土”而非“人群”。誠如張世明教授所言:中國邊疆學“學科的內核地帶是比較穩固的,但學科的外圍邊疆地帶則往往比較模糊,并且多系未開發的空白或者低度開發的區域”。所以,邊疆學研究的重點問題,在“邊疆”的前提下通常就是地理疆域,可以說邊疆是王朝抑或國家這類政治實體直接演化出來的產物。因而邊疆學研究自清王朝以降,可謂是學界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清王朝之前的歷朝歷代,對邊疆的關注基本上“集中體現在司馬遷《史記》‘四夷傳’開其端、20 世紀初葉《清史稿》‘吐司·藩部·屬國’殿其后的所謂‘正史’的系列編纂之中。這一系列關注的邊疆,是從王朝的中心朝向周邊外圍所做的延伸性觀察。”姚大力教授在《追尋“我們”的根源》一書中,認為清王朝是與“外儒內法的專制君主官僚制”對應的“內亞邊疆帝國的國家建構模式”。正是在這種復合型王朝的場景下,邊疆被賦予中原王朝核心之四周的人群及廣闊的疆土。然而明確提出“中國邊疆學”概念的,既不是清王朝時代的專家學者,更不是清王朝之前的專家學者。就筆者所接觸到的研究資料看,當代的邢玉林編審、馬大正研究員算是較早提出構建“中國邊疆學”的專家代表,方鐵教授更是力主創設“中國邊疆學”權威專家之一。包括其他諸多專家學者在內的、對中國邊疆現實問題研究的一系列成果,確實把中國邊疆學研究從幕后推到了臺前,促使中國邊疆學研究成為一個時期以來的熱點問題,在推動“‘中國邊疆學’的發展上有著里程碑式的地位”。
二、中國邊疆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及價值
(一) 邊政學研究是邊疆學研究的前奏曲
邊政學無論就其內容還是就其形式而言,都要比邊疆學的資格老得多,對邊政問題的研究在我國由來已久。“中國邊疆政治學”抑或“中國邊政學”,是在既沒有邊疆學學科體系,也沒有厘清邊疆學基本內涵和外延的情況下出現的。譬如,中央民族大學吳楚克教授2005年就出版了《中國邊疆政治學》,云南大學周平教授2015年也出版了《中國邊疆政治學》。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長期以來,邊疆就是史學界所關注和用心研究的重要問題。歷代先賢和專家學者,都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從不同的視角,對邊疆治理進行過可歌可泣的探索。在《二十四史》中,就有關于邊疆民族、邊疆社會治理的歷史記述,成為后世研究中國邊疆彌足珍貴的文獻資料。中央民族大學吳文藻教授1942年發表的《邊政學發凡》,可以說就是中國邊政學框架的雛形。中國邊政學研究發源于中國歷史地理研究。邊政學研究與邊疆學研究具有天然的內在聯系,邊政學研究實質上就是邊疆學研究的前奏曲。馬大正研究員曾經把中華民國時期的邊政學研究,看成是邊疆學研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學科的分立就如同社會分工愈來愈細一樣,體現了“具體學科對象的差別”和“術業有專攻”的學術發展規律。“民國時期邊疆學研究發展到了一個新高度,在學科構建上也初見成效,表現為邊政學的構建并形成體系。”反之,如果沒有邊疆學對研究邊疆具體問題的宏觀指導,那么,被視為邊疆學旗下的邊疆經濟學、邊疆政治學和邊疆社會學,幾乎就無法萌芽和產生。任何一門獨立學科的形成,一般都具有3個基本特征:“一是有獨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對象,二是有較為獨特的研究方法,三是有自己的理論體系。”
(二) 三大體系研究是邊疆學最主要的內容
中國是一個具有5000年文明傳承的國家,也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過文明延續性的國家,中國邊疆的概念和內涵具有悠久的歷史。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邊疆學就是中國特色的地緣政治學。以政治地理學為基礎,構筑中國的地緣政治學,也就是中國邊疆學。邊疆的本質規定,是國家政治利益的集中體現。中國邊疆學的理論規范,應當為國家政治利益服務;應當揭示邊疆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客觀運行軌跡以及發展變化的規律;應當遵循新時代中國政府的政治制度,為中國特色邊疆學學科體系建設作出努力。(1) 話語體系是學科存在與發展的基礎。中國邊疆學的話語體系涉及“中國邊疆是什么?”“邊疆從哪兒來?”“發展的最終目標是什么?”等一系列問題。這里所論及的話語體系,是指一整套表述某種思維系統的語言系統。本人在華中師范大學剛出道的時候,并非就是研究“民商法學”和“民族法學”的人,而是隸屬于政治學一級學科“科學社會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專業”的學科帶頭人。考察和研究政治學學科體系建設的成功經驗,類推證明中國“邊疆學研究”和“邊疆學學科建設”的根本問題,實質上就是邊疆學學科建設的話語體系問題。譬如,“中國邊疆的學科、學科體系、學科建設的現實情況以及學理層面,鮮明地透視出話語體系的重要性。一方面,話語是表達邊疆思想與傳遞邊疆知識的媒介,沒有科學、成熟的話語體系,學科便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中國邊疆學的理論價值和應用價值,主要是通過話語體系來體現和表達的。”一個成熟的學科,需要有一個合理可行的話語體系做基礎。假如話語沒有特色,學科難言價值;話語體系沒有形成,學科體系難言影響。中華民族悠久而深厚的知識積淀,正是中國邊疆學體系構建的厚重基礎。(2) 學術體系是學科存在與發展的核心。學術體系是指學術研究的系統化,最根本的是理論觀點的系統化,以及研究方法、科研手段和學術評價標準的系統化。這是學術能力和學術水準的根本所在,系統化通常“基于資料、始于問題、鏈以邏輯”,體現在學術帶頭人、學術成果、學術評價和學術傳承上面。包括中國邊疆歷史沿革、邊疆安全穩定、邊疆繁榮發展,諸方面理論與實踐的系統化,既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長期發展的產物,是邊疆學知識體系、學術體系的核心內容,也是歷代邊疆建設實踐者和理論者辛勤勞動的結晶。(3) 學科體系是學科存在與發展的支撐。學科體系是學術研究發展到一定階段和一定程度的必然產物。“學科體系的科學性和完整性,是中國邊疆學建設的前提,也是中國邊疆學持續進步的重要依托……打造中國邊疆學,必須按照邊疆研究的基本屬性,注重多學科有機結合、彼此交融,注重多學科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相互滲透;必須按照邊疆研究的學術規律,形成具有時代特點、內涵多樣、結構合理、立足前沿、適應國家需求的學科體系。”
(三) 邊疆學研究成果服務于邊疆治理的價值追求
新時代邊疆學的興起以及中國邊疆學學科體系構建問題的提出,從客觀現實上看,是實現國家發展戰略目標和邊疆治理戰略目標的需要。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里面就包含有邊疆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內容,邊疆治理現代化是當代邊疆地區社會治理現代化的中心任務。邊疆學的研究成果,源于邊疆治理鮮活的實際效果,是邊疆建設實踐者和相關理論工作者共同智慧的結晶。通過中國邊疆學研究達到有效維護國家領土完整、維護國家和邊疆地區安全,推動邊疆地區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是中國邊疆學發展的重要目標和現實出發點。邊疆學的研究成果尤其要服務于當下的邊疆治理實踐,為邊疆民族地區社會治理、鄉村振興和邊疆現代化建設提供強大的理論支撐,這是中國邊疆學學科體系構建的現實需求和強大動力。邊疆學研究成果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產物,是邊疆學研究的理論工作者,通過對邊疆問題的深入調研和現實考察,以具有思想穿透力和說服力的成果方式,服務于黨政機關對邊疆治理和邊疆建設的決策咨詢,為實現邊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出理論貢獻。專家學者把自己思維創造的成果,以提供智力支持的方式服務于邊疆社會,應當說這就是構建邊疆學學科體系的初衷,是邊疆學研究的現實導向,也是邊疆學研究和邊疆學學科體系建設的必然歸宿。
三、中國邊疆學學科體系構建及邊疆學建設
(一) 中國邊疆學學科體系構建的基本理論
“中國邊疆不僅是中國邊疆學研究的對象,也是歷史學、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地理學等學科的研究對象”。中國邊疆是在中國歷史上形成的,現實的邊疆是對歷史邊疆的延續。當下邊疆存在的諸多現實問題,實質上多是由歷史因素造成的。中國邊疆學是一門研究中國邊疆的科學,對邊疆現實問題的研究,離不開對邊疆歷史的解讀。邊疆歷史研究是中國邊疆學研究的基礎,中國邊疆學的知識溯源,需要從歷史學的分支“中國邊疆史地”開始。綜上所述,就是中國邊疆學同中國歷史與現實、同中國邊疆史地之間的相互關系。李大龍認為:“中國邊疆學學術體系由一體、兩足、八分支構成,即中國邊疆學是一級學科,其下有中國邊疆歷史學、中國邊疆應用學兩足支撐,研究的具體展開則是進一步劃分的中國邊疆學理論研究、中國東北邊疆研究、中國北部邊疆研究、中國西北(新疆) 邊疆研究、中國西藏研究、中國西南邊疆研究、中國海疆研究、中國海洋研究等八個分支體系。”學術體系之構建是學科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學術體系關涉到學科內部體系結構問題,同時還涉及邊疆學學科體系的研究方法問題。學科體系關系到學科的發展定位和未來方向,學科體系在理論上不僅包括知識的分類,而且包括有關知識分類的制度與規范。規范在這里體現了制度權威在知識體系產生過程中的作用,學科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知識與權力之間的關系,揭示知識體系既有的內部機制也存在外部條件。但是學科構建有它自身的發展規律,由知識生產規范與社會承認焦慮交織而產生的學科化沖動,需要接受知識生產規律與學科發展邏輯的制約與馴服。中國邊疆學是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具有綜合性、現實性和實踐性的特征。中國邊疆學研究屬于多學科的綜合性研究,需要十分重視對邊疆地區的實地調查研究,需要掌握多領域、多學科知識和跨學科研究方法,尤其需要處理好實證研究和理論創新之間的關系。中國邊疆學研究的內容,不僅涉及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邊疆政策,而且涉及到軍事、外交和國防、自然資源、地理環境和氣候特點等。
(二) 中國邊疆學構成獨立的知識體系和學科體系
學科體系在這里是指對專業學科門類整體設置的系統化,中國邊疆學的關鍵詞和第一要素是“中國邊疆”。在整個哲學社會科學知識體系中,中國邊疆學是以中國邊疆為其研究對象、區別于其他學科的一門獨立的知識體系。因而它的第二個關鍵詞和要素是“獨立的知識體系”。中國邊疆學體系在空間格局上,“把中國陸地邊疆和海洋邊疆作為整體進行全面考察,研究邊疆起源、演進的規律,以及國家治理邊疆的全過程。”在時間脈絡上,中國邊疆學覆蓋古代邊疆、現代邊疆和當代邊疆全時段,涵蓋國家歷史邊疆和國家領土的形成與演進全過程。必須從基本理論上進一步弄清楚邊疆學的學科目標。只有從理論體系上弄清楚邊疆學的學科目標,才能抓住邊疆學學科體系構建乃至建成的本質問題。中國邊疆學學科體系構建有3個基本目標:一是便于集中力量探尋邊疆形成、發展的歷史進程,研究邊疆歷史發展嬗變的規律,為闡釋統一多民族國家邊疆治理提供法律依據和理論基石;二是便于集中力量厘清現實邊疆治理、邊疆建設的來龍去脈,為邊疆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制度依據和理論支撐;三是便于集中力量探究邊疆開發經營的歷史軌跡、現實進程和未來的發展方向,為現實邊疆治理、開發、繁榮和長治久安提供決策咨詢。
(三) 中國邊疆學具有建成獨立學科的基本條件
一個學科之成為一個學科,就在于它有自己獨特的范式。范式有觀念層面的,也有社會建制和社會運作層面上的。學科建設就是在這兩個層面上進行范式的構建和鞏固。改革開放40多年來,邊疆史地研究取得了一大批豐碩的科研成果,客觀上既推動了中國邊疆學理論研究,也促進了中國邊疆學學科體系的構建,關鍵是初步形成了中國邊疆學理論研究體系和研究方法,為邊疆學學科體系最終建成奠定了基礎。但是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成果再豐厚,也不能意味著就可以從中衍生出邊疆學這個新學科。現實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學界對中國邊疆學的認識不透徹,對邊疆學的體系、內涵以及特點還缺乏一致的認識;二是邊疆學的研究主體多集中在邊疆史研究領域,且邊疆史研究又與中國史研究渾然一體,顯示不出邊疆研究是一門獨立學科;三是“在中國邊疆學研究對象、理論體系、知識基礎、研究方法等問題上的思考還不夠深入。”“經歷千年積累,百年探索,三十年創新,中國邊疆學已經基本完成學科層面的建構。一般認為,學科是集中知識的平臺,有關中國邊疆學的知識匯聚于同一個平臺上,便形成了有明確定位和鮮明特色的中國邊疆學。”同過去幾十年相比較,當下的邊疆學研究已經有了一個良好的平臺。譬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云南大學、四川大學、中央民族大學、陜西師范大學等教學科研機構,都設立了邊疆研究所或研究中心,有一批科研人員專門從事中國邊疆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長期以來一直在引領和推動全國對中國邊疆學問題的研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雜志,是當下國內外最具影響力的專業性學術期刊。邊疆學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學科化訴求,就其基本條件而言,突出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要形成特定的研究領域以及相應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二是要在專業設置、人才培養、學術出版、機構建設諸多方面得到制度性支持。“一個學科最終建立起來,并且得到普遍的社會承認,需要這兩個方面的相互支持與配合,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關聯,前者決定著后者。”對于“邊疆學”這樣一個還沒有成其為獨立學科的學術概念,多數學者是先入為主地把它當作一個既定的、不言自明的概念使用的,其實不然。要知曉一門新興學科的形成和發展,哪怕就是一個普通的學術概念,只有借助對學術發展史的梳理才可能獲得真知灼見。盡管中國邊疆學還沒有獲得國家的“出生證”,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公布的“學科、專業目錄”中,無論是一級學科還是二級學科,直到現在還沒有給予“中國邊疆學”應有的名分。既然邊疆學已經具備建成獨立學科的基本條件,名分固然重要,名不正則言不順。但是并不能從根本上中斷對中國邊疆學的研究和對邊疆學科體系的建設工作,應當群策群力先把事情干起來。對于任何一件新生事物的誕生,在眾人還沒有接受它之前隨時隨地都會遇到阻力。本人2000 年在學校黨委常委會上,提出把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的法學、政治學和行政管理學3個本科專業,建設成“從本科到博士一條龍的培養模式”的時候,就曾遭到一位時任副校長的黨委常委的反對。2003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批準中央民族大學在民族學一級學科下,自主設立民族法學、民族政治、民族地區行政管理3個博士、碩士學位專業并實現當年招生。這也即是說,中國邊疆學在“學科、專業目錄”還沒有“上戶口”的情況下,應當按照中國邊疆學自身的發展規律,借鑒國內其他學科建設的經驗,一邊扎扎實實地進行學科建設,一邊爭取得到更多同行專家的認同和認可,用扎實有效的學科建設成就去爭取獲得名分。
(四) 邊疆學學科體系隸屬于民族學科體系
構建新時代中國邊疆學學科體系,是中國特色民族學學科體系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邊疆學學科體系原本就隸屬于民族學學科體系。從類型上看,中國邊疆學是認識邊疆、把握邊疆歷史規律的重要學科和學術工具,是一門富有中國特色的、融合了民族、地區和邊界3種要素的新興學科,是專門研究和探討中國邊疆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的綜合性學科。從性質上看,中國邊疆學不屬于熱門學科,而屬于冷門學科;不屬于成熟學科,而屬于正在建設之中的學科。從定位上看,中國邊疆學是一門典型的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必須按照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的要求,遵循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的學術范式、學術標準、學術規則和學術規律予以構建和建設。要把中國邊疆學作為民族學學科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逐漸把中國邊疆學建設成為學科體系完備的成熟學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建設邊疆學學科體系需要推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三位一體建設,要求多學科在融合交叉的狀態下開展學術研究;需要按照“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總體要求,把構建中國邊疆學學科體系作為出發點,著力打造新時代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邊疆學學科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