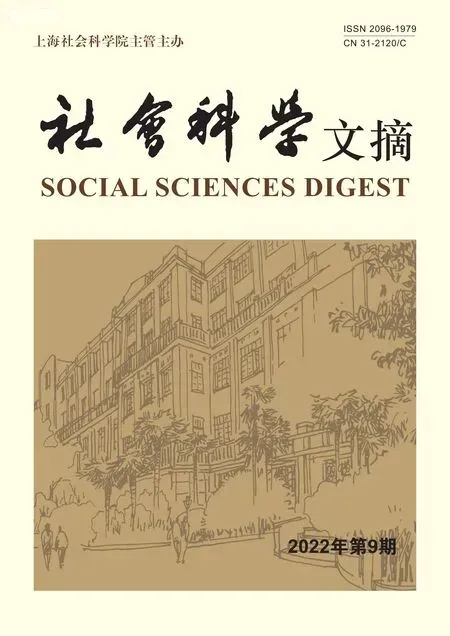關于“中國視角的全球史”之思考
——以若干概念工具為中心
文/胡成
提出“中國視角的全球史”的意義,在于確立本土學術主體性,讓歷史聚光燈更多照射到在地歷史,及其與不同時期全球化發展的多方聯結和互動。作為實際展開的一個歷史進程,中國早自16世紀就出現了大規模移民、勞動密集型產品輸出及龐大市場,或可被視為全球史日常生活結構層面上最持久的推動。再通過對以往研究范式的反思,本文討論了“歐洲省級化”“大時間”及“小時間”的概念,期望經由“外來/本土”“西方/中國”“全球/在地”之間的“對話”和“理解”,盡可能達到費孝通先生所期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
中國對早期全球化的正向推動
研究通常需要設置恰如其分的切入點,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研究視角,那么對“中國視角的全球史”的討論,似乎應基于自16世紀以來,中國在日常生活層面上對那個年代全球化發展所作出的三項重要推動:
首先,是大規模的海外移民,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發展。隨著歐洲殖民者在東南亞的早期殖民開發,抵達該地的華商將胡椒、肉桂、丁香、橡膠,以及從中國運來的絲綢、瓷器、茶葉,出售給歐洲商隊,并將歐洲商人支付的墨西哥銀元運回中國。再至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東南亞各地的殖民經濟快速發展,數以百萬計的華人勞工充當了種植園、錫礦開采最廉價和最高效的勞動力。與此同時,還有數百萬華人前往美洲、澳洲、歐洲,以及非洲。除了少許人經商之外,他們之中更多人從事淘金、修筑鐵路、耕作,是每一個當地社會最不能被輕視的勞動大軍。總體說來,作為在此過程中海外移民最多的族裔之一,直到1949年前后已有三千萬華人在海外定居,其中八成是在東南亞。
其次,是中國制造品和日用消費品的輸出,改善了當地的生活質量。這是因為15世紀以降,隨著帆船、快船及蒸汽輪船通行的大航海時代到來,瓷器和茶葉逐漸成為歐美社會的日用消費品。尤其在工業革命最早發軔的英國,很多研究已表明最初是來自中國的茶葉很快取代麥酒、啤酒而成為日常飲品。對于那些每天工作時間超過十小時的貧苦勞工,用熱茶配以冷冰冰的干奶酪、干面包,可以不至于過度疲憊;再加上工人們多蝸居在衛生環境骯臟的貧民窟,泡茶需將水煮沸,又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烈性腸道流行病的蔓延。由此一位英國學者認為飲茶作為英國工業革命的助推器,徹底重塑了其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可以說:“茶改變了一切。”
最后,是中國龐大的市場規模,促進了更大規模的貿易交往和資本流動。正如當年哥倫布之所以不顧一切,揚帆駛向波濤洶涌的無際大海,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關于東方、關于中國財富的神奇想象之強烈刺激。僅就市場規模來看,1800年全球十大城市,北京、廣州、杭州、蘇州榜上有名,最繁忙的口岸城市則是廣州。再至19世紀末,中國在列強武力脅迫之下,不得不開放幅員更為廣闊的內陸市場。就此,一位美國記者寫道:這里有四億消費者,“如果他們把大衣增加一英寸,那么新英格蘭紡織廠在未來幾年里就會忙得不可開交”。
追尋歷史“主體性”及對以往研究范式的反思
如果說全球史研究的重心,在于探討全球及在地關系,那么在地歷史的主體性就必須認真考慮。早在1959年黎澍刊發《中國的近代始于何時?》一文,談及馬克思主義史家之所以將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作為近代中國歷史開端,是從“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的概念出發,認為其時中國在遭受侵略后隨即出現了“覺悟的反抗人們和覺悟的反抗運動”,將之視為當時在地中國社會主體性的體現。劉大年于1965年刊發的《亞洲歷史怎樣評價》一文,一方面批評西方殖民主義把亞洲看成為一片“沒有歷史的荒漠”;另一方面高度贊揚近代亞洲成了世界人民反抗殖民主義的最大戰場。他說:“對亞洲歷史的這一個方面,我們是必須大書而特書的。”
以上或可看作“革命”史觀探尋、確立的中國近代歷史本土“主體性”。該研究范式的轉向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隨后在90年代初又興起“現代化”研究。其時倡導最力的羅榮渠先生,大力呼吁將研究轉移到注重生產力與社會經濟發展方面,也就是轉移到探尋社會變革的動力學方面來。在談及如何消除“歐洲/西方中心主義”,以及如何確立近代中國歷史本土“主體性”的問題時,羅先生認為現代化研究,特別是非西方國家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的研究,要用中國人自己的“現代化”概念,取代以往人們所說的“西化”概念。在他看來:“東方的西方化,這是一個西方的概念;東方的現代化,則是一個新概念,是第三世界發展中的新概念。”
盡管“現代化”研究,在探尋中國近代歷史本土“主體性”方面,相對于以往“革命”史觀,已有更多的歷史包容性,但其“一元多線歷史發展觀”,似乎仍未徹底摒棄帶有濃郁“歐洲中心主義”意味的線性進步史觀。接下來直接挑戰“歐洲/西方中心主義”,并努力探尋中國歷史本土“主體性”的著述,是美國經濟史家彭慕蘭于2001年出版的《大分流: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中國與歐洲為何走上不同道路?》。作者通過比較在國土、人口和內部多樣性與英格蘭頗多相似的中國江南地區,發現18世紀之前兩地民眾的平均壽命、資本積累、人口成長速度、營養與生活水平相差不遠。作者的結論是其時中國經濟并不落后,后來之所以出現了“大分流”,且差距不斷被拉大,重要原因在于歐洲得益于美洲新大陸的開發,以及英國煤礦的優越地理位置。這樣一來,以往支撐“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成功轉型以及歐洲工業革命的迅速騰飛等,都可以被視為偶然現象及歷史意外事件。
該書于2003年譯成中文出版,在中國史學界引起了較大反響。不過,令人遺憾的是某些研究夸大其詞地將帝王統治、男尊女卑、科舉制,乃至宗族血緣人際關系,標簽為所謂“現代性”。2006年,夏明方刊發的一篇文章指出:由于采用了一種越來越寬松的“現代性”定義,我們史學界進入一個“泛近代化論”的時代;持此觀點的學者堅信:“中國的現代性”,不是受到“西方”沖擊意義上的外發次生型,而是在“早期近代”時期就自主發展起來了。如果由此引申開來,難免不會回到當年“資本主義萌芽”研究中的那個尷尬問題:為何這些萌芽均無成長為“資本主義”的參天大樹?與此類似,如此眾多的早期現代性又為何沒有催生出中國現代化?
除此之外,巴勒斯坦裔、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薩義德于1979年出版的《東方學》一書,于90年代中期被引介到國內。這不僅在學術層面上有力清算了“歐洲/西方中心主義”的影響,還在現實政治層面上抨擊了西方學術界關于東方知識與西方帝國霸權及殖民主義的緊密聯系。然而,這里的窘迫就在于,如果片面或過分強調“外來/本土”“西方/中國”“全球/在地”的二元對立,忽視各方間還有一些正面互動、共通及聯結,在一定程度上又導致了文化相對主義的大行其道。
關于歷史“主體性”的新探索
反觀上述那些研究范式的缺憾之處:在“革命—現代化”研究范式中,由于對先進生產力的尊崇,我們不乏對“歐洲”的仰視;在“大分流”研究范式中,由于認為中國古代有不少領先當時世界的亮點,我們對“歐洲”多少有些俯視;在“東方主義”的研究范式中,由于“自我/他者”的勢不兩立,有時難免對“歐洲”持無視態度,甚至不乏鄙視或敵視。然而,在這個充滿差異、沖突和歧見的年代,我們需要尋找和確立一種恰如其分、通情達理的本土歷史的“主體性”。
這里有一個可供討論的選項,是梁其姿于2008年提醒我們注意的“歐洲省級化”的概念。這也是南亞學者查克拉巴蒂于2000年出版的《將歐洲省級化:后殖民思想與歷史差異》一書的主旨。倘若將之援引到我們的相關研究中,梁先生認為會是一個極為有用的分析工具,能夠讓研究者們重新檢討近代中國面對“西化”過程中的主動性。她相信,與之相應的研究成果“或許更能顯示出歷史的多元與復雜性,成為‘近代性’更有效的參考指標”。
身為中國疾病、醫療史研究先行者的梁其姿,談及此概念時專指中國近代醫療衛生史研究;如果將之放到“中國視角的全球史”的研究框架中,我們還須對之做一些適用性闡釋。因為查克拉巴蒂在1992年提出此概念時,認為如果擁有普遍性的“歐洲中心主義”,勢必抹殺了所有歷史的具體時空;然而,現代性的發展卻更多是一部地方史,因為歐洲到了非西方社會,進入一個陌生甚至敵對的環境,只能隨機應變地成為各種各樣的碎片化、地方性的歷史演化,“就像可以被方便地派遣到帝國的各個省份那樣”。由此說來,我們將外來“歐洲”歷史化、在地化,就是要尋找所到之處和所在之處的具體“地址”。這也意味著,從近代中國在地“傳統”社會的自主性出發,或能有效地避免將外來“歐洲”抽象化、普適化和絕對化,并進而探討各種“現代性”之間的復雜和多元的互動關系。
往前追溯,日本學者濱下武志于1988年出版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清末海關財政與通商口岸市場圈》一書,可能更早推出了將那個抽象化了的外來“歐洲”在地歷史化的構想。在他看來,各國學者在研究包括亞洲在內的世界各地之近代問題時,應該從各個地域自身的歷史過程出發來研究其歷史本來的發展規律,而不應將各種外來影響或外來模式抽象化、總體化。以中國近代海關的變遷為例,他指出近代中國所導入的這項外部制度,基本上被包含在了中國的社會關系之內,實際得到采用的只是其中的機能性部分。當然,相對于濱下武志的具體研究,查克拉巴蒂的理論探索提供了更多將那個外來“歐洲”在地化、歷史化的研究思路,其中特別是關于開掘“少數人的歷史”的提法。他認為這可以推動史家更多聚焦于在地歷史的主體性、自主性和多元性,自然也能夠推動關于東方/西方“平等地位歷史”的研究。
查克拉巴蒂雖矢志建構“將人類團結一致”的歷史敘述,接下來卻沒有進一步的理論探討。史學家張廣達于1998年在《我和隋唐、中亞史研究》一文中,為我們“中國視角的全球史”研究尋找新的概念工具,提供一個頗具啟發性的思考線索。張先生借用蘇聯重要思想家巴赫金關于“大時間”和“小時間”的概念,指出各種東方、西方的歷史,都曾處在各自經歷的“小時間”之內,一個最重要的走向是不斷匯入到全球史意義上的人類“大時間”之中。
具體說來,巴赫金關于“大時間”和“小時間”的概念,是基于對“人類基本生存方式”為“對話”的認知。不同于自我隔絕、自我封閉意義的“自言自語”,或“自說自話”;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就像我們通過他人才能看清自己的外表,并由此顯現自己的深層底蘊。也即巴赫金所說:“我們給別人文化提出它自己提不出的新問題,我們在別人文化中尋求對我們這些問題的答案;于是別人文化給我們以回答,在我們面前展現出自己的新層面,新的深層涵義。”此后,俄國出生、后移民至墨西哥的塔蒂安娜于2005年也曾寫道:如果要問何謂巴赫金的“大時間”,可能會令你失望;不過,從其在拉美近40年講授及傳播其思想的感悟出發,她聲稱:“這是一種來自差異及為了差異的體驗。它當然是對話式的。”
毋庸贅述,幾乎所有研究對“差異”都十分關注。如果稍作比較,一般史家眼里的“差異”大概就是“差異”,而全球史家需要將之整合起來,或者說進行一種擁有更多面相、意涵的“對話”和“理解”。像糖、銀、鉆石、棉花、煙草、茶葉、瓷器等商品的近代流動,我們需要在更大的時空場景內考察它們是怎樣以及如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和這個世界。畢竟,那些棲身在偏遠角落之人,即使很少有購買和獲得的行為,與那些相距十萬八千里的“全球主義之人”可能也存在不可忽視的某種相關性或共通性。故“中國視角的全球史”的講述重點,是我們與其他文化、文明的連帶發展和共同命運。
同時,對于“中國視角的全球史”研究來說,對話和理解意味著將獲得更多探究普遍真理的可能性。正如阿明對“東方主義”的批評,他說:如果只承認“差異的權利”(文化和地區的差異)意義上的“人們”,否認普世意義上的“人類”,那么,其勢必聲稱只有歐洲人才能懂得歐洲、中國人才能懂得中國、基督徒才能懂得基督教、穆斯林才能懂得伊斯蘭教,從而導致清除“一部分人的歐洲中心論只能由另一部分人的顛倒的歐洲中心論來完成”。
倘若“中國視角的全球史”研究,真能在上述“對話”“差異”“理解”等環節上,講述各種能夠打動人心的相關歷史故事,那么,就可恰如其分地建構起諸多“小時間”與“大時間”的分享、互惠和共有。與之相應,我們自然還可繼續使用以往“革命—現代化”“大分流”及“東方主義”等研究范式中許多行之有效的概念:如“革命”“改良”“轉型”“在地”“交互”“分流”“文本”“話語”“權力”“認同”等。因為在巴赫金看來:“在大時間里沒有什么會失去其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