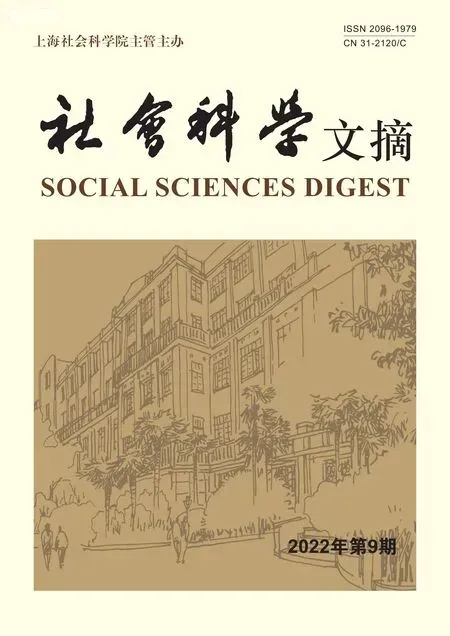現象學與中國哲學
——兼論中國現象學建構的可能性
文/蔡祥元
現象學是20世紀西方哲學一個重要的思想流派,尤其在人文精神方面有獨特貢獻。近二三十年來,現象學在中國大陸的譯介與研究不斷深入,與中國哲學之間的對話也在全方位展開,涉及形而上學、倫理學、美學、宗教哲學、科學哲學乃至文藝理論等領域。可以說,現象學與中國哲學的互動已經成為當前中國學界的一個“現象”。本文在相關討論的基礎上,對現象學與中國哲學的思想關系再做一些新的考量。在思想方法上,筆者將對現象學的“事情本身”進行提煉,表明它具有原初給予性、居間構成性以及直觀明見性三個基本特征,然后將它與中國哲學的工夫論做對比。接下來,結合中西哲學對話的歷史背景來突顯現象學與中國哲學的親緣關系,并借助學界有關中國哲學的現象學研究表明中國哲學的“事情本身”有某種哲理上的特質性。以此表明,我們有理由期待和展望,未來可能出現一種有別于德、法現象學,可以名之為“中國現象學”的思想流派。
什么是現象學
現象學的開創者是胡塞爾,廣義的現象學包括海德格爾、舍勒、伽達默爾、羅姆巴赫、薩特、梅洛·龐蒂、列維納斯、德里達等人的思想。現象學家各有其思想領域,他們以現象學方法為指引,圍繞意識現象、生存體驗、存在領會、倫理價值、知覺感受、文本闡釋等專題,打開了一個個獨特的思想視角。就現象學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思想方法。這個方法或態度通常被總結為“朝向事情本身”。要把握現象學的“事情本身”,首先需要將對待事物的日常態度和理論態度懸置起來,這就是現象學的懸擱判斷,也是現象學還原的第一步。
由于“事情本身”是通過現象學還原揭示出來的,如此獲得的“事情本身”首先具有原初給予性的特征。胡塞爾將它確定為“一切原則的原則”。不同現象學家關注不同的“事情”,但它們都具有這種“原初給予”的基本特征。舍勒稱之為“自身被給予性”,并認為它是現象學實事領域得以統一的共同性所在。海德格爾通過詞源學考察表明“現象”一詞在古希臘那里的原本含義是“顯示著自身的東西”,并據此將現象學的“現象”解讀為“就其自身顯示自身者”。此種原初給予性并不是通常意義上事物的直接顯現,它不同于現象主義、實證主義所號稱的那種只以眼前直接感知到的東西為實在。與它們相比,現象學所揭示的“事情本身”甚至具有某種先驗的、先天的特征。但是,現象學并不因此走向柏拉圖的先天理念論和康德的先驗論。此種“先天結構”,不同于先驗形式,它不是以使經驗現象得以可能的先驗條件的方式存在,而是經驗現象得以構造出自身的那個構造性活動本身。
為此我們把“事情本身”的第二個特點稱為居間構成性。西方傳統哲學一直以來受兩大對立的思想方式支配: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本質主義與相對主義等。現象學原則是要在哲學層面“解構”這些對立。當然,這不是對它們的簡單否定或拒斥,而是深入到對立雙方各自思想的根子處,然后再往前推進。由于現象學所揭示的“事情本身”總是處于這兩大對立的思想方式中間,因此具有“居間性”。現代西方哲學中具有此特征的哲學流派并不少,詹姆士的意識流、杜威的經驗自然主義、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叔本華和尼采的意志主義等。但是,他們主要只是描述了一種還未理論化的、處于主客對立之前的原本的“生活經驗”(生命沖動或生存意志),并把它作為世界現象的“根據”,而對此類“居間物”何以能夠成為世界現象的“根據”,這方面的展示整體而言還是“籠統”的,會成為某種單純的“先天論”。這就涉及現象學的“事情本身”的構成性特征,張祥龍稱之為現象學的“構成識度”。
“事情本身”的第三個特征是直觀明見性。現象學的直觀明見性不同于邏輯的自明性,后者是純形式化的、客觀化的。這涉及現象學與分析哲學、自然主義的區別。在對事情本身的考察方面,它們是當代西方哲學兩大主要的哲學流派,在思想方法以及在問題本身的考察方面都突破了傳統哲學的理路,都反對宏大敘事,而甘于“打零工”。但是,分析哲學和自然主義的推進,在我看來,有一種將“經驗”平面化、單一化的趨勢,正如科學將自然現象均等化為數理模型那樣。它們在分析問題的時候,也經常引入邏輯符號來進行“邏輯推演”。這一特征使其相比于現象學,看起來更有科學精神,也更加嚴密。而這種做法,在現象學文本中幾乎是不可能出現的。原因就在于現象學所打開的視野不是“平面的”,現象學理路地展開不是基于“概念”的邏輯推演。
“事情本身”上述三個基本特征之間充滿張力,要恰當把握現象學的“事情本身”并不容易。要把握現象學的“事情本身”需要某種工夫。我這里參考中國哲學,把這個特點稱之為現象學方法的工夫論特征。將現象學方法稱為“工夫”,不只是表明掌握現象學方法需要全身心參與,同時也是借助中國古代道論傳統中的工夫論來彰顯現象學“方法”與現象學的“事情本身”之間的內在關系。
現象學之于中國哲學
自近代中西文明碰撞以來,如何會通中西哲學是中國學人的頭等大事。清代的訓詁考據中斷了宋明哲學活潑的思想對話傳統,本身不能再產生出有生命力的思想體系。與此同時,西方文明的全方位“入侵”,從自然認知到社會制度各方面,從根本上改變了國人的“世界觀”。傳統觀念的思想構架在現代人看來缺少明見性,與主流的“世界觀”難以圓融。現代人做中國哲學,如果不滿足于“尋章摘句”,而希望在思想本身方面有所突破,那么融合、吸收西方哲學,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熊十力、馮友蘭、唐君毅、牟宗三等現代新儒家都深諳西方哲學。他們對儒家義理的重新闡釋,都參考、借鑒乃至融合了西方哲學的某些視角。他們因此對儒家義理有所新的發明。但是,整體而言,這些“發明”并不算成功。他們所倚重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康德、黑格爾等跟中國古代哲學的哲理差距甚遠,不能將中國哲學所具有的生存論關切充分展現出來。哪怕是現當代的生命哲學、意志主義、過程哲學等,它們盡管也注重生命體驗,但仍與中國哲學“貌合神離”,因為中國哲學不是滿足于單純的生命體驗,而是體驗其內部所具有的某種“超越性”價值。在這方面,只有牟宗三借助西方哲學而對中國哲學的義理有所推進。他的思想創新主要借助康德批判哲學,并因此找到了中西哲學傳統的“對接點”,但是,由于思想方法的限制,他并沒有把這個“對接點”打開。牟宗三、唐君毅都曾關注過現象學。唐君毅將胡塞爾的本質直觀的對象作為一種“純相”的世界,與柏拉圖哲學歸為一類,這個歸類并沒有看到胡塞爾與柏拉圖在思想方法上的差異。牟宗三從康德哲學的視角出發,對現象學進行過直接評判。如倪梁康所指出的,牟宗三對現象學的評價是“偏誤”的,他沒有看到,其“智性直觀”的理路在許多方面與現象學方法有相一致的地方,尤其是沒有看到,現象學方法跟人生哲學的緊密聯系。
對一種“先天”的東西的把握和展示如何不陷入空洞的概念思辨,正是現象學超出康德哲學乃至超出西方整個傳統哲學的得力之處。現象學“朝向事情本身”的思想方法,具有一種立足前概念、前反思的實際生活經驗來闡發精微洞見的思想旨趣。張祥龍把現象學方法的這個特點稱之為“熱思”,強調它具有不離開實際經驗的源發性、時機構成性的基本特征。現象學這種思想特點,相比于其他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思想傳統更為契合,后者同樣是一種不離人倫日常又不滯于人倫日常的思想經驗。
除了思想方法的契合以外,現象學所關注的“事情”本身很多地方與中國哲學也是相合的。比如,像倪梁康所指出的,胡塞爾對意識現象的分析跟佛教的唯識學和儒家的心性論有可能建立起緊密聯系。著眼于我們前面指出的廣義的現象學,那么,這種相合的主題有很多。例如,海德格爾著眼于人與世界的內在關聯來思考“人之為人”,相合于中國哲學的“天人合一”。舍勒對情感與價值關系的考察,相合于儒家在情感的發用中指點價值之根源的思想特征,“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梅洛·龐蒂有關身體主體性的揭示,與中國哲學“身心一如”的思想傳統遙相呼應。
雖然現象學與中國哲學存在親緣關系,但要真正從現象學視角出發研究中國哲學并不容易。很多時候這種解讀往往停留在從外部對中國哲學的義理扣上一個“現象學”的帽子,而對相關文本的闡釋依然停留在傳統哲學框架之中。哪怕將相關文本摘取出來與現象學文本進行直接比較,這也只是對現象學與中國哲學的比較研究,它們跟中國哲學與亞里士多德哲學、與黑格爾哲學乃至與實用主義等的比較研究,并無實質區分。對于此類比較研究的現狀,正如倪梁康與方向紅所評述的,還不是真正的“會通”。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中國古代哲理雖然也具有現象學的“雙非”特征,但它們只是“隱含”在文本之中。如何在古代文本中“剝離”出它所具有的現象學洞見,這需要現象學的“工夫”。這跟一般的現象學研究一樣,此種“洞見”不是任何意義上的現成存在物,它需要研究者進入文本空間以后進行“重構”。在中國古代文本中找到的現成的思想觀念,尤其是那些基本哲學觀念,大都已經積淀了太多的“想當然”,都不是現象學的。它們都是首先需要放在括弧里的“大概念”,可以說,都是現象學需要懸置的“自然態度”或“傳統觀點”的一部分。
中國哲學之于現象學
自胡塞爾開創現象學以來,現象學在歐洲大陸已經發展了一百多年,形成了一個波瀾壯闊的現象學運動,不僅出現了一大批追隨胡塞爾的思想大家,在存在論、認識論、倫理學、宗教學、美學、詮釋學等領域打開了新的視野,甚至成為一般的人文科學方法論。不過,新世紀以來,隨著伽達默爾、德里達等現象學大家的相繼離世,現象學也進入某種衰微狀態。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現象學方法本身有問題,而是說,它只是作為一種思想方法,在歐洲大陸的思想傳統中已經窮盡了它的可能性。
與歐洲大陸不同,現象學在中國哲學界整體上還處在引介階段。這幾年隨著胡塞爾全集(倪梁康主持)、海德格爾全集(孫周興主持)、伽達默爾全集(洪漢鼎主持)、舍勒全集(張任之主持)和列維納斯全集(朱剛主持)等現象學經典文集的系統翻譯與研究的展開,現象學在中國大陸的研究會出現一番新的勢頭。在中國現象學的研究方面,目前有兩個主要方面的突破:一個是張祥龍前后期的天道和孝道現象學;一個是耿寧和倪梁康的心性現象學。
張祥龍在其早期著作《海德格爾思想與中國天道》中,以海德格爾的思想為背景,吸取并借鑒其對存在的現象學展示,從時間性、境域性、構成性等維度出發,對中國古代的天道觀進行了現象學的闡釋。他所展示出來的天道,既具有現象學視野的基本特征,又具有中國哲學的特質,由此在德法現象學之外打開了新的現象學視野。之后,張祥龍轉向對儒家哲學的現象學研究,其代表性作品有《從現象學到孔夫子》《家與孝——從中西間視野看》和《儒家哲學史講演錄》。這些研究可以稱之為孝道現象學,它們主要圍繞親子之愛及其背后的意義生成機制而展開。在張祥龍眼里,這是儒家之所以為儒家的“心印”。孝道現象學對儒家哲理的重新闡發有別于新儒家直接從心性之體入手去接續宋明理學,而是彰顯了儒學一個更為古樸的維度。但它并不古老,因為它采取了現象學的視角,有別于學界對孝道文化采取的一般性的文獻疏證或義理研究。作者的這番“復古”不是為了回到過去,而是為了更好地面對未來。
耿寧與倪梁康的心性現象學研究,參考并借鑒胡塞爾意識結構的現象學分析,對唯識學和儒學中的心性結構進行了類似的現象學分析。相關的研究著作有:倪梁康的《心的秩序:一種現象學心學研究的可能性》《緣起與實相:唯識現象學十二講》等文章和論著,以及耿寧的《心的現象學》《人生第一等事:王陽明及其后學論“致良知”》。雖然倪梁康、耿寧主要參照胡塞爾的思想方式來研究唯識學、儒家心性之學,但他們由此展現出來的具有現象學意謂的心性結構與胡塞爾的意識結構有著根本的區別。耿寧從中國哲學視角出發向胡塞爾現象學提出三個基本問題來突顯兩者的區別。這些問題突顯出中國哲學語境下的心性現象學對胡塞爾意識現象學的超越。可以設想,就像海德格爾、舍勒做的那樣,心性現象學也將在諸多現象學領地中展現出自己獨有的“事情本身”。
此外,陳立勝從身體性維度出發對陽明心學的重新闡釋、張再林的中國古代身道研究、孫向晨有關家哲學的系統性建構也依托和借鑒了現象學的視角,柯小剛對書法和《詩經》的現象學闡釋與實踐、方向紅對中醫和《易經》的現象學研究、朱剛依托列維納斯展開的有關家的現象學研究、張任之依托舍勒對儒家心性與體知問題的現象學研究等,也都是在此思路下展開的。而王俊從羅姆巴赫的跨文化現象學視角出發,指出現象學內在地就有一個跨文化而生的維度。這一切都預示著現象學在中國大陸將有一個新的開端。